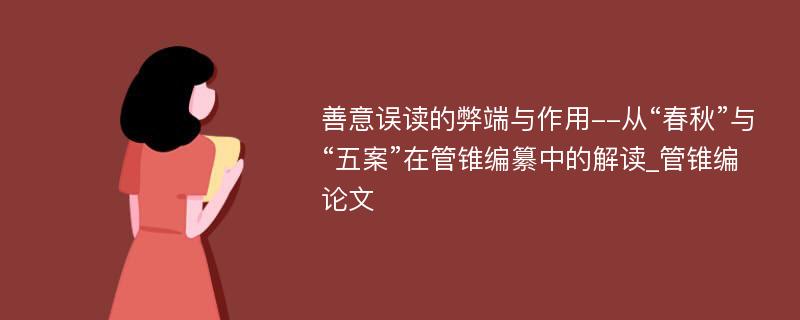
善意误读的弊与功——从《管锥编》对《春秋》“五例”的解读与阐发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误读论文,善意论文,春秋论文,管锥编论文,五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2)05-0013-07
晋代杜预在《春秋左传正义序》中提出《春秋》“五例”之说,钱钟书先生《管锥编》对其说解甚详,并对前人关于“春秋书法”之论作如下评骘:“古人论《春秋》者,多美其辞约义隐”,“春秋著作,其事繁剧”,“文不得不省,辞不得不约,势使然尔”,“古人不得不然,后人不识其所以然,乃视为当然,又从而为之词。于是《春秋》书法遂成史家模楷,而言史笔几与言诗笔莫辨”。钱先生认为,前人关于“春秋书法”之论,实为误读;而他自己所作出的论断:“窃谓五者乃古人作史时心向神往之模楷,殚精竭力,以求或合者也”,“五例之一、二、三、四示载笔之体,而其五示载笔之用”,以及说刘知几《史通·叙事》即“微”、“晦”二例之发挥,亦即《文心雕龙·隐秀》之所谓“隐”,也给我们留下了讨论商榷的余地。[1](P161-164)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建设,从传统资源汲取营养,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是对前人常用的术语的本义,对其概念、范畴的内涵,先有客观如实的了解探究,并梳理其演化历程,辨别各种误读,而不宜以今例古,牵古就今。本文拟以对“春秋书法”的释解和应用为例,做一最初步之尝试。
“五例”说所称道的“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劝善而惩恶”,确实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史上占有相当之位置,在文学理论史上更有深远的影响,由之导出了中国文论民族特色的重要方面,而各家对此说之诠解差异甚大,其中包含大量的误读。古代的误读多半由于对《春秋》景仰推崇太过,现代的误读不少则是由于忽略了对于“春秋书法”的“微”、“婉”在齐梁乃至唐代以后的新解,与春秋时期本义的质的演变。今天,要如实理解此说的理论蕴含,评议它在历史上和在当今的作用,似宜首先对其发生和演变的过程作一综合探讨分析,辨析其本义与引申、推演之论的巨大差别,并从各种诠说产生的历史环境,以理解之同情,衡议其得失,即使对那些远离本义的引申发挥之说,其价值亦当客观地予以估量。
“五例”一语出于杜预,“五例”说的内容却非杜预所自创,而是早见于《左传》成公十四年和昭公三十一年的本文。“五例”说中提出的论断最初既然发生在春秋时期,它的本义,只能在春秋时期史学、文学和整个社会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上去了解。所以,我们需要先来细读《左传》与“五例”之说直接相关的两处原文。
《左传·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孰能修之!’”
昭公三十一年:“《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
这两处文字被许多人征引,然而,众多论者没有深究的是,在这两处,“微而显,志而晦”等等并不是泛指《春秋》的文笔,而都是明确地特指《春秋》中的“称”而言。那么,什么是“称”呢?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在两处分别注释说:“称,言也,说也。此谓《春秋》之用词造句。”“《晋语》八韦注:‘称,述也。’谓叙述史事。”这种训释和《左传》两处上下文并不很吻合,不能帮助读者准确领会言语主体命意的指向。成公十四年说的是,《春秋》记载,同一个人受命到齐国为鲁成公迎娶夫人,先称呼为“叔孙侨如”,后称呼为“侨如”,前后对他用了两种“称”。“君子”认为,两个“称”的区别,显示了《春秋》作者的深心,显示了《春秋》的谨严、高明。“微而显”等等,指的就是《春秋》作者对这类“称”的精心选择。为什么对做同一件事的同一个人前后的“称”有两种呢?《左传》的解释是,称族名“叔孙”,表示对国君的尊重,因为他是奉国君的命令;后来但称其名而不称族名,则是因为要表示对先君宣公的夫人穆姜的尊重,她是新国君夫人的长辈,其时还在世。昭公三十一年《春秋》记载“黑肱以滥来奔”,为什么《春秋》要称举黑肱的名字呢?《左传》解释:“贱而书名,重地故也。”这是对土地疆域的看重,更重要的,是为了“惩肆而去贪”,警戒后人。黑肱之类人本来是“求食而已,不求其名”,结果却“欲盖而名彰”。在这里,《左传》中的许多地方,“称”的意思都是称呼、命名或称举其名,并不是指一般用词造句,不是指叙述史事。隐公元年《春秋》记“郑伯克段于鄢”,《左传》解释:“称郑伯,讥失教也。”隐公七年《春秋》记“滕侯卒”,《左传》解释说:“不书名,未同盟也。凡诸侯同盟,于是称名。”除了称人名,还有对事件的称说、命名。桓公十年《春秋》记“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三国挑衅鲁国,鲁国不愿与之交锋,这四个国家本是联合帮助齐国抵御北戎,《左传》解释发生纠纷的起因是“鲁以周班后郑,郑人怒,请师于齐,齐人以卫师助之,故不称侵伐”,《春秋》“称”这次军事行动为“战”。凡这类地方,“称”要解决的都是如何命名的问题,而不是如何叙述、如何描写的问题。
《春秋》如此重视“称”,是因为孔子非常重视“名”。他认为,为政的第一要务“必也正名乎”。《论语集解义疏》引马融:“正名者,正百事之名也。”正名,就是给人和事以正确的“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所以,在《春秋》里,对人和事怎样“称”,是至关重要的。《春秋》记述简略,不讲文采,但它的“称”精心推究,每每存有深意。所以,对于“五例”之说,把它理解为叙述历史的范例,甚至把它理解为文学的叙述和描写范例,则确如《管锥编》所言,“《春秋》实不足语此”;而按照“称”的本义,从“正名”去理解,则《春秋》又确实树立了典范。历来人们常说《春秋》一字以褒贬,就是这个缘故。
《春秋》只是记事,它没有“叙述”历史,只是记下历史事件的名目而不展开叙述事件的过程。这部书的最高目的,就是给历史人物和事件定名,用定名来定性,区分忠奸善恶,达到劝善惩恶的目的。因此,“称”就是《春秋》的著述者要做的基本的、关键的工作,也可以说,它所做的就是命名的工作。
确认了“称”是称名,则“五例”的涵义也要据此来辨析。对“称”理解不正确,对五例的各个词语和各例内容也难以正确理解。把“称”解释为叙述史事,必然使前四例被解释得彼此错叠,如《管锥编》所说,“一意重申,骈枝叠架”。五例不是平列,最后一例是讲根本目的,前四例讲为达到目的的方式方法。如何命名,根据在于惩恶扬善的原则,判别善与恶,根据的是礼。《管锥编》说:“‘微’、‘晦’、‘不汙’,意义临近,犹‘显’、‘志’、‘成章’、‘尽’也。‘微’之与‘显’,‘志’之与‘晦’,‘婉’之与‘成章’,均相反以相成,不同而能和。”这些说法,需要再具体细致地分析。四句都用“而”连接,两端的意思相反,属于所谓连词逆接;四句中的一和二、三和四,即“微而显”与“志而晦”,“婉而成章”与“尽而不汙”,各有其独立含义,彼此不重复,并且也是相反相成。
日本《左传》学家竹添光鸿说,“微者,文字希少之谓也”,“一字而义著”,“一字二字而义则广涉”[2](P1071)。把“微”说成文字稀少,十分牵强,因为人所共知,“春秋书法”的要义不是以少字替代多字。把人物称为叔孙侨如,比单称侨如多了两个字,那样才能微而显,显出对国君的尊重。至于“一字二字而义则广涉”,正证明“称”讲究的不是叙述,而是正名。与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配套的沈玉成的《左传译文》,把“微而显”译为“用词细密而意义显明”,“记载隐微而意义显著”,[3](P233,513)这与叔孙侨如、黑肱等等许多例句对照,也不能相合,那些文字都并不是细密、隐微。还有很多论者把“微”理解为微妙、精微,其实,就“称”而言,无所谓微妙、精微。“微”在这里是隐匿、遮掩的意思。《左传·哀公十六年》:“白公奔山而缢,其徒微之。”杜预注:“微,匿也。”晦,是隐藏、掩蔽的意思。《易·明夷》:“利艰貞,晦其明也。”其卦象为日入地中,隐晦光明。“微”也就是“不书”,“志”是“书”。微而显,是说不书而能显露;志而晦,是说书而能隐晦。
婉,是婉语;尽,是直言。章,是典章制度。《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王章也”,又哀公三年:“旧章不可亡也”,“章”都是指典章制度。汙,是污秽,引申为加以恶名。《左传·宣公十五年》:“川泽纳汙,山薮藏疾。”《楚辞·九辩》:“窃不自聊而愿忠兮,或黕点而汙之。”王逸注:“谗人诬谤,被以恶名也。”婉而成章是说婉语称名而符合礼制。尽而不汙,是说直言称名而不构成诬谤。前者如僖公十七年《春秋》记载“公至自会”,实际不是两方会见,而是僖公被齐国扣留而后释放。《左传》解释说:“书曰‘至自会’,犹有诸侯之事,且讳之也。”把扣留说成是“会”,是婉语,为的是符合礼制。又如僖公二十八年《春秋》记载,“天王狩于河阳”,实际是晋文公召周襄王到河阳去。《左传》说明:“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清代方苞《春秋直解》说:“其以‘狩’书,属辞之体然耳……册书之体,则舍‘狩’无以为辞。”“属辞之体”就是“春秋书法”。后者如桓公十五年《春秋》记载“天王使家父来求车”,直言“求”,《左传》指出“非礼也,诸侯不贡车服”,周桓王违背了礼制,如实记载不是诬谤。
总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说的不是文学修辞、文学描写或文学叙事,说的不是一般的用词造句,它说的是《春秋》如何称名,如何称人物之名、事件之名,以引导世人和后人维护礼制秩序,对违背礼制秩序提出批评和谴责。这是“五例”在春秋时期的本义。
《春秋》的语言极为简约。为什么简约?《管锥编》引前人之言,强调了“古人无纸,汗青刻简,为力不易”,简约是“不得不然”。这固然有些道理,但不足以为充分的证明。《尚书》里保存的文献早于《春秋》,其文字与《春秋》比,远非俭省。汉代的《尚书璇玑钤》说:“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其说不可尽信,但孔子可以看到的前代历史文献远多于《尚书》里现存的,则应无疑问。那些文献都是在无纸时代刻写的,文字不像《春秋》那样简约。《管锥编》提到而未具论的还有“寡辞远祸”之说,认为简约是避免因文字而受到迫害,那也是不足以服人的。《春秋》襄公二十五年记“齐崔杼弑其君光”,《左传》更详记齐太史书其事,所用不过五个字,即为崔杼所杀,其弟前仆后继,这成为历代良史的典范,直到文天祥《正气歌》还要举出“在齐太史简”。寡辞也可能贾祸,繁辞也可能毫不犯忌。在春秋时代,秉笔直书、为尽良史之责不惜生命的史官并不罕见。足见,在那个时代,寡辞与远祸没有必然关系。
这里的症结在于,在《春秋》的作者和《春秋》之前的史官的心目中,记载历史事件第一要紧的不是如何反映真相,而是如何有利于劝善惩恶。《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宣公二年《春秋》记载“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历史事件的真相是赵穿杀晋灵公,可是太史董狐却记载为“赵盾弑其君”。孔子赞扬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显然,在孔子看来,这也属于“尽而不汙”,也就是直笔而无诬谤。为了劝善惩恶的目的,对于晋灵公被杀的过程就不能够周详地记载,只能简约地用短短的一句话定谳。按照《左传》的叙述,赵盾是一个忠于职守、很有人格魅力的大臣,晋灵公一再加害于他,使他无法在朝中立足,只好出逃。后来的学者聚讼纷纭,甚至有人说《左传》的详细记载不可靠。刘知几《史通·惑经》则不满于对孔子的“虚美”,他指出:“此则春秋之世有识之士莫不微婉其辞,隐晦其说,斯盖当时之恒事,习俗所常行。”孔子不会在意说《春秋》若干记载不尽合史实,《春秋》隐匿了晋灵公被杀的实际情况,它要显示的是臣下必须无条件地忠于国君的政治伦理准则。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代的史官与后现代历史学家颇为相通。海登·怀特在《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的前言中说:“许多现代历史学家认为,叙事话语远不是用来再现历史事件和过程的中性媒介,而恰恰是填充关于实在的神话观点的材料,是一种概念或伪概念的‘内容’。”[4](P1)这里要讨论的不是《春秋》如此记事的对或错,而是要由此证明,春秋时代的史官,不在意史实的精确性,也不在意文辞的生动、形象性,他们追求的“微”、“婉”,与后世深谙文学特性的文人追求的微婉是两回事。
无论如何,文约意深,逐渐成为古代著述者心中的一种准则,文人们努力去追求,而对“微”、“婉”的涵义各自赋予它新的理解。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评价《离骚》说:“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这和他在《孔子世家》中说《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完全一致。可见,司马迁认为,“文约辞微”不仅是《春秋》树立的标尺,也是优秀的诗歌、优秀的文学作品应有的品格;司马迁让诗笔向史笔看齐,开了把“文约辞微”应用到文学领域的先河。本来,《春秋》的文辞偏于艰深,宋代富弼说过:《春秋》“隐奥微婉,使后人传之、注之尚未能通。疏之又疏之,尚未能尽,以之为说、为解、为训释、为议论,经千余年而学者至今终不能贯彻晓了”[5](P163)。而唐人却多美称《春秋》之“微婉”,司马贞《史记索隐》说:“《春秋》有微婉之辞。”李翰《殷太师比干碑》说:“俾后之人优柔而自得焉,盖《春秋》微婉之义也。”李白《泽畔吟序》说:“至于微而彰,婉而丽,悲不自我,兴成他人,岂不云怨者之流乎?”白居易《哭刘尚书梦得》说:“杯酒英雄君与操,文章微婉我知丘。”唐人以微婉自诩,并以之为文学的最高品位。宋代人把微婉用于解说具体作品的修辞,《彦周诗话》说:“东坡作《妙喜师写御容》诗,美甚美矣,然不若《丹青引》云‘将军下笔开生面’,又云‘褒公鄂公毛发动,英姿飒爽來酣战’。后说画玉花骢马而曰‘至尊含笑催赐金,圉人太仆皆惆悵’,此语微而显,《春秋》法也。”杨万里《诚斋诗话》:“《左氏传》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此《诗》与《春秋》纪事之妙也。……近世陈克咏李伯时画《宁王进史图》云:‘汗简不知天上事,至尊新纳寿王妃’,是得谓为微、为晦、为婉、为不汙秽乎?惟李义山云:‘侍宴归来宫漏永,薛王沈醉寿王醒’,可谓微、婉、显、晦、尽而不汙矣。”直到清代,《四库总目提要》评述宋代汪元量的作品也说,“其诗多慷慨悲歌,有故宫离黍之感,于宋末诸事皆可据以征信,……微而显、隐而彰、哀而不怨”。这众多的人把后世对文学特性的认识放进对春秋书法的理解,又把微言大义搬进文学阐释里,往往混淆诗笔与史笔的差异。事实上,只有在对于文学审美特性的自觉,在六朝以后,“微婉”才被赋予新义,才有可能成为文学理论的范畴。这个转变是由刘勰完成的。刘勰《文心雕龙》把五例之说,把“春秋书法”,袭其辞而改其义,移用到文学理论领域,建立全新的话语体系。他是经由对“微”、“婉”在春秋时代原义的误读和创建性的阐释来实现这一转换。
《春秋》之所以“微”、“婉”,之所以文字简约,除了书写技术条件的限制之外,另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孔子本人以及当时的史官,都有强烈的使命感,要使史书成为当世和后世君主为政的教科书,成为士大夫立身处世的教科书。这就要求史书的语句具有对多种情况的适用性,给后人以开阔的释解空间。历史的记述,越是简略,后来的阐释者越容易赋予多种涵义;越是详尽,阐释者越难添加新的内涵。在这一点上,《春秋》和《周易》异曲而同工。本来,当时的史官就与占卜有密切联系,史官往往同时也是占卜之官,记录史事与解说天象或解说卦象可以密切相关,其职业语言风格相互影响而彼此有很多相近之处。《周易·系辞下》说:“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这些话,与“五例”颇有相互交合之处,用之于《春秋》也大体适合。《周易》和《春秋》各自建立起一套符号系统,在这两套系统里,符号和编码方式之“微”、“婉”,都不是为了获得和强化文学性,而是为了暗示“天意”、昭示纲常,为了使后人从这两套符号系统可以寻求诸多千变万化的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
《文心雕龙》要建立一个有体系的文论,为了实现这一前无古人的目标,刘勰认为,首先必须征于圣、宗于经。从圣人那里,从经书中间,他“征”得什么、“宗”到什么呢?他在“论文必征于圣”之后紧接着说,他所“征”、所“宗”的是“辨物正言”和“辞尚体要”。这样说,符合圣的原意、经的原貌,但还未能回应齐梁时期文学观念进展的需要。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释《征圣》篇“精义曲隐”句时,不能不确认,“《易》理邃微,自不能如《诗》、《书》之明菿,《春秋》简约,自不能如传记之周详……不然,视《易》为卜筮之庾辞,谓《春秋》为断烂之朝报,惑经疑孔之弊,滋多于是矣”。所以,还要让魏晋以下逐渐意识到的文学需有的丰赡、华美,与《春秋》、《周易》的简约、邃微,人工地建立承传关系。于是,《征圣》篇笔锋一转,说:“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可是,圣人经典,《春秋》和《周易》,怎么是“衔华”呢?这就是刘勰的一个有意的、善意的误读。黄侃《札记》释“衔华佩实”说:“此彦和《征圣》篇之本意。……文多者固孔子所讥,奈之何后人欲去其华辞而专崇朴陋哉?”[6](P11-12)《春秋》原本无“华”可言,“五例”原非文学修饰,不是后人要去其华辞,而是刘勰要美之为华辞。刘勰把它们连接起来,他也不是没有论证的依据,他机智地抓住了《春秋》、《周易》符号系统与文学符号系统的一个深层的极其重要的相关性,把《春秋》、《周易》的复义性、多解性,嫁接到文学理论,提出了“隐”这一重要的古典美学范畴,在中国文论史上第一次深入细致地论述了文学的复义性、多解性,这是他的一大功劳。
《隐秀》篇的立论依据,在《征圣》、《宗经》两篇已经预先提示。《征圣》篇说:“四象精义以曲隐,五例微辞以婉晦,此隐义以藏用也。”《宗经》篇说:“自夫子删述,而大宝咸耀。于是《易》张《十翼》……《春秋》五例,义既极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四象”指的是《周易·系辞上》所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五例”就是杜预所说《春秋》五例。《春秋》微而显,《周易》微显阐幽,文学则需要精微幽隐,各自运用自己的符号,运用自己的编码方式,力图传达多重的、丰富的,甚至是难以穷尽的涵义,在这一点上,三套符号系统确实具有共通性。《隐秀》篇说:“故知繁略殊形,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会适。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刘勰以《周易》、《春秋》为师,把《周易》的卜辞之隐和《春秋》的一字褒贬之隐接过来,提出文学创作中的隐,实现了一个重大的跨领域的理论转换。
“隐”的最重要的特性是复意和重旨。“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隐以复意为工”。《周易》的卦象和卦辞都是有复义、重旨的,《春秋》在《公羊》、《谷梁》、《左传》的不同阐释中,显示了多重意旨。《春秋》的复意、重旨,是语句的一望可知的涵义与深层的微言大义两重,例如“称郑伯”是表示“讥失教”,“克”是表示“如二君”。这类微言大义,不经“三传”作者等后人解说,读者无法了解。《周易》的复意、重旨,是以卦辞解说卦象,比如乾卦第一“初九,潜龙勿用”,“初”是卦的自下而上的第一爻,“九”是指这是阳爻;阳爻在最下面,表示龙潜藏深水,蓄势待发。“既济”卦:“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孔颖达解释:“势既衰弱,君子处之能建功立德,故兴而复之;小人居之日就危乱,必丧邦也。”凡此之类,对于不掌握《周易》符号编码规则的人,无法从卦象得出卦辞的意义,也难以从卦辞引出更多的涵义,找到自己问题的答案。文学作品的复意、重旨,则是有语言和文学素养的读者,经过思索体会,都可以感受的。《隐秀》篇列举了古诗十九首、曹植的《野田黄雀行》、阮籍的《咏怀》,等等,“调远旨深”,都有从表层到深层的多重涵义,这些涵义,读者从文本可以慢慢体会出来。《周易》、《春秋》的复意、重旨,一旦解开,就稳定、凝固;文学作品的复意、重旨具有自身的生长力,“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余味曲包”是文学符号系统特有的效果。因此,《隐秀》篇说的复意、重旨,与《春秋》的微而显、《周易》的微显阐幽是不同的符号体系的编码规律,性质上有着原则的区别。
词是史书和文学作品最小的意义单位。上面说到,《春秋》之隐,多于一字二字见之,文学作品的隐,却不是单个词语的隐晦。刘勰反对在文学作品里用生僻艰奥的词语,《练字》篇说:“及魏代缀藻,则字有常检,追观汉作,翻成阻奥。故陈思称扬、马之作,趣幽旨深,读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岂直才悬,抑亦字隐。自晋来用字,率从简易,时并习易,人谁取难?今一字诡异,则群句震惊;三人弗识,则将成字妖矣。后世所同晓者,虽难斯易;时所共废,虽易斯难:趣舍之间,不可不察。”所以,隐,不在于识字、解词之难,而在于词句背后的深层意味。
用《周易》进行占卜,要观象系辞,以卦象、爻象联系到卦辞作出解释,但在具体操作中要使对卦象、爻象以及卦辞的阐发切合每一实际具体情况,是不可能的。于是,解卦者采用多种取象方法。刘勰对《周易》和易学有深入研究[7],他精心选择多种取象方法中的“互体”,借之生发出新意。《隐秀》篇反复讲到互体:“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蕴珠玉也。”“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辞生互体,有似变爻”。什么是互体,刘勰为何如此看重互体,易学里的互体和文学上的“隐”怎么会发生联系呢?互体是易学术语,指的是将一卦的六爻重新组合,主要是将中间的四爻重新组合,产生出新的卦;阴爻、阳爻的组合变化就叫作爻变或变爻。用互体解说《周易》占卜得到的卦象,渊源很远。《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记成周的史官用《周易》为陈厉公占卜,由“观”卦变到“否”卦,杜预认为卜者解说用的就是互体。杜预注释这个地方时指出:“《易》之为书,六爻皆有变象,又有互体,圣人随其义而论之。”孔颖达疏:“二至四、三至五两体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谓之互体。圣人随其义而论之,或取互体,言其取义为无常也。”①《周易》的卦,由阴阳二爻排列组合而成。阴阳两爻是两个基本符号,它们分别是两短画或一长画。画本身还不是爻,只有在组合成了卦,作为卦的构成元素,画才成为了爻,才有了象征的意义。每个卦里的每一爻,各有其象征意义,整个卦又有其象征意义。爻的涵义决定于它在卦里的位置,反过来说,爻的位置变化必定带来卦的涵义的变化。这和语词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作用非常相似。一篇文学作品有许多句子,每个句子由若干词语组成。文学作品里词语的含义只能在具体语境中去理解。例如,《春秋》里“郑伯克段于鄢”一句,“段”、“克”、“郑伯”三个很普通的词,放进这个句子里,《左传》认为,它们就都具有了很深刻的含义。一个词语在句子里位置的变动,往往也会使得句子的含义发生变化,有时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就是“辞生互体,有似变爻”。“秘响旁通”是讲词句变化的效果,“旁通”出于《周易》乾卦卦辞“六爻发挥,旁通情也”,孔颖达解释:“‘六爻发挥旁通情’者,发谓发越也,挥谓挥散也,言六爻发越挥散,旁通万物之情也。”朱熹《周易本义》解“旁通”谓“犹言曲尽”,旁通的意思是普遍通达,说的是符号具有广泛的表意适用性。
刘勰借用互体、变爻,强调符号的构成要素与符号整体的不可分割。单独一个词,无所谓诗意、文意,它还不是文学符号,只有经过作家把它与其他词语组合,成为文学作品的构成要素,它才获得了文学意义。接受者、阐释者“取义无常”,不再局限于词的词典上的含义,而是在文学作品的语句、篇章中,随其义而论之,领会到其复意、重旨,旁通多种境象,就可以体会到韵外之致、味外之旨。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里说:“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他只肯定三套符号系统的共同性,而不关心文学符号的特殊性。在这种思想背景下,汉儒阐释《诗》和阐释《周易》、《春秋》运用同样的方法。他们的这种阐释方式成为传统,对中国文学批评产生了消极影响。《毛诗》解释周代民歌,“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葛覃》,后妃之本也”;“《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则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国无鳏民也”……他们就这样在诗歌里寻找微言大义。所以,胡适说:“汉儒解经之谬,未有如诗笺之甚者矣。……汉儒寻章摘句,天趣尽湮,安可言诗?而数千年来,率因其说,坐令千古至文,尽成糟粕,可不痛哉?”[8](P11)忽略古代文学理论中的“隐蔚”与春秋书法中“五例”的区别的弊端,也就是以非审美的心态,用破译密码办法,穿凿附会,把文学作品的内涵归结为某种政治的道德的教条。追溯源头,乃在对春秋书法的误读、过度阐释和扩张应用。
总之,理解春秋书法,理解五例,应该回到历史语境,先确认其本义,对于后世的解读,则应将董仲舒等人的以“天意”为依归寻求微言大义的路径与刘勰等人的向审美理论的转换加以区分,客观评价其对于文学有益和有碍的两个方面。
注释:
①孔疏原文传本《春秋左传正义》此处漏“无”字,引文据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
标签:管锥编论文; 易经论文; 儒家论文; 周易八卦论文; 春秋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孔子论文; 国学论文; 左传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