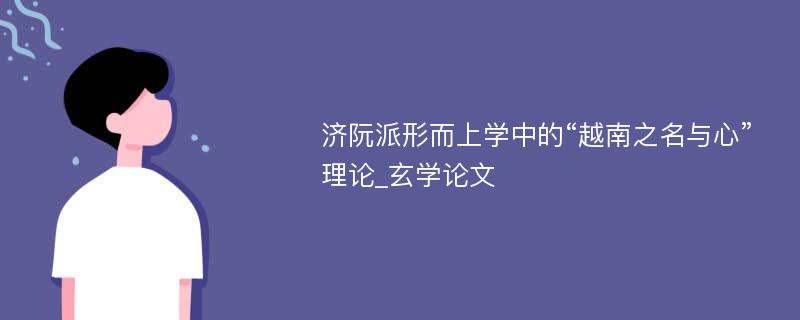
嵇阮派玄学的“越名任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玄学论文,嵇阮派论文,越名任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名教”即名分之教。能够规定和用来规定上下尊卑等级名分的是儒家的礼,所以,名教又称礼教,名教、礼教是一回事。阮籍前期信奉儒学,他的《乐论》是一篇论述儒家用音乐来“移风易俗”的文章。在文章开头,他以“刘子问”为名表明了他当时对“礼”的作用的看法:“孔子云:‘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夫礼者,男女之所以别,父子之所以成,君臣之所以立,百姓之所以平也;为政之具靡先于此,故安上治民莫先于礼也。”(陈伯君:《阮籍集校释》,中华书局,1987年,第77页)儒生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他们所谓政治比现代人所谓政治含义更广。现代人将国家与社会分离开来,政治是管理国家,社会包含了国家,但社会的许多领域是非官方的、不属于政治范围的。而儒生们却以为国家(“国”)就是社会(“天下”),治国与平天下是一回事。阮籍早年服膺儒学,自然继承了这一立场。“礼”是首要的“为政之具”即是说礼是最重要的政治工具。礼不仅可以立君臣、平百姓,而且可以成父子、别男女。这就是说,礼通过它的一整套严格细致的尊卑等级名分规定,不仅使统治阶层(君臣)内部关系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外部关系秩序化,而且使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诸多非官方的关系秩序化,因此它不仅是所谓政治的首要工具,更是所谓社会治理的首要工具,它使整个社会的产生、形成、延续、发展成为可能。这一点,《荀子·礼论》篇、《礼记》一书早有系统全面的论述,阮籍并未对此增加任何东西。礼对儒家而言是“人伦之具”,有礼与否是区别人与动物的主要标志(孟子有“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之说),因而,礼实际上是文明化的工具。礼教即礼的教化,就是用礼来教育感化全社会的成员,使他们成为文明社会中的一员。阮籍本有“济世志”,早年推崇礼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他从社会产生、维护、延续、发展的角度充分肯定礼乐教化的功能。
嵇康《声无哀乐论》虽然主张声音不包含哀乐之类情感,由此否定有声之乐的“移风易俗”作用,但他又认为“无声之乐,民之父母也”(《嵇康集校注》,戴明扬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223 页),无声之乐存于人心中而非乐声中,它具有移风易俗作用。嵇康在此与乐一起也肯定礼的作用,“夫音声和比,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之不可放,故抑其所遁,知欲之不可绝,故顺其所自。为可奉之礼,制可导之乐。……将观是容也,必崇此礼。……于是言语之节,声音之度,揖让之义,动止之数,进退相须,共为一体。君臣用之于朝,庶士用之于家。”(同上书,第223—225页)《声无哀乐论》虽有明显的重道倾向,但它大概系嵇康早年作品,其中并无贬斥礼教言论,反而与阮籍一样非常重视礼乐教化对社会文明化的关键性作用。
但是,在阮籍《达庄论》、《大人先生传》、《与伏义书》,嵇康的《释私论》、《难自然好学论》、《与山巨源绝交书》等文章中,礼教却成了二人猛烈攻击的对象。在《大人先生传》中,阮籍以不无讥讽的笔调刻画了一幅当时礼法之士的图像,由于言词并不深奥,不妨摘录如下:
“或遗大人先生书曰:‘天下之贵,莫贵于君子: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则磐折,拱若抱鼓,动静有节,趋步商羽,进退周旋咸有规矩,心若怀冰,战战栗栗,束身修行,日慎一日,择地而行,唯恐遗失,诵周孔之遗训,叹唐虞之道德,唯法是修,唯理是克,手执珪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阮籍集校注》,第163页)
他借“大人先生”之口把这种礼法之士比作藏身于裤裆里的虱子,它们“逃乎深缝,匿夫坏絮”,自以为找到了一个安全可靠的好地方;“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找到了进退从容的好方法;饿了就咬人,自以为获得了数不胜数的食物。但一遇大火,城邑被焚,虱子们死在裤裆之中而无法脱逃。“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同上书,第165—166页)
嵇康论及礼法和自己之反礼法时显得平和含蓄一些。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他说自己自幼由于母兄骄惯,养成疏懒习气,长大以后再也不能接受礼法的拘束了。本来就“纵逸”、“傲散”,“又读老、庄,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嵇康集校注》,第117—118页)。对山涛举荐自己做官,嵇康称:“又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同上书,第122页)极言自己不能遵守礼法,勉强为之,必遭祸害。 他所谓“甚不可者二”最能表现他的态度:“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同上书,第123 页)前一“甚不可”“非汤武而薄周孔”即“越名教”,后一“甚不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即“任自然”,这种“越名任心”(注:“越名任心”语出嵇康《释私论》:“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嵇康集校注》,第234页))者当然不能做礼法之士了。 嵇康在《难自然好学论》中也直接表达了同样的摒弃礼法的意思。
二
既然嵇阮二人早年对儒家礼教的社会文明化作用有过清楚的认识和推崇,那么,他们后来为什么毅然决然地弃儒入道,力斥礼教,鄙视礼法之士,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呢?人们已经从阮籍和嵇康个人的家庭出身、所属政治集团及其自身利益关系、个人经历等方面对此进行过解释。人们都同意戴逵“竹林之为放,有疾而颦者也”(《晋书·戴逵传》,《晋书》卷九十四)的说法,也赞成戴氏,嵇阮等竹林名士与王澄等元康名士不同之处在于有“所以为达”。(《世说·任诞》,第13条注)但嵇阮之“疾”、嵇阮之“所以为达”究竟何在呢?
在这里,我们不打算去联系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嵇阮二人的身世,而只从他们留下的文字中去探究一下这个问题。嵇阮反对礼教的原因之一是他们认为礼法在当时已经成了追名逐利的工具,也就是说,他反对的是礼法在当时的蜕变形态。阮籍《大人先生传》“或遗大人先生书”接着前引对礼法之士形象的刻画说:“(君子)少称乡闾,长闻邦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故挟金玉,垂文组,享尊位,取茅土,扬声名于后世,齐功德于往古;……”(《阮籍集校注》,第163—164页)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至嵇阮所处时代,以礼法修身,扬名乡闾和邦国,进而因名声入仕,“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享受荣华富贵,建功立业,名载史册,传之不朽,这种用礼法谋取功名利禄的途径成了“古今不易之美行”。这也可证之于《伏义与阮籍书》。在信中,伏义称“建立功勋者,必以圣贤为本;乐真养性者,必以荣名为主”为百代不易的为人大纲,就好象大道一样,人们之间有跑得快慢的差别但都在一条路上奔跑,声称:“贵德保身,非礼不成,伏礼之矩,非勤不辨”(同上书,第73页)。阮籍对此进行了猛烈抨击,指责那些“君子”“尊贤以相高,竞能以相尚,争势以相君,宠贵以相加,驱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并不是为了“养百姓”;揭露他们由于有这种无穷无尽的追名逐利私心存在而“惧民之知其然,故重赏以喜之,严刑以威之”,只可惜“财匮而赏不供,刑尽而罚不行”,终于招致“亡国戮君溃败之祸”(同上书,第170页)。在《达庄论》中, 阮籍谴责名教建立以后弄得天下大乱:“故自然之理不得作,天地不泰而日月争随,朝夕失期而昼夜无分,竞逐趋利,舛倚横驰,父子不合,君臣乖离。”(同上书,第145 页)以名利为目标的名教不再是自然和社会秩序的维持者,反而成了破坏和毁灭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东西。阮籍总结说:“是以名利之途开,则忠信之诚薄;是非之辞著,则醇厚之情烁也。”(同上书,第146页)
本来,按儒家创始人的本意及儒家的理想,礼是教化之具,是导引所有的人脱离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的首要工具,礼乐教化即是使人文明化。阮籍和嵇康早年也不同程度地理解和怀抱这种理想。但是,由于他们处身其中的险恶政治社会的触发,他们很快发现了礼和礼教在现实社会中的真正作用,与儒生们所梦想的礼的目的性地位相反,汉武帝以来的礼实际上经常处于手段性的地位:对社会而言,它成了巩固和延续一家一姓的江山社稷的私人工具;对个人而言,它成了获取君主家臣地位以享受荣华富贵的工具。利益成了它服务的最终对象,严格说来已部分丧失了抱有理想的儒生们赋予它的社会文明化功能。礼由目的性的礼向工具性的礼的蜕变,虽然满足了现实社会的需要,但却从根本上失去了其本身的内在合理性,不能满足嵇阮这类不无“迂阔”的人们的期望,嵇康在《太师箴》中用老庄观点理解历史演变,以为唐虞以前“大朴未亏”,天下为公,“下逮德衰,大道沉沦,智慧日用,渐私其亲,惧物乖离,擘义画仁,利巧愈竟,繁礼屡陈,刑教争驰,天性失真。”(《嵇康集校注》,第310—312页)以为仁义礼教乃是追逐私利的结果,是天下为私的结果。说到他自己所处的世界,他指责君主们“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刑本惩暴,今以协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丧乱弘多,国乃陨颠。”(同上)嵇康在这里已经几乎将礼教直接等同于工具性的现实礼教而不知有目的性的原始礼教了。
抗议礼教蜕变为工具性的礼教,对嵇阮来说,同时意味着抛弃礼教而崇尚老庄无私无欲的“自然”。嵇康、阮籍总是用怡然自足、少私寡欲的道家学说来理解历史和现实,批判名教沦为人们穷奢极欲、贪得无厌的工具。其言论充满了两人的文集,由于它们同我们此时此刻所关心的问题关系不很大,所以从略不加述及。总而言之,嵇阮二人以为私欲的膨胀导致了名教的工具化,名教成了一种卑劣的牟利手段。有鉴于此,他们不再从名教本来具有的文明化功能上去肯定它,而对它大加攻击,以为名教的出现乃是社会堕落的标志。由于这个原因,有些人以为嵇康、阮籍表面上脱落礼法、抨击礼法,实则骨子里最遵守礼法、推崇礼法,他们攻击的是蜕变了的伪礼法,赞成的是他们心目中原始的真礼法,这是造成他们放达同元康放达不同的根本原因,我们觉得这种推测虽然不无道理,但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嵇阮二人攻击礼法成为追名逐利的工具,与他们早年对礼法的期望不合,确实可以说在他们心目中似乎存在工具性礼法与目的性礼法的对立,但是,他们攻击礼法时所用的标准并不是目的性的真礼法,而是老庄的“自然”,是名教与自然的对立而非真礼法与伪礼法的对立,使他们抨击名教,追求放达。虽然我们不排除他们表达方式上的文学成分(即由情绪而产生的夸张),但就现有材料而言,他们是用自然反对礼法,而非用真礼法反对伪礼法,在他们的表述中,好像礼法本质上就是私欲的工具。
事实上,汉武帝以后的礼教虽然不合原始儒学对它的理想化阐释,根本上成了维护和捞取私利的工具,但同时我们应该肯定,这虽然是蜕变形态,但它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它原有的文明化功能,而且可以说,正因为它具有文明化的功能,它才能蜕变为维护统治的工具。礼法在现实中是一把两刃刀,在其积极意义上,它导引中国人摆脱野蛮走向文明;在其消极意义上,它通过向当权者献媚而成为统治工具。如果说,嵇阮从礼法变成工具角度非毁礼法仅只触及其现实的消极的一面,因而给人的感觉是他们只否定礼法成为名利的工具而不否定礼法本身;那么,当嵇阮攻击礼法戕害个人的情性时,他们就对礼法之为文明化工具的“积极意义”提出置疑,从而揭示礼法本身所包含的问题和困难了,与对礼法沦为名利工具攻击最力者为阮籍相反,揭露礼法本身的问题和困难从而力主任自然主要是嵇康的功劳。
三
嵇康在《难自然好学论》中反对张辽叔人天生好学礼法的观点,提出人是“困而后学,学以致荣,计而后习,好而习成”,看起来是自然而然的,其实是名利诱导的结果,这与他们认为礼法是名利之具的立场是一致的。更重要的是嵇康接着讲的几句话:
“推其原也,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故仁义务于理伪,非养真之要术,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嵇康集校注》,第260—261页)
这里所争论的“自然”指人的真性,是“不须学而后能,不须借而后有”、如同“口之于甘苦,身之于痛痒”一样的东西。按他所说,“推其原”即从根本上讲,获得自然的东西不必通过六经,自然的东西即人的本性,所以保全自己的本性,并不需要用来规范(“犯”同“范”)情性的、载于六经中的礼法。为什么呢?因为“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抑”,《说文解字》注:“抑,按也。”可见“抑”为“屈”的意思。与此相反,“引”为“伸”的意思。抑引就是屈伸合度的意思,所以“抑引”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规范”(主要取动词义)。“从欲”之“欲”可以指欲望,如《答难养生论》有“今以从欲为得性”之句;也可以指愿望,此处即是,可证之于“抑引则违其愿”一句。与此相应,“从欲”在嵇康那里也有两义:一为听从欲望;一为听从愿望。前者是他极力否定的,后者是他竭力倡导的。这里的从欲为听从意愿,恰与抑引的规范意愿相对,后者违背意愿。嵇康认为人的本性是服从自己的意愿,而六经所表达的礼法却要强行规范自己的意愿,所以,礼法是违反自然的东西,如果不是为了名利,人们是不会喜欢学习礼法的。由于从欲为真,抑引为伪,所以仁义不能“养真”,廉让不是出自自然。嵇康还把人的真性比作“鸟不毁以求驯,兽不群而求畜”,人喜欢随心所欲,而不喜欢受礼法的管教,这是“必然之理”(同上书,第261—262页)。嵇康在其《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贵得肆志,纵心无悔。”(同上书,第20页)《与山巨源绝交书》说自己“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同上书,第114页),表达了对矫性强制的否定态度。
嵇康在这里很明显是要说明礼教本质上与人的情性相对立,礼的本质是使人服从固定的规范,人的本性则是从其所愿。用现代人的话说,礼规定人“应该做什么”,人的本性则趋向于“愿意做什么(或‘要做什么’)”。按嵇阮的意思,“应该做什么”与“愿意做什么”(“要做什么”)是相互矛盾、不可调和的。我们认为,儒家的礼本来就是一整套规范体系,用以使社会秩序化从而建立、维持和延续、发展社会整体,它对个人在社会中的言行举止作了详细规定,其根本作用是训练每一个人成为文明社会中的一员,因而即使从其思维路径而言也主要是从社会存在的角度而非个人生存的角度设立的。对礼而言,人是作为社会整体中标准化的、无差别的一员而存在的,否则其固定的规范就毫无意义。礼只是把个人当作一个社会角色(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士、农、工、商等)的聚合体来看待的。阮籍描述的“君子”“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进退周旋,咸有规矩……”(《阮籍集校注》,第163页,见前引)即是例证。
无数的“应该”构成了社会对个人的强制性要求,它们合在一起有使活生生的个人沦为社会存在和延续发展的工具的危险:个人被迫去完成社会强加给他的一项项任务,个人的自我却在承担无数的社会责任中被压抑和牺牲掉了。这大概就是嵇康以为六经与人的真性无关的道理。我们说,人是一个社会存在物,他不可能离开社会而生存,因而礼的文明化功能自有它从社会角度讲的合理性。然而,活生生的个人并不能还原为一系列社会角色的总和,人的自我有他表现自身而不被压抑扭曲乃至牺牲的更为正当的要求,这正是嵇康以“人性以从欲为欢”所要表达的东西。我们记得,在儒家创始人孔子看来,礼和情性应该是统一的,他追求的是“应该”和“愿意”的统一,希望礼既是社会对个人的要求又是个人自我表现的需要,“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其最高理想。但是,事实上,“从心所欲”和“不逾矩”是很难统一的,礼的规定越详细具体,两者就越难统一,当礼成了维护私利的工具之后,其本身具有的强制性,对人的情性的压抑和摧残就更加变本加厉,二者就更无法统一了。嵇阮时代的礼甚至成为奸滑之人残杀正直无辜者的手段,无怪乎他们要坚持名教与自然绝然对立,不可调和了。
嵇康要求人的言行举止都是其内心状态的流露,要求人的视听言动不是循礼而是自我意愿的表现,他把这叫作“公”;而把那种把自己隐藏起来、为了某种目的按照外在要求去行事称为“私”。他的《释私论》以“无措”还是“匿情”区别君子与小人,“是故言君子,则以无措为主,以通物为美。言小人,则以匿情为非,以违道为阙。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恶;虚心无措,君子之笃行也。”(《嵇康集校注》,第234页)把自己隐匿起来就是“有措”,就是“私”, 就是小人的作为;把自己表现出来就是“无措”(“虚心”),就是“公”,就是“君子之笃行”。他解释“公”、“私”说:“夫私以不言为名,公以尽言为称,善以无名为体,非以有措为质。”(同上书,第243 页)他强调不加思索计较地行事:“值心而言,则言无不是;触情而行,则事无不吉。”(同上书,第237页)由于言行顺应自己的性情而生, 秉“公”而起,就不会有错误,也不会不吉利,所谓“言不计得失而遇善,行不准乎是非而遇吉”,嵇康称为“公成而私败之数”,相信上天也会成全这种行为。可见嵇康对无所隐蔽地表达性情之举的推尊。
阮籍也抨击礼法之士的虚伪,说他们“造伪以乱声,作色以诡形;外易其貌,内隐其情,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诳拙,藏智自神……”(《阮籍集校注》,第170页),他把按礼而形成的声、色、貌、言、 行等统统判为不真实的东西,都是为了满足私欲的诈伪举动。显然,阮籍肯定的也是嵇康所谓“虚心无措”的率性行为,而非匿情诈伪的循礼行为,阮籍与嵇康不同的地方是,他注意并强调了率性而动之人言行举止的“无常”性。他在《大人先生传》中说:“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同上书,第165 页)阮籍用老庄术语把“大人”的“变化散聚,不常其形”说得很玄乎,好象他是神仙似的。其实,这里的关键正在于“形”的“常”与“不常”上。礼法是一整套固定的规范,其所针对的当然只能是有定“形”的人,如果一个人无定“形”,礼法就失去了作用。所以,礼法之士必有“常形”,声、色、形、貌、言、行等都有固定的模式,而这种机械的固定模式又必然阻碍和压制真实性情的显发,因此反礼法就是反对僵化的生活模式,要求更活泼、更丰富的生活方式,以便使人的真实自我得到表现,阮籍用恍惚之言所要表达的就是这一点。《大人先生传》又说:“是以至人不处而居,不修而洁,日月为正,阴阳为期,岂希情于世,系累一时。乘东云,驾西风,与阴守雌,据阳为雄,志得欲从,物莫之穷,又何不能自达而畏夫世笑哉!”(同上书,第166 页)在《与伏义书》中,他甚至说:“夫人之立节也,将舒网以笼世,岂撙撙以入网;方开模以范俗,何暇毁质以适检。”(同上书,第70页)如果要立节的话,自当用规范去改造世界、立模范来铸造时俗,而不应汲汲于受既定规范约束,以扭曲自己遵从礼法。
由此可见,成熟的嵇康阮籍奉行了一种特殊的玄学观,即一种深刻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它可以用嵇康所说的“越名任心”四字加以非常简洁而又准确的概括。竹林玄学的精髓完全体现在这四个字中了。“越名”与“任心”是不可分割的两面。“越名”即毅然决然地抛弃名教,坚决不与名教调和;“任心”即毫不犹豫地听从真性情、真生命的指引,奔向自由的人生。二者的结合至少证明一点,许多人以为嵇阮派貌似大反名教实则极尊名教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嵇阮在庄学中找到了抗衡名教的可靠根据,并不需要对名教“阳违阴奉”。当然,嵇阮所代表的那种与名教决绝的姿态确实如某些人所说表现了一种对现实极其彻底的绝望情绪。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他们的“越名任心”论表明,他们不是真正的儒者而是真正的玄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