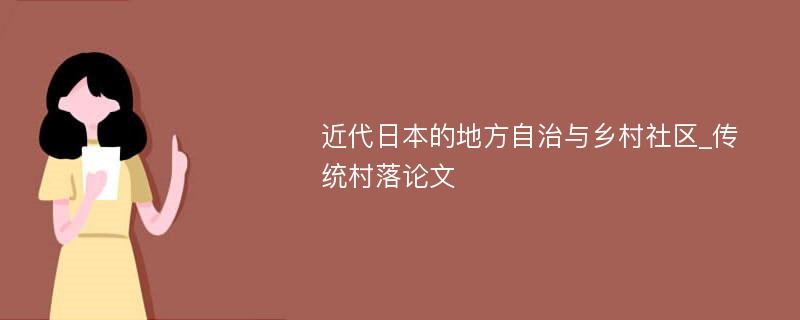
近代日本的地方自治和村落共同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同体论文,日本论文,村落论文,近代论文,地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313.4;D731.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593(2004)01-003
近代日本实行的地方自治,是日本政治近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它虽然具有官制性等各种局限,无法称得上是真正的近代意义的地方自治,但在日本地方制度的近代化中却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而且在上个世纪初的国人学习东瀛的热潮中,一度被当作地方制度上的范例。对于近代中日两国实行地方自治的成败原因,有学者认为,“日本的地方自治搞得比较成功,但这恰恰是和宪政民主齐头并进的结果,市町村自治与颁布宪法、召开国会大体同步,现行的地方自治法也是和新宪法一起制订的。”[1]对此,笔者没有异议。但是笔者在研究近代日本的地方自治中发现,近代日本地方自治的实现,传统地方共同体特别是近世以来形成的村落共同体对近代的地方自治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且这一本是矛盾的对立事物却复杂地互相作用,推动和制约着近代日本历史的发展。
一
近代日本的地方自治主要是仿照德国的地方自治建立的,但并不完全是照搬照抄,还是融合了日本的传统的。近代日本地方自治的缔造者山县有朋也承认,“我邦原来设立的五人组、庄屋、名主、总代、年寄等制度中,本来就存在着自治制度的精神”,并指出自治法案的形成即是“以我邦古来的自治的精神为基础”[2](P401),山县在这里所指的就是近世以来的村落共同体。
近世以来的村落共同体也被称为部落或自然村,实际上是由原来的行政村形成的,是幕藩统治下的纳税单位。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较低,村民必须互相协助,共同生产;对与生产相关联的事务如水利、山林等也要进行共同管理、共同维修;与此同时,在生活上,人们也共同生活,如共同祭祀等。由于长期的共同生产和共同生活,每个村落渐渐形成为一个村落共同体。村落共同体内设庄屋、组头和百姓代,称村方三役,负责管理村落共同体的事务和充当村与藩交涉的带头人。村落共同体内有许多团体,如老年人团体的老年会、青年人团体的若者组、未婚女青年则结成处女会等。不过其中最重要的是村中的议决机关——寄合。所谓寄合,可以说是村中所有户的户主联合会,基本上是由本百姓(年贡负担者)一户一人组成,但不承认水吞百姓(不负担年贡者)的参加。所协议的事情除了最主要的年贡的分割外,村役人的选出、村预算的决定、冠婚葬礼和祭礼等都是最重要的议题,以及村内的诉讼和犯罪的取缔等关乎农民生活的问题也都包括在内。最有趣的是在寄合里讨论问题时,实行的既不是权威者的发号施令,也不是近代的多数议决制,而是全员认可制。一个问题,必须得到所有成员的同意,才能付诸实施,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也决不执行。在第一回寄合上未取得一致的问题必须经过两次、三次的协议,达到全员同意才可以上升为整个共同体的意志。日本民俗学家宫本常一曾经于战后的1946年考察过四国等地,发现这种寄合还非常顽固地存在于四国的乡村间。[3]
东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富永健一指出这种村落共同体是前近代的表现形式,近代化的发展将导致村落共同体的解体。[4]然而,日本的近代地方自治从建立初就无法离开传统的村落共同体。
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地方制度上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反复的探索阶段。维新初期新政府初宣布实行府藩县三制,对村一级的事务还根本无暇顾及。村落共同体的村方三役原封不动地暂时保留了下来。但1871年实行废藩置县后,政府首先在户籍政策上实行了大区小区制。这种户籍上的大区小区制不久演变为地方行政上的大区小区制。地方的事务开始由新设的区长或副区长、户长等负责,原来的村方三役被否定。不仅如此,由于原来的村落共同体过于小,新设的区往往包括若干个村。大区小区制的实行是明治政府对地方实行官僚统治的开始,其特点是彻底否认了地方的自治传统,不仅在区的设定上否定了村落共同体,而且区长等官吏都由政府指定或任命,而非传统的由村民来共同选举。这使得在征税等地方事务上往往受到村落的抵抗,因而政府也不得不对村落共同体采取温存的态度。1878年大区小区制的矛盾日益显露,大久保利通等经过商议,废大区小区制,实行地方三新法。地方三新法由郡区町村编制法、府县会规则、地方税规则三法组成。其特点是重新承认了日本的传统的村落,并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自由民权运动以来蓬勃发展的地方民会。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国家议会成立前,日本的地方民会已经很发达。据统计,在三新法实行期间的全国府县中,召开公选民会的有7县、召开以区长和户长为议员的民会的有1府22县,未召开任何会议的有2府17县。[5](P89)而就当时民会发展的深度来看,在当时民会较为发达的滨松县,不仅所有议院全部是民选,而且如果女性是户主的话,也具有选举权。议员的选出方法是间接选举,首先由居民选出小区的民会议员,其正副议长成为大区的议员,然后再在大区的民会议员中选取县民会议员。由于当时滨松县民会的进步意义,被当时的人称作:“远州的民会价千金”。应该说地方民会的发达既是明治维新后自由民权运动蓬勃发展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决不能排除传统的共同体合议制的影响。自由民权运动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实行地方自治的要求,并为民众所接受,这不能不说同中国民众对地方自治的接受有很大的不同。正是由于民会的发达,一方面促使政府不得不提早下定决心实行官制型地方自治,以把握自治的主导权;另一方面也为日后实行的府县会、郡会和町村会等提供了经验。因而在这种背景下所实行的地方自治无疑更容易取得成功。
宪法发布前的1888年,在山县有朋的指导下完成的地方自治法——《市制町村制》发布,1890年《府县制郡制》亦完成,标志着近代日本地方自治制度的成立。
从最初的府藩县三制到断然实行废藩置县、大小区制和地方三新法的实施,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地方制度在经历了若干的探索和尝试后,最终成立了近代的地方自治制度。在这一段的探索中,明治政府对近世以来日本传统的村落共同体也经历了从利用到否认再到重新认识的过程。富永认为,近代化实现的可能性的多少,要看传统文化对他的受容程度。[4](P286)由此看来,由于日本近代以来存在的“自治的传统”,所以近代地方自治的成立过程就相对的较为顺利吧。
二
1888年《市制町村制》发布前,明治政府首先进行了大规模的町村合并,使全国的町村由原来的7万多一下锐减到1万多。[2](P424)通过合并形成的新町村是地方自治的基本单位行政村,但旧村并未因此而被全盘否定,因为部落有财产和林野并未统一到新町村,所以村落共同体实际上是被保留下来。这种由近代地方自治实行后形成的自然村和行政村的并存现象被学者称为“二重村问题”,或近代日本村落的二重构造。尽管在社会学上这是一对矛盾的事物,但在此后的近代日本,二者却发挥着相辅相成的作用。尤其是旧村,始终没有消逝,而是在日本近代每次加强天皇统治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自然村对行政村的矛盾和补充的关系一直随着近代日本历史的发展而发展。这在日俄战后和法西斯战争体制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
首先在日俄战后,战争中的巨额战争费用和战后军国主义步伐的加快,使帝国主义国家的财源更加紧张,在地方上町村的财政趋于破产。为了挽救町村的疲敝,政府实行了地方改良政策。首先是部落有林野的町村统一政策。在市町村制初实行时被保留下来的部落有林野在此时规定统一于行政町村,以增强新町村的经济能力。此外还强制实行了神社合祀。所谓神社合祀就是将那些不能置神祗的破败的神社合并到其他较大的神社中,以“实现氏子崇敬之实”。在日俄战后大规模进行的神社合祀中,尤其是内务省神社局倡导的“神社中心主义”下,通过强制实行一町村一神社来加强新町村的统合。政府实行的这些措施进一步破坏了传统的村落共同体,加强了行政町村的机能。但与此同时,政府为保证民众的纳税能力,使民众自主地向国家行政表示协力,又不得不利用了传统的村落共同体。地方改良运动主要以二宫尊德的报德精神为指导原理,鼓吹亲睦协和、勤劳的精神的同时,还鼓励各地成立农会、产业组合、卫生组合、在乡军人会、户主会、主妇会等,作为行政的辅助组织。这些民间团体大多是旧的共同体组织的再编和复活,有的地方甚至复活了近世的五人组制度。虽然有学者强调,“尽管表面上看来是共同体秩序的再编和复活,但必须注意的是它并不是共同体秩序本身的复活。”[6](P318)然而他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传统的村落共同体的组织来巩固近代的地方自治确是肯定的。
在1929年世界性大危机中,日本的农村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农村再次面临濒于崩溃的危机。面对此危机,官僚打出了经济更生运动的旗号,对农村进行再编成。在这里仍然采用了日本传统的家的制度和村落共同体的原理。一方面推广地主和佃农的亲方子方的家族拟制关系,另一方面加强了传统的村落共同体的规制。实行的农家组合强制要求农家共同作业和共同利用,使之从生产的共同体的强化变为法西斯的支配机构。
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军部更加紧建立高度国防的国家体制。日中全面战争爆发后,向军国主义国家体制的全面转换已成为当务之急,对传统的村落共同体的利用也进一步加剧。1938年国家总动员法发布,要求活用町内会、部落会等组织,1940年大政翼赞会实行,整备全国的部落会、町内会和邻组等,并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也就是说,“在总体战体制下,由于政治的统合的增强,在强力的中央集权下,自然村 = 部落作为行政上的单位被法制化。”[7](P607)
由上可见,在战前日本的地方自治中,行政村是为行政目的的实行而设定的统治组织,自然村是自然状态下的生活共同体,属于前近代的性质。两者性质的相异决定了他们本该是矛盾对立的关系。当然,这种关系在战前的日本也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特别是一战后,工业化、都市化的进展使共同体的强制基础受到侵蚀,地主和佃农的对立也带来了共同体连带的分裂。但是综观整个近代日本的历史发展,自然村对行政村的补充关系占据着更重要的一面。即在战前,由于急速的近代化,政府不得不采取了这种地方制度上的二元的构成。“行政村的自治既可以省政府的繁杂,又使居民练习地方之公事,而知施政之难易,促进政治的社会化的同时,又尊重自然村的邻保团结的旧习,并扩张之,以阻止议会政治的影响波及到地方社会。这种机能给近代化——工业化的实行以重要的支持作用。”也就是说,“承担着近代化作用的行政村由自然村的部落连带进行补充的关系成立,支撑着近代化的发展。”[7](P606)直到战后,随着民主化改革的进行和工业化的迅猛发展,行政村被自治体化,自然村的非民主的性格及其补充的作用才逐渐被克服。
三
尽管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以“同文同种”,来形容中日文化,但实际上中日文化的差异是很大的,这恐怕已经是大多日本学研究者的共识。[8]因而在研究近代日本地方自治取得成功而中国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实施地方自治的失败原因时,除其他因素之外,还有必要考虑一下中日传统的不同。“中国历史上的乡治,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乡治主要依靠乡官,朝廷和官府对于乡土社会实行全面和严密的控制;在第二个阶段,朝廷在乡间的代理人由职官变成了职役,官府对于乡土社会的管制有所放松,乡绅成为乡治的重要角色。但是无论在哪一个阶段,都谈不上‘地方自治的民主体制’,集权专制和缺乏自治,两千年来都是中国文明的一大特色。”[9],而相对中国来说,日本则形成了较为规范的村落共同体的合议制。因此在近代的地方自治实施前两国所具有的不同的前提条件不能不对其产生影响。
近代以来日本人的意识仍然大部分为家的意识和村落共同体的意识所支配。战后关于共同体的争论也一度极为激烈。以丸山真男、大冢久雄、川岛武宜等为代表的学者曾一度认为,日本的封建的农村共同体是导致日本社会近代化偏向的原因所在。如著名思想家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中即指出,近代日本的国家是以天皇制国体为精神基轴,在制度上采取近代化的官僚机构和底边的传统的部落(村落)共同体的连接。色川大吉则表示反对,认为丸山等人所谓的共同体是从“明治末期至大正、昭和初期“停滞期部落共同体”形态中抽象出来的,”是片面的。[10](P311)当然抛却其争论不谈,由此可见,共同体或曰村落共同体的存在确在日本的历史中占据重要的一席。
日本文化以善于吸纳外来文化和保持传统文化为特点,这在近代日本的地方制度上也表现出来。近代日本的地方自治的建立,是以日本传统的自治因素——村落共同体的存在为基础的,因而近代日本的地方制度取得成功。但由于日本近代化的急速性,所以近代的地方自治又不得不依靠前近代的村落共同体来补充,使得近代日本地方自治无法称得上是真正的近代意义上的地方自治。
日本社会学家富永健一认为:“日本人是集团主义的,缺乏个性自觉的原型可以说就在这种村落内部的强力结合上。”[4](P286)由此可见,村落文化也可以说是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日本传统村落的研究入手,是否也可以探究到日本文化的某些特质呢?
收稿日期:2004-0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