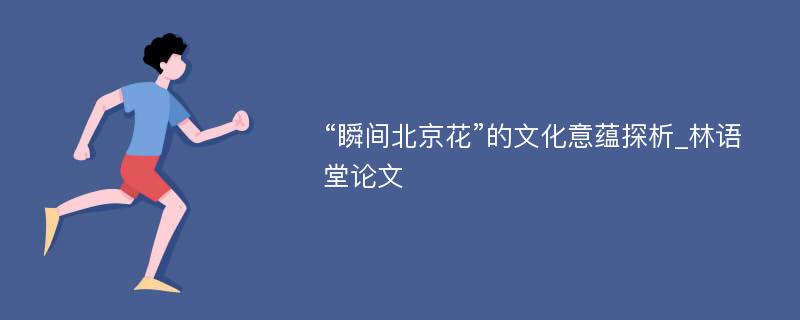
《瞬息京华》的文化意蕴探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蕴论文,京华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探讨了林语堂在其长篇小说《瞬息京华》中所表现的对人类文化思考的第一阶段内容: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中,通过儒道对比,褒道贬儒,倡导道家文化。
关键词 林语堂 《瞬息京华》
一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是林语堂一生的自我总结与写照。30年代,他的一位朋友谈到他最大的长处是向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的确,林语堂一生都在致力于“中西文化溶合”的理论与实践活动。特别在1936年出国后,“他已不再平均使用力量,明显地加重了其中一只脚的份量;把重心偏向于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那只脚上”〔1〕。除了他的散文、译著以外, 他的一部分小说也成为他介绍活动中所采用的一种重要手段,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文化小说”,以对中西文化的思考为创作本体的小说有:《瞬息京华》、《唐人街》、《奇岛》、《赖柏英》。
正如陈平原先生在《林语堂的审美观与东西文化》中所指出的:“对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如何协调东西文化的矛盾,无疑是一个十分严峻的课题。一方面是强烈的世界意识,一方面是强烈的民族感情,常常逼得他们徘徊于中西文化之间。”“汉唐时国势强盛,接受印度文化时充满自信,向传统文化的复归也就显得十分自然。现代中国积弱贫困,是在承认我不如人的前提下提出‘向西方学习’的,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否定”〔2〕于是“东西之争”和“情与理之争”纠缠在一起,使得这一文化抉择分外艰难与曲折。林语堂正处于这种东西文化大冲撞的时代,由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与文化氛围决定了他独特的思维方式,使他拥有与同时代作家完全迥异的心理历程。林语堂对人类文化的思考在他的“文化小说”中明显呈现出三个阶段:(一)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思考中,通过儒道对比,褒道贬儒,倡导道家文化;(二)通过中西比较,情感的天平倾向中国文化;(三)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以世界眼光审视世界文化时,发现中西文化各有利弊,提出了属于未来世界的文化构想——中西合璧。
《瞬息京华》属于作家对文化思考第一阶段的产物。
林如斯在《关于〈瞬息京华〉》中谈到对其父这部小说的印象:“此书的最优点不在性格描写得生动,不在风景形容得宛如在目前,不在心理绘画的巧妙,而是在其哲学意义”,“故此书非小说而已!”此实为有识之见。林语堂为了弘道批儒,不惜牺牲小说的艺术品性,疏略了作品中人物形象的丰满特征及其合理变化,使作品人物的血肉之躯抽象成为服务于叙述者意志的积淀着特定文化意味的符号。
《瞬息京华》以道家哲学为脉络,借道家的女儿姚木兰的半生经历为线索,描写了姚、曾、牛三大家族的兴衰史和三代人的悲欢离合,并以此为缩影,展示了中国广阔的社会人生,通过不同文化的人生方式在风云变幻的同一时代背景下的对比,揭示出道家总是比儒家胸襟开阔的结论。
我们只要分析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是不难看出作家这一创作意图的。处于全书的中心位置的是姚家的家长姚思安、大女儿姚木兰、二女婿孔立夫,他们都信仰道家自然主义,这就给社会人生增添了不少崇尚自然人生、充满人情诗趣的意味。界定名分,“父辈曰尊”,本是因儒学影响而形成的家族制度的关键,但作为一家之主的姚思安却“沉潜黄老之修养”,把家政分与妻子,把店铺托付给舅爷,只和书籍、古玩、儿女日夕相处。于国事,同情变法的光绪皇帝;不满义和团的迷信排外;出巨资支持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中日战争爆发后支持抗战,却从不涉足仕途。姚府也发生过姚太太拒纳女仆银屏为媳,致使银屏绝望自杀的惨事,但此事发生在姚思安南游之时,与他没有干系。他倒是对儿女婚姻一向很开通,热心于二女儿莫愁与穷书生孔立夫的婚事。即便他搬进了富丽堂皇的王府花园之后,对于幼子阿非与破落旗人的女儿宝芬的结合,他也认为是道的必然而顺水推舟。在完成了他认为他应该做的事情之后,一心研读道家典籍,静坐修炼,过着半在尘世半为仙的生活,最后云游名山古刹十年达到了佛家的物我两忘的境地,无疾而终。
孔立夫是作为一位理想中的青年出现的。他安贫苦学,奉母至孝,由一个儒家的儿子变成道家的女婿之后,深受信奉道家的岳父的影响,潜心老庄学说,致力于道教与科学的糅合,写出过《科学与道家思想》、《〈庄子〉科学评注》等文章,企图使庄子的观点获得现代性与科学性,甚至得出了庄子的《齐物论》就是相对论的观点。他也曾有过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敢于撰写针贬时弊的时事论文;并作小说嘲讽荒淫无耻的军阀、官僚,又能隐居苏州从事甲骨文研究,曾复出监察院任职,侦查有日本背景的津沪贩毒案,又能功成后急流勇退。
姚木兰,“道家的女儿”,“正如饱满的月球一般的美丽”,“除去了她两眼具有迷人的魔力,和婉转娇弱的声调之外,她真有一种神仙般的姿态”〔3〕。她心地善良,对上下左右都能推心置腹,和睦相处,对人间的一切苦难都深怀同情。作为道家的女儿,她继承了父亲的豪放、豁达,淡泊名利,胸襟开阔,天真而富于浪漫幻想。她从学校教育中受到过新思潮的洗礼,敢于篾视封建传统,追求个性解放。她敬爱孔立夫,却能按传统礼俗与世家子弟曾孙亚成婚,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当孔立夫被捕入狱时,敢于夜闯军阀司令部,取来开释的手令;丈夫有了外遇,她的胸襟风度也绝非一般女子可比,把陷入迷津的少女邀至家中,杯酒释嫌。她痛爱自己的亲生骨肉,但能忍受母子离别之痛,让儿子参加抗战;在大逃难途中,接二连三地收养孤儿寡女,这也反映了蛰伏在她心灵中的人道主义和博爱精神。总之,无论是作为女儿、媳妇、妻子、姐妹、妯娌、朋友、母亲、主妇,无论是用中国传统美德还是用西方社会公德来衡量,姚木兰都是那样周到完备,集中西文化美之大成,实为文苑中的一独特形象。
以上三位道家人物是作家最钟爱的人物。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作家的理想人生方式。他们都随着道的必然自在地舒展自身的性灵,自己主宰着自身而不为他物所役,这正是林语堂所毕生追求的。难怪林在结束这部小说的写作时曾道:“若为女儿身,必做木兰也。”〔4〕而他确非女儿身,那么年青的孔立夫,年迈的姚思安则自然而然地将成为他人生的两块路标。
中国的儒家文化在传统文化中属于一种官本位文化,历来崇奉“学而优则仕”的人生信条。因此《瞬息京华》中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大都为官场中人,如正统儒生曾文伯,腐儒牛思道。作家在刻画这些人物时,主观厌恶情绪的介入特别明显。他们显得或保守、或愚蠢、或丑陋、或可笑,甚至连同其子女也显得那样俗不可耐,如曾襟亚、牛素云、牛环玉(牛素云与曾襟亚后因接近道家人们而有所改观)。相反,他对信奉道家的士人(如傅增湘、辜鸿铭)、商人(如姚思安)连同其子女甚有好感,因而刻画得丰满、栩栩如生。
曾文伯,原为朝廷命官,后来成为前清遗老,饱受儒家思想浸染,异常保守,反对一切新事物。“他恨洋书,恨西洋制度和一切洋玩意儿”〔5〕。坚守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士、农、工、 商”的等级制度,对作为科学象征的金表也表示蔑视,“认为不过是低等头脑的产品。洋人制出精巧的东西只表明他们是能工巧匠,比农人低一等,比读书人低两等,只比生意人高一等,他们不配称拥有高等文化,拥有精神文明”〔6〕。若不是西医治好了他的糖尿病, 他对洋人的奚落大概永远也不会改变。他反对革命,认为民国建立,一国无君,则个人目无法纪,社会动乱,整个中国文明就受到威胁。因此,他在老母丧仪上恸哭不已,这哭不仅是出于礼仪观瞻之需,而是发自内心的,他熟知的华夏古国正在他脚下溜走。他更反对提出“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文学革命,把整个革新派称为蛮子、“忘八”和大言不惭地谈论自己不懂的东西(尤其是儒家学说)的人。他又是一切旧的封建伦理关系的维护者,对新道德视之如洪水猛兽,为了维护妇德,竭力限制曼妮、木兰等抛头露面,甚至不赞成木兰之雅爱诗词歌赋,因为他认为诗词歌赋少不了同男女私情有关,而女子有了私情便一定会堕落。总之,林语堂笔下的曾文伯形象是一个死抱着祖宗传统不放而最终被时代所抛弃的可怜虫。
另一位儒家代表人物是牛思道。如果说作家对曾文伯尚有一丝怜悯与同情的话,对牛思道的用词则无不泄其愤,极尽嘲讽之能事。当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曾文伯尚知共和之心已深入人心,已成为历史潮流不可逆转而决不同流合污,至少表明他还有一定的人生准则,人生追求,尽管他追求的是复古。牛思道则是一位毫无人生准则可言的混世魔王、社会蛀虫。他出身于一个经营钱庄有年的家族,在科举与吏治败坏的道咸年间买得一个举人头衔,又靠贿赂一个有势力的太监谋得陆军部军需总监一职,而后又凭借牛太太与大学士之妻的表姐妹关系在宦海中一帆风顺,青云直上,成为满清王朝的度支大臣。他贪得无厌,被朋辈称为“牛财神”,是民谣中受到诅咒的摇钱树下的“牛”。他愚蠢而庸碌,甚至不明白自己何以会飞黄腾达,认为是他满脸横肉的“福相”带来的。他常常训斥旁人,特别是对下属,可常因附庸风雅而闹出笑话而不自知。“鹤立鸡群”原本是说一个人的才能、美质超过同辈之意,他竟用这词音调铿锵地表示自谦:“兄弟有幸与诸位共处,实乃鹤立鸡群……”但我们应当注意到叙述人林语堂对牛思道的评论,他认为牛“也并非坏人”〔7〕,甚至借他女儿黛云之口说他“心地单纯”。这样, 我们就找到了林氏设置牛思道形象的真正动机:他真正要抢挑的是牛思道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封建官场及整个封建制度,而这一切又正是儒家文化繁衍的产物。前文已论及,林对儒家代表人物的嫌恶甚至涉及其子女,由此看来这并非一种情绪泛滥。在林语堂看来,中国儒家文化已经浸透了整个社会环境(包括家庭环境),并通过环境钳制了人性的发展,使之畸形,从而导致一些不合理的行为。林氏曾提出这样一个理论:“腐败官僚的子女不是学父母的样就会成为最彻底的叛逆,毫不妥协地反对父母的为人方式。”〔8〕因此, 林语堂又在牛思道旁设立了两个小丑形象:卑鄙阴险的牛环玉和荒淫无耻的牛同玉。唯有黛云成这个家庭的叛逆,在新思潮的鼓舞下谴责一切旧官僚的腐朽生活,后来成为抗日运动中“锄奸团”成员。
小说中,还有一位人物值得重视,那便是曾家大媳妇孙曼妮。她是一位充分体现着儒家传统妇德的女性形象。如果说上述人物的塑造是为了正面批儒,曼妮的塑造则是人们展示一份儒家文化的祭品。
孙曼妮原是一小镇上的一个纯朴姑娘,“眼睫毛、笑容、甚至牙齿和甜美的容貌全都很美”〔9〕。由儒家父亲抚养长大, 受过完备的旧式女子教育,接受了儒家礼教给女性所规定的一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并缠有一双小巧的脚。正如林氏所说,是从古书中掉出来的插画里的古董。曾家为了替病魔缠身的大儿子平亚“冲喜”,把年少的曼妮娶进曾家,随着平亚的夭折,曼妮便心甘情愿地过着漫漫无期的孀居生活。人性在这里受到戕害,人情在这里遭到虐杀,谁是凶手?曼妮的人生历程甚为简单,是从一个儒家的家庭进入另一个儒家的家庭。从她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儒家礼教的魔爪就伸向了这一幼小的心灵;当她思维成形,她就知道,她不属于自己,她的行为为礼法所制约,她是为未来的夫君生活的。在没人陪伴的情况下,她甚至连四周有高墙的后花园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因为她听她父亲说过,几乎戏曲和小说都把姑娘的堕落或者风流韵事的开头布置在后花园里。当她丈夫死后,她尚是一纯洁少女。但她另有一个念头:她的心灵今生和来世都应以曾家为栖息之地。一名如此美丽、纯洁、善良、温驯的少女就这样被儒家礼法以不流血的形式虐杀了。儒家礼法所塑造的悲剧主人公又何止曼妮呢?
二
小说贬儒倡道的主“意”已明,仔细分析,不难发现林语堂贬儒倡道主要是从三个层面上进行的:
(一)我们认为,文化的内涵应该是指人们对世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生、发展作出解释的整套思想体系,及这种思想体系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和人生方式的渗透与影响。道家的宇宙观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源,是实存的,永恒的。道生长万物,养育万物,使万物各得所需,各适其性,而丝毫不加主宰。”〔10〕林语堂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在《瞬息京华》中认为,人也应顺从天道,让人的自然之性获得自由发展,而不应受到社会伦理、道德的束缚,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小说中三位道家代表人物,也正是以这种观点认识人生,观察人生,体验人生的。尽管他们生活在古老的儒学文化中心北京,他们都拥有着一种潜在的自由、平等、民主意识,一旦西方文化中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传入,这两种思想的共鸣与融汇就成为必然。可以说,小说主要在探寻“平等”、“民主”与“科学”的时代精神与中国道家哲学的关系,至于是否探索成功,属于另外一回事,至少作者当初确是朝着这一方向前进的。
小说在赞扬道家文化的重自然,合乎个性解放的时代要求的同时,对儒家思想束缚与压抑人性自由进行了批判,表现出反传统、反人事的人生态度。古典美人曼妮形象就是这批判的武器。人们通过曼妮与木兰这两种人生的对比,就能鲜明地看到道家文化闪光的价值。
(二)在道家的“人生如梦”的人生观中,丝毫没有悲凉的感觉。《庄子·齐物论》中的“蝴蝶迷”正是主张以艺术的心情将人类的存在及其生存的世界给予美化。林语堂由此而得出“生活艺术化”的人生态度。要做到“生活艺术化”,就要求人们顺从天道,超脱名利,超脱是非,超脱生死,无心无情,追求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强调个体存在的价值,不为物役,从而实现“逍遥游”,享受人生天然之乐。姚木兰父女的人生正是这一理想人生的现实化。立夫与木兰游历泰山看到秦始皇立的无字碑时,木兰就曾发出过这样的概叹与感想:立碑人虽曾派五百童男童女驶入东海去寻求长生不老之药,但终究还是灰飞烟灭,但“岩石(注:指石碑——笔者)还在,因为顽石缺少人间的激情”。她“想到了生和死,想到有激情的人生和缺乏激情的石头的一生。她意识到此刻不过是永恒的时间长流中转瞬即逝的一刻,但这一刻对于她却是可纪念的——本身是一种完整的哲理,或者说是关于过去,目前和未来的完整看法,关于自我和非我的完整看法”〔11〕。
作家在赞扬姚家那种超脱的人生观的同时,对曾家一切都遵循旧道德,满足于做封建统治者的附庸和工具的“雅人之俗”作了揶谕;对牛家崇拜金钱和权势,为了满足自己的那种市侩式的庸俗追求,可以遗弃自己的良心与人格的“常人之俗”进行了批判。显然,牛家的人生观最为姚家所不齿,而曾家在传统和历史的重压下,没有个人自由,没有个人意志,在历史大变革时期,只能处处表现出封闭保守,无知专横和虚伪滑稽的可笑心态。
(三)道家的宇宙观还认为,宇宙万物的变化都是道渗入的结果,因而变化并不是消失,而是由甲物形状转变成乙物状态;当甲物转入乙物的境况时,乃是一种和谐的融化。同样,人之生也是自然之气演化的结果,人之死亦是气消散回归于自然的过程。因此,人不应为生死意念所困恼,应超脱生死,更不应该为生死所带来的哀乐情绪所束缚,否则就达不到以博大的心境与开放的心灵去迎接人生的境地。林语堂正是把这种道家的生死观贯串在姚思安父女俩的人生观中。我们且来看下面这段他们父女俩的关于生死的对话:
木兰问:“爸爸,您相信长生不老吗?道家总是相信。”
姚思安说:“这是无稽之谈!那是世俗的道教。他们不懂得庄子。生死本是生命的规律,真正的道家只会战胜死亡,他死的时候比别人欢乐。他不怕死去,因为他认为这不过是我们说的‘返归于道’……”
木兰说:“因此您不信长生不老么?”
“我信,孩子。我的长生不老是在你和你妹妹,还有阿非以及所有我的子女生下的子女身上。我在你身上再世为人,正如你在阿通和阿梅身上再世为人。没有死亡这回事。你制服不了自然。生命生生不息。”〔12〕
人的生命过程中,对人的威胁莫过于死亡,连死亡都莫之奈何,还有什么能羁绊他们的心灵呢?因此,他们既能做到思想自由,善于吸纳新事物,随时代而前进;又洒脱通达,半在尘世半为仙,尽情地享受人生。这是对更有意义的人生价值的追求,而不是消极出世的苟且偷生。
也正是基于生命是一种滔滔不息的自然现象的认识,所以姚老先生能够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夕,超越当时流行的“武器装备弱”,“国势贫弱”、“中国必输”等浅见,预见到中国必胜,胜利的力量源泉正在于这不可战胜的“自然”,不可欺的“人性”。
小说中有姚思安对中日战争的一段断语:“你们去问曼妮吧。要是曼妮说中国非打不可,中国就会打赢;要是曼妮说中国决不能打,中国就要打输”〔13〕。
曼妮是中国社会里不可再胆小的温驯柔弱的女子,虫豸和蝴蝶都不敢碰一下,看到战败的小蟋蟀都要洒下一掬同情之泪,连她都斩钉截铁地发出:“中国愿打不愿打都得打。”“我只知道,如果咱们非倒下不可,那么,让中国和日本同归于尽吧!”〔14〕合道与背道已判,正义与非正义已明,还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中国会打赢这场战争呢?
此外,小说的描写跨度虽长达四十年之久,但多次出现木兰父女对甲骨文的理解与对古董的偏爱的描写,显示了道家的时空意识与价值观,一方面为木兰后来投身抗日救亡洪流的行为方式提供了“前因”,另一方面为我们理解作家执意要把书名Moment in Peking译作《瞬息京华》而不满意于《京华烟云》这一书名的心理提供一把钥匙,因为《瞬息京华》比《京华烟云》更合乎“道”,更能体现道家的时空意识。
三
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主要课题是文化变革,它同民族救亡和民族现代化既紧密相连,又步调一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承认“我不如人”的前提下爆发的一场文化革命运动。传统的旧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大扫荡。《剪拂集》时期的林语堂,年少气盛,也高举其浮躁凌厉的笔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并获得“土匪”的美名。为什么十年后,他自己倒又积极倡导他所反对过的传统文化?我们应看到这种转变的缘由与承续性。
对于这一转变,有的学者简单归因于“客居异国,谋生的功利打算与寻根的感情需求合而为一”〔15〕,有的则归结于民族自尊心。毋庸置疑,它们都是导致林氏不遗余力地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的原因之一。但我们还应看到,林语堂在1933年出国前为打破外国作家写中国题材而存在的局限性、狭隘性,开始用英语写作《吾国吾民》,并英译了《老残游记》和《浮生六记》等中文名著,早已拉开了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序幕。1936年刚踏上美国国土,林就开始着手于这项工程的第二道工序——写作《生活的艺术》和编写《孔子的智慧》。从林如斯的《关于〈瞬息京华〉》来看,这部小说的写作仍然是这项工程的延续。她回忆道:“一九三八年春天,父亲突然想起翻译《红楼梦》,后来再三思虑而感此非其时也,且《红楼梦》与现代中国距离太远,所以决定写一部小说。”“《瞬息京华》在实际上的贡献是介绍中国社会于西洋。几十本关系中国的书不如一本道地的中国书来得奏效。关于中国的书犹如从门外伸头探入中国社会,而描写中国的书却犹如请你进去,登堂入室随你东西散步,欣赏景致,叫你同中国人一起过日子,一起欢快,愤怒。此书介绍中国社会,可算是非常成功,宣传力量很大。此种宣传是间接的”〔16〕。这段话大概与林语堂的真实心理不会太远。由此看来,林语堂从传统的反叛走向传统的复归主要原因不在于“感情”而在于“理智”,在于他认识思维的走向。早在“五四”时期倡导西洋文化的过程中,林就把眼光盯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个性解放思想上,反对压抑人性、窒息人性的封建礼教,在文学创作上则找到了擅长表现个性、舒展人性的克罗齐的“表现论”和斯平加恩的“表现主义”。为了找到适合“表现主义”生存的中国土壤,在周作人等的启发下,挖掘出了中国的浪漫派文学——明代“公安”、“竟陵”派“性灵文学”,并由此上溯到以强调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为核心的庄子学派,明确打出“幽默”、“闲适”、“性灵”等旗号。后来又由主张幽默、闲适的文学上升到倡导老庄式的幽默闲适的人生态度、人生方式,即生活艺术化。这样,林语堂就完成了“人生——文学——人生”的思维定型过程。《瞬息京华》这部文化小说就是在思维定型前提下的产物。
其次,只要回顾一下林语堂的思想发展过程,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林氏从未甘心自我个性的失落,他一直在矢志追求着出于自由意志的生活,并倔强地在大时代的动乱中保持着自我存在。林语堂前期反儒,是因为宋儒以来礼教对个人天性的束缚、压制;中期与左翼文坛论战,是因为害怕左联借口大同,为大众,搞“民众专制”、“众制”,压迫特殊的文化与思想,借口社会的平等,以压迫个体的自由。后期居国外,则看到了西方工业化后,科学与唯物主义的崛起而带来的种种负面现象,特别是辉煌的物质文明对人性的异化,物欲横流;社会憔悴,进步已停;人的性灵之光,愈益黯淡;宗教观念模糊,人类精神世界处于荒原状态。他认为,人类正处于一个“野蛮行为加以机械化”的超野蛮时代,惟有走神秘主义一途——道教,方能拯救人类灵魂,因为“‘道’的涵义之广足以包括近代与将来最前进的宇宙论,它既神秘而且切合实际”,而且“道家对于唯物主义采宽容的态度〔17〕”。所以,林语堂的倡道思想虽不无局限,但其进步意义也是不容抹杀的。
另外,西方世界紧张、喧嚣的社会生活,机器控制、战争威胁的社会环境,使本来有着自由传统的西方人从个性解放升华到“返归自然”。这时,娴熟于东西文化的林语堂惊喜地发现,中国的道家思想和道教传统本来就是彻头彻尾的归本于自然,使人与自然融成一体的自由王国。因此,《瞬息京华》有意取材于清末民初这一动荡的岁月,因为只有在时代大变革的洪流中,道家才较之儒家表现出更广大的包容性,有着开阔的襟怀,更能适应西方思潮(已传入中国并成为主流),有着强大的生存优势。道家文化也有着顺应天道、自然、发展个性的一面,这与五四时期的发展个性的思潮正好合拍。况且腐儒文化正是林氏在五四时期竭力反对的,因此林由“倡西反中”转向“倡道反儒”,并非纯为生活功利计,而是有其思想逻辑的延续性的。
也正因为如此,林语堂在《瞬息京华》中所张扬的道家文化并非纯然传统意义上的道家。他对道家的养生、知足、无为等消极面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老猾、散漫等国民劣根性和和平哲学、对改革的麻木冷漠等都有所扬弃。从《瞬息京华》中看到的道家文化实质是一种经过西方文化过滤了的道家文化,是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内核的。譬如,木兰爱女阿满死于“三·一八”惨案,“她对于一般杀害阿满的人并不感觉痛恨,她所感觉到的是她爱女的死,这是她唯一关心的,其余的事是没有什么关系的”〔18〕。这里绝没有庄子丧妻“鼓盆而歌”的洒脱,倒体现出一种人之常情的自然。沪杭相继沦陷后,木兰一家离杭州西撤。西行途中,木兰收留了三个孤儿和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这种行为固然可以解释为童年离散的人生经历与痛苦的体验的唤醒、促动,我们也决不能否认她在新式学堂所接受的朴素的人道主义和博爱精神的影响。木兰是林语堂理想的化身,我们怎能忘记这位作家生活过的基督教牧师家庭和就读过教会学校的经历呢?
总之,林语堂在《瞬息京华》中所表现的“倡道反儒”并不是思想上的复古,而是对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
注释:
〔1〕施建伟:《林语堂出国以后》,《文汇月刊》1989年第7期。
〔2〕〔15〕陈平原:《林语堂的审美观与东西文化》, 《文艺研究》1986年第3期。
〔3〕〔4〕〔5〕〔6〕〔7〕〔8〕〔9〕〔11〕〔12〕〔13〕〔14〕〔16〕〔18〕郁飞译:《瞬息京华》,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1版。304页、798页、322页、322页、149页、541页、56页、462页、463页、678页、700页、700页、797页、575页。
〔10〕陈鼓应:《庄子论“道”——兼译庄老道论异同》,《老庄论集》,齐鲁出版社,1987年4月版。
〔11〕林语堂:《我的信仰》,转引自《林语堂传》,1994年1 月第1版。* 本文于1994年9月9日收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