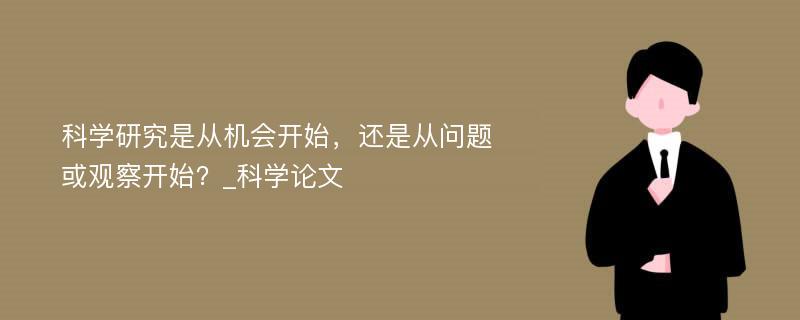
科学研究始于机会,还是始于问题或观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研究论文,机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研究缘起和背景
在科学哲学中,科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一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它的不同认识也是区分不同科学哲学观点的一个重要界石。自波普尔提出科学研究不是始于观察而是始于问题后①,科学哲学中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科学研究始于观察的观点变得似乎已无人问津,而科学研究始于问题的观点则大行其道。② 然而,近年来由于科学实践哲学的兴起,以及SSK和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研究的兴起,一种新的科学研究起点观正在悄然形成之中,这就是主张:科学研究始于机会。本文依据劳斯等人的观点,对“科学研究始于机会”的科学起点观做出评论,并初步讨论了这三种起点观的区别和新机会观的合理性及其意义。
本文的逻辑展开如下。首先,论证科学研究始于机会的观点及其立论基础,并讨论该观点与其他两种观点的重大区别及其意义。其次,给出支持“科学研究始于机会”观点的历史和现实案例。我将给出三个案例,以证伪“科学研究始于问题”的观点。虽然按照波普尔的说法,对“科学研究始于问题”这个全称肯定判断,我们只需找到一个反例就能够证伪它,但三个不同的案例会增加我们论证的强度。其中第一个案例,源于劳斯和平奇等人的研究,是关于历史上科学家对于太阳中微子进行研究形成机会的案例;第二个案例,来自关于复杂性研究领域:圣菲研究所的复杂性研究起源于经济学和人工生命研究,这是由当下的某些公司急欲寻求到不同的经济学启发和圣菲研究所急欲寻求到资助的机会造成的;第三个案例,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关于微小昆虫飞行状态的研究工作表明:这种研究的起点与其当下资源、仪器设备等研究资源所能提供的研究机会密切相关,而且研究机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制约和修改着研究目标和问题。最后,讨论科学研究始于机会的观点如何能涵盖和融合其他两种观点的逻辑和实践境况,从而提倡一种更加融贯的、历史的和多元化的科学研究起点观。
二、科学研究“始于机会”和“始于问题”或“始于观察”之区别
区别科学研究“始于机会”、“始于问题”和“始于观察”这三种观点,是重要而且有意义的。
科学始于观察的观点一直被视为支持着科学积累观,是观察与理论二分之基石。③ 自汉森提出“观察渗透理论”的观点后,由于观察与理论无法截然两分,使得“科学研究始于观察”相当于“科学研究始于理论”,因此,科学始于观察的观点受到很大质疑。
此后,波普尔提出“科学研究始于问题”的观点,成为支持证伪主义科学发展观的基点之一。但是,虽然后来证伪主义科学发展观受到质疑,科学始于问题的观点却逃避了检验,学界依然认为科学研究始于问题。事实上,这可能是由于还没有找到更为合适的起点观来取代科学始于问题观,而后者能较好地适合于表征主义科学观,所以没有受到本来就属于表征主义的科学哲学的质疑。
其实,不仅表征主义的科学哲学存在问题,因而从表征主义的观点根本无法产生对科学研究始于问题观的反驳,而且从论证的角度看,波普尔对于科学研究始于问题观的论证也并不充分。因为他只是基于一个诘难,即把观察作为科学研究的起点无法回答“究竟要观察什么”的问题,而提出其科学研究始于问题观的;然而,仅仅根据科学要研究问题以及问题可能指导观察什么,是推不出问题一定是科学研究的起点的。当然,在理论表征主义观点下,只要观察渗透理论的命题成立且具有普适性,观察的基础性地位就不复存在,从而也就无需再对“科学研究始于观察”做辩护了。
况且,从科学作为活动的观点看,构成当下科学研究的直接动因一定是问题吗?大量的事实证明不是这样。从科学作为理论表征的逻辑看,我们把科学理论中蕴涵的不相容性称为问题,把理论预期与实验结果之间的冲突也称为问题,然而,这些所谓的问题并不一定会成为在真正科学活动中实践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研究起点。
首先,从科学实践哲学的观点看,理论不是一张天衣无缝的信念之网:虽然理论之间会产生冲突,但冲突常常被科学家们视为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人类活动从来就不是完美无缺的,不同理论也是不同科学家活动的地方性产物,因此它们的冲突很正常,而不是科学哲学家们所谓不可容忍的事情。理论不是我们的统一“世界图景”,而是范围广泛的各种表象和操作。因此,即便实验与理论有冲突,也可能只是与某种理论表象相冲突。科学家在实践中并没有把这种冲突看成很大的事情。历史上科学家寻找“以太”的案例表明,虽然科学家为电磁波不断寻找自己相信的传统性“传递媒介”,但在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给出“零”的结果后,他们也十分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结果。因此,当不相容性无法解决时,它并非像传统科学哲学所言,是科学家完全不可容忍的事情。
其次,不是所有已经显现的问题都能构成科学研究的问题,更不要说那些潜在的问题,还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它们对科学家意味着“无”)。即便进入科学家研究视野中的问题,如果没有机会、能力和资源的支持,也不一定能够成为科学家当下研究的问题。“天空为什么是蓝色”这个小孩子提出的问题,只有当天文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及其资源仪器达到一定水准时,才构成天文学研究的问题。换句话说,没有机会,科学家不会意识到问题;没有机会或者研究条件不具备,即便意识到问题,科学家也无法进行真正的研究。所以,一概而论地、全称肯定地说科学研究始于问题是不能成立的。
在科学实践哲学看来,区分机会和问题对于科学哲学还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从表征主义科学观看,在被接受的理论中,要确定其中还存在哪些问题及其如何构成,主要应对其中隐含的不相容性进行探查,建构新实验以验证理论的内涵,评估理论领域中还不清楚的东西,这些才是理论性任务,值得去做;而实践性地确定哪些问题值得动用现有资源去研究,则是不值得去做的。因为前一种评估是规范性评估,后一种评估是实践性评估,受制于特定的地方性情境,而表征主义科学观只考虑规范性问题。
但在科学实践哲学看来,上述区分是错误的。机会性的研究概念打破了这种区分,因为研究机会的构成与现有的地方性资源和需要的思考是不能分开的。不存在与产生机会的具体境况区分开来的抽象的研究机会,从而也没有独立于特定情境的问题。并且,并非所有理论上可识别的问题都构成研究机会。如果没有人去研究这些问题,不论是因为缺乏资源、旨趣或者合作者,还是因为现在似乎没有解决的办法,那么它们就不会出现在我们当前的研究中(Rouse,p.88),甚至不会出现在我们关注的视野中。
这种对于研究机会的评估关注,就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寻视性关注(circumspective concern)。在这种寻视性关注中,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当下在手的资源和知识状态,例如,现有的可资利用的成果是什么,我们能够在这样的成果基础上做出多大程度的创新;现有可资利用的工具和技巧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我们的条件能够构成多大程度的科学进步。而且,我们的评估依然是实践性的、介入性的。加之体制要求,我们常从自己的地方性情境以及竞争环境的影响来考虑可能的科学研究进展。仔细想想我们周围所进行的常规科学研究和突破性研究,我们不都是从自己身处的地方性情境及其所掌握的技能、资源的前提上进行评估从而推进研究的吗?我们的科学方法论教科书在讨论获取科学问题的原则(即获取的规范性)时,常认为有四项基本原则,即科学性、创新性、需要性和可行性。这最后一条可行性原则,不就是在讲机会、资源的评估吗?可见,我们实际上是一边承认要先行对什么构成问题的机会进行评估,即作可行性评估,一边却在大谈科学研究始于问题;一边把可行性置于基础性地位,一边却又不假思索地认为科学研究始于问题;我们已经破坏了波普尔论题,但我们自己却浑然不知。
即便退让一步,也可以建立一个弱版本的“科学研究始于机会”观。当然,就这种机会观而言,即便是在一种综合的或者整合的视野中,也不应并列观察、问题和机会,不是说它们共同构成了科学研究的起点。我们的观点是,说科学研究始于机会,意味着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整合着观察和问题对于研究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只有机会真正地反映了实际中的科学研究。正是基于资源的机会性寻视,使得一些问题进入科学家视野,足以成熟到变为科学家当下可以研究的问题;机会也使得观察成为有意义的观察。科学的工作确实要研究问题,而不是研究机会。但是机会给出问题,机会挑选问题,机会磨砺问题。同样,机会使得观察成为深入的观察、有意义的观察。当然,有了机会后,还需要有资源:“机会+资源”造就研究路径,形成研究的历程。我们要研究什么,不是由问题决定的,而是由现有条件即基于资源的机会性寻视决定的。问题只构成我们可能要研究的空间,而机会和资源制约着这个可能性空间,给出实际的研究进路,决定着实际的研究起点。
观察、问题和机会共同形成一种科学研究的起点性链条,形成实践性的科学研究的解释学循环:(1)通过机会性寻视,我们在评估自己和同行所掌控的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先前的实践寻找合适的研究项目或者问题;(2)然后通过问题,我们去更加具体地实践,并且观察到新的差异和推进原有的研究;(3)接着在原有研究推进的基础上,我们通过实验室中的科学家社会协商的实践,寻找研究的新机会。
在这点上,SSK学者给出了很好的研究支持。拉图尔和伍尔伽在《实验室生活》中,通过考察科学家在实验室中的交谈,将交谈归结为四种类型:(1)利用“已知事实”:讨论关注的是自多久以来这一现象是已知的;交流的作用是传播信息,有助于重新发现与当下所关注的问题有关的实践、论文和过去的想法。(2)寻求正确的方法并且评估其可靠性:在这种关注中注意到了研究小组获得的投资额度以及避免对赝象(artefacts)进行研究的前景。(3)针对理论问题的项目评估,也涉及学科未来和实验室方向确定等诸多问题。(4)针对其他研究者的竞争性评估。而且,这四种类型的讨论经常从一个主题转移到另一个主题,从一个兴趣中心转移到另一个兴趣中心。拉图尔等人认为,实验室交谈(即话语实践)所关心的主要有:已建构事实、这些事实的个体创制者、事实制作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主张,以及最后,实践的主体和允许操作执行的铭写装置,其中绝大部分涉及的是研究者可能掌控的资源和对可能研究机会的寻视(Latour and Woolgar,p.167,Figure 4)。对于“谁(who)”、“什么(what)”和“怎样(how)”的机会性寻视分别导致了“铭写(inscribing)”、“宣称—争论(stating-arguing)”和“写作—发表(writing-publishing)”这些实验室谈话的更为显明的结果。经过研究,拉图尔等人也认为,研究人员在研究领域中更多地注重研究资源(capital):他们是从可能掌控的资源和对机会的寻视上开始研究的,并且经常从一种资源转移到另一种资源上,这些资源包括“承认(recognition)”、“获得授予(grant)”、“作为资本的货币(money)投入”、“设备(equipment)投入”、“大量的数据(data)产出”、“论据(arguments)”和“论文(articles)”,以及“正式的宣读(reading)”,从而机会和资源获得了类似解释学的循环(同上,p.201)。
皮克林和塞蒂纳也都认为研究源于机会。皮克林更早地指出,科学家的“研究战略是根据科学家个人以享有的资源在不同的语境下做出创造性探索的机遇而定的”(Pickering,p.11)。每一个科学家在选择和处理问题时都拥有自己独特的资源,这既包括物资设备方面的,也包括职业训练和专业技能方面的。这些资源将决定科学家在面对问题时会采取怎样的措施来进行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总是要使科学家自己的资源被最好的利用。塞蒂纳比喻地说,科学家就像修补匠,而“修补工是机会主义者。他们了解自己在特定的地方遇到的重要机会,并且利用这些机会来完成他们的计划。同时,他们认识到什么是可行的,并且相应地调整和发展他们的计划。当行动起来时,他们不断从事生产和再生产某种中用的物品,使其成功地符合他们暂时决定的目的。……谈及研究的机会主义并不是表明科学家在他们的做法中是无系统的、非理性的或以职业为导向的,……机会主义,表示了一种过程而非个体的特性”(塞蒂纳,第65页)。科学家在实验室中所做的工作与织补工类似,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资源、技能和机遇。因此,是机会而不是问题在科学研究中特别是科学研究的起点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皮克林也指出,这种机会主义虽不能解释所有实践中的问题,但它是针对新传统如何生长而言的。在皮克林的争论案例研究中,最能体现他的“研究中的机会主义”模式的是1974年11月新发现的J/Ψ粒子及其所引起的对该粒子解释的“色”与“味”之争(王延锋,第102页)。皮克林认为,是新老两派物理学家所占有的文化资源的差异,决定了他们在上述问题上所持意见不同,从而研究起点也不同。他指出,欧洲研究中心的Mary Gaillard和美国哈佛大学的Alvaro De Rújula拥有不同的学术经历,在面临一种研究传统向另一种研究传统转换的过程中,他们都只能在自身专业的基础上进行拓展,从而寻找到不同的机会,把握住对于他们是新的资源,分别成为粲夸克和规范场论的积极支持者。这一案例表明,科学家个人在面对选择时,一方面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原有学术背景等文化资源的影响,另一方面这种影响又不是完全决定性的:在面临新的语境时,他们也会努力使自己的研究资源与现有的研究机会相适合。在新的情境中不断调整自己的动机,调整研究的目标和问题情境——这正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观点在支配着研究中的选择,在研究中不断调整,使自己的资源发挥最好的效用。科学家在研究中采取机会主义的方式向他们视野中的自然界开战,对此科学哲学家需要做出恰当的说明和阐释,以帮助我们理解科学家的行为,而科学研究的机会观便提供了一种更好的阐释和理解。
三、“科学研究始于机会”案例:太阳中微子实验、复杂性研究和昆虫飞行测量
1.太阳中微子实验的机会特征
劳斯在探讨平奇所讨论的一个探测太阳中微子实验设计的历史时发现,在这个科学史案例里,什么成为当下能够进行研究的问题,取决于现有资源及如何利用它们的机会把握。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人们普遍相信自然界中的太阳中微子流太小,用现有的技术很难探测到。想要做这种探测实验的最初动力来自一个实验人员,他发展了实验仪器和技术,并且训练了能够直接探测中微子的相互作用的技术人员。在投入相当可观的资源去发展一种中微子探测器后,他开始试图为寻找中微子而做探测,并且也试图谋求一些理论家的支持,来提供关于太阳中微子流的某种预测值,以便作为他的探测目标。到1958年,关于恒星核反应的公认观点发生了一些改变,向少数理论天体物理学家暗示,太阳中微子流有足够的可能被观测到。到1962年,这种可能性已经建基于敏感的中微子探测器的有效性上了。这导致这些科学家通力合作,对太阳中微子流的可能预测值去进行复杂精致的计算。对于公认的认识而言,这里重要的是,在太阳中微子上不存在内在的理论旨趣”。(Rouse,p.87)由于研究仪器的进步而导致的对太阳中微子流的测量,至少不是科学家最初的目标,科学家开始并没有理论旨趣去探测太阳中微子。劳斯看到这段历史后,敏感地指出:对于研究太阳中微子这个方案而言,最初的研究理由并不是问题,而是机会(劳斯原话:“……the original reason for the project was not a problem but an opportunity”[同上])。
2.复杂性研究首先始于经济学的机会主义特征案例
我通过对复杂性科学的研究发现,复杂性研究之所以会从经济学开始,并且结合了计算机编程研究的人工生命研究,而没有从物理学开始,这其中也表现出很强的机会主义特征。
圣菲研究所建立的目的和研究方向一开始并不明确;而且在建立这个机构的开始,一些资深学者的想法也是各式各样,科学家的各种想法在公开和私下场合中不断碰撞、冲突和磋商着,学科整合的方向随着科学家的想法之间的竞争而不断摇摆。而最关键、也是最根本的问题是:这个研究机构究竟应该研究什么。对此学者们的想法五花八门:有的学者力图使这个研究机构成为研究大型甚至巨型计算机的研究中心;有的学者则认为研究任务可能要比这个更宽、目标更高。所以,建所时的研究主旨是从模糊的“新思维方式”经争论而逐渐清晰的——先是学科整合的观点,而后是“混沌科学”,再后是“突现”科学,最后确定到“复杂科学”上。
研究主旨确定后,从哪里介入复杂性的研究实践才算开始了真正的研究?既具有戏剧性的机会主义特征、又具有路径依赖性的是,这样的复杂性或者复杂系统的研究没有大量资金支持是根本不可能进行的。就在研究所四处寻找支持时,一些大型公司也在为经济预测而深感头痛:问题在于经济学建立在简单性的过分简化的模型基础上,因此那些模型即便有巨型计算机支持也无法得到突变的经济学结果。其中某个巨型公司的总裁(花旗银行总裁)希望得到不同的经济学启发,而圣菲研究所也在寻找资助人,希望做出与以往科学不同的东西来打动资助人——正是这样的机缘在这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两个方面的需要结合在一起后,双方都深感遇到了挑战。上述经济学需求刺激和推进了圣菲研究所的工作。事实上,正是与花旗银行总裁的接触机会促成召开了圣菲研究所把复杂性集中于经济学复杂性的讨论会,把阿瑟的“报酬递增”和新的非线性、复杂性经济学的思想推到前台,也把约翰·霍兰的“作为适应性过程的全球经济”报告中所蕴涵的“适应性造就复杂性”的思想推到了前台。
霍兰到研究所工作这件事情也改变了圣菲研究所原来的“复杂性系统”研究,把它变为了“复杂适应系统”研究。因为霍兰使得盖尔曼等人突然意识到他们的研究计划有一个很大的疏漏,即没有考虑这些突现结构究竟在干些什么,它们是如何回应和适应自己所在的环境的。霍兰在适应性概念上默默研究了25年,到57岁时才成为学术明星,其思想变成了圣菲研究所的计划。
上面的范例告诉我们,正是机会促成了圣菲研究所的复杂性研究首先从经济系统的问题开始。我们也看到,事实上具体研究产生的科学知识是具有地方性特征的,没有什么知识可以脱离开具体场合、特定的人;并且都需要某种激励的机会:如果没有霍兰,也许圣菲研究所的复杂性研究就不是复杂适应系统,而只是复杂系统。
3.随着研究展开、受到现有资源和机会的制约而不断修改理论目标的案例:昆虫飞行测量
我们手边也有一个关于科学研究源于机会而不是问题的深具代表性的现实案例。由于这个案例是普普通通的博士生的博士论文研究,因此它更具有广泛性和基础性意义。在这个案例里,研究目标先后有变化;现实条件制约着研究;通过实践还创立了最初谁也没有意料到的新实验方法。这个案例最终证明,是研究者所能够把握的研究机会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2005年,我接触到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一个做光学工程课题研究的博士生,他研究了昆虫飞行的测量问题。这个问题的最初目标是想为微小飞行器研究做仿生研究。平常我们都会对昆虫的复杂飞行技巧感到惊讶:昆虫是如何飞行的?但这个问题最初并不构成科学问题。即便它是一个问题,在我们没有测量工具和仪器时,也无法研究它。我们之所以对昆虫的飞行产生兴趣,是因为想借助于昆虫仿生研究微小飞行器。昆虫能够直飞、悬停和突然拐弯,其动作的动力学特性是什么?在没有合适的仪器之前,这个问题也无法构成研究问题。所以在开始时,研究只是建基于一些模糊的想法上。研究者最初不仅想系统地获得昆虫飞行的数据,而且想建立一个微小飞行器理论。然而经过初步实践尝试后,证明这些目标无法达到。其主要原因是,关于昆虫飞行如蜂的飞行只有经验直观而没有任何理论,而最为重要的是,对如何测量昆虫的自由飞行我们甚至无从下手。构成能够对昆虫空间飞行进行研究的机会取决于多方面因素,其中有无较好的跟踪飞行的观测仪器是最重要的瓶颈因子。因此,建构起一套对昆虫自由飞行进行观测和精确测量的设备仪器,就成了研究昆虫飞行的重要前提。论文作者最后完成的是由两个子系统组成的混合系统:磁场传感线圈测量系统和图像跟踪系统。研究者初步跟踪拍摄了熊蜂的飞行(直飞、悬停和拐弯)姿态,获取了若干相关数据。研究者还通过各种尝试,成功地用在熊蜂翅膀上粘接微型传感线圈来测量熊蜂扇翅角和扭转角的方法,对熊蜂进行了实验。(蔡志坚)由于最后粘接线圈方法的成功实践,这种本来只是试一试的机会主义工作,就成了这个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研究中,由于机会主义研究的成功,它反而构成了研究工作的核心。
以上案例至少证伪了“科学研究始于问题”这样一个全称肯定判断命题。它们也至少说明存在着科学研究始于机会的境况;说明“科学研究始于机会”的观点可能比其他观点更能提供对于科学研究起点的合理说明,并且可以整合其他观点。
四、科学研究始于机会观的意义
科学研究的机会观对于科学研究的意义在于:科学研究是对未知世界的开战;科学研究同时也是一个集体的社会竞争与合作过程,其中每一个科学研究的机构和组织所掌控的科学资源都或多或少有所区别(不仅是量的而且是质的),每一个科研人员也都具有研究经历、能力和实践上的差异,因此,从科学研究的过程上看,实践的地方性、时间性和机会性因素都是在实际上发生作用的,研究者不仅要对此有所了解和评估,而且还要充分地基于这种地方性基础寻视各种可能的机会。机会造就了研究的丰富多彩的特征,机会提供了实际的研究路径。研究人员对于机会寻视的把握,显示出其科学能力的大小和研究修养的高低。
科学研究的机会观对于科学哲学的意义可能至少有三点:
第一,它提供了对于基础主义的、表征主义的科学研究始于问题观的批判性反思。尽管“科学研究始于问题”已经好于“科学研究始于观察”,但是它们的替换仍然在重演着逻辑基础主义层面上的舞剧。“科学研究始于问题”的观点仍然把立足点放置在所有的科学活动都是为提出一个至高无上的理论服务的基础上;它与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相一致,也是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的重要支撑。
第二,无论是科学研究始于问题观还是科学发展的积累观、批判理性主义的科学革命观,或者库恩的范式替换观,都存在着非此即彼的绝对主义阴影,体现着现代主义的整齐划一的特性。而科学研究始于机会观则把科学研究的发展置于某种地方性境况中,认为其从多种不同的、差异化的实验室活动中,机会性地推进着知识的发展。这种观点不仅与真实的科学研究过程更为接近,而且体现了后现代思想的意蕴,因为它更多地提倡多样化、去中心性。机会观使得科学研究的过程变得更加合理、更加真实,从而也更加能够理解了;它为科学研究的多样性和科学、文化的多元化提供了新的理解。
第三,科学研究始于机会的观点并非仅仅是描述性的,它也是规范自然主义的。事实上,要合理地说明和解释科学研究,就要说明真知如何可能有效,说明实践活动的合理进步,而机会的起点观恰恰在这方面给出了科学研究应该如何考虑和如何进行的说明。不过,它所说的合理性和规范性是建立在科学研究是一种活动而不仅仅是表征体系的基础上的,是通过实践活动的规范性来说明科学活动的。它不仅更真实,而且更规范:它不是主张怎么都行,而是把研究置于当下研究的行动者掌握的机会的基础上,基于哪种机会可能给科学家研究带来最大效益而行动和评估的,因为机会是效益寻视性的,其一旦出现便规约着研究、引导着研究。所以,这种规范不是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的,也不是理论优位的,而是视科学为实践和活动的规范性说明。
注释:
① 科学研究始于问题的标准观点来自于波普尔的下述说法:(1)“应当把科学设想为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从问题到愈来愈深刻的问题”;(2)“众所周知,我们的预期从而还有我们的理论,在历史上甚至可能先于我们的问题。但科学只能从问题开始”;(3)“因而科学开始于问题,而不是开始于观察;尽管观察可以引出问题来,不期而然的观察,也即同我们的预期或理论发生冲突的观察尤其是这样”。(波普尔,第317—318页)
② 至少在传统科学哲学领域中目前还很少有人怀疑这一点,这也是中国科学哲学和自然辩证法教科书的标准观点。
③ 关于这个问题的标准的逻辑实证主义观点的提法出自莱欣巴赫,即“概括是科学的起源”,这是由“科学研究的本质是概括”而来的。(莱欣巴赫,第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