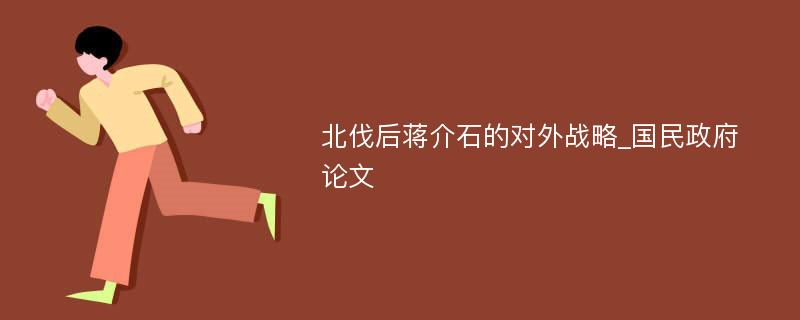
北伐出师后蒋介石的对外方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略论文,蒋介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誓师北伐,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率师出征。7月27日离开广州,经韶关、郴州、衡阳等地,8月11日进驻长沙,27日,离长沙入湖北,9月19日,又从湖南东进江西,11月9日,始进入南昌,其后设总司令部于江西数月,在前线逐步形成了一个新的中心。因北伐所经之地必然遇到的如何对待外侨、外国使节、外国公司、教堂、外国租界等问题,开始具体地介入对外事务,思考有关外交问题,对重大外交事务与外交交涉发表意见。关于蒋介石北伐期间与外交有关的问题,如与列强的关系、对日态度等,过去虽有一些论著涉及,①但系统梳理的文章所见似还不多。这是笔者选取此题加以讨论的一个原因。
一、“打倒帝国主义,绝非仇视外人”
在1926年7月9日的就职宣言等书告中,蒋介石宣称,革命战争的目的,是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推倒军阀与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②这还是此时期流行的一般性的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看不出有何个性与特色,也缺乏具体的政策宣示。但随着北伐军事的推进,蒋的态度和立场就开始明确起来,因在新占领的城市和区域,如何对待其中的外国人、外国公司、教堂、外国舰船等,是一个无法绕过和回避的问题,作为最高军事指挥官,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态度,以便各路官兵有章可循。8月17日在长沙,蒋介石“晚,开外交委员会,至十一时散”③。此会还有那些与会者?所议何事?年谱作者未录,但三天后的8月20日,蒋即在长沙发表了对外宣言与对全体将士的训令,申述对外策略,估计便与这次外交委员会的讨论有关。该宣言表示:“无论何国人士,能不妨碍国民革命之行动及作战者,一切生命财产,中正皆负完全保护之责。若有利用不平等条约,援助军阀,害我国民,致为中外人民所不容,中正纵欲保其友谊,亦恐碍于正义,此则不得不于战前伸明,以求我友邦谅解者也。”一切均取舍于其对国民革命的立场:“其扶持正义,赞助我国民革命者,中正爱之敬之;如其有妨碍我革命运动者,中正攘之辟之。”④同日,蒋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在长沙训令全体将士,申述对外策略,训令称:“吾党起而打倒帝国主义,绝非仇视外人。不但帝国主义国家中之多数痛苦民众,为吾国同胞吾党同志之好友,吾人应诚意待之;即侨居吾国之教徒、商贩,凡非妨害中国国民革命之行动者,吾人亦应加以爱护,一视同仁。”⑤
8月23日,蒋发表《告全国民众促实现必须条件书》,较为详尽地列举了其关于内政外交改革的33条基本主张,其中对外部分7条,依次为:(1)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求中国国际地位上之平等;(2)撤退外国驻在中国内地之海陆军;(3)撤销领事裁判权;(4)收回租界;(5)收回关税自主权;(6)取缔教会学校,收回教育权;(7)严定外国非得中国政府许可,不得在中国自由设置产业,创立银行,发行纸币。⑥这包含了近代以来中国要求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和控制、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基本主张,也是孙中山去世前一直坚持的内容。⑦
可能因为北伐出动后,引起一些外侨的骚动,并反映到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8月25日,外交部长陈友仁打电报给蒋介石,提出保护外侨问题。9月3日,蒋复电陈友仁称:“万急。广州外交部陈部长勋鉴:有电敬悉。关于保护外侨一层,已经通令各军遵照,对于外人设立之教堂及学校等,尤禁各军不得占住妨碍,请转达知照。”⑧陈虽是大革命时期“革命外交”的关键人物之一,但其态度和手段还是理性而平和的,“革命外交”的重心还是“外交”,遵循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而并非逸出常轨的自由行动。⑨
蒋介石对于外交部门从国际惯例出发提出的有关建议还是尊重的,一些维护在华外国人合法权益、维持正常外交礼仪的命令,就是根据他们所请发出的。9月23日,他致电虎门、黄埔守将王萼、方鼎英告知:“顷接外交部漾电称:‘驻北京美国公使麦加利敬日乘省港轮抵粤,依国际惯例外使有优待之礼文,所携各物,有免税之权利,其随行人员,亦一律加以礼貌;此次麦使进出虎门等海口,对于该使以其随员与前往迎接之船只,务请免除一切检查,以重邦交。’等语。合亟电饬遵照办理。”⑩10月12日,因在岳阳的北伐军屯驻教会事,引致美国领事抗议,蒋致电驻长沙的第8军参谋长张翼鹏,令即查明并“转饬该部队迅即迁让为荷。”(11)
关于外国军舰驶入北伐军作战区域的问题,蒋的态度前后有所变化。最初态度较为强硬,下令以武力禁止,其后亦接受了外交部的建议,同意在查明国籍后放行。9月9日,蒋电复岳州驻军团长罗树甲称:“现值戒严时期,对于汉口、岳州间水面交通,业经宣布封锁,无论何国军舰轮船,一律禁止入口。比电罗交涉员转知各国领事在案。该军舰竟于深夜向岳冲驶,自应以武力制止,藉策安全;以后仍仰严加警戒,毋稍疏忽为要。”但到10月中,外交部长陈友仁致电蒋告知,美国驻广州领事致函国民政府外交部,对北伐军限制外舰晚间不许在长江武汉战区航行,并须于白天在指定地点接受检查提出异议。外交部认为,依现有中外条约,外舰出入,未便检查,似可让外舰在指定范围停泊,待查明国籍后,即在晚间,也予放行;并已复函美领。“庶于防范之中,仍寓亲善之意。”同时亦声明,美舰不宜于此时驶入,致受战事之累。接此电后,17日,蒋即致电北伐军武汉方面的总指挥唐生智请其按外交部的意见查核办理。(12)其后,又将此作为统一处理办法通令前方各部队遵照办理,并于10月27日电陈友仁让其就此规定“向外交团切实声明”。(13)
11月19日,蒋在南昌接见外国记者时强调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标。他说,除非中国收回了各国租界,废除了各国在华的治外法权和各项中外之间的不平等条约,中国革命将永不停止。蒋在谈话中还竭力反对北京政府所主张的逐步撤废治外法权的原则,认为不平等条约应立即废止,所有外人监督管理下的海关、邮政、盐政等机关,均应交还中国主持,以完成中国革命的目标。(14)
二、“专对英国,不牵动他国”
1926年10月17日,邵元冲、郭泰祺等到北伐江西前线见蒋介石,“复初对外交有所陈述”,邵元冲也就政治、军事、外交等问题向蒋介石提出了若干意见和建议。关于外交,邵主张应集中反英,对日可联络:“外交上既弗克取一切帝国主义者而摧陷之,则当宜分别缓急,目下除英人为决不能妥协外,日本则欲与英人竞长江商务,颇对我表示好意,宜与之有相当联络,若法若美皆与我现在无利害冲突之点,故亦可予之表示联络,则英人之孤益孤,且有所惮而不敢肆,然后乃能渐就我之范”。(15)这类建议,应当对蒋发生了影响。即使是单独对英,蒋也倾向谨慎从事。在公开场合,他11月中旬、12月底还在大谈将来与帝国主义作战,但对于具体涉外问题的处理,蒋却表现得冷静、谨慎,这自然给外国人留下了温和、稳健的印象。1927年1月6日,得知武汉卫戍部队缴英租界公安局枪械,其他重要机关概由政府派队守卫,英兵撤回军舰,蒋表示:“此大事也,风潮已起,应慎重处之。”(16)
1月7日,英兵在九江残杀民众,蒋介石担心引起民众的激烈反应,急电驻军贺耀祖师长转令各团体,未得政府命令以前,不得自由行动。旋派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前往处理。在当晚召开的政治会议讨论“处置对外方针”时,蒋主张“以和平不辱国为主”(17)。
1月8日,在南昌开政治会议,在“讨论应付汉口外交”时,蒋“主张专对英国,不牵动他国”,并决定到武汉一趟。(18)这时武汉的反英气氛相当浓厚,左翼的《汉口民国日报》几乎每天都有对英斗争的文章和报道,而甚少触及其他列强。12日,蒋到达武昌,13日,到汉口。在汉口对民众的演讲中,蒋委婉地强调了单独对英的必要性,这篇演讲发表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其中关于外交方面的要点为:
一是单独对英,而不要仇视其他各国:“我们此次的外交方略,应该是单独对付英帝国主义,并且要结合英国以外的其他各国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共同打倒英帝国主义。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英国是帝国主义中间的首领!帝国主义的首领打倒了!一切的不平等条约自然都可以废除了!所以我们此次外交应当采取这种方针!对于法、日、意、美及其他各国,暂时不应仇视,而且要联合他们共同来打倒英帝国主义。对付各国!应当特别注意!要有分别。”这种意见被公开刊登在报纸上,日、美等国人士自然能够看到,当然也乐于看到,也必然影响到他们对蒋的态度。
二是要将帝国主义与一般外国人区别开来,不能盲目排外:“要知道压迫我们的,是各国的帝国主义,并不是外国人。外国人在他们本国之内也是同样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所以我们应当联合他们各国国内的被压迫民众,来共同推翻帝国主义。”蒋号召“农工商学兵各界要团结起来,受政府的指挥”,“严守秩序”,“在统一策略之下,去向帝国主义奋斗”。(19)
15日,蒋在武汉与外交部长陈友仁谈外交,17日,参加政治党务联席会议,议决外交宣言案。(20)18日下午,出席武汉各界欢宴蒋总司令大会,蒋在演讲中再次强调农工商学兵联合的必要性,蒋谓现在工潮已引起各界很大的恐慌,认为政府和商学界对农工的利益应特别给予照顾,但也批评了工友对商界的幼稚行为,称农工商学兵是五个兄弟,“商学比较程度高明,生活优胜,就象两个成年兄弟有独立生活,对于农工两个小兄弟要尽一份义务,相与提携,可是工友们举动不免幼稚,就是没有知识,这并不是对农工看不起,如绑人戴绿帽等小孩子毛病,我们当他小兄弟时代,要原谅,明白这一点商界许多恐慌,许多认为困难问题,都可以解决,一旦进而团结在一条战线上,去打帝国主义。至于工友们也要晓得在国民革命时代,对革命不忠实的人,早已跑到上海去了,留在此地都是最可怜的兄弟,都是革命民众,否则绝不会在武汉商界。”并说,“在中国国民革命时代谈不到打倒资本主义,是要打倒外国资本主义。”(21)实际上,对于工农运动对内冲击一般商人、对外冲击英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和一般外国人,蒋都既明确、又措辞谨慎地表达了不同看法,要求民众服从政府,严守秩序。
1月22日,蒋致电程潜、贺耀祖等整饬军纪,令程潜在九江、汉口间的日船上各派宪兵4名,防止在日船上肇事,“如有越轨行动之士兵,即依法严行拿办不贷”(22)。
这种对外稳健的主张,应当与听取了黄郛、张群等人的意见有关。1927年1月初黄郛到南昌,据黄郛年谱称:“先生在南昌时,与蒋总司令,张总参议群等研商克复京沪后财政金融之规划,外交之部署,人员之支配,绅商之联系,以及浙省之策动等等,无不深思熟虑,预为筹谋。”黄郛且受命到上海活动。因这时“武汉异心,奉军及残败之五省联军尚有力,经济中心之江浙,亦恐惧怀疑,外交上英日利害最切己”,为了安抚江浙资产阶级和消除英日等列强对蒋介石过激的疑虑,“非得中外深信其和平稳健而非过激危险如先生者,暗中居沪运筹,不易为功。”(23)黄郛是蒋介石两次专函、并派张群出马从北方请来的拜把兄弟,这时颇得蒋之信赖。
三、“取消不平等条约及收回租界,绝不用武力及暴动”
在1927年3月24日的南京事件后,3月30日,蒋在上海接见外国记者。德国记者问其对于收回租界拟取何种办法,蒋答:“当用和平方法,政治手续,绝非用武力解决者。”31日,接见日本新闻记者团,部分问答如下:问:“对于南京事件,总司令能负完全责任乎?”答:“能。”问:“既负责任,将采如何方法?”答:“须待调查之结果再定。”问:“不用暴力收回上海租界之事,总司令能保障乎?”答:“能。”下午,又在总司令部邀请英美日法等国记者谈话。在谈话中,再次明确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外兵外舰撤出中国等问题。他一方面表示对外侨在南京事件中的损失完全负责,待调查清楚后必给予满意之解决;另一方面,对英美未经任何交涉即实施炮击表示抗议,对某些西报记者不负责任的报道表示不满。蒋说,他在来上海途中,见到外国军舰及兵士甚多,尤其是租界内,有如临大敌、紧张备战之势,很受刺激,租界本来是我国领土,租界当局这样做,势必加剧紧张局势,故对租界当局不得不提出警告。“若各国仍用十九世纪之政策,采用军舰兵队之武力对付中国,不但不能有益于租界及侨民之生命财产,而反有害。因现在之中国,与十九世纪时之中国不同之故也。我国民革命军所过之地,各友邦均可不必派兵,因我国民革命军对于外侨生命财产,负完全保护责任。……我国民革命军对于各种武力及示威行动,毫不恐惧。”并就外交问题发表两点非正式声明:一、取消不平等条约及收回租界,绝不用武力及暴动,当由中央政府采用外交正当手续办理,各国侨民不必恐惧;二、国民革命的目的,是求国际地位之平等,各国如能谅解此点,自动取消不平等条约,归还租界,自当认为友邦。即以前以不平等待我者,只求其能变更以前之主张,亦可和好亲善。租界当局现在的做法,及一些外资工厂拒绝工人复工,民众甚为愤激,如不改变做法,将来发生暴动,应由租界当局负全部责任。国民革命军有责任保护租界中的华人,但又不能通过租界,是不合情理的。“总之,外兵外舰一日不撤退,国民革命军对于外侨之生命财产,一日不担保。甚望各友邦从速改变方针,俾得彼此早日修好。”(24)不过,一个读者容易发现的情况是,蒋介石发表这类反帝、爱国、维护主权的言论,一般是在公开演讲、宣言、公开会见外国记者的情况下,而与私下会晤的言论有所不同,但就其一生的立场和言行看,应当还是反映了其民族主义的基本目标。
蒋承诺保护外人生命财产,不树敌过多,宣称不以暴力方式改变租界现状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做法,含有对列强妥协的成分,与国民革命阵营内激进派的主张和做法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尤其在后期,他在外交方面我行我素,对政府和党的权威造成了严重损害。但如果撇开党派、政见的分歧,从单纯北伐作战的策略和利害而言,作为北伐军事方面的总负责人,这样处理,对于顺利推进北伐军事,集中有限的力量打倒国内的北洋军阀,还是有利的、必要的。问题在于,这时蒋以个人的意志支配国民革命、日益站到联俄联共政策的对立面、以血腥暴力方式对付左翼和工农民众的行为与他在外交方面并非完全错误的做法交织在一起,他对外策略合理的成分与迎合帝国主义分化中国革命、防止中国“赤化”的一面纠缠重叠,而使人们很难将其合理的一面从中剥离出来。
四、对日联络,有所期待
据1927年8月17日日本首相田中的一份谈话,蒋介石别有怀抱,暗中与日联络的动作是比较早的,谈话称:“蒋于广东起事之际,即派使者前来致意声称:不久即与共产党断绝关系,尚祈关照。”(25)
1926年11月,日参议员藤村义朗和池田长康到南昌拜访蒋介石,劝蒋派人去日本政界游说。1926年12月,币原外相派其亲信、外务省条约局长佐分利贞男南下,到上海、武汉、南昌、广州等地访问国民党要人,12月中,在武汉见陈友仁,经黄郛介绍,在南昌会见了蒋介石,感到蒋是国民党中“最好打交道的人”。(26)
1926年底,日本陆相宇垣一成派铃木贞一前往游说蒋介石反共,黄郛通过张群安排铃木到九江与蒋介石会见,宇垣交待铃木的使命是“中国如果和共产党携起手来进行赤化,日本将陷于困境。你去游说蒋介石,让他断绝和共产党的关系,搞纯粹的国民革命。”蒋对铃木表示:“为了保全东亚,中日两国的合作是必要的。”“我到南京后就正式表明态度,你等着瞧吧。”(27)
1927年1月20日,吴铁城代表蒋介石秘密赴日,交涉中日间政治问题,“向币原外相担保中国人永不反日”(28)。
1月25日,蒋在庐山接见日本驻九江领事江户千太郎,会晤后,江户也电告外相说,蒋介石谈话明确表示,他非但不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将尽可能尊重它们,并保证承认和如期偿还外国借款,及充分保护外国投资的企业。(29)
1月26、27日,蒋介石在庐山与日本海相财部彪的老相识、他留日时的老师小室敬二郎会见,据日本学者臼井胜美的书中披露,谈话中涉及许多重要问题,如对英、对苏俄、对收回租界的态度等,最主要的是对日关系,包括对中国东北与朝鲜问题的态度。(1)对英问题,蒋介石谴责了英国以保护上海租界为由对上海的出兵,表示不会将汉口的英租界还给英国;(2)对苏俄,蒋强调,国民政府采取委员制,对于鲍罗廷等苏联顾问的提案,国民政府作自主的决定,国民政府不但没有受苏联利用,更没有接受它的指导。这无疑向列强传递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即正在蓬勃崛起的国民党政权并无意成为苏俄的附庸;(3)对租界问题,蒋表示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待底定东南后,才提出合理收回它的提议;(4)中日关系,小室问蒋,中国能否与日本合作,蒋答:中国人很难了解日本的真意,不过能照币原外相的演讲实行就很好。小室问蒋对“满洲问题看法如何”,蒋答:“根据我们的主义,满州[洲]也应该收回。唯对日本来讲,在政治经济上,满州[洲]问题非常重要,我们又了解日本人在日俄战争中流过血的感情问题。我们也知道孙文先生对满洲问题有特殊的了解,因此我们觉得对这个问题应当予以特别的考虑。”小室又问革命军是否在支持朝鲜的独立运动,蒋答复的大意为主义上我们应该这样做,但实际上还没有给予任何援助。故臼井胜美对此的评论是,“蒋氏对于日本认为最重要的满洲权益和朝鲜独立问题,非常慎重。”(30)另有记载显示,蒋介石在小室面前对中日关系作了积极得多的表示,而对苏俄则表示疏远:“我不知道俄国援助是出于对革命的理解,还是为了利用我们”;“苏俄不可能重现于中国”;“如果日本正确评价我们的主义和斗争,我将乐于同日本携手”。(31)
2月15日,戴季陶受蒋的委派启程赴日。17日抵门司,对日本记者团称,此行“乃以国民党同志资格求日本朝野谅解本党真意”。2月26日,戴季陶访日外务省,与出渊次官、亚洲局长木村等会晤。戴称中国革命决不采过激手段,俄人援助只为精神的,说国民党赤化者全属误解,并力说中日必须提携,望日本朝野谅解与援助。(32)
3月10日晚,蒋在南昌宴请日本最大在野党议员、后任满铁总裁的山本条太郎。11日,蒋与山本谈中日关系,对山本所提“中日亲善”,蒋表示,“日本如欲与中国亲善,须从根本上着手,即对高丽台湾,亦应去其羁绊。诚能扶助弱小民族,则岂特中华民国愿对日亲善而已哉。”(33)
而蒋所期待的日本的“正确评价”在此前后似乎都有收获,1926年12月中旬佐分利贞男到汉口拜会陈友仁并到南昌见蒋后,向外相币原报告说,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并没有像所宣传的那么偏激。(34)币原断定,能取代“无能的北京政府”统治“除满洲之外”的中国本土的,非蒋介石莫属。(35)1927年2月间,币原对英国大使说,在理论上蒋介石虽然很激进,但其行动却是很稳健。
3月24日,发生英美军舰炮击南京事件,日本军舰未参与。蒋介石适在自安庆赴南京途中,得讯后当即派参议林石民至日本领事馆,表明处理态度并请代为转达英美当局:“刻由中国军舰利通前来报告,云在南京之英美军舰向南军开炮,其原因未详。但我军对英美两国并无敌意,蒋公拟亲赴南京,负完全责任,解决此事。故切望英美两当局,立即停止炮击。因目下通信机关断绝,无法将此意传达英美当局,请由日本官宪代办此事云。”(36)27日,又派原南京交涉员林赤民访问日总领事森冈,对南京事件表示遗憾。(37)
故在事件之后,“币原外相却坚持其不出兵的方针”。他认为这是欲使蒋介石垮台的国民政府内部激进分子的政治阴谋,采取强硬措施“等于促进稳健派的蒋氏没落,帮助激进分子掌握政府和军队的实权,因而牵制英、美,极力拥护蒋氏立场”(38)。这从美国驻日大使麦克维夫(Charles Mac Veagh)3月28日晚8时向国务卿的报告中可以得到证实:“今天下午同日本外相会晤时,他宣称日本政府不因南京事件而改变对华政策,日本政府目前认为派军队去中国是不必要或不明智的。外相相信,蒋介石强烈反对这些针对外国人的暴行,将竭尽全力予以镇压,维护秩序;他认为南京暴行是广州派中企图使蒋介石丧失信誉的激进派挑起的;日本已劝告蒋介石,他和广州政府的前途取决于维护秩序,镇压暴乱,如果维持不住秩序,便意味着蒋介石和广州政府的完蛋。外相相信,蒋介石既愿意也能够维持秩序。他认为目前任何强国采取压制措施都是错误的,因为这只会帮助蒋介石的敌人,并使广州派中的激进派得以控制广州政府和军队。”(39)这也是日本方面较为一致的意见。3月28日,日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松井石根向币原外相提出应对南京事件的对策:“如果革命当局至今仍不自觉深刻反省并迅速采取公正文明的态度的话,那么帝国也不得不预告:帝国不得不放弃从来之隐忍,与列国一致进而采取自卫手段。关于南京事件的解决,基于致力于拥护蒋介石等南方派中的稳健分子而将责任归之于该派中过激分子即共产派之旨趣,在英美各国与蒋介石之间进行调停斡旋,致力于和平解决的手段。(中略)为达到上述目的,帝国政府根据非正式手段,让在中国南部各地驻在的文武官员图谋南方稳健分子的团结特别是促进与国民党右派的提携,如果有必要,可提供其所需要的援助。”(40)4月7日,陆相宇垣对总理若槻建议,“压制并驱除长江上游及南方之共产派,主要由列国协同承担以军费及武器供给南北两派的稳健分子。”(41)
五、不满外交现状与争夺外交主导权
对外交问题,率师北伐的蒋介石是否应当发言?有多大的发言权?是根据外交部的要求具体予以配合,还是全权处置不受政府外交部门的约束?北伐三个多月后,广州国民政府对于主要是军人身份的蒋介石在外交方面表现出来的过于浓厚的兴趣似乎产生了警惕,“10月30日上午11时。陈(友仁)氏宣布:国民党会议最近通过一项关于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决议,外交职权集中于正式委任的广州外交部长之手,政府不受蒋中正等军事将领未得陈氏部门同意而订立的外交协定及盟约的约束。”(42)
但政府的这类决议似乎从来都不能对蒋介石发生作用,其后的几个月间,蒋介石的外交活动反而日渐频繁,且对广州—武汉政府的外交现状越来越感到不满,如1926年12月27日,蒋介石即表示:“外交、财政亟须改进,党务来日大难,革命不患强敌,而患内讧,如何能消弭此衅耶。”28日,又因“党事纠纷,外交无主,财政奇窘,孙传芳转猖狂,殷忧殊甚。”(43)
1926年12月31日,从广州出发的国民党中央代主席张静江、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及顾孟余、丁惟汾、何香凝等到达南昌,蒋介石将这批人留下,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住南昌,而不是到武汉与此前设立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会合,蒋介石挟中央以令天下的意图开始彰显。1927年1月7日,蒋介石、张静江等指令在武昌组织政治会议武昌分会,以取代临时联席会议,并明令归南昌政治会议领导。但10日的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却认为,武汉已有代表中央之机关,不必再成立政治分会。1月9日,蒋介石从南昌抵武昌,1月18日离鄂返南昌。这次武汉之行,应该是促成蒋介石对武汉中央与鲍罗廷愈加不满,决计走向破裂、公开反共的重要一环。谁代表正统的国民党中央?武汉、南昌间展开了公开的较量,双方互不买账,国民革命阵营实际上形成了武汉“激进派”与南昌“稳健派”对峙的两个中心,这种抗争不仅涉及政治话语权,同时也涉及外交主导权。
1月28日,中共在对时局宣言中,揭露了帝国主义诱惑国民革命阵营中的“稳健派”、“温和派”,以分化国民革命的企图,说以温和的方法对付帝国主义的主张是一种反革命的行为:“帝国主义者向中国国民运动的势力进攻,不但用直接的和间接的武装势力硬的方法,而且还用软的方法,从国民运动营垒中诱惑所谓稳健分子所谓温和派,和他们妥协,以打击所谓急进派,……破坏国民运动的联合战线。”对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决不是什么稳健温和方法能够得到的,……有些人提议可以用温和稳健方法向帝国主义者收回权利,不取急进的革命行动,这种反革命的说话分明是帮助帝国主义者消灭中国的国民运动。”(44)
2月上旬起,这种争执已完全公开。8日的《汉口民国日报》发表题为《要求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立即迁鄂》的社论,11日的社论明确喊出“扩大党的威权!严肃党的纪律!铲除一切封建势力,完成民主统一的革命运动!”等口号。13日,报纸对蒋介石的外交高参黄郛、王正廷厉声斥责,说对这些混入革命阵营的北洋走卒要“慎守门户,谨防扒手!”17、18日发表邓演达的代社论,批评有人欲“包办革命”,“以拿破仑自居”。21日,武汉方面决定以中央党部暨国民政府名义在汉开始正式办公。22日,南昌方面开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在党部与政府未迁以前,武汉不得以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名义另行办公。24日,武汉国民党员15000余人召开大会,要求统一党的指挥机关,拥护革命政府的统一外交。3月3日,南昌方面决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于本月6日全部迁鄂”,参加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在此背景之下,3月7日,蒋在南昌总司令部发表演讲,对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批评他“联合日本放弃联俄”的内容,不予承认。他说,“这种话有没有,各位同志相信不相信,当不待我言。我们总理为什么要联合苏俄,就是要求中国自由平等。苏俄既不放弃以平等之精神待我,我们哪有放弃联俄政策之理。至于日本,如果对我中国一天不放弃他的侵略政策,那我们就没有一天能和他妥协的。我们外交政策的立足点,是求中国自由平等,无论哪一国能以平等待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同他联合。对于苏俄也是抱定这个态度。”继之他对当前的外交政策作了阐释,他说:“现在我们的外交政策,是要使得各国谅解中国的国民革命,不与本党冲突。所以在广东联席会议同政治会议就决定,各国如果没有来压迫我们、妨害我们革命的时候,我们应该取一种和平的态度。我们现在的外交方针,同本党的政策,就是这样的。”(45)这个话,也并非毫无根据,对日联络的主张,在一段时间内,是苏联、中共、国民革命政府一致的外交策略,(46)但这时却成了蒋对付武汉的一种托词。
3月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开预备会,但蒋介石、张静江、朱培德未到。10日,会议正式开始。会议期间,“提高党的权威”、“反对军事独裁”的口号引人注目。至17日,二届三中全会共召开七次会议,形成了所谓指导机关之统一、外交政策之统一、财政政策之统一、革命势力之统一四大政策。《汉口民国日报》在3月中旬公开发表了《各级党部声讨老朽昏庸的张静江》、《长沙各界一致通电反蒋》、《蒋介石竟反对恢复党权》等文章,稍后又开始了对蒋介石外交活动的公开声讨,特别是对蒋介石“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谋妥协”的指控,要蒋“不要上了日本人的当,去替帝国主义者压制反对帝国主义的空气,不要蹈北洋军阀的覆辙,对于争外交的群众格杀勿论。”(47)但实际上对蒋介石已无任何约束力,倒是为蒋介石在日、美方面作了义务宣传,使他们更清楚了在中国国民革命内部应当争取和利用谁,打击和压制谁。(48)同时,可能也促使蒋介石更少了痛下杀手的顾忌。
3月26日,蒋介石到上海,向公共租界工部局来送特别通行证的西探表示,“保证与租界当局及外国捕房取得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与秩序。”27日,日本领事来见,“有质问宁日侨死伤意”。蒋叹曰:“奸党捣乱,使外交纷扰益甚,可痛可叹。”“晚商议外交事。”(49)30日,遵外相币原之令,日驻沪总领事矢田会见蒋介石,要求“对维持上海治安必须加以特别深刻的考虑”,蒋表示“充分体察尊意,定当严加取缔”。(50)
武汉国民党中央一再强调外交统一,上海这边蒋介石的外交活动却更见频密,包括前述的接连会见各国驻上海记者,发表对外交的“非正式”谈话。4月1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议决,通电蒋介石及各军事长官,须尊重二届三中全会议决之外交、财政、交通统一各案,违者以反革命论。(51)2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蒋介石“克日离沪赴宁,专任筹划军事”,“对于外交,未得中央明令以前,切勿在沪发表任何主张,并切勿接受任何帝国主义口头或文字之通牒,以强迫帝国主义直接与国民政府交涉”。同日,严电申斥蒋介石擅委郭泰祺为上海交涉员,下令拿办郭泰祺并开除其党籍。(52)
3月31日,日本外相币原训令驻沪总领事矢田,日本政府认为蒋介石“对于管束共产党的跋扈缺乏信心”,应促其迅速采取反共行动。(53)4月1日晚,矢田向蒋介石的代表黄郛转达了币原的意旨,“促蒋深刻反省与注意。”(54)4月2日,黄郛向矢田转达蒋介石的意见,对日方的意见“表示谅解和衷心感谢”,并称“整顿国民党内部已下决心,现在正召集将领仔细讨论中,一俟准备就绪,将立即断然采取行动。”黄透露蒋的具体计划首先是解除工人武装,然后由在沪的国民党中执监委员“取代武汉派,夺取中央党部,排除共产党。”(55)3日,蒋介石发表了一个支持汪精卫复职的通电,称“自汪归来,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皆在汪指挥下统一于中央,本人独司军令,俾专责成。”(56)这完全是在虚与委蛇以麻痹对手了。
日本一方面在上海加紧与蒋介石的联络,另一方面则对其厌恶的武汉政府给了狠狠的一击:也是在4月3日这天,因2名水兵与人力车夫的争执,日舰水兵竟武装登陆,制造了汉口“四三惨案”,很难说,这与上海的促蒋破裂的行动是毫无联系的。4日,汉口方面的唐生智亲访日本总领事高尾表示歉意,并声明极力维持治安,请日本撤退登陆水兵,遭到日总领事的断然拒绝,并对汉口实行经济封锁,所有在汉日人工厂、银行、会社、商店一律停业,日方的亲疏向背已再明显不过。
接下来,在4月6日,蒋介石命令,从本日起,所有武汉发来之电报、函件,武汉各报“妨碍革命”之记载及总政治部等各种“反宣传”广告,一概不许刊登及转载;如有违抗者,在戒严期内,应按戒严条例惩办。(57)12日,四一二政变发生。13日,蒋发表《告中国国民党同志书》,反指是中共打乱了国民党的外交策略。其中提到,“国民政府外交政策,先从集中对付一国着手,今各处事件发生,往往牵涉多国,投入国外特殊国家及特殊国体(疑为“团体”——引者)之圈套,不顾利害,听人指挥,破坏统一外交之责,谁实负之。”此处应是指此前的“集中对英”政策,所谓特殊国家和团体,当是影射苏俄和共产国际,因在4月18日的《建都南京告全国同胞书》中,蒋说中国现在有三条路,一条是“跟着共产党走,受国外特殊团体的指挥,以实行赤色恐怖的专政”,再次提到“国外特殊团体”,意思十分明显。(58)蒋攫夺国民革命的果实以为禁脔、反苏反共、与日美亲善的意图,已不用再作任何遮掩了。
这一结局,在激进派看来,是蒋与帝国主义勾结镇压左派,葬送国民革命;而在蒋看来,是不想因为激进派的冒进而影响他的北伐大业。但蒋的亲日主张很快就遭遇到严重的挑战,1927年4月田中内阁上台,对华转取强硬政策,希望蒋的攻势局限在南方,而不触动日本有特殊利益的东北和欲扩大势力的北方,与蒋北伐统一的民族主义诉求发生了正面的冲突,遂有济南事件及其后一系列针对蒋领导的国民政府的中日冲突之发生,蒋对日本虽日益不满和怨恨,但因国内问题的困扰而一忍再忍,最终在日本无休无止的紧逼之下,忍无可忍,终于走上对日全面抵抗的道路。
蒋的目标是在他的掌控下的统一建国,为此不惜与一切在他看来是阻碍和干扰他此一目标的力量宣战,而不会受意识形态的信仰所左右,也不会被传统道德或者革命的道德所约束,蒋为此举起他的右手,毫不留情地将中共和国民党左派打翻在地,但不旋踵间,又举起他的另一只手,将追随他反共但不赞同或不拥护他独裁的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胡汉民等一个一个打下去,而似乎没有片刻的犹豫和内疚。蒋的进攻北洋军阀、反帝统一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潮流,但蒋强烈的帝王思想,只许我负人不许人负我的极端、褊狭的个性,骨子里对下层民众的漠视,又使他无法成为一个符合近代大多数中国人意愿、真正为中国人民认可和接受的领袖。中国还没有成熟的生长近代民主政治的土壤,但中国人民也不喜欢一个不能改善民生,又将民主践踏于脚下的领袖。
(作者附记:本文为广州市黄埔军校重点研究基地资助项目。初稿提交2007年11月3-4日在东京大学召开的“清末中华民国初期的日中关系史——协调与对立的时代1840-1931”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承陈三井、家近亮子“座长”及黄自进等先生点评和指教,会后与日本中央大学客座研究员、天津师范大学高文胜教授合作进行了修改,并蒙在日本樱美林大学任教的张玉萍女士译成日文,将收入日方出版的论文集,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①就笔者所见,值得提到的有:牛大勇:《北伐战争时期日蒋关系的演变》(《江海学刊》1987年第2期)、郭曦晓:《评蒋介石1927年秋访日》(《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申晓云:《四一二前后的蒋介石与列强》(《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臼井胜美:《日本对中国不干涉政策的形成》(《近代日本外交与中国》,陈鹏仁译,台北:水牛出版社,1986年)、陈鹏仁:《北伐、统一与日本》(《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8年)、李恩涵:《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1925-1931》(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高文胜:《武漢国民政府期における陳友仁の对外交涉——南京事件と漢口事件を中心に—》(《情報文化研究》第14号,2001年)及《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の对日政策》(《情報文化研究》第18号,2004年)。
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年,第611页。
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653页。
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655页。
⑤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二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495页。《蒋介石年谱初稿》将之列入8月28日活动中(见该书第665页),确切日期待查。
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658页。
⑦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9页。
⑧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673页。
⑨参见李恩涵:《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1925-1931》,第65、78、79页。以后在多处场合,陈友仁均声明或要求切实保护外侨生命财产。如1927年1月6日对驻汉英领事、法领事的谈话,12日电各省军民长官,24日对各省政务会议的通令等。这实际上成为国民革命政府的一项基本外交政策(参见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二册,第553、557、561页)。
⑩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700-701页。麦加利应是这期间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John Van A.Macmurray)的旧译。
(1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727页。
(12)《蒋总司令令罗树甲严禁外国军舰入口电》、《蒋总司令嘱唐生智照外交部函意对待外舰电》,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十三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第232、244页。
(1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765页。
(14)参见李恩涵:《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1925-1931》,第52页。关于11月19日的这次谈话,《蒋介石年谱初稿》只有“回总部,接见自由西报记者”一笼统记载(《蒋介石年谱初稿》,第799页)。
(15)《邵元冲日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87页。据有关史料,当时冯玉祥甚至主张“亲日”。1926年11月4日,冯致函黄郛称:“现在先将以往无智识之过失,一笔勾去,而奋然不顾的努力革命,……至对于时局,则唯有击吴、和阎、联奉、亲日八字作根本。我兄对于国内外大局,知之极详,尤盼指示,盼帮助也。”(沈云龙编:《黄膺白先生年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第257页)
(16)《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台北:“国史馆”,2003年,第12页。
(17)《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第12-13页。
(18)《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第13页。
(19)《蒋总司令在汉口欢迎大会演说词》,《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5日,第3张第2页(此演讲对了解这期间蒋的外交、政治主张相当重要,但《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似未见收入)。
(20)《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第19、20页。
(21)《武汉各界欢宴蒋总司令纪盛,蒋总司令之演说词》,《汉口民国报》1927年1月20日,第3张第1页。
(22)《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第29页。
(23)沈云龙编:《黄膺白先生年谱》,第268页。
(24)《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第151-163页。并参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7年1-6月份卷,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7年,第441-443页。
(25)《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4页。
(26)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5卷“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11页。
(27)参见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日中友好の捨石秘録土肥原賢二》,东京:芙蓉书房,1972年,第196-198页。
(28)述之:《目前革命右倾的危险》,《向导》周报,第190期;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二册,第560页。
(29)参见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8页。
(30)臼井胜美:《日本对中国不干涉政策的形成》,台北:水牛出版社,1986年,第35-37页,访谈原文载于《时事新报》1927年2月9日。币原外相演讲应即指1927年1月18日币原在日本议会发表之外交政策演讲,表示尊重中国之主权与领土,不干涉中国内政(演讲内容原文可参见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下,东京:原书房,2007年,88-92页;中文译文参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7年1-6月份卷,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7年,第93-96页)。
(31)United Kingdom,Foreign Office(F.O.),405,Vol.252,pp.431-433,转引自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5卷,第339页。
(32)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二册,第568、574页。
(33)《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第118-119页。
(34)参见臼井胜美:《日中外交史——北伐の時代—》,东京:塙书房,1971年,第19-22页。
(35)参见家近亮子:《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王士花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63页。
(36)参见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Ⅰ第一部第一卷,东京:外务省,1989年,第514页。另见《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第138-139页。
(37)参见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Ⅰ第一部第一卷,第519页。
(38)臼井胜美:《日中外交史——北伐の時代—》,第37-42页。
(39)《四一二前后美国对华政策函电选译》,张文质、牛大勇等译,《历史档案》1988年第2期。
(40)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Ⅰ第一部第一卷,第520页。
(41)《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第135页。
(42)《驻华代办麦耶致国务卿电》,《北伐战争发动前后美国对华政策函电选译》,牛大勇译,《历史档案》1986年第3期。
(4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870-871页。
(44)《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宣言》,《向导》周报,第186期。
(45)《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第108-112页。
(46)参见于永:《论北伐时期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3期。
(47)《湖南救党运动之激进,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0日,第1张第2页;《责难蒋介石》,《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4日,第2张第2页;《莫把上海当南昌》,《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31日,第1张第1页。
(48)黄郛夫人沈亦云称:“上海总领事矢田在宁汉对立时,与汉口总领事高尾都同情南京的。”(《亦云回忆》下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第350页)
(49)《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第147页。
(50)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二册,第589、590页。
(5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009-1010页。
(5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908-911页。
(53)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Ⅰ第一部第一卷,第532-533页。
(54)参见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Ⅰ第一部第一卷,第547页。
(55)参见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Ⅰ第一部第一卷,第548-549页。
(56)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二册,第593-595页。
(57)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二册,第595-598页。
(58)《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书告,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4年,第31、44页。
标签:国民政府论文; 汉口民国日报论文; 蒋介石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武汉论文; 国民革命军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武汉生活论文; 台湾国民党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历史论文; 南京国民政府论文; 陈友仁论文; 汉口论文; 汉口租界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