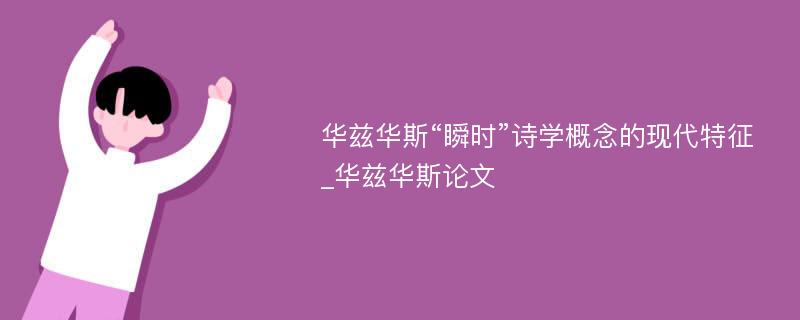
华兹华斯“瞬间”诗学观念的现代性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兹华斯论文,诗学论文,现代性论文,特征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文学发展史上,一个文学流派或思潮的发展往往是对前一个文学流派或思潮的强烈反拨。对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研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批评就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例如,浪漫主义诗学认为,诗歌是“宁静回忆起来的感情”[1] (P16),现代主义文学批评则认为,诗不是感情,也不是回忆,也不是宁静,而是许多经验集中后的东西,而且人的创作不是放纵情感,而是逃避情感,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等等。[2] 自上个世纪60年代起,人们对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批评观点开始有了新的认识。除了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不同之外,人们所看重的是现代主义怎样成为浪漫主义的继续。科尔默德认为,20世纪现代派的象征主义诗学直接来源于浪漫主义诗人对诗歌的崇拜。[3] 弗莱认为,浪漫主义作为一个思潮并没有在20世纪初结束,而是一直延续到现在。[3] 显然,现代主义文学批评对浪漫主义文学思想的批评有过激之处。布鲁姆将这种对浪漫主义的批评视为受到浪漫主义影响之后的一种逆向反应,即“影响的焦虑”[3]。如何评价浪漫主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通过简单的肯定或否定就能做出结论。其实,浪漫主义文学中已经孕育了许多现代主义文学的因素,华兹华斯的“瞬间”诗学概念就具有明显的现代特征。
一、“瞬间”与“顿悟”的客观机制
“瞬间”是华兹华斯在其长篇传记史诗《序曲》中提出的一个诗学概念,用来指因为某种东西引起作者对过去生活的回忆,通过这些回忆,作者在不经意的刹那间领悟到更高层面的意义。[4] (卷12,208行)自从华兹华斯提出“瞬间”诗学这一概念以来,许多批评家,特别是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批评家提出了一些与之相类似的看法,如斯蒂文斯的“觉醒的时刻”(moment of awakening)、伍尔夫的“敏锐的瞬间”(exquisite moments)、庞德的“魔幻的瞬间”(magic moments)以及乔伊斯的“顿悟”(epiphany)等等。[5] 综合这些概念,笔者认为乔伊斯的“顿悟”思想更有代表性,所以暂且借用这一概念来代表整个现代派文学批评关于精神显现这一现象。“顿悟”本是宗教术语,是指突然的精神感悟。在基督教中它是指初生的耶稣在东方三贤(the three Magi)面前的突然显现。[6] 后来乔伊斯把该术语移植到文学领域。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的初稿中他首次对这个术语作了如下界定:“所谓顿悟,指的是突然的精神感悟。不管是通俗的言词,还是平常的手势,或是一种值得记忆的心境,都可以引发顿悟。”[7] (P211)
在对“顿悟”这一文学现象的研究中,现代主义文学批评首先强调的是引起“顿悟”的东西的“卑微性”(trifleness)。莫里斯·贝佳(Morris Beja)在对“顿悟”和“幻想”进行对比时,提出了“顿悟”的“一般性”标准,即“顿悟”是由琐事或微不足道的东西引起的。他说,“但丁在《神曲》最后看到上帝光彩焕发,那是幻想;而现代主义的顿悟与引起顿悟的原因是不成比例的。”[6] 不难看出,对“顿悟”卑微性的强调实际上突出了“顿悟”的具体可感的客观现实性。罗伯特·兰波(Robert Langbaum)曾指出,“17世纪英国诗人沃恩的诗行‘几天前的晚上,我看到永恒/就像一个纯净的,无穷无尽的光环’不是‘顿悟’,而是一个对幻想的陈述,因为我们感觉不到任何东西,永恒也只不过是像一个大光环而已。”[6] 兰波进一步指出“顿悟”是由外在的事物引起的,但同时也离不开对这些事物的观察者。被观察事物的物质性(whatness)的瞬间放射(radiance)引起观察者心灵的发光(luminousness of the mind)。随着放射的不断强化,美的崇高的品质,鲜明的审美意象等便在观察者的脑海中产生了。值得注意的是,物质性的放射和心灵的发光是很难区分的,因为物质性的发光是一个内在化的过程,即观察者对物质性深入体会的过程。当这一过程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观察者所观察的事物便成为一个既是客观化也是主观化的意象。
“顿悟”的卑微性及其产生过程,可以在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得到充分说明。这个作品塑造了一个为追求高尚的艺术事业而决心摆脱社会、教会和家庭桎梏的青年艺术家斯蒂芬的形象。在他的早期生活中,他所目睹的是都柏林肮脏、狭窄和昏暗的街道,听到的是醉汉们嘶哑的吵闹声以及身穿长袍、涂脂抹粉的妓女们在大街上招揽客人的叫声。随着主人公意识的渐渐觉醒,他视野中经常出现的是大海或飞鸟的意象。在小说第四章结尾处,他注视着一只飞鸟。飞鸟自由的翱翔不断投射到主人公的灵魂深处。他从飞鸟身上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力量,“骤然展翅使他获得了自由,内心的呼喊使他情绪激昂。”他在鸟的身上看到“一个像鹰一般的人在大海上空正朝着太阳飞去”,他决心像古代希腊神话中那位擅长建筑和雕刻的能工巧匠德勒斯那样展翅飞出迷宫,“去生活、去犯错、去跌到、去胜利、去从生命中再创生命!”[7] (P172)
与现代主义作家相比,华兹华斯作品中的“瞬间”内容也突显了客观物质性的一面。根据柯勒律治在《文学传记》中的记载,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中的分工是从“日常生活”中选择一些事物,以此引起我们的类似超自然的情感。华兹华斯本人也承认他的诗歌通常选择微贱的田园生活作题材,他觉得在这种生活里,我们的各种基本情感共同存在于一种更单纯的状态,因此能让我们更确切地对他们加以思考,更有力地把他们表达出来。[1] (P15)华兹华斯这一文学思想与他的宗教观念也有直接关系。他认为人和造物主之间的沟通只有通过“以少喻多”才能实现。在“随笔,对序言的补充(1815年)”一文中,他对宗教和诗歌进行了对比:“在宗教和诗歌之间,前者以信仰来弥补理性之不足,后者对理性的传达充满热情;前者基本要素是无限,其终极真理是事物之极致,自身受制于(感知)限度,服从于(可感知物)替代,后者是卓越出世的,如果没有感性形体,它便不能维持其存在。”[8] 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华兹华斯在其诗歌中表现的人物一般不是国王、贵族、武士或者中产阶级的成员,也不只是农民、小贩和车夫,而且也包括那些下流的人、被剥夺财产的人、罪犯,以及流浪者、退役军士、乞丐、囚犯、遭遗弃的母亲、杀婴者、十足的傻瓜等等。他诗歌中经常出现的意象也多为自然界极其普通的东西。例如,他所喜欢的花是白屈菜和雏菊花,它们曾出现在他的许多诗歌中。诗人正是在这些最普通的人和事中感悟更高精神的存在。
对于“顿悟”产生的机制,华斯华斯的观点与现代主义批评家也有极为相似的看法。德昆西(De Quincy)回忆华兹华斯时说,“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专心致志地观察,或始终不渝地期待。然而,当这种紧张的关注突然放松下来时,某个或某些优美动人的视觉意象马上映入你的眼帘,传达到你的内心,它的力量之强大是在其他情况下所不具有的。”[9] (PP160-161)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选用华氏诗歌的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他的一首抒情短诗“我体验过奇异的情感波澜”。诗中的叙述者,即露茜的情人正朝露茜的房舍走去。在路上,他不断地对着天上的月亮凝思。月亮的形象不断地占据他的脑海,再加上单调的马蹄声使他神情开始恍惚,这为他后来突然顿悟奠定了基础。后来,月亮在露茜房顶后面突然落下,叙述者猛然从恍惚中醒悟过来,他把月亮的下落同露茜的死联系起来。于是,他祈求上帝的仁慈:
如醉如痴的情侣,
泛起的意念实在希奇,
“啊,天哪!”我失声惊叫,
“万一露丝突然死掉?!”[10]
华兹华斯在《序曲》的第五卷写了一个温德尔湖的小男孩儿的故事。这个男孩儿喜欢晚上在湖边模仿猫头鹰的叫声。有时,他的声音会得到猫头鹰的回应,但大多数情况下回应他的只是那凝滞的空寂。然而,这种越来越多的凝滞的空寂却成为引起男孩儿心灵顿悟的东西,因为当“那种凝滞的空寂,似嘲笑他的技巧”时,他感到
……眼前的
景色也在不觉中移入他的
心灵,带着所有庄严的形象——
山岩、森林,还有户种恬适的
怀抱中不断变化天姿的云霄。[4] (卷5,384-88行)
尽管没有成功,但在这种模仿性的关系中却产生出真正的意义。此时,男孩儿体验到了一种同自然交往的方式,即心灵同大自然的神交。男孩儿模仿猫头鹰的声音没有成功,我们可以说他创造一种人工语言的符号的企图没有成功。但也正是在这种失败中却产生了按照化身逻辑发展的由事件到精神的转化。此时,温德尔湖也变成了有生命的物体:她有一颗跳动的心脏,所有的景色都在她的怀抱中不断变化着他们的天姿。
二、作为叙述手段的“瞬间”与“顿悟”
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淡化情节。获得这种效果的一个主要方法在于顿悟手法的运用。作者经常打破传统的时间或空间发展的顺序,根据作品中情感发展的需要使用顿悟的手法。这种手法使现代主义小说中的情节降低到一系列静止的瞬间,从而使作品带有片段性的特点。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达罗卫夫人》中,作者以“顿悟”的手法反复描写不断变化的人物情感,从而使小说变成一首情感跌宕起伏的抒情长诗。现在让我们看一下女主人公达罗卫夫人的感情变化。六月的一个早晨,她要为她的宴会去买花。推开窗,清新的空气使她心旷神怡,由此她想到了她18岁时的初恋,这是小说中女主人公心头激起的第一朵情感的浪花。但是她的心情并不总是如此美好。午后时分,他听到伦敦大本钟传来的报时声,钟声慢慢消退使她怅然若失。就在这时,他又瞅见了对面房间的老太太正站在窗前。老太太的行动与大本钟的钟声在她脑海里联系在一起,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她的脑海里混杂了:大本钟的钟声、爱情、宗教思想以及这个迎着钟声准时站在窗前的老太太等等,她想从中找到问题的答案。在她看来,吉尔曼小姐企图通过宗教寻找生活的答案,她的丈夫理查德通过希望议会解决问题,而她却在老太太身上悟出了更为实际的东西:精神的独立和灵魂的清静。然而,这样一种境界,在这个纷杂的现代社会中是难以实现的。晚会上,尽管她出尽了风头。但是,一个人自杀的消息使她大为震惊。她看到“死神闯进来了,就在我们中间”[12]。她躲进斗室,再次陷入了对生活的沉思。她难以界定她称之为生活的东西,她似乎也像该作品中的另一个人物塞普提摩斯一样,走进了“某种不属于自身”的现实之中。
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一样,华兹华斯的许多作品也都强调情感在作品发展中的重要性。华兹华斯在谈到他在《抒情歌谣集》中的诗歌时说,“这些诗与现在一般流行的诗有一个不同点,即是,在这些诗中,是情感给予动作和情节以重要性,而不是动作和情节给予情感以重要性。”[1] (P17)与《达罗卫夫人》相比,华兹华斯的长诗《序曲》的展开方式也表现出人物(诗人本人)的情感在不同的生活阶段的波动,而且这种情感的波澜大部分是由于诗人在不同的生活“瞬间”对生活的不同顿悟造成的。在谈到《序曲》的结构时,德昆西(De Quency)说,尽管就表现诗人生命的历程而言,《序曲》是完整的,但它只是一个部分,是上一代浪漫主义者就人类发展的不确定性的一个例子。[9] (P161)德昆西的话说出了华兹华斯《序曲》的片断性特征。诗人不是有意追忆自己生活发展的各个阶段,而是通过顿悟等手段展现使人成长发展阶段上的思想情感的变化。
《序曲》的第一至四卷是关于诗人正式踏入社会前的生活。此时,年轻人的内心既充满了幻想也有许多迷茫。为了表达这种矛盾心态以及他自己对生活的感受,诗人多处使用了“瞬间”顿悟的手法。在第一卷中,作者回忆起自己在一个夜晚偷船,湖上泛舟的经历。当他轻盈地像一只天鹅划船前行时,他看到峭壁后露出一个山峰,凶险而有巨大,它似乎在自由意志的支配下,将黑色的头颅扬起。这一意象在他心灵上所造成的感悟是对未知生命形态的朦胧不清。这种意识在第四卷的一个视觉意象中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在这里,诗人说当你在平静的水面轻轻荡舟,从船舷探出身子,注视幽深的水底时,你会自娱自乐,看到许许多多美妙的景象,
……但是,你也会常常
感到困惑,分不清影像与实体。[4] (卷4,262-63行)
在《序曲》的第五卷:“书籍”中,诗人专门探索了情感与理性的关系问题。对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华兹华斯所采用的最有效的办法是“瞬间”感悟。该卷写了诗人的一个梦境。梦中他看到一个阿拉伯人手持长矛,腋下夹着一方石块儿,另一只手则拖着一枚明亮无比的海贝,正骑在一头高大的独峰骆驼上,匆匆从诗人身边走过,慢慢消失在沙漠中。诗人不解,追上前去询问缘由,阿拉伯人告诉他洪水马上就要来了,将要淹没地球上的孩子,他要寻找一个地方将他的宝物掩埋。按照某些西方批评者的观点,因为缺乏顿悟的客观基础,此处所写可能算不上是一个顿悟,只不过是一个幻觉。但笔者认为此时的梦境有它的客观基础。首先,它是诗人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在海边的一个凉爽的洞穴口小睡时做的一个梦。梦中远处的沙漠可能就是洞外大海的波光在诗人的睡眼中的景象,而骑在骆驼上的阿拉伯人也许就是诗人小睡时骑马正从洞穴口路过的过客。其次,梦中诗人的焦虑反映出诗人在法国大革命失败后的失落心态。因此,可以说,这个梦也算得上是一个诗人顿悟的一种形式。更为重要的是,诗人从这两件宝物身上领悟到了情感与理性的关系:那块石头是鸥几里德的原理,代表理性,而那个贝壳则代表艺术,它们都代表了人类的文明。诗人意识到他有义务像那个阿拉伯人一样去保护人类的文明:
我想我该去分担那位狂人的
忧虑与痴情,投身到同样的使命。[4] (卷5,159-60行)
诗的后半部分写大自然重新治愈了诗人受伤的心灵,从而使他从对大自然的爱中引发出他对人类的爱。对这样一种抽象思想的表达,诗人还是采用了“瞬间”顿悟的手法。诗的最后一卷写了诗人与他人前一天晚上登斯诺顿山,准备第二天清晨看日出的经历。爬到山上,他们看见月亮从至高无上的位置俯瞰着巨大的波涛起伏的云海:
此时此刻她这般柔顺、静默,只是
据我们立足的岸边不远处,裂开
一个云缝,咆哮的水声穿过它
升上天空。它是云潮的间歇——凝滞、幽暗、无底,传出同一个
声音,是百脉千川的齐语;在下面
传遍陆地与大海,似在此时
让银光灿烂的天宇一同感知。[4] (卷14,55-62行)
诗人的感悟之处就在于远处的云海处的裂缝,因为在他看来,它成了连接天上、人间的通道。缝隙下,百脉千川的声音可以通过它升上天,同样,天上的一个声音也是通过它传入人间。诗人在它身上看到了灵魂的表征,她正孵拥着幽暗的黑洞,专心致志地倾听着底下的喧声。世人感到这个心灵有超验的能力,能将感官引向理想之地。
三、直觉作为实现“顿悟”或“瞬间”的手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长期的战争厮杀使人们筋疲力尽,精神濒于崩溃,从而加深了他们对西方文明的没落感。残酷的炮弹打碎了人们的信念,美好的理想也变得四分五裂。战后,整个西方世界满目疮痍,诚惶诚恐,好像是刚从噩梦中醒来。这种精神状态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例如,艾略特在他的《荒原》中让象征着大英帝国昔日繁荣的泰晤士河漂浮着人们扔掉的空瓶子、面包纸、丝手帕、卡纸盒与香烟头等。庞德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深恶痛绝。在《休·赛尔温·莫伯利》中,他把战场上人们的厮杀比作死者肚中发出的狂笑。
人类理想的破灭的主题使得现代主义文学作品艰涩难懂,现代主义作家企图利用感官手段创造现代崇高,这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又一特征。从诗歌方面讲,诗人经常使用“蒙太奇”或“感官印象”等艺术手法将历史与现实不加说明地交织在一起,展示危机四伏的现代社会。庞德认为,现代诗歌不应采用华丽的词藻和冗长的句子,也不应使用刻板的韵律,而应采用得体的形式大胆地表现现实生活中的意象。他把意象视为一种能瞬间呈现直觉和感情的复合物,它能使诗人获得摆脱时间或空间的自由感。在其论文《意象主义的几个不准》中,他指出:“意象不是一种观念,它是一个中心点和聚合体;我能够而且不得不称它为一个漩涡,各种思想从这个漩涡中不断涌出来。”[16] 其实“各种思想从这个漩涡中不断涌出来”就是一种顿悟的形式。让我们看一下庞德《诗章》中的一个片断。
庞德诗学思想的一个来源是新柏拉图主义。这种思想相信理念的存在,认为它是“太一”,是“神”。“太一”是至善的、完满的,从他“流溢”出“理性”,从“理性”流溢出“灵魂”,再从“灵魂”流溢出物质。物质是最低级,因而是罪恶之源。人们要想摆脱物质的束缚,需要通过知觉,最后与“太一”或“神”契合为一。[12] 1945年前后,随着墨索里尼的倒台,庞德的政治和经济的理想崩溃了。“比萨诗章”记录了他在这个时期的绝望,反映出他同自己所处环境的斗争以及他如何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企图。可以说,这是庞德内心深处的“天路历程”。经过艰苦的心灵磨难,诗人终于恢复了到达天堂的信心:
安详地,在水晶般的玉石里
就像喷泉中涌出光亮的玉球
就像钻石那样晶莹剔透
山下的风是多么柔和
在那里让人想起大海。
走出地狱,深渊
走出世俗和眼花缭乱的邪恶
西风之神
这水流肯定是
心灵的财产
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心灵部分中的一种元素
可人的西风如此轻盈,黑色的铁石井然有序
我们也已走过忘川。[13]
(笔者译)
在以上所引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充分利用视觉和触觉等直觉手段,渲染诗人精神的升华。在诗歌的前半部分,诗人让我们感觉到了和煦的轻风、让我们看到了晶莹剔透的玉球。这些都是光明的使者,它们会引领诗人走出地狱和世俗的邪恶。在诗的后半部分,诗人使用了“流水”的意象。它代表了可以感觉到的现实。在这个现实中,我们可以寻找自我,这个现实也激励我们找到激流背后的永恒实在。因此,“流水”对我们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引领我们在混乱中寻求秩序的法宝。诗的最后一行又使我们想起了但丁的《炼狱》。在爬出地狱的过程中,但丁和维吉尔沿着忘川前行。忘川起源于人间天堂,它把地狱和炼狱分开,把炼狱和天堂分开。根据《炼狱》第27章,炼狱中的忘川会抹去人们记忆中所有的罪恶,这样但丁就可以进入天堂了。那么,“比萨诗章”中的“走过忘川”就意味着庞德在他的记忆中已经净化了他的灵魂,现在它必须寻找善的记忆。这些记忆既反思过去又预示未来,因此,它们具有顿悟的特点。它们不仅重视捕获过去,而且给诗人以勇气,帮助他重新建立自我。
华兹华斯的一个重要诗学观念是“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溢”。“自然流溢”意味着诗人的情感的表达必须是按照情感的本来面目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从这一意义上说,华兹华斯诗歌与意象主义诗歌或象征主义诗歌的直接表现方式有类似的特点。对于两者的类似,威穆塞特(Wimsatt)曾说,“对于一种赞成含蓄反对直言的诗歌结构来说,与玄学派诗歌相比,浪漫主义诗歌与象征主义诗歌以及当今最流行的各种后象征主义诗歌的关系要近的多。”[14] 在谈到诗的作用时,华兹华斯还说诗歌直接给人愉悦,诗人“依据人自己的本性和他的日常生活来看人,认为人以一定数量的直接知识,以一定的信念、直觉、推断(由于习惯而获得直觉的性质)来思考这种现象;他以为人看到思想和感觉的这种复杂的现象,觉得到处都有事物在他心中激起同情,这些同情,因为他天性使然,都带有一种愉快”[1] (P26)。
华兹华斯诗歌中的很多“瞬间”顿悟依赖于直觉。第一卷中的一个“瞬间”的例子写了冬日的一个傍晚,华兹华斯与其他孩子一起在湖面上滑冰的往事。冰鞋的刀刃和被冰刃划破的冰面都可让人感到冬日的严寒;在这样的环境下,“金属”的锒铛作响在听觉上也给人以寒冷的感觉:“喧声中,/悬崖峭壁高声响应,裸木/枯枝与每一块儿覆冰的岩石都如/生铁,锒铛作响……”[4] (卷1,439-442行)当诗人告诉读者他有时会离开那喧闹的伙伴独自一人来到偏僻的角落时,这时心理上的寒冷的感觉越发强烈。这种寒冷的感觉以及诗人从群体到个体的转换为他的顿悟做好了准备。这时,他意识到他尽管已停下来,
但那孤寂而又陡峭的山崖继续
在我周围旋转——似乎自转的
地球将她每日的运动向人类
展示![4] (卷1,450-454行)
和庞德意象主义诗歌一样,华兹华斯的“瞬间”顿悟有时要通过视觉来完成。第十二卷中的一个“瞬间”记述了他的一次可怕的经历。有一天他和管家骑马游玩。不幸的是,他们中途走散。当华兹华斯走过一个曾经是刑场的地方时,他顿时心慌意乱,跌跌撞撞地爬上了一个光秃秃的荒山。此时,呈现在他面前的是:脚下的荒山、山下凄清的水洼、水洼旁边一个衣衫在劲风中抖动的姑娘和远处另一个山头上的孤寂的烽火台。这一系列的视觉意象是华兹华斯“瞬间”顿悟的前提条件。对于刑场的来历,儿童的华兹华斯可能还不完全明白其中的原因,但对于周围他所看到的景象,他却要“寻求无人用过的色彩”来描述,因为在它们身上,他看出了生命的源头
……但我能
感觉到,他源自于你本身:你必须给出,
否则永远不能收获。[4] (卷12,276-78行)
即使日后诗人与心爱之人漫步时,当时那种色彩与情感还会重现在他的脑海,“快乐的/情绪与青春的金色辉光洒落在/那凄凉的水洼、荒凉山崖/那孤寂的烽火山。”[4] (卷12,263-266行)
四、结语
华兹华斯的“瞬间”诗学观念与现代主义“顿悟”诗学观念表现出相似的特征,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在本体论上的共同性。正如上文所说,无论是华兹华斯还是现代主义作家,都面临着精神方面的危机,尽管他们危机的内容和形式有所不同。对于现代主义者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他们觉得生活在一个地位不明的时期,它介于一个文明的过去和一个人们只能幻想的未来世界之间。马拉美在《局限的行动》中这样概述这个时代:
不存在现在时,是的,不存在。现实是不存在的……民众无动于衷,什么也不存在。声称自己是当代人的人不知道他再说什么……过去部分历史已经消失,而未来则姗姗来迟,抑或二者茫然地搀和在一起,以掩饰他们之间的差异。[15] (P57)
维耶莱·格力凡(Viele Griffin)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昨天和明天之间没有今天。”[15] (P57)
和现代主义作家相比,法国大革命的失败也使华兹华斯失去了精神寄托。这也是其他浪漫主义作家所遭遇的精神创伤。正如汉斯·罗伯特·尧斯所指出的那样,浪漫主义时代“所经历的现代性是很反常的,它不再是过去时代的对立面,而是与现在的时代发生冲突。……所有的浪漫主义者——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进步派——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有一种失落感”[15] (P54)。对于这种失落感,华兹华斯以其生动的诗歌意象给以形象的表示。像上文所提到的,当诗人湖上泛舟时,
但是,你也会常常
感到困惑,分不清影响与实体:
深深映入清波的岩石、天宇、
山峦、云霞与原居波中的
物体全都混在一起,而你自己的影子
也忽隐忽现,或者,一道
阳光也来碍事,还有,不知
如何,小船会忽然摇摆不止……[4] (卷4,262-69行)
自然世界是如此,人类世界也不例外。华兹华斯认为,当我们以同样的方式观察人类世界时,我们会发现“在时间的/表面长期进奉着妙趣的圣职,/也有困惑……”[4] (卷4,262-69行)如何摆脱这种困惑,如何更好地认识和表现这个世界?无论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代主义者都不约而同地选择“瞬间”或“顿悟”这种类似的认识事物和表现事物的方法。波德莱尔认为文学的现代性是一种“短暂的、易失的、偶然的东西”,而对这种东西的感受只有“从瞬时的角度去观察所有的事物,让你的自我跟着瞬时走”[15] (P57)。在他看来,正是在这种没有连续的瞬时中才能最忠实、最直接地捕捉现代性。作为自然主义者的华兹华斯来说,他认为世界是有灵的,客观的外在世界并不是死的物体,而是具有自己的灵魂。人的任务就是要同这个灵魂进行直接沟通:
岩石、巉岩、新普伦山口上的溪水
都和一刻心灵的活动一样,
是同一张脸上的器官,同一棵树上的花朵;
伟大的启示录中的人物,
永和的原型和象征。[4] (卷6,439-442行)
因此,华兹华斯要通过顿悟寻求一种更高的境界,在这里人的灵魂与自然的灵魂共处在一个和谐的整体中,在这里不仅自然的灵魂影响到人的灵魂,人对自然灵魂的感悟也带有人类灵魂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