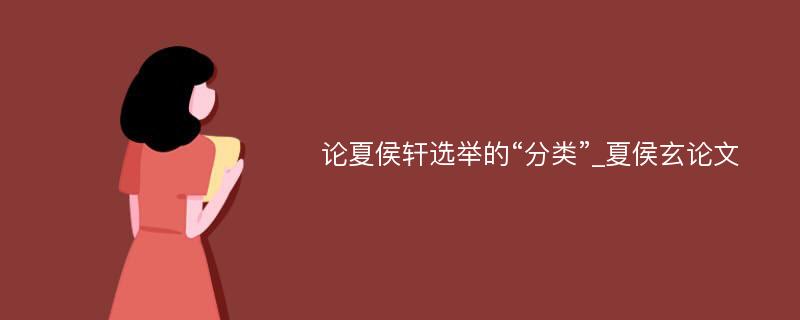
才性同异离合与夏侯玄选举“分叙”之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离合论文,夏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3)05-0064-07
才性四本之论是魏晋玄学清谈的重要命题,其在魏时讨论的基本观点,见于《世说新语·文学》“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刘注引《魏志》:“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所论的具体内容,今已难知其详。
魏晋才性论形而上学方面的意义,许多治思想史的学者在其论著中都有阐发,其论在当时政治中的若干实际意义,陈寅恪、唐长孺诸前辈学者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1](p41~47)《魏晋才性论的政治意义》[2](p298~310)等文中也曾指出。至于有关才性同异离合之论在当时政治和官制中的具体作用影响,尤其其论与官吏铨选的关系,论者尚少,似可稍加申说。如果结合当时引起才性问题讨论的具体政治背景来观察分析,可以发现,所谓同、异、合、离,实际上与汉末以来士之性行与才能是否为一,以及魏创九品中正制以来对人才的乡里评议(名)与台阁授官(实)能否分离这两大问题密切相关。其中才性同异的讨论重点,在于人的性行与才能的本质与相互关系本身,而才性离合所讨论的,或可以理解为建立在前一问题基础上的有关人才才性的评价鉴别标准是否一致、或曰对才性两方面不同的评价标准在现实中能否加以区别运用的问题。在此方面,王葆玹先生所著《正始玄学》认为离合之“离”,实际上指才能与性德的分离,在当时的人才选举制度中,具体表现为朝廷与闾里对士人才能与性行的不同的认定方式(注:王葆玹认为所谓“离”,就是才性的分别和才性鉴识方法的分离。);[3](p405.p408~409)并且,夏侯玄在正始改制中所议“中正、长官分权的选举方法,就是‘才性异’、‘才性离’两说的现实意义之所在”[3](p409)。其说颇具启发性。以下即从正始中夏侯玄有关台阁与中正对人才选任的不同职能与权限之议论的分析入手,结合相关史实,进一步探折才性同异离合的政治命义所在。
《魏志·夏侯尚附子玄传》载:
太傅司马宣王问以时事,玄议以为:“夫官才用人,国之柄也,故铨衡专于台阁,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闾巷,优劣任之乡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审选,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过其分,则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势驰骛之路开。下逾其叙,则恐天爵之外通,而机权之门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议柄也。机权多门,是纷乱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来,有年载矣,缅缅纷纷,未闻整齐,岂非分叙参错,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伦辈,伦辈当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于家门,岂不忠恪于在官乎?仁恕称于九族,岂不达于为政乎?义断行于乡党,岂不堪于事任乎?三者之类,取于中正,虽不处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则所任之流,亦涣然明别矣。奚必使中正干铨衡之机于下,而执机柄者有所委仗于上,上下交侵,以生纷错哉?且台阁临下,考功校否,众职之属,各有官长,旦夕相考,莫究于此。闾阎之议,以意裁处,而使匠宰失位,众人驱骇,欲风俗清静,其可得乎?天台县远,众所绝意。所得至者,更在侧近,孰不修饰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则修己家门者,已不如自达于乡党矣。自达乡党者,已不如自求之于州邦矣。苟开之有路,而患其饰真离本,虽复严责中正,督以刑罚,犹无益也。岂若使各帅其分,官长则各以其属能否献之台阁,台阁则据官长能否之第,参以乡闾德行之次,拟其伦比,勿使偏颇。中正则唯考其行迹,别其高下,审定辈类,勿使升降。台阁总之,如其所简,或有参错,则其责负自在有司。官长所第,中正辈拟,比随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称,责负在外。然则内外相参,得失有所,互相形检,孰能相饰?斯则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静风俗而审官才矣。”[4]
夏侯玄所议,在政治思想层面,涉及到士之才性同异问题以及在现实政治操作中对士之才性两方面不同的考评体系分离与否的问题。制度上则牵涉到九品中正制这类选举用人制度的许多具体操作问题。汉末经学衰落,名教之治破产,曹魏立国,针对汉末经学名教之弊,又面临天下未定时的人才争夺,在政治理论上亟待解决的问题无非有二,一是纠正名实相背的浮华之风以及由此导致的政风、学风、士风的衰颓,二是要厘清与前者密切相关的任用人才之标准。因而在社会中如何“静风俗”而在选举中如何“审官才”这类问题就一直是许多官僚名士在思想上及实际政治操作中所关注的热点,所谓本末、名实、才性之辨,也都是这种关注的产物。
透过夏侯玄此议,可以追溯从建安以来人们对当时用人之弊的认识。建安中期担任司空东曹掾的何夔尝进言于曹操:
自军兴以来,制度草创,用人未详其本,是以各引其类,时忘道德。夔闻以贤制爵,则民慎德。以庸制禄,则民兴功。以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乡闾,使长幼顺叙,无相逾越。显忠直之赏,明公实之报,则贤不肖之分,居然别矣。又可修保举故不以实之令,使有司别受其负。在朝之臣,时受教与曹并选者,各任其责。上以观朝臣之节,下以塞争竞之源,以督群下,以率万民,如是则天下幸甚。”[4](《魏志·何夔传》)
东曹掾分管人才选用,故何夔集中批评了曹魏前期选举及用人标准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他指出选用人才过于注重实用而忽视了儒学的名教伦常,不利于统治的长期维持及统治阶级内部各种关系的协调。所谓“制度草创”而“用人未详其本”,一定程度上也是后来九品初设时,用人只重才干情况的反映。只是,虽在战乱局势下尚可行此权宜之计,但若长期忽略道德之本,则仍然会走到汉末浮华一途,导致人心动荡,风俗衰乱。若要避免此弊,还是应考虑传统那种对人才“先核之乡闾,使长幼顺叙,无相逾越,显忠直之赏,明公实之报”的做法,使朝廷在选人时,才性两方面都能兼顾。此种看法,当然不是何夔一个人的意见,明帝时傅嘏难刘劭考课论,也说“昔先王之择才,必本行于州闾,讲道于庠序,行具而谓之贤,道修则谓之能。乡老献贤能于王,王拜受之,举其贤者,出使长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义也。”[4](《魏志·傅嘏传》)后来西晋刘毅上疏论选举,仍持类似的观点:“昔在前圣之世,欲敦风俗,镇静百姓,隆乡党之义,崇六亲之行,礼教庠序以相率,贤不肖于是见矣。然乡老书其善以献天子,司马论其能以官于职,有司考绩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党有德义,朝廷有公正,浮华邪佞无所容厝。”[5](《刘毅传》)
何、傅等人所言,自有其时代的背景渊源,尤与汉以来选举用人标准的演变有关。汉代选士,大体是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东汉以后根据需要,也举用某一方面的特异人才,如“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之属”,[6](《黄琼传附孙琬传论》)其所看重者,不外“经明行修”。所谓“贤良方正”或孝廉秀才等,本有才性两方面内涵,方正孝悌为德行,贤良秀异为才识(注:贤亦有才之谓,如王褒《圣主得臣颂》:“夫贤者,国家之器用也。所任贤,则趋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则用力少而就效众。”见《文选》卷47。),两者之间,虽有同异,但就通经致用而言,又是统一的。如《汉书·武帝纪》谓“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汉书·晁错传》言及朝廷举贤良之标准,亦是“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者,非如此,则不能谓之才。这一人才标准,本以经学价值理想为基础或本质,所以当汉末浮华之风起,此标准亦被抽空,变为徒留形式。汉末荀悦有鉴于此,在《申鉴》中一再阐述德行与才能的本末体用关系:
人之所以立检者四:诚其心,正其志,实其事,定其分。心诚则神明应之,况于万民乎?志正则天地顺之,况于万物乎?事实则功立,分定则不淫,曰:才之实也。行可为,才不可也。曰:古之所以谓才也本,今之所谓才也末也。然则以行之贵也,无失其才,而才有失。……遵路而骋,应方而动,君子有行,行必至矣。
或问圣人所以为贵者才乎?曰:合而用之,以才为贵(注:黄注:如元恺之类,才配乎德,体用兼全,故圣人贵才。);分而行之,以行为贵(注:黄注:若徒有智能技艺而不本于德,末之尚矣。)。舜禹之才,而不为邪,甚于(中有缺字)矣。舜禹之仁,虽亡其才,不失为良人哉?[7](《杂言》下)
荀悦批评当时贵行而“才有失”,与经学本质失落后的浮华风气有关。大义既失,建立于其上的德行亦流于虚浮,愈加强调,离真正的德行愈是南辕北辙。而行之不存,则才无所附。其立论乃本于“群生之性,章为五才”[8](《律历志》中)的传统,视才性为一体,本实末用合一,唐长孺先生所谓“以本质释性,以本质之表现在外者为才”者也。[2](P300)德行既为才能之本,故才行统一;而行者,其用则必须体现在才之上,非才不能见行。故贵才者,仍是重本实,本质上仍为汉代才性统一论。
然而荀悦所论,在客观上也确实表现出看重士之才能的倾向,反映出当时社会价值观变迁、德行与才能的轻重及具体内涵亦发生改变的现实。汉末以来,某些曾被视为天经地义的道德观念受到怀疑,重要性有所降低,而才能的重要性愈来愈受到强调。不仅如此,才能的内在成份也越来越趋向实用化,以前以能通经(致用)为才,战乱中则以用兵定乱之术为才。出于实用的考虑,才性统一也渐渐变为才与性在运用取舍上可以加以分离割裂,曹操求贤所言要用不忠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正是这种思潮的典型表现。何夔在其进言中提出用人在贤与庸、德与功两方面均要加以考校,先核之乡里,后上于朝廷,也是于无可奈何之下,对此思想现实加以认可。虽然他仍然站在大族立场上对曹氏任人唯才,轻视道本提出批评,但分才德考校人才的做法,无形中更促使才性趋于分离。
曹操建安中四道求贤令中的用才观念,与当时政治思想领域才性关系讨论密切相关,是汉末才性关系变异的具体体现。在建安八年庚申令中,[4](《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曹操提出“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实际上是在战乱的背景下,对才性是否统一问题,理论上暂时搁置不顾,只是依社会治乱的客观形势来决定是应重才能还是重性行。而建安十五年令中“‘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4](《魏志·武帝纪》)之言,与思想界对才性同异讨论的深入相应,具体说明士之才与行哪方面更有益于用,乃因时因地而异,德行之士,未必适用于纷乱复杂的社会环境,实际上已表明在实用的原则下,才与性是可以分离的。建安十九年十二月乙未令中,才性分离的倾向已表现得极为鲜明:“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并以陈平苏秦名行有亏而能建立功业为例,说明“士有偏短,庸可废乎”。[4](《魏志·武帝纪》)最后,在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中,[4](《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曹操更加直接地弃名取实,将建立在名教伦常之上的性行,完全视为与实相背的虚名,公然宣布对负污名而实具才德者,将不拘一格予以重用。至此,传统名教清议选拔人才的标准,已被破除殆尽。
当时思想领域对政治上人材观变化的回应,可以从徐干《中论·智行》对士之“明哲穷理”与“志行纯笃”两者关系的讨论中看到。针对世人“士或明哲穷理,或志行纯笃,二者不可兼,圣人将何取”的疑问,徐干明确回答:
其明哲乎。夫明哲之为用也,乃能殷民阜利,使万物无不尽其极者也。圣人之可及,非徒空行也。[9](《智行》)
由于时当乱世,徐干十分看重才智之实用,“圣人贵才智之特能,立功立事,益于世矣。……汉高祖数赖张子房权谋以建帝业,四皓虽美行而何益夫倒悬”。[9](《智行》)此言与曹操建安十五年令中“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也”的说法,几乎如出一辙。他虽仍然认为德行不能偏废,“愆过多,才智少,作乱有余而立功不足”者决不可取,但也指出那种有行无智者,其实同样无补于世。甚至还会由于其不明智聪睿之故,“助畔乱之人”。只有明哲而知权变之士,可以“威而不慑,困而能通,决嬿定疑,辨物居方。禳祸于忽杪,求福于未萌。见变事则达其机,得经事则循其常。巧言不能推,令色不能移。动作可观则,出辞为师表。”相形之下,那些空有“志行”之士,“不亦谬乎?”[9](《智行》)显然,徐干智行之辨,已使才性两者从统一而走向分离,其立论的出发点不一定与曹操相同,但在客观上,为曹氏“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
对士之才性的分辨,直接影响到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的用人标准。《魏志·常林传》注引《魏略》称:
先时国家始制九品,各使诸郡选置中正,差叙自公卿以下,至于郎吏,功德材行所任。[4]
在战扰不已的形势下,曹魏自建安以来所立制度,多如傅嘏所言,乃“经邦治戎,权法并用,百官群司,军国通任,随时之宜,以应政机”,[4](《魏志·傅嘏传》)后沈约在《宋书·恩倖传序》中,也称魏初是“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8]。早期的九品中正制,由于急需人才直接服务于割据政权,对才智较为强调,制度规定亦不谨严,虽然收到急用之效,也造成了一些问题,这就是何夔所言的“时忘道德”,以及夏侯玄后来不无担心的“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势驰骛之路开”的情况。如何达到“清教审选”,社会道德风气与官场政治秩序都良好,选举得人,行政不失效率的理想政治状态,夏侯玄从制度操作层面,认为朝廷用人应明其分叙,严格区分对士人道德与才能的考评任用两方面的不同事权与功能,改变当时州郡中正过多干涉朝廷对官吏的任用权的状况。他强调说明,中正台阁两者之作用不可偏废,权责必须分辨清楚。对士人的德行的评定,固然得由传统乡里组织的替代者中正根据“清议”作出,对士人的量才任用,黜徙升降,则应完全由中央台阁综合中正和有司双方对士人品行和为政才干的评价来进行。而保证士非虚才的关键制度,在于当时的考课之法。
由于汉以后事实上存在着的才性分离倾向,曹魏建国以来,有关考课法诸议,其潜在前提均是对人才唯“得其事实而课其能否”,[4](《魏志·刘廙传》注引《廙别传》)不必苛求德行之本,乡里之誉。任官者的才干操守治绩,可以通过国家权力,用各种行政的手段加以监督考察,责以实效,“圣主明于任贤,略举黜陟之体,以委达官之长,而总其统纪,故能否可得而知也。”[4](《魏志·王昶传》)如刘廙所言:
今之所以为黜陟者,近颇以州郡之毁誉,听往来之浮言耳。亦皆得其事实而课其能否也?长吏之所以为佳者,奉法也,忧公也,恤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来者有所不安。而长吏执之不已,于治虽得计,其声誉未为美。屈而从人,于治虽失计,其声誉必集也。长吏皆知黜陟之在于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为长吏皆宜使小久,足使自展。岁课之能,三年总计,乃加黜陟。课之皆当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以户口率其垦田之多少,及盗贼发兴,民之亡叛者,为得负之计。如此行之,则无能之吏,修名无益。有能之人,无名无损。法之一行,虽无部司之监,奸誉妄毁,可得而尽。[4](《魏志·刘廙传》注引《廙别传》)
曹操对其言深为赞同。后刘劭作《都官考课》,旨在改变官场“能否混而相蒙”状态,[4](《魏志·刘劭传》)实际上也主要考校官吏之才,傅嘏因此批评其法是不问德行之本:
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乡之举,其选才之职,专任吏部。案品状则实才未必当,任薄伐则德行未为叙,如此则殿最之课,未尽人才。述综王度,敷赞国式,体深义广,难得而详也。(注:据《傅嘏传》注引《傅子》,傅嘏自己在任河南尹时,虽号“以德为本”,治其下属,仍是“官曹分职,而后以次考核之”。)[4](《魏志·傅嘏传》)
杜恕从才性合一的角度,也对当时考课未由“四科”(注:按应劭《汉官仪》:东汉章帝时诏四科辟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经明行修,能任博士。三曰明晓法律,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任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照奸,勇足决断,才任三辅令。”(见《后汉书·和帝纪》李注)此四条体现了汉代才性统一的人才标准,杜恕所言“四科”即指此。)提出质疑,认为其法不足以“崇揖让之风,兴济济之治”:[4](《魏志·杜畿传附子恕传》)
时又大议考课之制,以考内外众官。恕以为用不尽其人,虽才且无益,所存非所务,所务非世要。[4](《魏志·杜畿传附子恕传》)
明帝时主持吏部的卢毓,出于对汉代那种才性德能兼重的传统考绩法的向往,批评当时的考课是“考绩之法废,而以毁誉相进退,故真伪浑杂,虚实相蒙”,但仍然主张“主者正以循名案常为职,但当有以验其后。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试以功。”[4](《魏志·卢毓传》)
不难看出,无论对考课法赞同与否,时人都加以承认的一个事实,就是在当时考课中,已不得不区别人物之才干实效与道德名誉两端,而更注重官才与政绩:“考绩之赏,在于积粟富民”。[4](《魏志·邓艾传》)而考课的方法和最终目标,也都按名法之治的要求,责以事能,“课之皆当以事,不得依名。……如此行之,则无能之吏,修名无益。有能之人,无名无损。法之一行,虽无部司之监,奸誉妄毁,可得而尽”,避免任官者“不念尽心于恤民,而梦想于声誉”之弊,[4](《魏志·刘廙传》注引《廙别传》)从而使得政途上“交游之路绝,浮华之原塞”。[4](《魏志·邓艾传》)
“表德行以厉风俗,核才蓺以叙官宜”,[6](《仲长统传》)汉末以来,人们已普遍注意到才与性在社会伦理和治国行政上,功能作用不同,不能一概而论。阮武说“才性可以由公道”而“器能可以处大官”,[4](《魏志·杜畿传附子恕传》)对于士人,国家是用其才,乡里则是注意他的品行,前者关乎国家实际利益,而后者关乎闾巷风气、名教伦常。夏侯玄进一步区分这两者一为“事理”,一为“人心”。理论上看,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前者则为后者之效用。但由于评价标准不同,对这两者进行考评的内容、方式与主者,也不得不是分离的,所谓“考实性行,莫过于乡闾;校才选能,莫善于对策”。[10](卷42.杜恕《笃论》)、[11](P349)乡闾舆论与朝廷用人机构,各司其责。东晋梅陶尝谓台阁铨士与乡里月旦,其为法有公私之别,铨士“官法也;月旦,私法也”,[5](《祖逖传附兄纳传》)正是从侧面反映了这种传统观念。
然而,乡里与官长乃至于台阁的关系,实质上又是地方大族与中央朝廷之关系,利益冲突的存在,使双方不免各执一端,分别强调倚重,才性亦由此更进一步成为两截。以本自居的性行,力主才能不可脱离德行而存在或被使用。由此影响,时人识鉴人物,也仍然会根据品行是否端正来判断其人能否成功施展其才,如魏明帝时秘书丞何桢批评谯人胡康(裴松之案:疑是孟康)称:“康虽有才,性质不端,必有负败。”[4](《魏志·刘劭传》注引《庐江何氏家传》)大族出身的吏部尚书卢毓选举用人,“先举性行,而后言才。”他为此解释说:“才所以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称之有才而不能为善,是才不中器也。”[4](《魏志·卢毓传》)而处于末用之才,则始终坚持可以脱离性行而致用,否则就是徒有虚名,“所谓有其才而无其用。”[4](《魏志·杜畿传附子恕传》)时人对此曾以木性喻之:“曲直者木之性也。曲者中钩,(直)者(中)绳,轮捔之材也。贤不肖者,人之性也,贤者为师,不肖者为资,师资之才也。然则性言其质,才名其用,明矣。”[12](卷21,袁准《才性论》)尽管如此,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对才与性从不同系统分别加以考评,却逐渐成为一种事实上的共识,越到后世,人们越倾向于乡里官府台阁各司其责。因此即便是有深厚汉学背景的葛洪,言及怎样公正选才,亦主张以乡议来核验才人的德行,“令亲族称其孝友,邦闾归其信义”;而对士人的实际才干,则要通过仕宦的经历,来了解其是否“有忠清之效,治事之干”,[13](《审举》P403)后者正是朝廷职责所在。
夏侯玄明确提出“官才用人,国之柄也,故铨衡专于台阁,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闾巷,优劣任之乡人,下之叙也”,也是基于此点。他看到了台阁擢用人才,原则上不能忽视品行,因此必须考虑来自中正的意见,否则可能会丧失道德之本;但代表当时闾巷清议的中正,若权限越过品鉴举荐之责,干预到朝廷官员的任用升降,则不仅有损行政实效,还有可能使朝廷用人之权旁落,政出多门,助长社会中奔竞钻营风气,当然最为严重的后果,便是汉末处士横议,大族操纵选举,权去朝廷的局面再次出现,引发政治的不安。因此,在台阁与闾里权责不分或重心失衡所造成的种种弊端中,夏侯玄重点批评的,主要还是闾里之议侵朝廷台阁之权。因为九品中正制下中正权力过大,同样会造成品评士人名实相失,直接妨害到曹魏自曹操执政以来综核名实,打击浮华的既定政治原则。
三
综观当时思想领域才性同异离合之辨,本有诸多政治背景。通常认为,论才性同者,主要反映了汉以来视性行才能为一整体,性为本才为末用,本末统一不可割裂的人才观;而主才性异者,主要反映了早期曹魏政权用人重实用,轻德行,唯才是举,主张性行与才能分离的传统。与之相应的是,在魏晋才性四本之论中,恪守礼法名教、诗礼传家的大族名士多持才性同,而与曹魏政权关系密切的官僚名士则多主才性异。但此点似不能一概而论,如夏侯玄之维护台阁铨衡用人之权,表面上,是看重人才的实际才能而对中正所品鉴的德行较为忽视。但实际上,他在自然人性论的前提下,并不否认德行为才能之本。他认为忠诚出于孝顺之性;在家族中宽厚关爱,处理政事才可能通情达理;在乡里急公好义,为官才能勇于任事:“夫孝行著于家门,岂不忠恪于在官乎?仁恕称于九族,岂不达于为政乎?义断行于乡党,岂不堪于事任乎?”不难看出,他在才性关系上所推崇的这些作为才能之本的德行,都出自人的天性,正是正始玄学“名教出于自然”的思想宗旨的体现。而由于他思想上比较倾向于传统的才性同观点,因此他对于中正在士人任官中“考行伦辈”的作用其实也相当重视。他提出“上之分”与“下之叙”之别,涉及到四本之论中才性能否相离的问题,而深入分析其意,可以体会到夏侯玄主张相离的,只是对才性的评价与使用,而在才性本身是否统一问题上,他仍倾向于主张才性合。因此,在才性关系上,我们或可认为,夏侯玄的“分叙”说,是既主张才性离,又承认才性同,才性的同异离合,在某种意义上被看作是一种相反而相成的关系,与正始玄学家糅合儒道,打通天人的哲学努力相一致。
正因如此,夏侯玄在提出对士之才性明其分叙的时候,并不抹杀士人德行在任官上的重要价值,从而也对中正在选举中应有的地位予以肯定——这就是中正虽不能直接干预官吏的铨选。但其对士人品性的评价却能自然影响到其任用,因此殊不必再去施加额外的影响。事实上,夏侯玄对由中正考评的德行抱有怀疑的重要原因,并不在于德行本身,而是由于他从循名责实的方法着眼,认为不仅才性之间有名实相失之弊,德行本身也有空有其名的情况存在。这是由于当时中正推举人才,没有客观标准,往往“以意裁处”,甚至徇一己之私,误导台阁从民间拔用真正的人才。士人因此也可行不由本,夤缘求进,“修饰以要所求”。此风一开,士人“所求有路”,自不必真正依靠进德修业来获取声名,“修己家门者,已不如自达于乡党矣。自达乡党者,已不如自求之于州邦矣。”而士人既然“饰真离本”,通过粉饰行为影响乡里清议,州邦推举,这样中正品评人物所依据的,就未必是士人砥砺名行之实际所为而可能仅是其矫饰之虚名。所以,如果台阁听任中正过于干预用人,让在德行上有名无实者进入仕途而不加核校,只能使社会风气更趋虚伪浮华,“虽复严责中正,督以刑罚,犹无益也。”(注:联系到西晋时刘毅对中正一职诸多“损政”譬如“中正知与不知,其当品状,采誉于台府,纳毁于流言。任己则有不识之蔽,听受则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爱憎夺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乱其度。既无乡老纪行之誉,又非朝廷考绩之课。遂使进官之人,弃近求远,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党誉虚妄”之类的批评(见《晋书》卷45《刘毅传》),可知夏侯玄之,所疑虑原本切于时弊,并非空论。)从这一意义上,夏侯玄主张台阁依据官长所第,中正辈拟的结果来铨衡授官,内外相参,互相形检,人才任用不致偏离道本的做法,也是一种通过综核名实手段而使才性相合的用人方法。
最后,虽然随着时间的迁移,才性四本之论原有的现实政治意义渐渐减弱,讨论重点逐渐抽象为哲学层面形上之性与形下之才的关系问题,(注:关于此点,可参考王葆玹《正始玄学》第9章《正始玄学中的人性论与人材论》中的讨论。)[3](P411)但才能与性行,却从来没有离开人们考察评价人物的基本视野。在这一时期的史籍中,可以看到大量用“性度恢弘,才经文武”、[4](《吴志·宗室孙桓传》注引《吴书》)“性清正,有才理”、[5](《陆云传》)性至孝,有文武才略”、[5](《明帝纪》)“性不弘裕,才不副意”、[5](《卞壶传》)“有贤人之性,而无贤人之才”[5](《隐逸·郭文传》)这类才性的概念,对人物性行才能的同异离合或优劣高下加以判断描述的内容,足见当时人们识别鉴赏人物,仍遵循着魏晋才性论的一贯眼光。而且在选官用人时,对才性关系的考辨仍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这也可以解释自夏侯玄、何晏等正始名士以还,有山涛、嵇康、阮咸、毕卓等许多清谈放达之士曾出任或被大力推荐去担任吏部选职的某些深层原因。
标签:夏侯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