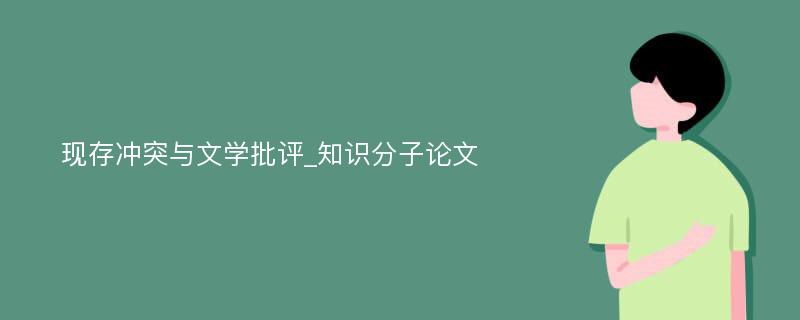
现存冲突与文学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冲突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中国作家经历了两次社会背叛。第一次是20世纪初期,第二次是20世纪末期。不过,第一次是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中国作家从统治阶级阵营里分化出来,成为革命阶级的有机组成部分。鲁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正如瞿秋白所说:“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他终于宣言:‘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消灭,后来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第二次是有些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中国作家从社会基层民众中分化出来,跻身社会上层,有的甚至蜕变成为西方话语霸权的附庸。我们从当代中国艺术的审美理想的裂变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个社会背叛过程。
中国艺术的审美理想在近20多年里经过了三次较大的裂变。第一次裂变是从文艺要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到鼓吹文艺不反映时代精神,也不表现人民创造历史的丰功伟绩,而是追求脱离广大基层民众的自我表现。20世纪70年代末,当人们对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个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进行调整的时候,文艺界出现了不和谐音。有人提出,当前出现了一些新诗人,他们的才华和智慧才开出了有限的花朵,但他们的影响却成了一种潮流。与其说这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这种新的美学原则,不能说与传统的美学观念没有任何联系,但崛起的青年对我们传统的美学观念常常表现出一种不驯服的姿态。他们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他们甚至回避写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英勇斗争和忘我劳动的场景,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这种自我表现必然脱离广大基层民众,这是当代中国艺术的审美理想的第一次裂变。第二次裂变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中国作家远离基层,浮在上面,迎合需要,粉饰现实,而不是直面现实的苦难,正视历史的阵痛。李公明指出,令人感慨的是,在大半个世纪前已经回响过“劳工神圣”口号的大地上,现在“劳工神圣”还是一个必须努力解决的问题。“许多艺术家不再愿意让自己的艺术与当下存在着的各种各样的具体的苦难发生联系。在那些无数人为的或自然的灾难面前,很难看到艺术家真诚的思考与创作,相反的倒是在各级的省展、全国大展上屡屡看到那些千篇一律的化苦难为颂歌的争名逐利之作。”李公明对这次裂变的历史根源作了深刻的挖掘。他说:“对于知识分子、尤其是艺术家而言,本来他们最理想的诉求对象是弱势群体,因为只有在这里他们才能充分获取批判性的养分、史诗性的激情和对社会公正的立法角色。然而现实所提供的图景却恰好相反,总是在权力与财富的周围集结了为数不少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即便我们可以承认这里有很大的因素是由于体制问题,但源自弱势群体本身和知识分子本身的因素才是至为关键的。就‘新穷人’来说,他们已不再具有早期产业工人所具有的那种阶级意识,生存压力取代了历史理性……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多数成为了体制现状的获利者和支持者,他们与‘新穷人’之间没有任何纽带可以连结在一起。这样,只有少数知识分子以道义、专业的立场继续关注‘新穷人’,如部分社会科学工作者、新闻工作者,而艺术家则基本上甚少自觉地充当弱势群体的艺术塑造者和代言人。因此可以说,在公共领域中的当代艺术对社会的关注是片面的、残缺的,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关于社会正义的思想远未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自觉诉求。”(参见2002年第1期《天涯》,《谁还愿意与苦难发生联系?》)同时,孙振华以“当代艺术与中国农民”为题也提出这个问题。他说:“农民和农村不仅仅是个题材的问题,艺术作为文化权利,它和农民的关系,体现的是社会的道义和良心,公平和正义。而在中国,真正站在农民的立场,关心农民的生存状态,关注他的喜怒哀乐,这样的艺术一直付诸阙如。”而“在中国,如何对待农民,已经成为检验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正义和对人的基本权利的起码尊重的标识。占中国人口近百分之七十的农民是中国的最大的弱势群体,他们中间的数千万人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这些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农民,其生存状态比城市贫民和下岗工人要悲惨得多,而中国农民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居然与当代艺术没有任何关联,我们的当代艺术居然对这个最需要关怀的社会群体无动于衷。那么,当代艺术的文化身份的基础是什么?”这种艺术是没有自己的未来的。(2002年第9期《读书》)不过孙振华没有像李公明那样追问这个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第三次裂变是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中国作家在精神上彻底背叛了社会基层民众,蜕化成为西方话语霸权的帮凶和帮闲。在艺术上,就是以艺术为名义拿穷人开心。陈履生以“不能以艺术的名义拿穷人开心”为题指出:“一段时期以来,所谓的‘行为艺术’却存着以艺术的名义拿弱势群体开心的情况”。他分析了两个例子,《有偿巴掌》和《一次雇佣的拥抱行为》。认为在这种以艺术为名义的行为中,表面上看是一种平常的雇佣劳务的合作关系,也遵守了一种自愿的原则。可是,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务,其“自愿”的背后透露出的是为了生活的无奈,正好像“逼良为娼”。最让人心里难受的是那位农村的“还没有恋爱”的姑娘的“初吻”,而最让人由衷敬佩的是那些“宁愿少拿钱也不愿裸体”的9个民工。当然,这里不仅是“裸体”和“初吻”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处于弱势的他们的精神伤害。而在这些表演中,那些以艺术为名义的“行为艺术家们”,正好像旧时拿穷人开心的恶少。接着,王仲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所谓的“前卫”艺术家,花钱雇佣一批工人和农民当众脱光衣服为他们表演“行为艺术”;两千年前,罗马贵族拿奴隶在斗兽场上取乐,今天,我们似乎又依稀重新看到消失久远的场景和看台上的人形鬼影。(参见2002年第4期《美术》)经过这三次裂变,当代中国艺术从为人民服务到把工人和农民当成艺术的“新材料”、“新载体”,让“人民”交出肉体来为他们的“前卫艺术”服务,终于在一定范围内完成了历史的蜕变。
对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中国作家这种社会背叛,当前中国文学作了深刻的反映和有力的批判。
当前中国文学的这种批判经过了两个历史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寻找”和“坚守”,即对精神之根的寻找和坚守。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悲壮的抵抗。张炜的长篇小说《柏慧》记录了这种“声音”。
在《柏慧》中,“我”没有退却,没有逃避。“退却的年代已经过去了。退却的机会再也没有留给我。我命中注定了要迎上去,要承受,要承受这一切。我说过我从属于一个特殊的家族,当我慢慢辨认出这一点时,我就明白了该做些什么。我只有一种结局,就是迎上去,奔向那个我应该去的地方。”小说中“我”的坚守虽然不过是血缘的不同,“我越来越感到人类是分为不同的‘家族’的,他们正是依靠某种血缘的连结才走到了一起……不是一族的人,最后仍然归不到一块儿。”但他却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中国作家的精神背叛问题。“由于我的特殊的经历,特殊的血脉,我一直铭心刻骨地记住了:永远也不要背叛和伤害,永远也不要对丑恶妥协。”而当前有些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中国作家在精神上却背叛了,对丑恶势力妥协了。这种历史分化不完全是血缘上的分化,而是社会的分化。
首先,“我”认识到了“善,就是站在穷人一边。”“这就是我的道德,也是我的立场,我出发求善的根本。”
其次,“我”对现实生活的认识是清醒的。“如果一个时代是以满足和刺激人类的动物性为前提和代价的,那么那个时代将是一个丑恶的、掠夺的时代。那个时代可以聚起粗鄙的财富,但由于它掠夺和践踏的是过去与未来,那么它终将受到惩罚和诅咒。”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些本质方面的反映。
最后,“我”坚守的“是一种被一代代继承又一代代扼杀,最终总是存活的——精神”。“我”找到了这种精神的根。“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人们都常常缺乏面对这个基本问题的勇气。人不愿意在血缘上确认自己,总是首先忘记自己是谁的儿子。”“我”没有精神背叛,“我们家遭难的人已经那么多了,他们为心里那块热辣辣的东西受的折磨已经够多了,我这个后来人可千万别溜掉,我得挺住。”
可以说,“我”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中国作家历史分化中坚守和弘扬了高贵的人生。
不过,在长篇小说《柏慧》中,张炜虽然认识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中国作家的精神之根在“穷人”一边,“我开始知道正在自觉地靠近谁,寻找谁了。我与贫穷的人从来都是一类,………“父亲长大之后,却开始慢慢地往自己的血脉上靠拢,这个过程简直就是靠本能来完成的。他大概记起了自己是准的儿子——那片大山的儿子、贫穷山民的儿子。于是他的生命开始有了着落。”无论是“我”,还是父亲,都自觉地把精神之根扎在穷人一边。但是,他仍然没有超越人性论的局限。“我从此更加明白,不同的家族无论以何种方式,因何种机缘走到了一起,最终仍要分手。善恶是两种血缘,血缘问题从来都是人种学中至为重要的识别,也是最后的一个识别。”“人为了追求高贵,可以贫困,可以死亡。这是不变的至理。关于它的认识,一直存在于一部分人的心灵之中。但他们究竟靠什么才把这种认识传递到遥远的未来?我一直不解。过去我曾认为依靠典籍,即纸页和竹简,现在看这种理解多么浅薄。文字只能是提供过去的证实,是个记载和提醒,而难以构成最有力的承接链条。其实传递的真正奥秘存在于血液之中。”“我”和穷人的联系不过是血缘的关系。
第二个阶段是深刻地反映了有些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中国作家的社会背叛,并有力地批判了这种社会背叛。从王跃文的长篇小说《国画》、阎真的长篇小说《沧浪之水》到尤凤伟的长篇小说《泥鳅》,可以看出中国作家对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中国作家的社会背叛问题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都突破了人性论的局限,挖掘了这种社会批判的历史根源。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中国作家的社会背叛不是人性的变化,而是历史的演变。
当前不少文艺作品在反映和描写现实生活中的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时,无论是写正面的英雄人物反腐败,还是写反面的腐败分子搞腐败,都归结为他们的个人品质问题。当前不少作家自觉不自觉地认为这场腐败与反腐败的尖锐斗争不过是人性的善与恶的激烈较量,而不是一场严酷的政治斗争。正如作家陈忠实说:“现在的文学作品包括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缺少的恰恰是政治。一些作家描绘的那些生活,相当生动、具体,语言已经精练得非常圆润、生动,结构也非常自然。但你读了以后总感到缺点啥,缺啥?缺思想。思想从哪儿来?政治!”当前的腐败问题从根本上说是革命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以后部分成员从社会的公仆演变成社会的主人,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人性的恶压倒人性的善的问题。当然,在这个历史演变过程中,也不否认存在极少数人是因为意志薄弱、恶欲膨胀而蜕化变质的。但这只是从属的。当前有些作家不能这样历史地把握和解剖腐败分子的腐败过程,往往不是渲染腐败分子的腐败生活,就是为这种腐败堕落寻找各种各样的原因,胡诌什么社会分配不公,家庭生活艰难,贡献大分配少,等等。而一些正面描写反腐败斗争的文艺作品,也是孤立地塑造那些反腐败的英雄人物,表现了脱离基层民众的狭隘的青天意识。这些反腐英雄之所以坚决地反腐败,不是因为有了基层民众的斗争、支持和推动,而是因为他们个人的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品格和嫉恶如仇的高尚品质。也就是说,他们的高尚动机不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他们不是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不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人们从这些“孤胆英雄”的个人命运中是看不到历史的未来的。而王跃文的《国画》、阎真的《沧浪之水》、尤凤伟的《泥鳅》等长篇小说则超越了这种人性论深刻地把握了当前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中国作家的社会背叛问题,有力地揭示了当代中国腐败的实质。
在长篇小说《国画》中,王跃文生动地描写了朱怀镜社会背叛的心理变化。“存折在朱怀镜的枕边,他也不去拿它。也难怪香妹生气,这么花钱真的让人心痛。父亲在乡下拱着屁股干了一辈子,手头还从来没有过二万五千块钱啊!朱怀镜平时再怎么大方,再怎么吃喝,也不敢太大手大脚,他总时不时会想起他熟悉的乡村。他买双皮鞋,买件衣服,或是下了顿馆子,总会突然想到花的这些钱,父亲得辛辛苦苦做半年或是做一年。父亲往往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做一年还挣不来他在外面吃的一顿饭钱。他太熟悉那些乡村了,太熟悉父亲一样的农民了!仍然很贫穷的广大乡村,是他永远走不出的背景,是他心灵和情感的腹地。但是,朱怀镜毕竟离开了乡村。离开乡村几乎是所有乡下人的愿望。乡亲父老巴望他有出息,可出来这么些年,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一个乡下人所谓的大出息,得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他朱怀镜这一代只能走完从乡下人变成城里人这一步。他只能为儿子创造条件,让儿子比他更高贵些。以后孙子比儿子又更高贵些。只有这样,他的家族才会慢慢进入社会的高层。不管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社会已经在事实上存在了阶层。生活在下层的人,你可以傲骨铮铮地蔑视上层,可你休想轻易地接近和走向上层。”朱怀镜只是真切地感到这社会的确越来越阶层化了,有些人更是越来越贵族化了。尽管做官的仍被称作公仆,尽管有钱的人仍尊你为上帝,可事实就是事实。下层人想快些进入上层,拿时兴的官话说,就是实现超常规发展,你就得有超常规的手段。“朱怀镜伸手拿起存折,握在手里。存折冰凉的,一股寒气直蹿他的全身。他闭着眼睛,体验着一种近似悲壮的情绪。存折在他的手心被捏得发热了,他的心情也就平静了。”这段心理描写较为有力地刻划了朱怀镜的内心冲突。朱怀镜经过这种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认同了异化和走向了背叛。
《国画》既反映了当前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也反映了当前社会的剧烈分化。在反映这种历史的分化中,王跃文深刻地揭示了腐败的实质。这就是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所写的导言中所指出的:“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自己共同的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种情形不但在例如世袭的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的共和国内也可以看到。”国家政权的这种演变与革命阶级在革命成功前后的变化是一致的。革命阶级和统治阶级即使是同一阶级,但在本质上也是不相同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说:“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惟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这一点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惟一的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来不及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革命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以后的确存在一个演变的问题。因此,当前的腐败问题从根本上说是革命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以后部分成员从社会的公仆演变成社会的主人,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人性的恶压倒人性的善的问题。而那些拒绝分化、拒绝蜕变的优秀分子正纷纷地被碾碎。我们在小说《国画》中看到了这种趋势。“不管论德论才,邓九刚都是应该重用的好干部,却硬是把他放在副处长的位置上压着。”在干部轮岗中,又被调到保卫处。这个很正派、很能干、很有骨气,而且也有自己思想的邓九刚在政府难有发展,辞职下海了。当满世界都在玩,成功的都是玩家!而不屑于玩,一本正经地想做些对得起良心的事的曾俚被挤出了荆都,走了。清醒而懂得廉耻的李明溪疯了。卜老死了。……而朱怀镜在分化和背叛后则逐渐地如鱼得水,游刃有余,步步高升。
在小说《沧浪之水》中,阎真更细腻更充分地凸现了池大为这种社会背叛的内心斗争、痛苦和煎熬。和朱怀镜这种典型的官员不同,池大为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既有从社会基层民众中分化出来,跻身社会上层的痛苦和矛盾,也有放弃一个知识分子的清高和骨气的失落和空虚。可以说,《国画》集中反映了既得利益集团的腐败,而《沧浪之水》则集中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化和堕落。阎真不但淋漓尽致地刻划了池大为的演变和蜕化,而且较为深入挖掘了这种演变的历史根源。池大为是双重背叛,一是从社会基层民众中分化出来,彻底地背叛了基层民众;二是主动地放弃了真正知识分子的价值和尊严。
《沧浪之水》中池大为也有小说《柏慧》中“我”的同样血脉。“我们的血管里流着的不同的血。”“平民也可以坚守自己心灵的高贵。”池大为对现实生活也有同样清醒的认识。“人间真实从来不从原则出发,利害才是真的,原则只是一种装饰,一种说法”。“道理是假的,利益是真的。道理随着利益转,因此各有各的说法。小人物如此,大人物更是如此,不同的只是小人物没有力量左右事情的方向。”“公事公办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个人化的时代改变了权力的存在方式。”“这个世界是强者恒强,大小通吃,一路吃过去,吃了鱼还要吃虾,能吐一点骨头屑出来,就是很有良心了。”这些真知灼见不能不说是对现实的真实感受的升华。但是,池大为没有悲壮的坚守,而是主动的放弃。
《沧浪之水》细腻而生动地刻划池大为的两次主动放弃,一是掌权之前,一是掌权之后。如果说池大为在掌权之前的主动放弃是为了“曲线救国”,为了自尊和尊严,希望掌权之后重建崇高,重建神圣。那么,池大为掌权之后的主动放弃就是完全彻底的了。池大为掌权之后,“还是想当个好官,做点好事。”然而,还是不得不主动地放弃。“我还幻想要群众口服心服,要让他们满意,这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我经历千山万水千难万险千幸万苦走到今天,本来是为了做点事的,但事情却由不得我。”
为什么有些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中国作家难以坚守而主动放弃一些原则呢?这是因为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中国作家从根本上脱离了社会基层民众,处在漂浮状态。这种处于漂浮状态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中国作家在社会权力异化的历史进程中不是零落成泥、潦倒,就是戴上镣铐,是没有力量抵抗的。“在这个时代,我们遇到了精神上的严峻挑战,我得承认这一点,我们没有足够强健的精神力量来回应这种挑战,在不觉中,就被打败了,缴械投降了。我们失去了身份,这似乎是时间的安排,不可抗拒。中国知识分子失去了根基,他们解放了自己,却陷入了万劫不复的精神绝地。”这是不可移易的真理。董柳说:“我们家有今天靠的是谁?靠人民群众?我们住筒子楼那么多年,人民群众谁说过一句可怜?人民群众是个屁!”董柳所说的可以说是当前中国不少知识分子的认识。他们在精神上背叛了其社会出身,既不依赖基层民众,也认识不到他们的斗争力量。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中国作家所追求“独立精神”超越不了“浮萍”的命运。池大为的人生感受就是这种漂浮状态的反映。“我为了自尊和骄傲而不愿顺势而为,可越是想坚守那点自尊就越没有自尊。”“我没有身份,这使我气短,我沉痛地感到了身份是多么重要。没有身份而拥有自尊,那不可能,这是痛到心尖尖上的感受。”为了摆脱这种难受的漂浮状态,“边缘的滋味,被人遗忘的滋味,可真不是滋味。”池大为争取“入局”,“这个局不是为小人物设计的,小人物要跳出去,惟一的办法就是想出无数的办法变成大人物。”这不就是从基层民众中分化出去,跻身到上层社会的行列吗?
池大为成为大人物后,似乎有了机会,下了决心要在自己心中重建崇高,重建神圣。但是仍然失败了。“圈子好像是个黑洞,好像有一种神秘的魔力安排了一切,进去了就身不由己。”
如果说《国画》全面反映了上层的腐败现象,《沧浪之水》深入反映了知识阶层的退化,那么,《泥鳅》则深刻反映了社会基层——进城农民——的堕落和毁灭。
在《泥鳅》中,尤凤伟虽然主要写的是进城农民的堕落和毁灭,但仍然清醒地提出有些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有些中国作家的社会背叛问题。进城农民国瑞和作家艾阳在批判当前有些小说时尖锐地指出了这个问题。艾阳说:“谁不想高高在上?当官愈大愈好,当作家愈著名愈好,这很正常,用不着遮遮掩掩。问题是……咱不说当官的,就说作家这行当,不怕脑袋升到天上,就怕脚跟离开了地面。”而国瑞认为,存在决定意识,他不大相信有那种脑袋在天上而脚还站在地上的人,那是多么高大的人啊,现时今有这么高大得顶天立地的人吗?未必。当前不少反映现实的小说,之所以不像现实,是因为不少作家远离基层,浮在上面,迎合需要,精神背叛。在《泥鳅》中,尤凤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我们对伪现实主义文学倾向的批判。这说明尤风伟更清醒更自觉地意识到了当前有些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中国作家的社会背叛问题。
标签:知识分子论文; 中国作家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基层反映论文; 泥鳅论文; 国画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柏慧论文; 沧浪之水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