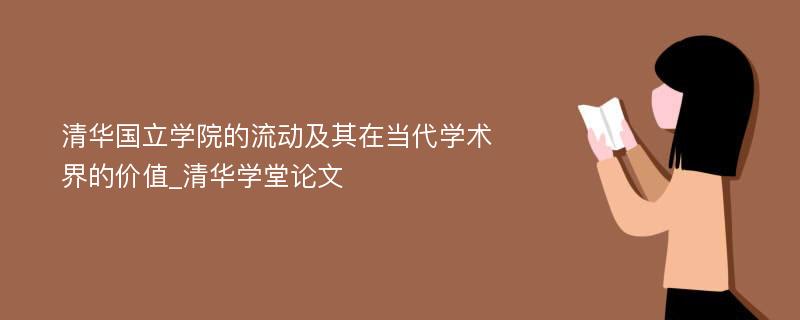
清华国学院的浮沉及其在当代学术界的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华论文,学术界论文,国学论文,当代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大学本身就是伴随西方世界经济体系形成过程中文化扩张的产物,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诞生都无不具有被征服和被殖民的背景。因而,也就是由于有了这段屈辱和痛苦的民族历史,在以现代性为标志的西化与以民族认同为旨归的本土化之间,第三世界的大学一度被置于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它本身就是西方化的产物,由于在先天上缺乏适宜的内生环境和文化土壤,它们不得不全盘移植了西方的大学学术组织形式和学科建制;另一方面,在新的历史境遇中,它们又往往被赋予了民族振兴和民族传统延续并将其发扬光大的双重使命。由是,从早期的被殖民一直到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一种内在的、持续的紧张始终居留于第三世界的大学之中。这种紧张的真正文化意义其实并不在于话语权力的争夺,因为自近代以来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文化没有为弱势民族的传统文化预留多少权力空间,而是在于弱势的民族是否并且如何能够借助西方意义的大学,为民族文化与传统的延续赢得一线生机,包括借助西方话语的植入,让传统与文化在全球化的语境中重现活力。
一、西学东渐:现代性与民族文化认同危机
从晚清中华民族在经年饱受外夷入侵之痛中觉醒,开始有了自觉学习西方的实利科学和技术的意识,到如今一个全球化话语风行的时代,近百年的中华民族史,既是一部民族自强和自立的自我奋斗史,又是一部不断否定自我甚至试图超越自我的文化革命史。同世界其他同样积贫积弱的民族一样,在西方国家主导的现代化格局中,面对在经济、政治等领域不断被边缘化的窘境,中华文明也经受了自古以来最为彻底、最具震撼力的强烈冲击。正如杜维明所认为的,如果说19世纪的90年代,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还不失为在对传统的认同与西学的适应间寻找一种妥协的话,那么,在五四之后,虽然“全盘西化”的口号,“或许只有极少数传统主义者的拥护,但是,却是一种普遍态度的表征。”(注:[美]杜维明:《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钱文忠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6页。)由此开始,在种的存亡与文化的遗存之间,有着强烈民族主义情结的中国知识分子,逐渐自觉地或主动地远离了自己的传统,甚至把传统视为中国落后根源。在把视线投向西方文明的同时,传统也成为一个被批判的参照对象。
可以说,整个20世纪,面对着中西方在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巨大落差,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关系到民族危亡的不同关键时期,再一次表现出强烈的入世精神,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然而,与以往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的是,如果说此前他们更多地担当了传统儒家精神的传播者和诠释者,那么,这一次,则在更为广泛意义上,他们更多地是扮演了传统的批判者角色,并不同程度地把西方文明作为摆脱传统、解救民族于危难之中的思想、精神、文化和制度的源头。然而,颇为意味深长的是,就整个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运动的运行轨迹而言,主动接纳了西方学术话语资源的中国知识分子,依旧没有真正摆脱自身的传统角色定位,即作为体制之外的政治参与者和体制内政治诠释者的角色。相反,在国运日衰、种的存亡维系一旦的危急情势之中,他们更表现出了空前旺盛的政治热情。诚如杜维明所言:因为激进变革的要求是如此的压倒一切,“这种情势绝对无益于冷静的反思和深入的思考。付诸行动的趋势是如此强烈,所有的写作活动都变成了引发社会具体变化的武器。逃避现实只是作为对这种集体卷入的冲动的反应而日益常见。政治问题支配了学术思想界。”(注:[美]杜维明:《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钱文忠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6页。)文化与学术思想界的泛政治化,不仅赋予了历次文化运动浓厚的政治色彩,而且也为本应属于纯粹学术领域的争论打上了政治斗争的烙印。而事实上,无论是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还是少数极端的文化守成主义者,在根本立场上并无二致,即都有着强烈的共同体关怀吁求。只不过,反传统主义所诉诸的是在民族认同前提下的对“惰性”十足的“旧文化”和“玄学”的摒弃,以及对以“民主”和“科学”为标识的“新文化”的全盘接收;而文化守成主义则是把民族的文化认同视为民族认同的精神之根。这种非此即彼的中西文化论争政治化的必然结果是导致人们浮躁、偏激心态,因而影响了文化研究和学术探索过程中本应具备的沉静心境和严谨、审慎的态度。而由这种浮躁心态进而所带来的后果是,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中,无论是关于西方文化还是本土文化的研究,大多成为肤浅的符码化的政治宣言和口号,并且随语境的变换而更换不同的“马甲”。因而,正如我们即使在今天也能够体会到的,中国的文化研究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一方面我们为革了命的民族文化传统而痛惜,另一方面,又为成为话语霸权的西方文化而愤懑不已。
陶东风认为,“离开政治权力系统来谈文化霸权只能是瞎子摸象”。他是就当下西方的文化后殖民主义话语在中国风行这一趋势而言的,由此,他进而指出:“中国的文化研究绝不能机械地‘进口’西方文化理论话语,尤其是话题。”(注: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46页。)然而,在我看来,他充其量只说中了一半。其实,无论是西方的现代性话语还是后现代话语,之所以能够风行于中国的文化研究领域,就在于我们始终没有能够得以脱离政治权力系统,恰恰是文化研究的政治化不仅使我们丧失了本土话语阐释权,而且也造成了我们对西方话语转向的误读,因而才不适合地把后现代话语转置到中国现代性尚未成熟的场景之中,并在中国构筑了一道“后殖民主义文化殖民化”的独特景观。
不可否认,文化以及文化研究本身就是关涉价值与价值澄清的领域,因此,在特定的语境下,因为政治权力介入,文化研究很难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但是,从一个民族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长期发展战略角度来看,文化研究的一个更为本位的目的是,如何在充分挖掘传统资源、吸纳其他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以更先进的文化和文明去塑造国民性格和国民精神。而从事这一文化研究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显然不应纠葛着太多的政治情结,不应该是为了服务于一时之功用,因为正是短视的工具性目的和激烈的情绪化倾向,才使得长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的和外来的、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往往做出了要么全盘西化、要么固守传统的极端选择。这种极端的倾向在现实中的直接不良后果反而是,在政治话语宰制下的文化研究,我们既看不到扎实的本土研究成果,也看不到富有创造性的西学研究精品。我们所看到的却是令国人痛心疾首的国学研究中心外移,正如国内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在提出大学人事改革方案时,面对来自部分文化学者的指责而回应道:如今有几位第三期新儒学大师级人物在国内?另一方面,就是西方话语充斥学术思想界,中国文化研究不仅因为话语依附而丧失了独立性,而且因为思想贫乏也失去了原创性。
在一个所谓的全球化时代,面对英语世界文化席卷全球各个角落的情势,中国文化建设再一次成为一个极为迫切的问题。与20世纪前期文化领域内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紧张对峙的时代精神氛围和社会背景既有共同性又略为不同的是,两个时代人们所悬垂的主题都不外乎民族认同的危机,只不过,当下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更趋于主动,而前者则完全陷入半殖民和依附的被动状态。因此,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境遇中,特别是在整个西方世界已进入一个对现代性反思的文化转向时期,再来检讨前期文化研究的取向,无疑有着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检讨过程本身的意义并不在于是否还要把话题断裂的语义及其时间之轴重新衔接上,再去澄清本来就永远不存在确定性答案的问题,而是有无必要重建传统资源,并形成本土的视角去审视全球化中潜在的主流意识形态,或者用外来的视角,重新理解和诠释中国文化之基本精神。
显然,最适合于这种检讨的氛围应是多少超越现实的学术理路清理和学术观点争鸣,它需要人们更为平心静气、在一个更为浮躁的功利社会中耐得住寂寞的繁琐考辨、新旧文献和资料的耐心整理。诚如葛兆光先生在其《中国思想史》中所倡导的,思想史的写作不仅要关注对经典的诠释,而且还要特别关照在历史中那些“日用而不知”普遍知识、思想和信仰,开展这种写作的基本准备则是,拓展文献资料的涉猎范围,重新建构中国知识史和思想史。(注: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7页。)在20世纪早期,这一工作被称之为“整理国故”,它在后期的被冷落也多少映衬了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暗淡无光、对世界文化寥无贡献的窘迫境况。今天它需要复兴的意义在于,不仅是为了充分开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形成带有拓新意义的本土学术视角,而且,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与他文化的平等对话,在彼此的交流与碰撞中发展民族的传统文明观,正如杜维明关于儒学在现代世界中的命运所断言:“‘文革’后中国的内在动力可能会在儒学研究中产生出不可预料的创造性。……对话会给全世界有关的儒学知识分子带来共同的、批判的自我意识,由儒学之根生发出来的原创思想,……会很快涌现出来,激励创造性的学术研究。”(注:[美]杜维明:《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钱文忠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页。)事实上,也只有在对本土文化传统有深厚学养的基础之上,文化学者才不至于仅仅是他文化的迻译者和诠释者,因而完全丧失了自主性和创造性,成为如陶东风先生所责难的机械“进口”外来话语和话题的知识分子。
在一个已被市场和权力资本所殖民化的文化系统中,无疑,创设这样一个有利于学者专注于中国知识史和思想史建构,并善于吸收他文化视角进行严谨的学理性思索氛围,会是何等的艰难。因此,这一关涉中国文化能否在21世纪全球化语境中再次崛起的历史责任,也就自然而然地需要学术性机构、特别是大学来自觉地担当。大学不仅具有传统文化底蕴相对深厚的优势,而且也是各种文化交流、撞击异常激烈的场合,同时,它本身所承担的教育与培养功能又先天地赋予它有条件把文化遗产代代相承、薪火相传的优势。20世纪二三十年代蔡元培先生执长的北大,以及虽然是仅仅昙花一现,却创造了短暂辉煌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即使在今天对我们也颇有借鉴与启发意义。北大蔡先生的“兼容并包”办学思想以及北大国学研究所对中国文化之卓越贡献所论者众,本文不再赘言,而拟就清华学国学院的短短创办史来展开全面的分析。
二、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的文化动因
在近代中国史上,清华可称得上是一个异数。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的创办本身即有着让国人屈辱的感情成份,同时它又是近代乃至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中绝对不可忽略的一个细节。老清华的前身——“游美肄业馆”(1909)、“清华学堂”(1911)和“清华学校”(1912)虽说在严格意义上是用中国人自己的钱创建并维持运作的。但是,它似乎又是美国人“慷慨贡献”的产物。1906年,美国伊里诺大学的校长詹姆士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一个备忘录中,一番苦口婆心的规劝吐露真言:“中国正临近一次革命,……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成功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上、知识上和商业的影响上获得最大可能的报偿。……把中国学生的留学潮流引向美国,并不断扩大这股潮流,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采取精心安排,得心应手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注: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早就对远东地区的利益深谋远虑的罗斯福总统,在派克(Rev.A.P.parker)、李提摩太等一班在中国的传教士和美驻华大使柔克义的游说下,最终接受了这一建议。1908年5月,在他的提议下,美国国会两院正式通过了庚子赔款中“美国应得赔款之余额”给中国的议案,并从1909年正式启动了退还庚款的方案。
由美国的庚子赔款计划而催产出来的清华,创立之初即以为美国大学培养留学预科生为己任,因而,它可谓是近代中国民族大学中西化特征最为彻底的一所大学。曾几何时,美籍教师的养尊处优,西文科华籍教师的优遇,有留美经历的管理者和大学教师主导的格局,课程设置一律照搬美国等做法,一度备受清华内外人士争议。终在1924年,在曹云祥主校时期新任教务主任张彭春的倡导下,清华进行了课程乃至学校结构和制度的变革。新的课程和学制改革的宗旨是“除强调学生应面向世界文化和现代科技外,亦应重视中国文化、国情教育和未来就业需要”,增设大学部(清华升格为独立大学建制之开始),以造就学贯中西,“熟悉世界文化和了解中国社会需要的领袖人才”为己任,而不再专事半成品的留学预备人才的培养。(注: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73-174页。)清华国学研究院就是在这一变革过程中而诞生的。
颇有意味的是,国学院的成立很大程度上是有着留学背景人士的功劳,无论是最早向曹云祥校长提出仿北大国学所建制而成立一国学研究机构,并“有所建言”的胡适,(注: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2页。)还是国学院的直接策划和筹办者的吴宓,乃至后来先后到任的教师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等,都有早先负箧游学美国的经历。然而,清华国学院又绝对不是一个美式教育机构。苏云峰先生称其制度“系略仿中国传统书院、英国大学制和道尔顿辅导制”,不同于北大国学所的“自由松散”,而注重“密集谨严”,在中国实属创举。(注: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7页。)换言之,国学院虽然秉承了中国传统书院重学术考辨、以学术大师主院,“教师以身作则、教学形式教学相长、师生共商”,(注:杨慎初等:《岳麓书院史略》,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56页。)等等传统精神,但它更注重吸收西方严谨细致的科学方法,即胡适所谓的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倡议,如曹云祥校长在国学院第一期学生开学典礼上所言:“现在中国所谓新教育,大都抄袭欧美各国之教育,预谋自动,必须本中国文化精神,悉心研究。所以本校同时组织研究院,研究中国高深之经史哲学。其研究方法可以利用科学方法,并参加中国考据之法,希望从研究中寻出中国之国魂。”(注: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91页。)另外,国学院博采众长,对学术大师的遴选基本原则是学贯中西,而无传统书院典型的一家一派的学派特色。
新成立的国学院由吴宓任主任,所聘请之师资最著名莫过于有“清华四大导师”盛誉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王国维国学深厚,曾是末代皇帝溥仪老师,同时兼通英、日文,并治西欧哲学。到任后,专心学问和教育,可称得上一代名师。人们常以王政治保守而视其为旧学名宿,其中多有偏颇。一封他致马衡的信函足见其包揽四海之学术胸襟:“现在大学是否有满蒙藏文讲座?此在我国不可不设者。其次则东方古国文字学并关紧要。研究生有愿研究者,能资遣法德学之甚善,惟需择史学有根柢者乃可耳。”(注:王国维:《王国维全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36页。)梁启超的背景最为复杂,早年追随康有为主新政,随后亡日立新社,办报编印书籍,“鼓吹开明专制”,(注:夏晓虹:《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2页。)兹后回国从政,继而发布讨袁著论,反张勋复辟,可以说大半生与政治结缘,直到晚年游欧回国后,据丁文渊回忆,受其兄丁文江影响,逐渐开始致力于学术,并淡出政治圈。在到清华从教后,他虽然身兼数职,但热情甚高,劳心劳力,死而后已。与其他四位导师相比,梁可谓一个罕见的通才。不仅对经史子集有深厚的积淀,而且,对西学兼蓄并收,且语言和文字表达极有文采和鼓动性。虽然在政论上有争讼之好,但在学术上对后生之辈循循善诱,且颇有谦谦君子之风。
陈寅恪先生可谓是中国传统学者的典范,甚至被人称为一位具有独立、自由和严肃学术精神与品格的现代中国学者的楷模。家学渊源深厚,通晓十几种(也有人认为二三十种)语言,这在中国学术人物史中可谓独此一家。虽然断断续续有十七八年的欧美游学生涯,但如傅璇琮先生所言:“不管现实是怎样的使人不满,不管自身的遭遇有怎样的不幸,他对于所从事的祖国文史之学绝不能放弃。”(注:张杰等:《解析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他终其一生,融合各国学术思想之长,专注于国学研究。他对中西文化的态度,诚如其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张岱年先生由此评述道:这段话“揭示了中外思想交流的基本准则。……真可谓关于中外文化交流的精粹之言”。(注:张杰等:《解析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111页。)陈寅恪的学术人格之高风亮节、学术思想之丰富,在清华已成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尽管他的学理玄奥莫测,所涉及到的语种繁复杂陈,但依旧深得学生青睐,甚至吸引了众多教师包括吴宓、冯有兰等文化名流来聆听教诲,因而,又被人戏称为“教授中的教授”。这种情景,在今天的大学校园中委实难得一见。
与以上三位背景略有不同的是赵元任。赵元任先生常被人视为一个“怪才”,被人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然而,他早年在美国康奈尔攻读的却是数学和音乐,毕业后留校任物理讲师。然后再到哈佛攻读物理学,并获物理学博士学位,任哈佛哲学讲师。1925年他应聘为清华的哲学教授,此后专攻方言和音韵,并为国学院学生开设《普通语言学》、《现代音韵学》和《中国方言学》。(注: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02页。)据传,此公所到之处,不日便将地方方言掌握到相当娴熟的程度。惜乎在清华期间,他常年专注于外地考察和研究,少有清华弟子得其真传。除以上“四导师”以及吴宓以外,国学院比较有影响的还有李济、马衡、蒋善国、林志钧等,这些人担当或讲师或助教之职。
清华国学院从开办到终止仅仅4个年头,然而,在由名师主授的短短4年中,它却创造了近现代大学史甚至文化史中难得一见的片刻辉煌。与自由、散漫的北大多少有些不同的是,国学院有几个特色颇值得玩味:一是国学院的名师无一例外地是学贯中西,不仅传统国学底蕴厚实,而且深谙西学学术规范、方法以及治学精神,因此,两者间的融会贯通比较自然,少有政论冲突色彩。没有北大胡适、辜鸿铭、陈独秀、刘师培等相互间激进与保守之针锋相对;二是国学院招生录取资格极为严格,首先要有一定国学基础方可,“报考者需先将各项证书及其所著书籍、论文、诗文或读书笔记,寄到清华,以便资格审查,合格者始发给‘准考证’。”(注: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92页。)因此,大多学生实为其他大学和清华旧制的毕业生,以及教师等。学习和研究过程也顺合了清华严谨、细微学风,学制一年,主要在导师指导下专心从事研究,少数优良者可准许继续研究一二年,毕业获证书,但不授予学位。由于学生的起点比较高,其中颇多成大器者。梁启超先生认为,他们之中“可以栽成者,实占三分之一以上,其中有三五人研究成绩,实可以附于著作之林而无愧”。(注: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94页。)事实上,从国学院毕业生后期影响来看,他们之中大多成为中国乃至海外国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和中华文化传统的传播者,据统计,在完成学业的68人中,除11人出国深造外,余下50多人分散在各大学学院担任教学和研究工作。如姜亮夫、姚名达、吴其昌、王力和王静如等一大批知名学者,便是国学院的毕业生,惜乎国学院存活期太短;三是清华国学院不仅开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种方式和途径,而且也创造了一种学术研究和国学人才培养中西合璧的模式。这种模式曾被南洋大学唐文治所仿效,一时间,南洋大学的国学专门学校也“蜚声江南”。(注: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33页。)
三、本土化的学术实践:清华国学院精神之当代意义
清华国学院的夭折,不可否认,王、梁二位导师的撒手人寰是直接原因,但完全以此为据恐怕不足以令人信服。要分析其中真正的内在原因,还应诉诸当时社会文化背景。换言之,国学院的命运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整体的精神状态和社会的人文生态。在急遽变迁和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国学院所追求严肃、审慎的治学精神和淡泊、宁静的心态与时代背景格格不入,因为思想文化界彼此间激烈的抨击和浮泛的批判,无论如何是难以使富有入世精神的人们甘于寂寞、孤守书斋的。也即是说,国学院的沉浮原本只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中一个小小的事件,然而,这一极易为人所忽略的事件,却注解了一个特定时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和运行轨迹及其时代命运。它同时也表明:在中西文化交锋最激烈的时期,我们错失了中西思想融合的一次绝佳机遇。余英时在论及中国文化重建时不无遗憾地说道:自五四以来,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中国文化的拥戴者们,都没有把持好自我,“即使是对于学术思想有真正兴趣的人也不免看事太易,往往根据西方某一家之言便要想贯通中西”,因而,杜威、罗素、黑格尔和康德等等,都先后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扮演过“西方圣人”的角色。“这种浮薄的学风一致流传到今天,还没有完全矫正过来”。(注:[美]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62页。)而在他看来,在今天,要实现中西思想的融合和中国文化的重建,“我们必须把注意力和活动力从政治的领域转移到学术思想的阵地上来”,也就是董仲舒的“退而结网”精神,“献身于学术思想的人永远是甘于寂寞的工作者;他们必须从热闹场中‘退’下来,走进图书馆或实验室中去默默地努力”,“退”不是消极逃避,相反,“从整个文化史的观点看,乃是最积极的进取”。他进而认为,正如儒教之兴起、佛教之进入中国的初期情形一样,我们只有秉承孔子晚年返鲁编定六经、唐玄奘埋头译佛经的退隐精神,一个“在思想上自成系统”的中国文化重建才有希望。(注:[美]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62页。)在此,我们很赞同余先生的“退而结网”精神,尽管它不应是所有文化学者之当然选择。
远离现实生活,经年从事繁琐的资料整理和考证,在今天似乎与时代对知识分子应扮演的角色极不协调。然而,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化的尴尬处境却又让我们不得不去正视这样一个现实:面对纷乱的世事变迁,文化研究领域中人们也竞相去弃旧从新,因而,即使是学术界也难以自持,纷纷热衷于把他文化片断作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良方。其实,这种浮躁正是现实中问题愈来愈多、积弊愈深的渊薮。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是一种止一时之痛的缓解策略,而绝不是标本兼治的长远之计。职是之故,在当下全球化时代,一个更容易产生浮薄学风的社会氛围下,我们才更需要至少是部分文化学者,从“热闹场”退下来,对中国文化之精神传统、外来文化的理路进行扎扎实实地谨慎考证、理性思索和认真的清理。这也就是产生于20世纪早期的清华国学院之制度和精神在当代的历史和文化意义所在。
当然,作为一所具体的研究和教育机构,清华国学院的模式也不是堪称典范、无可挑剔的,因为有“整理国故”之定位,国学院难免太专注于以西学之规范和方法来厘定中国之文化和历史,故而,如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路径常被指责为张之洞政治上“中体西用”在学术领域的翻版,却少了些许如何用中国本土之观念考察他文化的视角,因此,在“体”与“用”传统樊篱中,能否实现真正意义的中西融通颇值得人们商榷。(注:张杰等:《解析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31页。)然而,即使如此,国学院的办学宗旨、人才培养方式以及由它而涵育的学者治学精神、学者风骨,在如今西方话语主宰学术界,尤其是学院知识精英与民间草根力量间的背离愈加突出,学院文化已经丧失了对民间文化诠释权的情势下,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研究和大学制度变革无疑依旧有着广泛的现实意义。
真正的大师从来就不是一味地对外来文化“跟进”,而一点点丧失了民族文化的精神之根的他文化迻译者和诠释者,他是本土的,但又有开阔的世界文化视野;是本土文化的传承者、理性批判者与融合时代精神的新文化缔造者,而不是完全游离于本土传统之外与传统决裂的夹生的呓语者。鄙薄自己的传统和文化,无异于把传统变为博物馆中的古董,而成为他文化的附庸。
标签:清华学堂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清华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国学论文; 读书论文; 学术价值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科学论文; 中国大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