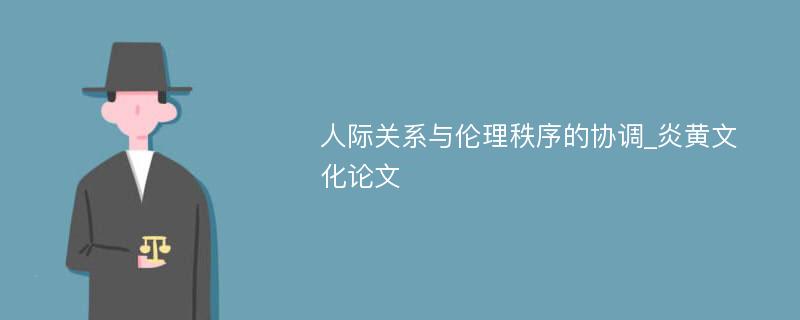
人伦坐标与伦理秩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伦论文,坐标论文,伦理论文,秩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伦”是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最重要的元素;是现代伦理精神建构的基础;同时又是现代伦理困惑中最基本的困惑。在任何伦理体系中,“人伦”都是建构的基础。因为,伦理作为人伦之理,首先必须给人伦定位,由此才能从中引伸出伦理之“理”,没有这样的“伦”,“理”只能是缺乏现实性的抽象。而且,任何伦理的变革与转换,都是基于这种“伦”即人伦关系的变化,其归宿也是最终形成某种新的人伦关系。“伦”变了,调节这种关系的“理”当然也要相应地变革。找到了“人伦”的变化规律,建立了新的“人伦”,伦理的转换也就有了现实的和逻辑的基础。“人伦原理”,是伦理的基本属性;“人伦”的概念,是现代伦理转换与伦理建构的基本概念。
1、人伦与天伦
“人道”基于“人伦”,“人伦”体现“人道”。“伦理”的人伦本性,传统的“人伦”基础,给现代中国的伦理转换与伦理建构提出的课题是:在现代社会中,是否存在传统意义上的人伦关系?是否需要建立一种基本的伦理坐标?是否存在某些基本的乃至可以作为范型的伦理关系?现代人伦关系建立的基础是什么?
人伦的混乱,是社会失序的基本原因;人伦关系的模糊,人伦坐标的倾斜,是伦理体系不能建立,伦理转换不能完成的内在原因。伦理在现实中与理论上的建立,首先必须梳理社会的伦理关系,并从中找到在其中起范型作用的基本人伦关系,以此建立起人伦的坐标与基本的人伦之理。在春秋之际的社会变革与伦理转换中,孔孟的思路也正是在于人伦关系的寻找与确立。春秋之际的伦理转换是对日后中国伦理发生深远影响的转换。孔子揭示了现实社会中的各种人伦关系,并指出了诸种关系的相互关联,把父子关系、君臣关系作为“人伦”的基础,从而把“孝悌”作为“人道”的核心,“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然而,应该说,孔子只是指明了一条思路,他对人伦关系的论述还缺乏系统性与结构性。对这一问题的突破作出重大贡献的是孟子。孟子提出“五伦”,确立了中国传统伦理的人伦基础。“五伦”的“人伦”意义有三个方面。首先,找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的人伦关系。“五伦”对于孔子人伦思想的发展,在于不只指出了现存社会的各种伦理关系,而且在诸多关系中找到了最后起制约作用的基本关系,从而把一切人伦关系都归结为“五伦”关系。其次,建立了人伦关系的结构坐标。“五伦”不仅是社会的基本人伦关系,而且具有内在的结构性、父子、君臣代表纵向的人伦关系,兄弟、朋友代表横向的人伦关系,夫妇则作为一切男女关系的范型,成为人伦坐标中的第三维。于是,一切伦理关系都可以在这个坐标系中定位。由于“五伦”关系是伦理关系的范型,因而一切的伦理关系也就具有了“人伦”的意义;也由于这样一种寻找本位的伦理思维方法,由于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五伦”也就隐涵着日后演化为“三纲”的可能性。第三,“五伦”说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社会的基本伦理问题的解决,也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体系的确立。作为一种人伦模式与人伦范型,“五伦”建立的基本原理是:人伦本于天伦而立。也就是说,社会的伦理关系本于家族血缘伦理关系。这是一种与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相适应和匹配的人伦模式,是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在伦理上的体现。“五伦”从人伦的角度,成功地解决了家国一体社会结构中中国伦理的基本课题,也正因如此,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伦理在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具有不可动摇的支配地位,成为中国伦理的主流与正宗。
“五伦”模式的特殊韵味及其对现代伦理建构的挑战的根本在于一个“伦”字。我们虽然无法判断以“伦理”对应“Ethics”在文化内涵上是否完全吻合,但有一点可以确定,“Ethics”至少不能体现“伦”字的全部文化韵味。在德文中,“Ethics”来源于希腊文“Janok”, 这个词的词根为“Eo—os”和“Novs”,前一字原意为品质气质,后一个字的愿意为风俗习惯。所以,从语意学的渊源看,在西方“伦理”原指社会的风俗习惯与个人的品质气质。“伦理”虽然在以善的价值处理和调节相互关系的意义上是相同或相通的,但在人伦关系的缔结原理及其善恶价值的具体内涵上,却体现出了浓烈的民族特性。“伦”之文化韵味的核心是什么?就在于其家族血缘的基础及其所导致的人伦的自我结构性。任何伦理,在理论上与现实中都必须有一个最后的基础,这一基础成为伦理的根源,在文化体系与伦理体系中,这种最后的或终极的基础决不是理性的结果,而是文化的设定。在文化体系中,伦理的设计与哲学一样,其根本的精神是理性的,但理性的最终的基础恰恰不是理性,而只能是基于一种设定。“理性建立在非理性的基础之上”,这是文化设计的通则。伦理所体现的文化精神是理性的,但这种理性的最后基础只能是生活的设定。于是,中西方伦理便赋予伦理以不同的基础与根源。西方伦理在宗教中寻找这种设定,中国伦理在家族血缘中寻找这种设定。西方文化认为,上帝是伦理的根源,是伦理准则的制定者,也是伦理的归宿与最高的价值取向;中国文化认为,伦理的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家族血缘关系之中,血缘关系既为伦理提供基础和出发点,又为伦理提供范型和最后的价值标准,社会的伦理关系植根于血缘的人伦关系即人的自然的人伦关系。至此,人们便不可能对伦理的基础再作进一步的深究。
传统伦理把人伦设定于家族血缘的基础上,一方面,使得人伦关系与伦理生活具有了最现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又使得伦理具有了与西方宗教伦理相类似的神圣的性质。现实性与神圣性的结合,使中国伦理具有无以匹敌的根源动力与源头活水。这是一种与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以及入世的文化意向相璧合的人伦设定。
人伦设定于家族血缘的基础之上,其最大的特点,便是自然性。家族血缘关系是自然形成的既具有生物性又具有社会性的伦理关系,是最基本的伦理关系,在长期的生活积淀中,这种关系以及处理这种关系的某些准则,具有天经地义的性质。尤其在中国这样的以家族为基础和范型的社会结构,以及农业性的生产方式中,家族伦理更是具有绝对的意义,家族血缘的存在往往先于个体生命的存在。而且,由于人在社会性之中所内在地具有的生物性与生理性的特质,由于人类文明社会是从氏族部落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血缘的人伦关系与人伦法则就具有某些跨文化的世界性意义。血缘人伦,既是人的生物性自然,又是人的社会性、伦理性的自然,家族血缘的人伦关系,是元人伦关系。而且,由于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族伦理在社会伦理生活中确实具有基础的意义。在中国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中,由于“家”直接就是“国”的缩影,血缘人伦直接可以构成社会伦理的范型。在整个伦理系统中,家族血缘伦理,就是人的“自然”伦理,家族道德,就是人的“自然本德”。与西方伦理把人伦设定于超越性的上帝的文化设计相比,血缘人伦的设定,不仅体现了中国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的特质,是“中国特色”的体现,而且也使得伦理的基础更具有现实性。从文化设计的原理上考察,以上帝为伦理的根源,当然使人伦具有了神圣的性质,但它只有在浓郁的宗教文化气质中才能运作,一旦文化还原为世俗生活,这种人伦就失去了自身的约束力,于是我们发现,宗教的人伦设定只是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才能发挥巨大的作用,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就需要强大的法律的支撑。血缘的人伦设定则不同。它同样具有宗教的人伦设定的那种神圣性,但同时又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具有现实的约束力,是入世文化的伦理设计。
血缘的人伦设定的另一重要特点,就是它的自组织性。在中国文化“伦”所体现的文化气质,首要的就是它的血缘特性,这种血缘特性由于它的先天性,因而是“天伦”。但“伦”同时又是一个社会组织的概念,准确地说,是社会的自我组织的概念。在中国文化中,血缘的概念,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的伦理秩序的概念。西周维新的最大成功,就在于把氏族血缘的原理,上升扩充为文明社会的国家社会的原理,形成血缘—伦理—政治三位一体的社会秩序原理,宗法的精神,是中国文化中血缘伦理的基本精神,它使得传统伦理具有极强的自组织性。这种自组织性,既表现为社会的人伦秩序的既定性,又表现为个体在社会的伦理秩序中的自我定位,同时还表现为这种血缘的伦理秩序,透过伦理的中介,向社会与国家扩充延伸,形成社会的自组织。这种人伦的原理,便是所谓的“伦理政治”——政治伦理化与伦理政治化。中国传统社会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从文化原理上说,就是透过血缘伦理的自组织,建立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原理。血缘的人伦设定,不仅使自然伦理自组织,而且还由于这种自然伦理的自组织,社会伦理也具有巨大的自组织功能。可以说,“家长制”就是这样的伦理政治,这样的在血缘伦理的自组织基础上建立社会伦理秩序与政治伦理秩序的集中体现。
既然血缘人伦是一种设定,既然社会的伦理体系无论如何需要某种最后的设定,那么,我们所可以做和必须做的努力,就是对这种设定本身的合理性进行考察。如前所述,这种设定本身是与中国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相吻合的一种文化设计,体现了“中国特色”,因而对这种设定在传统社会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就应当给予肯定,就是说,它是中国传统社会必然的和必须的文化设定。同时,由于这种文化设定创造了传统社会的辉煌的伦理文化,并且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因而对这种设定的历史合理性也必须给予肯定。处于20世纪末的人们可以对传统社会的文化进行各种指责,但我们不应忘记,这是在时隔几个世纪后作出的批评,时代的背景已经被历史垫得好高,我们的视野也已经被历史开拓得更为宽阔,只要联想我们今天遇到的伦理困境,以及人们在这种困境面前的一筹莫展,就应当为当初历史作出这种人伦设定智慧而惊叹!当然,也不可否认,由于这样的家族血缘本位的人伦认定与人伦设计,使得中国伦理潜在着许多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或者说,面临着许多难以解决的理论课题。譬如,家庭本位,如何完成家族人伦向社会人伦的过渡,如何为这种过渡找到中介环节,这些课题,被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出色地解决了。但隐涵于其内的深刻矛盾,如伦理生活中各种伦理角色的冲突,尤其是家庭成员与社会公民两个同时存在的伦理角色的冲突,又是传统伦理设计的内在的否定性。
2、人道与人理
人伦的设定,还只是对社会的伦理关系、人伦秩序的设定,这些伦理关系、人伦秩序如何获得现实性,还有待伦理主体对这种人伦设定的认同,因此,在客观性、客体性的“伦”之后,还必须有主观性、主体性的“理”,“伦”与“理”的结合,才使“伦理”具有真正的现实性。于是,“人理”的设定,就成为人伦原理设计的另一个重要构成。
如果说,社会伦理的基本概念是“伦”,那么,个体伦理的基本概念就是所谓的“份”。传统文化以“辈”训“伦”,而与“辈”紧密相联的是另一个字“份”,“份”构成“伦”的重要内容。“份”者,分位也。“份”的意思,就是在伦理关系、人伦秩序中的份位即人伦地位、伦理地位。从个体性与主体性的角度理解,“份”即是伦理的权力和义务。在社会的伦理网络和伦理秩序中,“伦”不同,“份”也就不同;人伦地位不同,个体的伦理权力与伦理义务也就不同。在传统伦理的设计中,“伦”与“份”设计的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二者之间关系的相对性。“份”由“伦”决定,“份”的伦理目的和最高取向是要维护这种“伦”,但同时“份”又构成“伦”的实质性内涵,二者形成一种以区分为中介,秩序为目标的伦理和谐。
“伦”与“份”的相互性,就构成了伦理关系的特点。人伦的设计,归根到底是一种关系或价值关系的设计,这种设计的目的是如何形成有机的、有效的、合理而又密不可分的秩序整体。对这种关系的设计,中国经典伦理的设计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在强调“伦”的相对性与差别性的基础上,突出人伦关系的相互性,即伦理主体之间“伦”与“份”的互动互惠。“伦”与“份”的相对性,伦理生活中“伦份”互动的相互性,在理论上与现实中就构成了人伦运作的所谓的“理”,即人伦之“理”。从“五伦”的坐标来说,“五伦”关系,就是五种相对应的人伦关系,这五种关系的处理,既遵循某些共同的准则,各种“伦份”上的人的地位又应有所不同。孟子在解释伦理起源时,言明“使契为司徒,教人以伦”的内容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亲、义、别、序、信,就是五伦关系分别应当遵循的共通准则。然而这些准则如何落实,又要根据各自的“伦”“份”而定,其具体的要求是: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这种原理体现了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伦不同,人伦关系不同,伦理的内容与体现也就不同,父的伦理是慈,子的伦理是孝,不可“一视同仁”,更不可置换,否则便是“乱伦”;二是伦理关系以相互期待为前提,而在相互期待中,又以在上者、在尊者为主动,隐含的逻辑是:父慈子才能孝,君仁臣才能忠,伦理的过程,是一个“将心比心”,“以心换心”的互动与互惠的过程,由此才有孟子的“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的结论。这当然体现了经典伦理设计的人民性,但也潜在着在相互期待中陷入伦理的恶性循环的危险性,因而潜伏着日后“五伦”演化为“三纲”的逻辑可能性。
“伦”与“份”的对应,“伦份”之中人伦之“理”的运作,在理论上提出的课题,就是伦理权力与伦理义务的问题。“份”的概念,本质上是由“伦”所导出的伦理权力与伦理义务的概念。对伦理义务的存在及其必要性,人们在理论上并不提出多少怀疑,伦理强调人对人、人对社会的责任,这种责任经过价值的提升,就转换为伦理的义务。伦理的本质,伦理的可贵,就在于这种责任不是外在于自身,而是“应当”履行的义务。在康德那里,这种义务被神圣化为“绝对命令”,因而提出所谓“为义务而义务”。一谈到伦理的权力,问题似乎就复杂化了。一方面,由于人们在观念中把伦理与义务简单地相等同,似乎一提及权力,就不在伦理的范畴;另一方面,权力的概念似乎又是具有某种功利性和强制性的概念,因而与伦理注重动机与行为的主动的特性不符。事实上,伦理的权力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没有这样的权力,伦理本身也无法运作,甚至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意义。在对传统伦理对“伦”与“份”设定的原理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迪:“伦”即伦理地位、伦理关系的定位,是伦理运作的前提;伦理的整个运作,其最后的目的,就是对某种伦理地位的尊重和维护。伦理是调节利益关系的,而利益关系调节的实质,就是对这种关系的肯定,如果从关系主体的意义上说,也就是对人伦主体的利益的肯定,人伦主体的利益,在伦理生活中,是通过他所在的“伦”来体现的。既然伦理调节的是利益,维护的是“伦份”,肯定的也就是人们的伦理权力,因为对利益主体与人伦主体来说,之所以需要伦理的维护,逻辑的根据就是因为它是自身的伦理权力。因此,从伦理主体与伦理个体的意义上说,伦理所肯定并维护的,就是伦理的权力,没有这样的伦理的权力,伦理就失去了对象与内容。这是伦理权力的基本内容。从主体之间的伦理关系来说,也存在一个伦理权力的问题。在上者、为尊者之所以负有主动的伦理义务与伦理责任,就是因为他们有着不同于与之相对应的伦理主体的伦理权力。譬如,在“君仁臣忠”的伦理互动中,可以对伦理权力作这样的理解:一方面,仁与忠分别是君与臣的不同的伦理权力;另一方面,仁与忠归根到底维护的是君与臣在各自份位上的权力;而且,当君施以仁之后,就有权力要求臣回报以忠。整个中国传统伦理,是建立在对“回报”的期待的基础上的,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回报是中国文化的三女神之一。“回报”就是一种伦理的权力。没有对伦理权力的肯定,任何伦理体系、伦理生活都无法建立。宗教伦理强调因果报应,肯定的是伦理的权力;世俗伦理强调善恶报应、“德”“得”相通,肯定的也是伦理的权力。当然,这种权力必须以伦理义务的履行为前提。伦理的权力和义务,就是经典伦理设计中“伦”与“份”相分相联的真谛。
“伦”与“份”的关系,又逻辑地演绎出“名”与“份”的关系。在中国文化、中国伦理的发展中,存在着“名”与“份”相关联的两种状况:一是“名”“份”相联,有“名”必有“份”,反之,有“份”就必须有“名”;二是“名”“份”相异:有“名”未必有“份”,这是徒有“虚名”,有“份”也未必一定要有“名”,这便是僭越。前一种情况,呈现的是伦理的有序状态;后一种情况,则被称之为伦理的失序。伦理的有序与无序,与“名”与“份”的关联状况有着直接的联系。经典儒家对伦理秩序的设计,就是首先确定人伦秩序与人伦关系,然后要求伦理关系中的每个个体都恪守本份,由此便建立起了伦理的秩序。这种设计的前提,是强调人伦秩序的不变性与伦理权力与伦理义务的神圣性。因此,孔子提出的治理春秋时期伦理失序的良方便是所谓“正名”,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民无所措手足。”“名”与“份”,即使在现代中国人的伦理生活中,也是一个事实上发挥着巨大作用的现实概念。
3、“安伦尽份”:人伦与人道的统一
伦理的努力在于建立某种伦理秩序,而伦理秩序的建立与维系,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人伦坐标的建构,一是处于这个坐标系上每个坐标中的伦理成员,都能“安”于自己的伦理地位,克尽自己的伦理本务。对这种秩序要求,中国传统伦理用一个特殊的概念来表达,就是所谓“安伦尽份”。“安伦”,是在人伦坐标中确定自己的伦理地位,既不僭越,也不“乱伦”;“尽份”,即是在各自的伦理地位上履行应尽的伦理义务,包括享有并维护自己的伦理权力。“安伦”是人伦,“尽份”是人道;二者的统一,就是“伦”与“理”统一,人伦与人道的统一。对于伦理主体来说,“安伦尽份”的观念,在伦理的意义上与西方文化的“自我实现”的观念有点相似。但是,如前所述,这种伦理性的“自我实现”首先必须以人伦关系的确定性为前提,人伦关系不确定,或确定了不稳定,“伦”就无以“安”;其次必须以人伦关系的合理性为前提,如果人伦关系不合理,“安伦尽份”的伦理努力就会成为一种惰性力。而事实上,这两个前提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具备或者都同时具备的。不仅如此,“安伦尽份”的实现,也需要某些特殊的文化机制,也内在着许多特殊的文化矛盾。这些矛盾就成为中国伦理精神现代建构的理论课题。
人伦设计与人伦建构的问题,在现代伦理建构中碰到的基本课题,就是个体本位还是人伦本位的问题。这一课题至今虽然还未能真正解决,但一些基本的方面似乎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达成了某种“共识”:人伦本位是中国伦理的传统,它给中国伦理与社会发展带来了诸多的弊端;个体本位是西方文化的传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着时代的精神。如何确立现代的伦理本位?人们似乎陷入了文化的二律背反中:个体本位与人伦本位似乎都有内在的缺陷。于是努力寻找“中国特色”,突出辩证综合,可是至今仍未综合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这时,关键还是建立什么样的文化哲学,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重要的还是一个理念:任何文化设计,乃至任何文化要素,不可能苛求它只有优点,没有缺点,因为特点本身就是偏缺。根本在于,在文化系统中,在各种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如何充分发挥这种文化要素、文化设计的优越性,扬弃其局限性。于是,在现实的运作中,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就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个人本位固然对建立充满活力的个体是有利和有效的,但它导致的个人主义,导致的人伦与生活情趣的失落,也是不可否认的缺陷,这种缺陷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社会与个体的自组织能力的低下,也造成了生活意义本身的失落。个体本位是与法制主义和上帝的最终裁决相匹配的文化系统。在文化设计的系统中,人人为自己,但为自己的行为必须受作为普遍意志的法律的制约;人人为自己,整体则由上帝来照顾,“上帝为大家”,隐含的意思是说,最后能否达到“为自己”的目的,则是由上帝决定的。
人伦本位的设计,对于个体主体性的理念似乎也存在某种背反:一方面,人伦本位的设计要求在人伦的建立和维护中必须首先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和自由性,使自己的个体性服从人伦的整体性的要求,放弃个性的独立性是人伦本位的逻辑要求;另一方面,人伦的自觉建立与维护,在人伦关系中的自觉定位,恰恰需要的又是个体伦理主体性、道德主体性的确立和弘扬,没有这种主体性,人伦本位就无法确立。在这个意义上,人伦本位,抹杀的不是个体的主体性,它扬弃的与其说是主体性,倒不如说是抽象的个体性,这种抽象的个体性,不是个性的现实,个性的现实是它的社会性,抽象的个体性不是现实的个体性,而只是个性的任意,是无社会性内容的个体性。因此,现实的个体性,道德的主体,是人伦本位得以确立的前提性条件。人伦本位的设计当然容易导致整体至上、秩序至上的文化价值取向,当与封建制度相结合时,它容易形成专制主义,在日常生活中也容易导致对个性的抹杀。但也不可否认,整体性、秩序性是任何社会持存的基本条件,人伦本位对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它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伦理根源。造就的是巨大的文化凝聚力和柔韧的社会自组织力。
从社会的伦理关系与现实的伦理生活的角度考察,个体本位与人伦本位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在建立和调节相互关系时,在对个体的社会定位中,对伦理主体的个体性理解和关系性理解。个体本位是对伦理主体的个体性理解,其直接的结果是对个体权力的追求和对个体义务的履行,但个体本位必须以明确的、普遍的、公认的规则的存在为前提,否则就是盲目的个体,个人主义就会流于利己主义。人伦本位是对伦理主体的关系性的理解,它从自身与他人的不可分离的“关系”的角度理解主体,把他人的要求和评价作为行为的重要依据,这当然会导致个体自主性与独立性的部分丧失,甚至适应依赖性的个体,但它造就的整体性和秩序性却是伦理的直接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伦本位,更能体现伦理的本性。
个体本位、人伦本位的伦理定位,在个体精神机制上的表现,就是理性本位与情感本位。从精神结构上说,个体本位的伦理定位的内在机制是理性本位;人伦本位的内在机制是情感本位。理性与情感的问题,在哲学上,在文化价值体系中,在人的精神结构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从文化特性上说,它体现着中西方文化、中西方伦理、中西方人的差异;从伦理精神体系上说,它体现着伦理定位的差异。在人伦关系上,在个体的确立方式上,理性主义的著名命题是:我就是我。我是权力的主体,也是义务的主体。权力不可侵犯,义务也不可逃脱。于是,理性主义便用“理性”的围墙筑起了一道“人”“我”之间不可逾越的疆界。在这里,并没有给情感留下太多的地盘。正如我在《文化撞击与文化战略》一书中指出的,在文化设计中,西方人的情感是在宗教中完成的,宗教,尤其是作为终极关怀的上帝,是情感的源头,也是情感的规范力量。中国文化的设计则不同。中国伦理的机制,从个体精神结构上说,是情感的机制;中国伦理中的主体,主要是情感的主体。与理性相比,情感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不能自我完成、自我实现,必须借助对象来宣泄和满足。离开了对象,情感只是抽象的心理,而不是现实的人的情感,于是,必然要求建立起个体与他人间不可分离的关联。情感的逻辑是:我就是我,同时又不是我;我是情感的主体,但我又是不能独立的。于是,他人、关系就是主体的必须。如果说,理性主义建立起了个体之间不可逾越的疆界,情感主义则用情感的流水冲破了这个疆界,或者说模糊了这个疆界。中国文化是一种血缘文化,中国伦理是建立在血缘的基础上的,而情感的逻辑,则是家族血缘的绝对逻辑。家族血缘不仅为伦理情感的滋生提供了深厚的根源,而且也提供了范型和巨大的规范力量。无论如何,情感的机制,情感的精神结构,是人伦形成的必要机制。在这方面,人们同样不能抽象地评价理性与情感的问题,而必须从伦理的本性、伦理的价值取向,从整个文化系统上进行考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情感更能体现伦理的本性。
“伦”与“份”的矛盾,本质上是伦理与道德的矛盾。“安伦尽份”,既是人伦秩序维护的必须,也是对个体道德的要求。在这种要求中,人伦与人伦秩序是被当作当然的前提和认同的对象,于是必然发生伦理与道德的矛盾。在伦理的设计中,“伦”表现为“名”,是伦理的地位;“份”则是个体道德的涵。“名”与“份”之间,既存在着逻辑要求上的一致性,在现实的运作中,又存在着事实上的分离性乃至背离性。就是说,享有伦理的地位,并不履行应当的道德责任;或者说,伦理地位只是一个空“名”,并不在事实上享有相应的道德权力。“伦”与“份”的这种背离,就是伦理与道德的分离,其结果就是人伦的紊乱与道德的失落。而当人们在一定的人伦秩序中“安伦尽份”时,如果这种秩序本身并不具有真实的合理性,道德所维护的也就是一种不合理的伦理,而由于伦理的不合理,道德也就事实上无合理性可言。当社会的伦理出现紊乱甚至败坏时,如果人们按照伦理的现存行为,就意味着伦理的混乱为道德的败坏辩护。人伦本位、情感本位,最后的价值取向是伦理至上,秩序至上,在这里,个体最现实的主体性,就是道德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的作用的结果,在追求伦理与道德的一致性的同时,也内在着二者的分离与背离。无论如何,伦理与道德的矛盾是内在于人伦与人伦的设计之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