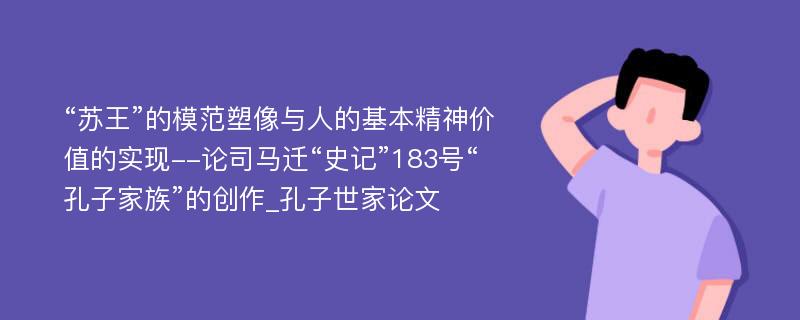
“素王”典范造像与人的本质精神价值实现——论司马迁《史记#183;孔子世家》的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孔子论文,造像论文,与人论文,典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12)05-0040-13
一、“素王”著述伟业传人与“素王”造像
在司马迁的《史记》写作中,《孔子世家》占有极为特殊的地位。古今对《孔子世家》的研究,既深且广,似乎少有置喙的余地。但我们仍可抱持“最深切的同情”,以思司马迁怎样写成《孔子世家》,并赋予古今研究结论以些许鲜活的思想色彩与情韵。而依据“最深切的同情”标准,尽管司马迁所写的历史人物不知凡几,但如果要问谁是与其自身生命价值追求及《史记》总体写作关联最为深密之人,则不得不推为孔子。
这可从以下三个层面来说:
其一,司马迁奉孔子为其思想精神之“父”,自视为孔子“素王”著述伟业的第一传人。①关于这一点,可从《太史公自序》知其大概: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②总括司马迁的自述,当包含两重用意:一方面,尊奉“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的封建伦理价值理念,继承祖上世代相传尤其是被其父视为生命的史家著述事业,是其以写“史”而非其他方式进行文化著述的现实原因;另一方面,宣称自己“史”的文化著述,甚至直接前承“素王”孔子,实有奉孔子为其思想精神之“父”的意涵。③由司马迁引述并认可父亲司马谈的论断可知,司马迁确实自认其“史”的著述,必将成为华夏史上继周公、孔子之后伟大文化著述的第三大里程碑:周公是有史以来以在位辅政之身进行文化著述的伟大典范,孔子开创了“素王”著述的伟大传统,司马迁本人则是真正接续孔子“素王”著述伟大传统的第一传人。④司马谈与司马迁以五百年为一周期的依据,正来自“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天命“圣王”观⑤,而其引述这一天命“圣王”观,则是为了强调:自周公之后,这种本当属于在位当政王者的伟大著述权,实际就落在了“在野”行“道”的“素王”身上,“素王”孔子之后,更是落在了史家司马迁本人身上。司马谈不提孔子身后的孟子、荀子等伟大的思想家,而是讲自“孔子卒后至于今”已有五百年了,应该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的文化王者出现,故寄厚望于自己的儿子,司马迁因此以“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表达其接受父亲重托,并以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精神传承孔子“素王”著述伟业的坚定信心与意志。由司马迁的自述,我们确实也感受到了其传承孔子“素王”著述伟业的伟大精神气象。⑥
其二,最为关键性的因素是,司马迁身处大汉王朝最为鼎盛的武帝时代⑦,却以“李陵事件”横遭宫刑⑧,这使其能够更为透彻地认知封建王权专制独裁政治体制的真实本质,从而实现世界观、人生观的超越、升华,真正进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自由创作王国,以《史记》成功构建其伟大庄严的人学价值体系。⑨而在这一生命的超越、升华过程中,历代“圣贤”遭受人生悲剧后的发愤著述行为,尤其是“仲尼厄而作《春秋》”,成为激励其勇敢面对巨大人生悲剧、坚持写作《史记》的强大精神动力。⑩
一方面,当其深刻反思人类的永恒精神价值追求及其普遍性悲剧命运与封建王朝专制政治体制的关系问题时,对具有伟大政治抱负,却终身坎坷,不得不“在野”行“道”以成就“素王”伟业的孔子事迹的认识,促使其能够更为彻底地从根本上反思现实政治权力结构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更加坚定地认同、肯定在封建王权专制独裁体制压迫下,人类精神价值追求的高度正当性与高贵性,更为自觉地高扬人的独立尊严与主体精神意志,从而将人的生命本质精神价值的真正实现与否,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第一标准,而不是注重现实利禄权位的获得与否。故当司马迁进行《史记》人物的总体构架时,就能够真正超越“在野”、“在位”观念,并在实质意义上将蕴含“素王”—“素臣”永恒精神价值的权力结构模式,树立为理想的政治权力结构的最高范本。其三十“世家”首选具有让位美德的吴国建国始祖吴太伯,七十“列传”首选有让国美德而甘贫乐道终于饿死的伯夷、叔齐,并直接将孔子及其弟子分别写入“世家”和“列传”。这种迥异于后世封建正统史家的“世家”、“列传”人物选择方式,就完全打破、超越了现实政治权力结构的常态,标示了其对封建政治权力结构存在意义的深刻思考。(11)司马迁对政治权力结构本质意义的认知,立足于深刻反思所谓“天道”与人类道德理想追求的因果背反现象基础上,最为关键的影响,显然来自孔子。而相比于吴太伯与伯夷、叔齐,如前所说,司马迁既自视为孔子“素王”著述伟业的第一传人,其认同、表现“素王”孔子,毋宁说就是另一种自我认同、表现方式。
另一方面,就孔子生平事迹而言,虽然其主要是以“在野”方式躬行“素王”之事,但其具有短暂、间接性特征的从政经历,也是其实践、追求政治理想的重要人生亮点,实可补偿司马迁由于没有机遇以实现其政治事功欲求,而不得不将全部精力投注于文化著述活动的心理缺憾。事实上,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借其父之口叙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所谓“续吾祖”,虽主要是指伟大史学著述,但在对其祖先“自上世尝显功名”的深情追忆中,显然也潜含着其对政治事功的心理欲求。我们认为,指出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学界迄今为止的研究,似乎还较为忽视司马迁的伟大史学著述与其自身的政治事功心理欲求的关系问题,这无疑也制约、影响了对司马迁全人及其史学著述成就问题的研究。
其三,司马迁不仅将孔子视为心目中的第一精神偶像(12),对孔子抱持“最深切的同情”,“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又亲往考察其遗迹和现实影响。《孔子世家》结尾的“太史公曰”,表达了司马迁无比崇敬热爱孔子的心情: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13)
对孔子最为亲切、鲜活、丰满、立体的认识,不仅激励遭受巨大人生悲剧的司马迁更为坚强、更“好”地活着,不仅为其将孔子写入“世家”和以何种写作方式成功塑造一代“素王”典范提供了充分保证,也为其《史记》总体思想写作与形象塑造高度提供了重要保障!
质言之,基于上述三点已可论定:在孔子身后,作为汉世一人而已的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已然就是最为合适的孔子“素王”造像者。
二、“素王”典范造像与孔子的大政治家风范
直接进孔子于“世家”,进以颜回为首的孔门弟子于“列传”,自然是由于在司马迁心目中,躬行“素王”与“素臣”之“道”的孔子及其门徒,绝不稍逊于历史上那些以事功名垂千古的王侯将相。(14)甚至还可进而这样认为:其以孔子及其门徒分别入“世家”、“列传”,本就含有将孔子及其门徒所构成的“素王”—“素臣”模式,作为政治权力结构的理想范本的写作意图。由此以观《史记·孔子世家》煞费苦心、周密编选史料的特定写法,当能更为深刻地体认本传以发显、褒扬孔子及其门徒躬行“素王”“素臣”之“道”为旨归。最需关注的是两大方面:第一,写由于孔子真正具备大政治家才器、风范与理想追求境界,却难得其“位”,于是就以“在野”方式躬行“素王”之道,成为能够宠辱不惊,善处“出”“处”去就,躬行“素王”之“道”的伟大典范;第二,写躬践“素王”之“道”的孔子,与追随他的贤徒,实际构成了与春秋时代现实政治权力结构对比鲜明的“素王”—“素臣”结构模式。
本部分主要讨论第一方面的问题。
在司马迁心目中,孔子真正具备伟大政治家的才器、风范与理想追求境界,只是由于难得其“位”,才不得不以“在野”方式躬行“素王”之“道”。故其在完整再现孔子成就“素王”伟业的人生历程时,格外注重全方位发显其政治禀赋、长才、理想与事功以及对从政的高度热忱,以映衬其遍历艰难困苦、躬行“素王”之“道”的伟大精神意义,甚至还由“最深切的同情”,不惜人为地美化与拔高。
其一,首先分五点叙述孔子三十岁以前的人生事迹,写出孔子卓异的政治禀赋、素养以及自我奋斗精神,以作为写其生不逢时、难以用世的悲剧人生的重要前奏。
一是开篇即比照“圣王”规格,写其神异的出生事迹及得名之由。尽管司马迁并不回避孔子是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之子,但“祷于尼丘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则刻意写出孔子降生乃是秉承上天意志:“生而首上圩顶”即是具有“圣人”特异之貌的明证。(15)无论孔子是否真正“生而首上圩顶”,司马迁采纳此一关涉“圣人”出生传说的用意,明显与借身体最显要的头部以指称帝王为“元首”同一思致。而在传的后面,司马迁写孔子于周游列国后,晚年愿意回到鲁国的原因是“鲁复善之”,而“鲁复善之”的原因,不仅由于孔子声誉广著,还因“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司马迁如此写法,除了解释孔子何以能够以极为充沛的生命元气与强大的精神意志顽强奋斗一生,是否也在暗示:如此特异体质,或当是天命“圣人”的身体标志?
二是写孔子在少幼时代,即嗜学自强,曾因以少幼之身而想参加鲁文学之士的聚会,遭到阳虎绌退:
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16)
三是写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故在十七岁时,就以娴熟于“礼”而获得鲁大夫孟釐子对其未来的预言:
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诫其嗣懿子曰:“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兹益恭,故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其恭如是。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身为鲁国地位显赫的大夫,孟釐子直到晚岁尚且不能得窥“礼”学堂奥,而少年孔子即已“好礼”(17),孟釐子由此联想到孔子本为“圣人”之后,且其祖上以让位美德与辅佐大功,累积了“三命”厚德,孔氏后人“虽不当世,必有达者”,故预言这“达者”之“命”必将应验在孔子身上。(18)司马迁写孟釐子预言,与其写吴泰伯与伯夷、叔齐均以善让美德成就事业正同一机杼;也与前引《太史公自序》述其祖上“上世尝显功名”而终以史学著述为业同一思致。
四是揭示孔子在早岁贫贱之时即已显露为政潜质,这是其日后能够成为鲁国司空的重要原因:
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这种写法在《史记》中经常可以看到,如《陈相国世家》就写陈平年少为社里宰肉公平,日后终于成为大汉相国。
五是写孔子还专以“适周问礼”为名,求见“仁人”老子,得到老子“送之”的特殊礼遇,并亲炙老氏“为人子者”、“为人臣者”这种“家”“国”“人”三位一体的政治学教诲: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19)特写“弟子稍益进焉”,是在孔子以向老子请益为目的而“适周问礼”,并得到老子指导返回鲁国后,这分明是说经过老子的指导,孔子已在人生事业选择的主导思想以及实际的教育方略方面达到成熟境界,且取得重要成效。
可见,司马迁历数孔子卓异的政治禀赋、素养、受教及自我奋斗精神,意在说明三十岁以前的孔子已经具备了实现其伟大人生抱负的基本条件。紧接着,司马迁就特别点出了孔子三十当立时的特定时代背景:
是时也,晋平公淫,六卿擅权,东伐诸侯;楚灵王兵强,陵轹中国;齐大而近于鲁。鲁小弱,附于楚则晋怒;附于晋则楚来伐;不备于齐,齐师侵鲁。就周王朝当时的处境而言,不要说昔日一统天下的辉煌鼎盛,就连诸侯辅助王室的霸业都已盛景难再;就孔子所处的鲁国而言,这由周公发始之礼仪之国,甚至已经弱小到难以自保。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孔子迎来了其三十当立的岁月。司马迁选择如此特殊的生命时间来写孔子生不逢时、难有适合其施展伟大抱负的政治舞台,确实耐人寻味。
其二,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写即便如此,孔子也并没有为迎合当世而放弃其大一统“王道”的政治理想。不遗余力地宣讲大一统“王道”理想,正是贯穿孔子政治生涯的重要内容。
面对现实政治情势,处于三十当立之年的孔子,其念兹在兹的,就是期望有诸侯能够起而复兴齐桓、晋文之事,以“道义”佐助衰弱的王室。故在本年,当“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的后人齐景公与其名相晏子访鲁,并向孔子请教秦穆公获得霸业的原因时,孔子即借以强调“王”业:
鲁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盖年三十矣。齐景公与晏婴来适鲁,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说。在孔子看来,即便有如此意愿的诸侯国或许弱小僻远,但只要志存高远,身行中正,任贤使能,艰苦努力,终可达成霸业。而“虽王可也,其霸小矣”,则见出孔子的认可、推崇霸业,只是不得已情势下的退而求其次,如何称“王”以实现“王道”理想,才是其终极关怀所在。再如:
吴伐越,堕会稽,得骨节专车。吴使使问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节专车,此为大矣。”吴客曰:“谁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纲纪天下,其守为神,社稷为公侯,皆属于王者。”客曰:“防风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为釐姓。在虞、夏、商为汪罔,于周为长翟,今谓之大人。”客曰:“人长几何?”仲尼曰:“僬侥氏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之,数之极也。”于是吴客曰:“善哉圣人!”当吴国在与越争霸的政治军事活动中,“堕会稽,得骨节专车”,遣使垂询于孔子,孔子也陈义甚高,指出只有足以纲纪天下之守,才配厕身“圣王”大禹所统御之群神行列。故其“大人”、“僬侥”云云,可谓意在言外。复如:
有隼集于陈廷而死,楛矢贯之,石砮,矢长尺有咫。陈湣公使使问仲尼。仲尼曰:“隼来远矣,此肃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峦,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贡楛矢石砮,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肃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分同姓以珍玉,展亲;分异姓以远方职,使无忘服。故分陈以肃慎矢。”试求之故府,果得之。在孔子心目中,有隼远来,其所中“肃慎之矢”,勾起的是对“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蛮”,建立“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类“王制”的追忆。怀想“先王”曾分陈以“肃慎矢”,而今王室衰弱,“肃慎矢”却来陈,“贡矢”职业安在?这里,司马迁写出的,不仅是孔子的博学多识,还当有其对“王道”理想的特别关切。
而孔子所推崇备至、思慕形于梦寐的,仍是建立伟大“圣王”功业的文王: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20)能够使其三月不知肉味的,仍是表现“王道”政治的“韶乐”:
……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
其三,司马迁以年代为序,交替表现孔子的政治事功与躬行“素王”之“道”,尤其不遗余力地表现其政治事功,以及其即便“在野”,从政热忱也从不稍减。
表现孔子政治事功的,主要是三大亮点:
一是写孔子得到鲁定公任用而以为政优异连获提升:
其后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
二是写孔子以大司寇行摄相事取得卓越政绩: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途;途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
三是写孔子于齐鲁夹谷之会“摄相事”获得重大成功:
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齐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夹谷。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曰:“诺。”具左右司马。会齐侯夹谷,为坛位,土阶三等,以会遇之礼相见,揖让而登。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于是旖旄羽祓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鲁君,为之奈何?”有司进对曰:“君子有过则谢以质,小人有过则谢以文。君若悼之,则谢以质。”于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21)
说孔子在当时取得过重要政绩,这当然毫无问题,但写其为政一年,就使“四方皆则之”;写其拨乱反正,而“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就使“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途;途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甚且使齐国因担忧“孔子为政必霸”会威胁到齐国,而刻意设计以使其离职(详见后论);写其“摄相事”,不仅以果勇智谋震慑强齐之君臣,捍卫、保全了较为弱小的鲁国之尊严、利益,甚至还使“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刻意将孔子塑造成在春秋乱世取得重要事功的杰出政治家,有无人为的美化与拔高成分呢?
表现孔子“在野”时仍对从政抱持一以贯之的热忱,则主要写其“在野”行“道”而备历艰困,但为了实现政治理想,不放过任何可能的从政机遇,甚且因时不我与、机遇难得而不惜委屈自己。所写两例最为典型。一例写:
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欲往。子路不说,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然亦卒不行。
佛肸为中牟宰。赵简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闻诸夫子,‘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亲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故当“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孔子听说后,就以急迫的心情抱怨子路,并教其如何回答:“由,尔何不对曰:‘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当“灵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更是不胜惆怅,“喟然叹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
而设想如何获得从政机遇以实现其政治理想,也成为孔子周游列国路途中与弟子谈论最多的热点话题之一。关于这一点,留待第三部分详谈。
此外,司马迁还写即便遭受挫折,孔子也绝不选择以隐逸方式洁身自好。如:
去叶,反于蔡。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为隐者,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彼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谓子路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与?”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与其从辟人之士,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虽然感伤没有遇到“天下有道”的时代,但却绝不后悔其人生追求与选择。再如: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兮,来者犹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去,弗得与之言。楚狂接舆的话固然促使孔子更清楚地认知“今之从政者殆而”的现实政治环境,但孔子对往昔的追求并无怨悔。
当然,司马迁同时也强调孔子坚守从政的原则和底线,其失去一些从政机会正与其坚执从政原则与底线密切相关。如:
桓子嬖臣曰仲梁怀,与阳虎有隙。阳虎欲逐怀,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怀益骄,阳虎执怀。桓子怒,阳虎因囚桓子,与盟而醳之。阳虎由此益轻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司马迁明白写出,“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的现实政治情势,是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的真正原因。再如居卫国三例:
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过曹……
他日,灵公问兵陈。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复如陈。
灵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叹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卫灵公不修德政,好色而不好德,不重礼教,失礼于孔子,以及懈怠于政,都成为孔子离开卫国的理由。复如:
孔子既不得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何谓也?”孔子曰:“窦鸣犊,舜华,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两人而后从政;及其已得志,杀之乃从政。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还息乎陬乡,作为陬操以哀之。而反乎卫,入主蘧伯玉家。本已行进在投奔赵简子的路途上的孔子,一当于西河听闻赵简子嫉贤妒能,杀害本国贤大夫窦鸣犊、舜华二人,立刻以“君子讳伤其类”而折返卫国。
这样,通过多方表现孔子“在野”时对从政的热忱,就既写出了其在艰困的行“道”历程中的心理煎熬与困惑,也写出了其坚持追求伟大理想的强大生命动能与精神意志。
其四,司马迁注重写出孔子对当世政要的巨大影响力。
司马迁从多方面写出了孔子对当世政要的巨大影响,例如,即便孔子仅在鲁国短暂为政,周游天下也不被列国所用,但仍被弟子推崇为“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质诸鬼神而无憾”的杰出政治家(说详见第三部分);虽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但鲁国君臣不忘问政于孔子(22),其他一些诸侯如齐景公、卫灵公以及诸侯之臣,也纷纷向其问政(23)。最值得关注的是齐景公。景公作为齐桓公之后,未必没有再造霸业的雄图,而孔子也在三十而立之岁最为心仪齐国,故如前所举,孔子曾对景公褒述秦穆公以弱小僻远之国成就霸业而深深打动了景公(24);孔子主张施政首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使景公颇觉受用(25);孔子“政在节财”的主张还使景公“将欲以尼溪田封孔子”,后虽被晏子劝止,仍欲处之于“季孟”之间。只是嫉贤妒能的齐大夫欲加害孔子,注重现实功利、并无决心真正追求“王道”政治的景公,遂以“吾老矣,弗能用也”的借口辞退了孔子。(26)
如写孔子在鲁的短暂执政,甚至使齐国恐惧鲁国从此强大,而设女色之计于鲁君予以阻止:
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师己送,曰:“夫子则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师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师己以实告。桓子喟然叹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如写楚、卫等国都曾欲用孔子,陈、蔡大夫还因担忧孔子为楚所用而发兵围困孔子:
是时,卫君辄父不得立,在外,诸侯数以为让。而孔子弟子多仕于卫,卫君欲得孔子为政。
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如写鲁国不但因弃用孔子而为诸侯所笑,甚至还因此失去复兴的重要机遇:
秋,季桓子病,辇而见鲁城,喟然叹曰:“昔此国几兴矣,以吾获罪于孔子,故不兴也。”顾谓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鲁;相鲁,必召仲尼。”后数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鱼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终,终为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终,是再为诸侯笑。”康子曰:“则谁召而可?”曰:“必召冉求。”于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将行,孔子曰:“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归乎归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赣知孔子思归,送冉求,因诫曰:“即用,以孔子为招”云。
正由于司马迁以饱满的笔墨写出孔子具有不世出的政治长才、获得足与王侯将相相提并论的政治事功,并对当世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力,故能深刻揭示春秋时代注重现实政治功利原则的诸侯各国终于难以真正任用孔子以追求“王道”政治理想;孔子的“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反鲁”,“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就更彰显了深刻的时代悲剧与个人命运的悲剧。由此再进而表现孔子以“在野”方式躬身实践“素王”之“道”,也就更能彰显其伟大的精神价值与人格魅力。
三、孔子与“素王”—“素臣”结构模式
下面,具体讨论司马迁叙写躬践“素王”之“道”的孔子,与追随他的贤徒,实际构成了与现实政治权力结构对比鲜明的“素王”—“素臣”团队。
在司马迁看来,师生关系在孔子的生命中甚至超越其家庭关系而占居第一亲密地位。而孔子的杏坛设教,本就是由于其难得政治之“位”,就以“在野”方式躬行“素王”之“道”的重要方面。故他特写孔子招纳门徒的过程,实际就是不断培育、发展亲密的“素王”“素臣”行“道”团队的过程,孔门师徒正是以躬行“素王”与“素臣”之“道”,共证“吾道不孤”。这也是值得关注的写法。
先从司马迁怎样写孔子的家庭关系及其家庭生活切入。
从司马迁对孔子的家庭关系与家庭生活的记述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孔子所遭遇的不幸和孤寂。孔子幼年丧父,甚至曾经不能确知父墓究在何处,母亲出身低贱且去世较早(27);其虽排行第二,却未见兄弟间有何交往,关系如何。如果说由于史料有限司马迁只能这样写,那么,对其妻子为谁,夫妻关系如何,竟也无一字交代,未免有些让人费解。给予一个勉强的解释,当然不能说不可以。因为司马迁在“世家”中写吴太伯、姜太公、周公等人的事迹,也没有写到这些人的夫妻关系。但毕竟其写《吴太伯世家》、《齐太公世家》、《周公世家》,只是借发始人冠名,却并非将其分别作为各自“世家”的唯一传主,在这些“世家”发始人物之后,还写到了不少后人的事迹;写后人事迹时,有的也涉及婚姻爱情关系。其在表彰一些“圣王”时,不但写到了婚姻爱情关系,并且有的还写得非常出色,如写舜与娥皇、女英,写大禹与涂山氏之女等。而与其他“世家”写世代相继的多个人物不同,《孔子世家》全传都是以孔子为主的,故无论孔子真实的爱情关系究竟如何,一字都不予提及,总让人甚感遗憾。个中缘由,应非由于史料欠缺。司马迁倒是写了“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也只是流水账写法,无一字提及在儿子孔鲤五十年的生命岁月里,孔子与他有任何的互动。(28)直白地说,将孔子写入“世家”,并且在事实上还专以孔子一人为传主,本就打破了写“世家”必写以血统世代相传的定例,而在具体写作中又轻忽家庭关系,甚至对孔子的夫妻关系不予齿及,这的确是特异的写法。这倒让我们想起了司马迁本人在《报任少卿书》中的话:
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孔子世家》中的孔子与司马迁本人的家庭关系及家庭生活,何其相似乃尔!甚至在有些方面,孔子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二人同样早失父母双亲,孔子更在幼儿时代丧父;司马迁无兄弟之亲,孔子虽有兄弟,在《孔子世家》中却不见踪影;司马迁淡于妻子儿女之情(29),《孔子世家》则完全不涉及孔子的妻子儿女之情。难道如此类型的家庭关系与家庭生活,是类似孔子与司马迁这样的文化巨人们所必须遭遇的人生宿命?司马迁的特异写法,不由不让人生发如此想法:司马迁就是以对自身家庭关系及家庭生活最深切的生命感受,来认知一代“圣人”孔子的家庭关系及其家庭生活的,故他也以如此生命感受为蓝本,剪裁取舍关涉孔子家庭关系及家庭生活的史料。之所以如此,不仅意在凸显“素王”孔子的“独身孤立”价值,以及其伟大生命精神价值追求高于家庭生活,也当为了彰显同“道”相求,为追求“王道”理想事业而活,使孔子与其高徒得以超越家庭血缘人伦关系,缔结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的亲密关系。(30)
以记载孔子具体教学活动及言论为主的《论语》也记载了孔子与其弟子之间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的关系。但与《论语》不同,孔子杏坛设教的具体过程及言论,并非司马迁关注的重点,故《孔子世家》连孔子设教的起始时间,都没有清楚交代。其最关注的显然是:孔子招纳门徒的过程,实际就是不断培育、发展亲密的“素王”“贤臣”行“道”团队的过程。故其最早涉笔孔子授徒,是在孔子与鲁国南宫敬叔受鲁君委托“适周问礼”,并在周亲炙老子政治学精髓,“自周反于鲁”之后,并且写明在孔子从教生涯中,此时已经处于“弟子稍益进焉”阶段了。而其真正形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的局面,则在本文第二部分所引述的“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之时。尤其是在周游列国过程中,孔子更与追随他的颜回等贤徒,构成了“素王”—“素臣”团队。
为了强调孔子及其弟子难以真正获得政治之“位”,不得不构建“素王”—“素臣”师徒关系以行“道”,司马迁特意写出,不仅孔子本人,其贤徒也多有从政长才,故可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司马迁还写了在孔子短暂和具有间接性特点的从政生涯中,贤徒对其施政起着重要的佐助作用。如孔子向定公建言废除鲁国僭越违制的权臣们的“三都”,就派擅长于政事的弟子子路为势力最大的季氏之宰: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于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先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率费人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曰:“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鄣,无成是无孟氏也。我将弗堕。”十二月,公围成,弗克。(31)再如第二部分所引,孔子“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正是门人“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的谏言,使孔子冷静下来,专心于拨乱反正之政,“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而使鲁国出现短暂的兴旺气象。
而孔子即便“在野”,对弟子的实际从政也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如前引季康子主政,不用孔子而召孔子弟子冉求,孔子判断“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并因此而生发返国之思:“归乎归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孔子欲归国以把握冉求施政的正确方向,自然还是希望能够在政治上东山再起,故子贡告诫冉求“即用,以孔子为招”。而冉求将在鲁国取得政治事功,也归功于老师的教诲,并由衷赞美老师行政境界至高,自愧不能脱却现实政治功利:
其明年,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对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质诸鬼神而无憾。求之至于此道,虽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对曰:“欲召之,则毋以小人固之,则可矣。”又写正由于孔子成功构建了以其为主导,以颜回等贤徒为辅翼的“素王”—“素臣”团队,并获得了重要成效,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些诸侯国君臣也将孔子及其贤徒与现实君臣关系相提并论,甚至认为其能力远高于当世诸侯国君臣。最为典型的例子是:
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又写即便孔子周游列国,遍历颠沛流离之苦,但设想如何获得从政机遇以实现其政治理想,仍是师徒之间谈论最多的热点话题。如:
而孔子弟子多仕于卫,卫君欲得孔子为政。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矣。夫君子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而师徒之间的相互激励、相互支持,更成为克服艰难困苦、坚持躬行“素王”—“素臣”之“道”的重要因素。如:
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再如:
将适陈,过匡,颜刻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颜渊后,子曰:“吾以汝为死矣。”颜渊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惧。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
在艰危的处境下,孔子的谆谆教诲与坚定意志,固然对弟子有极大的人格感召及鼓舞力量,而弟子们的不离不弃,勇于奋斗,对孔子来说无疑也是极大的安慰。正因如此,爱徒颜回、子路等的相继死去,就对孔子的精神造成了极大的打击。而在孔子死前,倾听其肺腑话语的,仍是其爱徒之一的子贡,而非孔子家人:
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喟然叹曰:“莫知我夫!”子贡曰:“何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明岁,子路死于卫。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后七日卒。
司马迁写在孔子去世后,对鲁哀公“生不能用,死而诔之”行为提出谴责的,也是孔子爱徒:
哀公诔之曰:“曼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贡曰:“君其不没于鲁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余一人’,非名也。”子贡所言,其实也正是司马迁所欲言。司马迁明白:比之于鲁哀公的虚伪作态(32),孔子的得意门生们才近似于其生命的知音,也真正发自内心地痛悼其心目中伟大的精神之“父”。故他们皆比照在人世所能做到的最高悼念规格,以父死之礼,为孔子服丧三年,子贡甚至“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而依傍孔子墓居家的弟子及鲁人,竟有百余家,以至于形成极为特殊的文化村落——“孔里”:
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这种非单纯由死者家族后人,而主要是由弟子主导,以崇敬死者的共同意志依傍坟墓聚居,自然而然地形成村落的情形,的确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最为感动人心的一幕,值得司马迁以“最深切的同情”大书而特书。而为了呼应孔子死前感慨天下“莫知我夫”、“知我者其天乎”、“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司马迁又写了由孔子弟子主导起始,形成了影响巨大深远的孔子崇拜效应与传统:
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故当“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的汉世一人司马迁,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的心情回望孔子,“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依然深受感动,“祗回留之不能去”,并因而专为一代“素王”孔子造像。
四、余论
需要予以强调指出的是,司马迁将对孔子的文化著述的记述,放在了“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之后。《孔子世家》的主体部分,显然是以记述孔子的政治活动,来塑造一个伟大的躬行“素王”之“道”的典范形象。而在塑造这一典范形象时,则特重彰显其具有大政治家风范,以及其与贤徒构成坚持“王道”理想追求的“素王”与“素臣”团队,从而将其树立为构建理想政治权力结构的重要范本。故尽管孔子的文化著述与教育活动,也是其躬行“素王”之“道”的重要方式,但司马迁实际略于记述孔子的具体从教生涯与从教活动;对孔子的文化著述活动的记述,也是于主体部分之后采取分类概述方式。而在其概述中,予以特别强调或较详揭示的,大约是如下方面:
一是表彰孔子系统整理《诗》《书》《礼》《乐》以重构礼乐文明的“素王”之功: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二是记述孔子弟子对孔子的推崇和高度评价: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闻也。夫子言天道与性命,弗可得闻也已。”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蔑由也已。”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曰:“我何执?执御乎?执射乎?我执御矣。”牢曰:“子云‘不试,故艺’。”
三是借孔子比较伯夷、叔齐等人物,以发掘孔子具有“无可无不可”的伟大超越精神: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行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四是特别发掘“乃因史记作《春秋》”是孔子成就“素王”伟业的重要标志: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所谓“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以及引述孔子的“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云云,不仅能够发显孔子的伟大精神价值,也见出司马迁对自己写作《史记》所具有的伟大精神价值的自我期许。
要之,以孔子“素王”著述伟业的第一传人自居的司马迁,以“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为依据,专为“素王”孔子写“世家”之传,也成为最为合适的“素王”孔子的造像者。(33)而在以政治权力的大小有无及成败论定人的价值的封建王权专制时代,司马迁关于“素王”孔子的特别写法,也当引起我们最为深长的反思!
[收稿日期]2012-04-16
注释:
①“素王”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天道》:“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司马贞《史记·殷本纪》之《索隐》谓:“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质素,故称素王。”王充《论衡·定贤》:“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春秋》。”
②本文所引《孔子世家》文字,皆出自《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后不赘注。案: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指出:“孔子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至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凡三百七十五岁,云‘五百岁’,误矣。”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述清儒崔适的观点:“云五百岁者,此以祖述之意相比,所谓断章取义,不必以实数求也。”(《史记会注考证》,卷一百三十,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1955版年,第20页)可见司马迁是刻意断章取义,虚拟历史时间,以彰显其伟大文化抱负继承有自。可分别参看郑鹤声《司马迁生平及其在历史学上的伟大贡献》、张维华《论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的相关论述,见瞿林东主编《〈史记〉研究(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页、267页。
③司马迁幼承庭训,但与乃父《六家指要》最为推崇道家与老子异趣,他最尊崇孔子,将“素王”孔子列于《世家》,称“至圣”,老子则与申、韩同传,但称“隐君子”而已。故其所谓引述父亲之言,或当有借父立言意涵。正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司马氏父子异尚》所说:“……而迁意则尊儒,父子异尚,犹刘向好《毂梁》,而子歆明《左氏》也。观其下文称引董仲舒之言,隐隐以己上承孔子,其意可见。”(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33页)也可参看阮芝生《史记的性质》、程金造《司马迁崇尚道家说》的相关论述,见瞿林东主编《〈史记〉研究(上)》第83—85页,《〈史记〉研究(下)》第224—225页。
④《汉书·司马迁传》记载,上大夫壶遂曾与司马迁深入讨论孔子著述《春秋》,并以之比拟司马迁的《史记》著述,司马迁自谦不敢与之相提并论,但从他与壶遂讨论时所展示的对孔子包括《春秋》在内的伟大著述的深邃洞见,也可概见其雄心所在。
⑤“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为先秦时代的重要思想话语。如《孟子·公孙丑下》记载孟子的话:“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司马迁《史记·天官书》则云:“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此说实有承继孟子处,其继承孔子“素王”著述伟业而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伟大儒者气象,更是超越了孟子精神。参看张维华《论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的相关论述,见瞿林东主编《〈史记〉研究(上)》第267页、283—286页。
⑥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认为:正是与继承孔子“素王”事业相关,太初改历之议实始于司马迁,始终总其事者也是司马迁,“孔子言行夏之时,五百年后卒行于公之手……此亦公之一大事业也”,故其于太初元年“造历”事毕,才真正开始《史记》的创作。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98—500页的相关记载。
⑦表面上,司马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宣扬汉命,称:“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史记》,第3299页)但司马迁既称引“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天命“圣王”理论,并以“素王”之业的第一传人自居,显然有其对汉武帝所谓“伟业”的特定认识。
⑧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对其因李陵事件获祸始末述之甚详,兹不赘述。
⑨司马迁得以以最为彻底的超越、升华姿态进入自由创作《史记》的王国,在人类文化著述史上具有永恒的普遍性启示意义。有无此类超越、升华,是衡量古今中外伟大著述的重要标准。如曹雪芹为了争取研究、创作《红楼梦》的自由,不惜穷厄困顿以死,但丁历尽流放苦难而创作《神曲》等,正与司马迁前后辉映。参看高阳《没有学术哪有自由——曹雪芹摆脱包衣身份考证初稿》(收入《高阳说红楼梦》,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19页)的相关论述。
⑩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11)关于首选吴太伯与伯夷、叔齐分别作为“世家”、“列传”之首的问题,学界论述甚多,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伯夷列传》,白寿彝《史记新论》认为“列传”七十篇,“首篇并非专为伯夷而写的。它是列传的帽子,带有总序性质”;赖长扬《司马迁与春秋公羊学》则认为“太史公是有意借伯夷而发论,总领七十列传;《伯夷列传》是七十列传之纲”。参见瞿林东主编《〈史记〉研究(上)》第72—74页,《〈史记〉研究(下)》第254—255页的相关论述。
(12)尽管司马迁将周公、孔子与自己分别列为五百年一个周期的文化代表人物,但其《周公世家》写周公事迹较为简约,周公对司马迁的实际影响也当远逊于孔子。
(13)《太史公自序》也提到自己曾“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史记》,第3293页)。
(14)司马贞《索隐》:“孔子非有诸侯之位,而亦称系家者,以是圣人为教化之主,又代有贤哲,故称系家焉。”张守节《正义》:“孔子无侯伯之位,而称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宗于夫子,可谓至圣,故为世家。”见《史记》,第1905页。
(15)司马贞《索隐》:“圩顶言顶上窳也,故孔子顶如反宇。反宇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傍高也。”
(16)张守节《正义》:“季氏为馔饮鲁文学之士,孔子与迎而往,阳虎以孔子少,故折之也。”见《史记》,第1907页。范晔《后汉书·孔融传》记孔子后裔孔融少时以老子与孔子相熟而自称与李膺有“通家”渊源关系,当是受到司马迁关注孔子少时如此行为的影响。
(17)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礼学居于极为重要的核心地位,《论语·颜渊》:“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受孔子的深刻影响,司马迁即将“礼”作为《史记·八书》之第一“书”。
(18)关于本年是否如太史公所言,孔子确为十七岁,学界看法分歧,因与本文论旨关系不大,兹不赘论。
(19)关于孔子受教于老子的具体时间及相关情形,学界也有不同说解,本文不予赘论。倒是应该关注:司马迁以黄老学派之著名学者司马谈之子,又得拜当世分别代表“今文学派”与“古文学派”的两大儒学宗师董仲舒与孔安国为师,就其深厚师学渊源而言,汉代几无人能出其右,故司马迁写孔子以老子为师,或当别有意味。
(20)《论语》记载孔子多次提到对文王的推崇,并以文王之道继承者自居,如《子罕》所记:“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司马迁写孔子对文王的思慕形于梦寐,即由此而来。这种认知在后世已为儒家定论。如王安石在嘉祐三年所写的《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也不忘举“夫在上之圣人莫如文王,在下之圣人莫如孔子”,宣称孔子“所守盖与文王同意”。
(21)按这种表彰孔子事功的写法,与《廉颇蔺相如列传》表彰赵国名相蔺相如出使秦国使完璧归赵同一机杼、先后辉映。
(22)《史记·孔子世家》写:鲁哀公问政,对曰:“政在选臣。”季康子问政,曰:“举直错诸枉,则枉者直。”康子患盗,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23)《史记·孔子世家》写:明年,孔子自蔡如叶。叶公问政,孔子曰:“政在来远附迩。”
(24)《史记·孔子世家》写:“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与郈昭伯以斗鸡故得罪鲁昭公,昭公率师击平子,平子与孟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于齐,齐处昭公乾侯。其后顷之,鲁乱。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孔子于鲁难中投奔景公,固然不无探寻解救国家危难的动机,但求仕也当是重要原因。
(25)《史记·孔子世家》写: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
(26)《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他日又复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景公说,将欲以尼溪田封孔子。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后景公敬见孔子,不问其礼。异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闻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鲁。”
(27)《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郰人挽父之母诲孔子父墓,然后往合葬于防焉。”
(28)《论语·季氏》曾记“陈亢问于伯鱼”,伯鱼即孔鲤。正可见《孔子世家》与《论语》的关注点有所不同。
(29)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指出:“迁子姓无考。《汉书》本传:王莽时,求封迁后,为史通子,是史公有后也。女适杨敞。”《汉书·司马迁传》:“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第508—509页的相关论述。
(30)司马迁这种写法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甚为深远。如《水浒传》关于梁山事业与家庭关系的特定写法,即当受到《史记》的深刻影响。
(31)《左传》定公十二年有“仲由为季氏宰”说、《礼记·礼器》有“子路为季氏宰”说、《孟子·离娄上》有“求也为季氏宰”说。《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岁。为季氏宰。……子路为季氏宰。”上博藏楚简《仲弓》篇简一开端就是:“季桓子使仲弓为宰”。参看廖名春《楚简〈仲弓〉与〈论语·子路〉仲公章读记》(《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32)司马迁这样的写法,让人想到《项羽本纪》以反讽笔法写项羽死后刘邦的悼念行为:“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史记》,第337—338页)虽然孔子与鲁哀公并非敌对的你死我活关系,但作为统治者,鲁哀公与汉高祖具有共同的伪善面目。
(33)王鸣盛评价司马迁“以孔子入世家,推崇已极,亦复斟酌至善”,认为其能深得古人“贵贵尚爵”的本真意义。参见《十七史商榷》第20页的相关记载。宇文所安《“活着为了著书,著书为了活着”:司马迁的工程》一文在评价司马迁时说:“司马迁惟一没有想到的,就是一部著作会孕育其他的著作,而那些其他著作会多多少少留下祖宗的影子。每次我们看到一套奉《史记》为源头的二十五史,我们都应该想到,那位失去了生殖能力的先人,当他把世系转移到文字的时候,开创了一个子孙绵长而杰出的家族。”正可借以准确理解司马迁将“素王”孔子写入“世家”的真正意图。参见《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8—104页的相关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