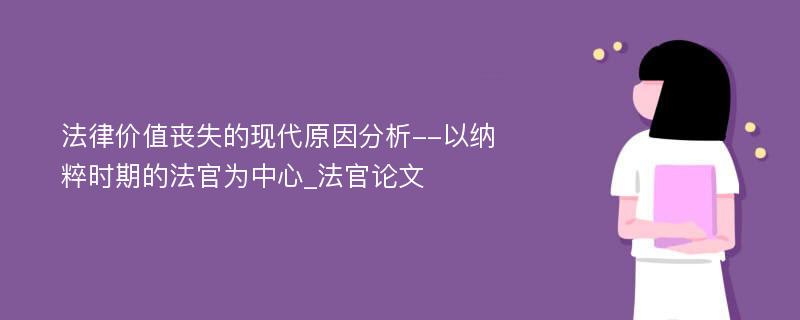
法律价值失落的现代性原因分析——以纳粹时期的法官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纳粹论文,现代性论文,法官论文,时期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自亚里士多德提出法治二重意义以来,对法律价值准则的论证、批判或合乎逻辑的适用就一直如庞德所言,是法律史的各个经典时期法学家们的主要活动[1](P55),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法律是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美好理念化身的观念深入人心。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屡屡遭遇法律价值的失落,尤其是二战时期法律不仅没能阻挡住纳粹侵略、屠杀的进行,反而成了纳粹暴行最好的帮凶,更是让人痛心不已。人们在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有人把它归咎于实证法学在当时的盛行;也有人针锋相对地认为这是个误解,因为在纳粹时期,以凯尔森为代表的实证法学家们受到了施密特等人的迫害,从而得出了纳粹时期法律价值失落的真正原因不是实证主义法学的盛行,反而是对其贯彻的不彻底;还有人如考夫曼比较全面地认为,一方面是恶化的制定法律实证论被纳粹主义操控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人们滥用自然法的思想,而以国民自然法的名义潜越于现行法之外”[2](PP40~41) 的结果。但在笔者看来,学者们这种动辄从法学思想流派来寻找原因的进路,纯粹是一种法律意识形态或者习惯性自恋的表现,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片面夸大了学者及其学术思想对现实的影响,因为我们在历史中看到更多的不是学者影响现实,而是学者们自动地“与时俱进”,改变自己以适应现实,纳粹时期的施密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此,从法律的外部而非内部寻找某个法律事件发生的原因,或许更值得我们尝试,这正是本文的方向所在。
二、何为现代性
纳粹时期法律外部的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韦伯给了我们迄今为止最为经典的回答:社会各领域理性化了的社会,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化的社会。在韦伯看来,西方近世以来深入各个生活领域(如音乐、宗教、科学与经济……)的“理性化”趋向,就像百川汇流的大河般,浩浩荡荡地冲破传统之一的樊篱,刷新了人类对于世界的控制和支配能力,也造成了今天我们统称为“现代”的文明成果[3] (P76)。“西方何以成为今天的西方”,是作为西方之子的韦伯一生都在追问的问题。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寻到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宗教根蒂”——禁欲主义。尤其是路德对“职业”概念的重新解释[4](PP50~68) 以及加尔文教派在宗教改革中所提出的“预选说”[4](PP74~98) 直接造成了世界除魅与逃世的救赎之路的断绝。救赎之道从原先冥思性的“逃离现世”转向了行动、禁欲的改造现世。他们“能以己为神之‘工具’而置身于世,并抛却了一切巫术性的救赎手段。同时,他无可避免地要通过在现世行为中的伦理禀赋——就像单只他蒙受召唤——在神前‘证明’他自己。”[5](P489) 由此而促生了现代性的新精神——“现世支配之理性主义”。
“理性化”落实到行动层面上,意指行动者对手段策略的选取应用,将更能说明有效达成预设之行动目的,韦伯将这种活动类型称为工具理性或目的理性式社会活动类型,以区别于其他的价值理性式、情感式和传统式活动类型[6](PP31~34)。其中纯由信仰而不管结果与否来决定行为的价值理性式曾长期是前资本主义时期最主要的活动类型。但随着宗教改革的成功,禁欲主义者“现世支配之理性主义”式的宗教生活方式,渐渐在社会各个领域展开,其地位渐被工具理性所取代。因为唯有工具理性最切合新教的伦理,最能展现上帝的荣耀,最能让他们相信自己就是上帝的选民。
目的理性的此种扩张,使其在经济领域以“计划的方式来达成经济目标”[7](P3) 的目的理性的经济活动彻底取代了“以固有之传统技术谋求需要之满足”的传统的经济行动;在政治领域以法制的支配类型逐渐取代了传统支配类型和卡理斯玛支配类型,并进而形成相互配合的社会组织与制度(最典型的就是官僚制度),使得人类支配外在环境的计算能力大幅提高,创造出了空前的文明成就。但同样,“目的理性”的制度化还意味着手段逐渐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这使得“价值理性”的行动倾向相对萎缩,现代文化受到资本主义的洗礼后,展现在个人面前的生活世界虽然是一个解除魔咒的,但也是世俗功利主义笼罩一切的世界。理性的计算、科技工具的运用以及计划性的社会变迁扩大了官僚化的影响范围,乃至现代的经济、政治、社会组织无不朝向“形式理性”的运作原则,在此意义下,个人除了注定背上“职业人”的硬壳之外,还要时时面对组织内部秩序的要求与主宰而成为只知顺服适应的“秩序人”。他们越来越像现代化社会这部大机器中的小零件,在严密组织的官僚科层体制里循规蹈矩地运转[3](P81)。其结果是原先滋养出禁欲精神的“宗教根蒂”逐渐凋谢,人类面临了全面的价值或意义失落的危机,这是纳粹时期法律价值失落的外部原因。下面我们具体以纳粹时期的法官为考察对象加以说明。
三、法律价值的失落与现代性
按韦伯的说法,罗马法之所以在欧陆取得胜利,并非因其实体法的存在而较适合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各种条件,而在其理性的形式,以及(尤其是)在技术上有必要将诉讼程序委诸经过合理训练的专家。这虽是一家之言,但也表明了法治与现代性的契合,而且按韦伯的说法,这是最契合的典范,此在埃尔曼对西方法律文化的比较性阐释中[9] 表现的非常明显。而与罗马法的乘续并肩而行的司法的官僚化更是这种契合的典范,它完美地展现了现代性的精神。
第一,从法官的任命来看,法官就是一个典型官僚制下的官僚。按埃尔曼的说法,选任法官的基本模式主要有如下三种:(1)由行政长官选择;(2)由公民直接或间接选举;(3)通过类似职业文官的方式选出。[9](P114) 在韦伯看来, 这三种方式中的第一种方式,最符合现代性的精神,因为不经选举的官僚,从技术角度而言,通常会比较精确地执行任务,因为他的是否被选用与未来前途,似乎更取决于纯专业性观点的考虑与资格。而且只要政党卷入任何方式的、经由选举来任用官僚的场合,他们通常会将此一候选人对政党有力人士的忠勤——而非专业性的竞争能力——摆在更具决定性的考量上。[8](P27) 这种被任命的法官,尽管在其被任命后就会取得一个非常独立的制度保障,但我们若因此就指望他们会在以后的司法实践中避免政党冲突,保持价值中立,那纯粹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象。如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在即将卸任时,就不会急忙任命自己内阁的国务卿、联邦党任马歇尔出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又利用联邦党人控制国会的最后机会,通过《哥伦比亚特区组织法》,任命42位联邦党人出任治安法官了。反而我们对法官独立性制度的保障,在现实中往往会成为法官为政党或某个阶层营私的最好的合法化保障。因为法官任命本身就是人们通过未来法官们的社会化而强化旧的价值和输入新价值的手段。[9](P112) 这是我们对司法独立必须重新反思之处。第二种选举的法官任命方式,在韦伯看来是最不符合现代性精神的,因为“通过选举来指定官僚无疑会松弛层级关系的严格性。基本上,选举出来的官僚对其上级而言,具有一种自主性,因为他的地位是‘从下’而来,而非‘从上’……”[8](P27) 这就使其弱化了“现代人”所具有的服从品格,违背了获得最高效率的工具理性。那它为何还在这个现代性的社会中存在,尽管是很少的存在。埃尔曼一语道破,那就是尽管它表面上是选举产生,但问题的关键是“行政任命根据谁的建议作出。谁选举了候选人,使他的名字出现在选票上?”[9](P114) 可见,表面选举背后的实质还是任命。至于最后一种类似于职业文官的选任方式,虽然不像第一种那样是最完美的官僚任命方式,但完全符合现代性的理念。只是升迁成了此种情态下作为职业人法官的中心诉求,为了获得升迁,服从、知识、效率成了他们必须具备的素养,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权力机构的任命。
可见,任命是法官选任的最本质特征。当任命成了目的本身的时候,按照目的理性的规则,如何最有效率地获得最高的任命就成了法官作为官僚的根本理性。由于任命的主体最终是握有社会资源最多的政治权力主体,因此,当政治与法律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期待法官去信仰法律而非政治。这对法官将意味着自己无法获得政治权力的任命,这是一种违背目的理性的价值理性,在现代性的社会里当然没有存在的余地。相反,选择服从政治权力而非法律,才是符合现代精神的明智选择,这也正是法律价值、法律信仰在现代社会衰落的根本原因。
纳粹之前德国法官的任命过程,就完美地展现了这种理性。那时想要出任法官者,除了须在法学院学习数年以及经过4年不带薪的司法培训期以外,还必须经过长达8~10年的助理法官见习期,在这期间,他们的工作完全没有司法独立的保障,并随时有被开除的危险。这样就为权力者提供了足够的时间来考察法官,消除所有桀骜不驯分子,换句话说,只有那些经得起艰巨考验的极度驯服忠诚者,也就是那些能够无条件地接受现存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者,方能获得任命,成为正式法官。但他们只能成为基层或中层的法官,因为“那些高层法官的空缺往往由久经考验、忠诚无限的检察官来填补。与法官相比,这些人在长期充当人民公仆的生涯中早就学会了‘唯上是从’的公仆精神。”[10](PP5~6) 难怪法社会学家厄思斯特·弗朗科对当时的法官行为感叹道:“司法程序对立?理论上从未有人怀疑它,在实践中却从未有人去争取它。”[10](P7) 为什么不去争取? 因为争取就有不被任命的危险甚至生命危险,比如,纳粹时期就有两名著名的法官因争取司法独立,而被判处死刑[10](P179)。这样的行为虽然很高尚,但完全不符合目的理性,而被当时绝大多数法官所排斥。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对1924年2月24 日慕尼黑人民法庭对希特勒所作出的荒唐判决感到惊讶了。因为他们已经预见到只有“同情”、偏袒纳粹才能使自己在将来更快地获得更高的任命,而法律公平、正义的价值根本不在他们考虑之内。等希特勒上台,纳粹真正获得国家权力的时候,尽管他们发现纳粹在肆意限制法院的力量,但他们不仅没有去反抗,反而对纳粹更加驯服,因为从目的理性看,此时的反抗更具不被任命甚至是被“大清洗”的危险,唯有更加顺从,才有获得任命的可能,而这又恰恰为纳粹进一步对法治的破坏扫清了障碍。鲍曼一针见血地将其称之为“受害者的自动合作”[1](PP155~199) 这在我们现在看来是非常荒唐可笑的,但“形式的理性,实质的非理性”恰恰是韦伯对现代社会的经典总结。
第二,从“支配现世之理性主义”来看,三权分立之所以能被现代社会所接受,其根本原因也并非是其能很好地防范权力的滥用,因为它毕竟是一种他律的方法,相比较于通过对人之人格、道德的塑造来达致自律地防范权力滥用的方法来看,它明显是落后和低效的。其在现代社会中获宠的真正原因在于它最能满足现代性对效率的要求,是分工这个现代社会基本特征在法律领域中的具体体现。比如,立法和司法的分工,就比两者未分工来得有效率,尤其对司法者而言,有了立法者的立法文本,就省去了很多寻求判决依据的精力。同样,律师职业的出现,也使他们大大减少了调查取证的工作,从而使司法判决能像一部分工明确的机器般有效率地运转,完全契合于目的理性对效率、准确、快速的要求。但这也同样带来了法律价值的致命伤害。
首先,分工就意味着一项工作的多人协作,行动主体的多个也就必然会带来责任主体的多个,从而造成责任主体的不明,并最终造成各个分工者责任感的衰竭。如果司法者、立法者甚至还有律师之间没有分工,而只有一个主体来调查取证、寻找判决依据、作出判决,那么他在整个行动过程中的责任心肯定是非常强烈的。因为不论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需要他对其负全责。而现在的分工却使其责任心大大降低。因为,判决的法律依据是立法者制定的,判决的事实准绳是律师提供的,而法官仅仅成了根据他们提供的这些大小前提判决的作出者,这就大大降低了法官的责任感,因为他很难想到自己应该对整个判决的不公正负责,这直接诱发了法律价值的经常性失落。
其次,分工还带来了一种约翰·拉赫斯所谓现代社会最大的特征,即“行动的中介”,亦即个人的行为通过另外一个人、一个中间人来表现的现象,这个人站在我和我的行为中间,使我不能直接体验到我的行动。意图和实际完成之间的差距,里面充满了大量的细微行为和不相干的行动者,挡住了行动者的目光,让他看不见了行为的结果。[11](PP33~34) 这种行为和结果的“不共场”使行为者——法官,很难真正感受判决的实际效果,即使他错误地判决了一个人死刑,他也很难感受到判决的非正义,更不用说道德的自责了。因为对一个事件感受的在场与不在场有着很大的区别,判决某人死刑和亲手枪毙一个人,虽然结果都是让那个人死亡,但前者和后者对“死亡”结果的感受完全不同。法官结果现场感的匮乏,必然会导致其行为时责任、道德感的常失却,并最终变成韦伯所言之“没有精神的专家和没有情感的享乐者”[4](P143)。这时当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发生冲突,需他抉择的时候,他一般会选择前者——形式正义。因为形式正义是对法官“在场”的判决行为的评价,他有最直观、切实的感受,而实质正义更多的是对法官“不在场”的判决结果的评判,对他来说是遥远的、模糊的。于是我们就会理解缘何纳粹时期会有那么多法官作出非正义的判决,甚至是战后也没有丝毫愧疚之意的原因。这也是导致法律价值时常失落的重要原因。
四、结束语
综上,法官屈从于政治权力而非法律;追求形式正义而非实质正义,绝非是我们原先想象的法官非理性的产物,或仅仅是个偶然性事件,反而恰恰是现代性精神——现世支配之目的理性的完美展现,法律价值在其中的失落就成了现代性的必然。最后我想套用鲍曼在总结大屠杀教训时的两段话来结束我们受篇幅所限不得不结束的讨论:首先,大多数法官在陷入一个没有好的选择,或者好的选择代价过于高昂的时候,很容易说服他们自己置法律价值问题于不顾(或者无法说服他们自己对面对道德责任),而另行选取合理利益和自我保全的准则[11](PP268~269)。其次,纳粹时期法律价值的失落不是人类前现代的野蛮未被完全根除之残留的一次非理性的外溢,反而是现代性大厦里的一位合法居民,更准确些,是其他任何一座大厦里都不可能有的居民。[11](P24) 那只是一次警告,而非结束。这两点完全有理由让我们对我国目前现在正如火如荼进行着的现代化(就我们而言亦即西方化)法治进程保持足够的警惕和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