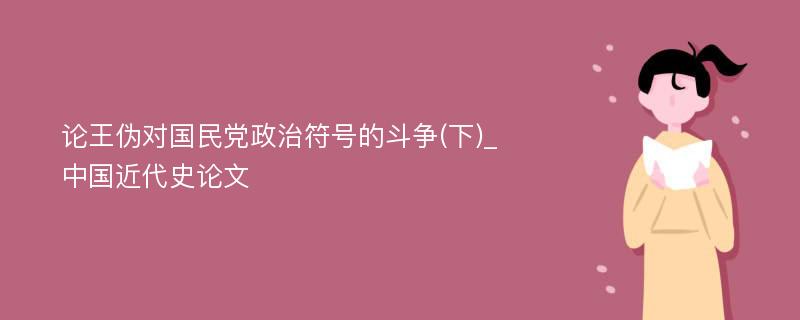
论汪伪对国民党政治符号的争夺(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二论文,国民党论文,符号论文,政治论文,论汪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 汪伪为运用国民党政治符号与日本方面的折冲
在日本开始诱降汪伪时,让汪精卫等人保持国民党内和平派这一较为“中性”的形象是既定策略。而汪精卫本人也打算结合国民党内的反蒋力量,在西南建立“和平亲日”政权。之所以不选择到日本占领区活动,是为了与王克敏、梁鸿志等划清界线,也是为了与“重光堂会谈”中“随着治安的恢复,在两年之内撤兵”的约定(注:[日]犬养健:《诱降汪精卫秘录》,任常毅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3页。)相呼应。但近卫声明发表之时,“这最为要紧的撤兵约定,竟忘得一干二净,实在让人担心汪精卫和平会走上歧途”。直接策划汪精卫出走的犬养健都表示:“我失望了。”(注:[日]犬养健:《诱降汪精卫秘录》,任常毅译,第83页。)
接下来,日本人更失望了——汪精卫等曾经吹嘘的国民党内“亲日派”(注:“亲日派”一词,在抗日情绪一再高涨的民国政治语言中,经常被过度使用,很多从事对日交涉的人都被唤做“亲日派”。这一情况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即已有之;抗战爆发后,中共方面、日本、汪精卫均认为国民党内有一个人数较多的“亲日派”,并基于此作出不少政治判断。)群起响应的情况并没有出现。不仅何应钦、张道藩、黄郛、熊式辉等所谓“亲日派”没有动静,张发奎、龙云、阎锡山等曾与汪合作过,被汪寄予厚望的地方实力派也无其期待的反应。被视为汪铁杆心腹的顾孟余不仅反对《艳电》的发表,而且对汪其后的一系列活动毅然保持距离。汪精卫后来悲伤地表示:“已遣使探顾(顾孟余)如何再覆,顾于仲鸣死,无一言之唁,其心已死,不必再注意其人矣……”(注:《汪精卫致其妹函电》(1939年12月21日),(台湾)国民党法务部调查资料室《汪伪资料档案》,转引自陈木彬:《从函电史料观抗战时期的蒋汪关系》,第83页。)汪政治牛皮的破产,使其丧失了与日本交涉、索取“重光堂会谈”中日本许多重要承诺的资本。这些承诺中,牵涉国民党政治符号、具有重要意义的,除撤兵外,尚有外国租界返还中国、治外法权返还中国,等等。(注:[日]犬养健:《诱降汪精卫秘录》,任常毅译,第93页。)
汪精卫在河内度过了一个碌碌无为的春天后,决定到上海开展“和平运动”,这使他进一步丧失对国民党政治符号的拥有。今井武夫分析说:“本来再重光堂会谈时,高宗武主张建立政权要避开日本军占领区,尽可能地选择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日军未占领的地区,由汪派军队加以占领,建立与重庆的抗战政府相对立的国民政府,这样的话,恐怕将会沦为所谓的傀儡政权,与过去的临时、维新两个政府毫无二致……即使如汪所主张的那样,对重庆方面可以做些工作,促使改变他们的抗战政策,但是汪政权本身已成为傀儡政府,连他本人也难免被视为卖国贼而遭受国民大众的唾弃。殷鉴不远,恐重复北平临时政府王克敏和南京维新政府梁鸿志的覆辙。”(注:[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辑委员会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103页。)
如认为日本的这种担心,汪伪诸人毫无察觉,那未免太低估了他们的政治智商。他们曾采取了措施,企图与王克敏、梁鸿志撇清关系,比如,他们筹划组府期间,很滑稽的拒绝与王、梁同处一室。但王、梁的靠山是日本,而汪伪能否保持对国民党政治符号的占有,关键在日本方面的态度。汪伪为此与日本进行了并不轻松的交涉。
汪精卫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商谈组府时。出乎一般人的意料,汪精卫把重点放在国民党的政治符号问题上,汪提出:“以国民党为中心……建立国民政府是最适当的。”他论证说:“对于国民党标榜三民主义问题,前次派高宗武来,日方提出应该清除与共产主义有关的连带性,恢复所谓新三民主义的意见,这是值得重视的。本来孙文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与共产主义截然不同的,今后我打算今后尽最大努力发挥三民主义的真意。”平沼则回应说:“在完全与共产主义分开的三民主义下促进国民党的更生,并联合各党各派组织中央政府,改变容共抗日的政策,采取这种办法,我是赞成的。”(注:《汪精卫与平沼会谈纪录》,杨凡译自《日本外交档案S487号》,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88—91页。)汪、平沼的这段对话,透露出几个信息:一、日本方面也清楚地认识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有“连带性”;二、汪精卫对三民主义这一国民党的政治符号的运用是断章取义的;三、日本政府高层在与共产主义划清界限的前提下,同意汪伪对国民党政治符号的运用;四、所谓联合各党各派组织中央政府,实际上是要求汪伪在运用国民党政治符号时,容纳本身与三民主义并不相容的王克敏、梁鸿志等既有汉奸政权。这一会谈的重要性,历来为史学界忽视,实际上它勾画出了汪伪运用国民党政治符号时对日折冲的轮廓和架构,尽管在面对不同的对象时,折冲的重点不一。
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是激进的对华“膺惩派”,在日本陆军视中国为其势力范围的情况下,板垣曾较长时间地主持对华政策的决策。汪、板垣第一次会谈时,他提出:“日本把三民主义看成是危险的东西,尤其因为有民生主义乃共产主义的文句,有种种误解。”对此,汪的解释是:孙中山“在当时的形势下把各种潮流、各种思想全部引进自己的主张,为了想在国民党中把他们同化,所以有这样的文句。如果细读全文,就了解这里讲了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完全不同的理由,结果,劝告抛弃马克思主义而采用国民党的主义”。(注:《汪精卫与板垣会谈内容》,钟恒译自《日本外交档案S487号》,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92—94页。)汪精卫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的解释显然有两重目的:既要继承孙中山的衣钵,又要使日本军方接受他对三民主义内涵的“新”界定。
汪精卫与近卫会谈时,除提出“孙文先生的三民主义,本来完全是着重中日提携”的谬论外,更进一步提出,“我之所以主张政府的名称为国民政府、国旗为青天白日旗,决不是面子的问题,这是为了扫除国民畏惧之念,使其安心地考虑问题的缘故”,他提醒近卫,“过于限制中国的行动,中国恰像不成国家的状态”。(注:《汪精卫与近卫会谈内容》,杨凡译自《日本外交档案S487号》,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106—108页。)把能否运用国民党政治符号,与争取中国民众对“和平运动”的“理解”结合起来。汪精卫在此道出了他反复争取国民党政治符号的终极意义。
日、汪在关于国民党政治符号的运用上有利益结合点。日本方面痛快地答应汪伪以“还都”名义建“中央政府”,而政府名称为“国民政府”,目的是向重庆方面施加压力,希望在将其贬为地方政权(注:在日本政府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后,虽作微调,但轻视重庆方面的情绪和政策倾向在日本政府内部和前线军人中长期保留,平沼1939年6月10日与汪精卫会谈时,就明确表示:“重庆政府现在已经不能说是中央政府了。”杨凡译自《日本外交档案S487号》,黄美真、张云:《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88—91页。另外,1938年7月8日,日本5相会议分别讨论了“现中国中央政府”(指重庆国民政府)屈服或不去服的对策,要求:如国民政府屈服,“(一)帝国坚持关于解决对华战争的既定方针,以现中国中央政府为对手,全面调整日华关系;(二)现中国中央政府屈服并接受后述第三条时,应视为一友好政权,使其同既成的新兴中国中央政权合流,或者使其同现有各亲日政权合作重新建立中央政权。同既成的新中央政权合流或者建立新中央政权等,主要由中国方面决定实施,而帝国从中斡旋。”而按照日本方面规定,现中国中央政权屈服的认定条件有4:合流或参加建立新政权;根据前项改称和改组旧国民政府;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及采取亲日、满防共政策;蒋介石下野。[日]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内部资料),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152页。)的前提下,将其纳入“和平运动”的轨道。汪伪如此强调国民党政治符号,自然是想取代重庆方面地合法地位,洗刷汉奸形象,成为日本唯一或主要的交涉对象。但是,日、汪在关于国民党政治符号的问题上又是有分歧的:汪伪诸人不能说没有自己的政治“理想”,而这些“理想”中,有些是日本并不乐观其成的,比如,使“新中央政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又比如,搞些“民生建设”,以争取沦陷区的中国老百姓。日本方面,扶植汪伪的终极目的是分化中国的抗日力量,促进中国内部分裂,进而解决“中国事变”,使中国成为其殖民地。这种分歧的性质在汪伪的“国旗”问题上充分的体现出来。
本来,组府前汪伪中央政治会议“充分”考虑了日本可能的反应,在确定青天白日旗为“国旗”时,已经决定“在国旗和党旗等旗子上部加上印有反共和平的三角形的大型黄色布片”。但日本方面提出“为避免混淆纠纷”,汪伪军队直接用写着“反共和平”大字的黄色旗,而不是用什么“国旗”等。汪的态度是,如此,“作为国家的军队,无论如何有损体面”。日方又提出,前线日军正和打着青天白日旗的军队进行战争,如汪伪突然又用青天白日旗,会“引起种种误解”;汪乃还价说,在前线“或者有此必要”,但在非前线地区如“军营”,还是应该用“国旗”,否则会“影响军队在精神上的统一性”。汪精卫的“顽强抗争”换来板垣厉声呵斥:“无论在前线或是后方,至少在军队方面使用国旗,会造成误解。这一点是政府和军方充分研究的结果。”(注:《汪精卫与板垣第二次会谈内容》,钟恒译自《日本外交档案S487号》,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109—116页。)
后经双方协商,日本终于同意汪伪使用青天白日旗,但须在旗子上加“和平反共救国”的黄色飘带。汪伪国民政府“还都”当日,伪中央党部悬挂青天白日旗帜,因未附加黄色飘带,遭到日军士兵的枪击。在周佛海1940年3月30日的日记中,他的记述是这样的版本:“惟因悬旗时,我方多未照协定办事,致使对方不满,为美中不足之事。此责应由我方负之,不能怪人。”(注: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上),第276页。)6年后,他制造了另一个故事版本:“南京政府成立的那天,敌寇有些下级军官要向青天白日旗开枪,有些嚎啕痛哭,要切腹自杀,闹了一个多月,南京的紧张空气才慢慢的缓和下来……可见南京政府的成立,对于动摇敌寇军心有了相当效力。”(注:《周佛海之答辩书》(1946年11月2日),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14—215页。)政客们翻云覆雨原是常见手段,不足为奇,但周佛海在这里企图说明他们在沦陷区运用国民党政治符号的实际效果,这固然出于编造,但可以看出他们的一种“理想”——希望利用自己对国民党政治符号的运用,从日本占领军那里争得一些利益;并把某种国民党政治符号的得以运用,视为他们确实从日本争得了利益的证据——1942年底,日本开始酝酿对华新政策,提出“强化国民政府”,汪伪的“地位”有较大提高。1943年2月3日,汪伪国民政府乃发布文告规定:自2月5日起,撤去青天白日旗上的黄色飘带。周佛海对此自得地表示:“一年来苦心及努力竟能实现,虽时机使然,亦努力之结果也。”(注: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下),第807页。)
如前所述,国民党的政治符号在很大程度上是孙中山个人的遗产。日本在兴兵全面侵略中国之始,确实有把国民党视为中国民族主义的代表,并因此有否定国民党政治符号的倾向,它先期扶植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意识形态上不仅与国民党政治符号没有丝毫衔接之处,相反,这两个伪政权具有强烈的反国民党色彩。伪临时政府称:“国民党窃据政柄,欺罔民众者十有余年矣……内则劫持民生,虐政相踵,外则土地日削,反复容共,倒行逆施,不顾社稷之将覆。”(注:《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宣言》(1937年12月14日),《汇编》,第2编第5辑,《附录》(上),第20—21页。)伪维新政府称国民政府“焦土政策,等于自戕,容纳共产,俨同招寇,是中国有史以来惟一之恶政府……”它否定国民政府作为当时中国合法政府的法统,称其“窃号自娱,已失统御能力”。(注:《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宣言》(1937年12月14日),《汇编》,第2编第5辑,《附录》(下),第43—44页。)在扶植汪伪政权的过程中,日本半推半就地接受了汪伪诸人夹带过来的国民党政治符号,但并不满意于在这方面被汪伪“利用”(注:感觉被汪伪“利用”,是日本方面广泛提及地问题,日本“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落合甚九郎就曾报告说:“(汪伪)只各自为维持和扩大本派势力用尽心机,以图最大限度利用日本。”见《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第655页。)的被动(注:日本坦承“缺乏统治异族的经验,对其(按:指伪政权)扶植实为不易。”见《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461页。),乃加入其中,“帮助”汪伪在国民党的政治符号体系中增添于己有利的新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大亚洲主义”。
孙中山长期利用日本作为革命基地,从日本迅速近代化、成为世界强国的过程中,孙中山看到了中国和亚洲解放、复兴的希望。1924年11月28日,孙中山在神户演讲,把日本称为“亚洲复兴的起点”,他说,“从日本战胜俄国之日起,亚洲全部民族便想打破欧洲,便发生独立的运动”,在高度评价日本打破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之功的同时,孙中山提出“大亚洲主义”,要用此主义“以王道为基础,是为打不平”,“为亚洲受痛苦的民族”争得解放和平等,他恳切地提醒日本:“你们日本既得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了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注: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第3册,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版,第535—542页。)紧接着,孙中山又演讲了《日本应该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可以看出,孙中山所说的“大亚洲主义”内涵是非常明确的,即要求日本放弃侵略中国,帮助中国成为国际秩序的平等成员。“大亚洲主义”在孙中山思想体系中不占重要地位,自不待言;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抽掉了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真正根基。所以,汪、日对之加以歪曲,作为国民党政治符号中对他们均有利的东西,就使汪他们的“大亚洲主义”(战争后期不知不觉地衍生为“大东亚主义”)仅仅与“孙中山”这个名字具有皮相性的联想关系。
以汪伪理论家林柏生对“大亚洲主义”的解说为例,他说:“孙中山先生提倡大亚洲主义唯一目的就是要把亚洲民族联合起来,把国际侵略主义从亚洲排除出去,恢复我们亚洲民族的地位,中日两大民族是亚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原动力,所以必要中日合作,才能够领导亚洲各民族,联合起来,才能够恢复我们亚洲民族的地位,才能够建设亚洲的新秩序,这就是大亚洲主义的真义。”(注:《林使节与关西学生对谈》,汪伪宣传部编印:《国民政府使节赴日答礼记》,1940年10月,第65—66页。)如此稚拙、空洞的概念游戏实非由于汪伪诸人的无知,而是因为日本作为“国际侵略主义”一员的事实无法改变,所以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日汪“大亚洲主义”迅速发展成为种族主义的言说,汪精卫论证道:此次战争若英美战胜,整个东亚民族将和印度民族、非洲黑人、澳洲棕色人种一起,同受奴隶待遇,整个东亚将永远为英美的次殖民地;而如日本战胜,英美百年侵略势力将一扫而空,东亚解放,中国也将得到自由平等。(注:汪伪宣传部第50号宣传要点,上海档案馆藏,转引自闻少华:《汪精卫传》,台湾李敖出版社1988年版,第373页。)日本扩大战争的企图,在这里反被标榜成了为解放亚洲而不惜对英美开战。汪伪“大亚洲主义”的穷途末路,和它自称对国民党政治符号的拥有一样,关键在于事实总不站在它这边。
四 中国战时的民族主义与汪伪运用国民党政治符号的困境
按照英国著名“新左派”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看法,西方的民族概念和民族主义运动勃兴于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后,在这之后,欲理解人类历史与社会,离开民族主义是不可能的。(注:[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导伦》。)这种看法显然在中国晚近以来历史解释中极易找到对应点。杜赞奇认为,20世纪初期的中国对描述民族国家的历史特别具有价值,“这不仅是因为现代民族主义在此期间在中国扎下根来,同时也是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启蒙历史的叙述结构以及一整套与之相关的词汇……主要通过日语而进入中文。这些新的语言资源,包括词汇和叙述结构,把民族建构为历史的主体,改变了人们对于过去以及现在民族和世界的意义和看法”。(注:[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尽管对民族主义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但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下,研讨汪伪对国民党政治符号的运用及其面临的明显困境,是不可能脱离民族主义范畴的。
厄内斯·盖尔纳说:“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注:[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霍布斯鲍姆基此演绎该原则的含义为:某一民族之人对代表这一民族的“那个政治体所负的政治义务,将超越其他公共责任,在非常时期(比方说战争期间),甚至凌驾在所有责任之上”。(注:[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10页。)国民党一党执政的国民政府在1928年取得国际社会的承认,成为当时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抗战爆发后,更获得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高度认同,而民族主义正是整合各股政治力量的利器。重庆方面在这方面的先天之利,使其能够要求国民和各政党、团体以其为中心尽团结抗战的政治义务。尽管各方尽这一义务的过程中不断出现矛盾和冲突,但即使在重庆方面最困难的时刻(比如1940年5月宜昌被占、1944年豫湘桂失利),以民族主义为主要纽带的统一战线抗战体制并未彻底崩溃,重庆方面得以在国际范围内保持中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它对国民党政治符号(尤其是可以与民族主义紧密衔接的部分)的保有和运用也因此具备绝对优势,这给汪伪造成巨大的困境。
以《艳电》发表后各界的反应为例。今天对这一文件的明确定性有后见之明的因素在内,其实,至少在汪等人当时的自我定位中,他们觉得自己在《艳电》中坚持以保持国民党政治符号的内涵作为对日议和的前提,是可以说服国人的。但是,在民族主义的语境中,各界对《艳电》的解读立即界定了汪精卫的汉奸身份和卖国企图,并“顺带”反复确认蒋介石的抗战领袖地位,以及对他坚持民族利益的期许。其中,毛泽东就明确判断汪精卫乃“叛国投敌”,表示中共将“拥蒋反汪”。(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页;(台湾)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作战时期》,第6编,《傀儡组织》(3),第55—76页。)
《艳电》发表后相当长时间内,国民党中央仅将汪精卫永远开除党籍(这在民国史上是很滑稽而无谓的处分),蒋介石甚至连汪一系列动作的准确性质也未公开判定。(注:张生、柴林:《蒋介石对汪精卫投敌迟未公开定性与表态原因探析》,《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2期。)但从各界反应看,一方面,除个别人外,认为汪言行系叛国性质的判定非常明确;另一方面,被汪寄予厚望、引人猜想的地方实力派比蒋嫡系还要激烈,而且,绝大多数人认为仅永远开除汪党籍的不够的,象与汪精卫渊源极深的张发奎就称汪“虽加寸磔,未足蔽辜”,要求国民政府将其“通缉归案,明正典刑”。(注:《第四战区代司令长官张发奎等以汪危害党国请通缉归案明正典刑之微电》(1939年1月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作战时期》,第6编,《傀儡组织》(3),第65页。)这些,反映了民族主义强势语境下中国各界的反应方式和趋向,事实上,陈嘉庚等人还提到当时国民参政会作出的抗战“中途言和,即为汉奸国贼”的决议,以提示、激励蒋介石。(注:《南洋华侨酬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以汪赞同日寇亡国条件请宣布其罪通缉办法之世电》(1938年12月3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作战时期》,第6编,《傀儡组织》(3),第55页。)蒋介石显然注意到了民意所在,他后来也以同样民族主义的态度告知孔祥熙:“以后凡有以汪逆伪组织为词而主张与敌从速接洽者,应以汉奸论罪杀无赦。”(注:《蒋委员长致电孔院长祥熙凡有以汪逆伪组织为词而主张与敌从速接洽者应以汉奸论罪杀无赦之佳电》(1939年10月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作战时期》,第6编,《傀儡组织》(3),第159页。)
汪伪深知战时民族主义是必须正面应对的情绪和思潮,因为当时的民族主义时刻冲击着其“和平运动”的根基,所以汪伪诸人乃不得不在民族主义的语境中,为其言行辩护。尤其汪精卫本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反制工作。
首先,汪精卫承认“军队和人民都已充分的表达了民族意识,这是不可磨灭的”,但他说“这种民族意识,如今已被共产党完全利用了”。汪说:“利用民族意识,在民族意识的掩护之下,来做摧残民族断送国家的工作,在共产党是以为当然的,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有所谓民族,有所谓国家”。(注:汪精卫:《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汪精卫问题研究组》选编《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判资料选编》(内部资料),1981年5月,第307—312页。)在此前的国共争斗中,曾有不少国民党人对中共恶语相向,但汪精卫所强调的,是中共的“非中国”特质,他说:“共匪向来提倡工人无祖国的,向来提倡阶级观念超于国家观念的……共匪之抗战目的,与中国人之抗战目的,完全是两样的。中国人之抗战,为本国而战。所以其结论自然是不得不战则战,可以和则和,共匪之抗战,为第三国际而战,其目的在使日本疲敝,使中国崩溃,所以其结论自然是抗战到底……共匪是另外一肝心的,不足为怪,所可怪者,是那些做共匪工具的,到底是全无肝心呢?还是已与共匪同样的另外有一副心肝呢?”(注:汪精卫:《和平运动殉难同志追悼大会献辞》,《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判资料选编》(内部资料),第332—337页。)这里,汪的意思可以表达为这样的三段论:中共是非国家、民族特质的——所以他们说抗战到底是别有用心——跟着中共喊抗战到底的也是别有用心。
其次,汪极力辩说,日本是中国实现民族主义目标的希望。如前所述,汪精卫对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进行曲解,是其宣扬中日合作的重要理论源泉,而在应对中国战时民族主义的冲击时,他再次乞灵于此。他说:在孙中山的理想中,“日本没有对于中国之顾虑,发展更快,中国得到日本之援助,发展也易,并且更可以中日两国之协力将欧美经济压迫的势力,从东亚排除出去。这是民族主义的精髓,也是民生主义的精髓”。(注:汪精卫:《三民主义之理论与实际》,《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判资料选编》(内部资料),第313—323页。)而中国之所以不能实现民族主义,“因为我们忘记了大亚洲主义”(注:汪精卫:《新国民运动纲要》,《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判资料选编》(内部资料),第375—378页。),汪说,大家对日本有很多疑虑,其实,“近卫声明”的实质是:“日本大声疾呼的向中国说,日本并不是走灭亡中国的那一条路,而是要走与中国协力共保东亚的这一条路。”(注:汪精卫:《和平运动殉难同志追悼大会献辞》,《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判资料选编》(内部资料),第332—337页。)“我们要本于民族主义与大亚洲主义,来与东亚的友邦合作,与东亚的各民族合作,以求中国民族的解放”。(注:汪精卫:《新时代的使命》,《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批判资料选编》(内部资料),第340—344页。)
汪在辩无可辩之处强说其理,只能是概念的游戏,而在民族主义理论中,亦面临深渊:“如果民族原则是用来把散居的群体结合成一个民族,那么它是合法的;但若是用来分裂既存的国家,就会被视为非法。”(注:Maurice Block in Labor,Cyclopedia of Political Science,vol.2,p.941.转引自[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第35页。)日本全面入侵中国造成的分裂状态是显然的,与日本合作而谈民族主义,诚非任何逻辑所能解释。
到汪伪“还都”前后,他们对国民党政治符号的营建已经较具体系,而日军对国民政府的军事压力随之达到颠峰(注:蒋介石在抗战期间感到最严重的危机是1940年6月宜昌被日军占领,同时,“桐工作”进入讨论蒋介石、板垣征四郎长沙会谈的紧要阶段。见《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540页。),包括中共在内的各种政治势力都在怀疑重庆方面被诱降的可能,这理论上应该是汪伪取得国民党政治符号使用权的好时机。但《日汪密约》刺激民族主义情绪再度高涨。与《艳电》发表时的反应相比较,以杜赞奇所云“民族国家”的角度声讨的更形普遍——考虑到当时的声讨者并不知晓当今政治学中“民族国家”的概念,其无意中的契合更具意义。而英美认定重庆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表态,强化了“民族国家”气氛中的中国国家认同,见表 一:
表一 汪伪“还都”前后各界的反应(注:据《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作战时期》,第6编,《傀儡组织》(3),第202—358页各团体、个人通电整理。)
反应者
对汪伪的定性、声讨
对国民政府的期许
蒋介石
签订了万劫不复的卖身契
不血战就会被汪逆出卖做奴隶
广西省临时参议会
阴行密约、出卖国家 争取国家民族独立
云南省政府 出卖祖国、签亡国之条约
御侮锄奸、完成抗建
吴鼎昌等
背叛党国、危害民族 歼灭暴敌、扫荡汉奸
反应者
对汪伪的定性、声讨 对国民政府的期许
马鸿逵等
出卖国家,秦桧、刘豫、张邦昌所不忍为
保障我国家民族独立生存
山西省政府 空前未有之汉奸
扫荡倭寇,奠定复兴民族之基础
绥蒙会委员长沙克都尔札布等 组织伪府、遗羞华夏 驱逐倭奴,还我河山
悉尼全体华侨数典忘祖 诛灭敌贼,抗战到底
温哥华华侨 丧权辱国、誓不承认 拥护抗战
越南南圻华侨通敌卖国 争取国家民族生存独立
泰国华侨
盗卖国族 拥护抗战
陈诚认贼作父 在蒋委员长领导下,灭此国贼
英国外相艾登重庆国民政府为合法之中国政府援助中国维护其独立
美国国务卿赫尔
重庆国民政府为唯一合法之中国政府
日本的侵略和暴行是中国战时民族主义极度高涨的关键激发因素,而以民族主义为推翻清政府利器的国民党,其政治符号以民族主义为旗帜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作为日本傀儡的汪伪因此面临悖论式困境,究其原因,从汪阵营里脱身的陶希圣曾敏感地分析到:“汪及周、梅的错误,就是失落了民族的壁垒。”相形之下,重庆方面在民族壁垒的后面,“战可以坚持,和可以对等”。(注:陶希圣:《“新中央政权”是什么》(1940年2月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作战时期》,第6编,《傀儡组织》(3),第229—239页。)
陶希圣说重庆在民族壁垒后面进退有据,大概暗指重庆在“桐工作”中令日本迷惑的若即若离。其实,在重庆方面的文宣攻略中,亦可看出它得以掌握话语权的民族主义原因。以重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汪伪政权建立前后对媒体的宣传指导为例:
高、陶出走泄露日汪密约后,它立即指示媒体:“(1)将汪逆卖国密约及有关文件印成小册散发,尤应送入敌占区,使国民知所警悟。(2)指示各地报纸刊物对汪卖国行为不断的撰载评论严予抨击。(3)对于高陶二人不予批评。(4)发动全国对于参加伪组织之一切汉奸予以社会制裁,如由宗族同学会及社团予以除籍处分或其他制裁。”(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快邮代电》(渝美宣字第10396号),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七一八,案卷号225。)日、汪就先前各伪组织与日本造成的“既成事实”进行折冲时,它指示:“(1)日梁密约及合同八种,举将华中之国防资源与企业,如矿业、铁路、航空、电报、电话、都市及港湾建设等尽归敌人独占与经营,此项卖国文件业经汪逆精卫一一承认,并经认为日汪密约中所谓既成事实之一部,汪逆卖国于此又得一铁证。我舆论界应加紧讨汪宣传,使敌亦知汪逆已为我国所共弃,同时发动战地民众加紧实施对敌经济破坏与反封锁,使敌经济侵略无法成功。(2)敌阀灭亡中国、独霸东亚之迷梦实为万变不离其宗,从日梁密件中可知敌寇独占中国之野心,不特现在排斥欧美权利,即各国过去在华之法益及未来对华之贸易亦决予根本推翻。(3)将日梁密约大量翻印,连同日汪密约普遍宣传,并说明敌伪此种毒辣阴谋之暴露,实为敌寇日暮途穷行将溃灭之事实的反映。(4)敌人攫取此项毫无法效之卖国条约后,妄思据此以为囊括中国之凭藉,近日更唆使汪逆等肆其狂吠,鼓吹其奴隶的和平论以达到诱降目的,吾人应根据我抗战国策外交自主立场痛予驳斥。”(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快邮代电》(渝美宣字第11192号),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七一八,案卷号225。)汪伪政权“还都”前夕,它指示:“(一)嗣后对汪逆之伪组织,应称为汪逆伪组织,不得再用伪中央政权或汪政权等名称,尤须避免用中央二字。(二)汪逆将于三月三十日成立伪组织,各地应于该日一律开始举行大规模的铸奸运动,即铸奸逆跪像于忠烈祠或无名英雄墓前,并尽量揭发汪逆罪恶及丑史,但不必举行宣传周。”(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快邮代电》(渝美宣字第11620号),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七一八,案卷号225。)重庆方面的上述指示不仅显示它对法统的坚持,而且始终站在“政治上正确”的民族主义立场上;不仅在当时掩盖了它本身强调“欧美权利”以对抗日本的并非完全正当的立场,对照后来的历史也是相当高明的。即以“使敌亦知汪逆已为我国所共弃”而言,在汪伪“还都”后,日军长时间不予以其期望的支持,而且不能忘情于重庆方面,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日方认为汪伪无实力,是中国人心目中的汉奸(注:1941年7月,日方坦率地表示:“国民政府还都已一年有余,但其政治上统治范围所及,没有超过皇军占领地区,南京的命令一出城门,就会遇到种种困难”。见中央档案馆等合编:《日汪的清乡》,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8页。);而“铸奸逆跪像于忠烈祠或无名英雄墓前”的对策,构建了令人会心的意象,直接导致民众将汪精卫夫妇与秦桧夫妇相提并论。
相对应的,汪伪这段时间也有宣传指示,据重庆情报,其指示要点,除对高、陶出走表示怨恨外:“1、不敢公然否认卖国密约之存在,2、在报纸副刊短评中作狡辩不敢以社论正式辩驳,3、不敢公布而狡称无公布之必要,4、妄指日本不撤兵为我(按:指重庆)抗战之反应,5、承认军事经济有日本顾问。”(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快邮代电》(渝美宣字第11275号),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七一八,案卷号225。)可见重庆的民族主义立场给其造成的被动。
中国战时民族主义对汪伪的不利,迫使它一面在民族主义语境中强行美化日本在中国的形象,汪精卫就曾在纪念孙中山逝世15周年时表示:过去两年多的战争已经证明,日本所说援助中国成为自由独立国家,“并非欺人之谈”(注:《汪逆伪中央政权运动近讯》(1940年3月1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作战时期》,第6编,《傀儡组织》(3),第239—248页。);一面“痛切”地劝说日本方面稍稍放权,以掩盖其傀儡实质。周佛海曾委婉地对日方说:“我常常听见说,日本的话,说得很好听,日本的声明也说得极漂亮,但是实际上所做的事,完全不是这样。口口声声所说的平等互惠的经济合作,事实上完全表现为垄断。英美的经济侵略,还替中国留下一点生机,象最近一年来,所表现的中日经济合作,比几十年来的英美经济侵略,要厉害得多,几乎不仅把肉吃光,连毛带骨都要吃得干干净净,中国没有生存的余地。”(注:周佛海:《回忆与前瞻》,《中华日报》1939年9月22日—24日。)但这样痛切的哀求并不能使日本改变其侵华的本质目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汪伪诸人对民族主义语境中他们的历史命运是十分清醒的:周佛海对日本陆海军人员演讲时曾说:“重庆各人自命为民族英雄,而目余等为汉奸,余等则自命为民族英雄。盖是否民族英雄,纯视能否救国为定。余等确信惟和平足以救国,故以民族英雄自命。但究竟以民族英雄而终,抑以汉奸而终,实系于能否救国。如余等以民族英雄而终,则中日之永久和平可定;如以汉奸而终,则中日纠纷永不能解决。”(注:《周佛海日记》(上),第213页。)后来历史对周佛海“远见”的证明,其实说明了民族主义在民国历史演进中的巨大作用。
标签:中国近代史论文; 汪伪国民政府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台湾国民党论文; 历史论文; 汪精卫论文; 国民党论文; 三民主义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孙中山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