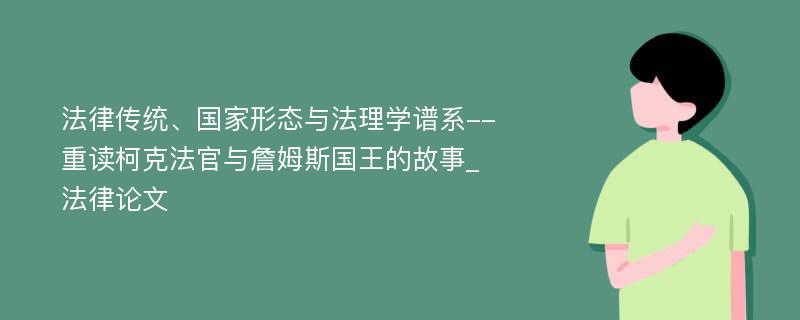
法律传统、国家形态与法理学谱系——重读柯克法官与詹姆斯国王的故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詹姆斯论文,谱系论文,法理学论文,法官论文,国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28(2007)02-0050-12
故事发生在17世纪初的英格兰,当时的君主是詹姆斯一世(James Ⅰ,1603-1625在位),具体日期是11月10日,一个星期天。应坎特伯雷大主教班克罗夫特(Bancroft)的奏请,詹姆斯国王召见了英格兰各法院的法官们。其目的是寻求法官们认可大主教给他提出的一个建议:①对于法院的法官审理的案件如果有疑问的,无论案件的性质如何,概可以由国王自己“以王者的身份”直接进行裁决;因为法官不过是国王的代理人而已,国王有权按照自己的喜好裁决案件。
针对国王的这一要求,时任高等民事法院(the Court of Common Plea)首席大法官的爱德华·柯克爵士(Edward Coke,1552-1634)回答说:
由英格兰全体法官、财税法庭法官见证,并经他们一致同意,国王本人不能裁决任何案件,不管是刑事的,比如叛国罪、重罪等等,还是各方当事人之间有关其遗产、动产或货物等等的案件;相反,这些应当在某些法院中,根据英格兰的法律和习惯来决定和裁决。
柯克接着援引了一些古老的先例以证明其观点。(以下为柯克第一人称的叙述)
对此,国王说,他认为法律是以理性为基础的,而除了法官之外,他和其他人也一样具有理性。
针对这一说法,我是这样回答的:确实,上帝赋予了陛下以卓越的技巧和高超的天赋;但陛下对于英格兰本土的法律并没有研究,而涉及陛下之臣民的生命或遗产、或货物、或财富的案件,不应当由自然的理性,而应当依据技艺理性和法律的判断来决定,而法律是一门需要长时间地学习和历练的技艺,只有在此之后,一个人才能对它有所把握:法律是用于审理臣民的案件的金质标杆和标准;它保障陛下处于安全与和平之中;正是靠它,国王获得了完善的保护。
听到我的这番话,国王感到受到了极大的冒犯,他说:那么,如此说来他将处于法律之下了,要知道这种说法是构成叛国罪的。
对此,我回答说:布拉克顿曾说过“Quod Rex non debet esse sub homine,sed sud Deo et Lege” (国王不应当受制于任何人,但应受制于上帝和法律)。[1](P478-481)
一、故事是真实的吗?
这就是著名的柯克法官与詹姆斯国王的论争。依据这一故事最初的出处——柯克法官的《判例报告》第12卷中的记载,我们所能确定的真实情景仅限于以上的对话。但颇令人费解的是,无论在柯克本人的著作中,还是与其同时代人的文字中都鲜有提及这一今天看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对话。以致后世的西方学者不断有人怀疑柯克所记载的这场对话是否属实甚或是否存在过?②
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对西学成果的隔膜,国内的研究还不曾对这一故事的真实性提出过怀疑,而多半将之作为确定无疑的经典予以接受和阐发。英国历史学家罗兰·厄舍(Roland Usher)教授曾专门撰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考证,[2](P664-675)使我们可以对这一故事的来源和真伪有一个较为客观的认识。
首先是记载该故事的柯克《判例报告》第12卷的真伪问题。由于柯克法官与王室的矛盾,其著作的许多手稿生前都未能发表;1634年,在柯克逝世后的数个月后,查理一世国王即下令查封了柯克所有的手稿。直到1656年,柯克的这些以法律法语写成的手稿才被重新整理与翻译成英文,并在议会的支持下作为《判例报告》第12卷得以出版。这些手稿在20余年间是如何被处置的,人们不得而知。因此,第12卷的《判例报告》很难被视为法律史研究的第一手权威资料。[3](P461)
其次是柯克同时代作者的记叙,是否能够印证柯克与詹姆斯的对话?依据厄舍教授的研究,关于这一辩论,除柯克自己的记叙外,同时代还有三份记录或多或少提及了这次争论。③但通过对四种不同记录的比较,我们会发现“其间的分歧和出入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柯克自己的记叙很难被证实是完全真实的”。比如,就这次会议的时间,所有四种记录都认为其发生在一个星期天,但其具体的年月与日期却各不相同。④此类抵牾之处还有许多,都从不同角度动摇了柯克《判例报告》中的记录的可靠性。
当然,以上同时代其他作者的记述与怀疑也未必就是完全真实的,可以肯定的是,面对詹姆斯国王扩张王权的言论,柯克确实在某种场合提出了自己的异议和忠告,只是时间、地点与方式也许并不如柯克本人所记载的那样清晰准确。因此,最接近于真实的情景也许是:柯克确实曾参加过几次类似的会议,詹姆斯在这些会议上发表了“由国王裁判案件”等有违普通法的言论。柯克终于感到无法容忍并向国王坦陈了自己的意见,并决意将之记录下来,以流传于后世。为了使人们确信其言论的正确,他有意隐去了许多国王的论证,同时对自己的言论进行了加工,许多话也许是他准备说却未能向国王表达的言辞。也就是说,或许柯克自己在多年后记录这段对话时,自己也已经混淆了“他本来想说的话”与“他在真实场合中对国王说过的话”。[2](17674)
通过以上考证,我们已经可以肯定柯克在其报告中记述的这段著名的对话并非对事实的忠实记录,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论证仅仅能动摇其在史料学意义上的权威,其本身意义并不因此而受到多大的减损,这则故事仍可以被我们用于分析其中人物与时代的特征。正如厄舍教授在该文最后总结到的“柯克是否引用了布拉克顿的名言,或是否曾在詹姆斯国王面前卑躬屈膝,这些都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它们丝毫不能改变最后的结局,即他最终未能容忍国王的行为。”[2](P675)
二、詹姆斯国王在主张什么?
抽象来看,詹姆斯国王在这场争论中扮演了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形象,是一个地道的“反派”角色。但是如果放到故事的文本以及这个故事相关的事件脉络和时代背景中,对詹姆斯国王的这一定位似乎并不准确,至少有欠公允。
(一)“专制”抑或“民主”?
面对柯克关于“国王不能裁决案件”的主张,国王回答说:“法律是以理性为基础的,而除了法官之外,他和其他人一样也具有理性”。
显然,国王在这里是试图论证国王可以裁决案件的理由。但值得留心的是,国王此处的说理与论证并非我们印象中的那样专横无理,相反,却是“有理有据”,甚至“入情入理”的。至少从逻辑上来看是严密的,其大前提是“法律以理性为基础”,其小前提是“国王和法官乃至其它人一样都具有相同的理性”。如此一来,国王可以如同法官一样审理案件便是顺理成章的结论了。
倘若詹姆斯国王确乎是一位专制暴君,他完全可以径直宣布其个人的意志处于众人之上,宣称自己拥有某种全知全能的才智;或者依据“君权神授”理论,认为其个人的意志即神的意志,等等。又何必将自己降低到普通人的地位,绕着弯子去论证“法律的理性”与“人人皆有理性”呢?可见,柯克法官与詹姆斯国王的论争并非我们传统意识形态中的“海瑞式”的刚烈谏臣对昏庸暴君的“犯颜直陈”,⑤而其实是一次双方基于各自政治与哲学立场的甚至不乏学术意味的对话。
更进一步说,詹姆斯国王的这一论证非但不具有丝毫“专制”的气息,相反,却是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司法民主”的因素。因为柯克所主张的“法官司法”是认为法官具有特殊的技能与知识并从而“垄断”司法,其实质是一种“精英司法”的观念。詹姆斯国王与之针锋相对,指出任何人的理性都是相同的、平等的,否认某个人或某一阶层对司法权的垄断。其目的或许是为了论证“国王裁决案件”的观点,但在客观上也承认了普通人能够运用与生俱来的常识或良心对案件做出公正的审判,而这一点正是“司法民主”得以成立的基石。
当然,我并不认为“精英司法”与“普通人司法”两者中的某一方具有必然的优越性。直至今日,我们的司法模式仍介于“两难”之间的选择。英国的司法活动在高度精英化的同时,仍实行着代表“普通人心智”的陪审团制度。但是,当这一近乎学术化的争论发生在国王与他的大法官之间时,人们却表现出了对柯克法官的观点近乎一边倒的支持;而詹姆斯国王的观点、论证及其间蕴含的学术价值则不假思索地被否定乃至被根本忽略了。⑥
(二)“国王”抑或“主权者”?
詹姆斯国王在对话中第二次打断柯克的发言,是当柯克直接宣称“国王受制于法律”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受到了极大的冒犯,并斥责柯克:“如此说来他将处于法律之下了,要知道这种说法是构成叛国罪的”。倘若说詹姆斯国王的前一句话在表面上还保持冷静、克制,并不乏学理的话,那么此时的国王显然已怒不可遏,直接将柯克的言论定为“叛国罪”。一副专制暴君“穷凶极恶”的嘴脸,似乎顿时原形毕露了。
事实似乎又并非那么简单。因为这仅仅是一种道德上的评论,我仍试图探寻詹姆斯之所以在此处发怒的其它原因。为什么之前还冷静克制的詹姆斯对于“国王应处于法律之下”这一言论如此不可容忍呢?这仅仅是所谓“专制”、“暴虐”所能解释的吗?
这就有必要回到詹姆斯国王本人的政治乃至哲学立场上进行回答。正如上文所分析的,詹姆斯国王并非我们传统史学中描绘的一味鼓吹“君权神授”、“专制独裁”的暴虐之君,相反,其本人在许多场合都表现出渊博的学识与思维缜密的论辩。更确切的说,詹姆斯国王除却其在英国政治史中扮演的专制君主的角色外,他本人同时也是一位著述颇丰的哲学家,并在欧洲17世纪的哲学史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早在1598年,当詹姆斯还是苏格兰的国王詹姆斯六世时,他就曾撰写并匿名发表了《自由君主之真正法律》一书。在该书中,詹姆斯明确地认为“君主拥有的是一种绝对权力,他们是凭借上帝的意志和万物的自然秩序而有此职位的”。[4](P1667)当然,“绝对权力”的理论并非詹姆斯国王的首创,他的许多思想来源于欧洲大陆的马基雅维利和布丹,尤其是后者的主权学说。在其名著《国家论六卷》中,布丹指出:任何一种政治体制要维持稳定,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存在一种能制定法律并在行使其立法权时不受任何其他人限制的权威,即国内意义上的主权。[5](P22)
倘若回到历史中看,詹姆斯的政治理论并不会像我们今天读到它时显得那样冥顽不灵。实际上,绝对君权的理论正是17世纪欧洲大多数国家流行的政治理论,同时也是最具革新意义的哲学思潮。 [6](P11)布丹已经为这种学说提供了哲学上的论证,而詹姆斯只不过从君主权力的视角将这一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更何况,詹姆斯的态度与立场也不是这一理论的极端表现,相比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的宣言,只能通过匿名著作与国会演说来表达其主张的詹姆斯一世,显然要相形见绌得多。
同时,“詹姆斯的理论在英格兰也并非是孤立无援的,绝对君主制的理论对于英国而言,在都铎时期就曾隐含存在。就两者的本质而言,斯图亚特基本的政治与法律理论与之前流行的政治理论并无差别”。[4](P1673)此外,詹姆斯理论在英格兰的受欢迎还可以从17世纪英国的哲学思想界得到最有力的支持,几乎堪称17世纪英国最伟大的两位思想家培根⑦与霍布斯⑧都是绝对君权理论的附庸或支持者。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詹姆斯国王在此处发怒的原因就并不仅仅是因个人的意气,而更多是因为柯克的言论触及了他所竭力主张的同时也是他不曾达到的绝对主权观念。国王与柯克第二轮回合的对话也同样隐含着重要的学术论题,而不仅仅是君主因臣下冒犯而本能的“龙颜大怒”。
三、柯克法官在主张什么?
现在回到柯克法官。与上述对詹姆斯观点的讨论相似,我们同样可以将柯克的上述话语转化成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司法裁判应当依据怎样一种理性?一是法律与主权者,谁居于国家的最高位置?
(一)“自然理性”与“技艺理性”
柯克在这里首先提出了“技艺理性”学说。面对国王关于“法律是以理性为基础”和“他本人和其他人一样具有理性”的说法。柯克没有一味否认国王的说法,而是对之进行了巧妙的区分。在承认国王具有“高超天赋”的基础上,将人的理性一分为二:一为自然理性;一为技艺理性。前者是人所与生俱来,也为每一个人所共有的理性,但却不能用来裁判司法案件;后者是需要长时间学习和历练才能获得的技艺,却是唯一可以运用于审理案件的理性。
可见,詹姆斯国王与柯克法官双方都将自己的法律诉诸理性,其内涵却大不相同。詹姆斯所借助的自然理性乃是希望从人类与社会共通的本性出发,找到建立社会秩序的一般原理,从而建立一套完美无缺的法律制度。既然普通人可以依据其“自然理性”对案件做出公正裁判,那么作为立法者的主权者在裁判案件上自然更具有天然的优势,并理所当然成为“最高的法官”。[7](P22-25)因此,这种对“自然理性”的尊崇,表面上继承了对英国“普通人司法”的古老传统,“但实际上为主权者通过立法来重构法律秩序和操控司法铺平了道路”。[8](P166)
与之相反,柯克诉诸的技艺理性从根本上否定了普通人尤其是主权者在制定法律、理解法律和运用法律的可能。因为技艺理性既非与生俱来,也非人所共有,它是“通过漫长研究、考察和经验而实现的一种技艺上对理性的完善,是经历了许多时代兴替,为无数伟大博学之士一再去芜取精,完善而成”。[8](P168)所以只有在法学教育中浸淫数年,阅读过无数历史判例的法官们才可能获得这种理性,也因此才能把握法律的内容,并依据其对案件做出合理的裁决。
诉诸于这一概念,也不难从中看出柯克的目的或是“用心”,那就是通过知识上的垄断来确立法官在司法上的独立权威。但这毕竟对于当时的思想界是一个异端,也长期为之后的法学家或哲学家所诟病。如霍布斯就认为,普通法的“技艺理性”是一种含糊不清的东西,因为世上只存在一种自然理性,并不存在特殊的法律理性。[7](P1-7)再比如法学家边沁也认为所谓“技艺理性”是纯属虚构的,普通法充满了缺陷、神话和误解,法庭程序复杂,完全是非理性的。[8](P164)
这种批评也许是正确的。严格地说,理性确乎只是一种,也只能是与生俱来的理性。而且这种技艺理性同样不能排除边沁所说的混乱、含糊不清等非理性的特征,在成功抵御主权者权力侵害的同时,也将其它社会成员的“常识”或“普通人心智”拒之门外。
但与此同时,柯克所称的“技艺理性”又并非是完全虚构的,而是真实的存在于英格兰的法律与历史之中。其实质是对英格兰古老普通法中的“判例传统”与“程序传统”的一种抽象与提炼。一方面,技艺理性乃是一种历史理性,其起源也超过了人们所能记忆的时代。⑨其真实的载体就是历史上无数法官因袭下来的判例,是历代法官所经历的实践尝试。另一方面,技艺理性乃是一种程序理性,程序性优先于实体性是普通法的特点。这种对程序的强调即意味着一种比掌握实体法更高要求的技艺,它几乎不能通过直接阅读法律而获得,而有赖于一种学徒式的言传身教。
因此,柯克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明确的,即司法裁判只能依据法官所特有的技艺理性做出。尽管柯克如此回答不乏“别有用心”甚至是“狡黠”,但詹姆斯国王何尝不是一个精明而狡猾的论辩对手,其表面上尊崇“自然理性”而实质是为国王获取司法裁判权寻求论证。如此一来,柯克既要否定国王的实际主张,又不能断然否定法律之具有理性。面对这一微妙而棘手的局面,柯克以“技艺理性”做为反击就不失为一种大胆而高明的策略。
(二)“王在法上”与“王在法下”
接下来是第二个问题:法律与主权者,谁居于国家的最高位置?
面对国王的愤怒与威吓,柯克近乎平静而优雅地回敬以英国中世纪法学家布拉克顿的名言:“国王不应当受制于任何人,但应当受制于上帝和法律”。我们似乎已经从中得到答案:柯克毫无疑问地支持法律处于王权之上。但这仅仅是似乎,真的没有疑问了吗?
疑问首先来自于材料的本身,即历史学家们怀疑,柯克是否真的以布拉克顿的话无礼地反驳国王。甚至依据同时代人的记载:面对詹姆斯的“勃然大怒”,“柯克忙不迭地乞求陛下怜悯他,宽恕他”。[9](P305)当然,这一疑问又是可以忽略的,这些记述至多只能证明柯克并不如我们原本所设想的那样有“骨气”,但并不足以否认柯克在内心是坚定地拥护法律高于王权的。
更大的疑问来自于柯克一生中对待王权的态度的“转变”与“矛盾”。至少伊莉莎白女王的时代,柯克的确是以强大王权的坚定拥护者出现的。他本人即被伊莉莎白一世任命以检察总长这一最具王权色彩的重要职位。为捍卫王权,他曾表王室提起了多个个诽谤罪和叛国罪的公诉。⑩英国宪政史权威斯塔布斯称柯克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赋予王室法律上法人地位的人,是他在封建权力的纷争中,将国王在法律上重新认可为国家的代表”。[10](P107)
这一疑问显然最具挑战性。我们当然可以将其中的原因归于柯克本人职位的转变。“作为检察总长,柯克是王室利益的首席辩护人,他的工作就是捍卫王室的特权;作为一名法官,他宣誓要忠于法律,他的职责乃是捍卫法律的利益。”[6](P12)但是如果将这一转变仅仅视作一种圆滑世故或一种缺乏原则,又似乎过于肤浅,仍停留在道德评判的层面上。
实际上,正如大多数柯克研究者指出的:柯克在王权问题上的态度前后变化如此之大,并不仅仅是因为其职位与立场的变化,而是“他越来越注意到新国王的绝对主义倾向”,换言之,“斯图亚特的英国不同于都铎时代的英国,一个人可以无比忠诚地支持伊莉莎白的王权,也可以同时极端贬损詹姆斯的王权”。[9](P293)伊莉莎白与詹姆斯在统治在策略上有很大的区别,前者的治理善于权衡利弊,懂得在必要的时候妥协,“绝对立法权”意义上的主权概念变成了仅限于国王习惯上“依照议会的建议并争得议会同意”而行使的那部分权力。[11](P41)但相比之下,斯图亚特的詹姆斯是在苏格兰相对落后的政治文化环境中长大的,对英格兰议会制度和普通法传统缺乏深刻理解,加之自身性格,一味宣扬君权神授与绝对至上,最终激怒了包括柯克在内的“伊莉莎白主义者”。
由此可见,在柯克的眼中,也许并不存在“王在法上”还是“王在法下”的问题,柯克只是坚信“英国政府是一个由国王、上院、下院与法院共同组成的混合政体”,[5](P254)它们之间的关系完全是由古老的普通法设计的,是一个和谐有机的整体。因此,对柯克而言,同样不存在赞成王权与反对王权的问题,历史决定他也无法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唯一需要讨论的仅仅是君主特权的范围问题,而这又只能依据普通法而非任何人或任何其它法律来裁决。
四、两种主张的背后——什么的对立?
柯克的故事为我们理解17世纪英国的政治与法律提供了许多线索和启示,它使我们发觉历史的复杂性远不如我们传统意识形态中理解的那样简单、泾渭分明。在这一则经典故事的背后,还有许多更深刻的文化信息留待我们解读。
(一)“普通法”与“罗马法”——法律史的解读
柯克法官与詹姆斯国王之所以冲突的分歧之一是关于法的理性,前者主张的是技艺理性,后者则推崇自然理性。究其实质,技艺理性乃是法官与律师等法律人之于案件裁判的一种专业技能,其核心观点是以为法律存在司法判例之中,因而我们可以称之为“判例法的理性”。而自然理性则代表了在承认人类共通理性的基础上寻求普适性规则的努力,其核心观点是认为人类可以依据其理性制定出完美的法律,因此我们也可以将其归结为一种“制定法的理性”。而判例法与制定法的区分正是英国普通法与欧陆罗马法之间最重要的分别。
放到故事的背景中,17世纪的英国正是本国固有之普通法,面临全面危机的时代。有如茨威格特所言:“在英国法律史中,只有一个时期,普通法曾全面面临被罗马法完全驱除至少被挤到一边的危险”。[12](P290)当时的欧洲大陆,从11世纪开始的罗马法复兴运动已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民族国家的潮流与立法理性相结合正孕育着法、德等国第一批近代法典的诞生,并迅速向四周传播与扩张。相比之下,英国普通法则仍然显得杂乱无章、晦暗不明,仍处于前科学化的“混沌和黑暗”之中。面对正在兴起的罗马法和衡平法,普通法受到了日益严厉的挑战。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对普通法进行改革,其中积极倡导的代表人物就是前文述及的弗朗西斯·培根。他专门起草了25条法律公理,希望运用“理性的一般命令来贯穿各种不同的法律事务”。[13](P204)
故事的主角之一詹姆斯国王显然也是以罗马法为代表的立法理性的代言人。这不仅是由于他本人所来自的苏格兰在很大程度是继受罗马法的,(11)更由于罗马法中“国王的意志具有法律的效力”这一主张对詹姆斯国王有极大的吸引力。同时,詹姆斯也明显偏袒衡平法庭及其它新兴的特权法庭,而这些法庭也多半是受到罗马法思维的影响。(12)
从这个意义上说,柯克法官在这场对话中关于“技艺理性”的主张实际上是代表英国固有之普通法对罗马法正在发起的进攻进行了反击。在柯克看来,普通法同样是具有理性的,只不过这种理性是不同于罗马法自然理性的技艺理性。他同样认为普通法需要系统化,不过他采用的形式不是培根的法律公理,也不是罗马法的法典化体例,而是通过在《法律年鉴》中添加新的判例,编纂更完善、案例更“现代”的《判例报告》来为普通法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个理性化的基础。[3](P465)如此一来,柯克法官与詹姆斯法官的论争表面上是“技艺理性”与“自然理性”这两种“理性”之间的分歧;但更深层次上,是英国传统的普通法与欧洲大陆正在兴起的罗马法之间的碰撞,是17世纪英国普通法所面临的总体危机的一个缩影。这也许再次印证了詹姆斯国王的论争绝非我们之前想象的那样“强词夺理”,相反,在其身后同样也存在着深刻的理论背景。他提出“自然理性”也绝非偶然,尽管不排除这仅仅是其推行专制理论的“说辞”或“借口”,但这恰恰说明了詹姆斯国王对整个欧洲哲学与法学思潮的深刻体察。在他身上同样不缺乏法学家的气质,尤其是罗马法学的素养。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就完全站在了詹姆斯国王或是罗马法的立场上。在我看来,柯克法官的智慧同样令人赞叹。面对罗马法这种显而易见的外在形式的优势与自然理性在近代哲学中几乎绝对的话语霸权,柯克法官既不丝毫屈服,也不一味守旧,而是凭借其对普通法古老传统敏锐的把握,创造性地提出了普通法中同样蕴含这一种足以对抗“自然理性”的“技艺理性”,并通过其编纂《判例报告》等活动亲身推进技艺理性和普通法的完善,从而有效地化解了普通法在17世纪所遭遇的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捍卫了古老普通法的传统。
(二)“封建主义”与“绝对主义”——国家史的解读
仅仅是法律史的解读还不足以充分理解这一故事,如果放大到政治与社会历史的视野中来看,我们会发现一些更为宏大的历史因素是造成故事中冲突的可能更深层次的背景。
从故事中争论的另一个焦点来看,在“国王是否受制于法律”这一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詹姆斯国王代表的“绝对主义”主权观念与柯克代表的“非绝对主义”观念的冲突。如果说在詹姆斯国王的“绝对主义”代表的是一股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潮流的话,那么在柯克所坚持的“非绝对主义”的背后,是否存在另一股力量的驱动呢?
一种比较有说服力的观点是认为柯克反对“绝对主义”王权的动因导源于其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立场,其“国王受制于法律”的观点皆来源于“国王与陪臣的封建契约关系之中”。[9](P293)萨拜因甚至毫不夸张地宣称“柯克之所以违抗詹姆斯是由于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保守派,甚至是反动派”。[14](P511)从理论层面来看,这种概括无疑是极为深刻的,其实质是将柯克反对国王的原因置于“封建主义”与“绝对主义”对立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下,是一般拘泥于将柯克的“反对王权”等同于现代“民主”或“法治”思想的人所无法观察到的。因而,至少对于中国当下流行的理论可能具有某种“颠覆性”。
而且,欧洲的历史的发展也似乎如此。中世纪的欧洲在10到11世纪形成了封建制度,并直接导致了王权的日益衰微。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张力维持了社会一定的自主性空间,一些新的因素在这些空间里生长出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法”的地位得到了提升,“统治者必须在法律之下统治”成了流行的政治信条。[15](P53)但历史发展到16世纪后发生了逆转,随着商业贸易与战争规模的迅速扩大,中世纪的封建体制开始瓦解,强大的王权开始成为历史进步的因素。欧洲的封建制国家逐渐开始向近代民族国家形态演变,开启了政治近代化的序幕。而以专制王权为代表的“绝对主义国家”正是这一转型的中间状态,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主权民族国家。(13)
詹姆斯国王与柯克法官的冲突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历史变迁的宏大背景之下。从这个角度来看,詹姆斯国王代表的是正在形成、尚不稳固但必将成为此后一个世纪全欧洲政治潮流的绝对主义国家;而柯克法官代表的是正在衰落但影响仍然巨大的封建主义传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詹姆斯代表的是一种“变革”的力量,而柯克代表的一种“保守”的力量。但我并不认为这种将柯克的立场归之于“封建主义”的观点就是完全正确的,在颠覆性的背后,它可能只是一种“片面的深刻”。在我看来,柯克所处的这个历史转型的时代恰恰决定了他的性格与思想是复杂的,甚至是“矛盾”的,似乎又无法为一种简单的“保守主义”或“封建主义”所能概括,至少不是那么纯粹。
正如本文在第三部分所分析的,柯克在要求限制王权的同时,其本人又正是王权的坚定拥护者,甚至是“绝对主义的理论信徒”。只不过他所拥护的是“伊莉莎白式”的绝对君权,是一种未曾逾越普通法范围的专制权力。詹姆斯国王却欲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试图将普通法的约束也置之不顾或是减少到最低程度。但在柯克看来,“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16](P257)
如果说前述西方学者的解说还带有很强的“唯心”(不含贬义)色彩的话,那么柯克身上所表现出的这种“矛盾”同样可以在封建主义向绝对主义转型的这一历史变迁中获得一种更为“实证”的解说。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同样是柯克所处的时代与环境:一方面,柯克处在17世纪英国政治的中心,必然强烈感受到绝对主义这一政治潮流的趋向,这促使他近乎真诚地忠于英国的王权;但另一方面, 16、17世纪之交的英国毕竟仍是一个封建传统依然强大的时代,柯克生长于这个时代,尤其是早年在内殿法律学院的学习,注定其基本的知识结构是封建主义的,这又决定了他不可能在绝对主义的道路上走的太远,至少不能接受王权对古来普通法的逾越。柯克的“矛盾”正是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特质的反映,“新的潮流”与“旧的传统”交织汇集,“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14)使柯克的一生也许都处在这种“进步”与“保守”的冲突与抉择之中,尽管柯克本人并不曾意识到这一点。
(三)“形式主义”与“现实主义”——法理学的解读
以上两种解读,分别从“法律史”与“国家史”的角度对这一故事做了“可能”是比较新的分析,但这并不意味着故事的意义仅限于“历史”的解读,它同样可能对现代有所启示。实际上,从法理学的角度来说,柯克法官和詹姆斯国王的论争已经触及了“法律是什么”这一法学的根本问题,这也就意味着两者的争论在当下并不曾结束。正如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1939-)所指出的,两者提出的“技艺理性”与“自然理性”的论辩思路在很大程度上隐含了“形式主义”与“现实主义”这两种基本法学观点的对立。
1.“法律形式主义”
如前所述,柯克在这场论争申诉诸的是法官特有的“技艺理性”,并认为国王也应当服从这种特殊的理性,其根本的观点就是认为法律是“脱离政治统治机构而存在的,是一种职业等级的领地”。也许这正是波斯纳将这一类观点称之为“法律形式主义”的原因,在他看来,柯克的观点在根本上将法律“独立于现实世界”,将法律的本质归之于“法官提出的并在他们的司法决定中表述或隐含的学理体系”。[17](P13)
回到故事的语境中,我们不得不承认波斯纳法官的洞见。“技艺理性”的实质本是将法律的权威归于历史上无数法官的司法判例,其初衷也许是以此作为抵御政治权力侵袭的屏障,但同时也造成了法律与现实世界的隔绝,使法律成为一种高度“形式化”的封闭体系。
柯克的这一观点在随后的两个世纪中为英国的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1723-1780)和美国的克里斯托弗·兰德尔(Christopher Langdell,1826-1906)所继承,并得到进一步的推进。布莱克斯通把自然法体系引入到英国法中,使普通法具备了来自上帝的超验效力,而法官则成为了“神谕的宣示者”,其职责在于发现并宣布永恒自然法的原则与信条。[18](1792)而19世纪的兰德尔则成功地将柯克与布莱克斯通的学说进行了综合。与柯克一样,兰德尔认为法律的权威来自于历史上已经公布的成千上万的司法判决,但同时他又认为法律的本质并非这些判决本身,而是隐藏在这些判决中的“少量的永存的、不变的、无可争议的法律原则,而这些判决不过是那些永恒原则的不完善体现。 [17](P18)
柯克与布莱克斯通开创的传统在当代的西方法理学仍不乏追随者,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就是其中的代表。德沃金坚定地认为法律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原则”,在他看来,法官并不是“运用公共政策改变和创立了法律”,而是“通过解释这些原则发现了适用于手中的法律”。尽管德沃金也区分“原则”与“政策”,但同时他又认为,原则问题才是更具实质的问题,也比政策问题更重要。[19](P117-121)
因此,柯克在这场论争中展现出的观点实际上代表了人类长久以来对于法律本质的一种倾向性看法,即认为法律首先应当是一套自给自足的形式体系,它本身即具有足够的合理性,而试图排斥一切外来世界的干扰。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的“形式主义”并不必然是贬义的,尽管它可能造成法律与现实社会的疏离,但它本身具有相当的合理性,至少在马克斯·韦伯那儿,“形式合理性”的法律乃是唯一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相适应的一种法律类型。[20](P118)而柯克的贡献就在于为这样一种进路构造了“技艺理性”的学理基础,从而使得形式主义的传统能够始终在法理学的谱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2.“法律现实主义”
詹姆斯国王的论辩思路与之针锋相对,其依据的是人类共有的自然理性,认为主权者是法律的来源与制定者。尽管詹姆斯国王囿于他的时代与自身立场,坚定地认为国王应当居于主权者的位置上,但其论辩思维的实质并不仅仅在于将法律视为国王的意志,而是将法律权威的来源归之于“占支配地位的群体的意愿”,而不再来源于法律职业阶层的内部。
依据波斯纳的划分,这种思路的实质是一种“法律的现实主义”,即认为法律的权威来源于活生生的现实世界,法律“彻头彻尾地就是政治”,因此普通法法院的法官在司法裁判的问题上并不具有天然的优势,任何人只要能洞悉其所处社会的需求与潮流,就能够对案件的审理做出“合乎情理”的裁决。
这一观点同样构成了近代以来法理学谱系中的重要一支,比如我们之前提到的霍布斯,就坚定地站在了国王的立场上,进一步论证了由强有力的君主做为立法者与“最高的法官”的原因。[7](P22-35)尽管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欧洲的专制统治纷纷被推翻,被代之以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的政体。但究其实质不过是将议会这一也许代表多数人意志的机构推上了主权者的位置,所不同的只是“占社会支配力量”的代表由“一人”变为“多人”,是一种数量上的改变。詹姆斯国王及其他专制君主的统治被推翻了,但其思维仍统治着这些国家。
18世纪的英国法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就是这一思维的杰出代表,他明确地反对柯克的“技艺理性”与布莱克斯通的自然法,主张法律的本质不过是实现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工具,因此制定法律的中心应从法院转移到更能反映社会主流意志的议会。[21](P38)尽管这一主张不乏民主的色彩,但其实质仍是詹姆斯所开创的“现实主义”进路。而19世纪的美国法官霍姆斯(Oliver Holmes,1841-1935)则比他的前辈更为明确地提出了“法律现实主义”的主张,在他看来,“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一个时代为人们感受到的需求,主流道德和政治理论,对公共政策的直觉”才是法官在判决中所更应当遵循的法律依据。[22](P11)
与“形式主义”一样,“法律现实主义”在美国当代法理学界也同样不乏其后继者,兴盛于20世纪的“现实主义法学运动”乃至“批判法学”都奠基于此,包括波斯纳法官本人也大体属于这一阵营。尽管其本人并不完全承认这一点,但他坚定的认为,如果仅就“法律是什么”这一法理学的核心论题而言,“法律现实主义对法律实体的把握要深刻得多。”[17](P34)如此一来,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詹姆士国王在这场论争中所提出的观点所包含的价值,无论其本人的真实动机如何,他的言辞本身就构成了系谱学上的意义,代表了近代西方社会对法律形式主义最初的质疑,也反映出人类对于法律本质的另一种倾向性看法,即认为法律不应当仅仅是一套形式的体系,在法律规则之外,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社会中普通人的主流观念与基本需求。
这样一种现实主义的声音从来没有停息过,尤其在进入20世纪以后几乎掌握了绝对的话语优势,即使极力推崇形式合理性的韦伯本人在晚年也指出了现代法律中的实质主义因素。(15)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主义就必然成为当今各国法学的主导思想,其本身同样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质疑,它毕竟脱胎于君主与强权者的言说,专制主义的影子仍不时地显露出来,以至于近代以来总有人不断指出这一进路同极权主义之间可能存在的内在联系。(16)因此,本文在发现詹姆士国王话语之价值的同时,也实际上构成了对“法律现实主义”所应有的一种“警惕”(同样不含贬义)。
总之,从这个意义上说,柯克法官与詹姆斯国王的争论实际上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提出了“法律是什么”这一法学领域的基本命题。时至今日,这依然是现代法理学中最具根本性的问题,至少柯克与詹姆斯两人所开启的“法律形式主义”与“法律现实主义”的两条道路之间的选择与争论仍在继续。而上述法理学解读的意义,也就绝非是为了评判两者的正误或是优劣,而是试图通过这则故事的隐喻揭示这两种进路各自可能的利弊,进而为我们当下的选择提供有益的智识资源。
结语——对重读的反思
柯克与詹姆斯国王的论争距今已近整整四百年了,也构成了法律史上为数不多的经典之一,有关他的文字也已经很多。但我依然觉得这则故事与当下中国的法律和法学有某些被忽视的关联,因此对它的重新解读仍然可能是有意义的。
首先可能来自于故事所包含的信息,来自于它对现今中国的政治与法律进步可能的启示。我们对这则故事的传统解读可能更多是以君主专制与近代法治的对立为视角,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我还应当看到其中所蕴含的法理学的智慧——不仅是柯克的智慧,还包括詹姆斯国王的智慧。因为相比宽泛意义的“法治”观念在中国的普及,有关法律形式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讨论还没有真正在中国的法学语境中展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接受柯克或是詹姆士的主张,或一定要采取“形式主义”或是“现实主义”的态度。但危险的是我们对任何一种进路都盲目地引进而吸收,而忽视了这些观点在西方语境中的原初含义与生存环境,因而对可能导致的不利后果与弊端不曾察觉。这也许恰恰说明我们对这场论争本身的意义挖掘不够,以至于看不到故事中双方人物的主张其实都蕴含着对当下中国有益的经验。
其次,重读的意义可能更多来自于故事的本身,来自于对中国法学中传统解读的一种修正。柯克的故事已成为中国法学的经典,但经典又往往是被误读的。故事本身的细节往往被“肢解”与“滥用”,而无须再仔细阅读原本的文献与案例。我国法学界对柯克的故事的原始版本及其真实性的忽视似乎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些具体、生动的故事往往只变成一个概念、一个符号,有的甚至被严重的意识形态化了,失去了其揭示法学理论问题,人类制度和智识难题的潜在意义,也因此失去了其学术的活力及其在中国的本土的繁殖力”。[23]通过细致分析故事文本及时代背景提供给我们的相关信息,我们会发现,无论是詹姆斯还是柯克,其人物的性格与内心世界都是极端复杂的,甚至是不乏“矛盾”的,而绝非传统的“专制”或“法治”等符号化概念那么简单。进一步深入到历史中,我们还会发现这些人物性格的矛盾又绝非偶然,而是其身处的宏大历史变迁的结果,从而有可能获得更多有关法律理论或历史的启示。
当然,这都仅仅是“可能”,甚至我自己也无法排除本文在某种程度上对这则故事进行了“新的误读”的“可能”。但我想,重要的是我们重新回到了故事的本身,回到了柯克所身处的那个时代之中。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故事对于今天的启示,但首先要听懂的是,故事中的“他们”在说些什么?
收稿日期:2006-06-10
注释:
①该故事的其他中文翻译可参见:[美]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刘山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09—510页;贺卫方:《柯克的故事》,载《司法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7-249页;[美]罗斯科·庞德:《普通法的精神》,唐前红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1-42页;[美]小詹姆斯·R·斯托纳:《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姚中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但由于以上的中文翻译的出入比较大,影响了对原文的理解,这里依据《柯克报告》中的英文原文重新翻译。
②Sheppard Steve为“Ptohibitions del Roy”撰写的按语,参见Sheppard Steve,The selected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sir Edward Coke,vol.I,Liberty Fund,2003,p.479.
③它们分别是:1、Julius Caesan关于会议的记录;2、John Herry的私人信件;3、Rare Boswell的私人信件。
④在柯克的报告中,只记录日期是11月10日,却不曾提及年份;在Boswell的信件中将这一时间推定为1607年,但实际上1607年11月10日是星期二;Caesan的记录则将时间定在1608年11月13日;这一时间得到了Herry的记录的支持。一般人认为这一时间可能最接近真实的时间。参见Roland G Usher,James I and Sir Edward Coke,English Historical Renew72(1903),p.670.
⑤梁治平先生曾撰写《海瑞与柯克》一文,将海瑞对嘉靖皇帝的直言犯上与柯克对詹姆斯国王的冒犯相比较,旨在探讨中西法律传统的不同。参见《海瑞与柯克》,载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7 -284页。
⑤相比之下,霍布斯撰写的《哲学家与英格兰法律家的对话》一书,尽管同样是讨论自然理性与司法理性的关系,但后人更多将之作为是哲学与法学的学术探讨来看待。可詹姆斯国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参见[英]托马斯·霍布斯:《哲学家与英格兰法律家的对话》,姚中秋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⑦弗朗西斯·培根长期担任詹姆斯国王的检察总长,始终对强大君权有着真诚的信念。他也是柯克法官一生的劲敌,在他撰写的《论司法》中将柯克归于坏法官的类型,并宣称:“法官应该是狮子,但他们是国王宝座下的狮子”。参见《培根论说集》,水天同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97页。
⑧霍布斯的绝对君权思想可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杨昌裕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英]托马斯·霍布斯:《哲学家与英格兰法律家的对话》,姚中秋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⑨关于普通法理性与历史主义的关联,参见Pocock,J.G.A,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a study of English historical though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Cambridge Univ.Rr.,1987,pp.30-55.
⑩直到詹姆斯国王的初期,在Raleigh一案中,继续担任检察总长的柯克仍然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将曾经反对詹姆斯登基的 Raleigh宣布为叛国罪。参见Bowen,Catherine Drinker,The Lion and the Throne: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Edward Coke,Brown & Company
Limited,1957,pp.190-218.
(11)苏格兰继受罗马法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为抵抗英格兰的侵略而与法国结盟的结果,参见[美]格林顿等:《比较法律传统》(影印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页。
(12)在1615年的牛津伯爵案中,他就坚定地站在与柯克相对的大法官艾尔斯密尔一边,宣布“衡平法优先于普通法”。关于此案的评论,参见Bowen,Catherine Drinker,The Lion and The Throne: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Edward Coke,Brown & Company Limited,1957,pp.356-369.
(13)中世纪以来,欧洲国家形态的近代化经历了从封建国家到绝对主义国家再到宪政国家的历程。参见[美]贾恩弗兰科·波齐:《近代国家的发展——社会学导论》,沈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4)这是不是使人想到20世纪初中国的风云多变,想到梁启超的“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呢?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儒家哲学》,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
(15)韦伯在著作中详细论述了“现代法律发展中的反形式主义趋势”,尤其是“现代法律职业中的外行人司法与合作的趋势”。参见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张乃根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6-317页。
(16)See Edward A.Purcell,The Crisis of Democratic Theory: Scientific Naturalism and the Problem of Value,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73.类似的批评,还可以参见[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9-1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