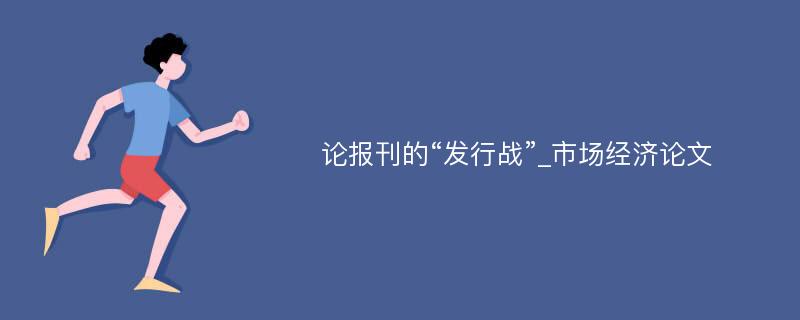
报刊“发行大战”面面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刊论文,大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跌”声中的繁荣
酷暑终于过去后的秋天,对于各报刊的总编辑们,将是一个更加漫长而难耐的季节。随着一年一度的征订发行大战愈演愈烈,不知从何时起,他们已全然顾不得“元帅与士兵”历来都有的分工以及诸如身份、矜持之类,纷纷亲征“前线”,持枪参战。时至今年,连位及“部级”官阶的总编辑也不能例外了。这之后,他们还要诚惶诚恐、度日如年地等待到年尾,等待一个渺茫的希望——来年本报(刊)发行量略有上升;至少等来一份可怜的安慰——跌幅不大……。
然而,本世纪以来,由于广播电视越来越成为公众获得新闻的主要媒介,报刊发行量的下降已经变成一个无法逆转的世界性趋势。早在20年前,美国芝加哥大学全国舆论研究中心就在调查中发现,进入70年代后,美国看报人数减少了7%,日报平日(除周末)的销路从6310万份下跌到6090万份。数目也从本世纪初的二千二百多家降到一千七百多家,而这时的美国人口却比60年前增加了一倍多。
从这一点来说,中国报界是幸运的。当外国同行在不可预料的沉浮中苦苦挣扎时,我们却享受着那么长“无忧无虑”的时光。没有财政困境,没有生存压力,而电视进入家庭则更是许多年后的事。
中国报界又是不幸的。在毫无“市场”经历,甚至未来得及先学会成本核算、广告经营等等,就像一个不会水的孩子被改革开放大潮不由分说地裹进了“市场”的海洋,并很快就遭遇了与西方报业那些老练的“水手”相似的命运——跌。再跌……。《中国青年报》10多年前曾有过发行量高居320万份的辉煌,今年,这份有着上亿青年作为既定“市场”的报纸竟差点跌破100万份!“界中人士”已差不多都“没出息”到只求自己跌得少点的份上。如果哪家果真略有上升,职业敏感便会告诉他:这是新闻!令人伤感的是,这样的报道今年年初人们确曾读到过,不论哪家报纸实际增加份数怎样地微不足道,但2%的升幅,毕竟是个堂堂皇皇的正数呵!
尽管一跌再跌让报刊的“老总”们再难摆脱挫折感的纠缠,中国报业却在跌声中有了第一次繁荣和发展。一个最简明的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仅被新闻出版署批准为全国刊号的报纸总数就已达到两千多家,比1978年前的180多家增加了十几倍。就在发行形势特别严峻的今年,前六个月仍有近400家新创办报纸获得了新闻出版署的批准。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庞大到连新闻出版署的主管官员也无法提供准确数字的“内部报刊”群。
一位在一家中央大报供职的中年编辑很感慨地说,当年他们从人大新闻系毕业时,北京可供他们“择业”的报刊社,寥寥可数,也就是“人民”、“光明”、“中青”、北京日报、晚报等几家。除此,好像就没有什么可去的地方了。而今天,报纸已多得让人目不暇接。的确,你现在几乎找不到没有机关报的中央部委,一些司局级单位也办起了自己的报纸。报纸读者对象的划定,也细到了可谓见缝插针的地步。有以地域划分的,有以年龄划分的,有以行业划分的,有以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的衣食住行等内容划分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正是“宏观”上的这种成倍增长,分流了远不可能同样成倍增长的读者,造成了“微观”上报报下跌,刊刊自危的局面。
竞争开始了
谁也没有发表讲话,谁也没有发文件,市场机制就悄悄地进入了新闻宣传领域,办报的书生们像一群旱鸭子一样被纷纷打落水中,扑扑楞楞地在发行市场学习竞争。
阴云般驱之不散的“跌”,使几十年来一直在中国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拥有很高地位、享有很高待遇的“无冕之王”们,第一次切肤地感受到,市场经济不承认特权,在报刊这个大“家族”里,最终也将以市场法则否定“贵族”。“发行大战”是无情的,甚至还很混乱,可它已在一定程度上教会了报界尊重读者,为读者服务,在竞争中求发展。
从一开始竞争就是全方位的,从报道内容到形式,从经营战略到推销手段……。但贴近读者,争取读者,使本报刊占有尽可能多的市场份额却始终是个基本出发点。如两年前热遍全国报刊尤其是一些严肃报刊的“扩版风”。虽然扩版后可增加广告收入,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动机。实际上,有些报刊原有的广告版都“稿件”不足。一家扩版动作较大的报纸的编辑告诉记者,他们报扩版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稳住继续下降的读者队伍。当时,突然增多并销路很好的“地摊”小报使他们很有些坐不住,人家为什么卖得那么“火”呢。于是,他们决定学习小报的一些长处,比如增加一些更贴近生活的内容,比如杂志化倾向等等。这一“招”,对以市场经济方式生存的报刊的确是有效的,与70年代美国报界试图制止发行量下跌所采用的对策不谋而合。当时,下跌中的《纽约时报》就是以增加四个杂志化版面使销路很快恢复到原来水平的。
但是,对于报刊而言,发行量的竞争最直接的还是发行本身的竞争,至少现阶段是这样。于是,10年前就有报刊一下就把“文章”做在了发行上。
1985年新年刚过,河南洛阳市委机关报《洛阳日报》首先树起“自办发行”的旗帜,第一次打破邮政部门几十年来不可动摇的独家经营体制。中国报业第二发行渠道从此诞生。
勿庸讳言,自办发行的起因首先是来自邮局发行费的压力。新闻出版署的耿峰说,到1984年,邮发费用已高达所发报刊订价的40%,全国很多报社都在赔钱办报。可再赔,任何报刊都决不会靠压缩发行量来维持“收支平衡”。因为对报刊来说,发行量不仅仅是发行量,在很大程度上它还决定着广告的数量和含金量。既要扩大发行,又要减少发行成本,才冒着风险自己搞发行。不料,这一原本只是为了解决经济困难的尝试,竟收到了意外的结果,报社不仅经济上活了,而且,发行量还上升了。
《洛阳日报》的成功,给了报界同仁极大的鼓舞,第二年就有《合肥晚报》、《柳州日报》、《太原日报》等六家,第三年又增加了《重庆日报》等十一家脱离邮局办“自发”。10年后的今天,据新闻出版署提供的数字,全国自办发行的报纸已达700多家,占全国报纸总数的三分之一多,其中有200家地市以上党报,占地市以上党报的70%。耿峰介绍说,大凡搞“自发”的报纸,“自发”后的发行量都比从前“邮发”时多。他认为,这是因为“自发”从一开始就是市场机制,把优质服务视为生命的结果。“比如给城市高层建筑送报,邮递员一般就送到一层的收发室或信箱,‘自发’的投送员就会爬上20层送到读者家里。像其它商品一样,谁服务得好,谁就能赢得消费者。”一家中央级刊物的发行人员说,曾有人鼓动他们脱离邮局搞“自发”,并承诺:你们交给我办好了,我保证让你们一年内发行量翻番。
然而,邮局仍然是我国报刊发行的主渠道,而且,只有他们才能把报刊送到深山老林、穷乡僻壤。面对自办发行的挑战,邮局也在抖擞精神,改善服务。从侧面了解到,他们现在不仅搞上门征订,而且准备扩大零售。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们不愿就此接受采访。近十个电话号码转圈打了十几天,邮电部的有关部门终究还是以十分得体的理由谢绝了采访,最后,干脆对“邮发45年成就”这个正面话题的采访请求也推辞了。
权力介入了报刊市场
众所周知,现阶段的中国报刊市场其实并不是个真实的市场。大致情形如下:消遣类报刊主要以各种能刺激读者的内容在竞争读者,而政治时事类报刊拼命你争我夺的则不过是每个单位允许从党费、团费、办公费等等中开支的那部分订报费,即公费订阅。在后一种情况中,单纯凭服务好“打动”读者,是不足以巩固“市场”的。
人们可以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至今还没有一家中央级政治时事报刊(不包括行业报刊)搞自办发行。省级报纸也只有天津日报一家独领风骚。开办“自发”的几百家报纸基本上都是地方性的城市报纸和行业报纸。这意味着,办“自发”需要条件,不是有“块块”地盘上的依托保护,就是有“条条”、“一杆子插到底”的行业便利。虽然此处“条条块块”更多的意义在于投递的可能性,但不能否认,物质(报刊)得以顺利流通的渠道,同样也一定是精神(指示、指令、指标)上传下达最畅通的渠道,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存在着或明或暗的摊派。至少今天是这样。
于是,就有人批评道:目前报刊市场上的竞争像是一场没有规则没有裁判的球赛。谁都想去“咬”一口公费,可公费不仅是有限的,而且随着机构改革的不断深入,用于征订报刊的事业费总量在减缩,再加上报刊连年提价,不平等争夺一直呈日益剧烈之势。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混乱”是必然的。因为市场经济的报刊生存方式——自由竞争,与计划经济的报刊消费方式——公费订阅之间,本身就是一个大大的矛盾,它不止是给“权力”提供了空前的用武之地,还给“权力”借助金钱来实现权力、达到目的提供了理由和可能。近些年“权力”的“权威性”在“市场经济”中受挫的事经常发生,因为报刊订阅终究是软任务。无奈之中,“权力”除了硬性摊派订阅外,也用起提成、回扣、奖励等等营销手段,用得很有特色,往往是级别低的“权力”比级别高的“权力”提成、回扣、奖励多;也用得很理直气壮:“现在是市场经济嘛!”这蕴含着一个很大的危险:如果权力能“卖”掉报刊,提高办报质量就会成为多余;如果回扣可以“推销”权力,在整个报刊市场上,我们的“上帝”——读者还会有什么权益可言?
对此,基层,尤其是广大农村反应十分强烈,他们尖锐地指出:这是一种腐败!那一捆捆、一摞摞送到造纸厂的崭新的报纸、杂志说明了什么?这里,直接受害的是被摊派者。但是,在它背后,是资源和资金的极大浪费。谁该对此负责?从目前情况看,这是一块三不管的地区,哪个部门都有足够的理由说这不归他们管,尽管我们有那么多吃俸禄的官员。而实际上,也许因为我们的官员队伍太庞大了,才办出那么多靠摊派订阅的报刊,变着法子来坑企业、农民。事情很清楚,那些凭摊派发行的报刊生存不愁,连广告也可以摊派的,所获利润就可以堂皇地作为奖金发放,而有关部门则有税可收,有注册费可收,对他们来说,报刊越多,收入越多,管它作甚?
“混乱”能否治理?
人们或许会想,既然订报公费是燃起发行大战弥天硝烟的根源,取消公费怎样?
记者曾请教新闻出版署的有关官员,国外是否也有用公费订阅报刊的问题。对方回答说:照理说不会有。
倘若读报仅仅是个人的精神文化消费,当然岂有公费之理?问题恰恰在于,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新闻事业本质上是党的耳目喉舌,承担着“用正确的思想教育人,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重任,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伟大事业中负有崇高的历史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理直气壮地做好党报党刊及其它重要、权威的政治时事类报刊的发行工作,让它们拥有更多的读者,就决不只是“消费”范畴的事。正是基于这一点,各地党委宣传部每年都要重点推荐一批报刊,邮局更是在它的整个发行网络规定了党报党刊的发行基数,完不成者要受罚。由此,人们完全可以这样理解,允许企事业单位有一定数量的公费用于报刊订阅,是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得以广泛传播并占领思想舆论阵地的重要保证。公费并无错,错只错在对无错的公费那般无序且不平等的“竞争”。
取消竞争当然是更不可能的。中国正在由计划经济努力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报刊的市场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终有一天会出现报刊因竞争失败而关门的事情。但是,有没有可能改革一下竞争的形式呢?中国的严肃报刊之间,什么时候才能不“竞争”发行“特权”而真正竞争新闻,竞争特色,竞争报刊质量呢?这一点,可以说是眼下被发行大战搞得苦不堪言的总编辑们的共同愿望。
一份只有七、八个编辑,办在西北边远省份的《读者文摘》为这个愿望提供了某种希望。这份品味高的严肃刊物,几乎全部是个人订阅,根本不用专门搞发行,仅在北京地区发行量就超过了20万份。
这只是指严肃而有益的报刊。还有那么多号称严肃但无新内容,那么多“有用”而并不严肃,那么多既不严肃又无用的报刊,凭借权力去和严肃而有益的报刊争夺那可怜的公费,这种情况,难道不应认真地治理一下吗?我们为什么不能搞出一个法律来规范报刊市场呢?
标签:市场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