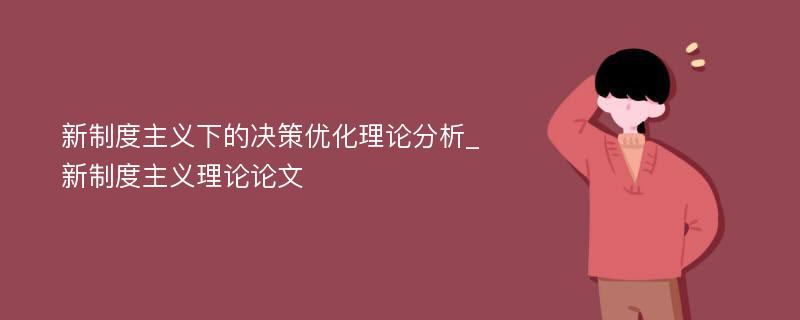
新制度主义决策优化理论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义论文,理论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制度研究曾经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其研究领域涉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体系。相关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甚至在新古典主义理论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制度主义者也有不小的影响,可以说在行为主义革命之前,整个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制度主义的。制度研究的兴衰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中期之前是早期的制度研究阶段;20世纪70年代组织概念被引入制度研究领域,由此拉开了新制度主义研究的序幕。1984年美国学者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发表《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一文拉开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研究序幕①。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以及制度变迁理论形成了新制度主义研究谱系。新制度主义的复兴并非制度分析的一种简单回归,而是制度分析的现代转型,新制度主义是在批判行为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制度主义的“新”体现在既关注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又吸收行为主义的动态、过程、定量化的研究方法。本文主要关注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从制度研究的角度出发,可以把整个政治学的发展概括为旧制度主义、行为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美国学者彼特斯(B.Gruy Peters)把这些分支概括为:规范制度主义(Normative Institutionalism)、理性选择制度主义(Rational Choice Theory and Institutional Theory)、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经验制度主义(Empirical Institutionalism)、社会学制度主义(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利益代表制度主义(Institution of Interestrepresentation)和国际制度主义(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ism)②。彼得·霍尔(Peter A.Hall)和罗斯玛丽·C.R·泰勒(Rosemary C.R.Taylor)在1996年的英国《政治研究》上发表的《政治科学和三个新制度主义》一文中提出把“新制度主义”分为“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理性选择制度主义”(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和“社会学制度主义”(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③。新制度主义各流派虽然观点差异,但都把制度看作政治生活的核心要素,重视制度安排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主张政治制度引导政治行为。与此同时,个体及其行为也是非常重要的要素,但是必须把个体放入一定的制度背景之中进行理解和分析。新制度主义关注制度对政策决策及其他政治选择的影响,新制度主义关于决策优化理论认为,制度决定着行为者的选择范围、行为偏好及其行动能力,它为特定社会化过程中的行为角色提供了某种内在化的行为规范,启示人们从全新的视阈去研究决策、检视决策。
一、新制度主义关于决策优化的理论阐述
新制度主义以前的研究范式关于公共政策决策的研究都不够全面。行为主义过于注重行为对决策的影响,认为政策的变化是个人所引起的,个人的行为导致政策的变化,而忽视制度在政策变化中的作用。旧制度主义则从宏观的、正式的制度和结构来研究政策的变化,认为政策的变化是正式的制度结构所引起的,托马斯·戴伊(Thomas R.Dye)在《理解公共政策》一书中提出公共政策分析的制度主义模式就注重正式的制度结构。但旧制度主义的制度范围过于狭窄,所理解和研究的大都是一些宏大的制度结构,在这种制度结构中,个人的偏好所起的作用甚微,只能服从既定的制度安排。因此,行为主义和旧制度主义都只对公共政策变化的研究给出了某些方面的解释,其研究成果不能很好地解释政策变化的实际过程。新制度主义则从制度和行为偏好两个方面来研究政策变化,认为只有结合两方面的因素才能准确理解政策的变化,做出合理的决策。
决策优化就是要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决策科学化是对经验决策、随意决策的扬弃,它表现为决策程序的科学化、决策手段的科学化以及决策结果的有效性。决策的民主化是对权力独裁和官僚主义的抛弃,能够保证决策集聚众人的智慧、代表多数民众的利益,从而使决策有效的程序和原则。决策的法治化是对盲目决策、武断决策的否定,使得决策程序和决策手段符合法治理念,决策主体更好地受到法律的监督。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是一项纷繁复杂的决策过程,而真正有效的治理最终必然要体现在制度层面上,即以制度的形式固化下来,通过有效的、可操作的制度来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新制度主义的现实意义在于它扬弃了早期制度研究中浓厚的学术思辨色彩和规范研究中主观判断所导致的混乱,旨在揭示制度、行为与决策间的逻辑关系,强调决策在国家治理中的核心地位。
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决定着行为者的选择范围、行为偏好及其行动能力。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个体理性会导致集体行动困境的出现。为了实现理性自身的价值和利益,制度就被创造出来了。制度一旦产生,就为相关行为者提供了约束和激励机制,它为特定社会化过程中的行为角色提供了某种内在化的“行为规范”和认知模版,即指明行为者在特定情景下把自己想象和建构成何种角色。
精英主义和多元主义一直遵循“行为——政策结果”的研究模式,即政治行为者的行动会直接导致某种政策结果的产生,制度是一种既定的外在因素,忽视了制度对政策结果的影响。新制度主义的研究视角发生了从“人”到“制度”的转变。“认为社会科学如果从对结构的分析开始,并在此基础上再考虑人的独立影响会获得更大的解释力。”④因此在决策研究中,“行为——政策结果”的模式不能真实反映政策决策过程。新制度主义对这种决策模式进行了拓展,把制度因素考虑进去,从而衍生出两种决策模式:即“制度—行为—决策”模式和“行为—制度—决策”模式。在“制度—行为—决策”模式中,制度是个自变量,它影响着行为者的动机和行为策略,从而使行为者做出某种决策。在“行为—制度—决策”模式中,制度是一个中介变量,是行为者进行决策的背景因素,制度为决策提供了外在的框架,行为者就是在制度的背景下制定公共政策。制度分析视角的引入,使公共政策决策的研究从“行为”和“决策”的双项变量,变成了“行为”、“制度”和“决策”的三项变量⑤。这使得公共政策决策的研究更加深入,进而能在制度的视角下进行多种理论模式的探索,构建多种政策研究框架和决策机制。新制度主义意识到政治行动者之间的偏好是在政治生活中发展起来的,宪法、契约以及政治生活中的惯例能够产生许多潜在的行动和许多不正当及不受关注的想法;一些备选方案可能在政治生活开始之前,就已经被排除在决策议程之外⑥。新制度主义作为一种政策决策研究范式,使得研究者重新审视制度的功能,使公共政策决策的研究视角和政策结果都发生了转变。
新制度主义通过对不同行为方式进行价值和道德判断,并赋予不同行为以不同标准。制度在社会生活中形塑着不同的角色,规范不同角色的行为准则,然后通过社会化的方式使其内化为个体行为,从而使个体的行为受到规范的约束。新制度主义认为,行为主义将个人行为的聚合看成是集体现象存在诸多问题。罗伯特·达尔(Robert A.Dahl)指出,对个人偏好的分析无法完全解释集体的决定,还需要研究个人意愿被聚合为集体决策的机制。制度在此发挥着双重功能,一方面束缚和规范人们的行为,同时也提供了人类自由的不同路径。制度作为人类的创造物,能够被政策加以改变。政治制度可以更公正,在这些制度下做出的政治决策也将为塑造更好的公民而改变它们⑦。所以,新制度主义的各流派拒绝承认利益聚合的可能性,认为决策不能建立在个人偏好的聚合上。通过制度形成新的理念、重新界定个人偏好,利益聚合机制在于重新塑造而不是简单的聚合。
制度对行为者的行动方向和方式,以及与其他行为者的关系格局具有建构作用。行为者的利益判断不是随意产生的,而是基于对特定制度结构的认知。制度对其框架范围内活动的不同行为个体的最终行为结果有重要的影响。不同的制度结构意味着种种非对称性权力结构的存在,在特定制度框架下会形成不同的力量对比格局,既定的制度往往维护着这种力量对比的格局。彼得·豪尔(Peter Hall)认为,在组织结构中的特定位置影响和制约着参与者如何去界定自己的利益,制度在这里帮助行为者确定在特定位置上的责任以及与其他行为者的相互关系⑧。所以,在不同的制度结构中会产生不同的行为方式以及同样的行为方式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能产生不同的结果。
新制度主义决策理论认为,通过对人类行为的约束,制度能够增加人类行为的规律性,减少其不确定性,使预测和决策更加科学。制度具有激励功能,诺斯在分析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时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⑨因此,能激励行为者不断努力和创新的制度就是好制度,因为它能给特定组织里的行为者提供持续的激励,从而影响行为者的决策和行为结果。
新制度主义借助有限理性、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等核心工具对决策目标和方向进行价值判断,然后进行意向性决策分析。新制度主义导致决策方式发生了一系列改变:首先,表现在从理性到有限理性、从经济人到行政人。理性决策的人性假设是经济人,有限理性决策的人性假设是行政人。“经济人与行政人不同点在于:一是经济人寻求最优——从可为他所用的一切备选方案当中选择最优者。经济人的堂弟——行政人,则寻求满意——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或足够好的行政程序;二是经济人同真实世界的一切复杂事物打交道,而行政人则认为,他自己头脑所感知的世界,是对纷繁杂乱的真实世界做过重大简化处理后所得到的一个模型。”⑩其次,表现在从最优决策到满意决策。决策是一种人的行为过程,人的行为存在动机和结果两个方面,动机与结果的差距总是存在的。满意准则和最优准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当决策者按照最优准则决策时,更倾向于决策过程中的意志或动机方面,体现了一种寻求最优的努力。最优的不可能性和满意的不确定性使决策者在两者之间难以取舍,所以詹姆斯·马奇(James G.March)认为在决策过程中存在“模糊性”,再充足的决策信息也无法解决不确定性的问题。决策的动态过程和注意力分配的模糊性使决策很难达到结果的最优化。因此,科学的决策只能是满意和最优的辩证统一,用满意准则对决策过程和结果进行衡量和控制,全面考量决策过程中动机与结果两方面的因素,才能促进决策过程的优化。
二、新制度主义决策优化理论存在的缺陷
尽管新制度主义对行为主义和旧制度主义的理论缺陷进行了很好的修正,但其自身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瑕疵。新制度主义决策理论认为大多数时候自利的个体会聚集在一起,人们更愿意合作。正如温格斯特(Weingast)所主张的,合作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信任是内生而不是外加的,信任取决于制度的供给,这种制度要避免某些集团能够控制整个国家为其私利服务。有学者指出,作为决策者的专家或精英群体能够运用所获得的知识和信息指导社会朝着事先确定的方向发展,决策的执行和协调都依赖于层级制的官僚机构,这些机构控制着大量的信息、人力等资源。然而,由于信息负荷超载,沟通失灵,官僚主义,以及在解析和处理与决策相关的各种因素方面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这种指挥体系企望成为稳操胜算的决策机制的可能性(11)。所以,新制度主义的各个学派拒绝承认利益聚合的可能性,但赞成政治决策不能建立在个人偏好的聚合上。新制度主义没有讨论偏好聚合的方向和内涵,更没有提出促进制度结果公正性的途径,也没有就公意的内容做深入的阐述;新制度主义集中于说明偏好和决策怎样成为制度的产物,而制度规则和程序通过各种方式会扭曲偏好和决策。但是,如果被扭曲了,那么“真正的”偏好是什么,新制度主义各流派都没有很好的回答。新制度主义责备行为主义者接受表面的偏好表达和政治中的利益聚合,试图通过正式程序来寻求真实的公正。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gueville)对地方政治制度和参与的兴趣就是新制度主义强调规范的例证。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所谓的“无知之幕”、哈贝马斯(Habermas)的“理想话语环境”,以及洛伊(Loy)的“司法民主”都是很好的例证,虽然其具体建议大不相同(12)。对现存程序及其扭曲的分析,为新制度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范式。但新制度主义没有提出可操作的运用于评估政治选择及其结果的规范理论。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Buchanan)和塔洛克(Gordon Tullock)将全体一致视为决策必须遵循的原则,成为促使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制度设置。但是,对效用最大化的依赖似乎又回归了行为主义的观点,而新制度主义开始时就曾对此提出了批评。
新制度主义认为决策处于核心位置,理性决策方式所要求的那种理性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新制度主义建立在以“心理人”和“经济人”相结合的“行政人”基础上。“行政人”不仅拥有个人的目标和理性,同时把个人放在组织中考虑,认为个人利益是和组织利益集合在一起的。但是“行政人”在决策时很少能看到所有的选择,也不能完全预料其后果,他宁愿“满意”,而不去追求“最佳”(13)。但新制度主义的“满意”决策理论存在严重缺陷:首先,“满意”是一个纯主观的概念,不同的人对“满意”有不同的感知或不同的衡量标准,同时对“满意”的认识也是会经常变化的。因此,“满意”是一个难以测量的、不稳定的变量,满意准则只是用一个难以确定的满意值去否定另一个不可能确定的最优值。其次,新制度主义决策理论侧重于从决策的最后结果来分析古典决策论的局限性,而不是从整个决策过程、特别是决策的执行过程来分析。从最终结果来衡量决策,“最优”往往很难达到。众所周知,人的行为存在动机与结果两个方面,而且动机与结果在实践中常常存在较大的差距。结果上的“最优”不能达到时,动机上的“最优”却是十分必要的,诚如射击手总要瞄准“靶”的正中心位置一样,以便能射到理想的范围内,尽管最终结果不一定是十环。所以,动机与结果总是存在差距,但不能因此而事先将差距肯定下来,然后去实现这个差距。因此,新制度主义宁愿“满意”而不求“最佳”的原则不可避免地存在瑕疵。
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认为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做权威的分配,公共决策就是通过价值分配来调整利益结构。在工具理性成为理性主宰的前提下,对公共决策目标的价值审视似乎变成多余的了,工具理性至上论导致“把现实同一切内在的目的分割开来”(14),工具理性的越位导致人的价值和内在责任感的缺失。所以,在进行决策时不能忽视工具理性片面发展的危害,同时要重视价值理性的作用,做到两者的合理取舍。正像哈贝马斯所指出的:我们务必小心翼翼,切莫将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然后再翱翔于非理性主义的天空中(15)。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中把握公共决策主体的责任,把客观制度性责任同主观伦理性责任统一起来。只有当外在的客观制度性责任内在化了,内在的主观伦理性责任外在化了,公共决策的规范作用才会充分彰显。新制度主义的主要流派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 Edward Lindblom)所倡导的渐进主义模式在决策实践中具有重要的工具理性价值。但是,其理论模式也存在“缺乏进取精神和反对创新”之嫌。正如德罗(Y.Dror)所指出,林德布洛姆的渐进主义模式只有在具备一些必要的条件时才能有效:①现行政策的执行结果是基本满意的;②所面临问题的性质相对稳定;③解决问题所需的资源能够持续获得。反之,在如下情况下渐进主义是不适宜的:①现行政策已经明显的不能令人满意,因而仅仅作出调整是没有意义的;②需要政府作出回应的问题变化太快或太大,基于过去经验的政策已不足以指导将来的行动;③解决问题所需的资源在不断扩展,因而存在某些有重要意义的新机会,但是这些情况很有可能为渐进主义的决策方式所忽略(16)。与此同时,渐进主义模式也存在决策评估标准不合理和过于强调当前利益等缺点。诚如拜瑞(D.Berry)所强调,如果对于决策的评价不是依据客观的标准,而是仅仅考虑它在某种特定情况下的可接受性,那么这样的决策有可能倾向于迎合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样的决策模式的应用性也会非常狭窄。另外,由于渐进主义模式过于强调满足当前所需而不是将来的利益,这种“小变化”对将来的影响可能会比现在所能知道的更多(17)。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无疑认识到了制度的重要性,但是制度和个人偏好是什么样的关系,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那里,核心概念依然是先天性个人偏好的行为假设、政治过程中的集体行动困境,用策略性行为即利益计算来解释制度对行为的影响(18)。那么个人偏好到底是如何形成的,理性选择制度学派将其在理论上“搁置”起来(19)。同时,新制度主义决策理论关于组织趋同、合法性机制和路径依赖机制的阐释,某种程度上缺乏有效的微观理论基础,只强调制度对组织变化方面的影响,但为什么制度会变化,以及什么原因导致了制度本身的变化等问题,并没有做出很好的回答(20)。其次,新制度主义决策理论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无法证伪”的问题,当一项制度效能没能充分有效发挥时,新制度主义往往辩称那是因为该项制度还不够完善,或者说任何制度都存在某种程度的价值偏离和时滞,这使得像“制度影响个体的行为选择”等理论假设无法有效证伪。所以,与任何理论一样,新制度主义有关决策的理论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弊端和瑕疵。
三、新制度主义决策优化理论的现实适用性
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功能、有限理性、制度变迁等理论和分析方法虽然存在种种缺陷,但它对于决策优化的影响分析还是比较独到的,对于现实中国制度转型的理论研究和政策设计,对于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建设,对于建立现代决策制度、优化决策方式,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和借鉴意义。
我国正处在改革和发展的战略关键期,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政治领域中公共决策偏离公共利益有失公平性、决策成本远远超过决策收益造成决策的低效率、决策监督滞后削弱决策的有效性等决策失效问题依然突出,这些问题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同时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时期,对公共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高科学决策能力,是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关键因素,通过优化决策可以提高政府决策能力,减少公共决策失效。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公共政策决策方式的优化日益迫切,同时也为决策优化提供了现实条件。首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促进了公民民主意识的提升,为公共政策决策优化提供了政治基础。政治过程的民主化使公民参与成为可能,公民越来越不满足于仅仅作为公共政策的客体而存在,而是强烈地要求向公共政策决策系统表达自己的意愿,参与到公共政策决策、执行和反馈的全过程。其次,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利益的分化和多元化,推动了公共政策决策的优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利益结构的多元化,促进了公民利益意识和自主意识的形成。因此,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成熟,公民和利益团体为了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必然要了解和参与同自身利益关系密切的政策、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政府决策必须充分关注这些利益诉求。我国传统的“部门行政”形成了众多的部门利益,在调整众多利益群体的多元利益时政府已经显得捉襟见肘。因此,需要根据我国的国情实际,同时借鉴西方国家公共政策决策的先进理念和方法,优化我国目前的公共政策决策方式。
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因素,中国的决策思维一直存在很强的激进主义色彩,这样的思维方式导致各种激进政策的产生。所以,需要倡导理性主义的决策方式,以便减少和克服激进主义决策思维的影响。新制度主义从现实的人出发,认识到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并注重从成本收益分析角度约束人们的行为和确保合理的行为预期。鉴于中国的决策现状,倡导理性主义的决策理念有利于削弱和清除主观臆断、长官意志和其它非理性因素对决策过程的影响,有利于摒弃传统政治与行政只看结果不计成本的观念对决策过程的影响。
同时,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治化需要有制度作保障。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深刻教训说明“过去我们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21)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也证明,在优化决策方式上,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但是目前在公共事务上决策拍脑袋、执行拍胸脯、问责拍屁股的“三拍”现象依然存在。加强制度的系统性建设,发挥制度因素在现实决策中的关键作用,仍然任重道远。依据现代科学决策原则,适应现代决策需要,应以决策组织制度、“智囊”辅助决策制度、决策程序制度、决策评估与责任制度等为重点,加强现代科学决策的制度化建设。
新制度主义构建出渐进主义决策的新路径,尽管渐进主义的路径不尽完美,但由于它所具有的种种可以被认同的优点,已经成为决策理论的重要范式。林德布洛姆倡导的渐进主义决策理论试图求得决策投入的最小化,减少因政策变更较快而带来的矛盾和冲突,使得连续性的政策更易于被民众认可和接受,以及减少决策失误等等。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所倡导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就是渐进主义的决策实践。“过河”是积贫积弱的中国摆脱困境的目标追求,但是,由于河床的地势不明,水流的状况不定,具体路径走向是不确定的,只能一步一步摸着走,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通过不断探索和修正方向,“过河”的总目标最终得以实现。所以,“摸着石头过河”是当时中国正确而且是必然的决策选择。新制度主义认为,当决策者面对决策信息和资源不足,所面临的未知因素较多,而又必须摆脱所面临的困境,渐进决策方式是适宜的、明智的。同时,渐进主义决策方式使得决策参与者在决策过程中相互协调,求同存异,向各方有可能认同的决策目标接近,有利于当今中国在决策实践中消除长期以来存在着的如长官意志、急躁冒进、以激情代替理性等决策弊病。
决策是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和分配,其最大问题就是因为共同所有,人们往往只关注与自己有关的部分,而忽视公共的部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以公共池塘资源为例,讨论了哈丁(Harding)的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博弈,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Lord Olson)的集体行动逻辑的三个模型,“这三个模型都预言,使用公共池塘资源的人都不会为争取集体的利益而合作,并认为人们会陷在传统的环境中无法改变影响他们动机的规则。”(22)为了避免这种窘境,以往学者们认为要么是彻底私有化,依靠市场无形之手去解决;要么是依靠中央集权,由政府来解决。可是,这两条路有时都荆棘丛生。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了第三条道路,她认为公共资源的使用者可以通过自筹资金来制定并实施有效使用公共资源的合约,使公共资源得到有效管理。就我国目前的所有制现状来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资源配置中所占比重较高,因此存在大量的公共资源。如何控制与使用好这些公共资源,仍存在不少困扰着我们的问题。新制度主义关于自主组织和自主管理的第三条路径,以及实现自主治理的决策原则,存在许多可资借鉴和适用之处。可以按照公共资源使用权的边界清晰、规则适当、集体决策、分层治理等原则,进一步发展和改造公民社会组织,改善社区服务体系,形成自主组织自主治理的决策方式,可以避免简单的政府管制和私有化倾向,真正的管好用好公共资源,成为决策优化探索的新路径。
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North)认为国家具有双重目标,一方面通过向不同的利益集团提供不同的产权,以获取收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国家还试图降低交易费用以推动社会产出的最大化。国家的这两个目标经常是冲突的,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又是经济衰退的根源,也就是说“没有国家办不成事,有了国家又有很多麻烦。”(23)针对国家的双重特性,曼瑟尔·奥尔森提出了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模式,即一个政府既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同时它又受到约束而无法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这样的政府与市场是一体的,政府权力与市场繁荣共生。“强化市场型政府”能够明确界定产权和保护契约的公正执行,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之道(2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对市场具有强势主导地位,许多重大决策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也有一些决策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许多决策维护和完善了市场规则,促进了市场繁荣,但也在一些方面使政府成为掠夺性开发主体。构建强化市场型政府的决策方式,有利于适应经济社会转型的需要,成功应对目前面临的严重国际金融危机。也有利于各级政府增强法制观念,更加注重依法执政,依法决策;有利于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更加注重保护一切市场主体的合法产权,增加最广大人民的根本福祉。因此,“强化市场型政府”决策优化理论对当下中国的科学发展具有相当的适切性。
注释:
①James G.March,Johan P.Olson,The Newinstitutionalism: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84,Vol.78.
②B.Guy Peters,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London and NewYork:Wellington House,1999,p.19.
③Peter A.Hall,Rosemarcy C.R.Taylor,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Political Studies,(1996),XLIV,pp.936~957.
④魏姝:《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⑤周健:《试论新制度主义对公共政策研究视角的影响》,《重庆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⑥何俊志等:《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第27~2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⑦Ellen M.Immergut,New System Principle Elementary Theory Question Politics & Society,Stoneham; Volume,26,Mar,1998.
⑧曹胜:《新制度主义视野中的制度与行为关系》,《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⑨道格拉斯·C·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第1页,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⑩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管理组织决策过程的研究》,第20~21页,北京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
(11)C.E.Lindblom,Politics and Markets,New York:Basic Books,1977.
(12)埃伦·M·伊梅古特:《新制度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6期。
(13)汪艳、管新华:《西蒙决策理论的优化运用》,《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14)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第24页,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
(15)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地平线》,第7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6)Y.Dror,Muddling Through:"Science" or "Inertia"?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64,(20),pp.153~157.
(17)D.Berry,The Transfer of Planning Theory to Health Planning Practice,Policy Science,1974,(7),pp.343~361.
(18)彼得·豪尔、罗斯玛丽·泰勒:《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年第5期。
(19)凯瑟琳·丝莲、斯文·史泰默:《比较政治学中的历史制度学派》,《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年第5期。
(20)B.Guy Peters,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London and New York:Wellington House,1999.
(2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2)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第273页,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23)《诺思在北京京城大厦的演讲》,《经济学消息报》,1995年4月8日。
(24)奥尔森:《权力与繁荣》,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标签:新制度主义理论论文; 行为主义理论论文; 决策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决策能力论文; 公共政策过程论文; 动机理论论文; 政治论文; 时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