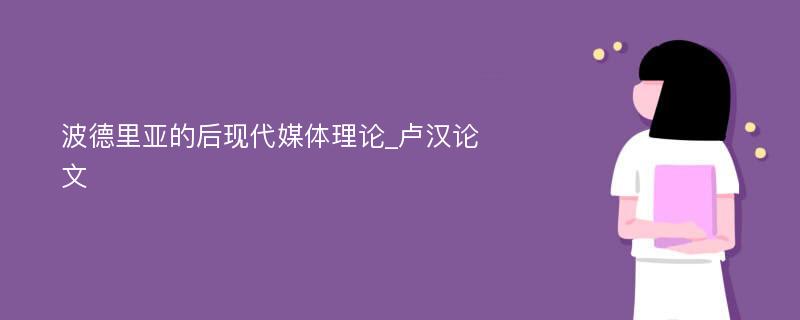
博德里亚的后现代媒介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论文,媒介论文,里亚论文,理论论文,博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917(2007)06-0180-05
根据道格拉斯·凯尔纳的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被叫做后现代的年代,让·博德里亚在某些特定的圈子里,作为最权威的媒介和社会理论家,一直被推崇为新的麦克卢汉。博德里亚的后现代社会理论其实就是一种基于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或者说是根据消费、媒介、信息技术的发展,重新思考现代生活的激进的社会政治理论。博德里亚早期关注消费社会的建构及其如何提供一个新的价值、意义和活动的世界,并由此扎根于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对政治经济学和消费社会的反思几乎完全从他的文本中消失了,他开始转向对由媒介和信息、仿真(simulations)和幻象(simulacra)、内爆和超现实所构成的后现代世界的关注。
在博德里亚的理论建构中,媒介在构成后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是他最受争议的观点之一。1967年,博德里亚写了一篇关于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名著《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的评论,对麦克卢汉进行了批判。他认为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信息”(the Media is the Message)是“技术社会中异化的一个恰如其分的表达形式”,他批评麦克卢汉使这种异化自然化了。这时的博德里亚与新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都认为麦克卢汉是一个技术还原论者和技术决定论者。然而,在70、80年代,麦克卢汉的公式最终成了博德里亚思想的逻辑基础[1]。博德里亚在《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972)中发表了《媒介的挽歌》(Requiem for the Media),开始发展他的媒介理论。博德里亚的《媒介的挽歌》并不是为“媒介”写挽歌,而是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写挽歌。在《媒介的挽歌》中,博德里亚抨击了马克思的经济还原论或“生产力论”,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几乎将生产力定义为一个被授予特权的领域,其中语言、符号和交流(Communication)都被排除在外了。他借用麦克卢汉的话宣称,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有生之年随着电报业的出现已经过时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在《生产之镜》(The Mirror of Production)(1973)中达到顶点,并最终与马克思主义决裂。在博德里亚看来,媒介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是完成了以生产为特征的现代文化到以仿真为特征的后现代文化的转向。他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由工业资产阶级控制的生产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是“外爆”(explosion),表现为商品生产、科学技术、国家疆界、资本等不断向外扩张以及社会领域、话语和价值的不断分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一文就从生产力的变革和扩大、新的交通与通信方式的出现以及整个世界的殖民化等方面描绘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外爆过程。而后现代则是一个由模型、符号和控制论所支配的仿真时代,这是一个以“去分化”为特征的时代,各种意识形态之间(如政治与娱乐之间)、各种文化形式之间(如俗文化和雅文化之间)以及媒体的符号制造术与真实本身之间(如真实与超真实之间)的界限均已消失[2]。
仿真(simulations)是博德里亚媒介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博德里亚用这个概念来描述先进的电子媒介(电视、互联网等)是如何为大众建造一个虚拟的世界、创造一种“幻象文化”的。仿真是没有原作、没有客体指涉的拷贝,或者说是对原作的嘲弄与戏仿。杰姆迅曾用“拼贴”一词描述这种仿真现象,认为拼贴就是一种模拟方式、一种中性的戏仿,拼贴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特征。博德里亚认为,仿真产生了一种普遍的“超现实”(hyperreality)幻象。“超现实”是指许多无源无本的幻象构成的新的现实秩序,顾名思义,就是指现实与非现实的区别已经模糊不清,非现实超越了现实,或者说比现实还要现实。这样,现实不再是自然的自在之物,而成了由电子符码模拟出来的幻境,自然意义上的现实在超现实中沉默了,人们以前对“现实”的那种体验以及现实的基础也都消失了。比如,影视中演员的形象往往被认为是现实中的真实形象,成功扮演过威尔比医生的演员罗伯特就曾收到了上千封求医问药的信;成功扮演过律师的某位演员也曾收到数千封寻求法律咨询的信函;那些在肥皂剧中扮演恶女霸男的演员则只有在保镖的护卫下方敢在大庭广众中露面,否则就可能招致愤怒的影迷们的攻击,这就是大众传媒所制造的超现实效应。
超现实作为仿真文化的一种结果或一种状态,其形成过程也就是真实与非真实的内爆过程。“内爆”(implosion)概念主要是麦克卢汉相对于信息的“外爆”提出来的。博德里亚借用这一概念描绘了一种导致各种界限崩溃的社会“熵”增加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以激进的类像制作和幻象增殖为特征的,包括意义内爆在媒介之中、媒介与社会内爆在大众之中、现实内爆在幻象之中等。在这里,辩证法已经失效,传统哲学和社会理论所主张的每一种二元对立之间所有的边界、范围和差别都已消失。这样一种内爆状态,在博德里亚看来,就是由高科技传媒手段所主宰的后现代社会状态。
伴随着符号和幻象在社会和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的迅速增殖,广播、电视、网络媒介已成为后现代社会的构成要素。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为止,博德里亚将媒介理解为主要的模拟机器。这台机器产生出大量的形象、符号、代码,而正是这些符号、代码构成了现实的独立领域并最终在取消现实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3]。博德里亚对模拟幻象和超现实的分析构成了他的社会理论和媒介批评的重要内容,在一个可以用符号和代码模拟现实生活的仿真时代,“模拟”这一范畴为激进的社会批判提供了一个重要工具,而“超真实”这一概念也是对媒介信息社会进行社会分析的一个极其有用的工具。
博德里亚的媒介理论实际上倒置了表征与现实的关系。以前,人们相信媒介(语言)是再现和反映现实的,而现在,媒介正在构成现实,形成一种新的媒介现实——比现实更现实的“超现实”(hyperreality),其中现实已经从属于表征并最终在表征中消失。媒介现实所展现的是一个平面的景观世界,没有深度,没有意义,因为深度和意义已在媒介对现实的取代中被削平和消解。这正如博德里亚在《媒介意义的内爆》(The Implosion of Meaning in the Media)中所说的,媒介中符号和信息的增殖通过抵消和分解所有的内容消除了意义——这是一个引向意义的瓦解以及媒介与现实之间差别消除的过程。在一个媒介社会中,信息使意义瓦解为无意义的“噪音”、没有内容或意义的纯粹景观。因此,博德里亚认为:信息对意义和内容具有直接的破坏性,意义的丧失直接关联于信息、传媒、大众媒介的崛起,信息吞噬了它自己的内容,吞噬了交流和社会……信息把意义和社会融为一种模糊不清的状态,其中真相已经难以辨认[4]。博德里亚宣称,媒介与“现实”已经内爆,这种内爆导致不可能区分媒介表征及其所表征的现实。博德里亚把媒介看作一个符号和信息的黑洞,认为媒介将所有的内容吸入控制论的“噪音”。在所有的内容都“内爆”为形式的过程中,“噪音”不再传达有意义的信息。
同时,博德里亚还认为媒介通过生产成批的观众以及大众化的思想和经验加剧了媒介效应大众化。也就是说,媒介迎合大众批量生产出符合他们的口味的产品,他们对奇观和娱乐的兴趣以及他们的幻想和生活方式势必又导致大众意识和媒介幻觉效应的内爆。博德里亚指出,大众只想要奇观、消遣、娱乐和逃避,既不能也不愿生产意义。他认为,大众吸走了所有媒介内容,抵消甚至对抗意义,并要求获得更多的奇观和娱乐,因而进一步模糊媒介与“现实”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媒介在某种程度上内爆为大众。因此,在博德里亚看来,“媒介即信息”不仅是信息的终结,而且也是媒介的终结。从此,不再有实际意义上的信息和媒介,或者说不再有一种力量,可以用来调解一种现实与另一种现实、现实的一种状态与另一种状态,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根据博德里亚的观点,“内爆”的含义就是:“一极并入另外一极,每一个不同意义体系的两极短路,明显的对立与界限消失,因而媒介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也消失了,这使任何两者之间或从一方到另一方的辩证的调解都成为不可能,而产生了所有媒介影响的环形性。因此,从一极导向另一极的单向意义上说,意义和真理也成为不可能。”[5]
在《论诱惑》(Seduction)中,博德里亚利用麦克卢汉对“热”和“凉”媒介所做的区分来描述媒介吞噬信息和消除意义的情况。博德里亚认为,媒介是把“热”的事件如体育、战争、政治骚乱、大灾难等,转变为“凉”的媒介事件,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媒介事件和经验。尽管一次亲身经历的体育活动和一次电视播放的体育节目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经验中的现实,一个是经摄像镜头调整过的(闪回、重放、特写)视觉幻象,然而,媒介与现实的内爆却使观众对此难以进行区分。对博德里亚而言,所有的信息和交流的媒介都失去意义并使观众处于一种单调的、一维的媒介经验中,他将这种经验界定为幻象的被动吸收或意义的抵抗,而不是意义的积极处理或创造。媒介因此与神话、形象、历史、意义或意识形态的建构无关。根据博德里亚的观点,电视是这样一种媒介:“它不传达任何意义,它令人着迷,它只是一个屏幕,或一个可以直接在你的头脑中找到的小型化终端——你就是屏幕,而电视正在看你。电视使所有的神经元晶体管化,并像一盘有魔力的录像带一样播放——一盘录像带而不是一个形象。”[6]
由此可见,博德里亚的媒介理论比麦克卢汉更麦克卢汉。他将电视和大众媒介仅仅看做一种技术形式、一种产生某种技术效果的机器,在这种技术效果中,内容、意义或社会功用都被认为是不相干的或不重要的。我们还可看到,博德里亚像麦克卢汉一样把媒介拟人化(“电视正在看你”),这是一种极端的技术神秘主义。像麦克卢汉一样,博德里亚也使媒介效果全球化,使媒介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和一种新的经验的创造者。所不同的是——这是一种天主教信仰与有点清教主义的新教信仰之间的不同——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可以克服书本文化的抽象理性所产生的异化,这种异化已被一种新的精神与身体、感觉与技术的联觉和协调所取代。而博德里亚则将媒介看做一种精神的偶像来继续新教的隐喻,它诱惑和吸引主体生产一种具体化的媒介意识以及个人化和碎片化的生活方式。因此,麦克卢汉把一种普遍的温和的社会命运归于媒介,而对博德里亚来说,电视和大众媒介的功能就是阻止交流,使个体孤立并离群索居,并诱骗他们进入一个幻象的世界:在那里,区分景观和现实是不可能的;在那里,个体变得喜爱景观胜过“现实”。于是,这一“现实”不仅失去了大众对它的兴趣,同时也失去了它自己在哲学、文学和社会理论中所特有的地位。现实的失落和缺席使传统的表征观念解体了,我们通过语言媒介(文字和音像)所把握的不可能是一个客观世界,而是一个由符码构建的虚幻存在,所以,任何认识论的哲学思想及再现论、反映论的艺术观念都在后现代的媒介时代遭到了摈弃。
博德里亚的媒介理论瓦解了“现实”或“真实”观念,从而使一个立体的、多维的、有深度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平面的、一维的、浅表的世界。根据博德里亚的观点,媒介传播消弭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内在空间与外在空间的界限,因为它们都被媒介空间所取代了。博德里亚宣称,在后现代媒介图景中,家庭生活或场景,或者说完全私人化的领域都被外在化了,变得可见和透明了,电视和国际互联网上有数不清的个人生活片段,家庭生活中最隐私的东西实际上成了令公众狂喜的奇观。反之,整个世界又在个人家庭的电视或电脑屏幕上任意展开,消费社会的奇观和公众领域的紧张刺激的事件也正在被媒介事件所取代。媒介事件利用屏幕取代了公众生活和场景,而屏幕正在向我们同步地、毫无顾忌、毫不犹豫地展示每一件事,一切都在信息和传播的刺目的光线下变成透明的和清晰可见的。这是一个没有秘密、没有深度的、公开的、浅表的平面世界,用博德里亚的话说,就是一个没有“藏匿的、抑制的、禁止的或朦胧的诲淫”[7] 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个内在性、主体性、隐私、具有深层意义的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充满诱惑、眩晕、同步、透明和过分暴露的时代开始了——这就是后现代世界!
在博德里亚看来,媒介的技术决定了媒介的效果(如单向传输、类制作、内爆、超真实、意义的消除),而不是任何特定的内容或信息,或它在特定社会系统中的建构和作用对媒介效果起决定作用。博德里亚认为,媒介技术是媒介实践和效果的创造者,媒介技术与特定的经济和政治势力、个人或群体对它们的使用以及它们作用于其中的社会系统相分离。博德里亚的媒介理论由于否认媒介是意义的生产者,否认媒介内容或媒介语境的重要性,只强调媒介技术形式和效果,因而被道格拉斯·凯尔纳称作一种形式主义。凯尔纳认为,博德里亚的理论消除了政治经济学、媒介生产和媒介环境,实际上就是消除了社会和历史的意义维度。在凯尔纳看来,媒介分析应当试图将媒介形象语境化,而不是仅仅关注媒介形式的表面;媒介分析应该抓住媒介传播中形式和内容的辩证关系,领会媒介形式如何构成内容以及内容是如何形式化和结构化的,尽管媒介形式本身就可能是意识形态的。然而,效果和用途、形式和内容、媒介与现实之间的区别,在博德里亚一维的媒介理论中都消失了,博德里亚用从语境中抽象出来的媒介形式和效果(幻象与超真实)取代了深层的意义分析与阐释,这种形式主义破坏了思想批判的计划。凯尔纳说:“在博德里亚的媒介理论中,没有一种真正的关于文化阐释的理论或实践。他的理论还产生了一种反阐释学的倾向,否定了内容的重要性并反对阐释。”[8]
然而,对博德里亚来说,反对阐释并非一个倾向性的问题,而是后现代的文化特征,或者说是一种不同于现代性的时代特征。在《论虚无主义》(On Nihilism)一文中,博得里亚把现代性描述为“表象的彻底解构、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以及对阐释和历史暴力的听任。”博得里亚认为现代性是指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的时代,一个过度依赖阐释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要么是将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诠释为经济的副现象;要么就是将任何事物都用欲望和无意识来解释。这些‘怀疑的解释学’采用深度模式来解除现实的神秘性,揭示隐藏在表象之下的实体以及构成事实的各种力量。”[9]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的革命是一场意义的革命,它以历史辩证法的完全停泊点——经济和欲望——为基础,试图对各种历史文化和生活现象进行阐释,以期找到现象背后的潜在本质。博德里亚对这个本质主义或基础主义式的现代世界嗤之以鼻,声称他赞成另一场革命,一场旨在消解意义和削平深度的后现代革命。相对于先前现代性对表象的解构,这场革命乃是对意义的广泛解构。“凡生于意义者必将死于意义。”对博德里亚来说,后现代世界里不存在意义,它是一个虚无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理论漂浮在虚无之中,没有任何可供停泊的安全港湾,没有意义所需要的深度——一个隐藏的维度、一个看不见的底层、一个稳固的基础——一切都是“赤裸裸的”、可见的、外显的、透明的,并且总处于变动之中。所以,后现代世界展现的是不具有指涉对象和终极目标的单纯的能指符号和各种变换形式的类像,它是一个无需阐释或拒斥阐释的表象世界。在一篇题为《残迹的游戏》(1984)的访谈录中,博德里亚再次明确采用激进的后现代话语,并再次指出其先前社会理论中的核心内容已经消失。他不无悲观地声称,后现代世界已经解构了它所有的一切,剩下的全部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东西,人们所能做的只是玩弄这些碎片。“玩弄碎片,这就是后现代。”[10] 尽管博德里亚对传统这个并非技术力量支配的社会流露出一种怀旧情愫,但他也不能否认:意义的阙如、反对阐释就是由高度发达的传媒技术所支配的后现代社会的文化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