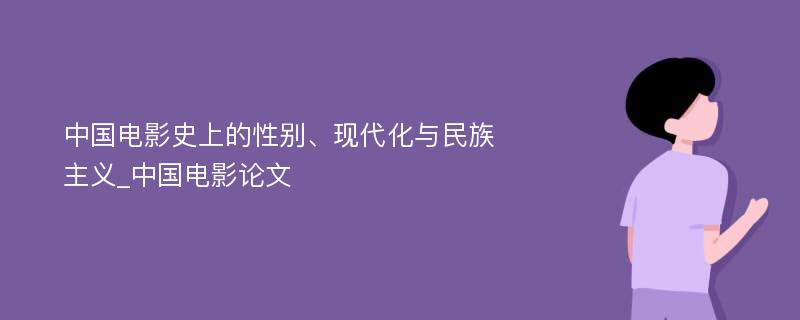
中国电影史中的社会性别、现代性、国家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主义论文,现代性论文,中国电影论文,性别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
中国电影中国家主义的建构从一开始便与社会性别构成有密切的联系。在中国电影中,是否涉及“妇女问题”或为观众创造明星形象这些性别问题居于首要位置。不是以男性为中心视角而是以自觉的、性别化的女性主义观点重新审视中国电影乃是我们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视角问题变得既重要而又困难,因为它必须同时是一个“跨文化”的视角。实际上任何涉及一种以上文化的视角所作的调查或以一种文化的视角去观察另一种文化所作的调查都必须意识到它自身所面临的种种风险、潜力与挑战。一个西方学者或受过西方训练的学者对非西方文本的研究总会导致某种形式的文化帝国主义或新殖民主义吗?
正如卡普兰(E.Ann Kaplan)在《读解的形成与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注:此文和下面提及的拉森等人的论文均为已被收入该论文集中的文章——译者注。)一文中所表明的,一个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在对待非西方文本时所做的第一件事是,至少要自觉意识到电影对她所造成的感情上的冲击以及她的主体性。在西方学术界受过训练的西方白人女性以特定的方式运用女性主义理论、精神分析、文化研究,对于她们的主体构成(subject—formation)机制的研究业已获得丰硕成果。在充分意识到它的局限性时,一个女性主义者在阅读中国电影文本时可能会运用各种不同的视角和框架,揭示本文化(originating culture )批评家未能意识到的多种意义,为了验证她的假设,卡普兰以她的已经性别化了的、白人女性主义的视角阅读中国电影文本《霸王别姬》。她没有关注跨文化的分析,而是重新以一种现实主义的角度去“做好自己的工作”。
自从中国早期电影以来,通过性别化了的话语将中国的历史与国家主义性别化是一种频频使用的方法。1949年以前的进步的左翼电影传统中,拍摄的许多影片都是为了表现中国妇女的困境。实际上中国电影中“现代女性”的主题已经与现代性、国民的精神健康、反帝国主义等许多重要问题相联系。受到左翼电影制片人渗透与影响的影片公司,如明星公司(20—30年代)、联华公司(30年代)、昆仑公司(40年代末)拍摄了一系列关于妇女问题的、片名具有争议的电影,包括《三个摩登女性》、《女神》、《现代一女性》、《新女性》、《丽人行》。女性地位经常是国家的一种转义素、一种民族讽喻。正如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所反映的,女性被描绘成封建压迫的受害者。在一个泯灭人性的社会中,女性的身心受到苦难与虐待的折磨。哈里斯(Kristine Harris)的文章《〈新女性〉事件:1935年上海的电影诽谤与奇观》研究了30年代默片中所表现的女性形象。与卡普兰的拉康取向的精神分析不同,哈里斯以女性主义的方法集中研究这一时期中国电影中女性、明星、观众的社会史。电影界的头号女演员阮玲玉,别名“中国的嘉宝”,在度过整二十五个年头后自杀了。她的故事成为一个传奇。她所饰演的电影角色以及她自身的生活经历都已成为中国现代女性的象征。1991年关锦鹏执导的香港影片《阮玲玉》展示了阮玲玉故事的永久魅力。似乎在这一类电影中,在可以被看作为中国女性主义话语的目标与超越性别特殊性的某种统摄一切的、宏大的、国家的、集体斗争的语言两者之间有着一种含混(ambiguity)和令人不安的张力。
1949年以后,为促进社会主义的国家建构,性别政治仍是常见而重要的问题。这里应强调的是,性别话语经常被简化并纳入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这样的宏大话语。女性象征压迫(如童养媳、纳妾、奴隶制这些形式)的受害者,而男性则代表革命变化的能动作用(agency)(通过一系列熟悉的象征物与人物:男政委、武装斗争、枪、党、太阳)。阶级意识掩盖了性别身份。女性刚从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以及帝国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随后又被整合到一个新的社会秩序,一种“社会主义父权制”中。在许多情况下,妇女的解放伴随而来的是一个消除性别(gender erasure)的过程(例如经常看到的中国妇女穿着单性的unisex毛式制服)。尽管革命的男女主人公被刻划成充满了新近被赋予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但是性特质(sexuality )本身实际上已被降到最低程度,甚至被略去了。
在《白毛女》(1950年)和《红色娘子军》(1961年)这两部革命的经典电影以及随后改编而成的芭蕾舞剧中,这些新的、革命的性别构成通过屏幕以及舞台上精心设计的芭蕾舞得到最为生动的展现。文革中这两部电影都被改编成“革命现代芭蕾舞剧”。(无须说,这两部芭蕾舞剧的生命力及其声誉都来自它们的电影版本,这些电影在全国各地放映以进行革命教育。)女主角喜儿和吴琼花是残酷的封建压迫的受害者,而男主角大春和洪常青则代表党、红军的革命性变化的能动体(agent)。男人把女人从奴役状态下解放出来并引导她们走向革命 (注: 1996年8月我在北京展览馆剧场观看了上海芭蕾舞团新排演的《白毛女》。北京展览馆剧院是一个具有苏式风格的建筑设计典型,就象中国的芭蕾舞本身一样其历史可以追溯到50年代。在舞蹈动作设计方面,新剧与旧的文革时的版本相比有许多变化。在喜儿与大春重逢这一场中,二人的双人舞的新的舞蹈动作设计使二人的关系更为亲密。而在以往的芭蕾舞剧中为了把个人的性欲动力降到最低限度并且突出革命的献身精神,原型故事中的浪漫情节基本上都被删去——原注。)。实际上影片《红色娘子军》的导演谢晋也把当时受欢迎的“白毛女”的传奇故事编导进另一个著名影片《舞台姐妹》(1964~1965年)的故事情节中。影片的女主人公春花起初是一个旧社会里受虐待、受压迫的绍兴戏演员,通过表演革命节目(鲁迅的小说《祝福》), 自身得到改造、 解放并被赋予权力(enpowered),在电影快结束时, 她在新改编的绍兴戏里扮演的喜儿赢得了女性观众的眼泪与认同(中国戏剧中一个富有特色的非布莱希特〔non-Brechtian 〕的时刻)(注: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989—1956),德国剧作家、戏剧理论家——译者注。)。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中,春花让她的舞台姐妹月红和她一起“把一生奉献给演唱革命戏剧”。在毛泽东时期以及后毛泽东时期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在许多中国电影中,“戏中戏”的闹剧成为新性别构成与社会变迁恰当的隐喻。(例如女导演黄蜀芹执导的《人·鬼·情》[1988]年与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中的“舞台兄弟”的故事。)
在中国新电影中,社会性别差异的重新发现与个性的重新发现是同步的,历史与国家主义的再性别化(regendering )涉及到有关男性气质、女性气质、性特质以及缺乏这些特征的多重评论。在这一部分的其余文章中,崔淑琴(音译)的《性别化了的透视:〈菊豆〉中主体与性特质的建构与表达》、拉森(Wendy Larson)的《妾与历史的形貌:陈凯歌的〈霸王别姬〉》、郑毅(音译)的《历史激情的叙述形象:那些“它者”妇女——论中国电影新浪潮中的它者性(alterity)》,都论述了这一时期中国电影中的性别政治。通过对电影《菊豆》的电影惯例(旁白、景点、叙述结构)的琐细检查,崔淑琴探索了张艺谋影片中性别建构的一些特点。我们目击了这样一种场面,那是一个无意识的男性在渴望寻找与重新维护已丢失的主体性和被阉割的性特质。女主角菊豆则体现为显而易见的女性性特质、一种男性愿望的能指、一个惩罚的承受者。不论菊豆是如何被有力地安置在引人注目的位置上,她既不是主体也不是变革的能动体,而仍旧是一种中国男人在受压制的社会体系中遭受心灵创伤的证明。看上去这些评论反映了后毛泽东时期电影的许多真实情况。拉森的分析认为,陈凯歌的电影经常是宏大的、男性的、自恋的叙述,其中女性只是扮演边缘的角色。在历史性的史诗片《霸王别姬》中,尽管有巩俐扮演的菊仙在场(prensence), 但却是通过几个男性的个人经历来勾画半个世纪的近代中国历史的概貌。历史的中心角色是由男人而不是女人扮演的。郑毅的文章主题是把中国性别化为“女性的”以及西方电影与中国新电影的想象中的“他者”。电影中经常表现的女性的自我重塑问题也是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受到关注的中国的再塑问题。中国电影表现中的女性是现代中华民族的转义素。崔淑琴、拉森、郑毅的女性主义批评都敏锐地指出,新电影的男性电影制片人已经把中国历史与现代性的重负转移到了中国女性的肩头。
一般说来,在毛泽东时代(1949—1976年)电影话语中的社会性别构成明显地表现为男性与女性通过革命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获得权力。在后毛泽东时期(70年代末与80年代),新电影文化批评与社会批评也同样很有必要采用性别术语。功能不良的性特质和“不正常的”性关系(如阳痿、阉割和纳妾)都是对国家的隐匿的讽喻。张艺谋的电影艺术是描绘中国男性处于困境与危机的一个范例。他给观众展示的景象是:阳痿和乱伦(《菊豆》)、纳妾与一夫多妻(《大红灯笼高高挂》)、受伤的阴茎和睾丸(《秋菊打官司》)、男性无力保护妻子儿女(《活着》)、通奸(《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另一部由谢飞执导的广为宣传的影片《香魂女》中,父亲与儿子这方面的阳痿、白痴与残疾是中国农村家庭缺乏情感和性欲得不到满足的原因。这部影片与李安的《喜宴》在1993年柏林国际电影节同获金狮奖(注:把阳萎转变为对中华民族的批评与讽喻的整套思想可以追溯到80年代中期的文学作品,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张贤亮的小说。 见拙著“ When Mimosa Blossoms: The Ideology of the Self in Modem Chinese Literature”[“马缨花开的时候:现代中国文学的自我意识”。]Joumal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28,no.3(1993):1—16.——原注。)。
90年代在跨国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中国男性的阳刚气质得到恢复与再现。香港动作与武术片向全球电影的急剧转变突出了亚洲男性的英雄气概。经过几十年的中断之后,另一名亚洲新星成龙最终填补了李小龙的位置。这些亚洲男主角现在必须与美国电影市场和国际电影市场上诸如史泰龙、施瓦辛格、Jean—Claude Van Damme之类的演员所创造的“本土的”美国男性神话相竞争与抗衡。所以才会有前面提到的周润发到好莱坞时的苦闷与不安。(至于香港动作片中的亚洲功夫女主角,恰恰相反,她们的身手不凡并不是断言独立的亚洲女性主体性的征兆。她们的女性气质似乎只是为了满足男性的视觉享受而虚构出来的,就象那些诸如女斗士之类的美国风靡一时的电影中穿着性感的女性们一样。)
1997年1月, 正当成龙的影片《警察故事之四·简单任务》在全美的影院上映时,另外两部被指责为色情的影片——《人民与拉里·弗林特》和《庇隆夫人》(麦当娜主演)也同时在放映。成龙在剧中扮演一个香港警察/侦探,在一次英勇的跨国冒险行动中着手破获乌克兰走私军火团体的活动。观众们先是在乌克兰寒冷冬季白皑皑的雪景中、继而又在地球另一端温暖如春的澳大利亚的蓝色海面上,欣赏到成龙极具个性的非凡而又惊险刺激的特技表演。我们又一次目睹了他为了正义事业走遍天涯的成功的破案行动,就象他在南斯拉夫(《龙兄虎弟》,1987年)与纽约市/温哥华(《红番区》,1995年)所做的一样。在这部影片中,成龙“吸引观众的肉体”、演技与表演可能胜过了他的美国同行,如在制止偷运核武器这同一主题的吴宇森的影片《断箭》中的 JohnTravolta与Christian Slater。但是成龙的性特质却仍象从前一样陷入矛盾与令人烦恼的状态。有时他被剥得浑身赤裸,晒得黝黑而又肌肉发达的裸体展示在过往的女人们面前,被她们品头论足。在这部影片的陈述中,最具有自我反思性的时刻之一是成龙说他的冒险生涯与詹姆斯·邦德的极为相似,只是没有靓女相伴。他把自己塑造得象一位无性的(asexual)中国/香港的邦德。他的角色永远是一个喜剧性的、 可爱的、乐观而又克尽职守的人,他全力以赴地完成安排给他的任务,尽管总有机会接触异性,但他却对追求异性不感兴趣,并予以躲避。
在90年代的大陆,中国的男性气质的堂而皇之地恢复并增长而且已经出现在国内的具有跨国性别特点的影视业中。姜文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姜武主演的《俄罗斯姑娘在哈尔滨》、《狂吻俄罗斯》、《洋行里的中国小姐》以及《洋妞儿在北京》等,描绘了中外男女之间的交易。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些文本描绘了中国男人依靠他们创造和增值资本与财富的企业家才干赢得了“洋妞”的爱情。 中国国民的力比多经济(libidinal economy)是与国家的政治经济连结在一起的。 藉中国男性气质为媒介的中华民族的恢复如今是通过跨国的力比多动力(libidinal dynamics)来实现的。这样一种跨国的男性想象的投射是复苏中华民族/父权制的一种经过掩饰的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