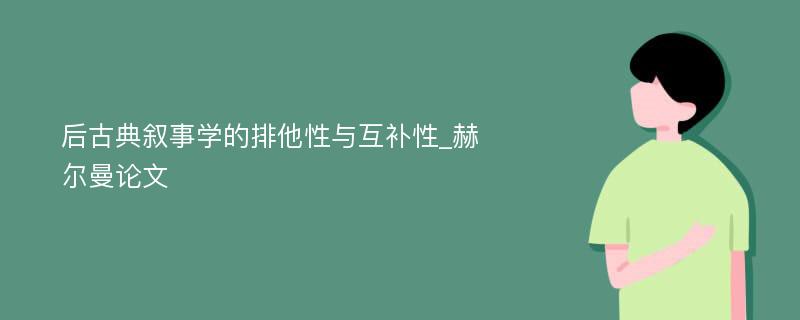
论后经典叙事学的排他性与互补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排他性论文,互补性论文,经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作为复数的后经典叙事学
后经典叙事学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戴维·赫尔曼(David Herman)在1997年发表的一篇题为《脚本、序列、故事:后经典叙事学的构成要素》(Scripts,Sequences,and Stories:Elements of a 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的文章中。在这篇文章里,赫尔曼从认知科学的角度对叙事序列加以全新审视,特别是借助于认知科学的“认知草案”理论,来阐释叙事序列、故事构建、叙事性等相关问题。赫尔曼认为,诸如女性主义、修辞理论、语言学、计算机科学等各种理论模式和视角均为后经典叙事学增添了活力。但是,他又坦言自己撰写该文的目的是为了整合一些研究叙述话语的认知因素。(Herman 1997:1049)据此,我们不难判断,赫尔曼在该文中所讨论的后经典叙事学实质为认知叙事学。始料未及的是,该文发表后,后经典叙事学这一术语非但没有被学界所普遍接受,反而遭到了部分学者的质疑。布莱恩·里查森(Brian Richardson)曾就“后经典叙事学”一说同赫尔曼展开过激烈的交锋和对话。(Richardson & Herman 288—290)
后经典叙事学这一概念真正为学界所熟知,是在《脚本》一文发表的两年之后。1999年,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赫尔曼主编的《作为复数的叙事学:叙事分析新视野》(Narratologies: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1999)一书。在该书长达三十页的“前言”中,赫尔曼对叙事研究的现状作了全面的回顾和精辟的概括。他认为,在借鉴了女性主义、巴赫金对话理论、解构主义、读者—反应批评、精神分析学、历史主义、修辞学、电影理论、计算机科学、语篇分析以及(心理)语言学等众多方法论和视角之后,单数的叙事学(narratology)已经裂变为复数的叙事学(narratologies),也即是说,结构主义对故事进行的理论化工作已经演化出众多的叙事分析模式。赫尔曼进一步指出,叙事诗学在过去十多年来发生了惊人的嬗变,叙事学已经从经典的结构主义阶段——相对于远离当代文学和语言理论的蓬勃发展的索绪尔阶段——走向后经典阶段。(Herman 1999:1—2)需要指出的是,正是这一转向使得一度消沉的叙事学走出解构思潮的阴影,再度崛起,迅速跃居文学研究的一门显学,更使得西方学界迎来了“叙事最受重视的时期”、“叙事理论最为发达的时期”。(申丹等203)
在该书出版之后,后经典叙事学这一概念,逐渐为叙事学界所普遍接受并被广为沿用。2002年,施劳米什·里蒙—凯南(Shlomith Rimmon- Kenan)在《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Narrative Fiction:Contemporary Poetics)一书的第二版“后记”中,使用了后经典叙事学这一概念,并对当下后经典叙事学的特征用“走向”(towards)一词加以概括,如“作为摇摆不定的走向”(towards as paralyzing oscillation)、“作为相互修订的走向”(towards as mutual modification)、“作为永久变化的走向”(towards as perpetual change)等。(Rimmon- Kenan 134—149)无独有偶,安斯加尔·纽宁(Ansgar Nünning)在《单数的叙事学还是复数的叙事学?对近期发展的评价、批判以及对未来术语使用的建议》(Narratology or Narratologies? Taking Stock of Recent Developments,Critique and Modest Proposals for Future Usages of the Term,2003)一文中,也使用了后经典叙事学这一概念。在这篇论文中,纽宁首先进一步阐释了后经典叙事学的含义,在详细探讨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之间关系的同时,还对后经典叙事学加以归类。(Nünning 2003:23—275)比利时的两位叙事学家吕克·赫尔曼(Luc Herman)与巴特·凡瓦克(Bart Vervaeck),更是将他们合著的《叙事分析手册》(Handbook of Narrative Analysis,2005)一书的一个主体性章节命名为“后经典叙事学”。国内学者申丹也将其新著《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的第三编命名为“后经典叙事理论”,详细探讨了盛行西方学界的数种后经典叙事学。鉴于后经典叙事学在学界的盛行,2005年后经典叙事学一词入选由卢特利奇出版社出版的《叙事理论百科全书》(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2005)的词条,也就不足为怪了。
作为当代叙事理论的主流之一,后经典叙事学力图修正经典叙事学在很多方面的过失,如经典叙事学“对核心文类的武断选择;没有承认对除此之外其他文类研究的意义;将故事视作是自足的产品,而不是由读者在持续修正的阅读过程中建构出来的文本;既排斥了心理力量、心理欲望,也没有考虑那些涵盖和塑造它们的文化、语用及历史语境”等,(Jahn 105)无疑为叙事理论研究增添了许多创新与活力。鉴于后经典叙事学的复数性,以下两点似乎就成为不得不说的论题:1.后经典叙事学的归类与划分。2.后经典叙事学之间的关系。
顾名思义,后经典叙事学,是相对于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而言的,它的复数意义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1)超越经典叙事学的文学叙事,走向文学之外的叙事媒介,即叙事媒介上的复数性。(2)超越单一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范式,走向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即研究方法上的复数性。由此,我们不难得出两种划分后经典叙事学的基准:一种是以叙事媒介为基准,另一种是以研究方法为基准。就叙事媒介而言,既有以玛丽—劳勒·瑞安(Marie- Laure Ryan)为代表的媒介叙事学研究,也有以具体叙事媒介为分析对象的叙事理论,如以艾伦·纳德尔(Alan Nadel)为代表的电影叙事学、以弗雷德·埃弗雷特·莫斯(Fred Everett Maus)为代表的音乐叙事学、以纽宁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叙事学、以彼德·布鲁克斯(Peter Brooks)为代表的法律叙事学,以及以盖瑞特·斯图尔特(Garrett Stewart)为代表的绘画叙事学等。
就研究方法而言,有以苏珊·兰瑟(Susan Lanser)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叙事学、杰拉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叙事学、以马克·柯里(Mark Currie)为代表的后现代叙事学、以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为代表的修辞性叙事学、以劳勒·瑞安为代表的可能世界叙事学,以及以赫尔曼为代表的认知叙事学等。同叙事媒介相比较,似乎以研究方法为基准来划分后经典叙事学的做法更具普遍性。在纽宁看来,考虑到叙事研究的诸多新方法,将叙事学继续视作一个单一的学科似乎是不恰当的。他认为后经典叙事学主要包括新历史主义叙事学、后现代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伦理与修辞性叙事学、认知叙事学、自然叙事学、可然世界叙事学等。(Nünning 2003:249—251)在申丹看来,后经典叙事学主要涵盖了修辞性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认知叙事学、后结构主义叙事学等研究领域。(申丹等203—398)而在《叙事分析手册》一书中,吕克·赫尔曼与巴特·凡瓦克也把四类后经典叙事学纳入讨论范围:后现代叙事学、叙事学与意识形态(包括性别叙事、伦理叙事等)、可能世界叙事学、认知叙事学等。(Herman & Vervaeck 103—175)
但是,不管是以哪一种基准划分出来的后经典叙事学,都没有背离其复数性质。与经典叙事学单一结构主义范式、单一的文学叙事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后经典叙事学不再是一元的理论流派,而是繁杂的“批评画框”(critical passepartout)。莫尼卡·弗鲁得尼克(Monika Fludernik)对此也持有相似观点,她说,“多元的研究方法以及它们同批评理论的携手联姻,催生了数个发展势头正旺的叙事学。”(Fludernik 37)由此又产生了另一个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即后经典叙事学之间的关系。曼弗雷德·雅恩(Manfred Jahn)曾在一篇关于认知叙事学教学问题的文章中指出,融合多门学派、多种研究方法的后经典叙事学也引起了一些相当明显的问题。(Jahn 106)遗憾的是,雅恩没有深入探讨这些所谓的“明显的问题”。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另一位德国叙事学家纽宁弥补了雅恩没有探讨这些问题的缺憾。纽宁认为,这些问题主要涉及“叙事性”与“理论化程度”等两个方面,他说,“第一,尽管所有的新方法都同样与叙事相关,但它们理论的复杂度和理论假设的清晰度大不相同。第二,有些新方法很明显和其他方法地位不等,即:有的方法能真正研究叙事学所要探讨的问题,而有的却不能。”(Nünning 2003:256)
近年来,学界关于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之间关系的探讨颇多。相比之下,对后经典叙事学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似乎就成了叙事学界的一个研究盲点,而这正是本文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实质上,后经典叙事学之间既存在排他性,又存有一定的互补性,通过对排他性的具体分析,可以增强我们对互补性的认识;而对后经典叙事学之间互补关系的认识,可以使我们拥有更为宽阔的批评视野,能对聚焦于不同媒介、不同研究方法的后经典叙事学兼收并蓄,进而推动后经典叙事学的健康发展,并使之在多元共存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二、后经典叙事学的排他性
《叙事分析手册》一书的作者吕克·赫尔曼与巴特·凡瓦克认为,语境和读者或许是当代叙事理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Herman & Vervaeck 8)从该书的“语境”看来,不难判断,赫尔曼与凡瓦克所言的当代叙事理论应该是指后经典叙事学。因此,要探究后经典叙事学的排他性,我们不妨从语境和读者这两个重要概念入手。实际上,只要对后经典叙事学的著述稍作留意,便会发现,在有关语境和读者这两个概念的论述上,不同流派的后经典叙事学家表面上立场相似,但他们所指涉的具体含义却有着本质的不同。
早在30年前,言语行为主义者就指出,“文学作品远非是自立的、自我包含的、自我激励的、不受语境限制的、独立于‘日常话语’的‘语用属性’之外的东西,它产生于一定的语境,同其他话语一样,文学作品不能脱离语境。”(Pratt 115)但是,由于经典叙事学过于追寻“叙事形式”和“普遍叙事语法”,以至于忽略了语境这一叙事研究的重要因素。查特曼认为,这也是语境主义者反对经典叙事学的主要原因之一,(Chatman 309—328)经典叙事学不考虑语境的后果将导致其“缺乏潜在的描述性和解释力。”(Smith 232)
历史文化叙事学兼认知(建构)主义叙事学研究的重要人物纽宁说,“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经典叙事学忽略了对语境、文化历史、阐释的研究”。(Nünning 2004:354)为弥补经典叙事学的上述缺陷,“后经典叙事学倾向于研究那些诸如语境、文化、性别、历史、阐释、阅读过程等研究课题。”(Nünning 2003:245)后经典叙事学对语境的关注和强调,无疑使语境成为后经典叙事学的重要标志之一,以至于很多论者干脆又将后经典叙事学称为“语境叙事学”。(Chatman 1990; Darby 2001; Shen 2005)
同语境相仿,读者也受到后经典叙事学家的重视和研究。申丹教授认为,关注读者是后经典叙事学的特点之一。(申丹等1)同样,唐伟胜也认为,叙事学由经典转向后经典,从研究范式上看来,也表现在叙事意义的阐释从“作者”走向了“读者”。(唐伟胜64—65)毋庸置疑,不同派别的后经典叙事学家都特别关注语境和读者。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就这两个概念的确切所指与内涵而言,各派的后经典叙事学家的观点又存在很大的分歧。我们主要以认知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以及修辞性叙事学为例,来考察后经典叙事学在语境和读者这对概念上所具有的不同理解与分歧。
按照申丹的说法,语境可以分为两大类别:一是“叙事语境”,二是“社会历史语境”。前者涉及的则是超越社会身份的“叙事规约”或“文类规约”;后者主要涉及与种族、性别、阶级等社会身份相关的意识形态关系。而与这两类语境相对应的是,我们也有两种不同的读者。与“叙事语境”相对应的是“文类读者”,而与“社会历史语境”相对应的是“文本主题意义的阐释者。”(申丹等308—309)一般认为,认知叙事学所关注的是“叙事语境”和“文类读者”。与此相对照,其他派别的后经典叙事学,如女性主义叙事学、修辞性叙事等关注的则是“社会历史语境”和“文本主题意义的阐释者”。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叙事学研究出现了醒目的认知转向(cognitive turn)。越来越多的学者将认知科学的相关理论应用于叙事学研究,使得认知叙事学应运而生,并成为后经典叙事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认知叙事学强调人类所共享的心理原型(prototype),从认知框架(frames,schemata)、优先原则(preference rules)、认知草案等理论出发,来探究人类构造叙事、理解叙事的共同模式。基于这些理论的认知叙事学,自然不会考虑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也不考虑处于这一语境下有血有肉的读者。在认知叙事学家看来,“无论读者属于什么性别、阶级、种族、时代,只要同样熟悉某一类的叙事规约,就会具有同样的叙事认知能力(智力低下者除外),就会对文本进行同样的叙事化。”(申丹等 310)
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叙事学还处于发展低谷的时候,西方以兰瑟为代表的叙事学家将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引入叙事学研究,为叙事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讲,后经典叙事学的崛起当以女性主义叙事学为先河。里查森认为,女性主义作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的知性力量,在很多方面都彻底地改变了叙事理论与叙事分析,并取得了累累硕果。(Richardson 168)与认知叙事学不关注历史文化语境和处于这一语境下有血有肉的读者形成对照,女性主义叙事学既强调历史文化语境,也强调性别化的读者,因为“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精髓就是故事如何被讲述、被谁讲述,以及对谁讲述的语境。”(Mazei 1)关于这一点,我们从罗宾·霍尔(Robyn Warhol)给女性主义叙事学所下的定义中也能看得出来。霍尔认为,女性主义叙事学就是“在性别的文化建构语境下,对叙事结构和叙事技巧的研究。”(Warhol 21)也即是说,在女性主义叙事学家看来,性别和文化在叙事文本的建构与阐释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兰瑟曾说,“叙事学对性别的强调是构建语境诗学的一个重要因素,阅读叙事,不可能不考虑叙事起作用的文化规约。”(Lanser 1996:256)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主义叙事学家对性别的强调,既指涉一定性别身份的作者、叙述者,也指涉一定性别身份的读者。在女性主义叙事学家看来,不同性别身份的读者,会对同样的叙事文本作出不同的阐释。在这一点上,女性主义叙事学和修辞性叙事学存在一定的交叉。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修辞性叙事学对读者的划分要比女性主义叙事学更为详尽。
主要发轫于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修辞性叙事学,在20世纪80年代末也异军突起,成为后经典叙事学的一个强劲分支。特别是詹姆斯·费伦的修辞性叙事学“以其综合性、动态性和开放性构成了西方后经典叙事理论的一个亮点。”(申丹等256)就读者而言,费伦在彼得·拉比诺维茨(Peter J.Rabinowitz)所提出的四维度读者观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另一种类型。在费伦看来,叙事学研究的读者可有以下五种类型:1.有血有肉的实际读者。我们每个人既有人类共同具有的特质,也有自己的个性。2.作者的读者,即作者的理想读者。修辞性叙事理论认为,有血有肉的读者为了接受叙事发出的参与要求,会努力地进入作者的读者的位置。3.受述者,即叙述者的叙述对象,可能不具有性格特征。4.叙述读者,即有血有肉的读者在叙事世界中所处的观察位置。5.理想的叙述读者,即叙述者假定的完美读者,可以理解叙述者所传达的一切信息。(Phelan,Scholes & Kellegg 301)而在语境的理解上,不同的后经典修辞性叙事学家之间也产生了分歧,特别是在对语境的重视程度上,有强弱之分。例如,以小说和电影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修辞性叙事学家查特曼认为,在依赖社会语言学及自然语言或“言语行为”哲学的基础上,修辞性叙事学把叙事视为行为,提倡探讨真实作者和真实读者的意图、动机、兴趣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Chatman 314)也即是说,查特曼强调的是真实作者和真实读者所处的特定语境。虽然费伦也强调语境,但是他所说的语境主要是指叙述者在讲述故事时的叙述情境,这一点可从他给叙事所下的定义中判断出来。在《作为修辞的叙事》(Narrative as Rhetoric,1996)一书中,费伦说,叙事是叙述者“出于一个特定的目的在一个特定的场合给一个特定的读者讲的一特定的故事。”(Phelan 1996:4)如果说,查特曼与费伦都只是强调某种特定的语境,是“狭隘的”语境主义者的话,那么另一位修辞性叙事理论家迈克尔·卡恩斯(Michael S.Kearnes)则是一位典型的语境决定论者或泛语境主义者。在《修辞性叙事学》(Rhetorical Narratology)一书的“引言”中,卡恩斯表达了极强的语境主义立场,认为一个文本能否成为叙事的关键在于语境,而不是文本的构成因素。他说,“恰当的语境可以使读者将任何文本都视为叙事文,而任何语言成分无法保证读者这样的接受文本。”(Kearnes 2)可以说,在语境这一问题上,卡恩斯走上了极端,他只单方面的强调语境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了文本的其他成分,因为“一个文本究竟是否构成叙事文取决于文本特征、文类规约、作者意图和读者阐释的交互作用,”(申丹等 257)而不是完全在于语境。
如上所述,虽然各派的后经典叙事学家基本上都强调语境和读者在叙事理论建构、叙事分析中的作用,但在语境和读者的具体含义上,他们的理解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认为,引起这些不同理解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不同派别的后经典叙事学在以下三个方面的排他性:1.不同的方法论基础。2.不同的阅读位置。3.不同的关注层面。我们重点讨论不同派别的后经典叙事学所具有的不同的方法论基础。一旦理解了这些不同的方法论基础,则不难理解不同派别的后经典叙事学的阅读位置和关注层面。
首先,不同派别的后经典叙事学具有明显不同的方法论基础。认知叙事学主要是借助心理学、人工智能、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模型和研究成果,探讨的人类在建构与理解叙事时,所共有的心理模型。换句话说,认知叙事学家旨在探讨叙事建构、叙事阐释的内在因素:人类心理。由此则不难理解,在这一思维模式的指引下,认知叙事学家为何排除了对外在因素的考察:社会历史文化、意识形态,读者的性别、年龄、国别、受教育程度等。
而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产生,主要归功于叙事学家将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引入进叙事学研究。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所关注的焦点在于通过对一定历史时期文本的解读,来探索女性和男性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特别通过揭示女性受压迫、受控制的事实,为建立平等的男女关系而呼号。同经典叙事学忽视“性别”叙事的做法相左,女性主义叙事学认为无论是女性写作还是叙事结构都受到作者、文本、读者之间隐含的权力关系的影响,而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研究具体的文本形式来探讨社会身份地位与文本形式之间的交叉作用,把叙述声音的一些问题作为意识形态关键的表达形式来加以解读。”(Lanser 1992:15)受到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影响,女性自然就会更加倾向于关注处在一定历史文化时期的叙事文本,以求考察女性地位、女性意识的变化等。在这一情况下,对叙述者、作者、读者的性别身份等因素考虑,自在情理之中。
修辞性叙事学的主要理论来源是20世纪40年代盛行于美国学界的芝加哥学派的“修辞诗学”。修辞诗学的理论旨趣在于强调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修辞交流,特别是作者试图向读者传达的修辞目的,通常以劝服读者接受自己的某种论点为主。在这一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修辞性叙事学,十分重视处于特定场合、特定语境下作者、读者、叙述者、受述者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强调叙事进程的动态性。也即是说,修辞性叙事学家的语境既是指作者与读者交流的文本外部语境,也指叙述者与受述者交流的文本内部语境。既然叙事进程的产生离不开读者的参与和反应,因此对读者种类的详细划分和考察也是理论建构上的必要程序。
其次,不同派别的后经典叙事学有着不同的阅读位置和关注层面。认知叙事学主要是从读者心理这一位置出发,来对各种叙事现象作出阐释的同时,探索形成这些叙事现象的心理原因。在这一阅读位置上,认知叙事学的关注焦点在于心理原型、认知脚本、认知框架、优先原则等认知因素在叙事文本解读中的效度。女性主义叙事学则主要从作者、读者、人物、叙述者的性别这一位置出发,来解读文本中不同性别身份的人所处的地位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因此,它的关注焦点在于挖掘和发现女性受歧视、受压抑等不公正的待遇,以及为建立和谐的两性关系而努力。与认知叙事学、认知叙事学相对照,修辞性叙事学的阅读位置则是作者、读者、叙述者、受述者的修辞交流,既关注作者对读者的修辞目的的传达、叙述者对受述者的影响,也考察读者、受述者的反应对叙事进程的作用,并分析在此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伦理效果。
三、后经典叙事学的互补性
学界普遍认为,互补性是当代西方文论的特点之一。(申丹 2000,孙胜忠 2004)就其发展而言,后经典叙事学不仅可以从经典叙事学那里吸取有益成分,获得支撑,不同派别的后经典叙事学之间也可以相互借鉴、扬长补短,以便得到更好的发展。通过对后经典叙事学排他性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互补性。本文拟以“不可靠叙述”为例,来说明修辞性叙事学与认知叙事学之间的互补性。
“不可靠叙述”(unreliable narration)是一个表面简单,实则复杂的论题。就不可靠叙述,在西方叙事理论界主要有两种研究趋势:修辞性方法与认知方法。申丹认为,由于这两种方法所基于的阅读位置不同,由于两者之间所存在的排他性,不仅认知方法难以取代修辞性方法,而且任何综合两者的努力也注定徒劳无功。(申丹 2006:133)也就是说。两种方法之间只存在排他性,而不具有互补性的可能,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韦恩·布思(Wayne C.Booth,1921—2005)最早提出了“不可靠叙述”这一术语。在《小说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Fiction,1961)一书中,布思说,“当叙述者的言行与作品的规范(即是隐含作者的规范)一致时,他就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Booth158—159)需要注意的是,布思的不可靠叙述主要发生在两条轴线上,即事实/事件(facts/events)、价值判断/伦理(values/ethics),并且判断叙述者是否可靠的标准是隐含作者的规范。四十年后,布思的学生费伦又将不可靠叙述从两条轴线发展到了三条轴线,即增加了知识/感知轴(knowledge/perception)。费伦还在每条轴上区分出两种亚类型,由此得出了不可靠叙述的六种亚类型: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misteporting)和不充分报道(underreporting),价值判断轴上的错误判断(misregarding)和不充分判断(underregarding),知识/感知轴上的错误解读(misreadng)和不充分解读(under reading)。(Phelan 2005:49—53)由此不难发现,不论是布思还是费伦,都将不可靠叙述归结为文本因素,而不可靠性与不可靠叙述的种类划分则是参考隐含作者的规范来加以判定。
就不可靠叙述而言,认知学派主要有两位代表人物较为突出,分别为塔马·雅可比(Tamar Yacobi)和纽宁。与布思和费伦给不可靠叙述所下的定义相左,雅克比把不可靠叙述定义为一种读者的“阅读假设”或“协调机制”。当读者在文本中遇到叙述有矛盾的地方时,会采用某种协调机制来加以解决。在《作者的修辞、叙述(不)可靠性、多样的解读:以托尔斯泰的(克莱采奏鸣曲)为例》(Authorial Rhetoric,Narratorial (Un) Reliability,Divergent:Readings:Tolstoy's Kreutzer Sonata,2005)一文中,雅克比详细地论述了关于不可靠叙述的五种协调机制:1.关于存在的机制,这种机制将不协调因素归因于虚构世界。2.功能机制,这种机制将文中的不协调因素归因于作品的功能和目的。3.文类机制,这一机制将文本中的不协调因素归因于不同的文类。4.关于视角的不可靠性原则,这一机制将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归因于假定的隐含作者规范。5.关于创作的机制,这一机制将文本中的不协调现象归因于作者的意识形态等问题。(Yacobi 108—113)纽宁延续了雅可比的思想,强调读者的阐释框架对理解不可靠叙述的作用,认为不可靠叙述主要是由读者的阐释策略所引起的。(Nünning 2005:95)纽宁从读者的视角和认知结构出发,对不可靠叙述重新定义,他认为“不可靠叙述的结构可用戏剧反讽和意识差异来解释。当出现不可靠叙述时,叙述者的意图和价值体系与读者的预知规范之间的差异会产生戏剧反讽。对读者而言,叙述者话语的内部矛盾或者叙述者的视角与读者自己看法之间的冲突意味着叙述者的不可靠。”(申丹 2006:138)换句话说,纽宁判断叙述者不可靠性的标准不是隐含作者的规范,而是读者的规范。
不难发现,两种关于不可靠叙述研究的方法存在明显的排他性。与修辞性方法关注叙述者的叙述与隐含作者的规范之间的关系形成对照,认知方法对不可靠叙述的研究则是主要聚焦于读者的阐释框架。修辞性方法在聚焦隐含作者规范的同时,忽视了读者的认知心理之于叙事判断的作用;而认知方法在注重读者的认知框架、认知脚本等阐释因子的同时,又忽略了对文本隐含作者立场、态度、意识形态等叙事规范的考虑。也即是说,修辞性方法意在寻找文本之内不可靠性,不关注读者对不可靠性的理解和阐释。与此相反,认知方法以读者为中心,意图探究在文本之外引起不可靠性的阐释根源,不关注文本之内的不可靠性。
若对两种方法的排他性加以仔细审视,不难发现在排他性的背后则蕴涵着互补性的必要与可能。既然两种方法都有其“盲点”与“洞见”,在叙事分析实践中,我们不妨借助一种方法的“洞见”来弥补另一种方法的“盲点”。如,认知方法可以揭示出读者的阐释框架或阅读假设,弥补了修辞性方法的盲点;修辞性方法可以从隐含作者的规范出发,为判断不可靠叙述确定一个合理的衡量标准,弥补了认知性方法一味地依赖读者的阐释框架的缺陷。从而,可以从文本内外两个方面更好地把握和理解不可靠叙述。
其实,我们在此分析不可靠叙述的修辞性方法和认知方法、揭示两种不同方法之间的排他性和互补性,意在说明不同派别的后经典叙事学之间的排他性和互补性。我们可以利用认知叙事学所强调的认知脚本、认知框架、优先原则等来叙事规约与文类读者在建构叙事、阐释叙事过程中的作用,来弥补女性主义叙事学、修辞性叙事学忽视叙事规约、文类读者的缺陷。同理,女性主义叙事学对社会历史语境、性别化读者等的强调也可以弥补认知叙事学、修辞性叙事学在这些方面的不足。而修辞性叙事学对特定语境、五维度读者的强调和划分,有助于我们关注叙事的动态性,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叙事进程。
无论是从后经典叙事理论建构的角度,还是从后经典叙事分析实践的角度,我们都不妨以敏锐的眼光来审视各个派别的后经典叙事学的优点,同时也包容它们的缺点。尽可能地减少它们的排他性,增强各个派别的交叉性和互补性,进而使后经典叙事学得到更良性的发展。那么,后经典叙事学究竟该如何减少排他性、增强互补性呢?笔者认为,多元主义是后经典叙事学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四、结语
在《作为复数的叙事学:叙事分析新视野》一书的“前言”中,赫尔曼指出,“后经典叙事学由于需要积聚诸多学科传统的资源和各种专门知识而成为非单个研究者、非单个视角所能胜任的事业。”(Herman 1999:14)也即是说,后经典叙事学作为一项庞大的理论工程,需要从多个理论视角、多个学科来对此加以探索,使其能得到健康稳定的发展。后经典叙事学这一“批评画框”下的各个派别、各种方法都是后经典叙事学持续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因子。我们需要站在“元批评”的角度,提倡后经典叙事学发展的多元主义范式。
在“后理论时代”,仅仅从一种视角来建构叙事理论、理解叙事作品,未免显得过于片面。多元主义的立场,要求我们持宽容的态度,能够包容各具特色的后经典叙事理论,只有这样,我们能够博采众长,多角度、多层次地发掘叙事作品的价值和意义。里查德·莱文(Richard Levin)认为,“当今,一个文学批评家最好能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做一名跨学科研究者。”(Levin 13)在此,我们不妨套用莱文的句式:一个后经典叙事学家最好能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做一名多元主义者。
在《文学叙事的修辞美学及其他论点》(Rhetorical Aesthetics and Other Issues in the Study of Literary Narrative)一文中,费伦曾说:“叙事理论与广阔的批评理论潮流之间所保持的对话,使得当下的文学叙事研究呈现出多样性色彩。”(Phelan 2006:86)倘若由这些广阔的批评理论潮流催发的后经典叙事学之间也能保持不断的交流和对话,跨越学科界限,走多元发展之路,那么多样化的色彩势必会更加浓厚,所取得的成果也会更加丰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