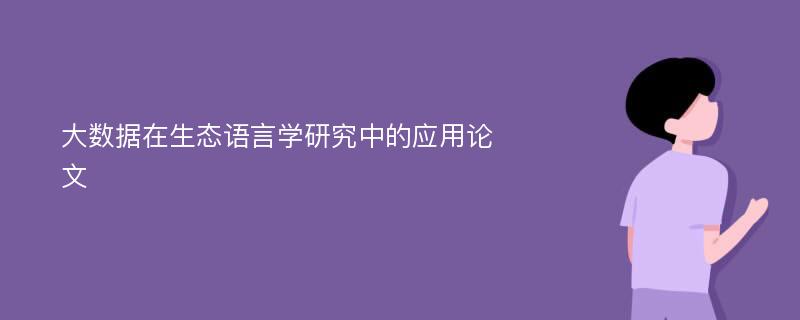
【语言与文化】
大数据在生态语言学研究中的应用
吴艺娜
摘 要 生态不可避免地成为21世纪的核心议题,而作为生态学与语言学的结合,生态语言学也应运而生,受到诸多学者们关注和研究。本文通过收集整理国内外生态语言学研究的文献,比对隐喻与非隐喻两个研究范式,即语言的生态学和环境的语言学,分析其发展前景以及现存问题,探讨大数据应用于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前景与挑战。
关键词 生态语言学;隐喻;非隐喻;大数据
一、生态语言学的产生
作为生态学与语言学的结合,生态语言学受到国内外诸多学者关注,成为研究热点。斯提布于2004年搭建了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框架,并于2017年1月正式成立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组织,会员1 000多人,这其中包括国内的黄国文教授和何伟教授。即便如此,至今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尚未成熟。目前,对该课题包含的术语的界定以及研究内容、范围和方法尚未形成明确统一的说法。当下,生态语言学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把生态语言学理解为“语言的生态学”,语言被视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另一个方向是把它理解为“环境的语言学”,其研究内容为语言如何作用于生态[1]。生态语言学的复杂性使得研究存在诸多困难,而传统的研究方法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大数据的发展给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带来了明朗的前景,也带来了挑战。
二、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发展
黄国文[2]提出,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任务是研究语言的生态因素以及生态与语言之间的关系,进而揭示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斯提布在接受北京外国语大学何伟教授的访谈时提到,科技的进步导致全球化,而全球化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消费主义,人类进入了“人类世”(也就是以人类为主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人类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变得尤其重要,因为这个关系是人类生命得以持续的关键。斯提布认为,从本质上说,生态语言学研究包括质疑那些支撑我们当前不可持续发展的文明的故事、揭露那些不起作用、正在导致生态毁灭和社会不公的故事以及探索更适用于我们当今世界的故事[3]。史蒂文森和菲尔把生态语言学定义为研究人类(作为个体、群体、种群和物种)为了创造一个更大的可以支撑他们生存的生态而利用环境的过程与活动以及研究这些过程与活动的社会与生态系统的局限[4]。总而言之,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包含语言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以及语言与语言环境的关系。
(一)生态语言学的两个研究范式
关于生态语言学,有隐喻和非隐喻两种说法。豪根[5]最先提出语言生态的“隐喻”说法,把语言和语言环境的关系类比为生物与生物的生存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将语言环境比喻成生物生态环境。根据豪根的说法,语言生态学研究的是“某一特定的语言与该语言环境的相互作用”。诸多学者认可豪根语言生态的“隐喻”说法,称之为“豪根模式”,并开始进行语言生态研究。“豪根模式”认为,语言生态的研究焦点应当包括语言如何产生、发展、灭亡、语言的多样化以及如何保护濒危语言等,如研究强势语(如英语)的国家化甚至国际化、一些少数民族的语言濒危甚至接近消失、方言的边缘化甚至消失以及互联网通用语的一体化发展态势等问题。张丹[6]指出,语言发展的基础是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只有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才能确保语言的良性发展进而促进语言生态的平衡。只有确保语言生态平衡,才能保证文化生态的平衡,进而确保人类社会得以可持续发展。
20世纪90年代,全球生态危机进一步加剧,全球变暖、环境污染、物种灭亡等生态问题为人类的生存前景敲响了警钟,有学者开始超越“豪根模式”,于是,“非隐喻”视角应运而生。韩礼德从生物的视角探讨生态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提出语言作为人类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用来反映现实、构建世界的重要工具,语言在环境保护与环境恶化的问题上起到一定作用,并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视角解释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7]。这一模式被称为“韩礼德模式”,它强调的是语言学家的社会责任,提醒语言学家要记住自己在环境保护方面能做哪些工作和贡献。语言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学者需要用批判的眼光鼓励、促进生态和谐的语言,反思和批判人们对自然的征服剥削以及对自然资源的榨取。斯提布与韩礼德观点一致,认为生态语言学的目标是揭示我们信奉和实践的故事,这些故事或许值得鼓励、推崇和发扬,或许需要改进然后理解地接受,或许应该要质疑、批判并抵制。他们把这些故事归类为有益性话语(如富有正能量的诗歌)、中性话语(如我们日常的多数语篇)以及破坏性话语(如鼓励人们奢华消费的广告语)。对这三类话语的区分取决于分析者的生态哲学,包括分析者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世界观、受教育情况以及成长环境等。
“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都是语言学与生态学结合的产物,二者都代表了生态语言学研究的途径、方法和研究领域,既有所不同又彼此相关。菲尔特意使用了“Sustaining Language”这个带有双关语的表达来涵盖生态语言学的两个研究范式。一方面,“Sustaining Language”可理解为“可持续发展的语言”,表明生态语言学的任务之一是保留语言的多样性;另一方面,“Sustaining Language”可理解为“可以维持我们的生命的语言(language which sustains life)”,表明生态语言学的另一任务是研究语言如何影响人类活动,以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菲尔收集的论文既包括某种特定的语言形式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也包括“语言生态(language ecology)”,也就是语言多样性的保护,这两类论文有区别也有关联,尤其是“语言生态”方面的文章强调了语言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关联。
泸州市9家医院10种中药注射剂行政干预和药学干预前后使用情况分析 ………………………………… 罗宏丽等(6):847
(二)生态语言学存在的问题
《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发改价格〔2006〕310 号)(以下简称 “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第七条规定:供水生产成本是指水利工程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合理支出,包括直接工资、直接材料、其他直接支出和制造费用。制造费用指水利工程供水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各项间接费用,包括固定资产折旧、修理费、水资源费、水质检测费、管理人员工资、职工福利费和其他制造费用等。
三、大数据科学对生态语言学研究造成的影响
大数据带来的信息风暴如同一场革命,正在改变我们生活、工作和思维方式,带来了重大的时代转型。大数据有三个要素:整体数据而非随机样本;混杂性而非精确性;相关性而非因果关系,这三个要素影响了人类的思维方式。“让数据说话”的思维方式代替了传统的思维方式。在大数据时代,宇宙没有中心,只有统一法则,形成的不再是点对点的线性因果关系,而是点对面的网状相关关系。在这个网状相关关系里,没有边缘,没有中心,周而复始,互为因果。用大数据思维思考世界,那么世界的均衡不是永恒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平衡的生态系统是暂时的,多样化的生态系统在不断变化。用大数据的概念来看待语言生态,是以循环理论和网格的整体观来对待语言和语言数据。大数据的三大要素也影响了生态语言学的研究方式,因为这三大要素正是目前语言生态调查所需要的。前文提及的当前生态语言学研究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传统的田野调查或个案研究遭遇挑战,无法全面、实时地考察地区乃至全世界的语言生态。目前,生态语言学研究主要从生态视角对环境与气候相关生态问题的语篇进行话语分析,揭示话语中违反生态的意识形态,或者研究某些濒临灭绝的语言,如穆尔豪斯勒对太平洋圈的语言生态情况进行调查,重点调查了皮钦语和克里奥语的语言系统、演变过程和现状。那么,大数据为我们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全球语言生态的全样本,这个全样本更深入而真实地反映了语言的一些本质特征,如语言的概率性。这个全世界语言生态的全样本还能帮助生态语言学家研究人类的语言规律和认知规律之间的关系,看到国际通用语与国家通用语乃至地区方言和混合语言之间互动的混杂性,让我们得以全面、实时、动态地考察语言生态。
大数据的发展给生态语言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语言学家应该看重“大数据”这个时代特征,关心数据驱动的语言研究方向,或者说应该关心大数据如何解决语言学问题,发现那些大数据时代之前没有注意到或无法研究的语言规律,因此,大数据为生态语言学家提供了一种研究范式和一种观察研究对象的工具与方法。
近年来,信息化进程不断推进,“大数据”开始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并形成了新的研究范式。大数据被定义为以体量大、处理时效高速性和信息类型多样性和价值密度低为特征的信息集合。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过去十几年里产生的数据量比以往三千年的数据量还要多,而这个巨大的数据“宝藏”就是“未来的新石油”。
目前,生态语言学还存在一大问题,即研究方法问题。生态语言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生态话语分析,包括广告、环保、资源、能源、生态旅游、气候变化和可持续性等话语分析。斯提布指出,批评话语分析、认知语言学、评价理论、身份识别理论、系统功能语言学和多模态话语分析等都是有用的生态语言学研究理论。目前的生态语言学研究有强大的理论支持,但是,在具体的调查方式和手段上还是存在问题。梅德明指出,目前而言,语言生态学调查主要依赖于实地考察,锁定用于案例研究的某一个目标语言,尤其是某个土著语言或濒危语言,通过记录“实时”语料库,分析、归档,然后形成报告或参加会议交流。梅德明认为,这种传统方法和手段相对片面,只看到树木看不到树林,不能全面、实时地研究某地区乃至全世界的语言生态,无法精确地理解语言的功能变化和结构变化,因此,无法为制定语言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如语言教育政策的制定和语言保护政策的制定[8]。生态语言学的研究需要一些新的转变:研究手段上,可以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和研究方法以弥补定性研究的缺陷;研究对象上,则需要利用新科技大批量收集真实的语言素材,如研究濒危语言可以利用大数据整理统计全球语言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大数据给生态语言学研究带来了乐观前景,也带来了挑战。从体量大、信息类型多样性、处理时效高速性和价值密度低的“4V”特征来看,前三个“V”对生态语言学的研究都具有积极意义,价值密度低这个“V”则对解读、应用和管理数据的研究技术人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语言数据信息体系的建设、语言数据技术的研发和计量语言学的发展迫在眉睫。
在两组患者接受临床治疗一段时间后,实验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97.62%,显著高于对照组的76.19%,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详见表1。
四、结语
生态语言学的发展符合语言、学科以及社会发展的趋势,但是,经历几十年的探索,生态语言学尚未建立起完整的学科体系,国内外学者就这门学科的概念、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还未形成一致的认识,存在隐喻的“豪根模式”与非隐喻的“韩礼德模式”两个有差异又相关联的研究范式。传统的研究方法无法全面、科学、实时的方式考察区域乃至全球的语言生态以及语言对生态的影响,而大数据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有希望实现生态语言学研究科学化。同时,大数据也对生态语言学研究带来了挑战,因此,大量的技术支持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
[1]辛志英,黄国文.系统功能语言学与生态话语分析[J].外语教学,2013,(3):7-10.
[2]黄国文.生态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J].中国外语,2016,(1):8-12.
[3]Stibbe A. An Ecolinguistic Approach to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J].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2014,(1):117-128.
[4]Steffensen V S,Fill A. Ecolinguistics: the State of the Art and Future Horizons[J].Language Sciences,2014,(41):6-25.
[5]Haugen E. The Ecology of Language[M].Palo Alto: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15-22.
[6]张丹.生态语言学研究综述[J].语言研究(学术综合版),2017,(4):123-125.
[7]Halliday,MAK. New Ways of Meaning:a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J].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1990,(13):37.
[8]梅德明.大数据时代语言生态研究[J].外语电化教学,2014,(1):3-10.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7725( 2019) 08-0207-03
作者简介 吴艺娜(1978-),女,福建南安人,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大学外语教学部,讲师,主要从事语言学研究。
【责任编辑:董丽娟】
标签:生态语言学论文; 隐喻论文; 非隐喻论文; 大数据论文;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大学外语教学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