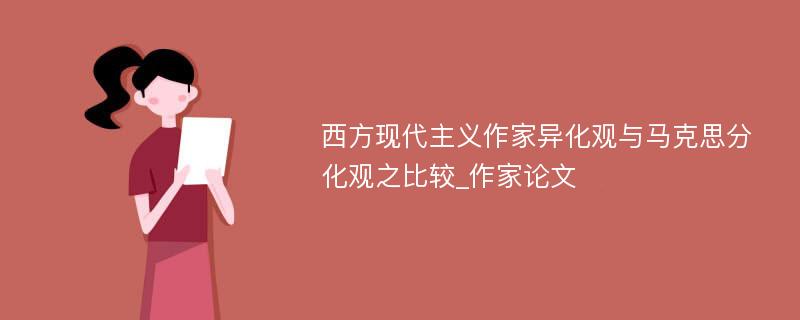
西方现代派作家的异化观与马克思异化观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现代派论文,观之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德裔美籍著名思想家埃利希·弗洛姆说:“在整个工业化的世界中,异化达到了近似于精神病的地步,它动摇和摧毁着这个世界宗教的、精神的和政治的传统;并且通过核战争,预示普遍毁灭的危险性,正因为异化已经达到了这种程度,越来越多的人才更清楚地认识到,病态的人乃是马克思承认的现代的主要问题。”①异化作为“现代的主要问题”已“吞没了全部现代文学”。但是,西方现代派作家的异化观同马克思的异化观显然不同。两者之间究竟存在哪些差异?这些差异又是如何形成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或制约着作家的创作的?下面我们拟从三个方面来加以论述:
一、“无因之果”的迷惑
现代派作家大都缺乏对异化原因的分析与探索,偶尔有之,也往往是偏颇的、形而上的、悲观绝望的。他们很少直接论及异化,虽然他们笔下反映的常常是异化主题。不过,萨特可算是例外,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一书中力求了解“人的实在”的一般结构。他将个人面临的浑然世界称为“自在的有”,而把个人自己的意识定名为“自为的有”。“自在的有”是浑然的、未分化的、无定形的、无知觉的存在,它是人的意识登场时在那里跟意识打照面的东西,它对于人的意识来说是荒唐的、讨厌的、令人恶心的。“自为的有”则永远不是什么东西,是无,它老是不断地要成为什么东西。宇宙万有当中,唯有人是“自为的有”。人是没有本质的,这就是“存在先于本质”。因此,人是自由的,正是这种自由将人的“实在”与世界上其他的万“有”区别开来。人人都是自由的,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只有两种可能性:不是甲作为“自为的有”把乙看成物(“自在的有”),就是乙作为“自为的有”把甲看成物(“自在的有”)。譬如,我坐在公园的长凳上,另一个陌生人从旁边走过,抬起头来看我。立刻,我就成为,并且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他的一个对象,一个物,一个物体。他在把我看成他的对象时就消灭了我的主体性。这时他就是“自为的有”,而我成为“自在的有”。我不甘心跟我坐的长凳一样,成为一个单纯的对象,于是反过来盯着别人,也把他看成一个对象。这时,情形又完全颠倒过来了。因此:
对象—他人是我凭借领会所使用的爆炸工具,因为我在他周围预感到有人使他闪现的恒常可能性,并且,由于这种闪现,我突然体验到世界从我这里逃走了,我的存在异化了。②
当我的“自为的有”变成了他人的“自在的有”时,异化便发生了。并且,这种异化是必然的、永恒的、无法逃避的。我永远不能捉住别人的自我,别人的“自为的我”也总不让我抓住,我无可奈何,只好把别人看成一种永远威胁着我这自由主体的存在。
萨特的剧本《间隔》是这一异化观的形象的表述。剧本写三个鬼魂:加尔森是在战争中叛国脱逃而被枪毙的胆小鬼;伊奈斯热衷于同性恋;埃司泰乐是溺死亲生儿的色情狂。他们在进入地狱后仍然无休止地争斗。他们互相隐瞒、互相戒备、互相封闭、互相折磨,每个人都是“刽子手”,又是受害者;既成为别人的障碍,又使自己坠入深渊。埃司泰乐狂热地追求加尔森,但加尔森说,只要伊奈斯看得见,他就没法爱她;而伊奈斯要和埃司泰乐搞同性恋,加尔森又成为一大障碍。他们就是这样互相追逐,永无宁日,欲逃无路,欲死不成。虽然他们置身其中的环境是地狱,但他们相互敌对却构成一座更加恐怖的“地狱”。“我万万没有想到,地狱里该有硫磺,有熊熊的火堆,有用来烙人的铁条……啊!真是天大的笑话!用不着铁条,地狱,就是别人。”③
显然,萨特的异化观非常接近黑格尔的异化观,而同马克思的异化观相去甚远。黑格尔认为,世界本体是客观精神、客观思维、客观概念,具有能动性。这种能动性就是自身的否定性,或自身矛盾、自身异化的发展能力。客观思维经过自身逻辑阶段的否定性发展,异化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又通过人的意识的否定性发展达到自我意识,在人的自我意识的否定性和异化的长期艰难曲折的发展中,人逐渐认识到这一切都无非是精神自身的各种异化和扬弃这种异化的种种形式,最终终于达到了对精神自身的绝对性认识,达到了绝对精神本身。总之,黑格尔的“异化”就是“对象化”,又叫精神变物质,是他辩证法中正反合三一体中由正到反的阶段。萨特的异化也大体等于对象化,但被对象化的却不是客观精神,而是人的“自为的有”,也就是人的自由。虽然他们的出发点不尽相同,但结论却出乎意料地趋于一致,所以,萨特宣称黑格尔的说法非常正确:人的一切关系的基础都是主奴关系。
像黑格尔一样,萨特的异化观的局限与错误也是一目了然的。虽然萨特的异化观反映了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小资产阶级受排挤、被吞没、身不由己、无可奈何的生存处境,但是,萨特将这种异化普遍化、永恒化,便从根本上限制并抹煞了人的自由,这使他“存在先于本质”的论断显露出难以弥合的裂隙。
但是,无论如何,萨特毕竟探索了产生异化的原因,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认识与批判的参照系。而更多的现代派作家虽然在作品中致力于表现异化主题,但他们却几乎从不使用异化这一概念,并且,通常总是略去了产生异化的原因,或者他们认为异化原本就是没有原因的。因为没有原因,所以异化又是永恒的。卡夫卡就是如此,他在《乡村婚事》中写道:
我手无寸铁地面对着一个形体,他安静地坐在桌旁,望着桌面,我围着他绕圈子,感到自己被扼住喉咙快窒息了似的。第三个人围着我转圈子,觉得被我扼住。第四个人绕着第三个人走,感到被卡住喉咙,就这样持续下去直到星辰运行到宇宙之外。万物都感到被卡住了脖子。④这种“被卡住了”的感觉与状态,也就是异化。
在卡夫卡的作品中,一切都体现了人的异化:政治、法律、宗教、事业、爱情,甚至连罪恶也是如此。《审判》是对无罪的审判。约瑟夫·K莫名其妙地被捕了,他自己不知道犯了什么罪;来抓他的看守也只知道:“你被捕,这是事实。”而审判他的法官竟连他的真实身份也一无所知,开口就对K坚定地说:“您是一个油漆匠吧?”这里,政治法律成了人类面临着的一种同自己敌对的、莫可名状而又强大无比的力量。《变形记》中人变成甲虫,异化为非人。人变成甲虫:甲虫便带着人的视角去看人类,它所看到的是一群多么冷漠、多么空虚的芸芸众生;从人的角度看虫性,甲虫就显得更加孤独、恐惧和不可理解了。主人公既是人又是虫,但他体验的只是人与虫双面的痛苦。《饥饿艺术家》中的事业是以生命作代价的,40天的饥饿表演只是求得肉体的生存,而绝食却成了艺术的最佳状态。有限的生命永远也不可能真正实现无限的艺术。《城堡》中K同弗丽达的爱情,决不是真正的爱情。当他们都追求纯洁、专一的爱时,他们就相互排斥,很快便失去了对方;而当他们各自心中另有所图时,他们又相互吸引,迅速地结合在一起。《在流放地》中行刑官已异化为行刑机器,最后当行刑机器将被废除时,行刑官宁愿同机器一道同归于尽。
总之,卡夫卡发现了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异化问题,他苦苦思索,但最终也未找到答案和出路,而他又不肯苟且地找一个模棱两可的替代品。“他感觉到被囚在这个地球上使他憋得慌,被囚禁的忧伤、虚弱、疾病、狂想交集于一身,任何安慰也不能使他宽解,因为那仅是慰藉,但如果你问他,他到底想要什么,他回答不出来。”⑤“目标只有一个,道路却无一条,我们谓之路者,乃彷徨也。”⑥因此,卡夫卡只知道人已异化为甲虫,但人为什么会异化为甲虫,卡夫卡却不得而知。
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垮掉的一代等现代派流派朝异化走得更远,走向彻底的荒诞和全面的垮掉。他们已不再相信有什么本质和本性,昔日的人道主义理想与传统已经分崩离析,烟消云散,因而也就无所谓异化和复归了。他们认为,人类生来就处在荒诞中,并且永无解救的希望,这就像海勒笔下那令人窒息的“第22条军规”,无时无处不在,永远无法摆脱。当然,这种彻底的荒诞在我们看来也只是人类异化的一种表现。但是,被异化了的现代派作家由于身临其境,却不明白其中的缘由,他们只是一味吞食异化的苦果,却不知这苦果从何而来,于是,他们在将异化视为荒诞抛弃的同时,也将异化的反面,即人的本质也一起抛却了,异化在这里成为一种更加不堪忍受的人生重负。
二、“无因之因”的启示
现代派作家放弃了寻找或者说没有找到异化的真正原因,这一事实本身却是有原因的。现代派作家绝大多数同马克思主义无缘,不了解马克思对异化的正确分析和阐述,少数作家如萨特虽然有志于发展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但他最终发展的仍然是存在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在理解了马克思的异化观之后,就不难看出现代派作家为何陷入“无因之果”的迷误了。
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就是劳动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劳动从主体来说也是人的根本需要。人类的历史不外是借助于自己的劳动和自己的生产而进行的自我创造。“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⑦因此,马克思从对劳动的研究出发,来考察私有财产的本质、起源和意义,这样便一下子抓住了异化的真正原因。
劳动异化表现出来的经济事实首先是劳动者同他的产品之间的异化,这又叫物的异化。“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这说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⑧产品原是工人劳动力量的对象化,但却同它的创造者形成了对立的关系,对象化成为丧失对象,受到对象的奴役。最终,劳动者的生命力变为同自己敌对的对象的生命力,变成了金钱、商品、资本的无上权力,他自己反而被这些对象所占有和奴役了。同时,劳动者把自身的力量对象化到一个外部对象上去形成产品,必须以自然界、外部的感性世界为前提。于是,劳动者在这里同自然界异化了。人同外部世界的多种多样的关系(包括审美关系)被唯一的关系,即人同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的关系所排斥。自然界的全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对于异化的人来说都消失了。
以上这种“物的异化”在现代派作家笔下有许多卓越的表现。例如,在卡夫卡看来,“生活对于他和对于穷人是完全不同的;首先,对他来说,金钱、交易所、货币兑换所、打字机都是绝对神秘的事物,它们对他来说是一些莫名其妙的谜。”⑨所以,卡夫卡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异化的世界”。但是,卡夫卡不明白这异化的根源是劳动异化,所以,他最终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这正如写在他手杖上的那句名言“每一个障碍摧毁了我”。新小说派和荒诞派戏剧作家也深切地体味到在现代社会中物质已越来越成为人类生活的主宰。于是他们着意写物而拒绝写人,或者把人当作物(对象)来写而排斥写具有丰富主体性的人。罗布-格里耶是“物主义”的首创者,他的“物主义”认为,作家的任务只限于将客观事物冷静地记录下来。所以,格里耶在写物时既细致又科学,往往不差分毫,但一写到人就戛然而止,甚至干脆弃而不写。他的著名小说《橡皮》可作例证。在荒诞派戏剧舞台上充斥着物以及被物化了的人:满台的犀牛,遍地的鸡蛋,无限增多的家具,不断膨胀的尸体,以及禁闭在垃圾桶里的人,半截子入土的人,脱离肉体的一张巨大的嘴等等。在尤奈斯库的《椅子》一剧中,一对年逾90的老人为了迎接宾客的到来,在舞台上摆满了椅子,最后,这对夫妇连立足之地也失去了,只好从窗口投海自杀。这满台的椅子令人震惊地表明了剧本的主题:椅子。在强大的物质洪流的挤压下,人已经失去了自己应有的位置,异化为一片虚无。
在现代派作家笔下,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也被异化了。由于现代派作家自身的异化,又将自己变成了异化世界的尺度,于是,大自然成为异化了的人的意识的象征:天空成为一块尸布,地球是柴炭和灰烬的混合物,风景用自己的线条表明它只是一具巨大的尸体,黄昏是一位被麻醉在手术台上的病人,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大自然已不再是美好与和谐的,也不再是人化了的自然,它成了人的对立物,无时无刻不在压抑人,限制着人的创造力和自由。这便是现代派作家所看到的异化的恶果。
马克思认为物的异化的根源及核心是自我异化,即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劳动从它自身来说是人类特有的创造劳动。在劳动中,人创造满足自己需要的对象:生产衣食住行的对象,满足和丰富自己的物质生活,生产科学艺术满足和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在劳动和占有劳动产品中,使自己的潜力得到发展发挥。劳动是人们获得自身自由的源泉,因而它的本质应该是自由的。这样的劳动就不会产生劳动者同自己产品之间的异化和敌对。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产品却同它的生产者发生异化关系。显然,这种异化不可能是由产品的对象的物的性质(如商品、货币、资本本身的对象性质)所决定的。马克思说:“如果劳动者不是在生产行为本身中使自己异化,那么劳动者怎么会使自己活动的产品像某种异己的东西那样相对立呢?产品不过是活动、生产的总结。因此,如果劳动的产品是外化,那么生产本身就必然是能动的外化或活动的外化、外化的活动。在劳动对象的异化中不过总结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化。”⑩
劳动的自我异化表现为:劳动对于劳动者来说是外在的、不属于他自己的,不是肯定自己、自由地发挥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而是否定自己的、非自愿的、强制的、被迫的劳动。劳动已不再是人的本质,而只是维持生存的一种迫不得已的手段。最后,人只有在运用自己动物式的机能(如吃喝等等)时才觉得自己是人,而在从事人的活动时反而觉得自己是动物。
人于是便异化为畜生,成为非人。西方现代派作家虽然对自我异化的过程及原因不甚明了,但对于这异化的结果及危害却是深有感受的。他们一方面非常关注自我异化这一主题,另一方面在表现异化时他们又往往抽去了其中的劳动内容,使人的自我异化变得十分抽象和模糊。“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成为现代派作家大声询问的问题。他们发现,人们通常所说的“自我”,其实只是人们各自戴上的人格面具,真正的自我已经失落,并且无从寻找。于是,人变成了甲虫、变成了犀牛、变成了机器……
美国黑人作家艾里森的《看不见的人》表现的就是这一主题。小说的主人公“我”,一直在寻找“我”那看不见的本质。他先是在白人的世界里寻找,却发现在那里根本没有自我的位置。后来他又去黑人中间寻找,他参加了一个叫“兄弟会”的黑人组织,在那里他为发现自我而斗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感到他已成功地找到了自我。但是,后来他发现兄弟会原来是一个残酷的、攻击性的组织。在小组里大家是兄弟,对外却绝非兄弟。而兄弟会的头目和他所信任的多数兄弟所关心的只是他们自己的私人权利。这个组织感兴趣的也只是破坏这个社会和政府,并不试图进行改良。他自己的演讲是有效的,但他的事业却无任何伟大方向。他在兄弟会中的经历是残酷的、危险的,但绝不使人满意。最终他寻找自身的努力宣告失败,于是,他蛰居地洞去自己的灵魂和肉体中寻找自我。这便是看不见的人寻找自我所走的必然之路,正像艾里森自己一样,看不见的人在地洞里仍然找不到他的自我,因为他所走的路,从一出发方向就错了。
接着,马克思从异化劳动已有的两个规定推出了它的第三个规定,即人同自己“类本质”的异化。人是类的存在物。马克思说,人能通过理论和实践普遍地加工自然界的事物,使之成为自己的精神食粮和劳动资料、生活资料,从而使人本身成为普遍而自由的类存在物。“正是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人才实际上确证自己是类的存在物。”(11)既然人的本质是由劳动来实现和确证的,那末,由于劳动变成了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走了生产和生活的对象和自然界,从事生产的人就不能再进行发展自身、肯定自身的劳动,人就失去了自己的类生活与类本质。劳动作为类的发展的自由活动,就变成了个人维持生存的手段,各人都为私利为谋生而活动,人“类”就丧失了自己的目的。
马克思这是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考察人的本质和异化。由于现代派作家本身的局限以及理论与文学的差异,现代派文学几乎没有表现人的这种类本质异化。不过,这种类本质异化的直接结果,即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异化,却是西方现代派文学最重要的主题。
人同自己类本质相异化,只有通过一个人与其他人的异化关系才能得到实现或表现,这就是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异化、对立。这是马克思异化劳动的第四条规定。马克思认为,如果人同自己的产品、自己的劳动活动是异己的关系,这些产品和活动不再属于他自己,那就一定要属于一个在他之外的存在物。这个存在物,不是自然界也不是上帝,而只能是人,只有人本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这个人是不同于劳动者的人,是劳动者之外的另一个人或一些人,这些人就是资本家。人要使劳动的异化和产品的异化变为现实,必须产生出资本家。“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同其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异化借以实现的那个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12)因此,阶级斗争和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产品和结果。
现代派作家由于不明白异化的根源,所以他们笔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异化远远超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范围,它包括任何时候的任何人,这时异化便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萨特认为,由于物质资料的匮乏,为了征服“稀有”,得以生存,人们就不得不彼此接触,于是就有人与人的交往关系。这种关系本质上属于物的关系。因为人与人之间,互为手段,彼此利用,因此,每一个人对于他人都是残暴的。这样,便有了萨特的那句名言,“他人就是地狱。”卡夫卡是以写异化著称的作家,他自身的孤独、异化就是其作品最好的注释。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在捷克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波希米亚人,他也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工工伤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也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是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而作为作家来说,他也不是,因为他把精力花在家庭方面,而在自己家里,他比陌生人还要陌生。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中的马丁先生和马丁太太竟然素昧平生,互不相识,在经过长时间攀谈之后,才恍然大悟:他们原来是同乘一趟车、同住一间房、同睡一张床,共有一个女儿的夫妻。另外,剧中的女佣玛丽和消防队长原是一对恋人,但见面后互相辨认良久,才相互认识。夫妻、恋人之间尚且如此陌生、冷漠,一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可想而知了。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认为,西方现代派作家虽然全面而又深刻地描写了现代人的异化主题,但是,这里的异化同马克思的异化观却大不相同。这种不同首先是现代派作家往往将异化的结果当作了原因,而对异化的真正原因反而略去不问。这正如当年被马克思批判的国民经济学一样,它从私有财产这个事实出发,却不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应当加以论证的东西当成了理所当然的东西。私有财产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社会结构原本是劳动异化的产物和结果,现在却成了现代派作家所表现的异化的根源,由于他们倒果为因,真正的原因便如同神学家眼中的原罪一样,成了一种合理的历史事实。这就使现代派作家笔下的异化与马克思的异化观又有了第二点不同,即现代派作家将异化普遍化、永恒化。异化于是不再是一定历史时期内工人同资本家的关系,而是与人类一样古老,又与人类一样永恒的问题。异化不再是具体的、历史的概念,它成了形而上的范畴。第三,马克思剖析劳动异化,其目的是为了人本质的复归,而在西方现代派那里,异化无时无处不在,复归却毫无希望,虽然人类可以作出不懈的努力,但其意义充其量只不过像西西弗一样,清醒的意识到这一异化事实而已。
由于现代派作家阶级的、时代的局限,我们自然在可能要求他们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水平,何况马克思的《巴黎手稿》1932年才正式问世,而这时现代派文学已经经历了它的高潮。相反,现代派作家非但没有理解与接受马克思的异化观,他们反而更多地倾心于黑格尔的“精神异化”和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本质的异化”以及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如叔本华的意志论和悲观主义、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及萨特的存在主义,这使得他们与马克思的分歧愈来愈大。
当然,这“没有原因”的异化的真正原因远不止以上几点,其余诸如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的背景,作家自我的异化,以及文学自身的特征等等,也都不可忽视。但由于这些原因在以往相关著作中多有论述,这里不再赘述。(第10页第三个小文件原文不清无法录入)
黑色幽默作家面对异化,“一概报之以幽默、嘲讽,甚至‘赞赏’的大笑,以寄托他的阴沉的心情和深渊般的绝望。”他们以一种全然“无所谓”的态度来对待“有所谓”,他们这种以笑当哭的态度自然不会根治异化,只会使人感到最大的失望与最大的恐惧。“垮掉的一代”的这种“无所谓”的态度较之黑色幽默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以更加全面、彻底的异化来面对异化,通过爵士乐、摇摆舞、吸大麻、性放纵以及参禅念佛和“背包革命”来“反叛”生活,逃避异化。这些“异化者”“不再认真寻求任何他们可能接受的生活方式”。他们主张,“一个人不应当委身于任何价值、运动或人”。于是,“他们没有目标而造反,没有纲领而拒绝,没有未来应当如何的理想而不接受当前的现状”(16)。“垮掉的一代”的斗争方法,使他们想到了日本的一个古老的风俗。这个风俗是,要想干掉自己仇敌的人,就在仇敌家的门槛上用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些“垮掉”的作家们,为了对异化进行鞭挞,便先将自己彻底异化掉。因此,“垮掉的一代”们的行动与其说是一种反叛异化的方法,勿宁说就是现代社会人的异化的直接结果。
现代派作家虽然没有找到正确的人本质的复归之路,但他们的探索与寻找却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人类已经异化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不克服这种异化人类就不可能健全地活着,同时,也使我们更加注意到马克思早在1844年给人们指出的扬弃异化的必然之路。
马克思认为,对人的异化的扬弃,不应从抽象的人和人性出发,而应从具体的人的需要的本性出发。人的复归不应是空洞的。只有深入研究在劳动、实践的历史发展中所产生的人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研究人在私有财产的虽是异化的形式中却仍然得到了发展的积极的本质,才能真正理解这种复归。在马克思看来,被物化为异己的、起决定作用的力量的生产关系,始终是社会的人的一定关系的对象化,因而,在这种生产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异化的消除,只有在它能为这种关系中的经济革命奠定基础的时候,才是全面的现实的。换言之,异化不仅是消极的、否定的,而且也是必然的、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类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力、工业和科学就是在私有制和人的异化中得到了高度的发展,这就为人性的复归创造了现实的前提。总之,“自我异化的扬弃跟自我异化走着同一条道路”(17)。人类只有通过私有制才能铲除私有制,只有通过异化才能扬弃异化,只有通过自己才能解放自己。
这种异化的积极扬弃便是共产主义的实现,也就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18)在扬弃了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之后,劳动便成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私有财产又是由劳动而不又异化劳动形成。这时,自然便真正成为人的基础和对象,人化的自然,自然通过自己的产物人而把自己发展到一个高级阶段,这是自然界的真正实现或新生;人重新获得了全部自然界,获得了自己感性生活的全部真正基础,使人本身得到了真正的实现。人和自然同时都得到了真正的解放。而扬弃了异化的人便成了人类对象化活动的结果和出发点。人自己创造了人——他自己和别人。同时,作为人的个性的直接体现的对象,对别人说来既是他自己的存在,又是这个别人的存在,并且对他说来也是别人的存在。
“因为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自身异化的活动。”(19)所以,虽然可以把工业只当作人类普遍活动的一部分一方面,但是,从根本上说人更应该把上述那些抽象的普遍的活动,如宗教的、政治的、文艺的活动,看作是劳动、工业、异化活动的一个特殊部分和表现。因此,随着作为异化根源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被扬弃,那些伴随异化劳动而产生的特殊的部分和表现也将随之一道被扬弃。这时,人类便从必然王国进入了自由王国。
今天,马克思创立的异化理论已经过了一个半世纪,如果我们现在仍原封不动地照搬马克思的理论,恐怕就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马克思主义了。弗洛姆说:“任何学说即使在60年内没有变化,它也不再与这个学说的创始人原初的理论完全一致了;由于僵化的复制,这一理论实际上遭到了损害。”(20)因此,发展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或对其重新进行解释都是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弗洛姆又说:
马克思没有预料到异化达到这种程度,变成绝大多数人民的命运,特别是变成人口中日益增多的这一部分人的命运,他们不是操纵机器,而是操纵着符号也操纵人。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办事员,售货员,总经理今天异化的程度比有技术的体力劳动者还要大。后者所起的作用仍然依靠如技术、可靠性等个人品质的表现,而他在讨价还价中不是被迫出卖他的“人格”,他的微笑,他的意见;而符号的操纵者之被雇用则不仅因为他们有技术,也是因为使他们成为“有引诱力的人格装饰”的那些个人品质,容易摆弄、容易操纵。(21)
这就是说,在这个社会中的其他人同他们本质的异化更甚于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的工人。
另外,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使我们越来越增加远离人类的异化感。诚然,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地把我们从无用的苦工中解放出来,并给所有的人提供了更多的创造性机会。但是,科学技术已经变成了一个目的,由于技术首先要作有用的研究,在生产与分配中要求数量和效率,结果我们的创造力实际上都瘫痪了。技术并没有带来个人发展和生产力提高的时代,反之却试图以消费的平均主义的概念来取代那种美好的生活。因此,科学技术使人的异化更加显眼,玛蒂尔德·尼尔说,“机械与技术有一种奴役人的自然倾向,因而它们可能变成像最不人道的那种资本主义一样危险的敌人”(22)。
因此,尽管异化的根源仍然是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然而,在消除了私有制或部分地消除了私有财产的一些国家里,异化并没有被根本扬弃。并且,人类今天的异化的方式及程度同马克思在1844年所作的分析显然有着许多不同。这样,我们便又一次理解了西方现代派作家笔下的异化与马克思的异化论的巨大差别。
注释:
① 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第62页,张燕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 萨特:《存在与虚无》第390页,陈宣良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
③ 《萨特研究》第303页,柳鸣九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④ 转引自《论卡夫卡》第60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⑤⑥ 卡夫卡1917年写的《箴言》,转引自叶廷芳《现代艺术的探险者》第83、186页,花城出版社1987年版。
⑦(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1、127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⑧⑩(11)(12)(15)(17)(18)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4、47、51、53、45、70、73页,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⑨ 《德国近代文学史》上册第398页,苏联科学院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13)(14) 艾略特:《四个四重奏》第104、109页,裘小龙译,漓江出版社1986年版。
(16)(21)(22) 宾克莱:《理想的冲突》第47、102、103页,马元德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20) 弗洛姆:《人之心》第2页,都本伟译,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