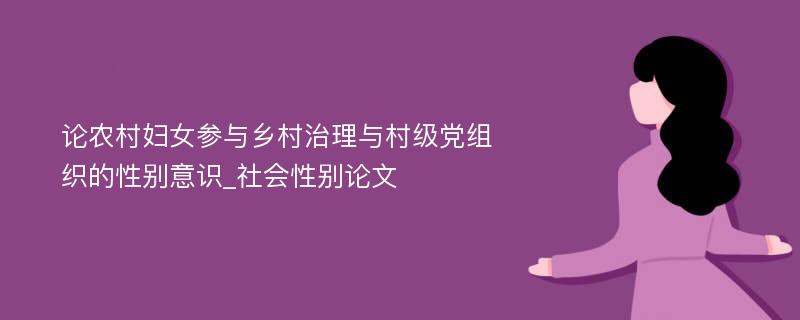
论乡村治理中的妇女参与与村级党组织的社会性别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组织论文,村级论文,乡村论文,妇女论文,性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6)01—0020—04
国家法律和地方法规都制定了保证农村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的相关规定,各地在推动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方面也有相当成熟的经验,为什么全国农村仍有相当数量的村委会是清一色的男性,被群众戏称为“和尚班子”①?以往研究往往将问题归咎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政策的缺陷,那么为什么在同一历史文化环境、同一政策环境下,有的村妇女在村庄治理中相当活跃,发挥了很明显的作用,而有的村妇女在村治领域相当沉寂,长期以来是“和尚”治村?显然,除了文化及政策等宏观原因之外,影响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还有其他因素。
根据我们长期的农村调研发现,在中国农村民主发展进程中,农村妇女村庄治理参与的程度与农村村级党组织建设有着直接并且深刻的关联。这是本文提出并且要加以论证的问题。
关于乡村治理中的村级党组织领导,姚锐敏等人有专著论述。他的结论是:村党支部对村委会的选举结果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有时候甚至具有决定性的影响②。近年来农村妇女入党难的问题也引起了政府相关部门、妇女组织的关注,有不少反映这方面情况的文章。但从社会性别意识的角度探讨乡村治理中的村级党组织建设与妇女民主参与的互动关系,通过政党领导和动员推动农村的社会性别平等和谐发展,改变农村妇女在乡村治理中被边缘化的现状,则是一个新的话题,目前这方面的成果还不多见。
一
中国共产党作为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支持并帮助妇女实现自己的特殊利益是其先进性的重要内容。妇女将自己利益的代表选入村庄治理决策结构中,是实现农村妇女特殊利益的一个渠道。丹哈特分析了决策机构中的各种群体代表性官僚的意义:“首先,尽管这些人可能不会在所有问题上代表他们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群体的利益,但他们确实可能在关键的问题上代表这种利益,从而抑制多数人可能的过分行为。此外,这些人的参与既有象征意义也有实际意义,因为它向其他人传达了决策中心向所有人开放的信息,而且,尽管我们不必期待官僚机构会自动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但我们可以影响这些机构。至少应该有人愿意倾听他们的意见。”③
农村妇女能否实现民主权益、在乡村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村级党组织的社会性别意识和社会性别能力是关键因素。作出以上判断,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村级党组织是村庄政治的领导核心,在村委会选举中对村民有很重要的动员力和号召力,是村委会选举的直接发动者、组织者和指挥者。
首先,尽管村委会选举采用了直选的方式,但村委会的选举工作包括主持村委会选举工作的村民选举委员会实际上都在村级党组织的领导或控制之中。在选举期间,每个村都要成立选举领导小组,选举领导小组一般都由村党支部书记担任组长,成员主要由村党支部的成员组成。领导小组要承担诸如选举工作人员的确定、选民资格的审查、候选人资格的审查等工作。这就明确了党组织在村委会选举中的领导地位④。除此之外,村级党组织对选举的控制和影响还表现在选举的各个环节中。
一是对村委会选举委员会的领导和影响。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选委会由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或各村民小组会议推选产生,并没有强行规定村民选举委员会中必须有村级党组织的成员,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经过民主选举所产生的村民选举委员会基本上都有村级党组织代表,大多数选举委员会的主任由村党支部书记(如果他不参加村委会主任的竞选)担任。2000年福建省村委会换届选举,福州等九个市12623个村中,有11653个村的选举委员会主任由村党支部书记担任,占总数的92.32%⑤。
二是村委会候选人提名。根据姚锐敏的研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实施以后,村级党组织失去了村委会成员候选人的提名权和确定权,从逻辑上讲,这种变化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村级党组织在村委会选举中的作用和影响。然而从最近的选举结果看,上述变化对村级党组织所造成的影响并不是十分明显。“将村级党组织排除在村委会成员候选人的提名与确定过程之外,目前并没有在事实上对村级党组织的参选目标造成很大影响。”⑥
三是由于村级党组织在村
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其政策宣传、舆论引导和倾向性意见,对村民的投票选择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在村委会选举中,比较常见的情况是,只要村级党组织倾向性比较明确的人成为正式候选人,其顺利当选通常不会有很大问题。
正因为村级党组织在村委会选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妇女能否成功当选村委会成员,村级党组织的支持与否便成为关键因素。根据相关的调研和观察,在村委会选举中,妇女落选,产生单性别的“和尚”村委会,村党组织应负有直接责任。“那些压抑的和令人受挫的社会状态之所以会存在,部分原因在于组织有意地使人们不能了解他们的需求所在以及社会关系的本质为何”⑦。
2002年,中国民政部在天津塘沽开展了“提高农村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比例政策创新示范项目”。塘沽试点主要是通过规定妇女当选比例的政策干预来促进农村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在文化和政策环境相同的情况下,该项目试点提供了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成功和不成功的观察样板。以妇女当选顺利和妇女参选失败的新城村和ZX1两个村作为观察对象,两村中直接领导选举的书记是关键。新城村书记对新政策的重视和落实,促使其在选举中基本落实了规程要求,从而保证了妇女的当选。ZX1村书记对新政策的强烈抵触和对女性的明显歧视, 使其领导的选举严重违反规程,从而导致了该村没有妇女当选。
在村委会选举中,村党支部的决定性作用是借助于对村民的影响力和动员力来实现的。其角色有些类似于阿吉利斯所说的“干预者”。阿吉利斯认为,在大多数组织发展计划中都涉及一个干预者,一般是一个来自组织之外、与客户系统一起来改进人际关系效率或帮助完成计划中组织变革的人。阿吉利斯建议,干预者的工作主要应该有三点:(1)帮助收集真实和有用的信息;(2)创造条件使客户做出知情的和自由的选择;(3)使客户自愿忠实于他们的选择。干预者的作用是促进个人与组织的学习,其结果是导致更为民主⑧。
二
在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政权的核心组织,党员是政权的基础。如果说西方国家中的工会、政党组织的会员、党员身份只具有很稀薄的参政分量,那么,在共产党国家中的党员身份却具有浓重得多的参政分量。女党员的人数比例显然可以被视为妇女参政程度的一个指标。在中国农村,因为党员所拥有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声望,以及村党支部每年发展党员的指标限制,使党籍成为稀缺的政治资源。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与妇女在其它资源分配方面的不利处境一样,农村妇女正遭遇入党难的问题。
据统计,目前中国有女党员1295.6万名,占党员总数的18.6%⑨。农村女党员的比例低于城市。以湖北省S市农村女党员为例,从绝对数看,农村党员总数54903人,其中女党员(含乡镇直部门)只有5848人,占农村党员总数的11%,大多数村女党员比例在5%—10%之间。从年龄结构看:35岁以下的977人,占女党员总数的17%;36—45岁1571人,占女党员总数的27%;46岁以上的3170人,占女党员总数的54%。从文化程度看:大专以上286人,占女党员总数的5%;高中、中专1598人,占女党员总数的27%;初中及以下的3916人,占女党员总数的67%。从入党时间看:全市69%的女党员是1992年前发展的,31%的女党员是1992年来发展的。从调查中我们看到,农村女党员现状存在着“三多三少”:即年龄大的多,年龄小的少;文化低的多,文化高的少;改革开放前入党的多,改革开放后入党的少,特别是农村女能人、女致富带头人入党的更少。
农村妇女入党难对妇女参与村庄治理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首先,拥有党员身份比普通百姓有更多的活动空间,为个人才能的展示提供平台,有利于提高个人在乡村的知名度。农村是一个半熟人社会,社会声望是农村社会重要的社会资本,是候选人能否当选的重要因素。其次,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农村发展女党员往往关注的是妇女干部,一般当了妇女干部,便可以获得党支部培养的机会。但在村委会选举中又偏重妇女干部的政治身份,人们在推选选委会成员、提名候选人、正式投票选举时,是不是党员,成为选民、村党支部、乡镇干部考虑的一个重要指标。这就陷入一个怪圈:只有当了女干部才能入党,只有入党才能当干部。在这种自相矛盾的怪圈中妇女往往被边缘化。其三,由于两委交叉任职,而女党员的人数少,且年龄偏大,符合条件的妇女少,选民可选择的范围小。其四,将妇女利益群体的代表推选进村庄治理的决策机构,需要一个妇女群体的支持系统。女党员是妇女群体支持系统的中坚力量,女党员人数少,这个支持系统就缺乏联系的纽带。其五,只有妇女广泛参与村治,才能体现农村民主治村的真实意义。毛泽东时代由于有比例政策的支持,农村基层组织中一般都有妇女代表,但这些进入决策机构中的农村妇女象征性意义大于她的利益群体代表的意义,其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妇女群体参与的基础。
三
为什么有的村党支部书记对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以及动员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的态度不积极?为什么有的村支部多年未发展女党员?其原因既有观念因素,也有具体功利性因素。
首先,基层党支部领导对男女平等的认识需要与时俱进。虽然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确定了男女平等的原则,但长期以来我们对男女平等的认识本身就隐含着性别的不平等,男女平等的标准是以男性作为衡量尺度,其途径不是要改变男性为主导的价值评价体系,而是要求妇女努力达到男性的标准。改变的重点在妇女。“只有妇女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并且在参与过程中提高自己的素质,她们才能真正地和男性竞争。我们从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呼吁全国妇女增强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不过,这种策略忽视了制度上存在的社会性别不平等,在追求平等的过程中将男性作为平等的标准。如此一来,制度的原则和标准不需要改变,男性的态度和做法也不需要改变”⑩。因此毛泽东时代,农村妇女参政的比例政策虽然得到落实,但是以妇女男性化作为价值取向,将妇女解放与男性化等同起来,社会并没有真正改变男强女弱的认识。在农村管理体制改革后,原来建立在男性主导价值基础上的对男女平等的认识,在新形势下演变为对妇女本身素质和能力的低评价,将妇女在村治决策领域的边缘化归咎于妇女自身的原因。因而在发展女党员、推选妇女进入村委会等问题上,态度不积极。
戴维·哈特曾对公平与公正作过区分,他指出,社会平等的首先含义是承认不同人的不同需求和利益,从而应该不同对待。“与公平对待所有人不同,平等强调的是给予处于最弱势地位的人更大的好处”(11)。由于历史的原因,妇女政治参与的起点低于男性,农村尤为如此。如果我们将平等与公平等同起来,将男女平等等同于性别中立,不考虑男女存在的现实差别,政策或态度不向弱势者倾斜,这种貌似的“公平”是在不平等基础上的“公平”,并没有真正体现社会公正。
其次,长期以来,基层党支部缺乏社会性别公平的教育,以致少于少数支部书记在性别平等问题上采取消极甚至是抑制的态度。改革开放以来,基层党组织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经济发展上,效率取向的价值观排除了对其他价值——如性别平等、妇女参与的关注,社会性别意识没有纳入到乡村治理的主流,使得一些农村党支部在发展党员中,把视野锁定在男性身上,而以种种借口把妇女排斥在党组织之外。虽然农村治理与公共行政有所不同,但同属于公共管理范畴,如果长期以效率作为单一取向,不考虑性别平等和谐发展,就有可能如弗雷德时克逊所说:“不能致力于改革、努力解决受剥夺的少数群体问题的公共行政可能最终会被利用来压迫少数群体。”(12)
其三,有些村支书不愿意选女干部、不愿意发展女党员,是为了在村委会选举时保护自己的小同盟,将发展党员作为稀缺资源来控制,进行资源交换。有的村前任村委会干部在任职期间为村完成缴纳税费任务而垫付了个人资金,未得到偿还,作为补偿,或是便于收回垫付资金,或是事先有约定,村支书都要力保这些干部留任。有的村支书与前任村委会干部有利益关系,因此对选村委会干部有自己明确的倾向性。为了保证自己所支持的人选在竞选中获胜,避免女性竞选者分散了票数,他们有可能利用自己在村庄的影响力和控制能力造成妇女候选人落选的局面。
其四,对村党支部成员在组织选举过程中的违规或不作为,缺乏制约手段。如上所述,由于村党支部在组织选举中的核心地位,其影响妇女当选的机会和程度很大。根据观察,村党支部在组织选举中影响女候选人当选与否的方法多种多样,例如,村支书在政策宣传上有意淡化支持妇女当选的政策;通过控制选举程序来实现自己的意图,致使女候选人落选,如不强调选委会中要有妇女参与;在提名候选人程序中就将妇女排除在外;妇女进入候选人名单后,临时改变程序或选举方法等等。由于对村党支部成员在组织选举中的违规和不作为缺乏制约,而选举规程或选举办法又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的余地,村党支部成员的社会性别意识就成为很重要的影响因素了。
四
男女平等和谐发展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之一,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也是衡量一个政党先进性的标尺。推动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实现妇女的民主权益,建立表达妇女的利益的渠道,加快发展农村女党员,将优秀的妇女吸纳到党组织中来,通过女党员来发挥组织、联系和带动妇女的发展的作用,是农村党组织保持先进性,建设农村和谐社会,实现性别平等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笔者建议:
第一,将社会性别平等纳入正在中国农村展开的党员先进性教育内容中,通过在基层党组织和干部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教育,逐步使社会性别平等意识成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乡村治理的主流,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社会性别能力,推动中国农村妇女在村庄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二,采取得力措施切实解决农村妇女入党难问题。各级组织部门在下达入党指标和积极分子培养指标中应明确规定妇女比例,在分配名额时注重向农村妇女倾斜。当前,重点在农村女能人、女致富标兵中间选拔培养一批思想进步,愿意参入村庄治理的妇女加入党的组织,为扩大妇女参政比例培养一批新生后备力量,以改变在村两委会换届选举中妇女干部后继乏人的现状。
第三,积极探索新的办法和途径确保农村优秀妇女进入村两委会领导班子。针对往届村两委会换届选举中妇女落选问题,建议在以后村两委会换届选举中,试行按性别推荐村委会候选人等做法。如,去年8月, 湖北广水市在城郊乡星河村进行“两票制”选举村委会的试点,即在推选村委会选委会成员、村民代表和村委会候选人时,分别采用了男性推荐票、女性推荐票和在正式选票上明确标明村委会成员必须至少要有1名以上女性的做法,收到了明显成效。
第四,将农村妇女民主参与的水平纳入到农村党支部工作考核指标中,对在促进农村妇女全面发展方面不作为的党组织领导,采取明确的制约措施。
注释:
① 2002年选举统计资料显示,全国农村村委会的女性成员比例大约在16.2 %左右,有的省女性成员比例只有6%。
②⑤⑥ 姚锐敏:《乡村治理中的村级党组织领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8、94页。
③⑦ 罗伯特·丹哈特:《公共组织理论》,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190页。
④ 金太军、施从美:《乡村关系与村民自治》,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页。
⑧ Argyris,Chris,Intervention Theory and Method:A Behavioral Science View.Reading Mass:Addison Wesley,1970.p.12.
⑨ 王黎:《全国共产党员总数超过6960万学生党员增幅明显》,《新华网》2005年5月23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5/23/content_2991018.htm。
⑩ 杜洁、娜芝琳·康季:《社会性别平等与消除贫困在中国:发展政策与实践相关问题》,《社会发展资源中心网》2005年3月16日。http://www.sdrc.org.cn/file/2005316222246873.pdf。
(11) Hart,Davit K,Social Equity Justice,and the Equitable Administrator.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January-February 1974.p.3.
(12) Frederickson,H.George,Toward a 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In Toward a 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The Minnowbrook Perspective,edited by Frank Marini,San Francisco:Chandler,1971.p.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