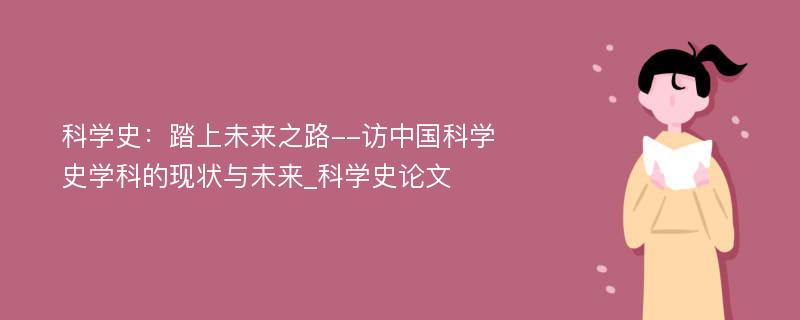
科学史:踏上未来之路——关于国内科学史学科现状与未来的访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未来论文,科学论文,之路论文,史学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史在中国是一个已经确立了地位但还没有经过充分发展,离成熟还很遥远的学科。与先进国家相比,我们的学术积淀还不够深厚,关于中国科学与技术史的研究还停留在史料考辩与理性重建阶段,由内史向外史的过渡与综合还有待时日,思想史和社会史取向的科学史研究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中国今天的科学史学科处于怎样一种状况呢?
刘钝教授认为,科学史学科在中国已经基本确立了学科地位。这主要表现在:第一,1997年,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制定的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中,科学史被定为理学类一级学科,经过多年发展,若干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已建成了一批科学、技术和医学史专业的博士点和硕士点;第二,中国科学史学科拥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这样的国家平台,这在国际科学史界也是不多见的;第三,1999年以来,在若干高校出现了系一级的科学史建制单位;第四,中国科技史学会现有1200余名注册会员,表明科学史学科建设在中国已有相当规模;第五,科学史学科已形成了学术共同体所认可的的奖励、学报、会议、出版规范或制度;第六,中国科学史学科的国际化正在加速。
但是,刘钝同时指出,科学史学科在中国的发育还很不充分,离成熟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以西方作为参照系,科学史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就开始了建制化的历程,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到五十年代获得了普遍的社会认同。而中国的科学史到五十年代末才刚刚开始踏上建制化之路。更不容忽视的是,与先进国家相比,我们的学术积淀还不够深厚,关于中国科学与技术史的研究还停留在史料考辩与理性重建阶段,由内史向外史的过渡与综合还有待时日,思想史和社会史取向的科学史研究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关于西方科学史和其他非西方文明科学史的研究还不具备与国外同行对话的能力。刘钝承认,作为中国科学史家,经常会在如下的问题面前感到难堪:为什么不是某个中国学者而是英国人李约瑟首先写出了蜚声世界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他介绍说,研究所的同事们一直在组织编撰30余卷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首批七卷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今年还可望出版四至五卷,可以相信,中国人撰写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完璧将在李约瑟生前设定的7卷34 分册的宏伟目标全部完成之前诞生。记者问他,我们的版本能够超过李约瑟版吗?他说在没有见到整个冰山之前不好妄评,但坚信自己11年前发表的一篇短文中的基本判断仍然适用,那就是“(李书)的宗旨在于解决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这一重大历史课题,这就决定了他的著作具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恢宏气势,这是国内一般科学史作家不能比拟的”。
刘兵教授也坦率地指出,即使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虽然国内在语言、史料占有和对文化传统的熟悉方面占有天然优势,但在研究方法、史学观念等方面,与人家就“没法比了”。
江晓原教授介绍说,从1978年至今的二十年间,中国的科学史学科,先是在“科学的春天”里借着东风一度非常繁荣,但接下来我们就目睹了她在市场化过程中的日益困顿,直至度日如年。市场化过程也许是一个社会不可避免的急功近利的时代,这个时代只有那些“有用”的东西——实际上就是能赚钱的东西,才会受人重视,才会吸引各界精英蜂拥而去。而科学史只能越来越被人忘却,人材零落,后继乏人,不少硕士点被取消,有的博士点也岌岌可危,不得不用各种变通之法去“力保”。
刘钝也感慨地说,中国科学史学科目前最大的危机实际上还是生存的危机。近年来,国家科研体制的改革不断推进,他们所属的中国科学院也处于不断的调整中,特别是中国科学院提出的凝炼目标、精简人员的要求,使他这个责任人一直提心吊胆。他说,虽然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在今年科学院以分类定位为核心的结构调整中通过验收,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达摩克利什之剑”仍然高悬在头顶。
科学史在中国发生建制化是在缺乏充分社会认知和学术积累的情形下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开始的,由于缺乏学术内部的驱动而使这个学科建设伊始就先天营养不足。
为什么科学史学科在中国的发育并不“茁壮”呢?为什么这棵学术之树会显得营养不良,未能结出饱满的果实呢?
刘钝认为,科学史在中国发生建制化的过程不同于西方,它是在缺乏充分社会认知和学术积累的情形下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开始的,由于缺乏学术内部的驱动而使这门学科建设伊始就在理论水平和研究方向上有所欠缺。从学术目标来说,1957年挂牌成立的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定位在“总结祖国科学遗产,总结群众和生产革新者的先进经验”,对科学史的理解显然还不够深入。此外,几十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与国外科学史界缺乏交流,学术空间相当封闭,这些原因都直接导致了中国科学史学科未能迅速地成长起来。
江晓原则认为,除了历史的原因,传统观念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某种程度上,几十年来,科学史学科的主要功能似乎主要是服务于爱国主义教育。科学史似乎就是编写“中国的世界第一”之类的“成就年表”。但是我们知道,真正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只能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而那些“中国的世界第一”之类的“成就年表”往往并非事实。同时,这样做也损害了科学史学科的利益,降低了学术的品格。
科学史在中国正步入一个再建制化的阶段,通过这种再建制化,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整体实力与研究水准有望得到提升。
令人高兴的是,科学史学科在世纪末的1999年显露出了新的生机,好消息不断传来——
·3月份, 我国第一个高校系一级科学史建制单位——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成立。
·6月份,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在科学院以分类定位为核心的结构调整中通过验收,并将进入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的试点。
·7月份,中国科技大学科学史与科技考古系成立。
·10月份,“共商科学史发展战略”研讨会在北京香山别墅举行,这可以说是中国科学史界第一次自觉的发展战略研讨会。
·10月份,江西教育出版社大型科学文化书系“三思文库”出版了“科学史经典系列”的首批3种图书, 预示着国外科学史名著译介极度缺乏的状况将有所改观。
……
这一切都传达出一个信息:科学史学科“否极泰来”的时刻已悄悄来临了。正如江晓原教授在上海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成立大会上所表达的:“最近国内五六个著名大学中,都有学者在积极谋求建立科学史系,这一现象决不是偶然的。社会生活的改变,文化生活的发展,已经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科学史的价值,领略到科学史的迷人魅力。”对于他领导的上海交大科学史系的成立,他借用证券业的术语评价道。“这是(科学史)走出阶段性底部的第一根阳线”。
刘钝则归纳说,科学史在中国正步入一个再建制化的阶段,通过这种再建制化,我国科学史学科的学术共同体才可能发展壮大,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整体实力与研究水准才能得到提升。
弥补差距的最有效、最便捷的办法,就是先实事求是地承认自己的不足,先去虚心地学习别人的优秀成果,尤其是学习经典之作。
当被问到对于如何加快科学史学科的发展的看法时,三名被采访者显然都对这个问题深思熟虑过,接过话头侃侃谈了起来。
江晓原教授认为,要缩小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差距,唯一的办法是扎扎实实地工作,其中包括研究成果的积累、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生的培养、课程的建设等等,此外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科学史研究著作和原始著作的翻译和引进。他说,近十年来,我们大规模地介绍引进科学哲学在西方特别是当代的研究进展,打开了一扇学术交流的窗口,大大方便了国内学界。与科学哲学著作的翻译出版相比,翻译和出版界对科学史著作的忽视相当惊人。比如,科学思想史学派的领袖人物亚里山大·柯瓦雷在我国甚至鲜为人知。近来他看到了江西教育出版社新出版的“三思文库·科学史经典系列”的首批推出的三种:C·C·吉利思俾著的《〈创世纪〉与地质学》,I·B·科恩著的《牛顿革命》, 皮特·J·鲍勒著的《进化思想史》,他认为这对学术界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刘兵教授认为,弥补差距的最有效、最便捷的办法,就是先实事求是地承认自己的不足,先去虚心地学习别人的优秀成果,尤其是学习经典之作。作为“三思文库·科学史经典系列”的主编,刘兵教授在此套书付梓之际明确地提出要“补经典之课”。他认为,在学术上,积累是非常重要和必不可少的,赶超不是任意的,有些阶段是不能略过的,如果该补的课不补,必然导致先天营养不良,后天底气不足。在有选择的补课中,自然补经典之课是首位重要的。
刘钝教授也认为,关起门来搞考证,中国科学史是没有希望的,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打开面向外部的大门,研究所要按照国家科学史研究基地的设计吸纳国内外的优秀学者。明年1月份, 他将借赴美开会之机拜见当今国际科学史界的两大重镇C·C·吉利思俾和I·B·科恩,并将带去新出版的他们著作的中文版《〈创世纪〉与地质学》和《牛顿革命》。刘钝介绍说他们正在筹划设置一个“竺可桢讲席”,旨在邀请国外第一流的科学史家到中国讲学,而首位理想的讲席教授应该是吉利思俾或科恩这样的重量级人物。
关于研究和学习科学史的意义,在学术界确实存在着不同看法,争议比较大。但学界的这些争议并不妨碍我们认识科学史的重要性。
本世纪初,伴随着西方科学的涌入,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史研究也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多世纪以来,虽然赛先生在中国的命运也颇曲折,但最终还是在主流话语中获得了相当高的地位(至少在表面上);而对于与他结伴而来的科学史学科来说,情况却没有那么乐观。首先,公众大多并不了解科学史学科有什么意义;其次,政府机构也多把科学史视为无用的学问重视不起来。
多年以来,有些学者一直在为中国的科学史研究寻找意义,结论之一是它能够揭示我国古代人民的聪明才智,揭示他们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增强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力。江晓原指出,这样的理解使纯客观的学术研究变成了充满功利之心的求证,必然大大扭曲这门学问。
刘钝则表示不能完全认同江的看法。他说,把科学史作为一门依赖个人兴趣进行的学问,作为增加人类知识的纯粹的学术,他毫无异议,那也是他内心的理想与追求,但是,把这种追求绝对化也有失偏颇。当今多数的科学史家都同意科学史有人文教化的功能,把爱国主义包含在人文教化中对科学史的生存是必要的,从学理上也没有大谬不然之处。
据了解,在中国科学院的最新规划中,科学史学科将被纳入知识创新工程,具体来说就是科学史研究要为国家制定科技发展战略服务,要创建国家科学史与科技宏观战略研究基地。对此,学术界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刘钝认为,科学史完全可以也应该承担这个任务,当今中国科学史家的生存空间不同于古希腊哲人,也不同于萨顿他们,我们是国家俸禄的享用者,坚守道德底线的领取俸禄者并不一定是御用史学家。他说,我们可以从世界强国的发展历程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也可以从周边后发国家和地区寻求启迪和借鉴。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过去50年乃至数百年中国科技发展的回顾,通过对古往今来世界范围内科学知识的进步、科研体制的演变、科技政策的制定以及科技重心的转移等方面的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以便对中国科技未来发展整体态势的分析提供有益的参考。他说,历史感是一种高级的思想体验,只有具备历史感的战略家才是伟大的战略家,科技战略研究和决策离不开历史学家。
与之针锋相对的,江晓原则认为,科学史虽然也可以为科技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某些帮助,但这不应该是科学史的主要任务。他说,我们总是要求一门学问“有用”——而这种“有用”通常又总是在急功近利的意义上的。这方面我们吃过的亏实在太大了!我们应该认识到“无用之用,可为大用”的道理,这已经被科学发展的历史多次证明过了。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当初有什么“用”?再说,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历史学家真能够预知未来。指望科学史专家能够预知科学的未来,也难免要失望。要求科学史主要为国家制定科技发展战略服务,并不是一个合理的任务。
刘兵教授则指出,关于研究和学习科学史的意义,在学术界确实存在着不同看法,争议比较大。但学界的这些争议并不妨碍我们认识科学史的重要性,因为也还有一些观点是比较一致的,如学习科学史可以加深对科学自身的理解、弥合自然科学和人文学术的鸿沟等。总之,对于各种层次的人,学习科学史都会有好处,都会有收获,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其实目前的争议主要在于科学史的理想发展目标和具体生存现实环境之间的矛盾。为了科学史能在中国生存,对理想目标作少许调整以利生存,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不能把理想目标给忘了,而且要知道这种妥协是有代价的,否则,即使科学史在中国生存了下来,也仍然可能长成一个怪物。
对新世纪的三个希望
当“科学史之父”萨顿于20世纪初期以满腔热情投身于科学史学科的建制化时,他曾经以公理的方式断言:“科学史是唯一能够说明人类进步的历史”,因而,科学史在所有的历史中就是最核心、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同时,他也预言了科学史在促进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整合方面的意义。
今天,处于新的世纪之交,中国的科学史学者对这门学科有哪些期望呢?
刘钝认为,20世纪,由于对科学的神话,科学史长久地匍匐在科学的神龛前。他希望,在21世纪,科学史家应该带着一种觉醒的独立人格与历史使命感进入他们的研究领域;中国的科学史家更应该强化自己的批判意识,因为中国学术最大的弊端就是理性批判精神的匮乏。
江晓原认为,当年,被誉为“科学史之父”的乔治·萨顿博士,将科学史视为沟通自然科学与人文学术的最好桥梁。这一点现在在国内也日益被人们所理解。在我们培养为21世纪服务的文理兼通人才的努力中,科学史无疑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
刘兵认为,虽然科学史在近年来获得了令人欣喜的发展,苗头不错,但要想达到国外的水平和规模,不是在短期内能够办到的。在中国现实的情况下,只有把目光指向更长远的未来,作更长期奋斗的打算。当然,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