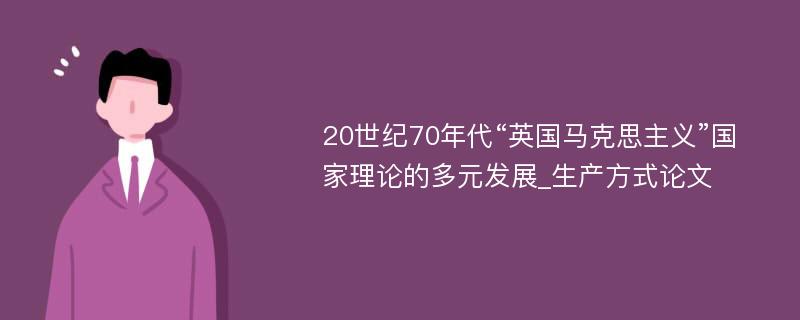
20世纪70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多元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年代论文,理论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7年,加拿大著名政治理论家麦克弗森向英国学界提了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国家理论吗?”他的回答是:接受现行自由民主制度的人并不需要国家理论,反对或者不相信这种制度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则需要①。麦克弗森之所以会在这个时候抛出这个问题,固然有为自己的新著《自由民主的生活与时代》做宣传之意,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真切地感受到,在自己曾经求学的英国,边缘化多年的国家理论已经因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而获得强劲复兴!历史地看,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离我们最近的一个“黄金时代”:旷日持久的“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1969-1979)激发了人们对国家理论久违的兴趣,欧陆思潮的大举来袭则使“英国马克思主义”阵营获得了多样化的理论资源,进而形成了多元发展的繁荣局面。然而,“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是如此耀眼夺目,以至于在它的映照下,那种多元发展格局都黯然无光、难以识别了。因此,在40年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超越“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图绘20世纪70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多元发展格局。 一、“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的思想史效应 “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是指1969-1979年间“英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密里本德与希腊裔“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普兰查斯围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本质和方法论发生的争论。历史地看,这场争论本身并无更多新意,争论的双方也缺乏充分的相互理解和实质性的理论交锋。不过,由于它是在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欧陆思潮大举进入原本相对封闭的英国,与英国本土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发生剧烈冲撞这个时代背景下发生的,所以,它强烈吸引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关注,加速推进了各种欧陆思潮和学术流派的传入与融合,有力推动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研究的理论转向,激发出了极为显著的思想史效应。 关于“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近40年来英美学界已多有评论,其中尤以美国学者巴罗的思想史考订分析最为翔实②。重新审视这段已经非常清晰的思想史,人们往往会赞同当代西方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家雅索普的观点:这场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论其实更多地像聋子之间的对话③。说到底,密里本德和普兰查斯是根本不在一个理论频道上的两个理论家!④首先,他们分属两个截然不同且此前从无交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1940年,密里本德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比利时逃难到英国,并在相对封闭的英国语境中接受学术训练、成长为一名本土化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他在理论上深受英国伦理社会主义和经验论哲学传统的影响,主张在分析、解决具体的英国问题的过程中运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反对抽象的理论建构。普兰查斯出生于希腊,20世纪50年代后期流亡法国巴黎,进入阿尔都塞的圈子,成为形成中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一员。尽管不是哲学家,但普兰查斯具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特征:反对人本主义、主张多元决定论、注重方法论且理论化(抽象化)程度高。这些都与“英国马克思主义”迥然有别。密里本德对普兰查斯早有耳闻,对他的著作甚至有所期待⑤,但在“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爆发之前,他们所从属的理论传统却并无直接交往。其次,他们与工人运动的关系不同。作为第一代英国新左派的一员,密里本德是属于英国工人运动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对英国工人阶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总的说来他坚持英国工人阶级依旧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同龄的第二代英国新左派一样,普兰查斯是为了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他们日益怀疑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在未来社会主义道路上的领导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传统工人阶级政治的批判者。再次,他们思考国家问题的理论出发点不同。在1877年为马克思写的传记词条中,恩格斯指出,对马克思而言,“在全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仅仅是社会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⑥。这一观点后来被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继承。密里本德同样继承了这一观点,强调“斗争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核心”⑦,因而也是分析国家问题的核心和出发点。普兰查斯则是在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的思想启蒙下走向政治学研究的,对他而言,由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理论的各个层次和要素构成的“生产方式”的“多元决定”⑧,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石之一,也是研究国家等特殊问题的出发点。照理说,密里本德和普兰查斯的理论如此南辕北辙,加之一个在英国、一个在法国,原本不应当“相遇”,即便“相遇”也不应当发生大的理论碰撞。然而,当1969年他们偶然“相遇”时,第二代新左派正积极引入欧陆激进思潮以实现对第一代新左派的理论清算,而普兰查斯正是佩里·安德森等第二代新左派心目中新的理论典范!于是,在代际冲突的背景上,偶然的“相遇”就演化为了必然的、不断扩大的“相争”⑨,从而深刻影响了整个70年代英国新左派的理论走向。 “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所呈现的思想史效应无疑是整体性的。首先,伴随其发生,佩里·安德森领导的《新左派理论》杂志加大引进欧陆激进思潮的力度,使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大陆国家的当代激进思想成批量、大规模地进入英国,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思想的相对封闭状态。其次,在它的直接推动下,结构主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英国流行,形成了一个跨学科的“结构主义转向”。70年代初,第二代新左派迅速集结在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此后,在它的示范下,历史学、文学理论、社会学等领域都发生了类似的争论,促进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思想交换、融合和再生。 同时,“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也更深刻、更直接地改变了70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本面貌,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较之于密里本德《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1969)所定义的起点状态,出现了三个显著的“转向”。第一,转向历史中的国家。密里本德关注的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努力超越具体国家的差别,凝练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本质。“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则让第二代新左派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存在(国家形式)是具体的,且不是仅仅通过一般本质(国家类型)就所能完全解释其形成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此,那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怎样呢?在既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传统的推动下,第二代新左派由此转向历史中的国家,试图描述欧洲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类型及其一般演化轨迹。在这个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工作是由佩里·安德森在70年代初期完成的。第二,转向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逻辑。1969年创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大会”是英国左派经济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第一个松散型同人组织,其中既有本土的新李嘉图主义者,也有德国资本逻辑学派的支持者、法国调节学派的支持者。“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激励该组织成员聚焦国家问题展开对话、争鸣,其中主导性意见是认为应当基于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来思考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形成与作用。随即,约翰·霍洛维、索尔·皮乔托以及西蒙·克拉克基于资本与阶级的冲突斗争,提出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第三,转向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批判。70年代初,英国的“结构主义转向”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与此同时,福柯登上法国当代思想的新王座,引领结构主义进入后结构主义,其对权力的微观政治学批判要求马克思主义者作出回应。在这个方面,普兰查斯这个非英国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率先作出回应,于1978年出版《国家、权力与社会主义》一书,公开了自己的新思考,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在80年代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动力。 二、佩里·安德森“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前资本主义国家理论 至少在1982年辞任《新左派评论》主编、前往美国的几所大学任历史学教授之前,佩里·安德森都是一名葛兰西意义上的有机知识分子。他以《新左派评论》为阵地、以笔为剑,坚持用理论介入现实,用思想引领左派学术的发展,蔑视、拒斥脱离实践的象牙塔式学术研究。不过,1974年,他却同时推出了两部“砖头”般的大书《从古代向封建主义的过渡》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系统阐发了自己关于前资本主义时代欧洲国家的形成方式与多样化类型的观点,在英语世界引起热烈反响,一下子就确立了自己的历史学家身份以及在20世纪历史社会学发展史上的地位。那么,安德森为什么会在此时转向前资本主义的国家理论建构呢?这就需要从安德森作为新左派知识分子的理论关怀、他与爱德华·汤普森当时的理论争论以及“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学术传统中去找寻答案。 1962年,安德森接手陷入危机的《新左派评论》出任主编。在他的领导下,《新左派评论》展现出了与爱德华·汤普森等第一代新左派主导时期截然不同的编辑取向:一是更具国际视野,特别关注第三世界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二是更加政治化,尤其重视国家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三是更加理论化,积极致力于从卢卡奇、葛兰西、萨特等欧陆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中汲取理论和方法资源。安德森很清楚,自己这种以国家为中心、“自上而下的历史观”和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所倡导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自下而上的历史观”相比照构成了反题。对此,他的回答是:“只要阶级依旧存在,国家的建构和瓦解就是生产关系基本改变的标志。‘自上而下的历史’——有关阶级统治的复杂机制的历史——的重要性就不亚于‘自下而上的历史’。实际上,如果没有前者,后者将是片面的历史(哪怕是更好的那一面)”⑩。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者的革命目标之一就是消灭国家!既然如此,安德森为什么不直接关注现实的资本主义国家,舍近求远研究前资本主义国家呢?说到底,这是因为历史学出身使得安德森习惯于“让历史告诉未来”、“从历史的灰烬中扇出革命的星火”,在他看来,只有搞清楚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起源和秘密,才能真正了解和掌握爆破现存资本主义国家的有效方法。所以,他的国家研究计划其实有四卷,除了前述两种著作外,还将分别考察“从尼德兰起义到德国统一的一系列资产阶级大革命运动,以及经历了漫长而隐蔽的演变最终从前述资产阶级革命中脱颖而出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11)。 安德森接手《新左派评论》时,英国新左派运动正因为工党的右倾化而陷入低潮或者说“危机”。1964年初,安德森在《新左派评论》发表长篇文章《当前危机的起源》,提出英国当前危机的根源不在现代,而在于17世纪以来英国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17世纪英国革命不彻底,它只改变了英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没有改变它的上层建筑,结果依旧是土地贵族在统治英国;因为17世纪革命不彻底,并且是以宗教斗争的形式进行的,所以,英国资产阶级从来没有形成革命的意识形态;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导致不成熟的工人运动,因此,英国工人阶级既缺乏革命传统,又无法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12)。安德森的这篇文章在第二代新左派中引发广泛共鸣,但遭到第一代新左派的批评。汤普森于次年发表《英格兰的特性》一文进行回应和批判,强调英国具有自身独特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讽刺安德森试图用一种抽象的普遍发展模式来臧否英国道路(13)。应当讲,在与汤普森的这一轮争论中,安德森处于下风(14),但他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只是苦于找不到新的论证视角和方法。而普兰查斯1968年出版的《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则让他一下子发现,资本主义的国家形式是“多元决定”的,因而是多样化的、复数的,既然如此,国家形式就可以进行比较,进而区分出成熟与不成熟!也就是说,普兰查斯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安德森回应汤普森的批评提供了新的方法武器,同时也刺激他将自己关于前资本主义国家的观点系统地表述出来。 另一方面,在1946年多布出版《资本主义发展研究》后,关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探索,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重要课题之一。1964年,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片段英译出版,同时还收录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相关内容,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6封相关书信,从而使马克思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理论第一次较为完整地呈现在英语世界,有力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开展。此后,在《新左派评论》的大力推动下,《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英文全译本于1973年出版,随即将英语世界关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国家形态的研究推向高潮。安德森关于西欧前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是这一学术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古代向封建主义的过渡》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出版后,迅即在历史社会学科引发热烈反响,此后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社会学的新经典(15)。在历史社会学视域中,《从古代向封建主义的过渡》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更多地呈现出与马克斯·韦伯、埃米尔·涂尔干甚至是塔尔科特·帕森斯等资产阶级主流社会学家的理论亲缘性,而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属性却被极大地遮蔽了。事实上,在《从古代向封建主义的过渡》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中,安德森力图实现的是将普兰查斯的生产方式“多元决定”论与马克思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相结合,建构一种“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前资本主义国家理论。这种国家理论大体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安德森提出向封建主义过渡这个新问题,并建构了欧洲从古代社会(国家)向封建主义(国家)过渡的“多元决定”理论。在1946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中,多布基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分析范式探讨了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问题。该书出版后在英美引发长期争论,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作为这场论战的敏锐观察者,安德森意识到,之所以人们在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有一个前提性问题,即向封建主义过渡或封建主义起源问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主题化研究(16),而他的《从古代向封建主义的过渡》就有意填补这个理论空场。在安德森看来,欧洲封建主义(国家)的诞生具有偶然性,实际上是罗马的奴隶制与日耳曼的原始部落公社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碰撞、融合的妥协产物:“欧洲的封建主义起源于一种‘灾难’,原先的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同时崩溃,那些崩裂出来的要素的重组恰恰使封建主义的综合成为可能,因此,封建主义总是具有一种混合的特点”(17)。日耳曼人对罗马帝国的入侵拉开了欧洲封建主义过渡的序幕,最终西欧、北欧、东欧以不同的方式完成各自的过渡。为什么这种“过渡”会呈现多样化的复数形态?安德森认为,这是因为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制形式与发展水平、城市的发育程度、国家政治形态(王权、贵族、教会的力量对比与平衡方式)等都参与到了决定“过渡”的过程中,同时战争、灾荒等外部偶然因素也对“过渡”产生了影响。简言之,安德森是依据普兰查斯的生产方式“多元决定”论,统筹考虑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理论等因素在向封建主义(国家)过渡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具体的决定性作用,建构出了一种主要适用于西欧的向封建主义(国家)过渡的理论。 第二,安德森聚焦向资本主义过渡过程中的绝对主义国家,就绝对主义国家的性质及其形成机制给出了自己的解答。绝对主义国家或绝对君主制是16世纪以后欧洲陆续出现的一种过渡性的国家类型。在这种国家类型中,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处于相对政治均势,并且在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绝对主义国家会迅速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在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争论中,绝对主义国家的性质(资本主义的还是封建主义的)及其形成机制成为焦点之一。在《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中,安德森就这两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他认为,文艺复兴之前,封建主义生产方式陷入困境、达到发展的极限,这使得封建主义之前的古代生产方式以某种形式得到复兴,并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发生碰撞和融合,绝对主义国家乃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这两种生产方式偶然相遇的产物(18)。具体地说,文艺复兴以来,势均力敌的城镇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发现,原本属于古代生产方式的罗马法可以满足双方的不同需要: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私有财产权,对封建贵族来说则是国家集权,于是基于这个法律凝聚点,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就与前封建主义的政治和法律上层建筑相结合,再造出了绝对主义这种新的国家形式:“军队、官僚集团、外交和王朝就构成了一个统治整个国家机器、控制其命运的坚固的封建复合体。绝对主义国家的统治就是向资本主义过渡时代封建贵族的统治。它的终结标志着其统治阶级的权力危机:资产阶级革命的来临,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诞生”(19)。 第三,安德森提供了一种绝对主义国家形式的多元冲突决定理论,并据此建构了欧洲绝对主义国家的地区类型学。在安德森看来,君主与贵族的权力关系决定绝对主义国家的形式,而这种权力关系又是君主、贵族、资产阶级和下层民众的冲突与斗争的结果;同时,君主、贵族、资产阶级和下层民众的力量对比、相互关系、冲突与斗争方式,又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此消彼长发展过程紧密相连(20)。基于这种多元冲突决定理论,安德森把欧洲绝对主义国家划分为西欧、东欧两大系列六种类型:西欧的均衡型(法国)、君主强势型(西班牙、瑞典)、贵族强势型(英国);东欧的均衡型(普鲁士)、君主强势型(俄国、奥地利)、贵族强势型(波兰)。总的看来,安德森较为欣赏均衡型的绝对主义国家(法国、普鲁士),因为,在这种国家形式中,与旧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贵族和绝对主义国家将被彻底毁灭,在它们的废墟上,将诞生更彻底的资产阶级和更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此相比,在贵族强势型绝对主义国家基础上诞生的,只能是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以及工人阶级)和不彻底的资本主义国家。——安德森显然是在影射英国! 第四,安德森认为,前资本主义国家也具有某种程度的相对自主性。普兰查斯认为,作为制度化权力的资本主义国家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具有相对于权力集团的阶级与派别的自主性(21)。现在人们普遍承认,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具有更高的相对自主性。那么,前资本主义国家是否具有相对自主性呢?不管是在《从古代向封建主义的过渡》中,还是在《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中,安德森都没有直接提出这个问题,不过他的立场还是十分清楚的:国家一旦形成,就成为一种客观的制度化力量,客观地参与历史进程并发挥自己的作用;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尚未充分发育,很多情况下甚至难以察觉它的存在;作为一种过渡形态,绝对主义国家出现了独立的文官系统和税收系统,它们的存在表征着向韦伯意义上的合理化的法治机器的转变(22),国家的相对自主性由此开始逐步发展起来。 三、“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大会”资本-阶级冲突论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 创立于1969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大会”(以下简称“大会”)是英国战后第一个左派经济学家同人组织,虽然至今仍然开展活动,但上世纪70年代无疑是其最具思想活力的鼎盛时期(23)。“大会”的倡议者以及最初的参与者是一些激进的经济学研究生,很快来自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激进研究生也加入其中,使之成为一个超党派的、跨学科的左派青年学者论坛。作为在1968年学生运动爆发后开始学术生涯、走上社会舞台的一代人,“大会”的核心成员们具有如下代际特征:第一,他们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虽然批判工党的威尔逊主义,但肯定工人阶级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主体,因而坚持把阶级和阶级斗争作为思考社会主义问题的轴心;第二,他们的思想成长受到当时正不断走向高潮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研究的深刻影响,把马克思基于生产方式分析的资本批判理论作为批判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的理论基础;第三,由于那个时期各种欧陆思潮大举进入英国,所以,他们的思想往往比较多元,也比较多变,通常会根据自身的需要“接合”多种资源,由此形成了自己的思想风格。由于存在上述代际特征,“大会”内部充满张力与活力,他们先后就资本的国际化与区域发展、价值理论与价值转型、国家、性别、后福特制等主题进行过热烈争论,产生了不少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其中,与“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同一时期开展的有关国家的争论,在70年代后期就结出了一个有影响的成果,即资本-阶级冲突论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该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约翰·霍洛维(时为爱丁堡大学研究生)、索尔·皮乔托(时为牛津大学研究生)以及西蒙·克拉克(时为埃塞克斯大学研究生)。 1978年和1991年,约翰·霍洛维和索尔·皮乔托以及西蒙·克拉克分别发表长篇述评文章,回顾和评论了有关国家争论的起源及资本-阶级冲突论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的形成过程(24)。由此,我们可以廓清以下思想史事实。 第一,国家争论源于对苏联和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理论的双重拒斥。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苏联和欧洲社会民主党提供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解释:前者基于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的经济还原论解释,把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理解为垄断资本的直接工具,视其为垄断资本与国家权力的融合;后者反对经济还原论,强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有高度自主性,已经从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独立出来,成为一个中立化的因而可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利用的政治实体。在“大会”成员看来,前者机械教条,后者虚幻幼稚,都必须坚决予以抵制和批判。 第二,德国的资本逻辑学派则力图基于《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资本批判理论实现对前述两种传统左派理论的超越,因而在正积极致力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研究的“大会”成员中引起强烈反响。70年代初,前述两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理论在德国展开论战,当时德国新左派的主流传统即法兰克福学派的传人们基于不同的立场介入这场论战:已开始向右转的哈贝马斯及其学生基于合法化理论强调了福利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其思路与社会民主党传统接近;与此同时,法兰克福学派中一批更年轻的传人们则秉承阿多诺50、60年代所强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力图基于《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资本批判逻辑阐释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功能与形式,从而形成了所谓的资本逻辑学派。在资本逻辑学派看来,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本质要素与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式与功能;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一旦形成就作为一种具有客观独立性的自主性要素参与到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并对这一过程发挥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对于“大会”成员来说,资本逻辑学派不仅提供了一种超越前述两种传统左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理论的替代方案,而且其方案还直接源于他们正关注的《资本论》及其手稿!因此,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都迅速转向资本逻辑学派,把该学派的资本批判逻辑作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基础。 第三,“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提升了“大会”成员的方法论意识,拓展了他们的理论视野,使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出身的成员取代经济学出身的成员成为论战的主力军。最初参与有关国家争论的“大会”成员大多出身经济学,他们或是新李嘉图学派的追随者,或是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立场的正统派。随着“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的不断深入,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出身的成员们日益成为争论的主力军,而这些成员大多与“大会”的“住房与劳动过程小组”有关联。通过争鸣,他们逐渐认识到: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问题的核心是结构(资本)与主体(阶级)的关系,如果阶级斗争无法突破结构(资本)的强制,社会主义就无法成为现实;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理论既要坚持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又要反对经济还原论;既要充分承认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又要警惕把国家理解为完全独立的政治实体;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功能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等等。总之,他们认识到,必须基于资本批判逻辑,“接合”更多的理论资源,方才能够建构出一种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理论。 1971年,“大会”创办了不定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大会通报》,用于内部学术交流。1977年,在《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大会通报》的基础上,“大会”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资本与阶级》(一年三期)。在1977年第2期上,“住房与劳动过程小组”的两位核心成员约翰·霍洛维和索尔·皮乔托撰写了《资本、危机与国家》一文,阐明了能够体现该小组集体观点的资产阶级冲突论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 首先,他们用阶级斗争充实资本逻辑学派的资本批判逻辑,把资本主义国家定义为内在蕴含阶级斗争的“资本关系”的“虚幻形式”。尽管接受了资本逻辑学派的基本逻辑,但他们意识到,资本逻辑学派的原初理论没有给阶级和阶级斗争保留位置,可是如果没有作为历史主体的阶级及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不可能从资本主义中自动生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回到《资本论》,并基于剩余价值理论,强调资本关系具有经济和政治(剥削、阶级斗争)二重性,从而使资本批判逻辑具备了阶级斗争的政治维度。据此,他们扩展了资本逻辑学派关于国家是资本关系的形式的观点,强调这种形式因为阶级斗争、阶级统治的存在而呈现为不同于其真实存在的“虚幻形式”。要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就了资产阶级的统治(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的统一)以及工人阶级的(被剥削的)自由和(相对于统治阶级成员的、形式上的)平等,源于后者,资产阶级的统治日益分离为经济和政治两种独立的形式,并在“看似自主实体的国家机器”上找到自己的制度表达(25)。 其次,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自主性或自主化,是由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的历史性分离所导致的“拜物教形式”。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增强的相对自主性呢?他们回到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自主性或自主化是由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的历史性分离所导致的商品拜物教的一个方面或者一个新阶段。作为一种拜物教形式,国家的自主化既是虚幻的,更是实在的:它不仅是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而且当代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乃至资本体制本身都依赖其所建构的经济与政治的分离。就此而言,“这种经济与政治的分离、这种国家的自主化已经成为统治阶级维持其统治的一部分”。因此,“工人阶级的任务就是要坚持不懈地与作为资产阶级阶级实践的拜物教做斗争,超越那些拜物教形式,把碎片化的‘经济’和‘政治’斗争转变为整体的阶级斗争,夺取和改造国家,把国家权力转变为工人阶级的权力”(26)。 再次,他们主张用阶级斗争和历史分析来补充资本逻辑学派的逻辑-形式分析,以把握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式与功能的历史变迁。就形成语境而言,资本逻辑学派主要致力于解答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形式的起源问题,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式与功能,则不在其问题域内。可对于身处70年代后期英国的“住房与劳动过程小组”成员来说,这些问题却是无法回避的。因此,霍洛维和皮乔托提出把阶级斗争纳入资本逻辑学派的分析框架中去,历史地具体地确定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式与功能的决定机制,并由此得出三个基本结论:(1)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商品生产的普遍化为资本积累创造了前提条件,在此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碰撞,资本主义国家则吸收、重组各种可能的因素构成了自己的最初形式;(2)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强势扩张,要求把符合资本积累需要的自由与平等原则运用于现实,从而决定了自由主义国家的形式与功能;(3)进入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末期,生产的社会化导致利润率下降,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开始尖锐化,为了镇压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维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再生产,资本日益退出直接的政治统治过程,而更多地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来实现自己的阶级统治,国家活动因此日益增多,国家的自主性日益增强。但不管怎样变化,资本主义国家形式都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给定的必要条件与限制条件的互动所决定的,且国家形式的变迁并非可预先确定的,而是在解决资本危机的过程中偶然“接合”形成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国家活动的限制条件、使国家活动更有利于资本积累(27)。1978年,西蒙·克拉克基于资本-阶级冲突论撰文对南非当代国家形式进行了颇有解释力的案例研究(28),在“大会”同仁中引发热议。 四、普兰查斯后期的国家权力批判理论 1968年,普兰查斯定居巴黎,成为法国左翼思想界的重要一员。与此同时,他更以不在场的方式深度介入“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成为一位非英国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如前所述,由他引发的“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为打破两代英国新左派的理论僵持局面提供了关键性的外部动力,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场构成,促进了跨学科的“结构主义转向”的发生。他那种关注现实政治、经济问题的介入姿态得到第二代英国新左派的热烈呼应。在1976年出版的影响巨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安德森激赏他超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失败主义倾向,成为青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典范(29)。因此,普兰查斯事实上成为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第二代新左派影响最大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法文著作被迅速翻译成英文出版,后期著作甚至是法英文版大致同步推出;他的几乎全部理论关切都在第二代新左派中得到迅速而积极的响应;70年代后期,他的理论策略发生了某种调整,进入所谓“新葛兰西主义”阶段,随即引发第二代新左派的“葛兰西转向”(30)。从某种意义上讲,普兰查斯在英国的理论影响要比他在法国的影响大得多,如果没有他,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图景将会怎样,完全无法想象! 1975年,福柯出版《规训与惩罚》一书,通过对欧洲近代监狱权力的历史考辨,提出了自己的微观权力批判理论,强调权力已经融入社会的各个层面,而马克思主义者着力批判的国家只是权力众多栖身之所中的一处。他认为:“如果人们仅仅根据法律和宪法、国家和国家机器来看待权力,那就会把权力问题贫乏化。权力与法律体系或国家机器相去甚远,也比后者更精密、更紧致、更具渗透性。如果你不同时掌握权力机器,你就不可能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得到发展。”(31)福柯的理论在法国思想界引起很大反响,在客观上要求马克思主义者作出回应。1978年,普兰查斯出版自己的最后一部著作《国家、权力与社会主义》,在回应福柯批评的基础上,初步建构了自己永远无法最终完成的国家权力批判理论。 首先,普兰查斯充分吸收了同时代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创见,提出作为“制度性实体”的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权力与知识的结合,在诸多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中都发挥着客观的作用。“制度性实体”是《国家、权力与社会主义》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虽然这个名词是新的,但普兰查斯据此要表达的意思却是旧的:强调资本主义国家一旦生成就具有了超越统治阶级的意识和意志的客观独立性,进而作为一种客观的关系实体发挥自己的客观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国家相对自主性概念的一种变形。不过,在《国家、权力与社会主义》中,“制度性实体”却因为吸收了两个方面的理论资源而变得更加丰富深刻:一方面,它吸收了福柯的“权力-知识”观念,强调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能够通过知识这种微观机制发挥作用,从而扩展了国家权力的作用深度;另一方面,它吸收了60年代、70年代早期德国、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研究成果,肯定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权力拥有更广泛的作用范围,能够在整个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中发挥作用,而不仅仅局限于政治统治。为了阐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性实体”功能,普兰查斯做了如下个案例说明:第一,它对作为生产关系的脑体分工的再生产发挥了客观作用,“不仅仅是根源于生产关系的脑体分工的结果”,“还在社会整体中、在生产过程的最核心积极参与这种分工的再生产”;第二,它对自身存在的社会关系前提——阶级的个体化和私有化——的再生产发挥了客观作用,“个人-私人领域……是国家在穿越它的时候建立起来的空间……它只能在并且通过国家而存在”;第三,它再生产出了“与前资本主义形式完全不同的”法律,一方面把传统的阶级统治形式即暴力法律化,用权力技术和同意机制来支撑暴力,另一方面创造了法律的“标准化”这种新型统治形式,通过规训实现软性的权力统治;第四,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是民族-国家,或者说是基于民族的国家,而民族恰恰是国家的产物,因为民族的“构成要素(经济统一、疆域、传统)都是通过国家的直接活动在时空的物质组织中被修饰而成的”,也就是说,“现代民族往往与国家相一致……资本主义国家是民族的功能映射”(32)。 其次,普兰查斯调整了自己关于国家与阶级关系的原有观点,强调国家是阶级关系的物质性凝结和阶级斗争的战略性场所。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普兰查斯一向关注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过,在其早期“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框架中,阶级、阶级斗争显然更多地受制于结构的强制,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和霸权机制的操控对象。70年代以后,一方面基于自身理论逻辑的转换,另一方面也由于同时代英国新左派的影响,普兰查斯逐渐强调主体之于结构的建构和反作用,肯定阶级斗争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形成及其权力的实施具有重要作用。他强调,“阶级对立正是国家的填充物:它们存在于国家的物质性框架中,构造国家的组织形式;同时,国家政策正是阶级对立在国家中发挥作用的产物。”(33)由此,他调整了自己过去的观点,并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不应当被视为固有的实体。和资本一样,它是一种力量关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阶级和阶级派别之间的关系的物质性凝结,并在必然确定的国家形式中表现出来”(34)。资本主义国家由此成为“相互作用的权力网格的战略性场所和过程,它既接合又展现(阶级关系的)相互对立和相互取代”(35)。也就是说,普兰查斯认为,作为一种关系存在,资本主义国家(结构)既质询、规训或者说建构阶级和阶级斗争(主体),同时也是阶级和阶级斗争(主体)的产物,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结构)固然强大,却不是封闭完满的,其中存在着由阶级斗争所导致的裂隙,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就存在于这些裂隙中。 再次,普兰查斯倡导直接民主和议会民主相结合,通过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既然存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那么,怎么才能超越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呢?对于当时的欧洲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通过民主走向社会主义是唯一可能的选择。问题主要在于选择何种民主道路。对于社会民主主义和欧洲共产主义推崇的议会民主,普兰查斯实际上认为是行不通的,因为议会民主归根到底只会强化资本主义国家;但对于源于第三国际传统的大众的直接民主(如工厂民主、自治运动等),普兰查斯也无法完全认可,因为历史表明,直接民主最终会导致权威主义政治。面对这种两难困境,普兰查斯选择了一条折中主义的道路,即将直接民主和议会民主结合起来:“通过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必须用不同的方式提出来,即究竟如何才能用一种方式彻底地改造国家,以把政治上的自由和代议制民主体制(大众所争取到的东西)的扩大和深化,与不断丰富的直接民主形式和不断涌现的自治团体结合起来?”(36)——必须指出的是,这种社会主义道路只是普兰查斯从理论上推导出来的可能性,对其现实可能性,他实际上是完全悲观的。 最后,普兰查斯回应了福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批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福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批评,就是对普兰查斯的批评。因为普兰查斯是当时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最重要、影响也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福柯的批评,普兰查斯既有所接受,也有所批判。他肯定,诚如福柯所言,权力的存在比国家的存在更为普遍,因此,不管国家有多重要,也不能把“权力等同于或者还原为国家”。福柯的问题在于:第一,他脱离了经济基础、经济过程抽象地讨论权力,结果“权力关系除了自身外再也没有任何基础,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局势’,其中的权力却是内在固有的”;第二,福柯低估并排斥阶级和阶级斗争,他所构想的平民“抵抗”也就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权力总是已经存在,如果权力‘局势’本质上是内在固有的,那么,为什么可能有抵抗?抵抗又何来并何以可能呢?”第三,福柯低估了国家在权力斗争中的核心地位,没有意识到他所分析的那些微观权力关系实际上已经被整合到资本主义国家之中,而他所推崇的那些远离国家的大众运动也无法避免被整合进既有权力之中,因为“外在于权力、逃避权力的独特关系是不可能的,单纯处于国家之外,人们根本不可能免受权力的羁绊”。总之,普兰查斯认为,尽管福柯的权力理论不无启示意义,但“他的那些分析根本无法与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并且,它们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起点,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37)。 1979年10月3日,普兰查斯在巴黎自杀。这使得他的国家权力批判理论再也无法完成。不过,他所开启的理论事业并没有中断:80年代,斯图亚特·霍尔和雅索普这两位“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不同的方式继承并发展了他的国家批判理论,前者聚焦新出现的撒切尔主义,建构了自己的当代英国国家批判理论,后者则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策略关系论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 ①C.B.Macpherson,"Do We Need a Theory of the State",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7(2). ②Clyde W.Barrow,"The Miliband-Poulantzas Debate:An Intellectual History",in Stanley Aronowitz and Peter Bratsis,Paradigm Lost:State Theory Reconsidered,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2,pp.4-52. ③Bob Jessop,"Dialogue of the Deaf: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oulantzas-Miliband Debate",in Paul Wetherly,Clyde W.Barrow and Peter Burnham(eds.),Class,Power and 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Essays on Ralph Miliband,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8,pp.132-157. ④关于密里本德的一般传记情况及其国家理论,参见拙作《拉尔夫·密里本德:在工党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文景》2010年第10期)和《拉尔夫·密里本德国家理论的当代重访》(《求是学刊》2014年第5期)。至于普兰查斯的生平与思想,雅索普的《尼柯斯·普兰查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战略》(Job Jessop,Nicos Poulantzas:Marxist Theory and Political Strategy,New York:Saint Martin's,1985)至今仍是最好的参考读物。 ⑤Ralph Miliband,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New York:Basic Books,1969,p.7.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4页。 ⑦Ralph Miliband,Marxism and Poli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17. ⑧Nicos Poulantzas,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London:Verso,1978,pp.13-14. ⑨参见张亮《马克思的哲学道路及其当代延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9~223页。 ⑩Perry Anderson,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London:NLB,1974,p.11. (11)Perry Anderson,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London:NLB,1974,p.11. (12)Perry Anderson,"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New Le ft Review,1964(23). (13)Edward Thompson,"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in Edward Thompson,The Poverty of Theory & Other Essays,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8,pp.35-91. (14)参见张亮《阶级、文化与民族传统:爱德华·汤普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1~144页。 (15)参见丹尼斯·史密斯《历史社会学的兴起》,周辉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126页。 (16)Perry Anderson,Passages from Antirquity to Feudalism,London:NLB,1974,p.18. (17)Perry Anderson,Passagese from Antirquity to Feudalism,London:NLB,1974,p.18. (18)Perry Anderson,Passagese from Antirquity to Feudalism,London:NLB,1974,pp.421-422. (19)Perry Anderson,Passagese from Antirquity to Feudalism,London:NLB,1974,p.42. (20)Perry Anderson,Passagese from Antirquity to Feudalism,London:NLB,1974,pp.428-429. (21)Nicos Poulantzas,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London:Verso,1978,pp.255-256. (22)Perry Anderson,Passagese from Antirquity to Feudalism,London:NLB,1974,p.33. (23)Hugo Radice,"A Short History of the CSE",Capital & Class,1980(Spring); Frederic S.Lee,"Conference of Socialist Economists and the emergence of heterodox-economics in post-war Britain",Capital & Class,2001(Autumn). (24)See John Holloway and Sol Picciotto,"Introduction:Towards to Materialist Theory of the State",in John Holloway and Sol Picciotto(eds.),State and Capital:A Marxist Debate,London:Edwadt Arnold,1978,pp.1-31; Simon Clarke,"The State Debate",in Simon Clarke,ed.,The State Debate,Houndmills:Palgrave,1991,pp.1-69. (25)John Holloway and Sol Picciotto,"Capital,Crisis and the State",Capital & Class,1977(Autumn). (26)John Holloway and Sol Picciotto,"Capital,Crisis and the State",Capital & Class,1977(Autumn). (27)John Holloway and Sol Picciotto,"Capital,Crisis and the State",Capital & Class,1977(Autumn). (28)Simon Clarke,John,"Capital,Fractions of Capital and the State:‘Neo-Marxist’ Analysis of the South African State",Capital & Class,1978(Summer),pp.32-77. (29)Perry Anderson,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rism,London:NLB,1976,p.102. (30)雅索普指出,普兰查斯始终像葛兰西那样把社会主义过渡作为自己国家理论思考的最终目标,在《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等著作中,这种葛兰西因素尚潜存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之中,进入70年代后,他日益突破“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束缚,雅索普据此把普兰查斯划归“新葛兰西主义”之列(Bob Jessop,The Capitalist State:Marxist Theories and Methods,Oxford:Martin Robertson & Company LTD,1982,pp.153-158)。当然能否把普兰查斯特别是其后期思想定义为“新葛兰西主义”,可以进一步商榷。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正是在普兰查斯的影响下,70年代后期以来,霍尔、拉克劳和墨菲等第二代新左派日益将自己的理论思考与社会主义战略相联系,从而促进了“英国马克思主义”之“葛兰西转向”的发生与发展。 (31)Michel Foucault,Power/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0,p.158. (32)Nicos 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ism,London:Verso,1980,pp.60,72,76,99. (33)Nicos 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ism,London:Verso,1980,p.132. (34)Nicos 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ism,London:Verso,1980,pp.128-129. (35)Nicos 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ism,London:Verso,1980,p.136. (36)Nicos 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ism,London:Verso,1980,p.256. (37)Nicos 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ism,London:Verso,1980,pp.35,149,152,68.标签:生产方式论文; 安德森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英国政治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资本论论文; 封建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