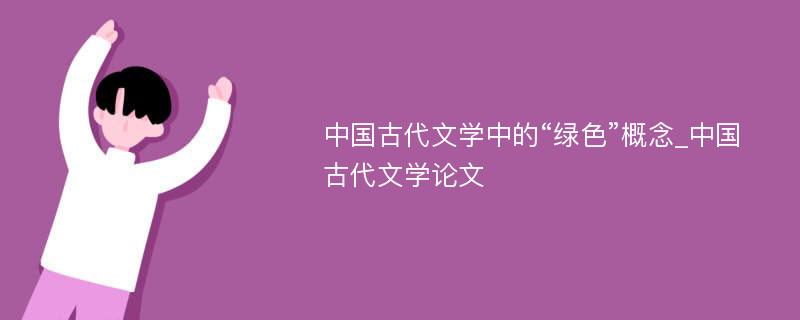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绿色”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观念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二三十年来,在各种传媒和许多学科的论著中,“绿色”成为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传达地球的各个地区人们对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处境的高度关注。然而,“绿色”意识并不是现代人的新发现新创造,更不是环境科学的专门术语,文学家和文学的研究者,有着对“绿色”的职业的亲近与敏感,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饱含“绿色”思想的资源。即以中国古代诗文和文论来说,就随处可以见到对“绿”的咏赞,字里行间流露着无限的欣悦与向往之情,流露着对一切生命的尊重与珍爱,比如:“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刘禹锡);“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王安石);“芭蕉分绿与窗纱”(杨万里);“庭竹无人绿满窗”(王恽);“绿玉(指芭蕉)窗前好写书”(吴伟业)……这类诗句,在各种集子里,可以信手拈来,真是不计其数。
如果说,以上诗句还是从书房里面远眺窗外的绿色,那么,诗人们更盼望的是,远离市廛,全身融入绿色的大自然。陶渊明的“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表达了浊乱政治下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的选择,即厌弃污浊的城市官场,想望回归朴素清静的田园,这样的价值判断给后世与之境遇近似的文人以启示。陶渊明的作品即使不直接写出绿字,但“鸟弄欢新节,泠风送余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不是饱含浓郁的绿意么!陆机的“翳绿叶而弄音”(《行思赋》)与上引陶诗的前一联相近,不过一个直接描出色彩,一个让读者想象出色彩;而苏轼谓后两句“非世之老农,不能识此语之妙”(《东坡题跋》),证明人们早从陶诗感受了绿意。李白写过,“春草如有情,山中尚含绿”;梅尧臣则更进一步:“寒草才变枯,陈根已含绿”,在初冬的萧瑟中就由地下的微绿遥想明春蓬勃的大片的新绿。王维诗:“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张说诗:“雨洗亭皋千亩绿”;白居易诗:“风吹新绿草芽拆,雨洒轻黄柳条湿”,“江南九月未摇落,柳青蒲绿稻穗香”;苏轼诗:“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辛弃疾诗:“泥融无块水初浑,雨细有痕秧正绿”——都充溢着绿色所逗引起的怡然陶然的恬美情绪。除了叶色之绿,还有水色之绿,水色与草、树、天空相映之绿。李白倾心于剡中之景:“竹色溪下绿,荷花镜(水平如镜)里香”;苏舜钦诗:“池中绿满鱼留子,庭下荫多燕引雏”;陆游诗:“瓦屋螺青披雾出,锦江鸭绿抱山来”;戴表元诗:“睛霞冠岭朝红洁,新涨连空晚绿酣”。绿水,是明净清澈之水,是得到人们善待、未纳污垢,也以洁净之躯回报人类的水。对绿色的喜爱是许多人的共同心理,赞美绿色的诗容易引起共鸣,哪怕是断章残简,也可能得以留传。《苕溪渔隐丛话》:“古今诗人以诗名世者,或只一句,或只一联,夫岂在多哉?如‘庭草无人随意绿’,则王胄也。”这么普通的一句诗为什么能被记住?应是受惠于众人对那自然存在、未受践踏、充满蓬勃生机的绿色的珍爱吧?“无人”、“随意”,是把草儿当作了具有独立品格的朋友,不去打搅她,更不去伤害她,让她自在自如地伸枝展叶。
爱绿色,就是爱一切生命,愿与一切生命体为朋侣,就是爱生命的摇篮——大自然。王维《别辋川别业》中“忍别青山去,其如绿水何”之句,多么情深意切!他的《戏赠张五弟諲》说,“入鸟不相乱,见兽皆相亲”,更是直接表达了万类平等的思想。古语所谓鸥鹭忘机,是要摆脱世俗功利之机心,不加害于各种动物、植物。《列子·黄帝》:“海上之人有好沤(鸥的假借字)鸟者,每旦至海上,从沤鸟游,沤鸟之至者百住(住,当作数)而不止。其父曰,吾闻沤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沤鸟舞而不下也。”《三国志·魏志·高柔传注》引孙盛之语:“机心内萌,则沤鸟不下”。黄庭坚《登快阁》:“此心吾与鸥鹭盟”;陆游《杂兴》:“得意鸥波外,忘归雁浦边”;余靖《留题澄虚亭》:“鱼戏应同乐,鸥闲亦自来。”人以友善之心待裸毛鳞介,裸毛鳞介才能用信任的态度待人。辛弃疾的《水调歌头·盟鸥》全面地表现了爱绿树、绿水和爱鸥鹭鱼鹤的心情:“带湖吾甚爱,千丈翠奁开。先生丈屦无事,一日走千回。凡我同盟鸥鹭,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白鹤在何处,尝试与偕来。破青萍,排翠藻,立苍苔。窥鱼笑汝痴计,不解举吾杯。废沼荒丘畴昔,明月清风此夜,人世几欢哀。东岸绿阴少,杨柳更须栽。”综观以上诗词可见,古人之赞咏绿色,乃是广义的绿色,其中深含着尊重生命、尊重自然的而非人为扭曲的生命形态、尊重人与其他生命体的和谐关系的思想。
地球上经长期演化形成的生命秩序,在近两三百年工业化进程中被人类大幅度地改变,由此造成人们原先不曾预料的严重后果。现代的诸种技术的令人惊讶的进步,造成人的思维、人的心理在很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的的数码化、格式化,这固然带来效率的提高,也产生某些令人忧虑的负面影响。现代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先是电视,后是互联网,使地球变得很“小”,千里万里不能再阻隔人们的交往;地理上的隔绝少了,心理上的隔绝在某些领域却加重了,人与人隔绝,人与自然隔绝,小小荧屏使人越来越孤独化。文字写作和工艺制作便捷了,文化也在变成工业,大量地复制,成批地生产。文化、文艺快餐化,快节奏,大音量,浓色彩。文学艺术的刺激性越来越强烈,而人们的接受感觉越来越迟钝,两者互为因果。谈到此类现象,我们要问:这些究竟是高技术为表征的新生产力带来的,还是制度,即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生活范式带来的?答案显然是后者。制度上的弊端带来观念上的偏差与心理上的误区。人类以大自然的主人自居,把大自然当作仆役,甚至当作敌人,要征服大自然,同自然界斗争,向自然界索取,而较少考虑养护大自然。针对这一偏向,从70年代以来,生态主义思潮兴起,并且已经成为世纪交接之际最具规模的社会运动,这就是所谓“绿色运动”。经过20多年,生态运动中发生了“由红到绿”(社会主义者加入绿色运动,传统社会主义向生态社会主义转变,出现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和“绿色红化”(绿色运动向社会主义靠拢)。此种动向表明,绿色运动在寻求更深刻的思想资源。生态运动中分化出越来越多的派别,但是,各类生态主义者们都还没有注意到东方的绿色思想传统、中国的绿色思想传统。生态运动是一种社会运动、政治运动,也有文化运动的性质,而从审美角度阐释绿色思想,似乎尚未获得高度重视。因此,可以尝试谈论一个话题: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绿色观念。
前引诗文中体现的爱悦和咏赞绿色的传统,有着哲学思想的根基。中国古代哲学和古代文学理论,有很强的心理学倾向、人生价值论的倾向,思考人的存在问题,人的存在的意义问题,思考人在宇宙中的位置问题,这也正是当前世纪交接时期的人们所关切的。自西周开始,即有人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天人合一,被从不同角度给予很不相同的阐释。先秦时期的天人合一与两汉时期的天人合一不同,道家的天人合一与儒家的天人合一不同,政治及伦理意义上的天人合一与艺术审美意义上的天人合一不同。老子、彭蒙、田骈、慎到、惠施和庄子对天人合一的阐释,对诗歌、散文、绘画等方面的创作和理论发生了深远而较为有益的影响。惠施说“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书中还描述世人对自然的热爱:“山林欤,皋壤欤,使我欣欣然而乐焉。”他们不是用“天”即自然界的秩序去证明人间某种政治秩序的合理,而是主张摈弃人为、保持天然。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向大自然索取、征服自然的思想,有明显的区别,后者近几百年曾被全世界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人们普遍遵奉。眼下,20世纪结束,新的千年来临,人类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之一,是人与自然的失衡。为了从根本上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端正人们的观念,人要恰当地认识、正确地处理好与自然界的关系。由哲学史和文学艺术史两条线索,我们都可能发掘出中国古代“绿色思想”的传统,这是一种主张人与自然协调相处的思想传统。
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整体上是主张人与自然的互养互惠,而各家各派的论证阐释又有所区别。道家向往的自然,是自然的本体;儒家赞赏的自然,是人化的自然。自古儒家一向“乐山”、“乐水”,鼓励艺术家表现人化的自然。儒家虽倾向于维护现存政治伦理秩序,以“象德”的方式,建立为其社会观服务的自然观;但他们对自然也持有亲近、爱护的态度。《孟子》说,“数罟(细密之网)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董仲舒《春秋繁露》有《山川颂》,谓山似仁人志士,“多其功而不言”;水则勇敢、智慧,不清而入,洁清而出,善化万物。《说苑·杂言》说,山为“万民之所观仰,草木生焉,万物立焉,飞禽萃焉,走兽休焉,宝藏殖焉”。董氏所说的山川是拟人的,但他对山川的歌颂、崇仰,对后世哲学、美学影响甚大。宋代理学家张载说,“乾称父,坤称母……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民胞物与,是极有价值的命题,是可以同后现代相通的前现代思想。《老子》早已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按照许多哲学家的看法,天、地、人、万物,都是气所凝聚;天地之性就是人之性,就是物之性。所以,世间万物都是人类的朋友。从比喻的意义上说,先秦道家可以说是最早的“绿党”,老子和庄子甚至可以说是“绿党”中的极端派即所谓深绿派。他们崇尚原始生活方式,否定人改造和支配自然界的一切努力,属于一种向后看的消极浪漫主义,具有神秘主义、非理性主义倾向。但是,他们倡导人亲近自然、善待自然,批判人对自然物的虐待和扭曲,则颇为深刻。道家对待自然,倾向于审美的态度;或者说,道家的自然观容易孕育、引导审美心理的发生和保持,并在文人的艺术心理中得到较好的体现。
“天”,在中国古代有多重意义,既指客观存在的自然界,也指一切事物以及人类的本性。我们现代所说的“自然”,也有这两重意义。陶渊明诗“复得返自然”句中“自然”一词,颇富意味。它与“樊笼”相对,既可以是指诗人自己的心理,是不再受拘束捆缚,返归天然本性;又可以是指丘山田园,“返自然”就是重新靠拢自然界。这里的“自然”与近代才有的“自然界”的涵义相类。人爱丘山,处于丘山之中,则其性也自然;人背离丘山而落尘网,其性也拳曲。现代发达国家或发达地区的人们,不是常常力图到远郊、到农庄、到戈壁大漠、到原始丛林,去求得心灵的和平与净化吗?他们对“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应该是能够引起深刻强烈的共鸣的。郑板桥说,“平生最不喜笼中养鸟:我图娱悦,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适吾之性乎!”他主张要养鸟就多种树,绕屋百株,为鸟国鸟家,天尚未亮,听一片啁啾,如聆清歌;起身后观其扬翚振彩,如观曼舞,总之,“各适其天,斯为大快。”博大的胸怀与精细的审美感觉多么融洽地结合在一起!
人对待自然,应该尊重它的本性,循着它的本性来利用它,享有它,与它和谐相处。这就是《庄子·秋水》说的“无以人灭天”,即不要任随人的主观意志而破坏自然物的本性。例如,“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庄子》的这一思想,不是道家独有的思想。柳宗元的名篇《种树郭槖驼传》和龚自珍的名篇《病梅馆记》所要鼓吹的,也是同一思想:“顺之以天,以致其性”,“纵之,顺之”,“解其棕缚”。对牛、对马、对树、对花,都要尊重它们的禀性,不要用人的强力拘禁它们。
绿色思想不仅仅表现在文学创作里面,也表现在文学理论中间。中国古化文论中的绿色思想,可由感应论和移情论以及虚静论和境界论两大方面,试作简略说明。
先说感应论和移情论。感应论认为,人与自然对应,人类群体的社会构成及其兴衰隆替,人类个体的身体构成及其强弱健衰,人的精神、性格和品德及其刚柔清浊,都与天象、山川相对应。《淮南子·要略》说人与天的关系,“其形骸九窍取象与天合同,其血气与雷霆风雨比类,其喜怒与昼宵寒暑并明。”《春秋繁露·阴阳尊卑》说,“夫喜怒哀乐之发,与清暖寒暑,其实一贯也。”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说,“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郭熙的画论《山水训》说,“春山烟云连绵,人欣欣;复山佳木繁阴,人坦坦;秋山明净摇落,人肃肃;冬山昏霾翳塞,人寂寂。”这是文学艺术创作中感应论的运用。人的情感与自然界的阴晴明晦、寒暑炎凉相对应。春风催燃快乐和希望,秋霜引发哀伤和沮丧。大漠孤烟激起壮烈情怀,晓风杨柳带动缠绵思绪。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在中国古代的移情论中,人们理解的移情是双向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青山见我”乃诗人的比拟之词,“我”可以把人类的情感注入青山绿水的自然景色之中,“青山”(这里是作为一切自然景象的代称)又可以激发、改变、酿造“我”的情感,可以对人的审美性格和伦理性格产生重大作用。人是自然之子,自然不但生成和养育人的肉身,也生成和养育人的心灵、人的精神。之所以发生感应和移情,是因为“天”和人由同样的“性”和“道”所支配。“性”和“道”的本质,它的运行、变化,从天、地、人几个方面分别体现。天道和人道,其实是一个道。违背天道,最终必然伤害人道,人的个体或群体要因此承受灾难性的后果;顺乎天道,保护大自然,人类的生存有保障,人类的精神也能健康发展。
哲学家努力参悟天道,文学家敏锐地感受天道;倒过来说,奥秘的天象诱发深沉的哲学思考,优美的自然景观培育诗情画意。《世说新语·言语》:“王司州至吴兴印渚中看,叹曰:‘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那里说的就是大自然陶冶人的审美情操,培育人对美的感受力。古人所谓钟灵毓秀,元代王恽诗云:“河山两界夏西分,孕秀钟灵产异人”,意思就是不同的环境造就不同的个性,崇峻或清幽的自然美孕育美好的心灵、超拔的性格。当人还在蒙昧、幼稚阶段,大自然启示人逐渐懂得对称、均衡,懂得美的最基本最普遍的规律。一个爱护自然、能够从自然景致获得快乐的人,是懂得美的人,有创造美的潜力的人;一个与大自然隔膜,忽视、蔑视、肆意斫杀生命的人,不可能真正懂得美、懂得艺术。早期的艺术直接来源于自然。《易·系辞上》说:包義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又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文心雕龙·原道》根据《周易》的这一论断发挥说,圣人“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柄辞义”,于是才有了文学。刘勰进而指出:“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屈原的杰出创造,得到了“江山之助”。文章江山助,这一说法为中国古代文论家普遍接受。《能改斋漫录》卷七记唐张说至岳阳,诗益凄婉,“人以为得江山之助”;杨亿《许洞归吴中》:“骚人已得江山助”;宋祁《江山宴集序》:“江山之助,出楚人之多才。”哲学和文学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最初都来源于对自然的感应。可是,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人与自然却日渐疏远,人们从书籍上学习哲学和文学,却不再重视从大自然去学习哲学和文学。宋代林光世《水村易镜·序》说,“古之君子,天地、日月、星辰,阴阳造化、鸟兽草木,无所不知,不必读卦辞、爻辞,眼前皆自然之《易》也”。日月星辰、鸟兽草木,即是眼前之《易》,也即是眼前之《诗》。从哲学书学习哲学,从文学书学习文学,已落第二义,用林光世的说法是“世道衰微”的结果,是离源而逐流,离本而逐末。今天,人们应该重新从自然去“读”出哲学与文学的意蕴。
当人在社会生活中,为口腹之需而屈心抑志,在彼此的冲突杀伐中备受伤损,大自然以母亲的怀抱,为人们本性复归提供最安适的栖居之地。陶渊明的归田园居,“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是身体回归乡村田野,更是心灵回归到自由纯洁的本性:“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他的眄庭柯、观云鸟与悦亲戚,与他的委心、寄傲,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李白经历了长安三年对皇帝的期望、幻想破灭之时,便散发弄舟、梦游天姥;李商隐“向晚意不适”,便要“驱车上古原”;欧阳修贬谪滁州,远离政治中心,然后意在山水之间,观四时之景不同而其乐无穷。自然是永恒的,人事是瞬息变化的。人远离自然,也就远离了“道”,也就迷失了“性”。当人滥伐林木、滥杀鸟兽的时候,不仅在毁坏自己的家园,而且在戕害自己的天性。人与自然亲和,彼此和谐发展;人与自然对立,彼此都受损伤,那时,人受损的不只是生态环境,而且还有心灵、本性。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写狐犬花木虽以喻人,也表达了万类同根的观点。《九山王》一篇,写李生杀狐之全族而遭灭族之报,就是一例。但明伦评此篇说,“物虽异类,不当有众生见存于中,即不能到得万物育尽物性境地,两不相妨,奚不可者?”又引别人的话说,“君子视六合飞、潜、动、植,纤细毫末之物,见其得所,则油然而喜,与自家得所一般;见其失所,则闵然而戚,与自家失所一般。”这正是蒲松龄要告诉读者的思想,这种思想存在于《聊斋志异》的许多地方。现代画家、文学家丰子恺在其师李叔同的启示下,积四十余年之力作《护生画集》,其序文说,“护生就是护心……救护禽兽鱼虫是手段,倡导仁爱和平是目的。”集中收录了大量古人关于爱护动植生灵的诗文,与画相映相配。中国文学中的这一思想,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绵延不绝。
虚静论和境界论并不是专门讨论美感与自然、艺术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但是它们却包含了关于自然可能给予人的精神何种影响、人应该如何对待自然的内容,特别是包含了对待自然的态度关系着人在审美上到达的层次的思想。大自然是一本打开的书,是一本打开的哲学书,是一本打开的诗集,是一本打开的画册,是一本打开的乐谱。但是,并不是任何人随时都能够读懂它。读这本书,需要虚静;读了它,能给人以美好的宁静。所谓虚静,首先就是要去掉争竞之心、占有之欲;所谓境界,其要义是思与境偕,是情与景的融合,人作为自然的一分子而融入自然之中。境界之“境”,首先是指物境,是王昌龄《诗格》中所说“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欲使诗有境界,写诗时心须虚静;欲使心虚静,最好的办法是寄情于山水。谢灵运说,“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白居易说“闲中得诗境,此境幽难说”(《秋池二首》之二);司空图诗中“更无尘事心头起,还有诗情象外来”(《山中寄梁判官》)“溪风满袖吹风雅”(《李山甫诗集》)之类诗句,说明良辰美景产佳诗。辛弃疾《贺新郎》词序称“水声山色,竞来相娱”,词中说的“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描画出了景中得静、静中得诗的过程。苏轼《前赤壁赋》说的,天地间之物,“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清风明月,自然景致,不同于酒肉、金钱、衣饰,不需要争夺和占有,并且也是不能占有的。有钱有势的人可以独占一座花园、一处别业乃至一个海岛,却并不意味着可以享受景物之美。《牡丹亭》里的西席先生陈最良对丫头说,“你师父靠天也六十来岁,从不晓得伤个春,从不曾游个花园。孟夫子说的好,圣人千言万语,则要人收其放心。但如常,着甚春伤?要甚春游?”剧作者安排这几句唱词,显然是为杜丽娘的游园这一极平常的行为提供不平常的背景。当时的思想环境和前此的意识传统,是教导人们“收其放心”,反对人们听任其天然本性的召唤,而要用礼教约束它,要人们拒绝读自然这本大书。被那主流意识驯化、腐蚀的人,闭塞了观看自然美色的眼睛和聆听自然妙音的耳朵,因此也阉割了自己人性的真纯。杜丽娘长到青春时期才第一次游自家花园,惊叹它的“良辰美景”,同时也就会怪异“恁般景致,我老爷和奶奶再不提起……锦屏人忒看待这韶光贱!”“锦屏人”的心被厚厚的功利之膜裹住,失去了对自然美的感受力。中国明代新兴思潮活跃时期,汤显祖的这种情调,与美国文艺复兴的哲学家和散文家爱默生构成呼应。爱默生在《论自然》中说,米勒拥有这片土地,洛克拥有那片土地,曼宁拥有远处的林地,“但他们谁也不能拥有这片风景。在这片视野中,有一种唯有那种能把各部分整合为一的人才可能拥有的一份财产。这样的人就是诗人。这份财产是所有这些人的农场中最珍贵的。然而,在他们的清单上却没有此项财产。”(注:(美)R.W.爱默生《自然沉思录》第5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 年版。)清风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却不是随便什么样的耳目都能够“得”。耳目受心的支配,心虚静了,没有机巧之心,没有贪欲之心,才可能滋生对自然的亲近感,才能够凝神谛听大自然的美妙音乐,才能够注目观赏大自然的绰约风姿。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乐,不可能领略自然之美。马克思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私有财产使人们变得愚蠢而片面,“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为这一切感觉的简单的异化即拥有感所代替”,“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7—8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对自然的破坏,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归根结底,不是来自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而是来自人类社会组织方面的弊病,尤其是来自刺激人的恶性的病态的消费欲的机制。人被煽动得竭力去占有最多最新的、其实他并不需要的商品,以此推动和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人们急速膨胀的物欲导致人与自然的进一步严重对立。为了制造塞进千家万户的垃圾广告,一片片的森林被砍伐;被霓虹灯刺伤眼睛的人们,怎么还能敏锐地观察树叶色彩每日每时的微妙变化?古今中外那么多诗人对着无垠的星空神驰意往,而今大城市整年里天天彻夜灯火辉煌,孩子们再也不能卧看牵牛织女星,甚至看不清银河(注:法国《问题》杂志不久前报道,“今天,100个孩子中几乎没有一个孩子会说他看见过银河。”它又说, 一个世纪以前,天文学家在巴黎市内能够用肉眼为行星和恒星编制索引,而现在,至少要离开城区100公里,才可以指望看到同样的星空。 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到如此的程度,以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2年就促成所有成员国签署了一份协议,共同承担保护夜间天空的义务。)。晋朝的陆机慨叹“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而到了现代,煤烟、汽车尾气的危害超过尘土的危害许多倍。生态主义者们批判异化消费,资本主义制度注定了必然要不停地追求利润最大化和市场持续不断的扩大,追求消费的持续不断的增长,它导致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这与生态合理性的要求根本不相容。生态危机的根源在资本主义积累的逻辑之中。
生态的保护要求现代化范式的转换,要求恢复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而这也就必然要求人们观念上的澄清,观念上的拨乱反正,要求人对自然关爱与亲近。《世说新语·尤悔》载,陆机卷入政治纷争,事败被诛,临刑时叹道:“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华亭是陆机的故乡,有清泉茂林,鸥鹭莺鹤逍遥乎其中,他和弟弟陆云,多年共游于此。《语林》中记述,陆机作河北都督时,闻警角之声,对身边人说,“闻此不如闻华亭鹤唳。”可是,他终于远离了鸥鹤,最终不免于杀身之祸。这很可以当作富有教益的寓言来读:人类疏远了自然,伤害了自然,悔尤往往来不及了。风吹草低见牛羊,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这些曾经是极平常的事,可复得乎?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前人的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