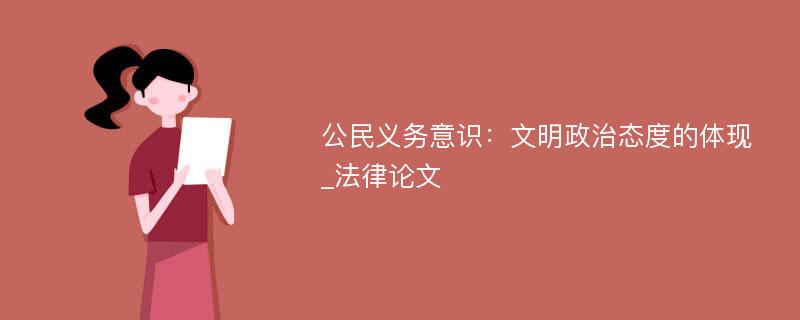
公民义务感:彰显文明的政治态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民论文,义务论文,态度论文,政治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希腊时期,公民身份意味着对城邦公共事务的义务;而近代至今,随着人权与平等概念的提升,使得公民、公民身份的概念更多地被当作权利、权利伸张的代名词。百年来的这种对公民身份内涵的权利导向(rights-oriented)观念,体现了我们的公民意识中权利义务对比失衡的倾向。不仅如此,学术界对公民义务感的认识与讨论也大都局限在思想教育领域;政治学的研究中缺少对公民身份概念中的权利义务的对比分析,更缺少从政治心理的角度讨论作为政治态度的公民义务感的唤起与养成。
讨论义务感,并不是要扭转当代社会强调权利的公民身份传统。如果政治是人们之间相互对待的方式,身份就是体现人们在社会中的相互关系。从契约论开始,社会被看作一个合作生存的体系,义务来自他人对自己的角色期待,以及命令或请求。一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也由服从这种命令或角色期待的义务而获得。然而,义务感与政治义务并不同步——公民担负起的服从的义务,并不必然伴随内心产生积极的义务感;公民内心的身份角色意识也不仅徘徊在权利义务之间,更在自己与他人的义务分担对比中。“为什么一个人觉得他有义务承受各种负担的这种义务感会因他相信别人也在承受相同的负担而增强,因他觉察到别人没有承受相同的负担而减弱”①?那是因为,义务感不仅伴随着公民对政治系统的认可、对政府公正程度的评价而产生的心理感受,更重要的是,它是自愿甚至主动承担社会合作成本的意愿,是一种出自内心的、积极的合作态度。决定公民这种政治态度的因素有很多,其中,重要的是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的公正与否。因为,“除了公益没有其他原则了。倘若利益首先产生了对政府的服从义务,那么那个利益在所有较大的程度上、且在大部分情况下停止了时,同时导致服从的义务也跟着中止”②。当政府不再是有益的时候,它就失去了赢得服从的能力。
在公共生活作为人类的共处方式依然是不可或缺的情况下,每个公民进入共同体时,都不可避免地承担了一定的角色——暂时的或长久的:子女、同事、朋友、合作伙伴等等;享有了一定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一个共同体成员的身份,就是集中在他身上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每种社会关系都体现了公民身上承受的角色期待。当公民在社会关系中行事的时候,义务就是在每种身份角色下“应当”完成的事务:公民“应当”遵守法律、“应当”完成赋税、“应当”服兵役……一个人,只要他在社会生活中,只要他与别人进行交往,就面临着各种应当(oughtness)与不应当,它不仅构成了对公民行为的各种限制,更体现了在这种角色下他人与社会对之的一种祈使:“法律并不去陈述人们想要做什么,而是规定了别人希望他做什么”③。同研究社会科学所有重要观念一样,社会性始终是我们讨论应当的概念与约束的含义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背景,“很难看到正义与平等的概念在社会关系之外还有什么含义”④。他人与社会的存在,不仅是一个人生存的需要,甚至可能是生存的目的。他人与社会对自己的需求,对自己的角色期待,不仅构成公民行动的动力,而且成就了公民的身份意识。义务感产生也首先是适应公民身份,对他人与社会的需求与期待做出回答。
他人或社会的需求与祈使反映出其在某方面的缺失、渴望或不幸。公民承担了这种角色关系,就成为那个被期望去为之解决的相应责任人。这种身份构成了对公民行为的一种限制,是自己进入公共交往的承诺,也是公民将要付出的努力和辛苦——根据边沁的措辞,它不仅是约束(sanctions),甚至构成痛苦(pain)。因为履行义务去解救他人或社会的苦难,需要自己付出努力。如果义务的履行包含了痛苦的因素,那么公民内心要产生义务感,则一定要克服这种痛苦,产生快乐与和谐。当不幸发生时,没有其他人可以依靠,人们会感到自己责无旁贷。但是他人的需求不会自然变成义务感,这种不幸或灾难对公民的感觉造成刺激,“我们最重的不幸来自于我们的感官状况与我们的社会关系与状况中。因此我们的动机不是我们的目标,而是我们受到的刺激”⑤。希望看到他人或社会的灾难因自己的努力与付出而减弱,就必须通过辛苦的付出来消除这种刺激;看到他人和社会恢复了平静与安乐,会让公民感到自己有力量、有能力去挽救他人、给社会创造福祉,“愉悦并非是缺少灾难,而是消减灾难的体验”⑥。有责任并有能力根据他人与社会的需要消减灾难能够给人带来快乐的体验,这是心理学验证过的不争的事实。这种履行了义务之后的成就感是激发义务感的因素之一。
他人的请求、社会的需要成为激发公民义务感的动力因素,但是,仅仅依靠他人的需要与公民的同情,无法证明除道德义务之外的义务感产生的正当性。所有的“应当”要有实施的规定与保障。从契约论开始,一国的法律是经过全体公民同意后制定的,立法的基础是公民的社会公共生活,也是以保证公共生活的秩序为目的的。因此,义务感也产生于公民服从的心理——对法律的承认与遵守。“这个‘服从’不仅仅是一种屈从,而且也是主体的一种安全化、持续化,一种对主体的安置,一种主体化”⑦。遵守法律规则,可以使我们很好地避免伤害他人与危害社会。法律对义务的规定伴随着惩罚的威慑,这种外在的物质力量能够保证行为的产生,却不能自然地激发公民自愿的义务感。以强力为后盾的公共权力,必须依靠公民的服从来完成公共秩序。生于或选择成为一国公民的身份意味着隐然同意(tacit consent)了该政府的权力与服从该国法律。这是一种基本的公民政治态度,遵守法律也是公民的一种基本的道德素养。然而,国家法律的实行,不能等待公民道德修养的提高而实现,国家的目标也不是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从我们成为一国公民,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第一天开始,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由社会各种法则所约束下的一张大“网”之中,这些约束保证了社会公共生活的正常运转,公民的身份就暗含了对国家法则的认可与遵守。服从的义务是伴随着公民的身份与之俱来的:“如果他(苏格拉底)不是希腊的一个公民他就不会感到有义务遵循希腊的法律;在当朋友们如此焦急地劝他逃亡的时候他早就逃掉了”⑧。
因此,规则也不仅仅是祈使,它还是一种选择:选择服从,或者接受惩罚。作为服从对象的法律、道德与权力,服从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截然分明,而政治义务却同时混杂了对外在约束的服从与对内在道德的戒律,并与之不同,它规定了一个好人如何成为一个好公民:“外在的物质的义务产生自强力或权力,而内在的自利的理性义务却来自对惩罚的恐惧与对宁静的渴求”⑨。政治义务规定了共同体的公共生活的秩序,它符合人们对于社会生活的需要,共同生存是它的目标。正是这种乌托邦似的目标,在每个人内心都形成一种内在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促使一个人成为一个好的公民,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脱离这种内心自律的影响和制约,尽管可能每个人显现的程度并不相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义务感产生于对国家的认同。
诚然,法律法规不能自然地获得人们对义务的理解与服从,公民义务感的激发需要有政府的价值引导。行为的目标或结果都不是行为的直接动机,甚至对义务本身的理解与认知也不是义务感本身。我们可以不理解法条的制定背景而直接遵守它,但我们无法不理解义务的本性而产生义务感。虽然对于大多数经验与知识都有限的公民而言,遵守比理解更重要,这要求我们的公民在成为一个社会的成员的时候有一种信仰:相信法律,相信权威;但是作为行动的向导,公民必须先了解法律规则,接着了解为何。事实上,我们社会的教育系统也是在同时进行着认同教育与理解教育。从“红灯停,绿灯行”的最基本的规则开始,社会教育系统在逐步地给那些预备成为公民的孩子讲述着这个社会的系统运转方式,以及如何更“好”地认同它。这不仅是一种教育,更是一种训练。人们内心更容易认同自己熟悉的东西,更容易对自小接触的内容怀有感情,更容易对自小接受的禁令心怀畏惧;在自小接受如何服从这种系统规则的训练后,人们更愿意对自己能够轻易掌控的技巧予以实施……这是义务感养成的心理基础。
然而,最终决定着一切价值引导能否有效的关键,却是政府的作为。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是否秉持公正的理念,决定着政策法规能否获得公民认可的政治态度。这不仅是公民对身份角色职责的正当性需求,而且涉及公民关心自己的权利是否得到了正义对待的公平感受。总之,是一国公民对国家权力系统的内心的“接受”与心理支持程度的体现。对公民来讲,一旦这种内心的承认与接受使他决心成为一国之“好公民”,那么这种义务感就不仅产生了遵守法律的行为,其他诸如纳税、服兵役等义务也都水到渠成了。就如同公民对遵守交通法的义务感,如果没有伴随着对这部交通法能够保证交通秩序的正常运行的认同,就无法真正去遵守它。“如果国家仅仅是一个有组织的惩罚系统,法律秩序也仅仅是关于强制力使用的规则体系,那么无论国家还是法律,都无法索取我们的效忠:那将不会有政治责任——没有忠诚,只有服从;没有‘公民’,只有国民;没有城邦,只有道路尽头可能的集中营”⑩。公民心中内在的义务感给公共生活赋予了联合与合作共存的价值,而不仅仅是一个权力的威慑。“道德或伦理的关键是从思想上和行动上识别祈使,即义务感。正是这种义务感把简单的行为(behavior)转化为行动(conduct)”(11)。正是因为义务感是公民面临选择做出的决定,才成为自觉的行动(conduct);义务感,在对待结果和主动性上,已经不仅仅是履行了。正义的含义,有和谐也有平衡,有伸张也有责任,有权利也有义务,有失有得,有对有错……但无论哪种,都需要在公民之间实现,因为毫无疑问,每个公民在进入公共生活的时候,都会希望自己能够受到公正的对待;然而社会是个大的合作体系,希望受到公正对待的心理出于私利的动机,但也出于一种责任感。
除了义务感产生的心理因素,公民参与履行政治义务的实践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义务感的产生。政治义务首先基于公平的合作。近代以来,天赋人权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权利被熟悉地描述为神圣的、优先的和终极的”(12),公民意识也首先被替代为权利意识。然而,权利却不是天然的、独立的和无限的。权利不仅有成本,而且与义务是相伴而生的。对权利成本的研究意味着“说明在追求更重要的目标时我们愿意放弃什么”(13)。关注权利成本的意义在于,让公民在获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时,必须意识到自己要为此付出的义务。这一方面告诉公民懂得权利不是无成本的,避免对权利的滥用;另一方面,公民对权利义务的权衡比较,正是体现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平导向。
是公民的共同合作纳税,完成了政府的财政目标。那么财政的支出自然就成为公民监督政治是否清明的主要方面:看它是否“带来了充分的公共利润,利益和负担是否被公平地分享”(14)。公平原则在激发公民义务感的产生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社会政策的正义标准,大多是通过分配得来的,公平感又是个人通过比较得来的感受,它影响态度,继而影响行为。社会政治生活离不开合作,涉及公共问题的共同体生活,本身就必须合作完成。权利义务虽然是相伴而生的,但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却是首先考虑到可能获得的权益,其次才会考虑是否同意承担合作的成本。也就是说,是获得待遇的公平感,才能激发人们为此承担责任的义务感。为了考虑到享受公共服务时可能存在的“搭便车”现象,乔治·克洛斯科(George Klosko)等人的研究把公共益品分为了可排他性的和不可排他性的,以避免承担了合作成本的公民内心产生不公平感,并提出了合作中的公平原则中的五个要素(15)。根据这些合作的公平原则,针对可排他性益品,比如新凿的井水,让合作者产生公平感的办法可以通过限制不合作者享受公共益品的方式实现,因此,不参与承担凿井成本的人无法得到井水就是正当的;针对不可排他性益品,比如清扫干净的大雪路面,则要复杂一些,也是公平原则重点讨论的情景。
然而,如果人数巨多,合不合作都能享受到公共服务提供的益品,那么“搭便车”就绝对是有益的,所以,逃税成了纳税人都会存在的侥幸心理。因为,在巨大的纳税分母面前,个人成为一个非常小的分子,纳税,成为承担合作成本的负担;而逃税,则可以改善生活。所以,主动纳税对一个理性人来讲,肯定是不明智的做法。然而,政府的公共服务,必须有足够数量的纳税人合作支持完成。虽然规范完成征税是政府的目标,但如果不纳税成了多数,那么要求少数人去纳税承担社会合作的成本,对这些纳税的少数人来说,就是不合理的了。这种基于合作而产生的义务感的公平性,不仅取决于公民个体享受公共益品的权利与尽责纳税的义务的对比是否公平,而且取决于政府对社会合作成本在公民间的分布是否公平。只有公平的权利义务平衡、同时公平的合作成本分担,才会带来公民自愿、主动的义务感的产生。
然而,社会成员彼此间如何负上了合作的义务?一个民族国家的公民的身份(citizenship)是一国公民与其祖国之间的一种法定联系;由此而激发的认同感,则是公民个体与其生活的共同体之间的一种心理的纽带。成为一国的法定居民而获得的法律上的身份,即意味着公民已经信任并宣誓效忠一国法律,并且服从这国政府。这既是从契约论上已经被证明的,并且也是为其他公民所意识到的。除了直觉之外,是什么提供了成员身份与义务之间的直接联系?“事实上,我因为成为一国社会的成员而实际获利了,所以我必须为此而完成赋予我自己身上的使命”(16)。西蒙斯在直觉之外为身份带来的义务感寻找到了受益的根源。而吉尔伯特(Gilbert)却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义务的来源。他形象地用“两人同行”作比喻来形容处于同一共同体的成员,因为彼此“同行”,就负有了一种“联合同意”(joint commitments),即,“我同意和你沿着同一路线行走”。这种对于“同路”的默认,也即同意了该路线以及同伴等相关的主题。这种基于“约定同行”的认同,也就为彼此负上了合作的义务。在这里,公民通过共同生活于一个社会共同体中,处于一种联合了的同意,他们在同一条船上,“我”就成为了“我们”。“我们”成了思考公共问题的起点,政府也成了“我们的政府”,国家也成为“我们的国家”。这一心态变化的重要之处就在于,“人们构造了一种多元的主题,不仅在行动和实践方面经常一起做特定的事情,而且在信念和态度上、在行动的原则上等等”(17)。这个变化,使得公民在表达任何观点主张之时,都暗含了这些观点看法是他所属的公民群体所共同同意和信仰的。这一点更为重要。因为,一个群体当中的公民未必时刻都能够一起做共同的事情,然而,信念和态度,却可以时刻分享:如,“我们能渡过难关”、“我们能战胜这场战争”(18)。这种群体的认同感让彼此负上了合作与告知的义务。即,同属于同一群体的成员在共同体生活中共享相同的多元主题;从而承认彼此负有了支持他们的国家,遵循它的法律,依法纳税等等的公民义务感。
此外还有沃尔泽(Michael Walzer)等人把公民的成员身份与其所享受到的利益以及自由相联系起来讨论,以确定公民义务感产生的来源。尽管这也遭到了批判与反驳,但是毫无疑问,在众多的讨论公民权利的文献中,都认可了由成员身份而来的社会共同体的认同感,认为整个社会成为一个整体,这种从权力的角度讲的团体原则(principle of association),必然带来了作为成员身份的团体性义务(Associative Political Obligation):“人们强烈地觉得自己是特定国家的成员,是英国人、法国人或美国人,这是一个人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一个人通过遵守一个团体的规则(即服从法律)来表达出自己的身份”(19)。此外,杨(Young)还从同侪信任的角度主张了群体性权利的概念,尽管同样不可避免地遭到批评,但是,也我们从身份角色的角度考察义务感的心理机缘启发了思路。
最后,成为一国成员身份而享受政府带来的公共服务,是否能换来公民的感激,从而激发义务感的产生?沃克(A.D.M.Walker)主张,公民从共同体那里获取了利益,由此而激发的对国家的感激之情能够带来内心的义务感的产生,甚至,对国家的感激可以带来公民的牺牲与献身的情怀:“事实上,无论多周到,报答(requial)的原则都没有明确体现真正的感激义务……感激,不是一种公平”(20)。但在克洛斯科看来,如果政治权力离不开强制与服从,那么以“感激”带来的服从却显得力量太过薄弱了。克洛斯科论证道,如果感激,是由于如西蒙斯所论述的,由于成员身份而获利带来的,既然是感激了,那么感激者获得如此利益就没有付出责任与牺牲。这不符合政治义务理论中的权利义务相对应的原则。然而,沃克引用了休谟的论述“在人类能够犯的所有罪恶中,忘恩负义算是最骇人、最悖逆的了”[21],并以苏格拉底的例子表示,在古希腊时期的公民个体,可以出于对城邦的无比的忠诚与感动而奉献生命。沃克仔细区分了感激的几种类型,区分了克洛斯科论述的由公平原则引发的政治义务,以及由西蒙斯论述的感激带来的政治义务。克洛斯科针对沃克批评的最合理之处即是指出了强力保证下守法、纳税、服兵役等的义务的执行,“国家并不请求公民的服从,而是要求他们的服从,对于那些不服从者,仅仅是惩罚他们就可以了”(22)。相对于费劲制造福利以换来公民相对微弱的感动,依靠国家强力带来的服从效应就容易和简单的多了。针对公共事务而言,责任比有感激带来的奉献感则有意义得多。克洛斯科举例说,身为议员,出于对出资人的感谢,并不带来义务以使他对抗公共的利益,忘记自己的任务与责任。
克洛斯科的批评不无道理。然而,国家真的不需要公民的感激吗?沃克接下来更进一步地维护他的立场:内心的力量才是最为强大和可靠的。在回应文章“感激的责任与政治义务”中沃克进一步指出,克洛斯科攻击基于感激的义务是薄弱的缘由是由于他没有区分开拥有明确内容却相对薄弱和拥有分散内容却力量很强的两种义务(23)。事实上,沃克的立场并不乏例证,如楚庄王的折缨之举换来手下大将的拼死营救,日本企业员工拼命加班为报答企业带给自己的福利。从管理心理学的视角来看,感动,的确是激励的最高境界,它引发的是组织成员内心无比强烈的义务感,它依靠福利激发组织成员内心对于群体的强烈的认同、归属感,从而激发成员的忠诚感,从而努力工作甚至奉献生命的义务意识。在沃克与克洛斯科的交锋中,无论沃克的论述是否准确界定了感激对于政治义务产生的严格支持,也无论服从的义务伴随权利同时被法律所规范是否自然;对政治权力的服从的义务可以由强制规定;而义务感却只能由感动激发。事实上,作为国家政治系统的代表政府,在它提供公共益品时,首先要做到的是恪守公平,接下来就是制造感激与忠诚了。
义务产生于法律对责任的界定;而义务感却产生于人们对义务的感知与认同。它不一定与义务同步——公民在履行义务时,内心不一定伴有心甘情愿的感觉;相反,在义务不是必需时,也许公民内心却充斥了义务感。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因为需要服从有关的约束,因此义务是人们“应当”(ought)从事的行为;从心理的角度看,这种约束下的“应当”行为,本是人们不愿从事的,因此才会被规定,被请求,同时人们在从事应当服从的行为时,也并不必然伴随着内心的意愿。也就是说,由法律的约束下被迫服从(to be obliged),与内心真正感到这是“应当”服从是不同的。这二者的差别,就在于是否还有其他选择。“应当”意味着,行为者有更多选择,可是他却要按照被期望的那样去行动;而被迫的义务则是没有其他选择,如果要实现目标,就只能如此行事,否则就要放弃目标,承受相应的后果。但是在更多情况下,法律所规定的情形就成为了严格限制,在这种条件下,行动者就别无选择了。义务产生自对行为的一种约束,而义务感是伴随着对责任的意愿,也就是说,义务感是在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内心愿意服从这样的约束。针对服从的三个对象:服从权威、服从法律与服从道德,他们分别意味着受到权力的约束、受到规则的约束与受到内心力量的约束。当我们受到约束需要服从的时候,我们会不断地发问:“服从的理由是什么?”、“我们为什么应当心甘情愿地服从?”这样的问题不仅仅是整个政治哲学的基础,而且也为我们提供了服从的理由,以及义务感产生的心理应当性(oughtness)。
佩吉(Edgar Page)举了两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应当与被迫的区别。领队由于天气的原因而改变船的行驶路线“就是意味着为了实现他所追求的某种利益,这么做是必要的”(24);领队的责任目标是要带领大家到达终点;为了这个目标,当遇到天气变化,为了达到目标只能改变路线。并且,我们也可以判断,他肯定会改变行驶路线,而不需要伴随内心的争斗与强烈的意愿。而医生应当依照约定而去看望病人只是在按照责任应当如此,如果他想很好地履行医生职责的话,他就会如约而至。但在也许还有别的事情要做的情况下,“他可能不得不决定一下两件事去做哪件,而且他可能决定哪件都不做,或者,就算说他哪件都不必做,也不影响说他两件都有义务去做”(25)。由此,尽管同样是等着我们完成的任务,只有那些不被外界条件限制,而是我们内心自律去从事的事情,才是“应当”的事情;也只有在从事这种行为的时候,内心才能伴随义务感。
在佩吉区分了“规则约束下的义务”(rulebound)与“道德约束下的义务”(moral principle)之后,引起了二者之间的讨论。怀特(Alan R.White)首先从哈特(Hart)对“有义务”和“被胁迫”的区分开始,指出,被胁迫虽然也是不得不做,但这不构成义务;只有法律或道德上的规定才能构成义务。这样就有两种意义上的义务。一种是,人们在规则上、道德上有义务做某事,这种他称之为人们有义务做某事;另一种是,人们受天气等的影响不得不做某事,他将这种排除在有义务做某事之外。这样,怀特首先区分了两种胁迫:被强(武)力胁迫,还是受环境(天气等)影响被迫。接下来,怀特指出受胁迫与有义务的两种区别:同样是原本不想从事的行为,受胁迫则是别无选择,只能如此;而有义务则是应当做,但也可以选择不做;除此之外,他们的差别还有:一个是被胁迫,一个是被期望;同时,根据对结果的预测,我们可以知道受胁迫的结果肯定是做了,而被期望的义务我们则不确定它一定是被实施了。比如,怀特举例说,由于风暴的影响,每个人不得不弃舟登岸,这个结果我们都知道,肯定是弃舟了;而按照合约,我们应当在十四周内发货,则未必一定被履行了(26)。怀特的结论是:究竟是否有义务,取决于构成强迫的因素是什么,环境,还是规定?如果是环境影响则不能是内心产生“有义务去做”,只有规则规定下才能产生“有义务去做”的心理效应。
佩吉要捍卫怀特的立场,但却修正了他的观点。佩吉提出,怀特所讨论的法律规定下的约束因素,其实也不必然激发内心义务感,因为人们只是在畏惧某种规则的惩罚结果而做某事,并非真正的别无选择;假如人们并不真正介意其违法的后果(罚金等法律处罚),那么法律约定就无法对人们形成真正的约束,产生义务感。比如停车,禁止停车的规定只是告诉人们这里停车会被罚款,而如果不介意被罚款的车主,则可以肆无忌惮地在这里停车。现代法律用相应后果作为威慑规定人们的行为准则,人们在从事这种行为的时候就承担相应的后果。对法律义务的服从,只是对于法律惩戒的畏惧,无法让人们产生“不要在这里停车以妨碍交通”的公民义务感。由此,佩吉纠正怀特说,对规则后果的畏惧也好,对强力威慑的畏惧也好,其实依然是一样的,都并非内心主动觉得这么做是应当的。
强力约束了人们的身体,法律规定了相关的后果,目标则限制了人们的选择,这些都限制了自由,无法激发人们内心的意愿与情操。那么,究竟什么情况下的约束才能成为激发内心义务感的真正因素?佩吉继续论证说,法律的规定无法构成义务感的来源,尤其是,当人们依照法律来履行义务时,看似“应当”,然而,针对那些相互冲突的法律义务,我们又怎样抉择呢?“如果某人有两个相互冲突的法律义务,那么他就被合法地赋予了两个不匹配的行为,其中每一个如果他不做,他都要付出违法的代价”(27)。相对这一点,道德义务(moral principle)是不同的。“一个人由于显然要实现另一个与之冲突的道德义务而没能完成这个,这并不是以道德上的错误为代价而没有完成义务”(28)。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何从道德代价的角度区分“应当(ought)”与“义务”(obliged)?佩吉继续以停车罚金为例讲到,法律规定此处不许停车,并以罚金的后果来威慑。如果我不肯将车挪走,就意味着我并不在乎罚金这种违反法律所带来的相关后果。但这并不是法律的初衷,所谓后果的设立,其实都是法条本身期望人们能够选择去避免它发生的。“除非我们可以决定不去实现我们的义务(比如不去做我们在法律上和道德上有义务去做的),否则谈在两个冲突的义务之间去抉择就是没有意义的”(29)。
因此,在怀特那里由法律规定便是义务,佩吉的论述清晰地提出了两点反对的理由:一是,规则并不一定带来义务,比如下棋,我们必须按照规则走棋,可是我们并没有义务一定要这样做;在佩吉看来,义务,只能更多的是一个道德概念——在他看来,与怀特的结是相反,不是外界的强力,而是要实现遵循规则的目标,才是无可选择的。二是,相对于规则(rules),道德原则对人们内心的约束太强了。在没有任何正式的法律规定的关系上,只有人们在道德上进行选择,才证明“应当”(ought)作为人们产生义务感的正当性来源。比如,佩吉举例说,让自己的研究生进行哲学课题研究,虽然并没有法律规定他一定要帮这个研究生安排工作,但是,似乎作为导师,却怀有义务感去考虑这个研究生将来的前途问题。这种“应当”,佩吉指出,才是义务感在内心形成的真正动力。道德力量在这里起到了避免伤害的作用。不给研究生找工作,不会触犯任何法律,可是却会伤害了研究生的研究动力,这一点,与避免法律责任时的目标追求一样,成为佩吉作为导师内心真正想要尽到的义务。
总之,公民的权利义务由法律的规定而获得,然而公民身份角色意识却并非能单凭法律而产生。当面临选择,能够以道德的“应当”作为实践公民身份行动能力的心理引导,才是真正主体意义上的参与和自决。在这里,政府自然要负起提供公正的公共服务、引导公民角色价值的重要责任。社会的文明、正义与和谐不仅是实现不同公民间的权利义务的平衡分配,也是公民权利意识与义务感的均衡体现。深入体察公民身份角色意识背后的义务感的内涵与形成,可以让我们更加珍视公民身份赋予的权利。法律和道德同样构成了约束,然而,为了共同体的利益而在公共生活中进行合作的义务,实现他人与社会对自己的角色期待,就不仅仅是服从道德与法律,而是服从自我权益与整体目标的明智选择。这,即是一个文明公民的政治态度。
注释:
①(19)[美]乔治·克洛斯科:《公平原则与政治义务》,毛兴贵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页,第5页。
②(21)[英]大卫·休谟:《人性论》(下),贾广来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33页,第376页。
③④⑤⑥(11)Harry L.Hollingworth,"Psychology and Ethics:A Study of the Sense of Obligation",NewYork:the Ronald Press Company,1949,p.17,p.146,p.94,p.100,p.3.
⑦[美]朱迪斯·巴特勒:《权力的精神生活:服从的理论》,张生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页。
⑧⑩A.P.D'Entreves,"On the Nature of Political Obligation",Philosophy,Vol.XLⅢ,No.166(Oct,1968),p316.
⑨M.Oakeshott,Introduction to Hobbes,Leviathan,Oxford,1946,p.lix-lxi.转引 自 A.P.D'Entreves,"On the Nature of Political Obligation",Philosophy,Vol.XLⅢ,No.166(Oct,1968),p314.
(12)(13)(14)[美]史蒂芬·霍尔姆斯凯斯·R.·桑斯坦:《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毕竟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第69页,第170页。
(15)1.共同事业或合作计划的存在;2.由规则来协调的合作努力给那些合作者带来了利益;3.合作要求服从各种各样的限制,因而对合作者来说是一种沉重的负担;4.要产生这种利益,需要一定的人数——通常是大多数人,但不是所有的人参与合作,因此服从必要限制的人不同于其他不服从限制的人(即不合作者)。[美]乔治·克洛斯科:《公平原则与政治义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页,第37-38页,第5页。
(16)[美]A·约翰·西蒙斯:《道德原则与政治义务》,郭为佳、李艳丽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0页。
(17)[18]M.Gilbert,"Group Membership and Political Obligation",Monist,76(1993).
(20)A.D.M.Walker,"Political Obligations and the Argument from Gratitude",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17,no.3(Summer 1988),p195-201.
(22)George Klosko,"Political Obligation and Gratitude",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18(1989),p354。
(23)A.D.M.Walker,"Obligations of Gratitude and Political Obligation",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18(1989)359-364。
(24)(25)Edgar Page,"On Being Obliged",Mind,April 1973.p283.
(26)Alan R.White,"Meaning and Implication",Analysis,October,1971.
(27)(28)(29)Edgar Page,"Senses of Obliged'",Analysis,Vol.33,No.2(Dec.,197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