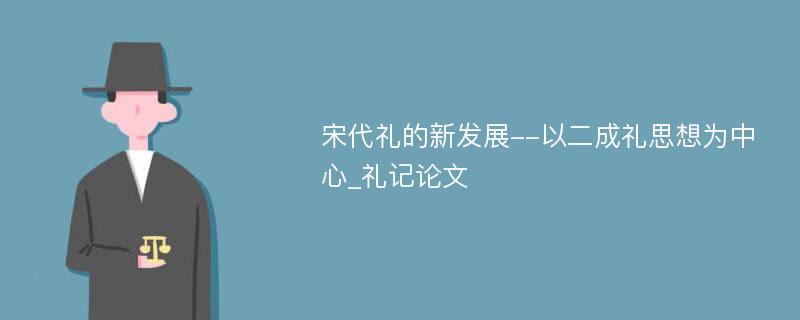
宋代礼学的新发展——以二程的礼学思想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新发展论文,思想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讲到宋代礼学时说:“宋人尽反先儒,一切武断;改古人之事实,以就我之义理;变三代之典礼,以合今之制度;是皆未敢附和以为必然者也。”①刘师培《经学教科书》也认为宋代礼学“掊击古义,穿凿浅陋,殊不足观。”②若从传统经学的立场来看,皮锡瑞与刘师培一主今文,一主古文,二人对经学史的判断、评价有许多看法是不同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但是,他们对于宋代三礼学的叙述与评价,却基本一致。这种看法是有代表性的。学术界普遍认为,宋代的理学是传统儒学发展的高峰,但宋代的礼学则成就不高。当代也有学者认为,宋代是礼学发展的衰微时期。具体来说,宋代虽有王安石《周官新义》与朱熹晚年编撰《仪礼经传通解》,“使此二礼稍有所振”,但总的来说,由于时代风气、学术思潮的变化,“礼学在理学兴起的风气冲击下,失去昔日的兴盛③。
我们认为,宋代是儒学发展的新时期,道学的产生与发展标志着儒学哲学思维发展到空前的高度。宋代的礼学与之前的两汉、魏晋南北朝与之后的清代相比,虽然没有出现有影响深远的三礼注疏作品,也没有清代学者考证辨析之精深,注疏之广博,但依然自成体系,自有特色,在古代礼学的发展史上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具有独特的成就。其中最为显著的贡献之一是礼学思想的空前发达。理学家将礼的思想纳入理学的脉络当中,将礼与天理联系起来,确立了礼的本体地位。这在礼学以及礼学思想发展史上是一次飞跃,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将以北宋时期二程兄弟的思想为例,具体说明理学家对于礼学思想的解释,并由此显示在理学的系统当中对于礼学思想的推进与发展。
二程兄弟是北宋道学的奠基人。他们开创的理学为儒学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在理学的脉络当中自然有其重要的思想史地位。同时,二程也是儒学家,他们对于儒学基本问题的探讨虽然有所侧重,但对某些问题并没有完全回避。对于儒学系统当中重要的礼学,虽然不是二程及理学关注的重点,二程也没有完成过完整的三礼注疏著作,但在流传至今的文集、语录当中也保留有一些解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从义理之学的角度对礼学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从礼学思想发展的角度来看有重要的意义,丰富、发展了儒家礼学思想,同时也是他们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值得重视与研究的。
从二程一生的经历变故来看,熙宁三年(1070年)是一个转折点。此前,他们热烈地议论时政,积极参与变法。此后的十多年间,他们退居洛阳,“玩心于道德性命之际,有以自养其浑浩冲融”④,涵咏天道性命之理,理学思想日渐成熟深化。就在二程思想逐渐转向内在发展的同时,他们并没有放弃对政治与现实问题的关注,还制定了修定礼书以及解经的计划。由此,我们对二程的道学应当有完整的把握。二程创立理学虽然是他们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大贡献,但儒学传统依然是理学产生与发展的背景。
传统礼学研究属于经学的范围,二程倡导义理之学,对经学不甚用力,而且认为训诂是为学的弊病之一,多次指出,“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187页),将文章、训诂与异端并列,表达了他们对传统以训诂为主的经学的强烈不满。
流传至今的二程著作当中,完整的经学著作只有程颐的一部《周易程氏传》,其他关于《诗》、《书》、《春秋》以及三《礼》只有一些零散的解说,不成系统。
据文集记载,程颐也有修订礼书的计划:
问:“先生曾定六礼,今已成未?”曰:“旧日作此,已及七分,后来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则当行之朝廷,不当为私书,既而遭忧,又疾病数年,今始无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闻有《五经解》,已成否?”曰:“惟《易》须亲撰,诸经则关中诸公分去,以某说撰成之。《礼》之名数,陕西诸公删定,已送吕与叔,与叔今死矣,不知其书安在也?然所定只礼之名数,若礼之文,亦非亲作不可也。《礼记》之文,亦删定未了,盖其中有圣人格言,亦有俗儒乖谬之说。”(《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239-240页)
程颐又说:“某旧曾修六礼,将就后,被召入朝,今更一二年可成。家间多恋河北旧俗,未能遽更易,然大率渐使知义理,一二年书成,可皆如法。”(《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240页)程颐“被召入朝”是在元祐元年(1086年)。按照程颐自己的说法,他修定六礼是在此之前。据上引程颐之言,程颐也有训解经典的完整规划,只是由于各种原因而最终没有完成。今存的《周易程氏传》应是这项计划中的一部分。按照程颐本人所言,《周易传》是他亲自所作,《三礼》则是按照他的指导原则,由精于礼学的三吕等人分头完成。由于吕大临“寿不永”,这项计划也只能中断了。但是,由程颐所言可知,他依然没有放弃这项计划。按照程颐的设想,虽然由于吕大临的早逝而影响到修定礼书的计划,但他认为,交付吕大临的工作只是具体的“礼之名数”,而具有指导性、原则性的“礼之文”,也就是礼的义理,还须由他亲自完成。言下之意,修定礼书的工作不会因吕大临的早亡而中断,吕大临的早亡也不会在根本上影响礼书的修定。但最终的结果是,程颐的修定六礼及《五经解》这样庞大的规划并没有完成。
就《三礼》来说,二程确实提出了一些精辟的看法。例如对于《周礼》,认为“《周礼》之书多讹阙,然周公致太平致法亦存焉,在学者审其是非而去取之尔”(《河南程氏粹言》卷一,《二程集》,第1201页)。有门人问“《周礼》之书有讹缺否?”程颐回答曰:“甚多。周公致治之大法亦在其中,须知道者观之,可决是非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230页)这是说,虽然《周礼》也讹缺之处,但其根本则是周公致太平之法,肯定了《周礼》在儒家经典中的神圣地位。
关于《仪礼》,有门人问程颐“如《仪礼》中礼制,可考而信否?”程颐回答曰:“信其可信。如言昏礼云,问名、纳吉、纳币皆须卜,岂有问名了而又卜?苟卜不吉,事可已邪?若此等处难信也。”(《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上,《二程集》,第286页)
关于《礼记》,二程认为:
秦氏焚灭典籍,三代礼文大坏。汉兴购书,《礼记》四十九篇杂出诸儒传记,不能悉得圣人之旨。考其文义,时有抵牾。然而其文繁,其义博。学者观之,如适大通之肆,珠珍器帛随其所取;如游阿房之宫,千门万户随其所入。博而约之,亦可以弗畔。盖其说也,粗在应对进退之间,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于童幼之习,而终于圣人之归。惟达于道者,然后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后能得于礼。然则礼之所以为礼,其则不远矣。(《河南程氏文集·遗文》,《二程集》,第669页)
这些都是相当有见地的看法,但惜之简略,没有把它们详细地贯彻到他的礼书训解当中。程颐在文集当中有《婚礼》、《葬说》、《葬法决疑》、《记葬用柏棺事》、《作式主》、《祭礼》几篇,以及对《大学》的改正⑤。我们可以合理推想,如果程颐完成了他的礼经训解工作,其中必然会有对这些观点的进一步的推演与发挥。
二程不仅在思想方面对儒家礼学多有创见,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也时刻谨守礼仪规范,保持了儒者的本色。据文献记载:
有人劳正叔先生曰:“先生谨于礼四五十年,应甚劳苦。”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劳何苦?它人日践危地,此乃劳苦也。”(《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二程集》,第8页)
伊川主温公丧事,子瞻周视无阙礼,乃曰:“正叔丧礼何其熟也?”又曰:“轼闻居丧未葬读丧礼。太中康宁,何为读丧礼乎?”伊川不答。邹至完闻之曰:“伊川之母先亡,独不可以治丧礼乎?”(《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一,《二程集》,第416页)
黄百家还指出,程颢“于兴造礼乐,制度文为,下及兵刑水利之事,无不悉心精炼。使先生而得志有为,三代之治不难几也。”⑥由这些记载可知,二程熟悉礼仪典制在当时也是得到众人认可的。这再次提醒我们,对于道学应该有全面的认识,不能简单地认为道学家讲理就忽视了礼。
关于程颐的礼学著作,有一个问题需要稍加讨论。今中华书局《二程集》之《河南程氏文集》后附有“遗文”,其中收录有《礼序》一篇,同时还有《易序》一篇。在朱熹所编的二程文集、语录等著述中,并未提及《易序》与《礼序》二文,因此后人便怀疑这两篇文字并非程颐的作品。
《易序》、《礼序》原收录在宋人熊节编的《性理群书句解》当中。熊节为朱熹弟子,《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是书采摭有宋诸儒遗文,分类编次。”⑦后元代谭善心所辑的《程子遗文》,收录了《易序》与《礼序》二文,以为程颐遗文。但是,今四库全书所收录的《性理群书》,于《易序》下署名为朱熹。《礼序》一文未署名,但置于《易序》和朱熹《诗集传序》之间,从这样的排序来看,也是以此篇为朱子所作。另,《易序》与《礼序》二文还见于程颐弟子周行己的《浮沚集》,名为《易讲义序》和《礼记讲义序》。由此可见,关于《礼序》一文的作者,有程颐所作、朱子所作和周行己所作等不同的看法。
今本《周行己集》的校点者周梦江先生认为,《易序》与《礼序》二文为程颐所作,“据估计,周行己当时传授洛学时,有可能将老师这两篇文章当作讲学授徒的教材,以后他身殁异乡,而整理周氏文集的人未加审察,遂将两文编入《浮沚集》。”⑧但后来,周梦江先生又对这一说法有所修订,认为《易讲义序》可能为程颐作,而《礼记讲义序》则是周行己自著⑨。周梦江先生两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是没有做进一步的论证。⑩认为《礼序》为程颐或周行己的作品,其实在文献上都没有其他坚实的证据,我们很难做出确切的判断。程颐、周行己为师弟,学术思想本身就有传承,由于思想的相似性,在编订二程文集的时候收入弟子的文章也不是没有可能,如《程氏经说》中就收录了本为吕大临所作的《中庸解》。这种类似情况出现在《礼序》、《易序》这两篇文章上也有可能。
《礼序》一文约五百字,整体论说并未超出儒家礼学思想的范围,把它与程颐整体思想相比量,也没有提出新颖的看法。在程颐的礼学思想以及整体思想当中,增加或减少这样一篇文章,并不会影响我们对程颐思想的评价。因此,既然今本《二程集》中的《礼序》一文是否为程颐所作还有疑问,我们在研究二程的礼学时,暂且将这篇文章存疑。
二程治经,明确主张要探讨经典当中的义理。二程说:
治经,实学也,譬诸草木,区以别矣。道之在经,大小远近,高下精粗,森列于其中。譬诸日月在上,有人不见者,一人指之,不如众人指之自见也。如《中庸》一卷书,自至理便推之于事。如国家有九经,及历代圣人之迹,莫非实学也。如登九层之台,自下而上为是。人患居常讲习空言无实者,盖不自得也。为学,治经最好。苟不自得,则尽治五经,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识违,所得多矣。有虽好读书,却患在空虚者,未免此弊。(《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二程集》,第2页)
二程认为,经学为实学,但他们所理解的实学与汉人以训诂考证、疏解名物制度为主的实学相距甚远。他们所谓的“实”,是与佛老的“虚”相对应的,其实也就是儒学以及儒学的核心价值。二程认为,研究经典首先要先识得儒家经典中的义理即道。就《三礼》来说,由于去古久远,经典本身就有缺漏,礼书本身的特殊性质造成了礼学研究中对于名物典章训释的不断纷争,因此更显得义理的重要。“古之学者,先由经以识义理。盖始学时,尽是传授。后之学者,却先须识义理,方始看得经。”(《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二程集》,第164页)二程认为,“孟子之时,去先王为未远,其所学于古者,比后世为未却也,然而周室班爵禄之制,已不闻其详矣。今之礼书,皆掇拾秦火之余,汉儒所傅会者多矣,而欲句为之解,字为之训,固已不可,又况一一追故迹而行之乎?”(《河南程氏粹言》卷一,《二程集》,第1206页)他们认为,通过训诂考证来恢复古代礼制的全貌并由此探寻三代圣王之治是不可能的,这其实从方法论和价值层面上根本否定了汉唐礼学。在他们看来,礼学的研究,探求义理更加重要,如程颐说:“大凡礼,必须有义。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七,《二程集》,第177页)
传统儒家的专长在伦理制度方面,礼学研究的名物制度的考证、礼仪制度的疏解,正是儒家所认为的规范社会的必要手段。而二程洛学则展开了对传统儒家并不看重的“性与天道”的讨论,将儒家的义理之学发展到空前的理论高度,并进而形成了理学。儒家传统的礼学与新兴的理学是何关系?理学的兴起是否意味着对传统儒学的彻底超越?对于理学的发展来说,这也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二程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与解决,主要体现在礼与理的关系方面。
其实,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思索礼的形上依据与意义。据《左传》记载,子大叔曾引子产之言:
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子大叔也说:
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齐晏婴又说:
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天”是早期儒学继承西周以来的思想所认为的最高的哲学观念。将礼与天地并列,认为礼是天地之经纬,这表明了早期思想家试图为中国古代文化当中最为重要的礼寻找哲学依据的努力。至战国中后期,这种将礼哲学化的努力终于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就,阴阳五行的哲学图式与礼学思想相结合。这在《礼记》当中有明确的反映(11)。另外,儒家还一直认为礼来源于圣人的制作,但是圣人也是根据天地的法则来制定礼:
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
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
礼与天地并立,儒家所传承的礼的哲学依据就是战国时期流行的阴阳五行哲学范式。圣人因天地而制礼,本质上也是对这种思想的另一种表述。战国时期确立的思想一直是延续到汉唐礼学的哲学范式。宋代儒学的发展,一方面反对汉唐的注疏训诂学,同时也反对玄学、佛学的以虚空为本的本体论。二程天理论的建立,就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之下完成的。在这种思想背景之下,二程认为礼即天理,使礼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这对于礼学以及儒学的发展都是一个飞跃。
如果仅就文字疏解来看,在《礼记》以及先秦文献当中对于礼与理的关系其实早已有明确的说明。比如:
《礼记·仲尼燕居》:“子曰:礼也者,理也。”
《礼记·乐记》:“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礼记·乐记》:“乐者,通伦理者也。”
《管子·心术上》:“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礼,理因乎宜者也。”
这些文献当中所涉及的“理”,其含义仅为事物之条理,如郑玄说:“理,犹事也”。从战国后期到两汉经学,儒家礼学的哲学基础都是天地阴阳五行结构。这样,《礼记》以及先秦文献当中所说的礼者理也,就不具有理学意义上的哲学本体论的意义。
在北宋道学的发展过程中,二程的老师周敦颐以及比二程年纪稍长的张载均明确提出了“礼者理也”的看法。周敦颐说:“德:爱曰仁,宜曰义,理曰礼,通曰智,守曰信。”(12)又说:“礼,理也;乐,和也。”(《通书·礼乐第十三》,《周敦颐集》,第24页)但是,周敦颐并未对这些说法作进一步的说明与解释,因此,仅凭这些论断来看,他所说的“礼,理也”还是在与《礼记》同等的层次上,理还不具有作为本体的天理的含义。
张载说:“礼者理也”(13)。张载这里所说的理已经具有了本体的意义。正如余敦康先生所指出的,“在儒学史上,把儒家所服膺之礼提到天道性命的哲学高度进行系统的论证,从而为礼学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应以张载为第一人。”(14)这个评价可谓公允。但是,张载的思想以气为本,天理在张载的思想中并不占主要地位,因此,张载虽然也认为礼者理也,但他并没有对这个命题作进一步的充分解说。
二程以天理作为最高的哲学范畴,创立了理学。二程虽然性格、思想均有异处,但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均以理为最根本的哲学范畴与哲学本体。二程洛学之所以成为理学的奠基,在理学发展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就在于他们最终坚定地确立了理作为最高宇宙本体的权威。他们的天理不是佛教华严宗的理,也与中国传统道家、玄学划清了界线,就在于他们所确立的是“儒理”。对于儒学所传承的礼,他们都认为“礼者,理也”:
礼者,理也,文也。理者,实也,本也。文者,华也,末也。理是一物,文是一物。文过则奢,实过则俭。奢自文所生,俭自实所出。故林放问礼之本,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言俭近本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二程集》,第125页)
礼亦理也,有诸己则无不中于理。(《河南程氏外书》卷三,《二程集》,第367页)
正如“天理”早在先秦文献中就已经出现,但程颢依然要说“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己体贴出来”一样,“礼者理也”同样在先秦就已出现,但二程的解释,却与先秦文献中的意义完全不同。二程说“礼者理也”,这里的“理”的意义已经不是先秦文献如《礼记》当中的含义了,而是具有本体意义的天理。这就是二程将礼等同于理的思想史意义。对于张载、二程礼即天理的思想,过去一般认为这是将封建社会的等级名分转变“成为天经地义的永恒真理”(15),“用‘理’把作为当世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道德风俗的‘礼’,从本质上规定为永恒不变的天道运行的客观规律”,“达到了使封建伦常本体化、永恒化的理学目的”(16)。这样的认识与评价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缺少了理论层面的梳理,将复杂的思想史的问题简单化了。如果我们从礼学思想的发展及其与理学的关系的角度来看,“礼即理”在理论上具有以下三层含义。
首先,在二程的思想结构中,理与礼的关系可以理解为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理与气的关系。
在儒家传统思想当中,《易传》已经提出了形而上与形而下、道与器的区别,形而下、器是可见的现象世界,形而上、道是无形的本质。在二程的理学系统中,与这一对范畴类似的是理与气。礼作为有形的礼器、礼制以及社会发展的文明形态是可见的,应当属于气的层面,但其本原则是理。程颐说:“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二程集》,第162页)道与气的关系、道与阴阳的关系,可以平行移至理与礼的关系上。二程虽然重视理,但并没有忽视气,理气虽然有形上形下的区分,但二者是一贯的。同理,理与礼也应是一贯的,不能割裂。二程说:“本末,一道也。父子主恩,必有严顺之礼;君臣主敬,必有承接之仪;礼逊有节,非威仪则不行;尊卑有序,非物采则无别。文之与质,相须而不可缺也。”(《河南程氏粹言》卷一,《二程集》,第1171页)程颐又说:“皆是一贯,不可道上面一段事,无形无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来,教入途辙。”(《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二程集》,第153页)从哲学理论上说,这是对既往哲学,包括理学先驱人物邵雍、周敦颐等人的批评,认为他们将本末分为两截,只注重“上面一段”,即无形的本体,而忽视了人事,将形上形下分作两截,这就不是一贯的了。
理与礼的形上形下关系,还可以从二程对《易》理的解说中来看。张载曾指出:“生有先后,所以为天序;小大、高下相并而相形焉,是谓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后经正,知秩然后礼行。”(《正蒙·动物篇》,《张载集》,第19页)社会秩序是从天序天秩中推导出来的。二程将易理归结为天理。他们说:
“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即是善也。(《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第29页)
大易的生化,是宇宙万物的流行,同时也是人类社会产生的本源。二程又说:“所以谓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只为从那里来。‘生生之谓易’,生则一时生,皆完此理。”正因为如此,“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既是自然之理,同时也是社会秩序。程颐说:
夫物之聚,则有大小之别,高下之等,美恶之分,是物畜然后有礼,履所以继畜也。履,礼也。礼,人之所履也。为卦,天上泽下。天而在上,泽而处下,上下之分,尊卑之义,理之当也,礼之本也,常履之道也,故为履。履,践也,藉也。履物为践,履于物为藉。(《周易程氏传》卷一,《二程集》,第749页)
天在上,泽居下,上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当如是,故取其象而为履。君子观履之象,以辨别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后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后可以言治。(《周易程氏传》卷一,《二程集》,第750页)
程颐在其《易传》中明确指出,人类社会的规则秩序之礼是自然之理的摹写与体现,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传统的儒家认为礼是圣人(如周公)制作的,但理学家将礼的本源上升到了天理的层面,这样就从本质上提升了礼的意义,人间的社会秩序也因此具有了本体的意义。
其次,理与礼的关系也是体用的关系。宋明理学成为儒学以及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高峰,其中一个原因(或表现)就在于理学家对于概念范畴的使用更加丰富,更加严谨。体用与理气、形上形下、道器等范畴相关,但又有所不同。体用是理学家表示本体与现象的一对范畴。理与礼的关系是体与用,也就是本体与现象的关系。
朱熹指出,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已经包含了“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道理:
盖尝窃谓先生之言,其高极乎无极太极之妙,而其实不离乎日用之间;其幽探乎阴阳五行造化之赜,而其实不离乎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之际。其体用之一源,显微之无间,秦汉以下,诚未有臻斯理者。(17)
周敦颐描绘的“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以至于“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包括人类的产生,都是宇宙万物的化生流行,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是,人在万物之中“得其秀而最灵”,圣人又为人制定了道德与规则,使人与动物以及其他万物有了本质的区别。周敦颐继承了传统儒家沟通天人关系的思路与精神,认为人以及人类社会与自然过程是一体的。周敦颐还对《太极图说》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是万为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小大有定。”(《通书·理性命第二十二》)从宇宙万物的生成这个角度来说,这一段话比《太极图说》更加抽象,且没有了容易引起歧义的“无极”,因此“二本则一”之“一”就是太极。太极通过二气五行的运作产生了万物,万物最终又反归于太极,这个过程周敦颐称之为“是万为一,一实万分”,万是现象,一是本体。本体与现象之间是畅通无碍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具体到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社会制度与宇宙本体之间的关系来说,也是这个道理。程颐在《易传序》中把他的思想概括为“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这本来是程颐研究易学,就易之卦象、卦爻辞与卦象后面所蕴含的义理之关系而言的。从易学方面来看,程颐认为探求《周易》义理离不开易象,理与象,是微与显的关系,卦象与卦义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从哲学角度来看,程颐所讨论的也是理与事的关系,即本质与现象的关系。他说:
至显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显一源。古之君子所谓善学者,以其能通于此而已。(《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二程集》,第323页)
易学的体用一源也就是理事一致。程颐提出这样的看法,从哲学角度来说,是为了说明万象具于万理之中,即事而求理。人类社会的礼仪制度、父子君臣之伦作为“事”,它们同样也具有理,而且理与礼是一致的,是体用关系,而且“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因此是“一贯”的,“不可分本末为两段事。洒扫应对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二程集》,第148页)。作为社会规范与制度的礼是其然,它的后面必有其根本(所以然),这个“本”就是理。
二程认为,体用不可分离,“圣人,凡一言便全体用。”(《河南程氏外书》卷七,《二程集》,393页)在二程看来,这是儒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作为礼仪规范、纲常名教与社会制度的礼与最高的哲学本体天理是贯通一体的,也不可分离。
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指出,明道为学,“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悌;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二程集》,第638页)尽心知性、穷神知化,虽然是理学对形上学的努力追寻,但它依然本于儒学的孝悌、礼乐。程颐对“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还有进一步的解释:“此句须自家体认。人往往见礼坏乐崩,便谓礼乐亡,然不知礼乐未尝亡也。如国家一日存时,尚有一日之礼乐,盖由有上下尊卑之分也。除是礼乐亡尽,然后国家始亡。虽盗贼至所不为道者,然亦有礼乐……礼乐无处无之,学者要须识得。”(《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225页)礼乐普遍存在于现实社会当中,无处不在,因此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去体认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论语·子张》篇记载: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子游与子夏虽然对洒扫应对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都认为礼有本末、先后、大小等区分,洒扫、应对、进退仅仅是礼之末节。就《论语》以及先秦儒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区分是合理的。但是,从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说法就有割裂本末的倾向与危险。程颢说:“洒扫应对便是形而上者,理无大小故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三,《二程集》,第139页)《粹言》又有:“形而上者,存于洒扫应对之间,理无大小故也。”(《河南程氏粹言》卷一,《二程集》,第1175页)程颐也说:“圣人之道,更无精粗,从洒扫应对至精义入神,通贯只一理。虽洒扫应对,只看所以然者如何。”(《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二程集》,第152页)在二程看来,洒扫应对等仪节是礼的外在表现形式,其中同时也蕴含了形上之道与天理,上下本末是贯通一体的,不应有所偏废。所以程颐又说:“洒扫应对至于穷理尽性,循循有序”(《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二程集》,第638页)。
二程的这些解释被朱子收入到《论语集注》当中。其实,从义理方面来看,二程的解释与《论语》原文已经有了差异,因此王夫之说,二程的解释“又别一理,非子夏之意,且不须看,未能了彻,徒增惑乱。”(18)但从二程的思想来看,他们将洒扫应对的礼仪实践同天理贯通起来,并且用“体用一源”的思想加以解释,这样一来,不仅具体的礼仪形式有了更高的本体的理论依据,而且也扩展、完善了二程本人的儒学思想,使他们的理论的一致性在更加宽泛的层面得以印证。
程颐还认为,洒扫应对的日常礼仪实践同时也是格物穷理的过程。他说:“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皆穷理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188页)二程主张从日常洒扫应对的礼仪实践中体认天理,因此他们对《论语·乡党》篇十分推崇。《乡党》一篇在《论语》书中极为独特,全篇以记载孔子的日常生活为主要内容。孔子是主张“复周礼”的,他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正是贯彻周礼的体现。二程认为,“《乡党》分明画出一个圣人出。”(《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上,《二程集》,第294页)《乡党》一篇所刻画的其实才是孔子之道。他们说:
孔子之道,发而为行,如《乡党》之所载者,自诚而明也。由《乡党》之所载而学之,以至于孔子者,自明而诚也。及其至焉,一也。(《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二程集》,第323-324页)
学圣人者,必观其气象。《乡党》所载,善乎其形容也,读而味之,想而存之,如见乎其人。(《河南程氏粹言》卷二,《二程集》,第1234页)
二程主张“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孔子的日常生活礼仪与孔子之道正是这个理论的一个完美诠释。理为体,礼为用,二者虽有分际,但又是上下贯通一体的,于日常礼仪中体认天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的日常礼仪实践获得了本体的意义。
第三,二程所说的礼即理也,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是体用一源的关系,这表明他们所体认的天理是儒理,天理不仅具有严密的哲学含义,而且还有明确的社会内涵,这样,理学的天理论就与释老二氏严格地划清了界限。
对于儒家学者来说,礼是儒家所尊崇的三代文明的象征与结晶。礼不仅表现为具体的名物制度与行为规范,而且还是社会形态与文明形态的体现。东汉后期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儒学的衰微,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礼坏乐崩的时代。随着中唐以来的儒学复兴运动,北宋时期欧阳修大力辟佛,提出用儒家的礼来排佛,这在儒学复兴的过程中自然是很必要的,也有其思想史意义,但是另一方面,欧阳修坚决反对心性之学,对儒学的义理缺乏深入的体认,因此他所提倡的礼义还显得很空泛,没有在整体上对礼与礼学的发展有所推进。北宋时期重视礼学的还有李觏和王安石。但是在二程看来,他们重视的礼过于实用,只重视礼在现实社会政治中的功能,而没有为礼提供进一步的理论解释,这样的礼还是不完善的。
二程提出“礼即理”,表明他们所竖立的天理是儒理。前人在论及中国古代易学的发展时曾指出:“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四库全书总目·易类》,第1页)二程天理论的建立,深受佛教华严宗、禅宗等教义思想的影响,程颐借用华严宗的一些思维方法解释《周易》而提出的“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连他的门人弟子都觉得“太洩露天机”(《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二程集》,第430页),这说明如果纯粹从理的角度来说,二程的天理论与佛教思想有时确实难以划清界限,程颐本人也承认“佛说直有高妙处”(《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二程集》,第425页),“未得道他不是”(《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195页)。但是从整体上来说,二程的天理论又不是佛教理论的翻版。程颐通过易学的研究,体悟出来的是儒学的宇宙本体论与价值论。天理不是虚空、高悬在上的哲学范畴,而是充实的,也是真实的,是人间社会秩序的反映,父子君臣等人伦关系建构了、同时也限定了天理的内涵。这样的天理符合儒学的要求,与佛教一些宗派有关理的思想有了本质的区别。
程颐说:“推本而言,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只此两字,含畜多少义理。”又问:“礼莫是天地之序,乐莫是天地之和?”曰:“固是。天下无一物无礼乐。且置两只椅子,才不正便是无序,无序便乖,乖便不和。”又问:“如此,则礼乐却只是一事。”曰:“不然。如天地阴阳,其势高下甚相背,然必相须而为用也。有阴便有阳,有阳便有阴。”(《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225页)这一段文字可以看作程颐礼学思想的一个简单概括。礼乐中蕴含了天地万物的普遍道理,程颐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是在其理学思想背景之下才可以理解的。正是在其理学的照射之下,礼即理才具有了哲学意义,同时也成为礼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次本质的飞跃。
在宋代儒学复兴的过程中,道学的兴起并最终成为主流的思想形态,除了社会政治等一些外在因素之外,道学在理论上所坚持的儒学本位立场以及其自身的理论成就,是根本的内在因素。理学天理论的建立,在理论上所针对的主要对象是玄学以无为本的本体论和佛学以现实世界为虚空的世界观。程颐提出的理事一致说,理与礼是体用一源的关系,都是对玄学以及佛学的否定,并且从各个方面正面肯定儒学的立场。他们将儒学的核心观念礼与天理等同起来,这就在哲学本体论上确立了礼的思想基础,是礼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飞跃。
在儒学发展的历史上,自孔子开始,仁与礼一直是儒学的两端,处在相维相异的关系之中。人的内在德性与社会秩序、礼乐制度是儒学的两端。仁与礼之间的张力,恰好也是儒学发展的内在动因。
理学是哲学化的、思辨化的儒学新形态。以天理作为哲学本体的理学体系的建立,是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重大飞跃。飞跃提升则有矣,但是儒学的本质并未改变。儒学以伦常日用、社会秩序为标识的礼,在天理论的体系当中如何安置,依然是理学以及儒学发展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礼者理也”固然赋予了礼以本体的地位与意义,但另一方面,又出现了所清儒所批评的“以理易礼”的思想倾向。如何平衡处理理与礼的关系,天理与社会秩序、本体与方法的问题,同时也影响甚至决定了宋明道学的发展。从某一方面,对《论语》“克己复礼为仁”一句的诠释,也展现了道学思想发展的路径。从二程发其端,历二程弟子的诠释与传承,直至朱子《论语集注》为其大成,展现了宋代理学关于天理及其落实与展开的思想历程。
《论语·颜渊》篇记载: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据《左传》记载,孔子曾说:“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左传·昭公十二年》)从训诂上来说,对于此章“克己”、“复礼”的解释,一直是汉学、宋学争论的焦点。从义理上来说,二程以及朱子等人的诠释,又是我们理解理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
在二程关于“克己复礼”的训解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对“己”的解释。何晏《论语集解》引马融曰:“克己,约身也。”皇侃《义疏》也认为,“克”训为“约”,“己”训为“身”:“言若能自约俭己身,反返于礼中,则为仁也。”(19)释“克己”为约身、修身,这是汉代学者一贯的解释。但汉代杨雄曾说“胜己之私之谓克”,隋刘炫又说:“克,胜也。己,身也。身有嗜欲,当以礼仪齐之,嗜欲与礼仪战,使礼仪胜其嗜欲,身得复归于礼,如是乃为仁也。复,反也。言情为嗜欲所迫,已离礼而更归复之也。克己复礼,谓能胜去嗜欲,反复于礼也。”(20)这个解释已经将“克己”解释为胜己之嗜欲,因此理学家对刘炫的这个解释评价颇高,朱熹说:“炫言如此,虽若有未莹者,然章句之学及此者,亦已鲜矣。”
至二程,则明确将“己”解释为“私”。程颢说:
克己则私心去,自然能复礼。(《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二程集》,第18页)
《遗书》记载程颐之言曰:
棣又问:“克己复礼,如何是仁?”曰:“非礼处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须是克尽己私后,只有礼,始是仁处。”(《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上,《二程集》,第286页)
克己之私既尽,一归于礼,此之谓得其本心。(《河南程氏粹言》卷一,《二程集》,第1199页)
清毛奇龄《四书改错》指出:“至程氏直以己为私,称曰己私,致朱注谓身之私欲,别以‘己’上添‘身’字,而专以‘己’字属私欲。于是宋后字书皆注‘己’作‘私’”(21)。
从训诂上讲,如果将“己”解释为“私欲”,那么下文的“为仁由己”该如何解释?阮元就指出:“己字即是自己之己,与下文‘为仁由己’相同。若以‘克己’己字解为私欲,则下文‘为仁由己’之‘己’断不能再解为私,与上文辞气不相属矣。且克己不是胜己私也。”(22)戴震等人对此都有辩驳。这也成为汉宋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
其次,二程将“克己复礼”之“礼”解释为理。以理释礼,将礼等同于理,这是二程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时也是儒家礼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重要的理论飞跃,上文已有详细的论述。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二程理解上的差异。在“克己复礼”这个过程中,程颢比较看重克己。《遗书》记载:
持国尝论克己复礼,以谓克却不是道。伯淳曰:“克便是克之道。”(《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二程集》,第28页)
程颢还指出,如果能做到克己,“自然能复礼,虽不学文,而礼意已得。”(《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二程集》,第18页)又说:“克己最难。《中庸》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二程集》,第128页)程颢引《中庸》的意思是要说明,克己有如中庸,是一个可望但不可及的、“不可能”达到的标准,所以说“克己最难”。
伊川则重视复礼的过程。他说:“敬即便是礼,无己可克。”(《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二程集》,第143页)《粹言》还说:“纯于敬,则己与理一,无可克者,无可复者。”(《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二程集》,第1171页)这一条没有记录为何人所言,相比较,应当也是程颐的看法。
由于程颐训己为私,训礼为理,因此他很自然地将克己复礼转换为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儒家经典《礼记·乐记》当中有“灭天理而穷人欲”,将天理与人欲相对立。《古文尚书·大禹谟》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程颐解释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四,《二程集》,第312页)程颐还说:
视听言动,非理不为,即是礼,礼即是理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人虽有意于为善,亦是非礼。无人欲即是天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二程集》,第144页)
程颐将《论语》的“克己复礼”解释成为天理与人欲的对立,要灭人欲而存天理,因此,通常便认为程颐的主张是禁欲主义。其实,对于这个问题,还应该作进一步的梳理。程颐曾分别儒佛的区别:
释氏多言定,圣人便言止。且如物之好,亦自在里。故圣人只言止。所谓止,如人君止于仁,人臣止于敬之类是也。《易》之《艮》言止之义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随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201页)
程颐特别重视《艮卦》。他说:“看一部《华严经》,不如看一《艮》卦。”(《河南程氏遗书》卷六,《二程集》,第81页)在程颐看来,佛教才是主张抛弃一切欲望情欲与人伦的彻底的禁欲主义,而儒学的规定是“止”,即止其所不当为。这其实就是礼的规定。因此,在天理人欲的问题上,我们还应当看到礼的调节作用,而不能简单地将之归结为禁欲主张。
从整体上来看,程颐将克己复礼用天理人欲做了重新的解释,将儒学的传统问题转变为一个理学的问题,在这个转换当中,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礼,仅剩下了天理,这自然引起了许多争论与讨论,而且同样也反映出程颐在礼与理的问题上还有不周延的方面,还有待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来弥补这个理论上的缺陷,从而更加完善儒学的理论体系。
第三,二程对“克己复礼为仁”的解释,在某种意义上扭转了儒学发展的方向。
孔子以仁释礼,将克己复礼看作是实践仁的具体途径与方法,传统的礼与新起的仁连结在了一起,仁与礼成为孔子思想的两个重要方面。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孔子的思想究竟以仁为主还是以礼为主?对此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就先秦儒学的发展来说,虽然一般而言,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学,荀子继承了孔子的礼学,但是总体上,我们更加倾向于承认,战国至两汉的儒学发展是以礼学也就是政治思想与政治哲学为主的。
在北宋儒学复兴的过程中,欧阳修、李觏等人提倡礼,但是由于现实社会政治变化等各种原因,以仁为集中体现的儒家心性之学与道德哲学逐渐成为儒学继续深入发展的方向。王安石撰写的《淮南杂说》世人比之以孟子,由此开启了士人关于道德性命之学的研究。二程在解释“克己复礼为仁”的过程中,虽然对于“克己复礼”的解释有所偏重,并且将礼解释为天理,也提升了礼的地位,可是在整体上二程更加注重仁的价值与意义,如他们所说:“克己复礼,乃所以为道也”(《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二程集》,第3页),克己复礼只是达到仁的手段和途径。儒学发展的重心开始倾斜了。
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二程集》,第16-17页)
程颢的这段话被后来的道学家们尊称为《识仁篇》。黄宗羲指出:“明道之学,以识仁为主。”其实,程颐也有相近的看法。他曾说:“学之大无如仁。”(《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二程集》,第433页)又说:“且如六经,则各有个蹊辙,及其造道,一也。仁义忠信只是一体事,若于一事上得之,其他皆通也。然仁是本。”(《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193页)
二程以“先识仁”作为切入儒学的方法路径,体现了他们对于儒学本质特征的理解。二程虽然也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视听言动一于礼之谓仁,仁之与礼非有异也。”(《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二程集》,第322页)但其实,他们更加重视的是仁。仁是根本。“仁义礼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体;四者,四支。”(《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二程集》,第14页)“仁载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谓义,履此之谓礼,知此之谓智,诚此之谓信。”(《河南程氏外书》卷一,《二程集》,第352页)从这些解说可以看出,虽然儒家历来讲仁义礼智信五常,但在二程的理解当中,仁与其他四德的关系并非并列、同等的,而是超然于其他四者之上,是其他四德的根本。二程对仁如此重视,在他们的理解当中,儒学的本质应当是仁学。与先秦儒学相比,二程对儒学的理解与定位发生了某种偏离。对仁的重视与突出,使儒学在理论上逐步走上内在心性义理之路。
二程将儒学定位为仁学,虽然他们在理论上也明确肯定了礼的地位与意义,强调洒扫应对等礼仪实践的重要性,但是从整体上来说,他们还是更加突出了仁的优先性。二程后学对礼的解释表现出某种空虚化的倾向,也与此有一定的关系。直至朱子对于仁与礼一再诠释,并且通过晚年编订礼经,全面探讨了礼仪制度、礼学思想在理学以及在儒学中应有的位置与意义,这样,礼在理学内部最终有了较为坚实的基础,由此也显示出理学作为儒学新形态的最终完成。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这是以如何解释、摆放礼在儒学中的地位和意义来判断的。朱子最终完成了这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则是从二程开始的。这也是我们为何要探讨二程的礼学思想在儒家礼学的发展以及宋代理学形成过程中的意义了。
①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84页。
②刘师培:《经学教科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9-110页。
③参见林存阳《清初三礼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85-86页。
④《河南程氏遗书》附录《门人朋友叙述并序》,《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32页。
⑤今本二程文集中还有《中庸解》一篇(见《河南程氏经说》卷八),朱子等已经指出系吕大临的作品。
⑥《宋元学案》卷十四《明道学案》下,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580页。
⑦《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787页。
⑧参见《周行己集》校点者“前言”,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⑨参见《二郑集》校点者“后记”,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199页。
⑩也有学者考证《礼序》为周行己所作。参见石立善《〈礼序〉作者考》,收入彭林主编《中国经学》第六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11)参见刘丰《先秦礼学思想与社会的整合》第二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0-99页。
(12)《通书·诚几德第三》,《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5页。
(13)《语录下》,《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326页。
(14)余敦康:《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348-349页。
(15)参见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1页。
(16)陈俊民:《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2页。
(17)朱熹:《隆兴府学先生祠记》,《文集》卷七十八,《朱子全书》第二十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748页。
(18)参见黄怀信《论语汇校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682页。
(19)参见黄怀信《论语汇校集释》,第1061页。
(20)参见朱熹《论语或问》卷十二,《四书或问》,《朱子全书》第六册,第798页。
(21)参见黄怀信《论语汇校集释》,第1063页。
(22)参见黄怀信《论语汇校集释》,第10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