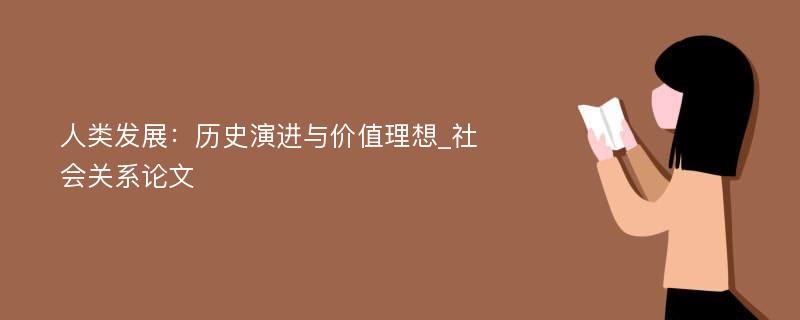
人的发展:历史演进与价值理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想论文,价值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194(2000)01-0008-05
一
一部人类历史,就是人争取解放与发展的历史。在交叉缠结、羁绊着人的重重矛盾中,归根到底,无非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在遭遇矛盾和解析矛盾的过程中,人类始终不渝地把关注自己命运的现实和未来作为追求的动力和目标,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和不同意义上,产生了种种谋求解放与发展的学说,表达了人类对从现实生存状态到理想状态的一种有意识的追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人的发展的强烈关注,既不同于近代启蒙思想家那种建立在人性本善假设基础上对人的发展的理性预设,也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者那种建立在批判“社会罪恶”基础上对人的发展的情感渲泄,而是建立在劳动实践基础上辩证规律的分析。
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宏观视野中,对人的任何现实的说明都是与社会的发展有机结合在一起的,都是从人与社会的共生互证来理解的。因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人们创造的全部社会关系,都是在劳动过程中生成与延续的,“全部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在劳动基础上形成的全部社会关系规定了人的主体地位,同时,也就规范了这个主体的真实社会存在。这些关系主要包括人对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的解放与发展,具体就表现在这些关系的变迁与升华上。
马克思从人的社会关系出发,以劳动为基础,以辩证否定的分析方法为指导,透视人的全部解放与发展的历史,提出了关于人的发展经历或将要经历的三个阶段的学说。第一个阶段就是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个人没有独立性,直接依附于一定的社会共同体,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只限于共同体内部,只是在孤立的地点和狭窄的范围内发生的地方性的联系。“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是同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原始关系相矛盾的”。个人只是“狭隘人群”的附属物,他们不但只能从族群获得自己人的力量和性质,甚至也只在归属于族群的意义上才被称为人。第二个阶段是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在这个阶段,由于社会关系以异己的物的关系的形式同个人相对立,所以人的发展依然受到社会关系的束缚和压抑。但是,社会形成了普遍的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要求以及整体能力的体系。正象马克思所指出的:“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从而为更高历史阶段的到来创造着条件。第三个阶段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社会关系不再作为异己力量支配人,而是置于人们共同控制之下,人们将在丰富的和全面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与全面的发展,成为具有自由个性的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二
在人对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人的本质活动能力的最突出特点,就是人与自然的直接同一。一方面,人与其对象自然而言,其间的关系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分化。因为这一分化所凭借的技术手段——工具,还没有摆脱自然生成状态,人们只能以自然形态的工具来改造自然形态的土地及其自然资源;这一分化所凭借的技术基础——科学,还没有产生或者没有符合规律地完善起来,人们只能利用自身的自然体力与同为自然对象的土地等进行直接交换。另一方面,人还没有能力割断他与血缘共同体联系的脐带,因而必须依赖天然的血缘共同体,这种依赖“正像单个蜜蜂离不开蜂房一样,以个人尚未脱离氏族或公社的脐带这一事实为基础的。”这种本质力量的实现过程,就是两种自然力量的直接同一。尽管在原始社会以后人类经历了前资本主义经济一个相当长时期,但这一特点始终未能得到根本改变。只是分工的发展证明了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冲破人对自然(地缘和血缘)的依赖,并逐渐取得成功。但交往的狭隘性和交往目的的具体性(只为取得使用价值),证明这一个历史时间的直接同一性始终突显着。
人与自然的直接同一性,产生和存在的根据是人的依赖所表现的物的役使。由于人的本质力量的稚嫩,使人的自然力难以战胜外在的自然力,两种自然力之间质上的相同性带来量上的有限性。在这种状态下,个体的生存及其活动根本无法进行。但人一经产生,就在创造着他们的历史,这一历史所追寻着的就是人要摆脱劳动的自然和自身的自然,以提升生命的意义。正因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稚嫩,所以人只能通过人群(氏族或其它社会集团)以战胜自然,并占有物。否则个人便失去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这一事实,又为人的追寻造成新的陷阱。正因为人只能通过人而占有物,为此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一部分人就利用其占有的物而占有另一部分人(劳动),造成社会分裂和阶级对抗。这种对人的占有直到资本主义,一直是超经济的,是一种没有活力的关系。这种关系对于占有者而言,占有被占有仍然意味着是对一种“物”的占有,是一种能说话但没有话语权的“物”,并且通过对这一“物”的占有而占有更多的物。这就使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被极大地压抑和束缚着,这种压抑和束缚作为自然必然性又强化了人的依赖关系。
人对自然的狭隘关系又制约着人对人的狭隘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人对人(群体)的直接依赖。由于生产力不发达,劳动生产率低下,人的劳动绝大部分属于必要劳动,即维持和再生产人的生命的劳动,因而可用于交换的剩余产品很少,“农民出售的仅仅是自己家庭的小部分剩余产品,产品的主要部分由他自己消费,因此他把其中的大部分不是看作交换价值,而是看作使用价值,即直接的生存资料。”所以商品交换还未取得社会经济的统治地位,生产的交往只涉及到人与自然,用自己的劳动换取自然的产品,而不是用自己的劳动换取他人的产品。人的生产——消费结构处于一种封闭状态。这样,人就难以突破自身活动的局限性,难以把他人的社会生产能力纳入自身。尽管个人也同他人发生一定的关系,但却不是以发达的社会分工为基础的人与人的联系,也不是通过交换发展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是在血缘上或在政治上的从属关系与依附关系。它非但不能促进人的能力的发展,反而限定了人的发展的地域和界限,它把个人束缚于一定的共同体之中,个人只能在狭隘界限内发展,只能在依附状态下发展,因而与其说是人的发展,不如说是窒息了人的发展。
历史的发展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和发展。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讲的:“资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种解放和发展,首先是由于人的解放与发展。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人们彻底打破了对自然的敬畏心理,摆脱了对自然的直接依赖。相反,人们完全把自然作为自己的征服对象,将人与自然完全对立起来,向大自然开战、向大自然索取,已经失去了自然边界,自然界资源的有限性已无法限制人们攫取的欲望。现在能对人们的征服活动起制约作用的只剩下人们自己的道德的和社会的界限。这种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动力因素,一方面来自技术的物质基础——生产工具的高度发达和走向独立。在自然经济中,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只能是人的自然体力,而人的体力的有限性,是难以与巨大的外部自然力抗衡的,即使是人们联合起来,对付自然的力量也是有限的。这就必然使人依赖于自然和自然的秩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则学会用技术秩序支配自然,把自然环境改造为技术的、人工的环境。不管自然秩序多么反复无常,人都能以一套技术手段和装备复制和再造生产过程及其结果,达到人对自然的有效控制和改造。另一方面是来自技术的理论基础——科学的发展。科学知识早在古代就从生产中萌生,但是,那时科学尚未充分发展起来,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门类。在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科学与生产相疏离,人们看不到生产的技术进步中有什么科学的作用。在近代,独立发展的科学回归到生产实践,同物质生产藕合在一起,形成了科学——技术——生产的互动链条,带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人不再依附于、屈从于外部自然,而是成为自然的征服者与统治者,“生产过程从简单的劳动过程向科学过程的转化,也就是向驱使自然力为自己服务并使它为人类的需要服务的过程的转化。”
市场经济不仅使得人从自然界中获得解放,而且打破某种社会共同体对人的先天制约,“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酋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人不再依赖于某个共同体,从个体存在来讲,个人具有自立、自主、自律和自由的性质,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从人与人的关系看,确立了平等关系。这种人的解放的物质动因来自商品。因为生产力的无止境的发展,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剩余产品,剩余产品的增多,使交换行为越来越经常化,交换范围越来越大,它不仅突破人们日常生活的地域界限和先天的血缘界限,而且冲破了民族的和国家的界限。“这样一来,不仅生产方式改变了,而且一切与之相适应的旧的、传统的人口关系和生产关系,旧的、传统的经济关系都解体了。”“物”(商品)的流动带来了人的流动和解放,打破了原来的日常交往,变为以赢利为目的的社会交往。在商品交换中,“确立了个人的完全自由:自愿交易,任何一方都不能使用暴力;把自己当作手段、或者说当作提供服务的人,只不过是当作使自己成为自我目的,使自己占支配地位和主宰地位的手段。”
然而,市场经济中的人的自由,只是建立在新的依赖基础上的自由。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商品交换是以货币为媒介的,每个人生产的直接目的都是为了交换价值,为了换取货币,每个人需要的产品都要用货币来换取。这样,个人生产对社会需求的依赖和个人需求对社会生产的依赖,就集中表现为对货币的依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依赖关系就表现为物的依赖关系,人与人的普遍交往是通过物化的形式实现的。“货币从它表现为单纯流通手段这样一种奴仆的身份,一跃而成为商品世界中的统治者和上帝。”人依赖于货币,也就是依赖于外在的、不依赖于人的社会权力。人作为生产者,其存在的权力来自其包含在商品中的价值能否实现,而作为消费者,其存在的权力来自其自身的劳动力价值能否实现。这二者实现的具体形式,是获取等量的货币,是对物的依赖。但商品价值的实现是在流通领域,而商品中价值的实现根据则存在于生产领域;劳动力价值的实现同样在流通领域,而实现的根据也在生产领域,即能否被资本所吸纳。资本家就是资本的人格化的代表,因而人对物的依赖,其实质是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列宁说:“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人对人的关系,就是社会的一部分人通过物(资本)而占有社会上的另一部分人,由自然经济状态下的人通过人(群体)而占有物,变成了人通过物而占有人(劳动);由自然经济状态下对物的役使,变成了人对人的役使。因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造成的社会普遍矛盾的基础,不再是自然经济状态下物的缺乏,而是物的过剩了。这一矛盾的解决,不再是对物(土地)的直接争夺,而是对资产阶级的革命。
三
人类社会走过或正在走的人的发展的历史轨迹,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的实现提供了历史根据,只有到了共产主义,“人终于成为自己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自由人的实现不是马克思的天才猜想,而是建立在社会劳动基础上的、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物质财富的充分涌流、人们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水平的极大提高等一系列社会历史条件为基础的历史必然,“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
在人与自然方面,共产主义发达的生产力,已不是资本的增殖动力所推动的人对自然贪婪的掠夺,相反,它是人与自然在本质上的和谐统一和相互确证。马克思说:“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自然界成为“人的无机身体”,人与自然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达到新的统一。自然对人的役使和人对自然的役使都将消灭。
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由于消灭了私有制,实现了共产主义,“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摆脱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只有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从这时起,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因而社会既消除了物的役使,也消除了人的役使,人与社会得以和谐统一。
[收稿日期]1999-08-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