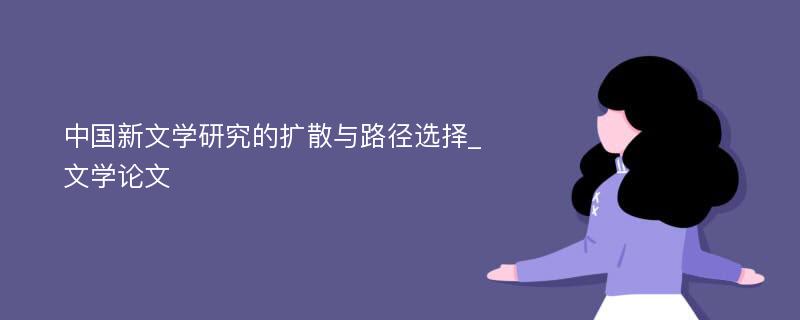
中国新文学研究增殖及其路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中国论文,路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227(2016)02-0099-09 DOI:10.16601/j.cnki.issn1002-5227.2016.02.017 如将中国新文学的起点追溯到清末民初,那么它也只有百余年的历史,这在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学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然而,作为中国新文学的研究队伍却相当庞大,其研究成果也可用汗牛充栋来概括。应该说,当前的中国新文学研究基本处于饱和状态,再要出新那是相当困难的。也是在此意义上,发现和开拓中国新文学研究新的增长点成为近年来的大势所趋,许多创新成果都与此有关。不过,也应该看到,至今的中国新文学研究在“饱和”中,仍有不少未被开垦的处女地,有的甚至是研究的盲点,这是需要进一步给予关注和进行研讨的。 一、“人”与“物” 自从“人的文学”被周作人于1918年提出后,“人”“人生”“人的个性解放”就被放在一个显著甚至是根本位置加以评说和渲染[1],于是“人是天地的精华和万物的主宰”也就变成再自然不过的观念。自此,“人的文学”成为中国新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并被奉为圭臬甚至顶礼膜拜。最突出的表现是钱谷融曾发表了《论“文学是人学”》,夏志清出版了文学评论集《人的文学》,他们都坚守着“人的文学”观念。毫无疑问,“人的文学”突破了中国传统文学不重视人及其个性的局限,为中国新文学带来了一次彻底革命;但另一方面,过于强调“人”,而忽略了“物”,尤其是将《西游记》《封神榜》《聊斋志异》《水浒传》等许多小说都说成是“非人的文学”,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是周作人所谓“人的文学”观的短板。 一直紧盯着“文学是人学”,就会大大缩小创作和研究的范畴,使自己变得近视、远视甚至盲目,从而导致文学的窄化以及异化。纵观天地自然,除了人还有更广大的世界万物,因此文学不可能只表现“人”,研究者也不可能只关注“人”和“人生”。不要说像卢梭这样的博物学家使其《孤独漫步者的遐想》充满博大的情怀,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饱含了对于万物的细思默想,就是鲁迅的《野草》和《朝花夕拾》也是写“物”的佳作。如果只研究“人”,那么作家笔下更为广大的“物”的世界也就被遗漏了。如在鲁迅笔下的动植物被写得丰富多彩、楚楚动人,但对它们的研究却很不够,它们像泥土一样被研究者用“人的文学”这把大眼儿筛子淘汰掉了。还有像陈从周、叶灵凤、周建人这样的小品作家,在“人的文学”观念底下,他们所创作的园林建筑、地方风物、植物生物几乎没多少地位和价值,然而站在天地万物的角度观之,这正是其创作丰富多彩、巧夺天工之处,应给予高度的重视和研讨。在当代作家中,写物的作品更是何其多哉!像张晓风、张抗抗、铁凝、张炜、周涛、莫言、鲍尔吉·原野、丁建元、杜怀超、李林荣、周晓枫、王族、黑陶等都是如此。他们关于物的散文往往有自己的语言密码,这不是“人的文学”所能解码的,需要放在物性和天地之宽中去理解和体悟。以鲍尔吉·原野的作品为例,他感兴趣的多是物的描摹,以及透过物性所展示的更为博大精彩的世界。王月鹏写伸向大海的栈桥:“它在面对大海遥望彼岸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欲言又止的表情。”“栈桥是一个态度。我从它的欲言又止的表情里,看到了一种坚定。置身波涛之中,它并不期望抵达彼岸,也无意于征服什么,它只是固守属于自己的一份命运,这是最诚实的生命态度。”“栈桥甚至拒绝作为桥的所谓使命,在遍地架桥的现实世界,它是另一种桥——不以抵达彼岸为目的。在道路断裂的地方,它承担人类与风浪之间的沟通,接续一些更为重要的东西。”[2]作家这样的对于物及其物性的展示,“人的文学”观很可能会让研究者失语或痖语,因为万物与人一样自有其天地,失于此则失之大矣。从这一角度观之,超越“人的文学”观,进入物及其物性的世界,就会为研究者提供一个更为广大新奇的天地,获得新的研究成果。 要克服“人的文学”观的局限,尤其是突破人的欲望的过分膨胀和个性解放的自大狂。以“人的文学”观研究文学,研究者眼中全是“人”,而没有物,于是人变成了凌驾于万物之上的主宰与精华,万物就变成了被漠视甚至踩在脚下的低级物种。纵观中国新文学研究,我们发现“人”、“人的现代性”“爱情”“个性”“欲望”“私心”是一个不断被缩小和窄化的过程,于是“人”进入了一个观念的囚笼和思想的穷途。以爱情与家庭婚姻为例,当中国新文学由写“人生”变成津津乐道于“爱情”,并变成自私的爱情,那么这种文学已开始走向其现代性的反面了。于是,“如无爱勿宁死”以及各种三角、四角和更多角恋爱也就成为新文学创作和研究的观念形态。而问题的关键是,追求爱情虽无过错,但有了爱情后并不爱惜,更不注意发展、创造,这是新文学的通病。所以,林语堂称中国现代人患上了一种“现代爱情病”,那就是:将爱情当饭吃,而将婚姻当点心吃。这也是钱钟书笔下的“围城”困局:在婚外的人想进去,结过婚的人又想出来。殊不知,在这个世界上,爱情固然重要,但婚姻家庭、世界人生则远大于爱情,是可以超越一己之爱的大情怀。从此意义上讲,将爱情看得比“死”更重要,这是一种现代爱情病态观,也是“人的文学”进入死胡同的典型例子。然而,中国新文学研究者多信守“爱情至上”“如无爱勿宁死”的“人的文学观”,于是让爱情逐渐失去了神圣之光,更失去了个性解放的特色,而变得越来越自私自利和狭隘化。另一个例子是,对于《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将它看成是个性解放的典型,孙悟空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俨然是“人的文学”中个性解放思想的最好注释。然而,林语堂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最大的价值是,让人看到了人自身的局限,即由一个无所不能的自大狂,经过“九九八十一难”的西天取经,变成一个自知有限、然后知足的敬畏者。当人看到了自身的局限时,人才能对天地万物存有敬畏,而后去掉狂妄无知和无法无天的“癔症”。还有,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过于强调人的“个性”,但对于集体性和国家意识强调不够,这也是他后来附逆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里牵扯到“小我”和“大我”的关系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言:“我们想到牺牲自己是为了尽义务,即使我们力量薄弱,也会促使我们努力去做。”“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那些为最大多数人们带来幸福的人,经验赞扬他们为最幸福的人。”[3]许多人一直赞赏周作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尤其欣赏其“人的文学”,但较少有人质疑其局限,即他将“人”从天地自然中抽象出来,将丰富和大写的“人”变为有“个性”与“自私”的人,从而让文学越走越窄。 “物”不仅是与“人”不同的所在,而且又有与人互动、相通、相启的作用,有时甚至会成为“人”之师,这是中国新文学研究应该注意的。从一般意义尤其是进化论角度看,人确实站在生物链的顶端,在聪明才智等方面是天地的主宰和万物之精华。不过,万事都不能一言以蔽之,更不能将观念当成永恒真理。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人又不能与万物一争长短,万物在许多方面是远超于人类的。也正因此,欧阳修曾在《秋声赋》中发出了人“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的感叹!毛泽东也在《采桑子·重阳》中表示:“人生易老天难老。”可见,在生命的意义上,人是不能与万物等量齐观的。因为仅从一块石头上说,它就要经历数百万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孕育,而人生却是七十古来稀!在《古诗十九首》中有这样的句子:“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曹操在《短歌行》中更是忧患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苏东坡在《赤壁赋》中也说:“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这种将人与万物生命进行比较,所产生的人生短暂之感喟,是人类智慧的表达,它是远离了“人的文学”的狭隘性的。然而,中国新文学研究者却较少能跳出“人的文学”的圈套,从万物身上获得更多的智慧,以点染我们智慧的文学与人生。如鲁迅研究者总是习惯于从“人的现代性”角度来研究,于是将鲁迅笔下的万物忽略和淡化了,即便探讨也是多赋予其意识形态内容。最典型的是对于鲁迅“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的解读,学界公认它们是刺向反动政府的匕首与投枪!这样的研究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显然属于“过度阐释”和“强制阐释”[4]。另如,郁达夫研究也容易陷入意识形态阐释的窠臼,不少研究者一直强调其对于人的“个性”的重视,但笔者认为对于物性的描摹是郁达夫创作的精华所在,像他的游记散文就很有代表性。在《故都的秋》中,郁达夫极尽物性描写之能事,将老北京的秋意尽情托出,从而渲染出万物在伤感中的美妙。他说:“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教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这是作为牵牛花知音才可能有的感悟。他还写道:“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这样的句子一向不为研究者注意,其实它在郁达夫散文及其整个创作中都极其重要:一是写得安静,真有宁静致远之感,于是智慧方能生于其间;二是写得真实,它仿佛活画了老北京的秋意图;三是写得细腻,“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一句,既观察得细,又捕捉得准,最重要的还有对于生命逝去与留存的感喟,这是充分体验生命的张扬与消逝的笔触;四是写得美好,在短短小文中充分展示了作者“文心雕龙”的功力与才情,整个作品充满着哀而不伤、泪中有笑的情调与境界,这是超出中国古人的现代意蕴。高洪波写“狗”,即写时下流行的网络名词“汪星人”,他借说一个六岁小男孩不为狗的寿命短于人类而难过,其理由是“那是因为人类需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学习爱,而狗生来就懂得爱和忠诚”[5]。朱以撒常在“物”与“我”之间架起桥梁,充分体验人与物之间情感的流淌,以及对于“以物为师”的崇尚之意。他这样写道: 蓬松的芦花和我每日用于指腕间的毛笔太相似了。一杆笔集中了走兽的万千毫毛,没有入水时,它们会蓬松地张开,像一朵花开到了最大。一个善于用毛笔的人,此时的心也像花那般地打开,娴雅起来了。 每一个人的内心,都会蕴藏着无尽的对毛笔的喜爱。柔软的笔锋带来了许多乐趣,导引日子走向深入,许多类型的锋颖在指腕间过往,渐渐悟出了其中的微妙分寸,多一分少一分地下力,快一分慢一分地牵引。笔是软的,宣纸也是软的,研墨之水也是软的。我的指腕在柔软中穿行,捕捉那似有若无、恍兮惚兮的感觉。由于柔软而无处发力,或者下力了,却被毫端化得虚无之至。 一个人长期把握一种柔性之物,他对于一些人事看法也有了修正,不是从柔软中生出许多奇思异想,而是越来越平淡、持中。不过柔毫还是不会给它的主人呈现一个边界,就像我们不知道尽头在哪里,或者不知道如何直到尽头[6]。 在此,朱以撒主要是写毛笔、宣纸、研墨之水、芦花,写它们的柔软,但更重要的是透过柔软表达书法及其人生观,那是一种以“柔软”为师而生出的柔性美学,一种“平淡”和“持中”的人生哲学。 人与物的关系应该是辩证的,我们既不反对“人的文学”的价值意义,也不反对对于“物”的“非人的文学”的批判性。但我们不赞成将“人的文学”无限放大,并用它来遮蔽“物”的世界,因为“物”是这个世界的底色和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学的重要内容。因此,在坚持“人的文学”观的前提下,不可忽略“物”在文学中的价值意义,尤其不能低估“格物致知”和“以物为师”的智慧,这应是中国新文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和支点。 二、“正业”与“副业” 长期以来,中国新文学研究往往存在这样的局限:不能处理好“正业”和“副业”的关系。不是将正业无限放大,而忽略了副业;就是放大副业,不顾正业的作用,从而形成正业、副业的分离、矛盾甚至对立。以鲁迅研究为例,尽管它是中国新文学研究的显学,研究成果数不胜数;但是,这主要集中在其文学事业上,而对其创收经营、艺术创作、家庭生活的研究则明显不足。张炜是个以写作为乐的作家,但殊不知他有“实业梦”,还造过两台机器,并创办了规模巨大的松浦书院。他自己曾表示:“我这个人好奇心重,总也闲不住,每到一个地方就想做点什么,一度喜好‘实业’,但又做不好。……有人说,如果生在旧社会,我在农村会是一个不善经营的地主,在城市则是一个失败的资本家——一旦接触那些戴眼镜的学者多了,还会尝试做起半生不熟的学问。……大概都是很自然的事”[7]。可见,除了写作外,张炜有颗为“实业”躁动的心。但我们很少有人从“副业”这一角度研究张炜的文学创作,因为有时副业就是正业的一个潜台词,而更有时正业又是对副业的一个纠偏。因此,未来中国新文学研究不仅要重视文学正业,也要关注非文学的副业,更要注重二者的复杂关系,以此开拓新的研究增长点。 (一)将作家的“副业”当主要对象研究 如果说以往研究中国新文学作家主要重其文学,那么今后应加大其非文学内容的研究,这是一个更广大的时空,其发展潜力相当巨大的。 第一,作家的科学生活。由于中国新文学建立于民主和科学的基础上,所以“科学”成为新文学作家不可回避的概念。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作家的科学生活却自觉不自觉被放在次要位置甚至删除了。最有代表性的是科普作家一直不受重视,尤其是他们难与经典作家相提并论。其实,在科普作家身上集聚的更多的不仅是文学性,更是其现代科学理念与梦想的思维方式。另以林语堂研究为例,研究者往往更关注其散文、小说,但他喜爱科学、一直想进科学院,并发明简易中文打字机,对于五笔电脑输入法的巨大贡献却鲜有人知,尤其没有将之与文学创作联系起来考察,从而大大降低了林语堂研究的力度和水平。还有鲁迅,其《科学史教篇》的意义是巨大的,但迄今为止对它的研究还停留在“科学”层面,未能进入心理学、文学、人类学、人才学等层面进行思考,因而大大降低了其价值意义。换言之,科学往往给作家带来创造性动力和想象力,而文学又反过来弥补了科学的局限。从此意义上说,如果能从作家的科学生活中梳理出一条线索,寻找其规律,尤其是科学与文学的辩证关系,那将是一个很好的新文学研究视野与方向。 第二,作家的艺术生活。由于文学与艺术有着天然的亲近,所以有时很难对其进行区分,所以古人有言:“诗中有画,画中有诗。”①也是在此意义上,中国新文学作家多是艺术家,至少都有较高的艺术天分。以书法为例,像王国维、李叔同、苏曼殊、蔡元培、梁启超、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胡适、茅盾、郁达夫、林语堂、闻一多、臧克家、台静农等都以书法名世,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的书法却较少引人关注,成为“一个被忽视的学术视域”,“从而使中国现代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被厚厚的历史尘埃淹没了”[8]。其实,从中国新文学作家的书法角度进行研讨,以开拓其文学研究视域,这是一个富矿,还有相当大的发展前景。与此相关的是,不少新文学作家也是画家,较有代表性的有鲁迅、闻一多、张爱玲、艾青、汪曾祺、顾城等,像鲁迅的书籍封面装帧画、张爱玲的时尚女子图都极其精妙,而闻一多、艾青都曾留学国外学画,其画作颇有影响。沈从文在《湘行书简》和友人通信时保留了他的一些速写,绘画风格极为简凝有趣。还有,一般人都不知道林语堂曾画过“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在画面上,身穿长袍的鲁迅弯腰站在岸上,手执长杆在打落水的叭儿狗,其形象栩栩如生。而且,林语堂还写过不少画论,阐述自己的绘画观与艺术观,如在《论曲线》中的绘画观由“曲”与“直”引发,作者站在中西不同的特点来比较和分析,其见解独特而有趣。然而,以往我们的研究却较少给予关注,更缺乏深入的研讨,尤其不能站在作家文学创作的角度给予阐释,这就大大限制了林语堂及其整个新文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当然,作家还有其他的艺术生活需要进一步探讨,如李叔同与音乐、林徽因与建筑等,都是扩大新文学作家研究的窗户,可以对之深入地挖掘下去。 第三,作家与收藏。在中国新文学作家中,有一个重要倾向,那就是不少人都喜欢收藏,有的甚至沉溺于其间而难以自拔。如鲁迅、郑振铎、阿英、唐弢、黄裳、姜德明的藏书甚富,鲁迅还是碑帖收藏大家;郭沫若、冰心、阿英、臧克家等人收藏了不少名人字画;贾平凹喜收奇石和汉罐,而冯骥才则是民俗收藏的专家。值得一提的是沈从文的收藏,早在20世纪20年代,沈从文就常逛北京的琉璃厂以及各种地摊,30年代开始收藏各种古董和藏品。与此同时,沈从文对于书画、锦缎、铜镜、漆器等都有研究,并写出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著作,这不仅填补了收藏史的空白,而且也是沈从文文学创作研究的另一参照系统。就目前情况看,将作家的文学创作与收藏分开研究,甚至对作家收藏多有忽略和熟视无睹的情况相当普遍,这就使得中国新文学研究大打了折扣。因为没有收藏参与的中国新文学作家研究,不只是残缺不全的,也是失语和无力的。我们很难想象,当没有收藏作为底蕴和兴趣,中国新文学作家能有健全的生活和富有特色的文学创作,而文学与收藏之间的阻隔与会通也一定是个更大的研究课题。以贾平凹的《丑石》为例,它之所以能成为经典作品,如果离开了他的奇石收藏和对奇石的痴迷,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二)将“非作家”的“正业”当主要对象进行研究 在中国新文学作家中,还有一种情况应该引起注意,那就是“非作家”以文学创作为业余爱好,并写出了大量文学作品。当然,如果从一般意义上说,从多角色来看,写出大量优秀文学作品的“非文学家”也是作家。像画家孙福熙、刘海粟、黄永玉、黄苗子、吴冠中、范曾、韩美林、陈丹青等都写出了不少优秀散文,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王充闾、梁衡、张成起、厉彦林是政治散文家,梅兰芳是戏曲散文家,而作为书法家的朱以撒在散文创作上也有不俗的表现。这类不以文学为正业的文学创作较少有人研究,即便研究也不像对于作家的研究那样全面、系统和深入。更重要的是,对其研究不应脱离他们的正业,否则就无法探讨“文学创作”在这些“非作家”身上生成的动因及其特色。以黄永玉为例,他的散文写得大胆张狂、放任自肆,如江河之奔流,似脱缰之野马,甚至没一般作家的规矩和方圆,读其文就如同喝高度烈酒,既爽快又刺激,但又总有点怪味儿。这与他画作的童心放达、富有创新是一致的。如果不从绘画与生活这一“主业”来考量,我们很难理解黄永玉散文的真谛与妙处,也无从理解其局限和不足。黄永玉曾表示:“‘隔行如隔山’是句狗屁话!隔行的人才真正有要紧的、有益的话说。”“作家有如乐器中的钢琴,在文化上他有更全面的表现和功能,近百年来的文化阵营,带头的都是文人。”“一个作家归根结底是要出东西,出结实、有品位的东西,文章横空出世,不从流俗,敢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闲事管得舒坦,是非清明,倒是顾不上辈分和资格了。”[9]黄永玉曾问黄裳的女儿是否了解其父,是否见过她父亲放肆的大笑,黄裳女儿不知如何做答。于是,黄永玉说黄裳五十年前就开美军的吉普车,有一番无与伦比的丈夫豪情,这与后来痴迷于书、温文尔雅的黄裳判若两人!黄永玉喜欢收藏烟斗,其数量多达六七百个,他养过猴子、猫头鹰甚至还有梅花鹿,更养过各式各样的狗,香港有老虎狗,意大利有牛头狗,北京有温和的贵妇狗,还有来自德国的斯那萨狗,以及来自俄罗斯的高加索狗狗大、狗妹,来自阿富汗的灵缇狗五五[10]。从一般意义上说,黄永玉的爱好就是玩物丧志,但从画家观察生活、养育情趣、提高见识、培育创造性等方面来说,这无疑于是真正的生活与创作源泉。也只有从这里,方能体会黄永玉绘画的底气与创意,以及他进行文学创作的风貌与动力源。因此,从“非作家”的主业出发进行研究,以理解其文学创作,进而把握其对于中国新文学的贡献,这是一个颇有前景和潜力的学术视域。当然,这也为研究者的品位与境界提出更高的要求。 (三)将“两栖创作”作为研究方向 在中国新文学发展中,还有一种现象是“两栖创作”,即一方面是文学创作,另一方面是其他方面的创作,问题的关键是二者有时不好区分主次、正副。如沈尹默既是著名的文学家又是书法大家,丰子恺在文学创作与绘画上并蒂双修,陈从周在园林艺术和小品文写作上可谓双峰并峙,林徽因在文学创作与建筑设计上相得益彰,叶灵凤在文学与绘画上的成就难分伯仲,等等。目前,对于他们的研究还停留在分离状态,更没有看到这种“两栖创作”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优势。以丰子恺为例,在画界他被奉为代表人物之一,在文学界他也享有盛誉;然而,这双面的价值并未因此使他增殖,有时甚至被双方的成就对冲、稀释或消解了。其实,丰子恺的境界甚高,文风与画风也简洁明快,有世俗的宗教情怀,二者也有可不断对语、互文的功能,研究者应该从中升华出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以弥补其他非两栖类创作的局限。另如黄裳,他既是图书收藏大家又是散文名家,对他的研究至今还相当薄弱,研究者很少能从两栖性这一角度理解其境界与品位,即他身上饱含的那种宁静致远、甘于孤独、快乐超然、平淡如水的内在精神气质。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境界和品位很难达到,所以黄裳研究一直比较冷落,也处于中国新文学研究的失语甚至无语状态。像白菜豆腐的长久与美好所包含的难以言说的内容一样,至今很少有人能像黄永玉的“黄裳浅识”那样力透纸背,真正理解黄裳的精神气质与价值魅力。 总之,迄今为止中国新文学研究的最大局限在于,就文学而研究文学者多,而与之相关的“非文学”内容较少进入研究者视野,这就带来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限。就好像研究站立着的那个人,只全神贯注于“他和大地的接触面”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一旦将接触面之外的土地清除掉,那么这个人不仅站不住,而且会坠入万丈深渊。因此,表面看来,支撑一人的只是脚底那两片极有限的土地,其实却离不开广大深厚的大地。如果能跳出“文学”这一限度,从正业与副业的辩证关系入手,中国新文学研究就会获得勃勃生机,进入一个全新的境地。 三、“人道”与“天道” 将“人的文学”作为标尺,当然信奉的就是“人之道”,这是中国新文学研究长期以来坚信不疑的理念。“人之道”对于打破“非人之道”当然有益,因为人毕竟要按人性的逻辑生存与发展。不过,如果只讲“人之道”,尤其是让“人之道”不断受到异化,这样的中国新文学研究就会走向反面,甚至变得南辕北辙。因此,在强调“人之道”时,不能不顾及“天之道”,这一观念或理路可能是未来中国新文学研究的重要转向。 “人之道”最大的问题是人的为所欲为,对所有的人与事都缺乏同情之理解,尤其是缺乏敬畏之心,这也是中国新文学创作和研究中“暴力叙事”异常强大的重要原因。早年陈独秀就大胆地表示:“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上帝也是骗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骗人的;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11]“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台湾作家李敖曾在《笑傲五十年·题记》中放出大言:“五十年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李敖还自诩“为百年来中国人写白话文之翘楚”“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何以会出现这样的自大狂,主要是“人之道”异化的结果,因为在现代社会和人生中,个性、欲望及其膨胀不是受到限制,而是受到张扬甚至鼓励和鼓吹,王朔的“我是流氓我怕谁”②就是这一“人之道”的逻辑演绎,世俗人生流行的“好人不长寿,坏蛋活千年”的说法也是这种“人之道”异化的产物。其实,“人之道”如不能佐以“天之道”,其弊端和危险就会慢慢暴露出来。 “天之道”是天地大道,它包含着天地的法则与智慧,有时能让“人之道”的弱点暴露无遗。以人的眼睛为例,有多少年轻人对自己有1.5甚至2.0的眼力引为自豪,他们也让许多近视者相形见绌;然而,人到中年尤其是老年,许多近视者眼睛不花,而年轻时不近视者则多变得老眼昏花。这就是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的道理:“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当一阵狂风吹过,多余的风沙就会填满坑凹,这与许多人不知厌足、得中求得、希望多中再多,形成鲜明的对照。事实上,“天之道”最后会抹平一切,尤其是将“人之道”的不平抹平!也是在此意义上,有着天地大道藏身的人会注意克服和修复“人之道”的局限,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清代李密庵最著名的“半字歌”就是不求满溢,只求“半半”,因为他深知老庄的“满受损,谦受益”的道理。林语堂也将“上帝”与“天”作为生活与文学的原则,他一生从没放弃对于“上帝”的信仰,他还强调:“老子思想的中心大旨当然是‘道’。老子的道是一切现象背后活动的大原理,是使各种形式的生命起的、抽象的大原理。”[12]从此意义上说,如何从“人之道”的盲点之下,找到“天之道”这方明镜,是打开长期以来中国新文学研究的天窗。 如按天地之道的“日夜”与“阴阳”进行划分,中国新文学作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正序型,即“日出而做,日落而息”,较为代表性的是林语堂。据林语堂说,他一般是下午和晚上打腹稿,晚上经过一夜的安眠,早晨起来,拉开窗帘,阳光洒满房间,于是香茗在手,烟斗在口,然后一句句将要说的话说出来,让打字员用打字机打印出来,每日三千字,风雨无阻。这是一种与天地时序相适应的生活和写作方式,而林语堂的生活与写作也充满阳光与快乐,这恐怕与他的人生遵从“天之道”有关;二是倒序型,即喜欢夜生活与写作的人生态度,较有代表性的是鲁迅。据许广平说,鲁迅与别人的生活和写作习惯不同,他一般是夜里11点多送走客人,后到床上和衣而眠,像战士在阵地上一样打个盹儿,马上起来泡上茶,吃几块点心,于是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换言之,鲁迅是在别人晚上睡觉时,起来开始写作的,是一种夜生活状态。还有贾平凹的创作比鲁迅更甚,有人这样描述道: 贾平凹的生活习性写作习惯与常人颇为不同,他通常昼伏夜出,写作前,喜欢登上夜晚的古城墙,充分吸纳城市上空浓郁诡谲的阴气。这还不够,他要在他的书房四周摆满从古墓里出土的大小形状各异的土陶罐,每只陶罐大张阔口,倾吐千百年来养精蓄锐的阴气,置身于这浓郁沉重的阴气里,他神奇般地灵感喷发、文思泉涌,下笔如有鬼,他的文字有着原汁原味的古音古意,他的语言有着月光般的空灵、飘忽和清凉;还有那么一点儿月光掠过古城墙的森森鬼气。他就是靠着这千年不散的诡谲阴气滋补浸润他的锦绣文章,也靠着这股阴气医治好了他严重的肝病[13]。 这与林语堂形成了鲜明对照。作为研究者,是否可从“人之道”与“天之道”的关系中来审视林语堂与鲁迅、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在林语堂的作品中,光明、辉煌、华采、灿烂、天堂、会心、微笑、诗化、自由、潇洒、闲适等是其关键词;而在鲁迅作品中,则多是充满黑暗、夜、无常、冰与火、地狱、彷徨、匕首、投枪、箭、血、死亡等意象,在贾平凹则阴气更重、鬼影森森,有如进入坟墓一般,这难道与他们在日与夜的不同时间进行写作没有关系?作为时序颠倒的作家,鲁迅与贾平凹作品中的创作固然多了些灵感与神秘,也有着与常人不同的感受;但其作品中的阴冷、暮气、鬼气却是异化的,不论对于读者还是作家本人都有其负面作用。当然,还可从这一角度对中国新文学作家进行研究,以体味其在“人之道”与“天之道”上的顺势与逆势,以及给作品、作家、读者所带来的不同影响。 贾平凹还有个习惯,就是夏季写作一直到秋天,冬天则进入休眠期,很少写作。他说:“回想这10多年,我基本上是冬天不写作,要写都是夏天动笔,差不多一个长篇写两三年,总是在秋天写完。这也符合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吧。”[14]这一写作节气是符合天地之道和充满智慧的,因为一年的春夏秋冬四季确有这样的规律:春种、夏忙、秋收、冬藏,万物也是如此,当树木经过春天和夏天的挥发与浪漫之后,秋天开始收获,而冬天则树叶落尽,将能量收敛和珍藏起来,以待严冬的到来和考验。以此推演开去,在一年四季中,其他中国新文学作家是否有自己的写作个性和趣味呢?如果有,那其中有何规律可循?这对于作家和整个中国新文学有何影响?所有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探讨,也是颇有意义的重要话题。 我们还发现,在中国新文学中存在的其他“人之道”和“天之道”特征。如表现四季和日夜时间的作品甚多,从中可见作家的季节观与时间观。如巴金的《寒夜》、茅盾的《子夜》、鲁迅的《朝花夕拾》、曹禺的《日出》、朱自清的《春》、田汉的《获虎之夜》、吴强的《红日》、贾平凹的《白夜》、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张炜的《九月寓言》等都是如此,透过节气与时间顺序,我们分明能感到作家的心绪、情感、倾向和思想逻辑,以及其文学表征和内在规律。这既表现在具体作家身上,也表现在不同的作家身上,还表现在中国新文学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以曹禺为例,他由《雷雨》到《日出》,表现的是一个从“人之道”到“天之道”的转换过程,由那种“反人伦的雷雨之夜”到“喷薄日出的光芒照耀”,亦可见出作家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的改变。在《雷雨》之夜中,一切都是昏暗甚至错乱的,也充满难以言说和无以言说的秘密,人生和人性也沉沦其中;然而,《日出》中的陈白露,虽也经历了夜的洗礼,其自身的“白露”也包含了与《雷雨》中的“萍”一样的命运,但它毕竟有“日出”照耀,在易逝中却有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华光异彩。这是一种新解读,一种对于“人之道”与“天之道”隐喻关系的发现。还有巴金,他从受压抑的《家》《春》《秋》中透出一股新鲜气息,到更为严酷的冬的《寒夜》的窒息感,其实是一种借助四季和日夜变幻展开的向纵深掘进,其间的由“天之道”映衬的“人之道”更加分明显豁。还有鲁迅作品中的四季与日夜变化,它们更多呈现出“秋”与“冬”的悲凉,以及“夜”的黑暗与绝叫,但是春夏与日光却不多见。这是否可以说,鲁迅的写作是与许多作家反向而行的,是在“天之道”的阴气中体会世态炎凉,这与乘阳气而行和进行创作的作家形成了鲜明对照。 鲁迅只活了50多岁,到晚年他多病缠身,对此林语堂曾在《悼鲁迅》一文中有所披露。贾平凹也是如此,他身患肝病,一度因身体影响创作和生活。从创作角度看,夜生活确会让作家更为专注和安静,也给作家带来某些新鲜感与新发现,甚至会让作家获得有异于常人的灵思与体悟;不过,夜生活毕竟有违时序和“天之道”,它也同样会给作家创作注入某些阴暗、怪异、暴戾之气,并直接影响作家的健康,成为一种非健康的人生方式。我们研究中国新文学作家,就是要通过“人之道”与“天之道”在其身上的表征,寻出带有规律性的内容,并从中受益。 “人之道”与“天之道”各有其规矩方圆,中国新文学作家如何待之,是顺应还是逆反,其中有怎样的规律可循,其得失怎样,都是值得研讨的。不过,更多的中国新文学作家信奉的是“人之道”,而且将之推向极端甚至异化状态,却忽略了“天之道”,尤其是无视“天之道”的秩序与尊严,这是造成中国新文学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问题的关键是,研究者很少从这一角度切入,也就难以获得新的观念及其理论与方法。 应该强调的是,中国新文学并不只是指“新”文学,也包括“旧”文学,如中国近现代以来所有作家的旧体诗、像鸳鸯蝴蝶——礼拜六派那样的通俗文学、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甚至连那些为人耻笑的所谓色情文学,都可置于研究之例。这是因为:第一,由于身处中国现当代的整体氛围,许多“旧”文学不可能不被现代性因素所熏染和浸润,这也是近些年来“旧体诗”这一文体备受关注的重要原因;第二,“新文学”是与“旧文学”甚至“恶文学”相对而言的,不研究后者而只专注于前者,既不能很好地解释“新文学”,又失去了“旧文学”与“恶文学”这样的参照,更不能整体反映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的整体风貌;第三,衡量文学往往不能简单将“新”与“旧”作为标准,而应该用“好”与“坏”,这里还牵扯到观念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不同的观念底下,同一文学就会呈现不同的结果。如长期以来在道学家眼里,《金瓶梅》一直是淫荡之书,并被禁锢起来;然而,个性解放和人性解放思想却改变了人们的看法,在现代学人的视野中,它不仅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还有着重要的经济、文化、文学价值,尤其是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更增加了作品的分量。同理,对于《红楼梦》,“红学”专家俞平伯的评价不高,因为他主要依据的是西方小说标准,他说:“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若讲起结构,在此方面更劣于描写。即有名的《红楼梦》细考较去,亦是一塌糊涂。”[15]今天看来,俞平伯的看法有些可笑,但却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红学观”。对于中国新文学和旧文学的认识也是如此,许多看法是会变化甚至会产生根本变化的,有的甚至会整个地颠倒过来,就好像周作人当年将郁达夫的《沉沦》由“色情文学”一变而成为爱国文学一样。因此,只有在包括整个中国新、旧文学的研究中,才能避免只研究“新文学”的简单与狭隘,真正走向包容、全面、开阔与深入。新世纪以来,学界出现对于中国新文学重新命名的趋向,如朱德发用“现代中国文学史”代替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史[16],张福贵用“民国文学”代替以往所使用的“中国新文学”等概念[17],这都是为中国新文学进行增殖的尝试与努力。不过,名称与概念的转换要真正达到目的,还必须具备有效的路径与方法,以上几方面是我的一些思考,即在不改变“中国新文学”概念的情况下,通过观念、理论、方法和路径的更新达到增殖的目的。 [引用格式]王兆胜.中国新文学研究增殖及其路径选择[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7(2):99107. ①苏东坡在《东城题跋·书摩诘〈蓝关烟雨图〉》中有:“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②赵勇在《王朔的流氓观与作家观——从“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出处说开去》(中国作家网,2007年1月9日,11:03)一文中认为,王朔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呀!”这句话,来自王朔的小说《一点正经没有——〈顽主〉续篇》(《中国作家》1989年第4期),是小说中一个叫“方言”的人说的。但我认为,这句话不论如何都显示了王朔的自大狂,也表明他对“人之道”异化后的推波助澜。标签:文学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艺术论文; 鲁迅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黄永玉论文; 林语堂论文; 爱情论文; 作家论文; 散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