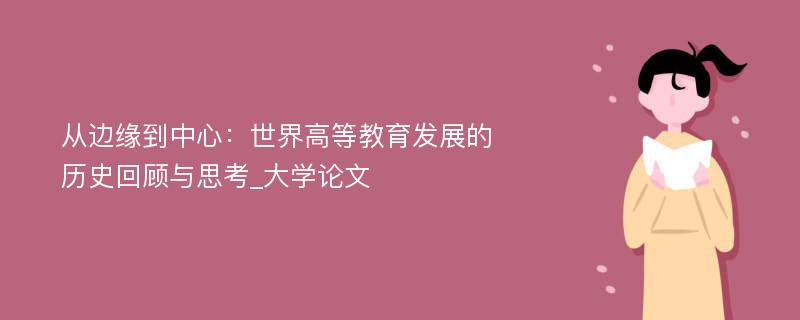
从边缘走向中心: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回眸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边缘论文,走向论文,历史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916(2004)07-0005-04
历史学家哈罗德·珀金教授在研究大学发展史后指出:如果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大学千百年来的荣辱兴衰,来说明它是怎样从中世纪的宗教和世俗的知识团体演变成今日在以知识为基础、以科学为方向的技术型后工业社会中起关键作用的机构的话,那就是:大学是人类社会的动力站[1]。换句话说,大学近千年的演变就是逐渐由边缘走向中心,特别是走进经济社会的中心的历史。审视高等教育发展如何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发展历史,我们从中可以看到3条基本的线索:一是社会和时代的要求,构成了演变发展的外部动力;二是高等教育自身在主动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所做的努力,特别是思想上的变革、影响更为深远;三是各国政府以及社会公众在政策与实践层面的支持。三者紧密联系,相互交叉,共同构成高等教育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演变历程。
一
潘懋元先生在《高等教育将走进社会中心》中指出: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不需要高深知识,高等教育的地位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的“学府黉宫”,或“象牙塔”中;在工业经济时代,高等教育将逐步走进经济社会,为工业生产提供服务[2]。由此可见,高等教育的变革和发展总是与一定的经济、政治制度、社会进步和科技的发展的需要相一致的。在新的形势下,社会要求高等学校走向社会的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疑是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战争的结束宣告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的来临,以原子弹、电子计算机及空间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在50年代演变成世界范围的技术革命浪潮,成为一场方兴未艾的世界性运动。由于科学知识和信息量急剧增加,有人将此贯之以“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知识,特别是科技知识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扮演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人类的发展也越来越依靠科技的力量。90年代以来,由于苏联的解体,世界由政治、军事冷战转向经济热战,各国纷纷以科学技术作为综合国力的重心,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进高科技产业化,以提高国际竞争力。可以说,围绕人才、成果、知识产权的争夺愈演愈烈,以科技竞争为焦点的国际规则已成为大势所趋。因此,国家都把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提高国民科学文化素质看成是21世纪竞争成功的关键。在知识经济时代,无论是经济的知识化,还是知识的经济化,都极大地显示了知识在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而与知识直接相关的大学也进入经济运行过程之中,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正是基于这一点,构成了大学由居于经济社会的边缘走进经济社会的中心的外部动力。
二
当然,虽然时代和社会要求大学成为社会的中心,但并不意味着高等教育就能一定能够成为社会的中心。高等教育必须主动地、全面的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才能真正走进社会的中心。新的理论和概念的发展与突破,是高等教育从边缘走向中心的理论基础。
(一)高等教育认识论哲学到政治论哲学的冲突及融合
布鲁贝克将高等教育事业为何应当存在与发展的哲学理论分成两种:一种哲学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3]。前者强调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认为学术事业探求知识是为着知识本身的缘故,而与人类的利益无关,主张“任何社会都应有这样的机构,其目的是对社会最令人困绕的问题进行尽可能深刻的思考,甚至思考那些无法想像的问题”,后者则更侧重于探讨深奥的知识对国家的影响,认为人们探索深奥的知识,不仅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要理解和解决当今复杂社会中的复杂问题,有赖于学院和大学所创造的知识和所培养的人才。
19世纪初(1810年),由洪堡为代表建立起来的柏林大学以及其代表的经典大学的办学理念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教学和科研统一代表了认识论哲学的辉煌时代,但这种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贯穿19世纪不断加强的工业革命的力量,赋予大学所发现的知识越来越现实的影响。大学特别是占优势地位的研究型大学所提供的知识,不仅发展了工业生产上的奇迹,也被用于确定政治目标。“过去根据经验就可以解决的政府、企业、农业、劳动、原料、国际关系、教育、卫生等问题,现在则需要极深奥的知识才能解决。而获得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知识和人才的最好场所是大学”[3]。于是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逐渐与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并驾齐驱,甚至压倒了认识论的哲学。二战期间,高等学校被卷入了为战争培养急需人才的活动,实验室被用于军事科研,大学教授参与了与军事技术有关的研究工作,青霉素的发现、雷达系统的改善和核武器的研制成功等,一方面保证了战争的胜利,另一方面使得高等学校明显地成为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这为战后高等教育政治论哲学的盛行奠定了重要基础。二战后的几十年,是世界高等教育空前发展的几十年,同时也是高等教育政治论哲学大为盛行的几十年。由于高等教育对于国家的未来、社会的发展、个人的前途越来越重要,高等教育不可避免的更加深入地走进了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公众的个人生活。高等教育俨然成为社会的“服务站”、“动力站”和中心。
当然政治论哲学的盛行并不意味着认识论哲学的消亡。当高等教育愈益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工具,因为过分关注眼前利益而陷入非理智、盲目、自私以及冲动之中时,要求人文价值和人文精神的回归,强调大学应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承担起引领和批判社会的责任和社会良心的呼唤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潜流。
毫无疑问,认识论哲学和政治论哲学由冲突走向融合不仅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高等教育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哲学基础。仅仅满足于对知识的探索和对真理的无限追求,而漠视社会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的需要,大学就永远只能是传统意义上的藏经阁,永远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也只能重蹈古典大学衰落的覆辙;同样,如果大学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等诸多力量的牵引下失去方向,陷于功利主义的泥沼不能自拔,而忽略了对人类自身命运的思考和自身终极目标的追寻,这样的大学最多也只是知识的市场,而不可能真正成为社会的中心。
(二)二战后以政治论哲学为基础,许多重要的理论和概念相继提出,对人们的教育观念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1.极大地提高了政府和公众对高等教育性质、地位、作用的认识,并把高等教育视作关系国家安危和生死存亡的关键因素[4]。从美国《国防教育法》的通过到皮希特的《德国教育的灾难》等文件中,我们可以普遍看到各国在这方面达成的共识;而在第三世界国家,高等教育不仅被看作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且由于第三世界国家一般是从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国家脱胎而来,因此,更对高等教育赋予了摆脱殖民统治、实现国家民主、独立的功能。
2.对战后高等教育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无疑首推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在经济生产过程中存在两种形式的资本即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会产生更大的效益。所以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作为直接培养专门人才的关键成为人力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力资本理论的启示下,一大批经济学家和教育学家在60-70年代进行了对教育投资的社会和个人回报率的研究,并使研究成果逐步推广。战后日本、德国经济的迅速复苏与崛起从实践方面也论证了人力资本理论的正确性。于是美国乃至世界普遍形成了一个基本观点:人力投资是最好的投资,国家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的缩小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皆系于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发展[4]。虽然说传统的大学所培养的人才客观上或多或少地为当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人们对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前景并不关心。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改变了过去人们把高等教育视为奢侈品的传统想法,也为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之间找到了一条直接联系,为大学走进经济社会的中心找到了落脚点。
3.高等教育民主论。伴随人力资本理论的推广,高等教育成为社会、政府关注的焦点。教育民主化的核心内容与基本前提是教育平等,包括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平等。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指出,“高等教育的入学,应根据才能对所有人完全平等地开放”,从而拉开了教育民主化的序幕。教育民主化运动首先在美国发起。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美国与苏联争霸世界和努力开发“新边疆”的野心,英才教育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某种程度上,这种英才主义民主化打破了贵族教育哲学所设置的障碍),但随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许多青年人由于经济障碍不能进入学院不仅仅导致了人才的损失,同时涉及公民权利平等的问题。因此,如何帮助穷人、少数民族以及女性获得更多的入学机会,就成为大众关注的问题。1965年,美国通过了第一部《高等教育法》,规定联邦政府设立基本教育机会补助计划,大量资助家庭条件不利和少数民族学生进入高等学校。高等教育民主化的推行有利的推动了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同时也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因此,高等教育民主化迅速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起来。德国、日本、法国等发达国家也加速了对民主化运动的推行。
在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以及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如:研究表明国家的经济和劳动力已变得越来越依赖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的稳定供给;就个人而言除少数例外,男、女劳动力参与都随教育成就的不断提高而提高;对许多国家来说,高级中等教育是一个分界点,在此之上增加的教育能获得更高的额外报酬,特别是对女性,影响则更为明显[5]。既然个人受教育程度与个人前途以及生活质量紧密相连,因此,大众要求扩大高等教育机会的呼声也越来越大。
此外,终身教育思想、国际化等教育思潮的兴起都有力地冲击了过去传统的教育观念,对高等教育的改革提供了思想和理论来源。正是在这些思想的发展变革的引导下,高等教育的职能不断丰富与发展,高等教育第三职能的确立,是高等教育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关键。也是高等教育自觉承担起社会的要求的主动反映。如果说《莫里尔法案》标志着高等学校第三职能的发端,那么威斯康星思想则标志着高等学校与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的先河。但是威斯康星思想在当时还是星星之火,高等学校的服务职能真正大规模地开展还是在二战之后,以大学创办知识型企业为开端逐渐发展成高科技园区的中心,其中的代表就是“硅谷”与斯坦福大学的合作。一方面硅谷的企业依托与斯坦福大学的科研力量和人力资源,另一方面硅谷企业的繁荣也促进了斯坦福大学的繁荣,使斯坦福大学从一所农村俱乐部式的学校跃进至当今地位煊赫的世界著名大学。硅谷的成功,证明了教育与产业在现代科学水平上的结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生产力,引起了美国以至于全世界模仿硅谷的热潮。波士顿128号公路、三角研究园、中关村等相继成为各国、各地区高科技中心地带,也为大学更进一步走进社会的中心提供了新的途径。
三
国家、社会的关注与实践使高等教育真正从边缘走向中心。由于高等教育政治论哲学以及教育思潮对传统教育观念的冲击,对战后世界高等教育的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具体而言有以下几方面:
(一)由于高等教育被各国视为克服国家危机的“工具”,再加上人力资本的推波助澜,战后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政策来支持和改善高等教育以及公众、社会和个人投资高等教育的热情
首先,国家和政府对高等教育方面的投资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如英、法、德等国的政府拨款在80%以上,美、日在60%左右。虽然在70年代中后期由于世界性的严重的经济危机,各国政府纷纷削减高等教育支出,英国下降了37%、荷兰下降了38%,法国和德国下降了31%[6],但高等教育经费占教育总经费的比例却呈增长趋势,如美国从1985-1986年度的33%增加到1991-1992年度的38.6%,英国从1980-1981年度的21%增至1992-1993年度的29.3%。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却成增加的趋势。但从全球的趋势来看国家投资的主导地位没有改变,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重视也没有改变。
第二,社会公众投资办学以及捐助大学的热情有增无减。表现在民办大学或私立大学的增加以及大学校友和公众募捐的热情。
在拉丁美洲和亚洲,发展最快的是私立高等学校,如中国民办院校约占高等学校的1/3,在东欧和中欧私人办学的兴趣也相当高。而校友和公众的募捐在国外已经成为高等学校经费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在某些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开始实行学生承担相当一部分教育成本的举措,由不交学费到愿意承担相当一部分学费,反映了公众对自身或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视。在非洲虽然出现了因为校长宣布要交学费而被打死的情况,但从世界范围来看,私人自己承担高等教育的成本已经成为必然趋势。
(二)高等教育办学理念正在世界范围内发生深刻变化
按照马丁·特罗的观点,世界高等教育必然要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并发展到普及教育阶段。随着工业化的实现,早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发达国家,正在从高等教育是为多数人到为所有人的理念转变。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欧洲在1987年时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就已经达到25.2%。高等教育在拉丁美洲国家中的正规教育里可算是发展最快。1960年在高等学校注册的人数约为50万人,1975年达340万人;就全世界来看:1980年,小于8%的有71个国家,小于15%的有88个国家,大于15%的有41个国家,而1990年,小于8%的有49个国家,小于15%的有71个国家,大于15%的有51个国家[7]。
虽然在拉丁美洲和印度等地区或国家,由于忽视了本地区的发展特性,盲目仿效发达国家,造成了很大的浪费。但正如OECD1998年高教政策文件所明确指出:高等教育是人生必经之路,必备之经历。甚至曾经明确提出投资小学回报率明显高于投资高等教育的世界银行,在其2000年正式发表的报告里也明确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指出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能提供更多更好的高等教育,他们将发现要从知识经济中获益会变得愈来愈困难,高等教育不再是奢侈品,而是一个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世界银行还警告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带来的好处愈来愈明显,因高等教育落后而要付出的代价也会增长[8]。与此相适应,少数民族学生、女性等弱势群体的入学机会大大增加。在美国女性已经占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基本实现了男女平等,在第三世界国家,虽然在这方面仍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进步却是明显的。
此外,政府、社会和公众的支持也有力地促进了高等教育向着国际化、信息化、多样化方向的发展。这正是高等教育得以发展的社会基础,也是高等教育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原因,更是具体表现。
潘懋元先生指出,大学从边缘走进中心需要两个基本条件:(1)大学应具备适应知识经济社会的智力资源优势;(2)大学能够培养知识经济社会需要的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2]。考察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我们可以发现大学已经从近代象牙塔的阁楼里走出来,但真正从边缘走进中心还有一段距离。可以说,从边缘走向中心不仅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过程,也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但是,当我们为高等教育走向社会中心,感到鼓舞的时候,却不能不同时面对新的问题和挑战。例如,高等教育越来越成为政府以及社会所关注的问题的同时,高等教育如何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学术自由如何在功利主义与自身内在逻辑之间寻找平衡?高等教育与市场的结合,曾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了世界高等教育规模上的大发展,并为经济的复兴提供了极大的机会和便利。但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是传统大学使命的迷失,企业为大学下定单,不仅使大学课程设置更加功利和短视,而且也导致大学科学研究重应用,轻基础,重眼前,轻长远。市场手段介入大学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也是提高高等教育效率的有效途径,但把大学发展交给市场支配是极其危险的,大学如何在市场中寻找合适的定位?诸如此类问题,都引导我们思索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即如何界定高等教育,如何界定大学?大学在变化的社会与时代能否有所作为?能在多大的限度有所作为,有学者曾指出:人类起于困惑,而止于更高层次的困惑。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是如此,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反思、不断超越正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