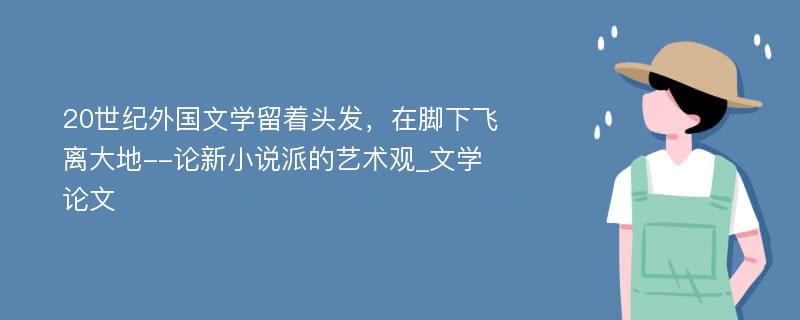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 揪着自己的头发不能飞离脚下的大地——论“新小说”派的艺术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己的论文,头发论文,外国文学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揪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尽管“新小说”派的作家并没有形成以严格方式追随一个明确目的的目标一致的文学运动,他们的艺术创作各有特色,彼此甚至很不相同,但在其复杂多变的现象后面,我们不难发现共同的思维背景,以这个背景为依据,才派生出了万花筒般令人眼花缭乱的灿烂景观。而洞悉这个深层背景的切入口之一,便是直接分析其特殊的艺术观。
本体论:无目的的目的
“新小说”作家是以其反传统的举措而拉开小说创作之幕的,而他们反传统的第一声号角,就是声讨西方文学一二千年以来以道德论为目的、以认识论为手段的文艺本体论。这种文艺本体论由古希腊苏格拉底提出,经柏拉图和亚理士多德理论化、系统化后,一直牢牢地统治着19世纪以前西方文艺理论的基本方向,因而也深深地影响并制约着西方文学长河的基本流向。尽管在19世纪以后,标榜“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思想登上了文学历史舞台,它们也曾将矛头指向了传统的以道德为目的、以认识为手段的文艺本体论思想,但我们仔细一看,便不难发现,它们不过是从逆反心理的角度,颠覆了传统道德论、认识论的理性主义尺度,从而偷换了传统道德论和认识论的内容:自然欲望代替了社会意志、情感体验代替了理智认知、人性的肉体代替了神性的灵魂、生命的直觉代替了思维的悟性。但从根本上说,它们并没有、也不可能从形式上彻底摒弃传统的文艺本体论。“新小说”派的艺术反叛,则是试图从根本上摒弃这种传统的文艺本体论。罗伯-格里耶在《未来小说的道路》中宣称:“我们必须制造出一个更实体、更直观的世界,以代替现有的这种充满心理的、社会的和功能意义的世界。”①
“新小说”派对传统文艺本体观的冲击是从两个方面发动的:
首先,它将攻击点直接指向了传统文艺本体论的道德目的。我们知道,从古希腊苏格拉底以来所建立的文艺的道德目的的核心并不在于它具体的道德内容,而在于它密切关注的社会人生。“新小说”派的创作也就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无情地抽去了小说中人的生存、人的行为,中止了传统文学围绕社会人生所编织的悲喜剧的继续上演,代之而起的则是“物”的堆砌。如罗伯-格里耶就毫不动情地描写事物的“既无虚伪光彩也不透明”的表层,单纯关注物件的物理属性,它的度量、空间位置等等。由此,他小说中的人物逐渐消失了,剩下不多的人物也往往成了毫无生命特征的字母符号。小说中从头至尾呈现出的是冷漠、细密而又繁琐的景物外观。娜塔丽·萨洛特的笔下虽然似乎有人,但却没有动人心魄的生生死死,代之而起的是转瞬即逝、漂泊无定的人之意识的地下活动。正如萨特在为萨洛特所作的《<陌生人肖象>序》中所说:“娜塔丽·萨洛特在观察我们内心世界时具有一种原生物的视觉,你翻掉常理的石块,就可以看见吻口、流涎、沾液,阿米巴虫似地蠕动。”②
在此基础上,“新小说”创作进而抛弃了传统文学里充满绵绵情意的拟人化描写,代之以漠然的平铺直叙,如罗伯-格里耶名为《嫉妒》的小说,失去了传统小说中那使人死去活来的亢奋、激烈、疯狂,代之而来的似乎只是一架摆放在一个封闭角度的无生命的自动摄像机的摄像。罗朗·巴特在《不存在罗伯-格里耶流派》中说:“罗伯-格里耶之所以用准几何学的方式描写物,那是为了摆脱人赋予它们的涵义,使它们改掉隐喻和拟人法。因此,罗伯-格里耶作品中细致的目光(与其说细致,还不如说是越轨)纯粹是否定的,它什么也不立,或者更确切地说,它立的是物中那种非人性,就像遮盖着虚空并指明虚空的存在的那层凝固不动的云一样。”③
其次,“新小说”派攻击的是传统文艺本体论的认识手段。我们也知道,认识是文艺道德目的的前提和逻辑起点。在古希腊苏格拉底那里,知识与美德是合一的。柏拉图判定文艺优劣的尺度是认识论。亚理士多德就直接称求知为实现文艺目的的必由之路。“新小说”派的创作则以故意的闪烁跳跃的印象流动,淹没了人与世界关系的确定性,以繁琐、零碎的拼凑,以幻觉、梦境的交错遮蔽了人的生存状态的清晰度。由此,“新小说”派的创作也就斩断了连接文艺行为与道德目的的认识论桥梁。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个互不相干、四分五裂的破碎的镜头切割,我们无从洞见人类世界的真象,也就无法窥测人类生存的善恶方向。小说失去了认识世界的功能,也就失去了寄寓情感、净化灵魂的道德目的。
“新小说”派对传统文艺本体论的两个方面的攻击,既从目的又从手段,从而既从情感又从逻辑上疏离了作品里人与世界的关系、作品外读者世界与作品世界的关系,因而也就中止了文艺与社会现实认识的、道德的联系,将传统小说源远流长的文艺本体论轰毁了。
“新小说”派果真跳出了传统文艺本体论的魔圈,从而果真超越了文艺之道德的、认识的本质属性吗?
我们不妨以巴尔扎克的文艺思想作为传统文艺观的参照标准与“新小说”派相比较:
巴尔扎克现实主义的核心就是西方传统的以道德为目的、以认识为手段的文艺本体论思想。但我们在评价“新小说”派的时候,却不能将巴尔扎克的小说当作文艺创作的“达玛斯忒斯的床”,不能退到巴尔扎克所站定的历史起跑线上。巴尔扎克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世界正以无可抗拒的魔力逐渐代替并消灭旧有的封建贵族秩序。其历史的必然趋势令人欣慰,但其对人类情感、伦理的赤裸裸的践踏又令人心悸。于是,巴尔扎克式的小说家,自觉地响应时代的召唤,秉承着传统文艺目的论、认识论的本体观,着力暴露社会黑暗,批判现实罪恶,从而为人们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形象解说,以打碎人们对资本主义现有秩序的幻想。
然而,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性悲剧,使遍体鳞伤的西方世界进入了娜塔丽·萨洛特所称的“怀疑的时代”。西方人对其以往的精神旗帜的信念发生了全面怀疑与动摇。上帝死了,人道主义理想在漂浮不定的世界面前彻底破灭了。一方面,是难以捉摸、纷纭变幻的荒诞世界,另一方面,是同样不合逻辑、难以理喻的人自身。这是文学所不得不面对的人类真实境遇。为此,小说家还能以过去人的眼睛来观注这个多变的世界吗?还能在这荒诞、破裂,千奇百怪的世界面前,看出一个头绪,清理出一条清晰的序列吗?此时,小说所秉承的传统的文艺本体论又如何面对其历史的挑战而调整自己?罗伯-格里耶这样说:“从巴尔扎克到‘新小说’派,小说艺术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巴尔扎克笔下有真实,‘新小说’派笔下也有真实,两种真实是有差异的。”④显然,这时对世界的任何巴尔扎克式的真实再现都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传统文艺本体论的认识能力首先遇见了强有力的挑战。因为世界在我们面前已变得陌生,我们无从亲近这个世界并与之沟通,我们只能发现跳动不居、闪烁不驻的模糊表象。由此,“新小说”派不得不转移传统文艺观直接认识现实的企图,而将关注的焦点移向对世界人生的朦胧印象和猜测。如同克洛德·西蒙所说:“如果说在艺术史上产生了断裂或根本变化的话,那就是作家们继画家之后,不再声称表现了可视世界,而仅仅表现了自己从可视世界接受的印象。⑤于是,现代西方人千头万绪的错综情感也就物化为“新小说”派的艺术世界了。通过这个世界,终于使不可言说的关于世界的理解得以诉说,使难以捕捉的漂浮流动的感受有了一个具体形象的外观。如罗伯-格里耶的小说《橡皮》所展示的令人迷惑不解的阴错阳差,《窥视者》所展示的虚实迷离,克洛德·西蒙的《农事诗》、《弗兰德公路》中时空交错重迭的历史与人,以及娜塔丽·萨洛特小说中那骤然而至、转瞬即逝的意识流动,原来都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传达了现代西方人对外在现实难以捉摸、无以把握的心理感受。
在此基础上,“新小说”派的创作也就自然向前延伸至对现实世界的批判,从而也就延伸至对道德目的的实现。再观《像皮》、《窥视者》,我们于是体验出它们包含着对理性规律、社会法则多么深重的失望和无可奈何的痛苦。偶然与巧合使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曾经大放异彩的人的生命也失去了对生死抉择的庄严意味。从这个角度看,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与存在主义是植根于相同土壤之中的,不过,他们不像存在主义那样向这样的世界公开挑战,而是用技巧、表现手法为外壳把自己包裹起来,到形式中间去寻找出路。”⑥
“新小说”派从否定传统的文艺本体论开始,转了一个大圈后,又从新的层次上回到了传统的文艺本体论。所不同的是,它是将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符号,一方面让人从认识论的角度从中领悟到世界的本原以及人类生存的本象,从而完成了艺术符号不可替代的认识功能,另一方面,又从文艺最终诉诸于人之情感的目的,使人在获得对世界的认识后得到心灵的绝大自由,也得到道德的寄托,从而也就在本体论的层面上实现了文艺之无目的的目的。
创作论:无内容的内容
“新小说”派吹响反传统文艺本体论号角的同时,自然也就擂起了反传统文艺创作论的战鼓。他们一反传统小说对所谓社会内容的钟爱,着力关心的是小说的表现技巧和手法。在此方面,他们煞费苦心。米歇尔·布托就毫不讳言地把自己的小说看作“叙述者的实验室”⑦。他因此主要在小说中致力于从事各种各样的技巧的实验。从其它“新小说”派作家的创作实践看,他们对文学艺术的社会内容似乎确实没有兴趣,读者似乎很难从他们的作品中找到对重大历史内涵或现实信息的陈述,以及对历史和现实的道德评说。他们把传统文学创作论称之为形式的东西置于首要的、也是唯一显要的位置上。于是,在罗伯-格里耶的《嫉妒》中着力描写的是毫无社会性内容的静物排列组合,人物只成了一个影子般的叙述者或一个“A……”;《在迷宫中》反复展示的是毫无变化的街道和走廊。克洛德·西蒙的《农事诗》、《弗兰德公路》展示的是一组组镜头的切分、组合、复现、交叉以及游移不定的视角变换、时空上的蹈袭迭合、周而复始;在叙述中,不少段落故意无标点,干脆拒绝回答对内容的追问。
“新小说”派创作论果真仅是“形式”的刻意求新,其创作活动果真仅是一种无内容的文字“游戏”吗?
现代人类文化学、心理学及艺术哲学的深入研究,使我们不再怀疑那以直接感性外观呈现于我们眼前的完整的艺术品本身就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因为艺术的形式中就蕴含着一种情感和生命的“力”的模式,它以“完形”的方式与我们的心和灵魂相撞击,使之迸发出灿烂的火花,从而突然领悟到某种生的苦恼、死的奥秘,一方面获得对深厚的情感内容的感知,另一方面也获得审美的狂喜。如娜塔丽·萨洛特在《从陀斯妥耶夫斯基到卡夫卡》中所说:“小说所打透的并不是读者表面的、荒芜的智力领域,而是无比丰富的境界,即感觉心灵的不在意、无防备的领域。这种力量在感觉心灵中引起神秘的有益的撞击,情感上的震荡,使人如闪电一般霎时间就能抓住整个事物及其各种细微差异,抓住这些事物可能具有的复杂性,甚至抓住这些事物深不可测的奥妙——如果出于偶然,这些事物确实有什么奥妙的话。”⑧也就是说,“新小说”显然不是以传统小说的习惯方式传达所谓的内容,而是以形式符号本身的魔力,打透那心灵深处与之同构的审美心理形式结构,从而引起灵魂的震颤,在瞬间如神灵附体般顿悟到世界的奥秘,实现了文艺的道德目的,即也就同时获得了被称为内容的东西。对于“新小说”派文学创作的千变万化的形式,我们应像观看毕加索的画一样,不必也不可能将绘画中的细节与现实中的真实一一作所谓内容的对照,而应从整体上用自己的心去体味其中的生命和激情。这里需要拉开一个距离,将日常的观看转化为审美的注视,将细致地寻觅内容转化为整一性的情感体验,将逻辑的分析转为心灵的观照。于是,我们也就会发现在千姿百态的形式后面,潜含着无比丰厚深广的历史现实内容。
同时,还应看到,“新小说”派创作的形式革新,也不是随心所欲地自由发挥,而是应运而生的时代之子。也就是说,它们的形式变换来源于现实的人之情感呼唤。生存在世界上的人,一方面没有不变的情感体验,另一方面也没有任意变幻的艺术形式,一定的形式总是与一定的情感方式密不可分的。正如苏珊·朗格所说:“艺术乃是象征着人类情感的形式之创造。”⑨艺术形式的产生和发展,常与我们的感觉、理智及情感生活的变化发展所具有的动态形式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布托在其《漫谈长篇小说的技巧》中说:“现代生活使时间的间断性不可比拟地显著起来了,所以,许多作家为了表现这种显著的间断性,便开始用一个个的组合结构来组织叙事。”⑩由此观之,“新小说”派小说中那交错重迭的时空序列、一鳞半抓的事件碎片,本是现代西方人对理性逻辑再不能把握纷纭复杂之现实的情感体验。罗伯-格里耶作品中的不确定性、含混性、漂浮性;克洛德·西蒙作品中的时空交叉;娜塔丽·萨洛特作品中的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皆来自于现代西方人失去了对自我认识能力的信任。罗伯-格里耶《嫉妒》中的“嫉妒”,作为人类情感的激烈形式之一,之所以褪去了传统小说所具有的亢奋、激烈及疯狂感情的支出,在于今天的“嫉妒”已经失去了丰厚的情感、心理、道德的真诚投入,它变得平淡、单薄,只是一种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生活节奏的一个环节而已。因为,“新小说”派作家觉得他们完全面对着一个荒漠而又无情的异已世界。要从这个世界汲取爱与恨的激情、生与死的亢奋,得到的只是“人看着世界,而世界并不回敬他一眼”(11)。这里面包含着更深沉的一种“哀莫大于心死”的苦涩滋味。
最后,还应特别看到的是,“新小说”派作家都否认有一个等待着被传达、诉说的现成的被称之为内容的东西。也就是说,否认在形式的外套下面有一个清楚的赤裸的内容身躯。他们确信他们的艺术形式本身才创造出了内容。他们以文艺的“怎么写”代替了传统的“写什么”的命题,以“叙述的历险”代替了“历险的叙述”。这种创作重心的转移,标志着20世纪语言科学的新成就给文艺家的启迪。现代语言学对语言“能指”功能的研究表明:语言处于人类精神活动的重心地位,它本身就是一个通向人类所有领域的精神实体。对于将语言作为艺术媒介的文学来说,尤其如此。文学作品,一方面作为内容的载体,另一方面更帮助人们构建起情感体验的对象,从而最终创造出内容。莫瑞斯·琼斯就特别强调艺术作为情感语言的这种功能,他说:“通过这种语言,艺术家对变幻不定的情感进行了探索和发现,并赋予他们名称和栖身之所。”(12)“新小说”派的创作也就并不在于传达先知先觉的现成内容或情感,而是以特定的构成力量去组织乃至形成人类社会的现实内容和情感经验。如同克洛德·西蒙所说:“当我面对白纸而坐时,我遇到两件东西:一方面是我内心各种感情、回忆和印象的模糊混杂体,另一方面是语言,我所寻觅的借以表达的词和单词赖以排列成序的句式,它们将凝聚在那句式中。于是,马上就得到第一个证明:人们从来不是记述(或描写)一件在写作之前已经发生的事情,相反,对象是在写作过程中产生(这里‘产生’一词应取其一切意义)并与写作本身同时出现的。它并非来自最初的非常模糊的写作计划与语言间的冲突,而是形成于以上两者的紧密结合,至少在我身上这种结合所产生的结果比起最初的意图来不知要丰富多少。”(13)米歇尔·布托也认为:“叙述这一现象大大超过文学的范畴,是我们认识现实的基本依据之一。从我们听懂说话直到老死,我们始终处于叙述的包围之中……”(14),“我们对世界的了解大部分是通过别人对我们叙述的:谈话、课程、报纸、书籍等等。因此,我们亲眼所见的东西,我们亲耳所闻的东西仅在这片叙述的大合唱中才具有意义。”(15)“新小说”派对叙述的这些见解与他们的整个文艺观念体系是一致的。他们撕裂了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幻梦。认为人类作为类存在而言,无可奈何地受制于物,受制于客观冷漠的外部世界;每个人作为个体存在而言,又毫无例外地受制于所处的文化,受制于语言的叙述。所以,与之相应,他们在本体论层面上强调对物的世界的关注,在创作论的层面上也就自然强调对语言叙述的关注。娜塔丽·萨洛特在其作品《金果》中借其中人物之口说:“把看不见的东西融合在含混不清的词义中,从而取消了这种看不见的东西。此处所谓“看不见的东西”是人对世界的揣测及难以言状的体验。它与含混不清的语词叙述互相吻合,融汇为二而一的具象,终于能让人看见了。由此可见,“新小说”派作家以为,艺术形式并不是外在地装饰已经可见的现成内容,而是让人第一次找到并看见内容。罗伯-格里耶也说:“我的哲理不像萨特那样,他是先有哲理,然后把哲理写进小说,而我的哲理存在于小说形式的本身,是体现在小说的形式上,因此,我们‘新小说’并不是无思想、无意义的。”(16)由此,“新小说”派的小说对事件因果联系和常见时空形式的大破坏,是为了揭示和探索复杂多变、不可测知的现实世界。它对人物形象中心地位的故意否定,也是为适应揭示和探索个性被抹杀、人失去自身的时代本质。可见,“新小说”派的形式是从新的层次上包孕着极其丰厚的历史时代内涵,包孕着深沉而又冷静的对现实关系的明智洞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小说”派的艺术创作与存在主义的艺术创作相比,也就不过是对世界挑战的方式不同罢了,存在主义文学试图颠覆的是现存社会制度,“新小说”派则是试图颠覆现存社会制度赖以生成的文化形式之一--语言叙述。
“新小说”派以迂回曲折的方式,通过对形式的精心选择、构筑、创造,最后终于让我们获得了容量不能算小的社会情感内容,由此,它也就实现了在创作论层面上的无内容的内容。
价值论:无意义的意义
“新小说”派在擂起反传统的战鼓,开始了文艺创作重心转移的同时,其革命性行为也就必然延伸至对传统文学意义的重新阐释。他们以反对人的自我中心主义为逻辑起点,拒绝承认人类世界有现成的意义。克洛德·西蒙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仪式上这样说:“(我)活到今天七十有三,凡此种种,我还没发现出什么意义来,除非像莎士比亚之后我想大概是巴特说的,‘要是世界有什么意义,除了世界本身的存在,其意义也就在于无意义可言’--仅此而已。”(17)
“新小说”派对意义的否定,既源于它对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反叛,也源于它对19世纪以来的“非理性主义”的背离。传统理性主义坚信有一个终极的最高目的支配着人类社会历史,同时也支配着人类社会文化行为之一的文艺创作。“非理性主义”不相信世界之上有一个终极的最高目的支配着世界。他们以为世界之最根本的目的就在人自身潜意识之中。不管是传统理性主义还是非理性主义,它们的核心都是人本主义,两者的区分不过是一枚金币的不同面而已。理性主义将人的社会共性、道德意志异化为至高的神灵,非理性主义则将人的自然个性、情感欲望异化为难以捕捉的外在力量。文艺的意义无非是从不同的侧面将其必然与自由沟通,从而取得现象与本体的平衡和谐。
“新小说”派则不认为世界本身在本体意义上有任何以人为参照系的终极目的。所谓至高无上的上帝,难以洞见的“理式”、“理念”,高深莫测的“意志”、“生命直觉”、“利比多”等,不过是人的自我中心主义的假定。世界本不过由外在于人的物质所构成,物质的千奇百怪的偶然状态决定着世界的存在,人对此是束手无策的。由此,“新小说”派捣碎了人之自我中心主义的梦幻,也就拆除了由此产生的关于文学之人学意义的假定。人类世界既然并无实在的意义,那么,作为人类文化行为之一的小说创作也就没有了连接世界与人生的所谓意义。如同罗伯-格里耶所说:“在我们的周围,世界的意义只是部分的、暂时的、甚至是矛盾的,而且总是有争议的。艺术作品又怎么能先知先觉预先提出某种意义,而不管是什么意义呢?”“作品成立之前,什么也没有,没有肯定、没有主题、没有信息,认为小说家‘有些事要讲’,然后又寻求如何讲,这是一种最严重的误解。”(18)
世界是无意义的,但人在这无意义的世界上总还得凭自己创造文化的能力有意义地活下去。文学作为人类与世界相交的重要文化形式之一,不可能不为人类的生存提供或制造活下去的勇气。
终于,“新小说”派吃惊地发现,他们从认识论前门所扔掉的文艺的人类自我中心主义外套,还得从价值论后门重新拾回来,以遮蔽在荒漠的世界上索索颤抖的赤裸的人生。由此,他们也就与存在主义文学殊途同归,把本属价值理性的文艺还归了价值理性。既然认识论告诉我们,人类面对的是一个荒漠而陌生的世界,这个世界不赋予生存于中的人类以意义,那么,反过来,我们便可以,甚至必须从价值论出发,用文艺的行为给世界、也给人自己创造一个生存的理由和意义。也就是像萨特一样,以“我写作故我存在”赋予世界、人生以意义。正如西蒙所说:“在启蒙世纪末和‘现实主义’神话诞生以前,诺瓦利斯就以惊人的明达指出了下列矛盾表象:‘语言像许多数学公式一样,自己就构成了一个自身的世界,而且只在相互之间发生作用,除了表现它们本身的奇妙特性外,什么都不表达。正是这一点使它们变得那么富有表现力,以致事物间各种关系的奇特作用就体现在它们身上’。或许正是在研究这一奇特作用的过程中,人们才构想出写作行为。每当写作行动稍微改变了一下以语言维系的人与世界的关系时,它也同时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世界。”(19)罗伯-格里耶也称:“我们不再信服僵化凝固、一成不变的意义,在先它是陈旧的神喻,尔后是19世纪理性主义将这种意义强加给人类的,而我们对于人却寄予希望,只有人创造的形式才可能赋予世界以意义。”(20)
人淹没于物的毫无意义可言的世界,人却同时可能以文艺行为创造出值得为之激动、狂想的意义世界。据此,再读罗伯-格里耶的《去年在马里安巴》,也就有了新的体悟。X与A游移于呆板的墙、走廊的宫殿中,既非荒诞、也无意义,存在着,如此而已。人们重复着单调划一的火柴游戏、多米诺骨牌的赌博,以之区别于僵立不动的人形。X极力想弄清他之所以来此,之所以如现在所思所为的理由。他要确定他的现实存在的依据和意义。他极力以动人的、诗一般的“叙述”来激动A,也激动自己。于是,他们似乎发现并确证了他们确如“叙述”中一样存在,同时,也只有果真如此存在才有价值与意义。
文学是人学,文学的人学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是否直接描写人的感情,而在于从价值理性的角度寄寓人的历史中失落的情感和受伤害的心。如克洛德·西蒙的《农事诗》,它令人清醒地认识历史并非完全是传统理性主义所坚信的文明不断征服野蛮的进步,战争的硝烟与血腥并非总有正义与献身的悲壮意蕴,历史只是像无情自然一样,周而复始、循环相继。但是,人的行为也就像顺其自然流动不已的农事一样,本身也就是超越自然的诗,它赋予虚无的世界人生以诗的审美意趣。由之,“新小说”派也就从认识论层面上的“哀莫大于心死”的苦涩而走向了价值论层面上的“却道天凉好个秋”的通脱超迈。
“新小说”派否定世界有先定的意义,它把文艺意义理解为无意义中的有意义行为。反过来,它也同样毫不居高临下地对待它们的读者,因为读者在阅读一本小说之前,也不可能从本无意义的作品中接过来一个现成的意义,相反,读者的阅读行为本身才是意义生发的契机。所以,罗伯-格里耶说:“我劝读者们阅读时要有完全自由的思想,彻底忘却固有的观念。”(21)在审美活动中,读者是自由的,它可以凭自己的能动参与、对话而获得存在的明证和意义。这犹如在球赛中一样,被争抢的那个球本身并无意义,有意义的是围绕球而展开的争夺本身,这就是审美游戏的根本特性。萨特以“我写作故我存在”替换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传统命题,“新小说”派则又进一步以“我阅读故我存在”的命题拓宽了萨特自由的范围。
理解了这种赋予读者以自由的思想,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新小说”派在创作中常用第一、二人称叙事,或者叙述者在小说中又兼以角色。这种改变第三人称全知全能叙述角度的作法正是旨在改变读者与作品的传统关系,改变其被动的接受为主动的对话参与。如米歇尔·布托的《变》,它所采用的第二人称叙述方式,将每个读者推入对自身生活现状的反思: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使家庭关系表现为凝滞、沉闷。婚姻表现为习惯、义务。于是作为其婚外恋的情人开始扮演激情与生命的替身,但谁又能保证这种替代不会同样沦为第二个沉闷、凝滞的家庭,从而失去陌生的动人心魄的魅力呢?这种深刻的反思迫使每个读者不管“情愿与否,总要在自己的内心深处进行一番比较、排斥、认同,甚至不自觉或被迫戴上代尔蒙这个人物面具进入小说。”(22)
这也就是“新小说”所描述的事件飘忽不定、逻辑混乱的又一个原因。如《橡皮》、《窥视者》就给读者提供了参与“游戏”的多种可能。读者完全可以自由地从自我生命的感悟出发,发掘或创造出不同的象征意蕴,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自由展现。
到此为止,“新小说”派从认识论的否定意义开始,以价值论的肯定意义结束,终于从新的层次上回归于文学之为人学的传统范畴,从而耐人寻味地实现了价值论层面上的无意义的意义。
“新小说”派以反传统作为其文艺创作的起点,沿着无目的、无内容、无意义的轨道走了一个半圆以后,又回到了目的、内容、意义的另一半圆,从而也就回到了与其起点相迭合的终点。作为人类文化行为之一的文学创作,“新小说”不可能脱离文学之为人学的范畴,就像人不可能揪着自己的头发飞离脚下的大地一样。
注释:
①《未来小说的道路》,引自《新小说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63页。
②《<陌生人肖象>序》,引自《新小说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63页。
③《不存在罗伯-格里耶流派》,引自《外国文艺》1990年第4期。
④(16)柳鸣九《“于格洛采地”上的“加尔文”》,引自《新小说派研究》第567、569页。
⑤(13)(17)(19)《在斯德哥尔摩的演说》,引自《世界文学》1986年第4期。
⑥王泰来《从阿兰·罗伯-格里耶的三篇短文看新小说》,引自《世界文学》1982年第3期。
⑦(14)《作为探索的小说》,引自《新小说派研究》第89、88页。
⑧《从陀斯妥当耶夫斯基到卡夫卡》,引自《新小说派研究》第5页。
⑨《情感的象征符号》,引自《美学译文》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24页。
⑩《漫谈长篇小说的技巧》,引自《法国作家论文学》,三联书店,1984年,第427页。
(11)《自然、人道主义、悲剧》,引自《新小说派研究》第74页。
(12)《情感语言》,引自《英国美学杂志》1960年1月号。
(15)《对小说技巧的探讨》,引自《新小说派研究》第136页。
(18)(20)《新小说》,引自《法国作家论文学》,第400、401页。
(21)见《世界文学》1988年第5期。
(22)林青《<变>的第二人称的叙述视角》,载《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2期。
标签:文学论文; 本体论论文; 艺术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嫉妒论文; 巴尔扎克论文; 农事诗论文; 窥视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