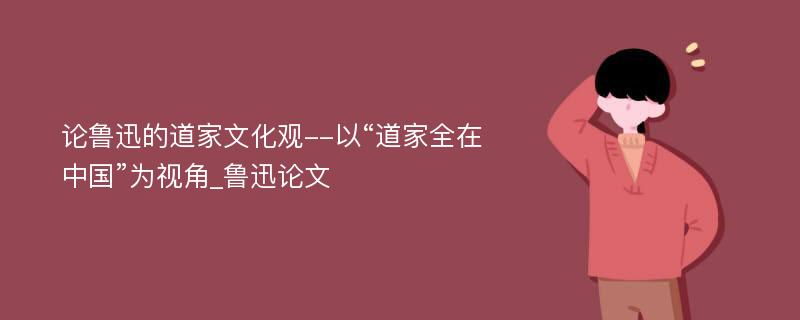
论鲁迅的道教文化观——从“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教论文,鲁迅论文,中国论文,文化论文,根柢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鲁迅先生在一九一八年致许寿裳的一封信中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注:鲁迅180820致许寿裳,见《鲁迅书信集》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鲁迅所言“中国根柢”,当指中国文化之根柢,为什么说它“全在道教”?这句话表达了鲁迅什么样的道教文化观?鲁迅先生在信中未作具体阐释,后人对这个论断的理解可谓众说纷纭。二十多年来,国内道教学界也对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至今仍是见仁见智。笔者以为,从“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论断出发理解鲁迅的道教文化观,须从三个方面入手:(一)、鲁迅是把道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来看待的;(二)、鲁迅从“改革国民性”的客观需要出发,对道教给中国国民精神所造成的影响、特别是负面影响作出了深入的剖析和批判,这集中反映出鲁迅对道教文化的基本态度和看法;(三)、对鲁迅的这个著名论断须作进一步的具体分析,才能更准确地把握鲁迅的道教文化观。
一、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鲁迅的一生,处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最为严峻的时代。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鲁迅,深刻而敏锐地认识到,民族的生存危机主要来自一种民族文化的危机,一种人心的危机,即中国的民族精神和信仰世界出了大问题。因而他主张“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注:鲁迅《两地书·八》,见林非主编《鲁迅著作全编》卷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弄清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他通过对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和文化的深入剖析和深刻反省,认为国民的精神和心理状态,主要是受传统文化的主体儒、道、释三教及其合流的长期而直接的熏染与潜移默化的结果,而道教,一直是封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处于与儒、佛鼎足而立的地位。
从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来看,他们大多以儒学作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儒家的“尊尊”、“亲亲”的思想传统以及严守“贵贱”、“大小”、“上下”的等级伦理说教一直是统治者用以维护其专制统治的主要工具。同时,统治阶级也利用道教和佛教作为麻醉、欺骗广大民众的辅助性意识形态。鲁迅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他曾对好友许寿裳说,“孔子提出三纲五常,硬要民众当奴才,本来不容易说服人,而佛教轮回说很能吓人,道教炼丹求仙则颇有吸引力,能补孔子之不足”(注:转引自郑欣淼《鲁迅与宗教文化》第266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的确,“正像在巩固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方面,儒家早已于被独尊的汉代之前就吸取和运用了法家的不少主张那样,在巩固封建专制主义的精神控制方面,历来的儒家却又吸取和运用了道家的许多主张。这是因为儒、道两家在有些根本的方面来说,也有其相同的地方。他们都是以远古时代作为自己憧憬的理想,从而陷入保守与封闭的精神氛围中间,丧失进取和创造精神。这正如鲁迅所指出的那样,儒、道两家都是‘理想在不撄’”(注:林非《鲁迅与中国文化》第38页,学苑出版社2000年。)。
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人生哲学来看,儒道释三教及其合流对于他们的人生态度和行为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鲁迅指出:“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人总有三种小玩意,一是《论语》和《孝经》,二是《老子》,三是《维摩诘经》,不但采用谈资,并且常常作一点注疏”(注:鲁迅《准风月谈·吃教》。见《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本文所引鲁迅杂文据此,以下引用只注篇名。)。可见,道与儒、佛总是结合在一起,融合在传统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身上,并成为一种理想的人格追求。从思想发展的历程看,儒道两家有入世、出世之别,但文化史上的儒道合流由来已久,道家、道教的人生观往往是儒家人生哲学的必要补充和调剂。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居庙堂之高”和“处江湖之远”、得志与失意两种交错的心态中。有了道家、道教人生哲学的必要补充和调剂,就有利于他们更好地生存下去。鲁迅对这种儒道合流的实质看得很清楚:“登仕,是噉饭之道;归隐,也是噉饭之道。假使无法噉饭,那就是连‘隐’也隐不成了”;“汉唐以来,实际上入世并不算鄙,隐居也不算高,而且也不算穷,必须于‘隐’而不得,这才看作仕人的末路”(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吃教》。)。
三教合流、三教归一的文化心理同时也影响到普通民众对于鬼神和宗教信仰的态度,那就是缺乏“坚信”,讲求实际,不管是非彼此,也不讲什么信仰、原则,对各种信仰和各类鬼神一律采取兼收并蓄的方式,见庙就焚香,见偶像就膜拜,只要对自己有利就行了。而道教的复杂的神仙系谱既是这种文化心理的反映,也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文化心理。道教沿袭了上古时期自然崇拜和鬼神崇拜的传统,将各类天神、地祗、人鬼、仙真以及古圣王、古圣人乃至民间信仰的神灵、英雄人物,通通纳入其神仙系谱内,为广大民众提供了众多的偶像,满足了他们各式各样的实用的和精神的需求。
此外,道教教义上的独特性也使它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获得了不可忽视的地位,至今仍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鲁迅说:“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的大半。”(注:鲁迅《而已集·小杂感》。)为什么这样呢?因为道教是唯一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而形成的民族宗教,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具有与佛教、基督教等宗教不同的价值追求,集中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人生理想、需要和追求。如果说一般的宗教都不把注意力放在现实的生的快乐和幸福的追求上,而是转向死后的世界,即虚幻的天国与来世的话,道教却相反,它受到中国《易》文化“生生之谓易”的观念和道家哲学贵生、重生思想的影响,在人的生与死,存在与灭亡的对峙中,抓住“生”的一端来观察宇宙万有和人生,认为人这个生物,有无穷的潜能,如果通过修炼把它发掘出来,就可以“参赞天地之化育”,弥补天地万有的缺陷。“道家(道教——引者按)的学术思想,基于这种观念出发,认为人的生命,本来便可与天地同休(龄),日月同寿(命),而且还可以控制天地,操纵物理。……这种对于人生价值,与生命具有大功能的观念和理论,在世界文化思想史上实在是史无前例的,只有中国一家——道家首倡其说”(注:南怀瑾《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第158-159页,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4年。)。从对生命的这种理解出发,道教主张重生、贵生、乐生,追求长生,最高理想是不死成仙,使形体和精神都达到长生不死。这就迎合了人们追求健康长寿甚至长生不老的本能欲望。这对于素有重生、养生传统的中国人就具有广泛的吸引力了。所以,从历代的最高统治者、官宦和士大夫到下层民众,都有相当多的人信奉道教,因而道教能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流传不息,产生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正如鲁迅所说:“然而假如比较之后,佛说为长,中国却一定仍然有道士,或者更多于居士与和尚:因为现在的人们是各式各样,很不一律的。”(注: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小说世界〉》。)鲁迅还说:“儒士和方士是中国特产的名物。方士的最高理想是仙道,儒士的便是王道。”(注:鲁迅《且介亭杂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方士是道士的前身,鲁迅用儒士和方士指称儒学和道教,并称其为中国的两种“特产的名物”,可见在鲁迅看来,道教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不了解道教,就不能真正了解中国社会和历史,也不能深刻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二、鲁迅对道教文化的剖析与批判
鲁迅在充分肯定道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时,从改革国民性的客观需要出发,对道教作为宗教的实质、道教中的种种方术和封建迷信及其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所起的阻碍作用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无情的批判。鲁迅认为,道教有三个主要的源头,一是殷周以来的鬼神崇拜和巫术迷信,二是自战国中期和秦汉以来的神仙方术,三是先秦道家思想。他对道教的剖析批判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展开的:
(一)对道家思想的批判:
道家思想是道教重要的理论来源。鲁迅和他同时代的许多思想家一样,没有严格区分道家和道教,他对道教的批判首先表现在他对老庄哲学的批判上。
对道家思想的开创者老子,鲁迅主要批判了他的倒退复古的政治理想和消极无为的人生观。老子从天道自然无为的原则出发,认为理想的政治就是回复到远古时期的小国寡民的状态,并认为“无为而治”就是实现这种理想的主要途径。针对这一点,鲁迅指出:“老子书五千语,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以无为之为化社会,而世即于太平。”(注:鲁迅《坟·摩罗诗力说》。)他从进化论观点出发,认为社会的向前进化犹如“飞矢”,总是飞向前方的,而“幻想中的唐虞,那无为而治之世,不能回去的乌托邦,那确实性,比到‘阴间’去还稀少”(注:鲁迅《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复古倒退的社会理想,使人“心如槁木”,不思进取,丧失理想和斗志,只顾眼前实利,最终变得卑俗、懦弱、吝啬、胆怯。同时,“无为而治”还使统治者奉行一套“使民不争”、“常使民无知无欲”的愚民政策,暗中玩弄一套阴险狡诈的“君人南面之术”,对封建政治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老子还根据“反者道之动”的原则和“无为”、“不争”的思想,推行一套消极退让的人生哲学,鲁迅认为这只能塑造出怯懦、保守、畏缩、苟且偷生、不思进取、不敢为天下先的国民来,逆来顺受、含辱忍垢和麻木软弱是其最大特点。“无为”、“不争”的结果,“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然而人性岂真能如道家所说的那样恬淡;欲得的却多。既然不敢径取,就只好用阴谋和手段。从此,人们也就日见其卑怯了”(注:鲁迅《华盖集·这个和那个》。)。鲁迅在其小说《出关》中以“孔老相争”为线索,借老子这个形象鞭挞了懦弱、退让的国民劣根性。鲁迅这样评价孔老:“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却是我的意见:老,是尚柔的;‘儒,柔也’,孔也尚柔,但孔子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老则为‘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注: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
对于庄子,鲁迅主要批判了他的“欲并有无修短白黑而一之”的相对主义。鲁迅认为,庄子这种思想与儒家的“中庸”原则对国民性格的负面影响尤为恶劣,使人们在大是大非面前丧失原则,在思想和信仰上缺乏“坚信”,对思想、主义一概从实利主义原则来决定取舍,没有追求真理热爱真理的执着精神。鲁迅断言,中国国民性格中的“无特操”和“无坚信”的通病,便是相对主义是非观带来的恶果:“要做事的时候可以援引孔丘墨翟,不做事的时候另外有老聃,要被杀的时候我是关龙逢,要杀人的时候他是少正卯,有些力气的时候看看达尔文赫胥黎的书,要人帮忙就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注:鲁迅《华盖集·有趣的消息》。)总之,不管什么信仰、原则,只要对自己有利就行。
老庄思想还推动和强化了历史上早已存在的“隐逸”之风,并为之提供了理论依据。鲁迅对“隐逸”这种历史久远的文化现象和人生哲学进行了批判,认为这是一种逃避现实、回避斗争、缺乏社会责任感、自私的人生态度。他指出:“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但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的一伙的,则虽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聪目明,奋袂而起,好象事件之大,远胜于宇宙之灭亡。”(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吃教》。)
(二)对道教的神仙信仰的批判:
不死成仙的信仰是道教的核心内容。道教为了扩大自身的影响,极力夸大和渲染神仙境界的快乐与享受。葛洪的《抱朴子·对俗》篇说:“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变化飞行,失人之本,更受异形,……老而不衰,延年久视,出处任意,寒温风湿不能伤,鬼神众精不能犯,五兵百毒不能中,忧喜毁誉不为累,乃为贵耳。”(注: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52-53、52、129页,中华书局1996年。)《对俗》篇又说:“果能登虚蹑景,云舆霓盖,餐朝霞之沆瀣,吸玄黄之醇精,饮则玉醴金浆,食则翠芝朱英,居则瑶堂瑰室,行则逍遥太清。”(注: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52-53、52、129页,中华书局1996年。)道教所宣扬的这种快乐和幸福,实际上是对封建帝王和官僚贵族的特殊地位和享乐生活的进一步夸大和想象。“追求肉体长生或飞升,无非是奢望官僚名士的享乐生活得以无限延长”(注:陈兵《道教之道》第20页,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的确,封建统治者除了政治权力之外,唯一需要的几乎就是肉体生命的本身,是“健康长寿”和“万寿无疆”,只要他活着,就能永久地拥有人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但肉体生命的有限性终究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自然律,诚如鲁迅所说,封建统治者“欲望没有衰,身体却疲惫了;而且觉得暗中有一个黑影——死——到了身边了,于是无奈,只好求神仙。这在中国,也要算最高理想了”(注:鲁迅《热风·随感录五十九“圣武”》。)。
鲁迅认为,长生不死的神仙信仰,对中国人特别是处于社会上层的统治者,有着极大的消极影响。这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以长生不死为最高理想,一味耽于物质利欲的享乐,使得“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而且许多论者反要以此自豪”(注:鲁迅《热风·随感录五十九“圣武”》。)。神仙信仰的另一个消极影响,便是一种极度自私的个人主义人生观支配了“大小丈夫”们的头脑,在他们的思想里,只有一个“我”,“单要由我喝尽了一切空间时间的酒”(注:鲁迅《热风·随感录五十九“圣武”》。)。这种人所希望的,只是“大约别的都可以老,只有自己不肯老”;“不必再有后进”,好由他们自己“占尽了少年的道路,吸尽了少年的空气”(注: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九》。)。汉武帝所向往的“嗟呼!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躧耳”(注:《史记·封禅书》,中华书局1997年缩印本。)的感叹,就是这种极端自私自利思想的最形象的注脚。
(三)对道教方术和封建迷信的批判:
道教中素有“道无术不行”和“道寓于术”之说,道教正是凭借各种方术来制造和扩大它的社会影响的。在长期的宗教实践中,道教发明和运用了上千种方术,而两千多年来中国民间流行的各种封建迷信活动,差不多都与道教的方术有关。鲁迅以科学为武器,对道教方术的愚昧落后的封建迷信本质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服饵,在道教中指服食仙药特别是金丹大药以求长生的方术。历代的帝王、官僚贵族及文人士大夫中都有不少人,不惜冒着中毒身亡的危险热衷于服食丹药,根本原因在于鲁迅所说的,总是把“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当作是“最高理想”(注:鲁迅《热风·随感录五十九“圣武”》。),幻想永保其威福、子女、玉帛及其它种种享乐。
房中,属道教中所谓“采阴补阳”、“还精补脑”的一种修炼方术。鲁迅认为房中术是一种极端恶劣的纵欲成仙的思想,他指出:“无论古今,谁都知道,一个男人有许多女人,一味纵欲,后来是不但天天喝三鞭酒也无效,简直非‘寿(?)终正寝’不可的。”(注:鲁迅《准风月谈·中国的奇想》。)房中术不仅有害于健康和生命,而且是对女性的一种极不道德的性掠夺。
道教的服饵、房中等“养生术”表明了道教既没有佛教、基督教那种摈弃世俗欲望的苦修精神,也缺乏一个绝对超越了尘世苦乐的彼岸世界,它是从生理上和心理上全面迎合了人们享乐的需要。如果说服饵、房中等方术需要一定的财力作基础,主要流行于社会的上层,那么道教中与鬼神崇拜和巫术相关联的符箓、扶乩、祈雨、施咒、招魂、堪舆、谶语等方术和封建迷信活动,则流布在整个社会上下,它们实际上代表了古代民间文化中愚昧、庸俗和落后方面的汇集。在鲁迅看来,由于道教的各种迷信和巫术活动充斥了整个社会,使得人们不修人事,群趋鬼道,不相信科学的力量,整个社会弥漫着“鬼气”和“妖气”。鲁迅对这些至今还颇有市场的迷信活动进行了猛烈抨击,现择要分述如下:
符箓是道士专用的一种文字或图形。道士宣称符箓乃妙气所结,故具有神力,可以遣神役鬼、镇魔压邪、治病求福。鲁迅揭露其实质说:“符的驱邪治病,那就靠了它的神秘性的。文字既然含有尊严性,那么,知道文字,这人也就连带的尊严起来了”;“如果文字易识,大家都会,文字就不尊严,他也就不尊严了”(注: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符箓不过是道士为了蒙骗民众,故作神秘的东西,故鲁迅称其为“一团糟”的“鬼画符”(注:鲁迅《华盖集·论辩的魂灵》。)。
在《热风·五十三》、《花边文学·偶感》等文中,鲁迅批判了扶乩这种迷信在现代的死灰复燃。针对当时一些人鼓吹的风水合于地理学,炼丹合于化学,“灵乩”合于科学的谬论,鲁迅倍感痛心:“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此弊不去,中国是无可救药的。”(注:鲁迅《花边文学·偶感》。)
祈雨,也是道教中极为普遍的一种迷信活动。每当有水旱灾害发生,农民总会请道士来祈雨祷晴。鲁迅认为这是一种愚昧无知的观念和典型的迷信行为,他深感悲哀的是:“自从由帝国成为民国以来,上层的改变是不少了,无教育的农民,却还未得到一点什么新的有益的东西,依然是旧日的迷信,旧日的讹传,在拚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注:鲁迅《花边文学·迎神与咬人》。)
禳解,是道士通过向神灵祈祷而为人求福消灾的一种方术。中国人一方面相信运命,另一方面又相信这运命是有办法转移的,而禳解、符咒、拜祷就是转移运命的主要手段。鲁迅认为,信运命的中国人而又相信运命可以转移,是值得乐观的,“不过现在为止,是在用迷信来转移别的迷信,所以归根结蒂,并无不同,以后倘能用正当的道理和实行科学来替换了这迷信,那么,定命论的思想,也就和中国人离开了”(注:鲁迅《且介亭杂文·运命》。)。
道教中的咒语,在迷信的人们看来是有法力的。义和团运动兴起时,人们迷信所谓“神拳”,相信念咒可以“神降附体,刀枪不入”。针对这种迷信的幼稚的做法,鲁迅指出:“打拳打下去,总可以达到‘枪炮打不进’的程度(即内功?)。这件事从前已经试过一次,在一千九百年。可惜那一回真是名誉的完全失败了。”(注: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七》。)鲁迅认为仅靠“鬼道”精神是救不了国的,顶多只能作无谓的牺牲,唯有科学的力量才能救国。他说:“在五六年前,我对于中国人之发‘打拳热’,确曾反对过,那是因为恐怕大家忘却了枪炮,以为拳脚可以救国,而后来终于吃了亏。”(注: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这回是第三次〉按语》。)
鲁迅还对道教的其它方术进行了批判。在他看来,中国的愚昧和落后,在很大程度上与道教方术和各种封建迷信的盛行有关,它们都是科学的死对头。“要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那种‘孔圣人张天师传言由山东来’的方法,是全不对症的,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的科学!——不是皮毛的真正的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注: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三》。)
总之,从鲁迅对道教所作的多方面的剖析和批判中可以看出,道教在历史和现实中对国民精神和民族性格所起的负作用是非常大的,民族劣根性的诸多特征都与道教的长期影响有关。
三、准确理解“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鲁迅对道教的评价是很低的。“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论断,主要是就道教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负面影响而言的。在鲁迅眼中,道教实际上是国民性中“兽性方面的欲望”的集中体现,也是种种愚昧无知的封建迷信的集中体现。换言之,道教是民族劣根性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的这一著名论断,仅从字面理解,似乎是说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或道教文化代表和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全部,然而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知道鲁迅的原意并非如此。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论断作进一步分析,以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鲁迅的道教文化观。
首先,鲁迅先生是作为文学家的思想家,他认为最善于改变国民精神的,当首推文学,因此他弃医从文,终身致力于以文学为手段进行文化剖析与社会批判,以唤醒民众重振民族精神。这就决定了鲁迅主要是以文学家的直接感悟和无休止的批判来辐射他的思想能量,而不象哲学家那样在逻辑系统的思考中来论证他的思想凝结;加之他本人没有对道教的历史做过系统的研究,他对道教的认识和评价,也只是从某个特定的角度出发的,确有不够全面的地方。因此,“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论断,有些偏颇,而从他对道教给中国人的精神与心理所造成的种种影响的分析和解剖来看,无疑是十分深刻的,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其次,“改革国民性”是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奉献给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的思想财富,也是理解鲁迅复杂精神世界的一把主要的“钥匙”。因此,通过剖析和批判包括道教在内的传统文化,改革国民性的恶劣方面一直是他主要的着力点,这并非意味着他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文化和“国民性”中也有良性的一面。鲁迅在1936年3月4日致尤炳圻的信中就谈到,中国的国民性“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注:鲁迅360304致尤炳圻,见林非主编《鲁迅著作全编》卷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因而,鲁迅对道教文化的认识和评价,主要是批判而不是赞扬,这完全是为了服从和服务于“改革国民性”这个最要紧的事业的。所以,我们必须从鲁迅的“改革国民性”这个一以贯之的思想取向出发来理解他的道教文化观。
再次,鲁迅说过,“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进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注:鲁迅《华盖集·〈突然想到〉》。)这表明了鲁迅对待传统文化遗产的态度,“他的着眼点显然不在于各种文化派别的‘原教旨’,而在于它们对后世的影响。也就是说,鲁迅是从现实情况出发来评价传统文化,并决定对它的取舍的”(注:吴中杰编著《吴中杰评点鲁迅杂文?〈序论:重新解读鲁迅〉》(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而道教自明代中叶以后就逐渐走向了衰落,在鸦片战争后至民国间的一百多年中,更是江河日下,“近现代中国道教逐渐失去固有的本色。一些宫观殿堂变成了赚钱的场所,为信徒做功德也成了一些道士糊口谋生的手段,做道士成为一种职业”。(注:卿希泰《简明中国道教通史》第18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甚至玄门清静之地也经常出现政治权利、经济利益和教内派系的斗争,道教用以影响社会生活的主要是它的封建性和保守性的方面,它已从整体上失去了探索宇宙人生的热情与动力。不可否认,鲁迅所观察和认识到的道教,实际上恰好是道教史上最衰微、最缺乏活力与创新的道教,它与当时进步的思想家们所倡导的科学精神、理性精神是格格不入的,与时代精神的发展背道而驰,已成了阻碍中国社会前进和发展的障碍。出于对道教文化的这种社会影响的认识和对它的愤激之情,所以鲁迅先生采用了这种比较激进的表达方式:“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标签:鲁迅论文; 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道教文化论文; 迷信活动论文; 道教论文; 读书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科学论文; 道士论文; 国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