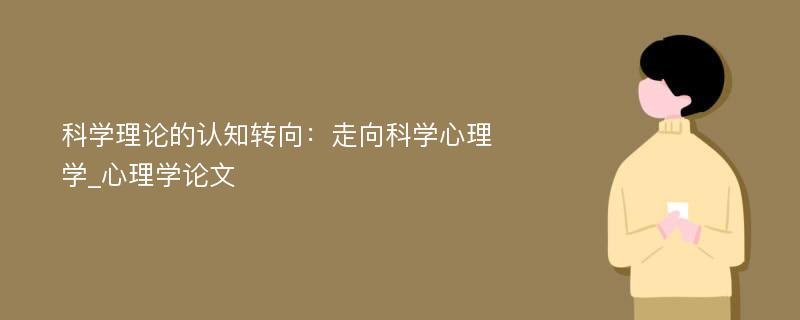
科学论的认知转向:走向科学心理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论文,认知论文,心理学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2;B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71(2014)06-0021-08 科学论(science studies)汇集了各种理解科学的努力,包括哲学的、历史的、社会的、人类学的、心理学的,甚至是政治学的。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多么有包容力的大舞台。迄今为止,除了认知科学外,还没有一个研究领域能够吸引这么多的学科。认知科学由于所研究问题的复杂性而召集了人工智能、心理学、语言学、神经科学、哲学和人类学的共同参与——它们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人类理解力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即理解心智与智能。这是学科汇聚的典范。但科学论不是,不同的学科并未真正地汇聚起来,而是在不同的时期轮番占据着主导地位,就像是在一个舞台上上演一部连续剧。剧情大概是这样的:哲学家在20世纪初拉开了序幕,接着,历史学派在60年代粉墨登场,稍后,70年代社会学和人类学便迅速占领了舞台。但好景不长,到了90年代中期,社会研究便开始出现明显的衰落①。这当然与审美疲劳有关。当人们逐渐习惯了各式各样的激进观点后,哗众取宠的做法自然也就没那么灵验了。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随着社会研究的过度扩张,它的局限性也渐渐暴露出来。②于是人们便开始寻找另外的出路。在这种背景下,科学心理学(psychology of science)慢慢发展壮大起来。以2006年“科学技术心理学国际协会”(ISPST)的成立与2008年《科学技术心理学期刊》的发刊为标志,“一门新的科学论诞生了”[1]1。看来,科学论新一轮的学科更迭又要开始了。 本文有两个主要目的:第一,说明科学论当初在六七十年代发生的社会学转向是不恰当的,因为那些支持社会研究的理由其实更支持心理研究;第二,指出科学论现阶段应加强科学的心理学研究。此外,本文还会说明,科学论走向科学心理学不会引发元哲学危机。 一、科学论的社会学转向 拉卡托斯(Imre Lakatos)曾说:“尊重科学是人类最为独特的一个特征。[2]1早期的科学哲学家正是出于尊重才去研究科学的。他们为科学所取得的智力上的突破与实际应用中的成功所折服,于是想一窥堂奥,看看科学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初步的答案很快就被给出:科学的成功就在于它准确地反映了外部世界,而科学之所以能够准确地反映世界,是因为科学家按严格的程序去观察自然,并按严格的逻辑从观察数据得出科学理论。根据逻辑实证主义所给出的更为精细的版本,科学是通过将一套数学的或逻辑的符号系统施加于观察数据之上的方式产生理论命题的智力活动。完成这项活动需要做两件不同的事:首先是以收集证据为目标的观察以及由之引发的科学假设与理论的建构,这件事被认为发生在发现的情境(the context of discovery);其次是理论的检验与证实,它们被归于辩护的情境(the context of justification)。第二件事为哲学家留出了一份工作,即发现和完善科学符号系统的一般性句法规则。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将之称为“理性重构”[3]31。 然而,上述方案招徕了众多批评。例如,以蒯因(W.V.Quine)和汉森(Norwood Hanson)为代表的意义整体论者论证了,观察并不是独立于理论的,而是和理论相互渗透在一起作为整体面对实在。这意味着,观察与理论的两分法是不成立的。历史主义者则争论说,科学其实并不服从逻辑。当反常出现时,科学家的做法通常是将它解释掉或视而不见。这表明,传统方案描绘的并不是科学的真实形象。真实形象应该到科学活动中去找,到描述研究活动本身的历史记载中去找。这是库恩(Thomas Kuhn)的建议[4]1-9。他说:“要分析科学知识的发展就必须考虑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5]4“我们都关心获得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关心科学成品的逻辑结构。”[5]4 库恩的建议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些人认为,库恩的建议实际上将我们引向了科学的社会研究。按照库恩,科学是科学家的实际活动,而科学家的实际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进行的。这些条件可以是社会的、政治的以及心理的。它们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科学活动得以发生的小环境。库恩称之为范式。范式一旦形成,就会对隶属于它的共同体成员施加规范。因此,通过考察范式,考察那些科学活动得以发生的具体条件,科学活动本身就得到了阐明。那些主张社会研究的人争论说,像范式这样的小环境只是社会大环境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应该把范式扩大到整个社会,以容纳利益、权力与权威等社会因素以及阶级、传统、文化等社会结构。在他们看来,科学是彻头彻尾的社会活动,它完全可以用社会因素来解释而无需引入真理、合理性以及实在等哲学概念。 然而,假如社会研究的主张是对的,那么,它们自身也应该可以社会地解释。当时的社会情况似乎印证了这一点。二战后,以贝尔纳(John Bernal)为代表的主张对科学进行社会控制的思想在英国就一直很盛行。这种思想与六、七十年代在欧洲出现的一系列批判科学的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引发了公众对科学的可说明性的要求。作为对公众要求的响应,英国政府在1964年工党上台后推行了一系列治理科学的措施,其中一项就是成立科学论小组(Science Studies Units)。这一举动直接导致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诞生。几乎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掀起了一场影响广泛的认知科学运动。这场运动从人工智能开始,接着是心理学,然后是语言学和哲学。在50年代到70年代的短短二十年间,它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了心智与智能。很快,一门新的学科——认知科学——就诞生了③。奇怪的是,当时的科学论却无视这场革命,兀自走了社会研究的道路。在那些醉心于社会研究的人看来,认知科学即使不是无关的,也是无足轻重的。一些人更是表现出了“深入骨髓的厌恶”[6]201,他们甚至提议,应该“将科学的认知解释推迟十年”[7]280。是什么促使他们产生这样态度?难道仅仅是社会原因吗?不。他们的蛮横态度更多地来自他们对自己的论辩的过分自信。 二、社会转向的问题 据认为可以支持社会转向的理由有很多。不过,那些主要的理由却万变不离其宗,可以概括为自然主义(naturalism)。当然,这里所说的自然主义是认识论的。认识论的自然主义指这样一种观点,所有现象都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本体论的自然主义则认为,所有现象都是自然现象[8]4-10。社会研究不是本体论的自然主义,因为它认为科学是社会建构的,是非自然的。很显然,要想从方法论的自然主义推进到科学的社会研究,就要做两件事:第一,说明科学自身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第二,说明那种方法就是社会科学的方法。社会研究的提倡者的确想做这两件事,他们想证明:(一)辩护的情境与发现情境的两分法是不成立的,认识论不是先验(apriori)事业,科学知识的内容一样可以用经验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称此主张为“DJ论点”)[9,10,11];(二)对科学知识的研究就是给出一种社会学的解释(称此主张为“SE论点”)[7,10,12,13]。在做这两件事时,他们主要用到了维特根斯坦和库恩的思想。 据说,维特根斯坦和库恩的思想蕴含了DJ论点和SE论点。先看DJ论点。DJ论点的否命题对传统科学哲学的重要性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只有承诺了一个免于经验污染的领域,纯逻辑的理性重构才有可能,纯哲学的科学认识论才有可能。库恩的贡献就在于,他通过历史分析无可辩驳地表明,科学论是个经验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不存在完全不服从经验管辖的独立王国。 维特根斯坦也被认为是DJ论点的创始者。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告诉我们:“语词的意义在于它的用法。”[14]561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无法像卡尔纳普所设想的那样,为语言设计出一套规范其用法的逻辑,恰如为火车铺设一条让它行驶的轨道一样。比起那些被设计出来用以规范语言的规则来说,用法具有优先性。规则只不过是在语言游戏的过程中产生的,并且在重新应用时总有可能改变。这意味着,在过去的实践与它们在新事例的拓展之间有个逻辑规则所不能填平的间隙。因此,撇开用法所在的发现的情境去辩护的情境谈论语言的逻辑是没有意义的。 我承认,维特根斯坦和库恩为DJ论点提供了充分论证。甚至可以说,他们为科学论的自然化铺平了道路。然而,社会研究的提倡者们却别有用心地夸大了维特根斯坦和库恩对社会研究的认可。按照他们的论证逻辑,似乎维特根斯坦和库恩认可了DJ论点也就认可了EP论点。在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中,巴恩斯(Barry Barnes)争论说,库恩已经告诉我们:“社会学的解释范围完全可以延伸到自然科学的整个辩护的情境。”[12]391布鲁尔(David Bloor)则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发展出了所谓的“有限论”[9]159-165。根据维特根斯坦,理性的规则不能解释科学家为何相信他们所相信的,所以,需要别的解释来说明他们为何终止他们的争论。有限论认为,这个解释是彻头彻尾社会学的,因为是不同类型的社会联系填补了过去的实践与它们在新事例的拓展之间的鸿沟。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审查维特根斯坦和库恩本人的思想,就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他们似乎更倾向于心理学的自然主义。维特根斯坦认为,心理现象与人类行为和外表的偶性特征有概念联系。“疼痛在我们的生活中具有这种地位,具有这些联系。”[15]533另一个例子是“希望”:“‘希望’一词指称的是人类生活的一种现象。(微笑的嘴只有在人脸上才是微笑的。)”[14]583哲学的一个任务就是考察这些心理学概念是如何使用的。维特根斯坦的考察表明,“似乎存在着与语言活动相联系的某些特定的心理过程,只是通过这些过程语言才能起作用。我指的是理解和意指的过程。没有这些心理过程,我们的语言符号似乎是死的;而且,似乎我们的语言符号的唯一功用就在于诱发这样的过程,它们才是我们真正感兴趣的东西。……语言活动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是无机的部分,即对诸符号的操作;另一个是有机的部分,我们可以称之为对符号的理解、意指、解释和思考。这一类活动似乎是在心灵这种奇特的介质中进行的。而心理机制——对它的本性我们似乎并不完全理解——能产生任何物理机制都不能产生的效用”[16]3。有人认为,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心理机制指的是意向性(intentionality)[17]。不管它是什么,有两点可以肯定是维特根斯坦所想表达的:第一,要理解语言和知识,就要理解那些使得它们成为可能的心理机制;第二,心理机制的本性不能完全通过语言分析的方式获得理解。这两点合起来正好就是心理学的自然主义。 相比于维特根斯坦,库恩的心理学倾向就更为明显。在库恩的理论中,没有什么比如下两个问题更为重要了:范式是如何形成的?范式转换是如何发生的?在说明这两个问题时,库恩都用到了心理学。根据库恩的描述,范式的形成过程是新手通过身体规训和心智训练进入共同体的过程。库恩后来以实指教学为例进行了说明。一个小孩在学习使用“鸭子”、“鹅”和“天鹅”这些概念。一个大人指着某只水鸟对小孩说“鸭子”。开始,小孩经常会把鹅当作鸭子或把天鹅当成鹅。经过大人的不断纠正,小孩最终知道了如何区分三种水鸟之间的相似特征与不同特征,从而掌握了“鸭子”、“鹅”和“天鹅”等概念[18]476。据说,库恩这样的描述蕴含了心理学中的概念原型理论[19]19-30。库恩对范式转换的描述也是心理学的。根据库恩,反常的发现包含了概念同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概念范畴被调整。在某个阶段,范畴的调整突然引发格式塔转换,于是新的范式被开启,最初的反常现象随之也就变为预期现象。库恩自己也承认:“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即范式转换,笔者注)要求有心理学家的本领更甚于历史学家的本领。”[4]8当然,库恩也提到了社会学。他说:“最终的分析所得出的解释必然是心理学或社会学的。”[4]21但无论如何,库恩都没有传达走向纯粹的社会研究的信息。更合理的解读似乎是,科学论应该走向社会心理学。然而,社会研究的提倡者却以维特根斯坦和库恩的思想为桥梁直奔社会研究。 尽管提倡者们就社会转向达成了一致,但对应该给出什么样的社会解释却莫衷一是。早期的提倡者,例如布鲁尔和巴恩斯,认为解释应该是因果的,同时还要遵守公正性、对称性和反身性原则。他们将这四个原则合称为“强纲领”[13]7。在强纲领的信奉者看来,科学产品只不过是由人类构想出来说明他们的生活世界的建构物或“宇宙论”。科学论的任务就是描述和解读这些建构物,阐明能解释它们的文化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条件。然而,人们很快就发现,用宏观社会学去解释科学的微观内容的努力充满了困难,只有那些像世界观和文化等宽泛的特征得到了较好说明。这是不难理解的。强纲领的解释模型很像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只不过它将行为刺激换成了社会条件。自然而然地,它就会遇到与行为主义相似的问题:在作为输入的社会条件与作为输出的科学知识之间有太多的变数,它们中间似乎还有一个未打开的黑箱。 意识到因果分析的问题,一部分人转向了人类学。人类学进路更加关注知识在实验室中的制造过程。其后的科学的文化研究更是将重点收敛到某个事件的动力学,它试图通过对科学研究的地方性条件的揭示,揭示出科学知识是如何通过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产生出来并引起人们注意的。新进路赋予了科学论新任务,即通过描述的方式揭示科学知识生产的社会机制。它为我们带来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自然主义。这种自然主义不是诉诸因果关系及其所例示的规律,而是通过揭示某个现象的生成机制来解释那个现象的产生。这种思想可追溯到笛卡尔。笛卡尔的以太漩涡学说是典型的机制解释,它与牛顿的规律解释明显不同:前者针对的是“how”问题,而后者则试图回答“why”问题。正是在笛卡尔式的自然主义的意义上,一些稀奇古怪的科学论,例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与社会认识论都被认为是自然主义的——它们都声称自己揭示了更为可靠的知识生产的社会机制。 我常常对所谓的社会科学自然主义(即将科学方法理解为社会科学方法的自然主义)感到不安。显然,社会科学自然主义如果成立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结论:自然科学最终得靠社会科学来解释。这个结论着实让人不安,它完全颠覆了自然科学的形象。通常我们认为,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是最可信赖的知识体系,是我们智力成果的典范。社会科学是以自然科学为榜样建立起来的,它并不享有自然科学那样的尊荣。直到现在,它的科学性都受到质疑,有关它的方法论问题的争论依然没有平息的迹象:社会科学有属于自己的方法吗?它可以产生知识吗?如果可以的话,又是如何产生的呢④?这些问题的悬而未决损害了社会科学的形象。尽管如此,社会研究的提倡者们却言之凿凿地说,应该用社会科学去解释自然科学。这着实有点匪夷所思。 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科学自然主义忽视了科学的一个固有维度,即心理的维度。正是这一点导致社会研究不能解释科学认知的特殊性——它们认为科学与其他人类活动之间没有任何差别。然而,谁都无法否认,科学需要极高的智力支持。你可以说科学是项社会活动或别的什么,但它首先是项复杂的认知活动。这项活动开始于科学家从自己的感觉接受器接受体表刺激,终止于理论输出。正是那些在这之中发生的心理过程才使得科学成为可能,没有它们也就没有科学。传统科学哲学认为,尽管科学的产生依赖于心理活动过程,但科学知识的内容却有其独立生命。可是,假如DJ论点是对的话,那么内容与过程的二分法同样也是不能成立的。这意味着,研究科学恰恰就要研究那些使得科学成为可能的心理过程,用蒯因的话来说,就是要研究“贫乏的输入和汹涌的输出之间的关系”[20]82。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弄清楚证据是如何与理论相关联的,并且人们的自然理论是以何种方式超越现成证据的”[20]82。因此,科学论与认识论一样,是“心理学的一章”,因而也是“自然科学的一章”[20]82。社会科学自然主义虽然也反对内容与过程的二元论,但它们想当然地认为,可以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揭示科学活动所发生的社会过程或机制而无需提及个体科学家的心理活动过程。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下面我将给出一个论证。 我的论证开始于这样一个显明的事实:人是有精神生活的。人感知、相信、欲求、思考、知道。这些精神状态会影响我们的思想与行动。例如,我知道火车马上就要开了,可我离火车站还有一段距离,于是我开始奔跑。倘若此时你问我:“你为什么要跑?”我会给出我行动的原因,即我要赶火车。在这种情况下,我将赶火车作为理由来解释我的行动。所以戴维森(Donald Davidson)说的是对的:行动者的理由可以引发他的行动,并且,至少有时最好的解释应该根据行动者的理由给出[21]3-20。这意味着,任何一项涉及人类思想与行动的解释事业,包括科学论,都应该给予心理因果关系恰当的位置。哪怕在最后的解释方案中,心理因果关系可以被还原到更为基本的关系,例如物理机制,我们也不能不提它,否则就会留下解释的鸿沟。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能够依理由行事,这一点仍然没有得到解释。所以,作为被解释项,心理因果关系必须被保留在整体方案中。然而,仔细地考察表明,社会研究并不容许心理因果解释。社会研究要求解释具有对称性,即同一类型的解释既可以说明真信念,也可以说明假信念⑤。对称性要求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假如真信念的解释需要另一种类型的解释,例如逻辑说明,那么,两种情境的区分就被重新引入,从而社会学的解释也就被排除在科学知识的内容之外。但对称性在拓展了社会学解释的同时,却使得理由解释变得不可能起来。设想一个人S基于主张p而相信主张q,那么,在他相信p的情况下,他是不会有意识地相信非q的。在这个事件中,社会学解释甚至无法承认S的主张p是他相信主张q的理由,因为承认了这一点就意味着它将信念非q排除在外,从而就不再是对称的。可是,如果放弃了对称性,社会学解释就会失去完备性。也就是说,科学论还需其他的解释。基于心理因果解释的不可排除性,我们又被引向心理学。 至此,我说明了社会转向的问题。首先,被援引来支持社会转向的维特根斯坦和库恩的思想其实更支持科学的心理学研究。其次,认为可以用社会科学来解释自然科学的想法是站不住脚的。最后,一个健全的科学论应该而且必须容许心理因果解释,但社会研究不可以。这些问题提醒我们,该为科学论另谋出路了。 三、走向科学心理学 科学论应该转向科学心理学。科学是生产知识的认知活动,它涉及了一系列复杂的认知过程,包括抽象和符号思维、推理和逻辑、模式识别、假设检验、数学分析、直觉猜测、融贯的和有效的语言表达。在这些过程中,心理学原理一直在发挥作用。这决定了,对科学思维和行为的完整理解需要心理学的视角。西蒙顿(Dean Simonton)说得好:“不加进心理学的维度,我相信,是不可能完全理解科学想象的本质的。而没有这样的理解,科学的起源,关于自然现象的新想法的出现,都不会得到理解。”[22]200 科学心理学主张用认知科学尤其是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科学思想、科学行为以及科学成就。其中,科学既可以是狭义的,也可以是广义的。狭义的,科学指职业科学家与技术专家的思想与行为;广义的,它指任何参与理论建构、问题发现与解决的人的思想与行为。“只要我们是在检验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观念,我们就在做科学。”[23]27广义理解的根据就在于,大量的证据表明,科学认知者的认知过程和普通人并无本质不同。或者说,科学心理学与民众心理学是连续的[24]73-95。连续观为科学心理学开辟了广阔的空间,让它能够面对一系列范围广泛的问题。例如,科学家真是那些到了成年时期仍然完好无损地保留着孩提时的认知特性的少数人吗?对于这类问题,科学心理学力图用心理历史、心理传记、观察、描述、系统实验等方法进行研究。这样的研究是经验的,它们的目标是,通过揭示认知得以发生的心理机制,来理解科学家是如何从事科学活动的,以及作为科学活动的结果的科学知识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 机敏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科学心理学的主张其实并不新颖。的确如此。用心理机制来解释人类知识与行为的想法甚至可以远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想想柏拉图的三等份灵魂学说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主义灵魂学说)。其后,笛卡尔、洛克、休谟和康德提出了许多有关心灵如何运作的有趣猜想。不过,虽然科学心理学有着久远的过去,但却只有简短的历史。“科学心理学”一词最早是由史蒂文斯(S.S.Stevens)在20世纪30年代创造的,用以表达这样一种思想,对科学的研究仍然要以科学的方式进行⑥。然而其后科学心理学却进入沉寂期。直到五六十年代才重新出现一些研究。那个时候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科学家的人格特征与创造性。到了8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将科学心理学作为与社会研究相竞争的一门科学论来提倡。1989年,孟菲斯小组出版了《科学心理学:原科学论文集》,他们试图为科学心理学制订一个路线图,以促进它的发展[25]。(Gholson,et al.1989)但事与愿违,科学心理学在90年代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⑦。直到最近,科学心理学才被认真对待。随着“科学技术心理学国际协会”的建立与《科学技术心理学期刊》的发刊,科学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总算得到确认。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科学论虽然错过了与认知科学携手共进的大好时机,不过,如果现在能在科学心理学上下足功夫,也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正如平克(Steven Pinker)所注意到的,尽管认知科学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例如对视觉、语言、记忆等心灵的诸多方面有了深入理解,但有两个现象至今仍然难以解释:其中一个是意识,另一个就是科学[26]3-60。人类何以能够进行科学思维与科学推理?至今,我们仍然对此所知甚少。可是,要理解科学,要想建立关于科学知识的认识论,就不得不去了解心灵的实际运作过程。“对心灵的实际运作一无所知的认识论是误导人的、无用的。”[27]12在自然主义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我们突然发现,科学认识论的重担已经落到了科学心理学上。 科学心理学要能肩负起科学论的重托,就需要有足够多的学科资源。目前来看,科学心理学能动用的学科资源包括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生物心理学和人格心理学。认知心理学主要集中于“柏拉图—皮亚杰问题”:“新概念是如何从大脑中已有的那些概念中产生出来?或者说,一个系统是如何产生远远超出它所包含的陈述的结果的?这是个创造性问题。”[28]227-228比如,理论是怎样形成的?概念转变是如何发生的?科学推理或科学家解问题的实际过程是怎样的?发展心理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科学思想与行为随个体年龄的增长的变化。比如,一个完全无助的婴儿是如何成为一个会仔细观察与复杂计算的科学家?成为科学家的必要才能与技能是什么?它们又是如何随年龄的增长而变化的?生物心理学想弄清楚科学思想与行为多大程度上受我们的生物能力的限制。例如,我们的大脑有哪些结构是“硬连接”的?又有多大的可塑性?人格心理学关心这样的问题:科学家与非科学、杰出科学家与一般科学家的人格有何差异?人格是如何影响科学行为的?等等。 鉴于科学认知现象的复杂性,科学心理学还应该与其他学科联合起来,形成面向问题的跨学科研究范式。科学心理学并不否认科学有多个维度,只不过它认为,科学首先是项认知活动,所以,应该将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分析与心理学结合起来。令人欣喜的是,有些研究者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这么做了。例如,纳塞西安(Nancy Nersessian)提出了科学论的“认知历史”进路,通过考察科学家的日记、实验室记录、出版物以及通讯等方式再现当时的认知过程[29]194-211。福勒(Steve Fuller)等人提出,科学论应加强科学社会心理学的研究[30]。邓巴(Kevin Dunbar)用人类学的方法考察了科学家实际上是如何解问题的[31]365-396。值得一提的还有哈钦斯(Edwin Hutchins)的分布式认知与巴斯(David Buss)的文化心理学⑧。这些交叉领域往往是新增点容易出现的地方,应该加强研究。这样,当科学心理学走向科学论的中心舞台时将不再是一次学科更迭,而是学科汇聚格局的真正形成。 说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哲学呢?哲学在科学论走向科学心理学后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个问题是自然主义所引发的“元哲学危机”的一部分。所谓的元哲学危机是这样一种担忧:如果哲学变成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然则哲学何以成为哲学?对于这个问题,我想从两个方面进行回答。第一,哲学虽然失去了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它所特有的先验方法,但它仍然可以以它对实在一般特征的特别关注,对人类精神生活的执着追求,而在知识体系中占一席之地。第二,哲学家既可以像以往一样提出大胆的猜测,也可以和科学家进行合作研究,甚至还可以像实验哲学家所倡导的一样亲自做实验来验证哲学假设。福多(Jerry Fodor)堪称第一类哲学家的代表。他的思想语言学说与心理模块论深刻地影响了认知科学。哈克(P.M.S.Hacker)则是第二类哲学家的典范。他与神经生理学家贝内特(M.R.Bennett)合作,出版了《神经科学的哲学基础》一书,受到广泛关注。可以说,很多当代哲学家事实上已经适应了哲学的自然主义转向。所谓的元哲学危机更多地是观念上的:部分人仍然认为哲学不受经验证据的约束。事实上,所有的哲学观点都应该接受科学的审查。 黑格尔认为,历史是逻辑的展开。然而,这一点对科学论似乎并不适用。科学论的发展并没有遵循逻辑。虽然它与认知科学有着相同的旨趣(理解思维与智能),但却无视同样在六、七十年代发生的认知科学革命而转向社会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件憾事。如果历史能重来,不知科学论会不会选择科学心理学。据说,在曼哈顿工程时期,心理学家希尔加德(Ernest Hilgard)受邀请去研究“众多科学家合作解决问题这一十分有趣的实例”。可惜的是,希尔加德拒绝了邀请。有人说,如果当时希尔加德接受了邀请,也许科学论的历史就会大不相同:它将集中于集体解难题这样的社会心理学问题,而不是科学实在的社会建构[32]。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科学论现在应该走向科学心理学。 ①文中社会研究泛指科学知识社会学之后所有主张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科学的理论进路,包括实验室研究、科学的文化研究、女性主义认识论、后殖民主义科学论等等。 ②吉尔(Ronald Giere)认为,社会学解释缺失了某些重要的东西,这个东西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合理性,而是科学家与世界之间的因果互动关系,参见Giere R.Explaining Science[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还有人指出,社会研究所倚重的案例研究也是有问题的。它们揭示的往往是理论的接受而不是理论的产生,它们涉及的仅仅是理论的早期阶段,而忽视了理论所产生的后果,参见Collin F.Science Studies as Naturalized Philosophy.Dordrecht:Springer,2010.有关社会学解释的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可见Zammito J.A Nice Derangement of Epistemes:Post-positivism in the Study of Science from Quine to Latou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 ③一般认为认知科学是在七十年代正式诞生的。“认知科学”一词最早在1971年开始使用。1975年,“斯隆基金会”决定资助认知科学研究,并组织召开了第一次认知科学会议。1977年,《认知科学》期刊正式出版。1979年认知科学召开了第一次正式的年会。 ④有关社会科学方法的讨论可参见Flyvbjerg B.Making Social Science Matt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⑤无论是早期的社会学进路还是后来的人类学进路,甚至是科学的文化研究,都是承认对称性的,分别参见Bloor D.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6; Jasanoff S.States of Knowledge.London:Routledge,2004。 ⑥参见Stevens S."Psychology:The Propaedeutic Science",Philosophy of Science.1936(3):90-104以及Stevens S."Psychology and the Science of Science",Psychological Bulletin.1939(36):221-263.据考证,高尔顿(Francis Galton)是第一个探讨科学心理学问题的人,参见Galton F.English Men of Science.London:Macmillan,1874。 ⑦有关科学心理学的发展史与研究现状可参见Feist G.The Psychology of Scienc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cientific Min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 ⑧分别参见Hutchins E.Cognition in the Wild.Cambridge:MIT Press,1995以及Buss D.Evolutionary Psychology:the New Science of Psychology.Boston:Allyn and Bacon,1999。标签:心理学论文; 科学论文; 自然主义论文; 心理学发展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认知过程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哲学家论文; 自然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