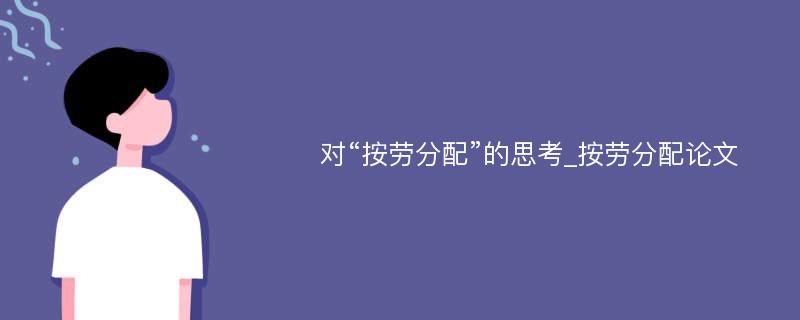
关于“按劳分配”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按劳分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4期发表了《按劳分配与市场机制》一文之后,一些同志对我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因此我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表述我的观点。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在共产主义阶段没有商品、货币。但是,他又说,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实行按劳分配,而在高级阶段实行按需分配。“按劳分配”并非马克思的原话。马克思的意思可以概括如下:按劳动量分配;劳动要成为尺度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劳动成果相同,从社会消费品中分到的份额也相同。按劳分配体现着资产阶级权利。一个人的天赋、工作能力高,他在同一时间内的劳动成果就大,因而可以分到更多的消费品;一个人未结婚或子女少,在劳动成果相同的情况下就会比另一个已结婚、子女多的人富些。我们撇开后一种情况不说。前一种情况下的天赋、工作能力高的劳动是一种复杂劳动。在确定一个人的劳动时间并计算他应得的劳动券时,必然会出现一个把复杂劳动还原为简单劳动的社会过程。这种劳动券按照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可以交换任何消费品,因此这种劳动券也具有一定的一般等价物的性质。一物的价值是由该物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不能把等量劳动相交换与等价交换绝对地分开。
共产主义阶段没有商品、货币,但是商品、货币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必须有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就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从商品经济到产品经济的过渡、从价值规律到节约时间的规律的过渡不可能一下子完成。货币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虽然不存在商品交换,但仍存在等价物交换,虽然不存在货币,但仍存在具有某种一般等价物性质的劳动量。这种等价交换的性质和一般等价物的性质只是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会消失。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按劳分配与资产阶级权利、等价交换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据此我在《按劳分配与市场机制》一文中得出了市场机制是按劳分配的题中应有之义的观点。这一观点与这一问题上的传统的从概念出发的思维定式发生了矛盾。
按照这种思维定式,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不能说等价交换,只能说等劳交换,因为等价交换是商品生产条件下的产物。把等劳交换和等价交换绝然分开,使之属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做法显然是不符合辩证法的。这里的分歧根源于对《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句话的不同理解。马克思在那里说:“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存在于平均数中,并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对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认为,这句话中的“而在商品交换中”指的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以前的社会,这句话是在比较两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不存在等价交换,只存在等量劳动相交换,资产阶级权利的原则和实践不再互相矛盾,也不存在等价物交换借以存在的平均数;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以前的社会中存在等价交换,等价物的交换只存在于平均数中,原则和实践的矛盾被理解为价值和价格的背离。按照这种理解,资产阶级权利的原则和实践不再互相矛盾是指不存在价值和价格的背离。另一种理解认为,这句话不是在单纯比较两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而是在比较等价物交换在两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中的状况,等价物的交换这种资产阶级的权利的原则和实践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已不再互相矛盾,而等价物的交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则只存在于“平均数”即平均劳动之中。前面一种理解显然受到了俄译文的影响,前面所引的那句话的中译文的词序基本上是与俄译文相同的。这样的词序安排有可能产生这样的理解,即这句话是在单纯比较两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从而有可能得出这样的认识,即等劳交换属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而等价交换则属于资本主义社会。这句话的德文如下:"Das gleiche Recht ist hier daher immer noch-dem Prinzip nach-das buergerliche Recht,obgleich Prinzip und Praxis sich nicht mehr in den Haaren liegen,waehrend der Austaush von Aequival-enten beim Warenaustausch nur im Durchschnitt,nicht fuer den einzelnen Fall existiert."按照德文,这句话可以译为:“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权利,虽然原则和实践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等价物的交换在商品交换中只存在于平均数中,并不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显然,在这句话中,平等的权利,资产阶级的权利、等价物的交换具有相同的含义。因此,这句话是在比较等价物的交换在共产主义第一
阶段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同情况,等价物交换的原则和实践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不再互相矛盾,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则是矛盾的。由此可见,在这句话中根本不存在把等劳交换和等价交换分属于两个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根据。在弄清楚了对这句话的不同理解及其原因之后,现在还要讨论这句话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什么是资产阶级权利?资产阶级权利表现在哪里呢?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资产阶级或市民(Buerger)最初的意思。资产者是与封建贵族相对应的概念,也是与无产者相对应的概念。资产者或市民与封建贵族的区别之一是他不靠他人的劳动为生;资产者与无产者的区别之一是他拥有一定的财产。在这个意义上,资产者的权利之一就是使用自己的财产并增大自己的财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的权利表现为以等价交换的形式在市场上购买工人的劳动力,而在交换之后,资本家的权利就是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劳动力,增大自己的资本。这是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的基本内容,也是《资本论》的一个基本内容。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阶级没有了,剥削也没有了,但是权利在这里仍然是不平等的,因为虽然在这里是等量劳动相交换,但是由于人的身体状况、天赋、家庭状况不同,人们之间的富裕程度是不一样的。因此,在这里,平等的权利即等价物的交换所产生的结果是权利的不平等。马克思说,“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第二个问题:这里的“平均数”是什么意思?一种意见认为,在这里原则和实践的矛盾是指价值和价格的背离,因而“平均数”是指高价和低价的平均。另一种理解认为,等量劳动相交换实质上就是等价物的交换,等价物的交换只存在于平均数就是只存在于社会平均劳动之中。那么,为什么说资产阶级的权利即等价物的交换只存在于平均数中呢?我认为,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是按照它们所包含的相等的平均劳动量来交换的;资本家按照这一原则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而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家总是追求达到或超过社会平均劳动的生产率,以实现增殖自己的财产的权利,而当所有的资本家都起而仿效时,社会平均劳动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于是又开始了新的竞争。我主张后一种理解,因为前一种理解必然要求把等量劳动相交换和等价交换分开,使之属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必然要求机械地把按劳分配简单地理解为按劳动时间分配,从而否定智力优势和个人天赋也是体现资产阶级权利的重要因素,必然要* 否定社会平均劳动概念。
按照这种思维定式,按劳分配不能理解为按劳动效果分配,只能理解为按劳动时间分配,而且在这里劳动强度可以忽略不计,劳动的熟练程度也已被舍弃掉了,因而这里不再有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的差别,也就没有效果问题。这一结论的逻辑推理进程很清楚,但有几个问题。1.资产阶级权利表现在何处,马克思所说的“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如何理解?2.既然没有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差别,没有效果问题,只能按劳动时间分配,那么,资产阶级权利是否就表现为劳动时间的多少?是直接的劳动时间,还是产品折合成的劳动时间,如果是,如何折合?如果不是,那么,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又表现在哪里?有一种意见认为,复杂劳动是不能折合成简单劳动的,这种意见还进而否定社会平均劳动概念的存在。首先这里要说明一点,社会平均劳动是抽象劳动,而不是具体劳动。对于反对社会平均劳动的宏论我不想加以评说,只想用马克思的话来回答,马克思说:“另一方面,当问题涉及到价值生产时,较高级的劳动总是要化为社会平均劳动,例如一日复杂劳动化为两日简单劳动。如果某些有修养的经济学家反对这种‘武断的言论’,那么用一句德国谚语来说,他们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们指责这是分析的诡计,但他们所指责的恰恰是在世界各地每个角落里天天都在发生的过程。”<%《资本论》(法文版)第1卷中译本第186-187页。%>把社会平均劳动与具体劳动混为一谈,这也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表现。那么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平均劳动概念是否意味着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之间的换算要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呢?我认为不是这样。未来社会的人完全有能力确定一种尺度来衡量体力、智力和天赋各不相同的各人的劳动,而完全不需要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这种思维定式还认为,按劳动效果分配就是拉萨尔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对于这种推论,我想只能用“武断”来解释。
按照这种思维定式,按劳分配也可以理解为按劳动力价值分配。如果是指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那么这里首先要提出一个问题:既然按照这种思维定式,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不存在价值概念,那么劳动力价值概念又从何而来?劳动力价值概念是否要以劳动力是商品为前提?如果是,那么这一前提是否与这种思维定式的出发点相矛盾?其次,如果按劳动力价值分配是指当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按照劳动力价值分配,全部剩余产品归社会所有,固然不会有拉萨尔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之嫌,也不会有吃光分光之虑;但是我认为,由此导致的结果也许是既无东西可分也无东西可吃。
马克思说:“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些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1版第3卷第12页。%>如何理解这句话的“劳动成果相同”("gleiche Arbeitsleistung")?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认为,这里的德文可以理解为“提供的劳动相同”。另一种理解认为,这里的德文可以理解为“劳动的成果相同”、“完成的工作量相同”、“产出相同”。在1961年莫斯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19卷第19页上,"gleiche Arbeitsleistung"被译为“相同的劳动”。在1978年莫斯科出版的《哥达纲领批判》英文版单行本中,相关的这句话被译为:"Thus,with an equal performance of labour,and hence an equal share in the social consumption fu-nd…"。根据英译,"gleiche Arbeitsleistung"可以理解为“提供的劳动相同”、“完成的劳动相同”。可见,1978年莫斯科出的英文版的理解和1961年莫斯科出的俄文版的理解是相同的。1972年北京外文局出版的英文版的理解也相同。这些版本的理解属于以上第一种理解。还有两个英文版属于第二种理解。在1943年伦敦出版的英文版单行本中,有关的这句话译为:"Thus,with an equal output and hence an equal s-hare…"。在1989年莫斯科进步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中,这句话被译为:"Thus,given an equal amount of work done,and hence an equal share…"。这两个英文版的理解是相同的,即理解为“相同的产出”、“完成的劳动量相同”。比较一下莫斯科出的两个英文版,我们可以看到,俄国人对"gleiche Arbeitsleistung"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我引用这些版本是为了说明,按劳动效果分配这一层含义不能否定。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否定了按劳动效果分配,也就否定了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区别,也就否定了平均尺度存在的必要性,也就部分地否定了资产阶级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