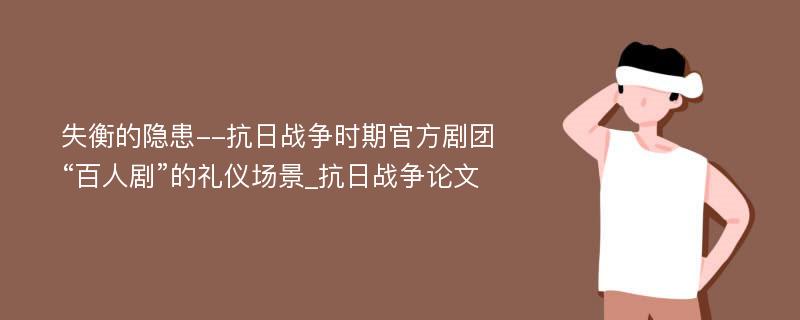
失衡的隐患——论“抗战”时期官办剧团“百人大戏”的仪式性场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剧团论文,大戏论文,隐患论文,百人论文,仪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82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549(2014)06-0119-11 “抗战”初期,官办剧团在陪都重庆多次组织“百人大戏”的演出,以推广“抗战”宣传。“百人大戏”,顾名思义即出场人物众多,场面宏大,气势雄浑,一般以普通民众的集体觉醒与不屈斗争为主要内容,在舞台上以史诗般的叙事展现中华民族“抗战到底”的钢铁意志,多见于“抗战国防剧”的演出。如1938年怒潮剧社(以下简称“怒潮”)演出的《中国万岁》:“伟大悲壮国防剧!中国电影制片厂演员百余人参加。”[1]民间剧团(含民营剧团)虽然也组织“百人大戏”的演出,但由于剧团组织的临时性与演出实力所限,只是偶一为之,并不常见。在某种意义上,“百人大戏”已成为官办剧团的特色剧目。但是,“百人大戏”的成功在于导演者借助一系列仪式性场面,让观众与演员在热烈的互动中完成了对中华民族战争苦难的集体体验。而当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期,大后方市民生活陷入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的困苦时,简单的战争苦难已不足以涵盖意义深远的民族苦难。观众对苦难有了新的理解,这就要求剧场提供给他们新的集体体验。1940年,大后方剧坛打破“抗战八股”的呼声已越来越高,《雾重庆》的轰动性演出更是证明观众对苦难体验有了新的诉求,而官办剧团却在此后的一段时间继续局限在“百人大戏”对战争苦难的仪式化再现上,忽略了这一诉求。而且由于“百人大戏”的剧本普遍存在情节模式化、人物脸谱化等问题,导演不得不过度利用炫目的舞台装置,通过打造仪式性场面的视听效果来迎合观众,演剧失衡的隐患也因此而生。 一、苦难体验与仪式性场面的构建 “百人大戏”的仪式性场面建立在观众与演员对中华民族的战争苦难进行集体体验的基础上。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决定移驻重庆。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以《国民政府令》正式确认重庆为陪都。在这段时间内,官办剧团的“百人大戏”配合重庆的各种大型募捐、节庆活动,本身就已构成了陪都剧坛的一种特殊仪式。正如马丁·艾思林所言:“剧院就是一个民族当着它面前的群众思考问题的场所。”[2](P.97)这一时期的“抗战”形势也正如国民政府所宣称的:“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3](P.37)剧场需要提供给观众的是“中国万岁”、“民族万岁”、“全民抗战”、“抗战到底”等集体意识。虽然迁都初期活跃在重庆的剧团数量众多,但大多数的业余剧社、职业剧团或是昙花一现,或是转移阵地,真正坚持在重庆长期演剧的只有官办剧团中的“怒潮”与业余剧社中的“怒吼”①,而有实力演出“百人大戏”的却只能是财力雄厚的前者了。 “怒潮”是隶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国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中制”)的官办剧团,拥有舒绣文、黎莉莉、史东山、马彦祥、应云卫等一批知名编导与演员。1938年9月“怒潮”随“中制”迁至重庆,其在重庆的首演就是9月16日—19日的“百人大戏”《为自由和平而战》与《血战九·一八》。因演出效果轰动,“怒潮”又再接再厉,于1938年12月16日—21日演出“百人大戏”《中国万岁》,一举奠定了自己在重庆剧坛的领头地位,后又凭借该剧获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嘉奖,改名为“中国万岁剧团”(以下简称“中万”)。作为初到重庆的开锣戏,《为自由和平而战》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怒潮”的“百人大戏”的演出模式,剧中仪式性场面的塑造更是成为全剧的高潮段落。1938年10月4日—7日,为响应募集寒衣运动,“怒潮”再次公演《为自由和平而战》,其规模更盛过其在重庆的首演。该剧分日夜两场在重庆国泰大剧院演出,“怒潮”为其出动了庞大的导演团:王为一、袁丛美、袁牧之、郑用之、史东山、王瑞麟、应云卫、罗静予、宗由、唐瑜,其中“中制”厂长郑用之为执行导演,舞台监督由应云卫担任。“怒潮”演员百余人参与演出,计有黎莉莉、舒绣文、陈波儿、俞佩珊、叶仲寅、朱铭仙、虞静子、王斑、何非光、宗由、戴浩、潘直庵、王豪、刘犁、王珏、井淼等。另有国立戏剧学校、华北宣传队、国民政府侍卫队、重庆警备司令部、青年剧社、民众歌咏会等机关和团体协助演出。“怒潮”为其撰写的广告词:“融化戏剧、电影、音乐之大成、创造抗战戏剧的一支洪流。怒潮剧社全体演员百余人总动员,募集寒衣话剧公演《为自由和平而战》。”[4]再现出当年的盛况。 《为自由和平而战》由王为一编剧,全剧通过一位解说员的讲解将日军的暴行、中国军民的奋起抗争(包括根据徐韬《八百壮士》独幕剧的改编片段)、民众劝募寒衣等场面串联起来,最后由解说员带领大家高呼口号,激发观众的“抗战”热情。从1939年版《为自由和平而战》的剧本可以判断,导演兼编剧王为一重点塑造的是中华民族领土受侵、平民受害、军民抗战、全民捐募寒衣等仪式性场面。“仪式就是一个原始部落以及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用以体验这种(团体的)一致性的手段之一。”[2](P.20)抗战初期,中国剧人将因战争而带来的民族苦难设定为仪式性场面呈现在陪都的舞台上,提供了这一时期中国观众所需要的国家形象与民族精神,激发了其抗战意识。重庆《新蜀报》记者张志渊曾记录了《为自由和平而战》现场演出情景: “为自由和平而战!”一声锣响,幕布揭开,中国广大的版图展在眼前,右边是拈花微笑的和平天使,左边是高擎火炬的自由之神。中国整个的国家,原在自由与和平的空气中向前发展,然而,不幸在八年前这广大版图的东北角上,红色的灯光亮了,而领导全剧演出的舒绣文女士同时喊出了:“看!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要实现他的大陆政策,便以夺取我们的东北为其开端。”这时从中国的地图背后,慢慢地伸出了一双魔爪,继而出现了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来扰乱人类和平的日本法西斯军阀,他狂笑着,怪叫着折去了和平天使的翅膀,吹灭了自由之神的火炬,因而东北三千万同胞便成为了他们的奴隶……[5] 很明显,王为一在一开场即借助某些具有象征性的舞台布景来展现中华民族正在遭受的战争苦难。紧接着,又借助舞剧的形式展现了日寇强暴中国妇女、刺杀婴儿的残忍行径。在展示了“八百壮士”死守上海四行仓库等一系列军民壮举后,导演安排演员高举火把唱着主题曲,从观众席走上台;三个孩子用火炬引燃了自由神的火炬,中国地图透出亮彩。孩子们为和平神插上翅膀,台上台下形成壮观的群众场面,孩子们在舞台上欢跃。[6](PP.50-51)这些由苦难——抗争——胜利三种意象构成的仪式性场面,成功地取得重庆观众的共鸣。《为自由和平而战》的主题曲是徐滔、王为一作词,贺绿汀、盛家伦作曲的同名歌目:“我们燃起自由的火炬,我们高举和平的旗帜,同胞们,起来,起来,为民族自由解放而斗争,同胞们,起来,起来,为人类的和平而抗战。”[7](P.7)根据演员黎莉莉的回忆,演出结束时,“台上演员与台下观众手持火炬合唱《为自由和平而战》,情绪激昂,如火如荼。”[8](PP.63-64)在合唱声中,“怒潮”圆满完成劝募寒衣的任务。根据重庆《中央日报》的报道,仅10月6日两场观众就不下4000人。其中,演员谢畹华打花鼓唱《募寒曲》:“毕露将士需寒衣之迫切。座中观众深为感动,慷解义囊。”[9]“观众中间时常会表示出一种共同的反应,一种同感;这种共同的反应在舞台演出过程中,无论对于演员和观众自己,都越来越趋于明显。……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观众不再是一群孤立的个人,而成为一种集体意识。”[2](P.17)从《为自由和平而战》的演出效果来看,观众与演员通过对民族苦难的体验,已完成了对“抗战”意识的集体认同。 二、形式新奇与舞台装置的突显 以《为自由和平而战》为代表,官办剧团特别注重舞台装置在仪式性场面中的突出作用。而随着观众对“八股化”的“抗战”剧本产生厌烦情绪,官办剧团的导演在重视舞台装置的同时,也开始追求“百人大戏”演出形式上的新奇。 在《为自由和平而战》的导演构思中,王为一非常明确:“这个戏它不靠故事情节,只靠‘抗战’中各方群众支持抗战的各种生活情景,在舞台上分成左右两个演区以灯光的变换来换景。”[6](P.61)所以,极具表现力的灯光效果是解决原剧本结构松散、情节性较弱等问题的关键。 舞台左右上空悬挂强烈聚光灯,左灯开,左灯光下演戏,右灯开,右灯光下表演,两边时常变换,或作宣传演讲,或作群众制寒衣,或医疗伤兵等。地图前根据演讲者的台词变幻,当说到日帝侵略我国东北时,地图上的东北部分就突出血染的红光。之后侵略者又粗暴地打灭了自由神的灯光,折断了和平神的翅膀,丢在地上。[6](PP.50-51) 这种灯光效果与深具象征意义的舞台布景,以及讲解员声情并茂的解说相配合,加深了观众对中华民族所经受的战争苦难的直观性体验。除此之外,王为一还大胆借用了电影手法中剪影效果,在舞台后景中的平台上,设计了不断地行走、扶老携幼的难民剪影,被著名导演史东山称赞为“舞台上出现这种情景,有电影蒙太奇的感觉”。[6](P.61)至于让张志渊印象深刻的:“第二次幕揭开后,一片火光耀着全台,我国英勇的士兵正在电网后与暴日作殊死战,枪声与炮声不绝于耳。”[5]则是出色声音效果的体现。正是由于这些舞台装置在仪式性场面的构建上起到的重要作用,王为一才会强调这个剧本“不够完整”,但因为“形式与内容以至舞台技术还有些新颖,引起了一些朋友的注意”。[10](P.1)事实上,《为自由和平而战》由于情节性较弱,所以着重依靠民族苦难与军民抗日的仪式性场面激发观众的抗战激情。而这些仪式性场面在扣除了舞台装置的效果后,就只能依靠演员精湛的技巧来支撑了。如由黎莉莉担当的农妇角色,“我(黎莉莉)扮演一个遭到蹂躏的农妇,用舞蹈形式与一个敌人搏斗,发挥了我的艺术特长。全剧对白很少,近乎哑剧。”[8](PP.63-64)剧本的孱弱与演员演技、舞台装置的过分凸显揭示出整场演出出现了演剧失衡的危险,仪式性场面的轰动效果反而在一定程度掩盖了“百人大戏”演剧失衡的问题。 如果说“抗战”初期,如《为自由和平而战》一般的“百人大戏”尚能够利用炫目的舞台装置掩饰剧本的薄弱,塑造仪式性场面,那么随着演出的频繁,情节模式化的八股剧本已经越来越吸引不了观众。“百人大戏”不得不在重视仪式性场面的同时,追求演剧形式上的创新,以求得观众认可。1939年3月,“怒潮”演出《民族光荣》②,其广告词为“剧情紧张,布景伟大,装置新奇,演技娴熟,全体演员百余人参加演出。”[11]该剧代表了这一时期“百人大戏”普遍的创作模式。在扣除“布景”、“装置”、“演技”后,该剧被批评为:“剧本有点紊乱,前后的事实不大一贯还不说,而给予观众的印象,似乎还没有把握住一贯中心。虽主题是在写‘自卫队’,而表面却写成了《群魔乱舞》。”[12]这其实直指“抗战剧”的“八股化”问题,宋之的《民族光荣》与陈白尘的《群魔乱舞》都是写群众觉醒后,杀死汉奸,抗击日寇,情节上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而人物脸谱化又导致两剧中汉奸、群众的形象都不甚鲜明,且大同小异。为了引起观众的兴趣,导演应云卫在剧中多次制造“噱头”,“令人感觉到是在看《雷雨》《日出》”,[12]而这些内容又不是一个“抗战剧”的演出中所应该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布景的宏大与装置的新奇,配合“噱头”共同掩饰着剧本“八股化”的问题。宋之的在1940年10月的文艺界自我批评座谈会上曾对“抗战”戏剧做出总结:“‘抗战’初期大家都抱着兴奋情绪来创作”,“作者要将自己兴奋的情绪通过作品传达给观众,我自己的作品也是同样的情形”。但现在“我怀疑,那些能够使观众兴奋的作品究竟给了观众什么实际的影响,恐怕除了一时的廉价的感情满足之外没有别的”。[13]所以,他提议“一个作家在‘抗战’初期的兴奋情绪已经过去的今天,应该需要冷静,更深入地去观察现实,把握现实。只有更深入地在作品中把握现实,才能给观众以更深入的对于现实的认识。”[13]在此之前的1940年9月,宋之的刚刚完成《雾重庆》的创作,这种剧作家创作上的转向揭示出大后方观众已出现新的精神诉求,而这种诉求已不是“百人大戏”依靠以往的创作模式所能够提供的。 1941年4月5日,为庆祝抗建堂剧场在重庆的落成,“中万”特别公演马彦祥的新作——四幕七场“报告剧”《国贼汪精卫》。该剧由马彦祥亲任导演,全体演员百余人合演,是“怒潮”改组为“中万”后最具规模的演出。《国贼汪精卫》“把我们这一代中的这群民族罪人的丑态赤裸裸地揭开在我们面前。”[14]马彦祥围绕着“讨伐汪逆”这一主题,除塑造汪精卫及其狐群狗党的丑态外,还精心设计了南京市民在市民大会高喊口号“打倒卖国贼汪精卫”,并与日本宪兵同归于尽的悲壮场面。此外,他还假托汪精卫的梦境,在舞台上真实再现了“重庆各界讨汪铸逆募捐游艺大会”的会场。“会场里观众早已挤得水泄不通,墙壁上到处贴满了各项讨汪的美术画和标语:(一)消灭汪逆伪组织!(二)汪逆伪组织是敌人政治阴谋的最后把戏!(三)汪逆伪组织是罪犯汉奸的总集团!”[15](P.184)游艺大会由知名艺人山药旦表演《骂汪》鼓词、阮振南魔术团表演《汪精卫变狗》等。以上场景即是该剧最重要的两个仪式性场面。除此之外,剧组还特邀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录制斥汪广播词,并将其作为该剧的一大亮点广为宣传。但即便如此精心创意,在1941年4月的戏剧批评座谈会上,与会者却纷纷表示《国贼汪精卫》看后“印象不深刻”。[16]剧评人曲辰认为:“这个效果的产生,是应该由剧情发展的散漫与不集中,只有平面而没有立体的发展来负责的。”[17]阳翰笙则指出《国贼汪精卫》“给人印象是不深。这正说明感染力不够,也就是艺术形式的创造与刻画不够,一个汉奸走上背叛民族的道路是有他的必然性的,如果就其真实生活的复杂矛盾,加以更深的刻画,减少理论,加强形象,我想效果或者能更好”。[18]这就证明《国贼汪精卫》的核心缺陷在于汉奸人物塑造上的平面化。剧本在人物塑造上的硬伤,导致了演员们对剧中人物形象的把握停留在表面上。“演员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的性格还未能更深刻地理解和表现。或者可以这样说吧,演员对典型人物的创作还没有尽最大的力量。”[14]所以,该剧虽被包容地评价为:“如果说它失败的地方多,那么它成功的地方应该更多。”[19]但实际上,这些失败已在很大程度上暴露出演出的不足。《国贼汪精卫》在艺术上最大的成功其实集中在对“报告剧”这一形式的采用上。“这样一个报告形式的戏,‘抗战’以来还是第一次见到。因此,有提出商讨的必要。”[17]但剥去“报告剧”的外衣,该剧的剧本是粗糙的。正如编剧马彦祥自己所说的:“就自己的一点点写作经验来说,是从来没有处理过这样琐碎而又复杂的题材,因此作为整个的反映汪逆叛国的政治阴谋的剧作来看,免不了还有许多缺陷是无疑的。”[20](P.3)仪式性场面固然激发了观众对“汪逆”的愤恨之情,“报告剧”的新奇也与以往的“抗战剧”不尽相同,但剧本骨子里还是“抗战八股”,剧界对其提出批评自然是意料中事。 三、规模缩水与市民场景的涌现 1940年12月,《雾重庆》在重庆的轰动演出标志着在观众产生“打破八股”的诉求后,以“抗战”时期市民生活为题材的剧本即将成为职业剧团的首要选择。同时也预示着“百人大戏”通过仪式场面所构建的“苦难”、“不屈”、“抗争”等集体体验已经满足不了大后方观众的需要,取而代之是《雾重庆》《残雾》《蜕变》等剧中通过“不合理生活的暴露与讽刺”[21]对“一个自由平等,新的形式的国家”[22](P.394)的呼唤。正如《雾重庆》的观众李榕所提议的那样:“我们不再需要日本鬼子当场杀人的刺激了……新作品的产生,是应当配合了新中国的建树,使坚定的、光明的、向上的思想存在,予犹疑的、黑暗的、堕落的现象,以无情地彻底地打击。”[23]在这种情况下,官办剧团若要继续上演“八股化”的“百人大戏”,不仅会流失观众,在仪式性场面上的重金投入还会让剧团面临着入不敷出的危险。 1941年6月,重庆剧界已经注意到某些大型剧目出现的演剧失衡问题: 陪都几大剧团演出的一般情形,参加他们演出的演员都是优秀的,布景服装是华丽的,照明是鲜跃的,在这战时的情况环境之下,有这样堂皇的演出,确实非常可观了……但我觉得只顾到布景怎样的堂皇,灯光怎样的华丽,只在布景及灯光上显其身手,结果大家都说“布景不错,灯光也还好”,看起来剧情及演员的演技比起灯光与布景来是差劲的,结果布景及灯光胜过于剧情,胜过于演员的演技,观众看完以后多说“这戏演的还算热闹”……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24] 在此要特别指出1941年10月中华剧艺社(以下简称“中艺”)在重庆的精彩亮相。作为首家可以在重庆长期活动的民营剧团,它的首次大型公演《大地回春》不仅揭开了重庆“雾季公演”的大幕,也宣告了重庆剧坛不再由官办剧团一统天下。鉴于1941年10月“中艺”公演《大地回春》之前,活跃在重庆的基本上是“中万”、“中电”两家官办剧团,所以“布景及灯光胜过于剧情,胜过于演员的演技”这一问题很明显是在批评官办剧团的“百人大戏”。如果说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官办剧团尚可依靠充裕的演出经费,不在意亏损问题,在仪式性场面的构建上可以斥以重资,那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大后方经济突然恶化之后,它们已没有了原来的财力。官办剧团的成员此时依靠官薪已很难维持生计,剧团不得不考虑剧目的票房盈利。重庆的三大官办剧团——“中万”、“中电”、“中青”③在第一届“雾季公演”的中后期阶段,即1941年底至1942年中旬这段时间,几乎同时完成了大幅度的职业化转向。官办剧团不仅要依靠营业收入来维持剧团生存,而且还面临着与民营职业剧团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百人大戏”的演剧失衡问题尽管在第一届“雾季公演”之前就敲起了警钟,但却是在第一届“雾季公演”中,伴随着营业亏损、观众流失、剧团地位下降等问题才正式受到了官办剧团的重视。 受演出成本上涨与经费缩水等因素的影响,第一届“雾季公演”中官办剧团的“百人大戏”不论数量还是规模都呈缩水趋势。“中电”、“中青”本就不热衷“百人大戏”的演出,所以继续坚持该种演出形式的还是资金相对宽裕的“中万”,但在规模上也做不到全团百人总动员了。如《江南之春》虽算得上是当年的大型演出,但实际只出动了31名演员④,可被视作“百人大戏”的小型化。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中万”的《陌上秋》⑤《战斗的女性》⑥中。在三剧中,演剧失衡问题最突出的是马彦祥导演的《江南之春》。如果说《国贼汪精卫》是对“报告剧”展开了尝试,那么《江南之春》便是在探索面向农村观众的戏剧新形式⑦。“当我自己(马彦祥)为中国万岁剧团主持这剧的演出时,由于工作计划的精密和排练的纯熟,不仅克服了一切舞台工作的困难,而且创造了当时重庆话剧换景时间的最迅速记录。”[25]《江南之春》在换景速度上取得了新突破,但其重点构建的仪式性场面却未必达到同样的效果。全剧结束时,村民们齐心合力歼灭了来犯的日寇,并在舞台上怒吼:“我们要杀尽东洋鬼!”[26](P.211)客观而论,这是“抗战”前期“国防剧”常见的仪式性场面,但放在1942年,就让看惯了“抗战八股”的观众反应平平了。《新华日报》剧评人刘念渠⑧将《江南之春》评价为“凌乱的演出”,“不过由始至终是一片叫喊,用叫喊向观众报告了一件‘实录’罢了”。[27]重庆剧界也认为:“《江南之春》的导演马彦祥,也同样挽救不了他自己编剧手法上组织散漫,甚至变本加厉地揭露了此剧在情节方面时断时续的毛病。”[28]正如剧作家胡绍轩所说: 第一期“抗战”中,因为中国人民对于敌人的侵略和“抗战”的意义还不能普遍地认识和明了,所以那时期的戏剧是需要带有说明性和激发性的。第二期就不然,因为人民对于敌人的侵略已有深刻的认识,对于“抗战”的意义也深切明了,所需要的是如何站在自己的岗位参加抗战,所以这时候的戏剧是应该带有指导性的。[29] 归根到底,从《民族光荣》到《江南之春》出现的批评之声,其根源问题在于剧本的概念化、人物的脸谱化、情节的模式化,已让官办剧团的“百人大戏”不能像“抗战”前期一样,仅仅凭借灯光、音效、布景等舞台装置打造出仪式性场面就可以获得观众的共鸣了。大后方观众在剧场中需要得到的集体体验是中国该如何“忍痛蜕掉那一层腐朽的躯壳”,让新的愉快的生命降生。如果不在舞台上呈现这一主题,“百人大戏”无论进行任何形式上的新探索都会面临着演剧失衡的危险,并引发观众的流失与票房的亏损。 1943年7月,陈白尘的《秋收》更名为《大地黄金》,再次由“中青”上演于重庆。但该剧不仅没有取得营业上的成功,还引发了颜再生与新上任的“中青”社长马彦祥的一场论争⑨,论争的焦点在于重庆观众是否需要、是否接受《大地黄金》这样“一种与抗战有关而描写都市以外的伤兵农妇之类细民的,‘朴素’而且‘真实’‘动人’戏剧”。[30]虽然马彦祥认为《大地黄金》“不失为一种富有教育意义的抗战剧”,[31]但该剧在重庆“不被高贵的人们所喜爱”[32](P.1)却是事实。颜再生认为此时的重庆观众需要的剧本应该“着力在那些浑浑噩噩与‘抗战’脱节的都市生活上,而绝不能以农村中的割稻之类的事业来作对症的下药”。[33]这其实是较为客观地指出了该剧在重庆不受欢迎的原因。《大地黄金》之后,可能是出于营业上的考虑,类似的“抗战剧”在官办剧团不再出现。而在《大地黄金》演出之前,官办剧团已演出了《蜕变》《结婚进行曲》《金玉满堂》等市民题材剧目,向观众反映了市民生活中某些深层次的苦难,如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妇女问题、家庭问题等等。这些剧目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百人大戏”在官办剧团剧目建设中的特色地位,不仅赢得了观众的认同,亦保障了票房。写实化的市民生活场景也配合“斯坦尼体系”在大后方的推广逐渐取代了“百人大戏”的仪式化场面。可以说,以1942年底“中万”版的《蜕变》为代表⑩,官办剧团已经开始重视演出上的艺术完整性,在努力克服演剧失衡的危险倾向。 但是,1943年初国民党再次加强了对官办剧团的监管力度,剧团的上演剧目被限定在国民党认定的题材无碍之作中。而大后方观众希望从剧场中获得的集体体验已升华为对自由、民主、平等的向往。这就决定了官办剧团难以提供给观众他们所需要的精神食粮。在这种情况下,官办剧团为赢得票房,维持生存,又加大了对舞台装置的投资力度,从而引发了新一轮的演剧失衡问题。 ①该时期与“怒潮”实力相当的官办剧团是隶属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中央电影摄影场的“中电”剧团(以下简称“中电”),但该团长时间不在重庆活动。“中电”在重庆的首演是1939年3月赵丹导演的《战斗》,演出结束后,全团即远赴昆明从事电影拍摄工作,返渝后直至1940年12月才演出了宋之的编剧的《刑》。 ②该剧又名《自卫队》。 ③“中青”的全称为中央青年剧社,是隶属三青团中央团部的官办剧社,但成立之初实力较弱,只能演出一些短剧。直到1941年2月改组,由熊佛西、张骏祥担任第一任正副社长,并吸收了一批国立剧专的毕业生后,才具备了组织大型公演的能力。 ④1942年3月23日—31日,该剧由“中万”上演于国泰,共演出9场。 ⑤即陈白尘的《秋收》。1941年10月11—22日,该剧由“中万”上演于抗建堂,共演出12场。 ⑥该剧系“中万”与“中艺”合演,自1942年4月26日—5月5日上演于抗建堂,共演出10场。 ⑦《江南之春》系马彦样根据陈瘦竹小说改编而成。马彦祥在《〈江南之春〉前言》中表示该剧要从民众熟悉的艺术形式中学习经验,故采用旧形式首尾贯穿的写法,全剧因此分场较繁,达16场之多。 ⑧刘念渠常用笔名为颜翰彤。 ⑨颜再生疑为刘念渠的化名。 ⑩该版《蜕变》是“抗战”时期重庆剧人学习“斯坦尼体系”,追求演出完整性的代表作,具体论述见笔者《从史东山〈蜕变〉看斯坦尼体系在重庆剧坛的实践》一文,已发表于《戏剧艺术》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