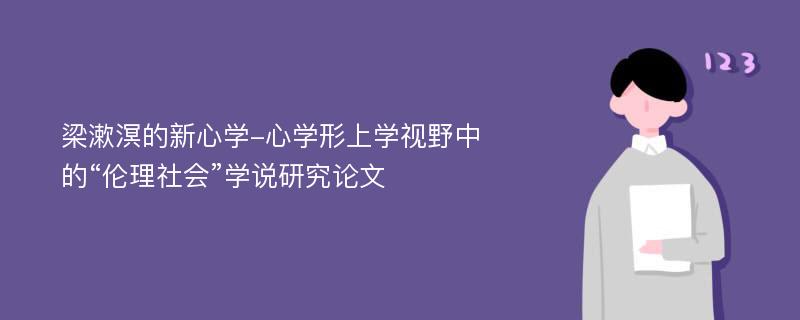
梁漱溟的新心学*
——心学形上学视野中的“伦理社会”学说研究
陈 畅
摘 要: 心学形上学探讨事物之间普遍存在的内在关联,作为感应之几的良知是激发事物间真实、高效联系及活力的根源。从心学形上学视野考察梁漱溟的伦理社会学说,能够呈现梁氏学说中独特的心学思想方法与哲学内涵。针对晚清民国时期传统社会结构的崩溃以及儒学游魂化的问题,梁漱溟侧重以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联来诠释儒家的良知观念、理性观念,并强调理性制度化(组织化)之必要性,由此重塑新的礼乐秩序。其实质是以心学的致思进路回到伦常生活的大本大源,重建儒家伦理的公共性和凝聚力。梁氏的新心学思想为思考中国问题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解读视角。
关键词: 梁漱溟;伦理社会;理性;心学
20世纪著名思想家梁漱溟(1893-1988),一生致力于“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的思想探索与实践。“伦理社会”学说可谓是其毕生思想精粹。这一学说不仅仅是梁氏对于古代中国社会结构与性质的具体判断,也是其对中国文明未来发展的期待与实践方向。梁漱溟在思想立场上倾向于王阳明心学,伦理社会学说亦展现了心学独特的思想方法与哲学内涵。众所周知,心学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学术思想,乃至有“言心学者必能任事”(1) 康有为:《南海师承记》卷二,载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二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8页。 之说。衡之于20世纪中国学术史,梁氏可谓“心学任事”之典范,其学说堪称一种融汇了历史传承与时代特质的“新心学”思想类型。
本文将基于心学的形上学视野,深入考察梁漱溟的伦理社会学说,厘清梁氏学说中独特的心学思想方法与哲学内涵,重构其对儒家政教理想的诠释脉络。经由这种发明和重构,呈现一个现代心学形上学体系及其实践路径,进而探讨梁氏新心学实践品格的根源所在。这种考察方式将彰显其在以往的研究中隐而不显的思想内涵,亦将更加立体地呈现心学多元而复杂的面貌及其当代意义。
在动物疫病监测工作中,法律是其中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需要重视动物疫病监测的法律建设,做好普法宣传工作,以提高养殖户的动物疫病监测意识,这对于后期防疫人员的工作有重要的影响[3]。其次,要加强市场监督管理,逐渐做到对所有动物进行监测,并且颁发合格证。对于无合格证的则需要根据法律法规进行打击。
一、伦理社会学说与熊、梁“家庭之辩”
“伦理社会”或“伦理本位社会”,是梁漱溟对中国传统社会构造和性质的基本判断。他认为晚清民国所表现出来的中国问题是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具体表现是社会构造的崩溃。在他看来,任何社会的良序发展都根植于自身文化传统,中国问题的解决必须走“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西洋人的长处”的融和之路。(2)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载《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8页。 故而其乡村建设理论试图以此融和方式重建社会构造,解决中国问题。当今中国社会与梁漱溟提出这一主张的年代相比,无论是国力还是国际地位都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伦理社会学说不仅仅是梁氏个人对于历史的某些洞见,或对其所处时代的某种理想化陈述;而是一种兼具现实感、历史厚度和实践精神的中国哲学学说,具有多层面的理论意义。
《裴通远》一篇中,家在崇贤里的主人公裴通远的妻女,去通化门观看唐宪宗的殡葬,至夜方归。坐车到天门街时,夜鼓响起,母女两人再往前行,遇到一位跟在车旁的白发老妪。一问之下,老妪也住在崇贤里,母女两人便邀老妪她同行。不想老妪在里门下了车后就消失不见,而与这位神秘老太同车的几个女子竟相继死去。
梁漱溟完成于1949年的《中国文化要义》系统论述了伦理社会学说,熊十力在1950年多次与梁漱溟通信论及此书,其中一函严厉批评梁氏伦理社会学说“巧避家庭本位之丑”、只做伦理本位之好文章。熊十力认为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民族观念、公共观念,有私而无公、见近而不知远,这一切近代以来饱受诟病的恶德,均来自于家庭;故而怒斥家庭是万恶之源、衰微之本。(4) 梁培宽编注:《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下卷,载《熊十力致梁漱溟(195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92页。 事实上,梁漱溟并非如熊十力批评的那样取巧而一叶障目,两人只是在思路上根本有别。天地间万事万物皆有其历史发展,中国古代的宗族制度有其富有活力的阶段,也有极其衰败的阶段;有其温情脉脉富有情谊的面向,也有专制压迫的一面。熊十力的批评只聚焦于其负面因素,而无视其积极因素。历史学家科大卫的研究指出,宗族制度在将华南地区纳入中央王朝国家体制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5) 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卜永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科大卫:《明清社会和礼仪》,曾宪冠译,北京师范大学2016年版。 这是宗族制度最具活力的功能展现,并在一定意义上能够成为梁漱溟下述观点的佐证:伦理本位的特殊社会结构“具有对于外族人巨大的融合吸收力”、“为汉族所以拓大无比之本”(6) 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载《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435页。 。之所以说“在一定意义上”,是因为梁漱溟所说的伦理社会与宗族社会既有联系,又存在着微妙而重要的区别:宗族社会是小集团本位主义,容易陷入以邻为壑的对抗性;伦理社会是以互以对方为重的情谊为纽带,将差异个体协调共处,它没有边界,不形成对抗。这种区别是儒家对上古封建宗法制度加以改造的结果。换言之,华夏民族以及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证明了其政治与社会形态的确具备“巨大的融合吸收力”;但是宗族社会有其天然限制,无法成为融合吸收力的制度和精神来源。例如,明清时期华南地区不同宗族之间为了争夺生产、生活资源而持续发生的大规模械斗,即可作为梁漱溟观点的旁证。(7) 郑振满:《清代闽南乡族械斗的演变》,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 这说明有另外的规则和力量在起作用。梁漱溟认为,答案就在伦理本位的社会结构之中。如果不是因为人人心中具有伦理本位之情感,并得以扩充至不同社会情境,各自不同的个体和群体何以能彼此相安共处而构成社会?(8) 梁漱溟:《人心与人生》,载《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615页。 综上,梁漱溟的伦理社会学说正视宗族制度的局限,并由此超越了有边界的宗族制度,力图找到中国社会兴衰背后更加深刻的内在逻辑。相比之下,熊十力的批评没有抓住重点且显得武断。
中国古代社会是伦理社会,这是梁漱溟以西方文化中的个人本位和集体本位为标准衡量中国传统社会而得出的结论。他发现中国古代既非个人本位,亦非集体本位,而是介乎二者之间的形态,并且根本精神颇有异,故而另取一名。伦理社会是指以伦理组织社会的形态;而伦理则是指人与人之间互以对方为重的关系之理。互以对方为重,是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它使得远近亲疏人人皆联系于情谊之中——“痛痒相关、好恶相喻”。梁漱溟强调,伦理社会在根本精神上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迥异:伦理本位在人与人互相关系中,互以对方为重,而不是固定在任何一方;这种精神反乎任何之固定本位主义。因此,伦理社会与“家族本位的社会”不同,前者是古代圣人基于对人性的洞见而作出的制度性建构,后者则是“各自看重其家族,鲜顾及旁人”的小集团本位主义。(3) 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载《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338-339页。 伦理社会中的人性自然与制度制作之辨,是其核心内容。梁漱溟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长处与短处皆由伦理社会而来。例如,互以对方为重的伦理习俗,塑造了中国人特爱折衷妥协,不爱走极端,好文(讲理)不好武,对人温和而谦逊自处的头脑心思和气质;但同时也使得中国古代流于“社会家庭化”之一偏,社会生产和生活都落在家庭这个小单位上,大集团(譬如国家)生活组织纪律的缺乏就成为严重问题。质言之,梁漱溟的诠释思路是越过中国古代具体的家庭、宗族形态,直接追溯其精神及制度源头,再回过头来诠释古代社会的功能以及“社会家庭化”之流弊。这种思路颇有禅宗及心学“去其枝蔓,直探本源”的风格。
事实上,在熊、梁“家庭之辩”的背后,涉及到两人对于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不同理解,以及对于中国文明的未来发展方向的不同思路。前者留待本文第四节讨论;就后者而言,熊十力仍然停留在以西洋社会形态比附中国的惯常看法上。正如梁氏的判断,熊十力《读经示要》《论六经》《原儒》诸书根据《大易》《春秋》《礼运》《周官》各经,“以革命、民主、社会主义之义阐明孔子的外王学,有许多惊世骇俗的议论”。(9) 梁漱溟:《读熊著各书书后》,载《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744页。 梁漱溟的思路与熊氏迥异,他认为中国古代文明走上了与西洋不同的道路:古代中国并非尚未发展出民主、科学和资本主义;而是向别途发展去了,不能进于民主、科学和资本主义。伦理社会学说正是对古代中国所走的“别途”之概括。梁漱溟坚持认为,一物之兴衰有其共通的逻辑:以此而兴者即以此而衰,曾食其利者亦必承其弊。既然伦理本位的社会结构给中国人带来如此丰厚的收益,承受其弊端并基于其根本逻辑作出改造,就是最恰当的解决方案。梁漱溟对于“老中国”的独特认知与他建设“新中国”的理想方案是一体相关的。他从罗素那里得到启发:中国的独立自主最终意义不在其自身,而在其将西方科学技术和自身夙有品德(即伦理社会)相结合,开创新局。(10) 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载《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203页。 显然,即便是在20世纪的新儒家思想家群体中,梁漱溟的构思方式也是非常独特的。而这种独特构思的理论基础,以及伦理本位如何塑造中国社会的古代形态以及未来发展的具体机制,都在他对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概括之中——理性。
二、理性概念:心学致思进路及其形上学意义
儒家政教秩序的基础是理性,其限度也在于理性自身。道德、礼俗、教化等互为影响的理性启发形式,本质上是对个体反省精神、公共之心的挖掘,其同时也是对于政教秩序的奠基。梁漱溟借用《大学》古语“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来描述儒家政教结构的维持之道。因为启发理性工夫的要点是教人反省自求,也就是引导民众修身自治(自我管理)。在这个进路中,在上位的施政主体与在下位的受众之区别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每一个体的道德自觉。士农工商四民在伦理上能够依此自觉各尽其道,在职业上各奔前程;君臣、父子、上下、长幼、贵贱皆得其分,互相配合,一切关系良好,就是中国人向往的治世。相反,社会各阶层不能自尽其道,伦理社会的基本构造失去其功用,关系破裂,就成了乱世。儒家士人以主持世教为要务,本质上是基于形势而为社会各方指点提醒,维护此社会构造。在梁漱溟看来,这就是中国古代社会陷于一治一乱的周期循环,无法提出新的政教秩序的根本原因。(28)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载《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209页。 儒家政教秩序的另一个限度,表现在伦理社会的核心是“互以对方为重”的伦理义务与责任观念,个体权利并不受到重视,因此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的最大偏失在于个人永不被发现。(29)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载《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251页。 这是以西方社会为参照系得出的结论。如何通过中西汇通以弥补这一缺失,是儒家在现代社会面临的要务之一。
关于梁漱溟理性概念的具体提出过程,学界已有许多精彩研究。(11) 详参干春松:《梁漱溟的“理性”概念与其政治社会理论》,《文史哲》2018年第1期。 就理性概念的具体内容而言,梁漱溟采取的是阳明心学进路的定义。梁漱溟认为人类在生物界中最突出独有的表现是在生物机体(身)之外发展出生命现象(心),其生命重心遂转移到身体以外:一面转移到无形可见的心思;一面转移到形式万千的社会。他把人类心思作用区分为两面:知的一面曰理智;情的一面曰理性;理智、理性各有其所认识之理。理智静以观物,其所得者是“物理”,是夹杂一毫感情(主观好恶)不得的。理性则是以无私的感情为中心,即以不自欺其好恶而为判断,其所得者是“情理”。无私的情感与理智同样地是人类超脱于本能而冷静下来的产物,其表现为人们的一种平静通达、清明安和的心理状态。梁漱溟喜欢使用一个通俗的例子说明:当一个人心里没有事情,你同他讲话最能讲得通的时候,就是理性。(12)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载《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314页。 讲得通,是指对于旁人的感情意志能够互相理解、互为照顾,进一步便可形成人与人之间“好恶相喻,痛痒相关”的和谐一体。因此,梁漱溟所说的理性,是在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与沟通基础上产生的伦理责任之自觉。伦理自觉代表着由通达而建立的公共意义。例如俗语“通情达理”“明事理”,都是这个意思。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由于理性的通达与否,表现为两种类型:情感关系和欲望关系。梁漱溟认为互以对方为重的情感关系是人类社会凝聚和合的基础;自私自利的欲望关系是社会冲突的源头。(13)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载《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91页。 这是从理性的定义出发,扩展到人类群体、公共社会的建立;其解释进路一如既往地简洁高效。
综上所述,梁漱溟所说的理性,其核心特征可概括为三点:(1)其主要内容是平静通达、清明安和、无私的感情,具有不自欺其好恶而为判断的客观性,此之谓“情理”。(2)其客观性来源于人与人之间最为根源的情感互通和关联,人们在这一层面好恶相喻、痛痒相关;梁漱溟称之为心的生命现象,区别于人人而殊的“身”。(3)其最重要的功能是因情而有义,构建人类公共社会。贯通这三个特征的是人与人之间最根源且互相关联的情感或本心,有公义的公共社会即由此而奠基。回到宋明理学的语境,这种诠释方式与心学进路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在宋明理学中,天理观最有影响力的定义来自朱子:“至于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14) 朱熹:《大学或问上》,《四书或问》,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这种定义既包括当下事物之变化的个别性之理,也包括超越个别性限定的根源之理、结构之理,天下万事万物因此而被纳入相互通达、彼此相与的贯通状态。上述两个涵义分别代表个体性与公共性,说明性理之学本身就内在蕴含着个体性与公共性的恰当平衡结构。这是理学家针对宋代以后平民化社会“一盘散沙”之政教秩序问题而提出的解决方案,具有最根源的政教意义。(15) 进一步的分析论证,可参见陈畅:《理学道统的思想世界》导论、第一章,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版。 大致而言,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在哲学立场上各有所侧重,或从公共性或从个体性的角度出发提出该平衡结构的诠释。由此观之,梁漱溟的理性概念显然是基于心学立场的天理观念。
实际上,梁漱溟的诠释不仅契合心学传统,且能作出独特的发明。此即其对情感如何达到普遍化的诠释。梁漱溟认为伦理社会有两个最基本的构成要素:一是礼乐制度,二是伦理名分。前者源自古宗教,后者则脱胎于古封建宗法社会。两者在经过孔子的理性启发、制作之后,就不再是古代宗教与封建原物。就礼乐制度而言,上古时期的人类社会,从政治、法律、军事、外交再到养生送死等一切公私生活均离不开宗教;而礼就起源于上古宗教,是一种祭祀天地神祇和祖先魂灵以求获得福佑的仪式。儒家的创造就表现在以彻底理性化的方式将此类宗教安排转化为礼。这种转化蕴涵了儒家礼乐的另一个功能——涵养理性,教化人心。因为儒家礼乐运动消除了宗教迷信和独断因素之后,人在履行礼乐仪式时自然生发的清明、虔敬、安和心情,就是理性。就伦理名分而言,“名”是君臣、父子、兄弟等封建等级关系;“分”是其相应的责任与义务。梁漱溟认为孔子的正名是以旧的封建宗法秩序为蓝本,并根据理性作出全新估定,使一切旧观念都失其不容质疑的独断性,而凭着情理作权衡。其另一个效果则是广泛推行家人父子兄弟间的感情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俾社会关系建筑于情谊之上。因为不同的名分对应于不同的职位,各各配合便构成社会。总之,梁漱溟疏理的礼乐制度和伦理名分起源过程,核心机制是“以人心情理之自然,化除那封建秩序之不自然”。(27)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载《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115-122页。 梁漱溟对“化除”过程的描述,展现了心学思维的特质;事实上同时也揭示了儒家对情感如何达到普遍化的处理方式:通过对上古宗教与封建宗法制度的改造,令情感突破血缘亲情的局限,得以提纯、扩充,亦即作出了普遍化和公共化处理;而宗法社会亦被改造为充满情谊的公共社会。换言之,情感的普遍化和制度化(组织化)是相辅相成的,是儒家公天下理想实现路径的一体两面。
上文借助心学形上学视野对梁漱溟观点的扩展论证,目标在于实现双重激活:一方面,以心学形上学为梁漱溟的理性概念奠基,化解理性概念所面临的种种理论困难,真正成为一种完善的学说;另一方面,通过这种联结,在当代社会重新激活心学形上学相应的面向。而这种联结,也是古典思想的一种现代转化。试以熊十力对梁漱溟的批评为例说明。从感应之几的角度考察梁漱溟的伦理社会学说,不难发现,前述熊十力“家庭是万恶之源,衰微之本”观点之局限在此展现无遗。在阳明心学的感应结构中,真诚恻怛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21) 王守仁:《传习录上》,载《王阳明全集》,第2页。 ,贯穿于不同情景中的是同一种情感,“发之”即是将其扩充至不同的情境。换言之,宗族社会与伦理社会的联系与区别亦在此真诚恻怛之心扩充与否:这种情感停留于家庭小集团本位,便是容易陷入以邻为壑之对抗性的宗族社会;将这种情感扩充出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便构成具有巨大融合吸收力的伦理社会。扩充是以人性自然为基础的,而自然情感亦需要后天教养和制度的依托。这是梁漱溟所说的古代圣贤基于对人性的洞见而建构社会的制作原理。这一思路是建立在中国古典形上学对普遍性与超越性的独特理解之上的:普遍性与超越性不是来自经验的抽象或理念的建构,而是来自于事物之间的贯通通达。在这一意义上,心学形上学是古代中国人伦社会最精巧的哲学表述。明乎此,即可知熊氏观点之局限:其忽视了儒家社会建构原理中的人性自然与制作之辨。
如上所述,梁漱溟理性概念最核心的内容是人与人之间最根源且互相关联的情感,此义蕴对应于阳明心学中的感应之几。宋明理学中的感应不是神秘主义代名词,而是指人物之间的联系与沟通。如《咸卦·彖传》所言:“天地感而万物化生”,感应是对万物化生秩序的本然描述:天地万物处于互相敞开的境域,处于一种动态、本真的关系之中。但感应并不是人与物联系的工具和手段,而是一个囊括人与物的结构,它在逻辑上优先于这一结构中的构成因素。二程有云:“天地之间,感应而已,尚复何事?”(17) 程颢、程颐:《二程集·二程粹言(天地篇)》,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226页。 换言之,感应是天地万物最基本的存在方式,是天地间一切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在这一意义上,感应是理学最基本的思维模式,理学实践的原型就是重建感应:破除事物彼此隔绝的不相通状态,重建事物之间的本真联系,实现万物在时空上恰到好处的配置。梁漱溟多次论及“恶起于局,善本乎通”(18) 梁漱溟:《人心与人生》,载《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672页。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言说。在阳明对良知与感应关系的论述中,值得注意的地方有两点。一是阳明说“在感应之几上看,岂但禽兽草木,虽天地也与我同体的,鬼神也与我同体的”(19) 王守仁:《传习录下》,收入吴光、钱明、董平、姚廷福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页。 ,其意在指出良知唤醒了感应中的生机关联:我的良知灵明唤醒了我的世界(感应链条)中的生机和韵律,激活了我的世界(感应链条)中的万物生机、力量和秉性,令人物以“活泼泼地”的方式共在。二是阳明指出良知的内容是真诚恻怛之心,能在每一个具体情境(感应场域)中自知其所当为,切中“天然自有之中”,此之谓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20) 王守仁:《传习录中》,载《王阳明全集》,第96页。 真诚恻怛之心,不单是指个体真诚恳切之心,而是指人与物以“活泼泼地”的方式共在的存在方式本身。换言之,真诚恻怛之心的意义不仅仅在其自身,更在于其祛除了种种虚假造作的遮蔽,恢复人与物之间的感应结构。创造力来自于真实、高效的事物间联系;衰败、软弱与无力是由虚假造作所致。在这一意义上,真诚恻怛之心首先意味着活力和创造力,它自能感应和激发周围事物或系统的高效运作,实现事物在时间、空间上恰到好处的配置。而阳明心学的工夫论,正是围绕感应之几开展工夫,以事上磨练的方式锻炼良知的力量;其最终目标是良知明觉随时呈露,契合现实事物的轻重厚薄的各种情形,具备理则的客观性。在这种心学形上学与工夫论体系中,前述梁漱溟理性概念面临的种种理论困难,都能轻易化解。
非线性化误差模型没有对旋转矩阵定位器各移动副方向向量对应的微分算子进行简化,将微分算子中的二阶、三阶项纳入约束方程。求解非线性化误差时,定位器坐标系设定与托架运动学反解时的坐标系设定相同。
员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满意度是员工对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整体客观存在的主观感受、认知和印象所组成的一个有机复合体,其中包括“客观资源”和员工“主观感受”两个方面的内容,是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员工的满意度是源于心理活动,是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这两方面并非孤立存在的,而是紧密融合。
三、理性的普遍化与制度化:儒家政教原理及其限度
形上学探讨规范赖以成立的条件根据、变化背后的终极原因等根源问题,它构成了人类各高级文化的最基础部分。因此,一种形上学原理犹如风对于万物的赋形,开展出一套以它为基盘的日常生活、社会、政治形态;而不同的形上学原理则塑造出不同的政教秩序与意义系统。梁漱溟认为,不论是情理抑或物理,理都是公共的、人们彼此共同承认的;正是这种公共性,使得不同的人们能够彼此相安共处而构成社会。但是,由于中国人与西方人对于“理性”的不同思路,导致各自建构的社会政治形态迥异。《中国文化要义》一书通篇所述不离此义。梁漱溟认为孔子对于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在于孔子专从启发人类的理性作功夫,教人反省自求,除了信赖人自己的理性,不再信赖其他。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的行为准则(伦理责任与义务)之根据是反求诸己,是理性精神,亦即儒家所说的仁、良知。这种理性主义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区别于人类其他社会文化的特质所在。由此,梁漱溟将儒家政教秩序原理诠释为情理的普遍化与制度化:通过启发众人的理性,实现一个“生活完全理性化的社会”;此理性化的社会秩序之维持,不是依靠法律等外力强制而是依靠理性自力,并开展为一个道德、礼俗、教化与政治合一的政教系统。(22)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载《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111页。 在梁漱溟那里,这一套原理的开展应用有两个面向,一是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解释,二是检讨其所处的时代状况并提出解决方案、塑造未来。
就历史解释而言,将梁漱溟的学说放置于儒家政教思想诠释语境中,更能彰显其理论意义。众所周知,儒家的政教理想可归结为“天下为公”。按郑玄的注解“公犹共也”(23)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8页。 ,“天下为公”是指天下是全天下人共有的天下,不为一家私有,天子之位传贤而不传子。这是一种主张权力多元分享的政治原理。在周代宗法封建制创立后,特别是经由孔子“述而不作”之后,“公天下”原则被提炼为在仁与礼统摄下“通过差异的协调,而非差异的取消,来实现和维持共同体的存续与繁荣”。(24) 此处参考了张志强先生的精彩研究,详见氏著《如何理解中国及其现代》,载《文化纵横》2014年第1期。 王阳明自述其提揭良知学说“欲挽而复之三代”(25) 王守仁:《书林司训卷》,载《王阳明全集》,第282页。 ,人人自有的良知“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体”(26) 王守仁:《传习录中·答聂文蔚》,载《王阳明全集》,第79页。 ,这也是在“公天下”政治原理的意义上言说。良知源于个体心,又能协调差异个体,做到公是非、同好恶,正是“公天下”之道的核心内涵。梁漱溟伦理社会学说中,互以对方为重的情感关联最显著的功能,是通过协调差异个体,建构和谐的共同体。由此可见,梁漱溟对于儒家政教秩序的诠释与重构,正是在阳明心学的视野中展开。
我们家那时生活条件差,穿的都是自己家纺织的土布,添置一件新衣服后穿上要爱惜,新衣服平时不能穿,只是出门时穿一下。一件衣服大的穿后小的穿,直到烂得不能再穿了。出门时没有新衣服就是旧的也要洗干净,家里人很重视仪表和声誉。
然而,由于梁漱溟并非专业哲学家,其理性概念在论证上稍嫌粗糙且不够深入。如学界研究指出的,梁氏“互以对方为重”的理性观念是笼统的道德原则,一般大众在日常生活中难以把握,需要很高的人生修养和社会历练才能把握其合宜性。(16) 详参冯书生:《比较视阈下梁漱溟的道德哲学及其时代价值》,《人文杂志》2018年第11期。 并且,清明安和之心何以能与他人感通,进而具备判断的客观性?在现实生活中,偏执之人自以为是的例子比比皆是。如何判定此心之状态,分辨其中的是非对错?梁漱溟并没有对这些疑难问题作出进一步的分疏。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借助心学形上学视野,通过挖掘心学形上学中与梁氏思想相对应的元素,厘清其思想机制,对梁漱溟的观点作出进一步的深化和扩展论证。
梁漱溟一生的思想探索成果,集中于其对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系统解答——理性精神。梁漱溟所说的理性并非西方文化意义上的理性——亦即人类独特的判断、推理的思考能力以及使人的行为符合特定目的等方面的能力;毋宁说是对中国古典性理(天理)观念的现代诠释。
除此之外,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面临的更大困难在于文化失调、社会结构的崩溃。这已经不单纯是乱世的问题,而是传统上支撑乱世得以复归于治世的政教结构已经完全崩溃。故而梁漱溟说,中国社会崩溃已到最深刻处,建设亦须从深刻处建设起。(30)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载《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270页。 所谓深刻处的建设,就是重建社会结构。梁漱溟找到的方法是乡村建设。如吴飞先生所论,梁漱溟的乡建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其在思想文化层面有特别的意义;其以礼俗重建为核心的乡建运动,充分凸显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复杂性,为后人思考中国问题和中国的现代性改造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31) 吴飞:《梁漱溟的新礼俗》,《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 所谓礼俗重建,也就是建构中西交通时代的礼乐秩序。换言之,梁漱溟乡建运动的思想文化意义远超其现实意义。这就犹如老子哲学以批判文明的造作为特质,虽然现实中无人愿意回到原始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老子哲学没有思想价值。下文将从心学及其实践的角度考察梁漱溟乡建运动的思想意义。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文明的独特性在于理性,中国社会、政治是由理性组织起来的;中国问题的解决必须通过重新激活理性,速成一个有组织、有秩序、有理性的国家。需要注意的是,他认为重新激活理性必须通过社会组织化的形式进行,这个观点来自中国历史和西方社会的双重启发。
在中国历史方面,梁漱溟认为理性组织化的典范是由宋儒创造的乡约组织。乡约是一种伦理情谊化的教化组织。在理学家针对宋代以后平民化社会“一盘散沙”之政教秩序问题而提出的解决方案中,乡约与书院、宗族建设共同构成宋明儒者将理性制度化(组织化)的重心。前文分析的梁漱溟对情感关系和欲望关系的界定,事实上就是宋明理学中的道心和人心概念的简化版。情感关系(道心)是公共社会的基础,欲望关系(人心)是社会冲突的源头。它能有效解释宋代以后理学家所推动的教化运动与理学形上学建构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而提醒我们注意:梁漱溟重释理性概念,与宋明理学家的形上学体系建构一样,本来就是针对时代政教难题而提出的解决方案。在西方社会方面,梁漱溟认为西洋人的长处主要在于团体组织、尊重个人和财产社会化,它们能够对治中国人散漫被动、不重视个体权利的缺点,亦能增进社会关系。梁漱溟从中受到启发,认为乡村建设应该将乡约与西方社会的团体组织结合起来,塑造新的理性组织及其礼俗。梁漱溟乐观地认为,这种新礼俗融会贯通了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方文化长处,代表着人类正常的文化、世界未来的文明。(32)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载《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278、309页。 梁漱溟对西方文化的认知毫无疑问有简化之嫌,这是时代的限制,不必苛求;而事实上这种认知表明他是带着“先见”来打量西方的。此即伦理社会学说的核心洞见——理性及其制度化(组织化)。这正是梁漱溟考察中国问题的独特视角。
首先,将对比组的所有病患进行子宫按摩和注射药物以进行治疗,并观察其状况,若病患的状况没有改善,将对照组的病患进行宫腔填塞手术。手术前需要将治疗所要用的纱布进行消毒,并将纱布裁成长度为2厘米,宽度为7厘米的条状,再对病患进行填塞处理,手术者在治疗过程中,应该将子宫在腹部做好固定处理,然后再实施填塞操作,填塞时应注意不能出现死腔,填塞需要使用卵圆钳。手术者应该将纱布条压住,并将其均匀的填入,手术者要时刻关注病患是否出现大出血状况,如果大出血则需要及时采取急救措施,以防病患在手术过程中危及生命。
四、余论:熊、梁之辩与现代心学的多元形态
经由心学形上学与梁漱溟伦理社会学说的相互发明,可得出两点结论。第一,梁漱溟的理性概念强化了天理观念对于事物之间本然联系(秩序化)的表述;侧重阐发其公共性、凝聚力内涵,亦即令差异个体得以交流和沟通,建立美好共同体的内涵。第二,从社会构造的角度看,人性自然与制度制作之辩证关系是不可或缺的:一方面,如果没有在教化制度(组织)层面为情感的普遍化作保证,血缘亲情无法摆脱蒙昧狭隘的宗族形态之局限;另一方面,若要解决伦理秩序崩溃形势下欲望主体一盘散沙的问题,则需要激活理性及其组织形态,建立相应的新礼俗。上述两点结论是梁漱溟伦理社会学说的独特思想内涵。通过与同时代的学术思想之间的对比,更能彰显其可贵的理论特质。事实上,熊十力与梁漱溟之间的“家庭之辩”,是理解梁漱溟伦理社会学说之当代哲学意义的关键要点。本文的考察为我们全面思考熊、梁之辩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概言之,梁漱溟伦理社会学说是心学的现代形态;熊、梁之辩正是基于各自对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不同理解,体现了现代心学的多元形态。
梁漱溟伦理社会学说对理性内涵的诠释和发挥,其实质是回到伦常生活的大本大源,重建儒家伦理的公共性和凝聚力。这种发挥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针对性。前文提及梁漱溟观察到的时代问题表现在文化失调、社会结构的崩溃;其反映在制度上,就是儒家体制的全面崩溃。余英时对此有一个著名的描述:随着传统社会的全面解体,儒学与现实社会、与制度之间的联系完全断绝了,儒学成为一个游魂。(33) 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困境》,载《余英时文集》第二卷,广西师范大学2006年版,第263-264页。 当儒学游魂化之后,人们对于儒学思想的理解和诠释就很容易去脉络化,各得一察焉以自好。作为对儒学现代困境有着清醒认知的历史学家,余英时对熊十力一系的新儒家学术亦有敏锐的观察。他批评新儒家学术以宗教性的、超理性的证悟经验作为重建儒家道统的前提,表现出“良知的傲慢”。(34) 余英时:《钱穆与新儒家》,载《余英时文集》第五卷,第26页。 证悟是富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身心体验。按熊十力在《船山学自记》中的描述,其对于“真我”的理解是基于万有皆幻的生存体验,进而体悟到“幻不自有、必依于真”,此“真”即作为“能觉”的“我”。(35) 熊十力:《心书·船山学自记》,载《熊十力全集》第一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这显然是一种宗教性的解脱经验,由此“本真”经验出发,现实历史中一切有形的伦理习俗制度都容易被视为后得性障碍而加以批判祛除。明乎此,即可知熊十力为何激烈批判“家庭为万恶之源”。此即前文所说熊、梁两人对于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不同理解,这种对比具有丰富的思想意义。宗教性的解脱经验当然是古典心学的元素之一,但绝非心学的唯一基础;梁漱溟立足于伦常生活经验的思想建构,为我们指出儒学、心学的伦理政治内涵才是其核心基石。正是在伦理政治的语境中,梁漱溟通过重构理性的部分组织形态,激活传统思想的实践性。这就是梁漱溟新心学实践品格的根源所在。
总之,梁漱溟的伦理社会学说为现代学术界理解心学、思考中国问题提供了另一种解读视角。其新心学具备的积极回应现实、勇于任事的特质,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可贵气质。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应通过检讨和总结其思想经验,以更好地回应现实、塑造未来。
Liang Shuming ’s New Idealism Theory :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Ethical Society
Chen Chang
Abstract : Wang Yangming's philosophy of conscience explores the ubiquitous connection between things.This paper examines Liang Shuming's ethical soci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cience Philosophy.Liang Shuming's theory of ethical sociology lays a foundation for ethical life and rebuilds the commonality and cohesion of Confucian ethics with the help of the ideological method of conscience philosophy. Liang's theory is a new theory of mind, which provides a unique perspective for thinking about China's problems.
Keywords : Liang Shuming;Ethical Society;Reason;Idealism Theory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项目编号:17ZDA013)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19-05-21
中图分类号: B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5833(2019)09-0127-08
作者简介: 陈 畅,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 (上海 200092)
(责任编辑:轻 舟)
标签:梁漱溟论文; 伦理社会论文; 理性论文; 心学论文;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