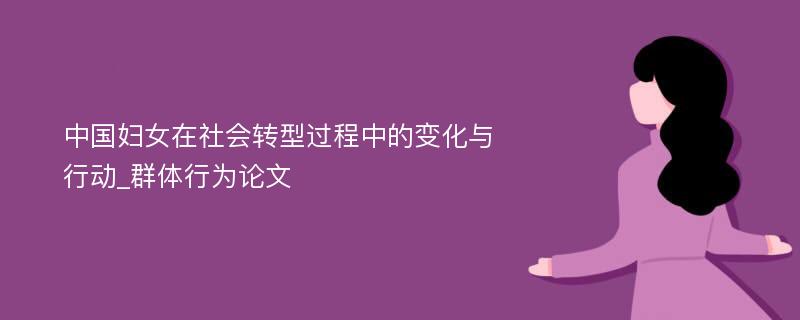
中国妇女在社会转型中的变化和作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妇女论文,社会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处在急剧变化的转型期。
和所有男性公民一样,在新的变化了的社会结构中,每个(女)人都有必要重新寻找和确立自己的生存位置和发展空间,以自身的发展去参与和推动全社会的发展——或者相反,因为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将被社会淘汰。
在新的压力下和新的选择过程中,中国妇女的现实生活较之过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甚至是本质性的)变化,从群体层面上看,至少已经呈现出以下两大特点:
一是在社会结构变化中,女性社会急剧分化,已经形成并且正在生成越来越多的不同的利益群体——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针对外国人,再去笼统讲一个“中国妇女问题”,象是无的放矢。
二是不同的妇女问题融汇在不同的社会层面上,体现出社会转型中的特点,而不是单纯的妇女问题——这种背景下,除非独犯了法规需要诉诸法律,单方面的要求“女权”或“法律保护”都不足以真正解决问题。
1988年,针对联合国的一项调查,将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排在132 位,我提出了“分层研究”的必要,根据当时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和城镇人事制度,曾在“认识我们自己”的题目下,将中国成年妇女分成三大部分:农村妇女、女工、知识妇女。
今天再看这个“分层”,显然已远远不够。妇女的社会分化已经呈现出全方位态势,表现在地域、职业、年龄、民族等各个层面上,不再局限于社会分配或行政干预范围。
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在市场经济发育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职业阶层”,如企业家、商人、律师、经纪人、艺人、自由撰搞人、个体劳动者……所有这些职业人中都有女人。
女人的社会分化不仅表现在职业上,也表现在各种职业内部。比如女工,如今不仅有国营的,集体的,还有外企的,合资的,私营的;不仅有长期合同工,也有流动的“打工妹”和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其间不仅就业方式不同,待遇不同,连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也有很大差别。
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说一个“妇女利益”,即使用在就业保障或劳动保护上,针对不同的群体,也会有不同的反应。拿“就业”来说,一边是国营和集体企业中女工的“下岗”,另一边是农村出来的打工妹“上岗”;城镇女工面临着就业压力的时候,可能恰恰是农村妇女新的就业契机。
即使在农村,妇女也不再是板结一块。一部分人离开乡土,进城做了小保姆或“打工妹”。不论她们日后是留在城市还是回乡,都大大地改变和影响着未来农村妇女的发展走向。留守乡村的中年妇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仍然在集体经济中做事或务农,如在大邱庄、刘庄、小靳庄、西华村、竹林村的;有些几乎全部进了村办企业,如在苏南农村的。自家务农的,也不尽相同:有的以副业为主,有的专事养殖,有的搞联产承包,有的搞庭院经济……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以及不同的地域、民族、信仰,也将农村妇女分化成不同的利益群体。
在市场成熟、法制健全的社会中,职业分化并不一定导致社会分化,也并不必然导致不同利益群体的生成。
今天的中国社会,市场远未成熟,法制尚待健全,社会改革在循序渐进中艰难前行。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形容在摸索中探路。从此岸到彼岸,是一个质的转变:既要完成这个变化,又要避免社会动乱,对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崇尚传统、厚土重迁的国家来说,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局部试点因此为社会改革的先头兵。
我们不难发现,在全国全民共同享用的法律颁布之前,总有一系列针对局部现象的政策性法规出台——局部的“失衡”和“制衡”,因此成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突出特点;它不仅是社会分化的根源,也是不同社会群体分化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这样不间断的、有针对性的局部调整,以渐进的方式有效而稳健地促成了社会的结构性变化。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天的中国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而所有的社会问题无不伴生着妇女问题——妇女问题较之改革初期,较之新时期中期,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但这些问题的现实分量却显得“轻薄”,不再成为“热门话题”,不再打动或激动人心,甚至在女界内部也热不起来。
这是为什么呢?
显然,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不只是妇女自己的问题,甚至主要不是妇女问题了。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用“转型”来表述是准确的。经过十几年的酝酿、争论,社会转型已经全面进入实质性“运作”:不只是“要变”,而是已经“变了”;不是某一层面上的局部变化,而是对我们原来(1949年以来)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的全面触动。每个组织、每个单位、每个企业,以至每一个人都感到生存的压力,都面临着新的选择的必要。在这种环境中,如果仍然单纯地强调妇女问题或单一地固守妇女利益,不仅不会有什么实际成效,反而会显得狭隘,失去原有的社会同情。
比如“下岗”问题,显然不只是针对妇女,在今年开始的企业兼并、破产中,危及到所有的这一类企业中的职工;男性工人绝对数量可能更大。
比如“妇女权益保障”问题,与全社会的公民权利保障密切相关;倘若整个社会尚不能保证法律的实施,又怎么能单独去侈谈妇女的社会保障?
比如“女童失学”问题,集中在缺乏就读条件的极端贫困地区和利用女性劳工正在走向富裕的地区,与经济发展有直接关系。
比如今天的“拐卖妇女”问题,与社会的进步和进步的不彻底有关。所谓“进步”,表现为即使在贫困地区,人们手中终于也可以有一些余钱,除了盖房子,也能花钱去“买人”;贫困地区的妇女也希望以“走出去”的方式走出贫困。可见,贫困和封闭仍然是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根源。
从以上议论中,也许可以窥见中国妇女目前的一些基本面貌:
一边是身体力行地参与社会改革,妇女群体利益分化;正在以“个体”为单位重新组合,产生众多的不同的利益群体,以适应改革的需要。大量的妇女NGO在女性群体利益分化的基础上应运而生, 代表着妇女自助自强的发展趋势。
另一边是社会变迁中妇女问题增多,几乎是每出台一个改革政策,就会伴生相应的妇女问题,社会层面上普遍显露出妇女“群体”的弱者态势。“妇女权益保障法”在这种情况下出台,再一次体现了国家对妇女整体的保护态度。
对形形色色,强弱不等的女人来讲,简单地说一个“保护”,实在难以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女性社会群体的分化,已经将女人的利益搞得支离破碎,因此要求各不相同的女性群体为改善自身生存条件,做出有针对性的努力。
再看我们原有的条件,一个“男女平等”,却可能把女人置于两个极端,使之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走向:
——能够将“平等”当作发展的基础、积极参与社会改革者,多半成为强者:其强者,可能远在“性别差异”之上。
——凡将“平等”当作生存的保障、满足于吃“大锅饭”者,在改革中处于被动境地,不论在社会还是在家庭生活中,都呈现出全面弱势。当今的妇女问题主要出现在这一类妇女中。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妇女中究竟还有没有共同的、最主要的问题呢?
我以为还是有的。
长期以来,由“保护”政策所造成的弱者心态,潜伏在我们心中,从各个方面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以为,这就是今天在我们中间普遍存在的问题:
表现在(弱)女人身上,仍然是对社会、对男人的期待:期待理解和扶助,而不是从自己脚下做起;
表现在妇联干部的工作中,仍然是对上级、对政府的呼吁:呼吁资助和保护,而不是从自己的社区做起;表现在“女强人”心里,仍然是与女人、与女性群体划清界线:将妇女的进步和发展看作是社会的责任,而不是自己应尽的义务。
凡事有利有弊。许多弊端,往往就是受益的结果。
比如,“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将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提高到一个空前的历史水平;我们学做男人,在放弃“女性”的同时丢失了身为女人的自信。因此,十几年来,我们奔走呼号,只在呼唤一个“女性意识”。
又比如今天,“妇女保护法”继“社会主义解放妇女”的传统而来,为中国妇女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我们成为被保护对象并且习惯于“被保护”,在衣食有靠的环境中丧失了自主意识乃至独立自主的能力。因此,我以为,重建“主体意识”,力争做自己命运的主人,是我们今天的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