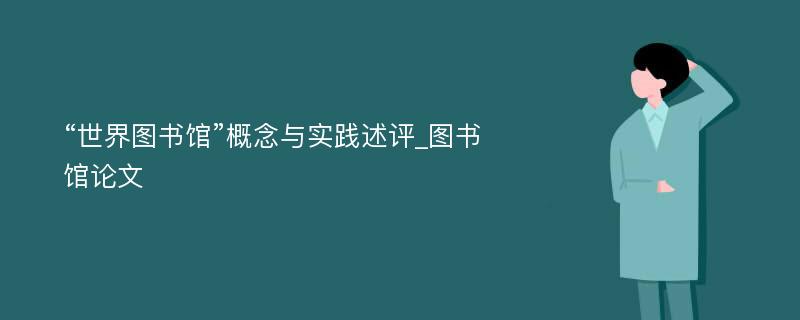
“世界图书馆”理念及其实践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理念论文,图书馆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图书馆”(Universal Library,或译为“寰宇图书馆”、“普世图书馆”)是指具有广泛收藏的图书馆,即包含一切存在的信息、有用的信息、所有图书、所有作品(不论格式)乃至所有潜在作品的图书馆[1]。作为一个术语,“世界图书馆”可以追溯到近代动物学和目录学的奠基人之一、瑞士苏黎世大学生物学教授格斯纳(1516-1565)于1545年出版的《世界总书目: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全部书籍目录》。而世界图书馆实践的最早范例,则一般认为是建造于公元前3世纪的古亚历山大图书馆。据说,当初建造这个图书馆的唯一目的就是“收集全世界的书”,实现“世界知识总汇”之梦想。确实,经过托勒密王朝几代国王的努力,这座人类早期历史上最伟大的图书馆,其鼎盛时期曾收藏了成千上万种手稿,拥有最多的藏书、最多的文种、最全的书目记录。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这种无所不包的性质,被后世看做一种图书馆现象,不仅激励一代又一代图书馆员为实现世界图书馆的理想而不懈努力,而且还进入文学作品中,甚至被视为政治乌托邦,成为谋求世界和平的一种手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普及,世界图书馆成为跨越时空的梦想,催生出一些数字化的实践案例。
1 近代图书馆员的世界图书馆理念与实践
1.1 世界图书馆近代化的开端
文艺复兴时期,世界图书馆成为一些信奉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学者之梦想,其中最具代表者即是意大利的尼古拉五世(1397-1455)。被誉为文艺复兴教皇的尼古拉五世是一位热情洋溢的人文主义者和杰出的学者,也是一位藏书家和图书馆行家。在当选为教皇之前,他曾受意大利大商人、佛罗伦萨僭主美第奇(1389-1464)所托,为其创建的美第奇家族图书馆编制了一份图书采购目录Canone。这份目录,考虑了异教徒的经典图书,涵盖所有学科,被认为是第一份现代的、完备的图书馆标准采购目录。后来尼古拉五世在创建他的教皇图书馆时,为同时方便大学这样的学术机构和图书馆的管理,该馆馆藏建设自然采用他的Canone。尼古拉五世的馆藏理念在当时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其中最具代表者是他的目录学家韦斯帕西安(1421-1498)。韦斯帕西安在谈及尼古拉五世在罗马创建梵蒂冈教皇图书馆时,描绘了一幅清晰的世界图书馆图画:收藏希腊、拉丁文抄本和一切学科的书籍。另外,梵蒂冈图书馆的“世界性”也从韦斯帕西安和意大利的另一位人文主义者、尼古拉五世智囊团的主要成员曼内蒂(1396-1459)对梵蒂冈图书馆与托勒密二世时期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文献比较中得到彰显[2]。
显然,尼古拉五世的世界图书馆梦想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文献的语言只是拉丁语和希腊语,除但丁的《神曲》外,本国语言的文献均被排除在外;文献涉及的学科也并不反映人类的所有知识,即仅指理论知识,不包括实践知识。不过,尼古拉五世所倡导的馆藏标准,显示了世界图书馆近代化努力的开端,他所奠基的梵蒂冈图书馆,是文艺复兴运动初期人文主义者世界图书馆实践的杰作。
1.2 作为机构的世界图书馆
文艺复兴运动于16世纪波及法国,促进了17世纪法国文化运动的高涨。这一时期,图书馆无所不包的观念继续拥有无穷的魅力。在1584年法国的图书馆学和目录学家狄曼恩(1552-1592)出版《在此以前的法语出版物总目录》(以下简称《总目录》)至17世纪60年代法国科尔贝时代的皇家图书馆合并期间,世界图书馆思想真真切切地已从复兴古典学术的观念发展到组成机构的实践。当然,与当时图书馆的发展差不多,这是世界图书馆观念本身进化的结果。在这一时期,世界图书馆观念从虚无的教规变为现实中存储信息的场所,从而使图书馆取得了一种全新的知识和机构身份[3]。
1627年,大约在《总目录》出版后半个世纪,作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首席大臣、红衣主教马萨林(1602-1661)的私人图书馆馆长诺代(1600-1653)发表了第一部组织和建设图书馆的指南手册——《关于如何创办图书馆的意见》,对那种图书馆的静态模式直接提出了挑战。在这部书中,诺代设想了一个完美的图书馆雏形,陈述了他选择图书的原则,强调图书馆的现代图书与古籍珍本同等重要,异教作品与支持宗教的书籍同等重要,坚持用简明易懂的主题方法编排图书的分类体系。其核心思想是:图书馆不应该专为特权阶级服务,必须向一切研究人员开放。他一直坚持:“图书馆为此目的收藏所有类型的图书,是非常必要的。既然图书馆是为了公众利益而建立的,它就必须是世界性的;如果图书馆不收藏所有各类学科——尤其是文科和理科——的著作,其世界性的理念将不会变为现实;……这样,读者来到图书馆寻求他们所需要的书籍时,当然就不会有什么收获……”[4][5]。在这里,诺代将巴黎教会图书馆所信奉的图书馆模式与培根的科学研究模式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图书馆变成一个学习和研究的活跃场所。诺代将图书馆设想为存储信息的场所、百科全书的起点和试金石。尽管曾经在巴黎人的智力生活中起很大作用,奠定诺代图书馆模式基础的教会图书馆在巴黎很快变得不合时宜,但图书馆“世界性”的特点在巴黎并没有消亡,那些伟大的教会图书馆和皇家图书馆均以各自的方式践行了诺代的世界图书馆理念。
1.3 理性主义时代的世界图书馆
17、18世纪是西方思想史上的“理性主义时代”。这个时期,一批科学家或思想家,深入研究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影响广泛的基本理念:创造和传播有用的知识是社会进步的关键。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宣扬科学与理性的同时,亦积极倡导并践行世界图书馆理念,其中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是杰出的代表。莱布尼茨在实践上是一位有所建树的杰出图书馆长,首次将“巴罗克图书馆”(即“大厅图书馆”)引进德国;在图书馆理论上,他也颇有建树,创立了一个图书目录与分类体系。他曾憧憬一个广泛而系统的世界图书馆,其要点可概括为:图书馆应当是用文字表述的人类全部思想的宝库——凡是杰出人物的著作,不论是哪一族,哪一时代的,只要其思想对后人有可取之处,都应当收集,因此,图书馆可称为人类的“百科全书”,“一切科学的宝库”,甚至可说成“人类灵魂的宝库”;大型图书馆要为科学家提供学术交流的条件,应在各国科学院设置的图书馆基础上,建立联系全世界的图书馆网;设想把大量的文献资料用细致的分类语言标引,组成“世界百科知识体系”,以便为学者们提供所急需的参考资料[6]。
1676年,莱布尼茨开始担任德国汉诺威布伦瑞克—吕讷堡公爵府图书馆的馆长。期间,他拟定了一个建立世界图书馆的计划。为此,他将文献分为两组:一组是图书馆绝对需要收藏的图书(比如词典、特定参考书、课本、手册或指南等),他称之为“硬核文献”;另一组为“硬核文献”之外的文献,只具有普通的用途。莱布尼茨认为,丰富的馆藏和有效组织的图书馆,对人类所企及的一切领域都是十分重要和有用的,它与学校和教堂的地位是一样的。为了丰富馆藏,莱布尼茨草拟了“世界图书馆文献选购一览表”。该表显示出古代、中世纪经典文献与16、17世纪文献之间的完美平衡,也充分地反映了包括莱布尼茨那个时代最著名的科学期刊在内的科学出版物。其中几个分类以“……和其他类似的图书”结束,说明该一览表是建议性的,而不是终极的选定。另外,莱布尼茨图书采购一览表的分类顺序与他的图书馆编目分类秩序之相似性,表明他是有意识地将图书馆分类作为他世界图书馆馆藏建设的一种方法[7]。1690年,莱布尼茨开始兼任著名的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馆长。期间,他为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建造了一所具有巴罗克风格的新馆舍。在新馆舍的分类特点、经济状况和审美观上,世界图书馆观念与他建构的通用语言错综复杂地连在一起。
因此,莱布尼茨的世界图书馆观念可从他的图书编目分类与巴罗克图书馆设计两方面的实践进行理解,正如德国魏玛安娜·安玛利娅公爵夫人图书馆的Ulrike Steierwald所言:“与莱布尼茨思想的理论和应用相对应,其世界图书馆观念会按照两方面进行重塑:第一是聚焦图书馆目录和图书馆分类系统的现象,以检测这种作为一切知识的形式描述工具之适应性;第二是一种源于巴罗克图书馆建筑原则的观念,即用大厅图书馆的空间代表世界上的一切知识。”[8]
1.4 研究性的世界图书馆
18世纪,以支持学术研究为主要特征的莱布尼茨图书馆思想开始逐渐地被认识,并被德国一些图书馆采用,其中格丁根大学图书馆最具代表。当时德国大学图书馆普遍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唯有格丁根大学图书馆大放异彩,而主政该馆近半个世纪的海涅(1729-1812)功不可没。格丁根大学图书馆创建于18世纪30年代,1763年海涅开始就任该馆的第二任馆长。关于该馆的馆藏建设,海涅设想过一个“世界图书馆”的愿景:坚定执行之前图书馆理论家(如诺代、莱布尼茨)的传统,建设一个包罗万象、严格满足学习和研究需要的资料库。他的这个理想,从“编制格丁根大学图书馆1801年之前所藏英文书籍目录”工程中得到了体现,因为该书目显示,格丁根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英文书籍为当时世界上除英国本土外最多者,几乎涵盖当时大学的所有学科。海涅不仅具有非凡的管理才能,而且对馆藏建设十分重视,从书籍挑选开始的整个过程,均是由他亲自执行或在他的严密监控下完成的。在海涅的努力下,到1800年,格丁根大学图书馆的馆藏达13.32万册(当时德国北部的大学图书馆和英语国家的大学图书馆馆藏一般在一、两万册),涉及当时研究机构的一切学科,从而使该馆像亚历山大图书馆和Vivarium修道院图书馆记录了古代和中世纪的世界那样,反映的是近代世界,即格丁根大学图书馆通过使收藏官僚化,促成了“世界图书馆”的合理化——选择对公众“有用的”收藏[9]。难怪歌德(1749-1832)1801年在造访格丁根大学图书馆后感慨:“我曾携带一份之前我无法获取的所有书籍和论文之目录,交给了罗伊斯(?—1837,海涅的助手,继海涅后任格丁根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并得到他及其他馆员的帮助。最后我得到的不仅有我已经在书目中所列的所有资料,而且还包括许多我不曾想到,但该馆藏有的文献……我在格丁根的那段时间受益良多。”[10]甚至在海涅逝世将近180年后的1990年,他的世界图书馆方针仍然被证明是有效的——在德国印刷物遗存征集的SDD(Sammlung Deutscher Drucke,德国虚拟国家图书馆)工程中,格丁根大学图书馆被委任充当18世纪德国国家图书馆角色。
格丁根大学图书馆的历史意义还体现在它对欧洲近代研究图书馆的示范作用,尤其对19世纪的英国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影响最大[11]。创办于1753年的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现英国国家图书馆的重要源头),其宗旨一开始就是建成收藏英文和外文书籍的“世界性”图书馆,但到1800年其藏书仅6.5万册左右。到了19世纪以后,尤其是帕尼兹(1797-1879)在此工作时期,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的馆藏以帕尼兹及其助手所信奉的世界图书馆观念为指导而成倍增长,至1900年已达150万册左右,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图书资料中心。帕尼兹是意大利人,1823年逃亡至英国,1831年进入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工作,1837年任印刷图书部主任,1856年被任命为第六任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在任印刷图书部主任期间,帕尼兹就设想: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作为“一所公共图书馆,必须提供所有国家、所有语种、一切学科知识的文献获取方法,这些文献应该适当地排列,牢固而美观地装订,精细而全面地编目……能够与人类知识的增长同步。”[12]帕尼兹在后来的图书馆管理实践中,还提出一个选择性的世界图书馆理念:“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应当满足用户当前和未来的需要,应当收藏世界上一切语种的有用的珍贵图书:英文的藏书应当是世界第一的,俄文藏书应当在俄国境外是第一的,其他外文的收藏也应当如此。”[13]由于帕尼兹的努力,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转型为具有一定资金保障的世界性研究型图书馆,其收集图书的方法也变得系统而有选择性,以至于40年代到80年代,成为该馆19世纪发展的黄金时期。帕尼兹的世界图书馆理念,尤其体现在外文文献收藏实践中。这一时期,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馆藏文献涉及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斯拉夫语以及其他外国语种,且每一种语言的书籍都平等对待,都可为英国及其他地区的一切研究者提供服务,其馆藏的外文书籍,有的语种(如德文文献)甚至比其许多本土研究图书馆还要丰富得多,为一些人文科学学者提供必不可少的材料和“世界性”的信息结构[14]。
2 现代作家的世界图书馆理念与实践
2.1 文艺作品中的世界图书馆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图书馆观念开始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即图书馆收藏由实用转变为“文化”。这一变化的主要表现是过去图书馆员所梦想的世界图书馆开始出现在一些文艺作品,尤其是科幻小说中。这种浪漫的世界图书馆,不仅声称含有已经面世的书面作品,而且还包括潜在的书面作品。该主题最著名的作品是几乎终生在图书馆任职的阿根廷作家、诗人博尔赫斯(1899-1986)于1941年发表的短篇科幻小说《巴别图书馆》(又译作《通天塔图书馆》或《巴别塔图书馆》)。该小说实际上是由他自己于1939年发表的短文《完全图书馆》衍生而来,而《完全图书馆》的主题又源自德国作家、科学家和哲学家拉斯维兹(1848-1910)于1901年发表的短篇科幻小说《世界图书馆》。在《巴别图书馆》中,博尔赫斯用不可思议的语言和密码描述了这个等同于“世界”的图书馆:巴别图书馆是万有的,即任何个人或世界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个图书馆的某个地方找到有说服力的答案,从而给人带来一种“奇特的幸福感”;它也是无限的,但其中的每一册书或著作是有限的,因此该图书馆中这种有限的书籍或著作必定表现出时间上的无限性,正如小说结尾所描述的那样:“这个图书馆是无限的、周转的。假如一个长生的旅人从任何方向穿过它,几世纪后他将发现同样的书籍会以同样的无序进行重复。”[15]在这里,博尔赫斯独特而怪异地预言了万维网的存在,难怪近年一些探讨博尔赫斯作品的著作命名具有数字化的特征,如Perla Sassón-Henry所著的《博尔赫斯2.0:从文本到虚拟世界》、Stefan Herbrechter、Ivan Callus所编的《赛—博尔赫斯》。
《巴别图书馆》对后世作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催生了不少作品,如英国作家David Langford(1953-)的《巴别网络》(载1995年的科幻杂志Interzone上),美国作家、哲学家、认知科学家Daniel Dennett(1942-)的著作《危机四伏的达尔文思想》(1995年出版),澳大利亚的计算科学家Russell Standish的《零理论》(2006年出版),意大利的符号学家、小说家翁贝尔托·埃可(1932-)的神秘探案小说《玫瑰之名》(1980年出版),英国作家Terry Pratchett(1948-)的奇幻系列小说《碟形世界》(1983年出版第一本,截至2011年已出39本)[16]。在这些作品中,都可以找到世界图书馆的影子。例如,《碟形世界》设想,多元宇宙中的所有图书馆,通过“L空间”联成一体,形成一个类世界图书馆。
另外,世界图书馆观念在科幻影片中也有体现。例如,《星际旅行》第三部第18集The Lights of Zetar(1969年1月31日首播)中的“α存储器”行星就类似于世界图书馆。α存储器相当于一个计算机数据库的集成仓储,里面容纳一切现有的文化历史和科学数据。
“科幻小说描写科技发展的后果……探索人类和人类的价值。”这些有关世界图书馆的作品,都诞生于一定的科学背景下,是来源于现实或高于现实的想象,反映人类对吞揽一切知识、可方便利用的世界图书馆的向往。因科技的进步,其不少幻想的奇迹已基本实现。例如,现在的互联网就已经接近了巴别图书馆和α存储器了。
2.2 政治学意义上的世界图书馆
在作家的笔下,还有一种政治学意义上的“世界图书馆”。例如,西班牙著名作家、诗人、哲学家,“九八年一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乌纳穆诺(1864-1936)的短篇政治神话小说《休达缪塔图书馆的革命》就反映了“九八年一代”在20世纪初热衷于宣传世界秩序的观念,而这种观念的显著象征就是世界图书馆[17]。不过,政治乌托邦式的世界图书馆观念集大成者,乃现代科幻小说之父,英国著名的作家、社会改革家、历史学家韦尔斯(H.G.Wells,1866-1946)。
韦尔斯一生痴迷于图书馆和信息网络的潜能的开发,其中知识的世界传播尤甚。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韦尔斯设计了一种政治世界图书馆,即他所称的“世界大脑”或“世界百科全书”等,并为其实现而进行了种种努力。韦尔斯的世界图书馆思想出现在他的多本著作中,其中最相关的是1920年出版的《历史纲要》和1932年出版的《人类的工作、财富和幸福》,而1938年出版的演讲和散文集《世界大脑》,则是他的世界大脑观念的汇总,给出一幅完整的政治世界图书馆景象:世界大脑即是一部崭新、免费、综合、权威、永久的世界百科全书,它可帮助世界公民最大限度地利用全球信息资源,从而更好地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韦尔斯最早精确描述他的世界大脑观念是在《人类的工作、财富和幸福》中。他写道:世界大脑是世界上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和大学所拥有的知识的混合体。在该书中,他还为这些知识的组织和传播设计了一种源于法国百科全书派的综合分类法[18]。之后,韦尔斯通过发表演讲、撰写文章等形式宣传他的世界图书馆思想。1936年11月20日,他在英国科学研究所周末晚会上发表主旨为“世界百科全书”的演讲,进一步阐述他的“世界大脑”内涵、特征及对维持世界和平的意义:“我喜欢我的世界尽可能地连贯与和谐……现代的世界百科全书应该包括选择、提炼、引用,应该在得到每个学科的著名专家首肯后认真地汇编,应该仔细地核对和编辑,应该批评地呈现。它不是杂物,而是浓缩、分类和综合。这种世界百科全书是世界上每一个智者的精神支撑;由于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原创者都可进行修改、扩充和替换,它又是不断更新、扩展和变化的……如果没有一部用类似通俗化解释本体那样的东西将人类知识保存在一起的世界百科全书,世界冲突只是表面上的暂时缓和,其他的就没有任何希望。”[19]
次年,韦尔斯为法国新版《百科全书》撰写了题为《永久世界百科全书观念》条目:“永久世界百科全书的核心是全世界书目和文献索引库的集大成。许多工作人员将不停地完善这个人类知识索引库,使之紧跟时代的步伐。这种永久世界百科全书可称为‘新型全人类大脑’,不必集中存放在某一地点。它也不会像人的大脑和心脏那样脆弱,可在世界各地精确、完整地被复制。永久世界百科全书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更不是白日做梦,只要依赖问世不久的缩微技术,很快便成为事实。基于这种永久世界百科全书的理念,是化解人类冲突、增进人类和谐的一种可能的手段,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唯一的手段。”[20]在这里,韦尔斯继续阐释他的世界大脑观念,并首次提出其赖以实现的技术基础——缩微技术。
实践韦尔斯“世界大脑”理念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37年8月16—21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的首次世界通用文献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有来自45个国家的作家、图书馆员、学者、档案管理员、科学家和编辑等各界代表参加,不仅讨论了韦尔斯的“世界大脑”理念及其践行的方法,而且还通过了一项重大决议——为了让信息能在全球广泛地被获取,缩微胶卷及其技术须得利用[21]。韦尔斯在为大会所作的演讲中指出,他的“世界大脑”理想是与会其他代表在这次会上所提议的观点之先驱,并且明确地将此次会议正在讨论的这项计划与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工作连接在一起。
另外,1937年韦尔斯还在巴黎的国际博览会和美国也发表类似主题的演讲。其中在纽约的演讲,还通过无线电广播传遍全美。在美巡回演讲期间,韦尔斯利用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进餐的机会,成功地游说美国为他的“世界大脑”计划提供资助。遗憾的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韦尔斯直到逝世时,也没能正式着手他的这个计划。
韦尔斯在不同类型的作品中涉及过“世界大脑”,这使得他的世界图书馆景象变得扑朔迷离,从而引起更大范围的讨论。针对当时出现的种种回应“世界大脑”的挑战,韦尔斯提出了解释。他的这些解释,均蕴涵着一种进化决定论,即暗示一种源自我们赖以繁衍的复杂社会序列、具有意识的超级有机体正在形成[22]。可见,韦尔斯的世界图书馆,有别于历史上那些图书馆员的世界图书馆理想,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图,正如英国学者Dave Muddiman所言:“在较为精确和历史的特定意义上讲,‘世界大脑’是一个‘现代’乌托邦,因为它不会给予我们一点有关未来的信息,而仅仅告知英国20世纪早期对信息和知识的理解程度及其意识形态。”[23]
韦尔斯的世界图书馆思想与他的科幻小说一样,是从当时的科学背景出发,由幻想到科学,从而具有现代性色彩,因为只要将缩微胶卷改成互联网,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许多数字图书馆工程,不正是半个多世纪之前韦尔斯所描绘的“世界大脑”吗?
3 当代基于信息技术的世界图书馆理念与实践
信息技术包括以缩微技术为核心的传统信息技术和以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基于信息技术的世界图书馆实践,使人类古老的世界图书馆梦想离我们越来越近。
20世纪初,缩微技术开始在图书馆广泛应用。20世纪20年代,文献的缩微品开始被图书馆收藏。1936年,缩微胶卷问世,使缩微复制品生产朝着集约化方向发展,也被韦尔斯视为当时世界图书馆实践的技术基础。韦尔斯曾描述过这种基于缩微技术的世界图书馆景象:“任何一个学生,在世界任何地方,均可以通过其书房的缩微胶卷放映机,方便地阅读任何书籍、任何文献的精确复制品。”[24]1937年8月,根据韦尔斯的提议,世界通用文献代表大会倡议,利用缩微胶卷及其技术,让信息能在全球广泛地被获取。该倡议即刻得到图书馆界的响应。例如,1937年起法国国立巴黎图书馆着手缩微复制印刷出版物;1938年,英国图书馆收藏的全部博士论文,拍摄成缩微胶片。
20世纪50年代后,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使人们对世界图书馆又产生新的遐想。例如,英国现代科幻小说家克拉克(1917-2008)在1962年出版的《未来的轮廓》中,从技术的层面对韦尔斯的“世界大脑”进行描绘:建构那种被韦尔斯称之为“世界大脑”的东西,将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世界图书馆”(World Library)的建设。这种世界图书馆基本上源自韦尔斯的“世界百科全书”概念,人们通过家中的计算机终端就可以利用它。克拉克预言,到公元2000年,这一阶段(至少在发达国家)将会完成。第二阶段,世界大脑将变成一台超级计算机,人类与它可以进行交互联系,以解决各种现实的问题。在这一阶段,“世界图书馆”会并入“世界大脑”而成为它的组成部分。克拉克预言,到2100年,第二阶段的“世界大脑”会完全建成[25]。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克拉克的预言开始进入现实的技术、法律、经济等层面。1993年,第59届国际图联(IFLA)大会的主题就是“世界图书馆:全球信息源中心”,大会对其相关国际互联网、版权和文献传递等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1995年,倡导并主持后来著名的“百万图书工程”的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Raj Reddy博士曾设想: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世界图书馆代表一个强大的观念,不纯粹是传统图书馆的电子等价物。这种图书馆是一个信息的复合体,可按需提供图书、杂志、报刊,甚至录像、电影和音乐。它花费巨大,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实现,故实现这个目标的最有效的方式很可能是真诚的国际合作。”[26]1996年8月,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在北京第62届国际图联大会上也畅想:“以网络为中心的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信息数字化技术以及计算机国际语言化技术的突破,正在把传统分离割裂的图书馆推向全球一体化、网络化的新境地。图书馆将真正地摆脱地理环境的制约,成为世界性‘大图书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个用户将成为世界所有图书馆的用户……全球的信息资源将及时、准确、方便地为公众所共享,人们不必再亲临图书馆,只要在工作地点或家里,就可通过电脑查询到所需信息,可以浏览文字信息,也可以浏览声音与图像的多媒体信息。”[27]不到10年的时间,通过那些基于数字储存、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的数字图书馆工程,如百万图书工程、世界数字图书馆、谷歌图书搜索、开放内容联盟、维基工程、古腾堡工程、欧洲图书馆,以及国内的读秀学术搜索等,Reddy、费孝通等设想的世界图书馆愿景,已接近实现。这些数字图书馆工程,均力求将任何语言的人类的知识片段,连接在一起,并储存在一个数据库中,通过互联网向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开放,可谓真正跨越时空的世界图书馆。
这种跨越时空的世界图书馆要完全实现,还存在一些技术、法律等方面的问题,如版权、图书审查制度、未出版的原稿等。尽管目前也有一些举措,如各国版权法规定文献可以合理使用,图书情报界倡导作者执行知识共享协议、科学共享协议等为代表的通用许可协议,图书情报界携手出版界、作者等共同推行针对版权保护的开放获取运动,但要真正实现世界图书馆的愿景,图书情报界还有较长的路要走,甚至为之要不惜抗争。2012年初发生在美国的互联网界抗议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2012年1月中旬,为了抵制美国《保护知识产权法》和《禁止网络盗版法案》两份法案,降低它们在国会被通过的可能,美国互联网界组织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尤以维基百科英文版在1月18日的黑屏24小时抗议活动引人注目。结果美参众两院领导人表示这两个反网络盗版案的进一步立法程序将推迟。
不过,当今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世界图书馆,由于计算机病毒、火灾和一些尚不可预测因素的存在,也可能会像古亚历山大图书馆一样的脆弱,在一瞬间神秘地消亡,正如Jon Thiem的猜想那样:“电子世界图书馆中的数据几乎全部被抹去,其未来的一切情况都不明朗,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它的持久性和可靠性已经受到挑战。”[28]因此,我们在尽力实现这种跨越时空的电子世界图书馆时,也不能过度将其神化。
4 结语
亘古以来,世界图书馆就是各界人士,尤其是图书馆员的梦想。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也是各个时期图书馆理论发展和实践进步的催化剂。古代和近代的世界图书馆,力求提供所有的人类知识,其中的每一本书是孤立的;当今的世界图书馆不仅设法提供用任何语言写作的任何文献,还要让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在任何时间能够方便获得,其中的书籍是相互联系的。世俗的世界图书馆包含人类一切有用的知识,是图书馆员永远无法实现却又执著坚守的美好梦想;文艺作品中的世界图书馆则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其中应有尽有、包罗万象。这种不同时期、不同意境下将所有书籍都包含在一个图书馆的企图,均反映各个时代人们在文化问题上的一种内在张力:能够包罗所有文献的世界图书馆只可能是非物质性的,如一种目录、一种理念,而作为物质性存在的图书馆则只能是有限的,仅仅包括了已知知识总体的局部。不过,作为一个理念、一个目标,世界图书馆已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图书馆员和其他各界人士,而且还将继续影响他们,从而推动图书馆学理论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促进人类社会科学、健康、和谐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