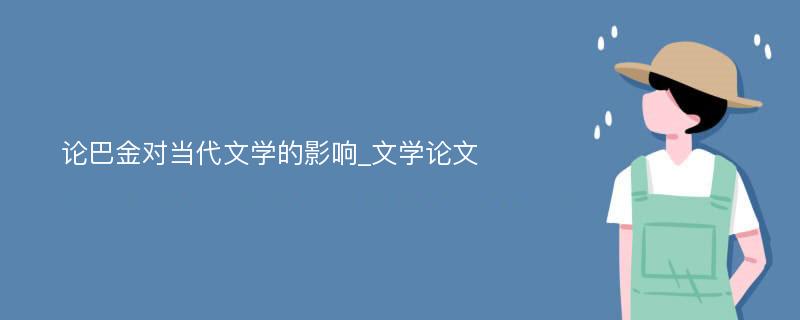
试论巴金对同时代文学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金论文,试论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成都召开的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笔者提供过一篇《巴金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论文①,主要梳理、论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施惠于巴金,即巴金所受同时代文学熏染、影响的问题。显然,这只涉及了问题的一个侧面。本文试图对另一个侧面,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如何受惠于巴金,也就是巴金及其创作对于同时代文学的反熏染、反影响问题作些探讨,以弥补前文的不足。
(一)
巴金自踏入文坛后,曾反复声明自己“不是文学家”,“不是艺术家”,直到晚年写《随想录》时仍是如此。他这样说,因为最初是由于偶然的机缘跨进文坛的,不期然成为作家而成了作家;虽然成了作家,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不满意这种生活,渴望摆脱。这种情况后来有了变化,巴金终于安于笔墨文字生涯了。但开头毕竟太重要了。巴金闯入文坛的特殊性及开始几年的创作情形,对他以后的整个创作面貌都带来影响,也使他的文学观、文艺思想烙上独特的色彩和印记。全面、系统归纳、阐发巴金的文学观、文艺思想不是本文能胜任的,我们只就主要几点展开谈谈,然后对它们发生的影响作些考察。
首先一点是对于文学功利目的和社会作用的强调。巴金踏上文坛前曾热心于无政府主义运动,迫切希望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他是在这一运动受挫后开始小说创作的。如他所说“我的文学生命的开始是在我的挣扎最绝望的时期”②,而且就在那些年里还写作了有关无政府主义的政治性著述。即是说,在写作《灭亡》等作品中的小说家巴金之前和同时,有一个社会改革家的巴金存在,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就不难理解他何以从一开始乃至终生都着重文学的功利目的和社会作用。
当然,巴金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也是变化、发展的。大致在四十年代以后,一方面由于现实生活的教育,另一方面因为作家生理、心理上趋向成熟,他意识到社会改造和人类进步的艰难不易,自然不再指望文学在现社会的改造方面产生显豁可观的奇迹。而巴金对于人类的挚爱和改造社会的愿望仍是那样强烈,这就使他深入思索如何通过文学作品同现实社会进行坚韧、深入斗争的问题,于是有了《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等作品。随着这一过程发生的,是其作品审美特征和审美力量的加强。但话要说回来,巴金在任何时候都没有离开过真和善谈美,始终不曾忘记文学应当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的信念,并毫不掩饰对于“为艺术而艺术”倾向的反感。这似乎就是当年那个社会改革家的巴金留给文学家的巴金的终生馈赠吧!
其次一点是对于文学情感性特征的强调。巴金常常直接通过文学创作达到宣泄感情的目的,他曾经说:“你不知道热情在我的自体内燃烧起来的时候,那颗心、那颗快要炸裂的心是无处安放的,我非得拿起笔写点东西不可,那时候我自己已经不存在了,许多惨痛的图画包围着我,它们使我的手颤动,它们使我的心颤动……”③并不是任何作家都愿并能通过作品较为直接地宣泄自己感情的,巴金这样做,是因为他把写作当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对待,在写作中所走的路径和生活中所走的路径是一致的,他在写作中混合了自己生活中的血和泪,暴露、表现着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矛盾、痛苦和追求。
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也是有变化、发展的。大体说来,写作前期作品时对文学情感性的认识还是有偏颇的:强调作品应有真情实感,应自然流露是对的,强调文学创作需要激情也是对的,但对如何有效地把感情传达给读者,取得圆满的传达效果却考虑不够。文艺活动——如同托尔斯泰指出的——是以这一事实为基础的:“一个用听觉或视觉接受他人所表达的感情的人,能够体验到那个表达自己的感情的人所体验过的同样的感情。”④既然是创作者与阅读者之间的情感交流,就要考虑如何更好地引起对方共鸣,如果艺术形象跟不上情感表达的需要或者不在必要的当口对感情加以控制,就难以取得好的传达效果。巴金前期的作品正有这样的缺陷。但在后期创作中,明显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在一篇创作谈里自述说:“在后期的作品里我不再让我的感情毫不节制地奔放了,我也不再象以前那样唠唠叨叨地讲故事了。我写了一点生活,让那种生活来暗示或者说明我的思想感情,让读者去作结论。”⑤
再次一点是对于文学“无技巧”境界的强调。既然巴金是意外闯进文坛的,开始创作时免不了从社会改革家的角度看待文学,何况郁积的感情使得他迫切需要找到喷发口,那么对于艺术形式和表现技巧的相对忽视就是自然的。我们从作家当年的文章中可以经常读到这一类话:“我完全不是一个艺术家,因为我不能够在生活以外看见艺术,我不能够冷静地象一个细心工匠那样用珠宝来装饰我的作品。”⑥虽然如此,巴金那时仍写出了一些很不错的作品,原因在于因丰富的生活、感情积累造成的作品内容的新鲜、丰满和独特。
到四十年代以后,随着作家思想变得成熟和深沉以及上面说的文学观、文艺思想方面的发展,他在艺术表现方面也迅速进步,那时创作的《憩园》《寒夜》等小说已实现了思想与艺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说它们达到了“无技巧”境界并非溢美之辞。所以能实现这一飞跃,我们以为原因有二。一是长期艺术实践造成的高度熟练,如他谈“无技巧”问题时说的:“什么是技巧?我想起了一句俗话:‘熟能生巧’。”二是作家事实上已注意到了技巧,只是因为更看重作品思想感情的表达和生活内容而没有特别加以强调,这样说不是没有根据的,前引巴金话里“不再让我的感情毫不节制地奔放”、“不再象以前那样唠唠叨叨地讲故事”而让生活本身来“暗示”,难道说的不就是传达技巧?
巴金文学观、文艺思想还多,但最能显示其独特性的却是以上几点。这些主张、思想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自然不无局限——最初孕育、萌芽阶段尤其如此。但从总体上和最后完成阶段看,却具有开放、包容广阔的特点。巴金同时喜欢各种流派的作家、作品,自己的创作也兼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钢格倾向,他认为创作应有自己独特的东西、每个人应用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语言来表达,又说不受文学规律限制、不怕被人赶出文坛等,都说明开放、包容广阔是他文艺思想最本质的特征。巴金这种独特、自成一体的文艺思想,是他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并有着广泛的影响。巴金对于萧乾的启迪、帮助是突出的例子。萧乾创作的起步阶段,巴金常对他说这样一句话:“写吧,只有写,你才会写。”这种强调艺术锻炼、鼓励大胆去闯的开放思想,使萧乾受益非浅。萧乾还谈到读了巴金一篇文章后的收获:“一个由刻苦走上创作道路的前辈近来曾作文否认灵感和天才的存在。这不仅是破除了一件寒人心的、帮人偷懒的迷信,且增加了正在踌躇的人的勇气。”⑦巴金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文学应关心社会和人生、有益于人的思想更对萧乾有积极影响。巴金欣赏萧乾的短篇《邮票》,但同时向他指出:应把视野放宽、把心放宽,不要把自己关在个人的小天地里,应该更多地关心同胞以至人类。这样,作品才有力量。在读过《矮檐》后,巴金不劝他写点更有时代感东西。萧乾后来回忆说:“我初期的小说,写的大都局限于我早年的个人生活以及童年的一些见闻。结识他之后,我一直努力冲破那个小天地。在带有象征意味的《道徬》中,我又反过来劝读者,不要沉醉于安乐窝中而忘记世界的危境。我还写过几篇揭露教会学校的小说。后来在《答辞》中,我曾不厌烦地提醒比我更年轻的朋友们‘不要只考虑个人的出路’,而忘记大时代。”⑧巴金熏染了萧乾,萧乾又影响着比之更年轻的朋友,他的文学主张、见解就这样象震荡的水波那样,一层层、一圈圈地扩散开来。
一度与巴金接触颇多的田一文,也曾受到许多教益。田一文很早就从巴金作品里吸取营养,理解前进的人生和奋斗的生活。巴金创作的情感性特色及其主张使他“领悟到作家自己要有那种燃烧的激情才能点燃读者的感情。”⑨解放后巴金给田一文看稿,曾针对他感情表达方面的缺陷指出:“你自己受到感动,却不能通过人物、通过具体事件,来感动读者。只说自己如何感动(我也常犯这个毛病),却忘了如何使别人感动。”还批评说:“不能说这些文章没有感情,但感情不深,你只触到很表面的东西,有些地方只是在堆砌漂亮的文字。”⑩这些话,是上述文艺思想的体现和深化,由此可见作家文艺思想的连贯性,也可见出它们对后来者的熏染、影响。
巴金近年提出的“无技巧”主张,更在文坛引起关注和热烈讨论,成为许多作家的共识。张贤亮就很赞同这一见解,曾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印证说:“恰恰是在我写到我不熟悉的生活时,才最需要运用我们所说的技巧,以一般的技巧来掩盖生活的不足。在我写到熟悉的生活那部分,丰富多彩的形象竞相奔来,甚至在视觉、听觉、嗅觉几种感觉形式上都同时重现过去的记忆,这时,我根本不考虑,也无暇考虑技巧。而最后的效果证明,这样的部分却是读者认为我表现了自己的‘艺术功力’的地方。”(11)诗人公刘谈到对朴素美境界的追求时也说:“我非常信服巴老的一句名言:无技巧是最高的技巧。我相信巴金同志不只是单指小说而言,他指的是整个的文学领域。”(12)巴金通过几十年创作实践归纳、总结的这一新鲜、富有辩证法的艺术主张,已经、也必将在文学界产生深远影响。
(二)
对于封建制度及其观念形态的否定、批判是贯穿巴金整个创作的重要、鲜明的思想线索。这其实是历史赋予二十世纪中国先进分子的最重要的使命,也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和悲壮的景观。作为一个作家,巴金当然主要通过文学作品,在思想、观念形态方面对封建主义展开斗争。他是继鲁迅之后,又一个具有彻底反封建精神的作家,一个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与封建的东西进行了坚决,持久斗争的战士。无论《家》《春》《秋》还是《雾》《雨》《电》,无论《憩园》《寒夜》还是晚年的《随想录》,人们都可从中读出反封建三个大字。
巴金创作的这一思想主题以及采用来表现的独特的题材和视角,对后来的写作者产生很大影响。《家》《春》《秋》——尤其《家》,是巴金创作中影响最大的力作,主要通过“家”的题材和视角来透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进行反封建的启蒙和呼唤。这一创作特点,在著名剧作家曹禺那里得到直接而鲜明的表现。曹禺的《雷雨》虽然很早就在构思、酝酿中,但大体成形是在《家》于《时报》连载的一年之后。剧本描写一个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罪恶、危机以及它的崩溃,成功塑造了专制家长周朴园,美丽、个性和生命遭受严重压抑的年轻女性繁漪,忧郁、怯懦的大少爷周萍,以及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女性侍萍、四凤等形象,通过他们间的矛盾纠葛和冲突对压抑、摧残人性的旧家庭和封建势力进行严正的控诉。写于四十年代的《北京人》是《雷雨》主题的发挥、深化,集中表现曾家这个没落士大夫家庭内部的各种矛盾,通过描绘旧家庭统治者曾皓、曾家长子曾文清和寄养到曾家的名门世家之女愫方等形象,揭露封建统治对于人性、人的灵魂的迫害、吞噬,展示其必然崩溃的命运。贯穿于曹禺这两个剧作的主题是:“摧毁黑暗社会吧,让人成为人!”我们的研究者以往更多注意曹禺作品受到《批出幽灵塔》等二十年代剧作的影响,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与巴金旧家庭题材作品的联系。实际上小说和戏剧两种不同体裁的文学类型也是相互渗透、影响的,巴金与曹禺由于相近的出身、创作个性以及相互间的密切关系,使得这种渗透、影响变得更为可能。
这样的思想主题及透视视角在其他现代作家的创作中也有反映。首先应提及《前夕》。靳以这部长达八十万言的长篇描写抗战爆发前几年里的动荡生活,主旨除了表现中国人民——尤其青年知识者在国家、民族危亡关头的振作、奋起外,对封建家庭腐败的揭发及它之不可挽回的命途的揭示也是重要内容。它集中写一个黄姓的大家庭,写了他家众多成员在封建重负下的各种不幸和痛苦精神世界。如果说小说在地表现振作、奋起的主题方面存在一些研究者指出的“反映生活比较浮面,艺术上缺乏感染力量”等缺陷的话(13),那么在传达后一主题时却是相对成功的,它所塑造的静宜、菁姑等人物也因个性的独特和发掘的深入让人难以忘怀。除了题旨、表现视角的接近,《前夕》在人物形象塑造、情节和细节组织及对人物内心世界描绘等方面也可见出《激流》的启发。
其次应提到《财主的儿女们》。与《前夕》相同,路翎这部小说的主题蕴含也不是单一的,主要探索中国特定历条件下青年知识者的精神世界,同时表现旧家庭制度的没落。后一主题在小说的上部得到充分展开,它以一二八事变后激烈动荡的社会生活为背景,全面描写苏州巨富蒋捷三家的衰败、分崩离析:二子的叛逆出走,长媳的弄权,蒋家的入不敷出,蒋捷三无可奈何的死,对于家产的争夺和诉讼,长子的沦为乞丐和亡命……作为一部表现中国家族生活及其子女命运的长篇小说,《财主的儿女们》既烙有《红楼梦》的痕迹,也可见出巴金作品对之的熏染。这种熏染也不但是主题、题材方面的,同时包括了形象创造、情节处理等。如两部小说写曾经不可一世的旧家长死亡时,都安排了与“家”的叛逆者——一是高觉慧,一是蒋少祖——会面的情节,写了前者的颓唐、慈爱和相互之间的某种谅解;都安排了他们尸骨未寒,子女们就为家产哄闹的情节,写了相互之间的攻讦和明争暗斗。对于这种相似性,似乎只能从影响角度加以解释。
以上是从主题和题材、视角的连结上,较为全面地汲取巴金旧家庭小说的创作经验。但文学创作的影响关系是错综多样的,在更多情况下,后来者往往只是从某一方面、某一点上受到既有作品的启迪和感悟。他们有时主要在题材、视角上接受启发,如《四世同堂》。这部小说也反映抗战时期的社会生活,但选择来透视的是北平一个下层市民家庭和它所起居的那条小胡同里的一些人家,老舍主观上又要更多展示传统文化、民族性格中正面因素的上扬,因而《四世同堂》并不必然包容反封建主题。但巴金作品对之的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主要是:以一个祖孙几代的大家为中心,以他家与其他一些人家及社会的连结来观照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再推广些说,象赵树理这样的作家也不能撇清与巴金小说的关联,只是赵树理写的是小家,而且是农民的家,如《小二黑结婚》、《孟祥英翻身》、《传家宝》、《登记》等。虽然巴金是写大家、封建地主的家,赵树理是写小家、农民的家,但都以家庭为立足点,以家庭生活为基本内容则是一致的。赵树理解放后曾谈到受巴金启迪准备写《户》的打算:“尽管功劳工分是按人记的,但到了分配时,仍然是以户为单位的。所以,巴金写了一部《家》,反映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写一部《户》,反映农民的问题。”(14)赵树理后来没有写《户》,但在业已写成的《小二黑结婚》等作品里,不已部分实现了“以户为单位”“反映农民的问题”的意图吗?
如果单把主题抽出来考察,则巴金作品贯穿的反对封建婚姻和旧道德的思想蕴含甚至也影响了新时期创作。在现代作家中,同是反封建,巴金更侧重批判封建婚姻制度和旧礼教,正如他所说:“为了反对买卖婚姻,为了反对重男轻女,为了抗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用笔整整战斗了六十年。”(15)他小说的这一特点与鲁迅不尽相同,也是其他现代作家难以比拟的。而在新时期文学创作中,表现这一思想主题的作品仍有一个相当的数量。在《未亡人》《挣不断的红丝线》里,我们可以看到现实生活中由权力、金钱,政治偏见和伦理习俗织成的线和网既可以剥夺妇女改嫁、追求爱情的正当权利,也可以使许多没有爱情作基础的婚姻变成“天作之合”;在《天云山传奇》、《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里,可以看到包办婚姻也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只是说辞已不是“门当户对”,而是“报答救命之恩,服从革命安排”;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远村》里,可以看到贫困和愚味是如何扭结在一起制造出一幕幕新的爱情悲剧……自然,这些作品对新式包办婚姻和旧意识的批判具有新的视角和艺术追求,但在大的方面说却继承、借鉴了巴金等作家的反封建传统和特色。
在角色设置和形象创造方面,后起作品也曾从巴金那里受益不浅。上面提到的几部描写大家庭生活的作品,不约而同地用力塑造起长子长孙的形象(也有是长女的),写了他们在对立力量之间的逡巡徘徊,写了他们的复杂性格和痛苦内心。这在曹禺那里是周萍、曾文清,在靳以那里是黄静宜,在路翎那里是蒋蔚祖,在老舍那里是祁瑞宣。这些形象既有可厌可恶的一面,也有善良可爱的一面,作者对他们所取的态度也既憎又爱,颇为矛盾。这种设置、表现模式,与巴金对高觉新的处理一脉相承。
上述形象中,静宜、瑞宣的情况与觉新尤其相近。静宜作为长女,早年也有舒适的家和快乐的少女生活,有自己的理想,她甚至有幸读完了大学。但那时家是在衰落的路上,她意识、性格中又太多浸漫了传统的东西,为了整个可怜的家决定牺牲个人幸福,象男子那样担起全家的责任。于是整天陷入琐碎、烦人的事务中,渴望摆脱,却不能,只好低声抱怨。她常常象夹在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母亲为治病请来和尚做佛事,受过高等教育的她明知无用,但为了母亲心安、自己心安竟然违心依从了,并且代母亲磕统し跪。事后受到弟妹们的严厉责备,她感到委屈,抱怨“谁都不关心这个破落的家”。虽然巴金写的是长子长孙,靳以写的是长女,但可以肯定,后者的塑造受到了前者的启发。顺便提一下,做佛事也与《家》里捉鬼的情节相似。
瑞宣虽然是下层市民家庭的长子长孙,但也象觉新那样早早挑起了支撑门户的担子。他也常常委屈求全——用老舍小说里的话说是:“求全盘的体谅”。他其实早知道恋爱神圣、结婚自由,仍违心娶了父亲给他定的那门亲,因不忍看祖父、父母的泪眼,也考虑到未婚妻的难处。娶时他不无痛苦,笑自己软弱,但看到长辈们脸上由忧愁改为快活,又感到一点自我牺牲的骄傲。他也常常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精神上十分痛苦,只是让他不易作出抉择的究竟“尽忠”还是“尽孝”。日本人占领北平后,老三劝他一同出走,他不能,他支持弟弟去“尽忠”,自己留下来“尽孝”。但他是“有思想有本事”的人,这样的选择让他感到沮丧、惭愧、不甘,于是常常自责、自我折磨……老三瑞全要走时,瑞宣最初劝他等一阵,但看他决心已定,就帮他出主意混出城、为他筹钱。读者不难看到,他与《家》里觉新的处境、性格极为相象,某些情节和细节也相近。
巴金塑造的女性形象,似也对后来者不无影响。在曹禺剧作中,愫方是与繁漪、陈白露不尽相同,更具民族传统性格和色彩的女性。她温和大方,逆来顺受,善待一切人,是一个具有黄金般内心的倩美女子。由她,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家》中的瑞珏。尤其在善良这点上,她们对自己所爱的男子都有一种完全忘我的境界。瑞珏悉知觉新与梅深心相爱的隐情后,一无妒嫉或责备,倒设身处地为他俩着想:“我真想我走,让你们幸福地过日子。”愫方更是痴心,文清暂时离家时,替他侍侯上人、为他保管字画、喂鸽子,甚至连他不喜欢的人都觉得应该体贴、喜欢和爱。瑞贞问这是为哪桩,她敞开了心扉:“为着他所不爱的也都还是亲近过他的!”在这两个女性身上,都有某种理想主义色彩。而在路翎塑造的蒋淑华、靳以塑造的黄静婉身上,又可多少见出梅的影子,她们全都青春早逝、婚姻不尽如意,性格内向、忧郁、多愁善感。
(三)
巴金说他是中国作家中受西方作品影响较深的一个作家,是照西方小说的形式写处女作,以后也顺着这条路走去。这在很大程度是指对人物内心世界描写的注重,尤其直接描写方法在作品的大量、广泛使用。以《家》对鸣凤得知要嫁给冯老太爷“做小”一直到她跳湖自尽看,巴金着眼于人物内心生活的各个时刻,主要采用直接描写方法(辅以某些必要的动作、环境等描写),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这一不幸女性在人生最后一刻全部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类似的描写在巴金小说里时有可见。即使在一些小的情节、场面展开中,巴金也喜欢把各别人物做某件事、说某句话后面的内心想法和情绪变化交代清楚。如果说到巴金小说的风格、艺术特色,这是不能不提的。
巴金作品的这一表现特点,有人认为是缺乏长族特色。其实,民族的东西也在不断丰富、变化的。从中国文学日后演进的趋势看,这样的写法还是被普遍认可、接受了,而且有新的发展。中国文学描写、表现手段的这种进步,是与新文学众多作家对外国文学的大胆借鉴、实践分不开的,巴金则是其中突出的一个。
从实际创作看,上面论及的靳以、路翎的小说似乎也在这方面承袭了巴金的路子。《财主的儿女们》艺术上最大的特点,就是注重人物内心世界描写,时时注意揭示人物言语、行动背后细微、复杂的内心活动,展现人物内心情绪的激烈冲突和急剧变化,绘出人物特定时刻的心理过程。如王桂英亲手掐死她与蒋少祖的私生女那段描写,虽然王桂英是一个与鸣凤出身、经历、性格都不同的不幸女性,但由于两位作者都笔墨淋漓地展现了她们在特定瞬间丰富、完整的心理过程,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笔者还是能把她们联系起来,而且隐约感到后一描写受到前者的滋润。
巴金后期作品的心理描写更趋园熟,减少了静止的剖析,增加了人物各种感受和细微、隐秘内心活动的揭示和描绘,对人物心理过程也有更细致、更完整的展示。这在《寒夜》里表现得尤为充分,可以说是一部“准意识流”小说。笔者当年读王蒙的《春之声》等小说,就感到与《寒夜》有相通之处,及至见到他论及应注重写人物感受的创作谈,禁不住发出感叹:简直就是对着《寒夜》说的!王蒙原话的大意是:在写作时不但要求助于自己的头脑、心灵,而且要求助于自己的皮肤、眼睛、耳朵、鼻子、舌头和每一根神经末梢。例如写到冬天,写到寒夜,如果只是情节发展的需要或是展示人物性格的需要使你决定去写寒冷,而不去动员你的皮肤去感受这记忆中的或假设中的冷,如果你的皮肤不起鸡皮疙瘩,如果你的毛孔不收缩,如果你的脊背不冒凉气,你能写得好这个冷吗?(16)——如果人们从这样的角度去重读《寒夜》,相信不难发现王蒙一些小说与它的联系。如确乎如此,笔者在《巴金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中提出的以下看法又多了一个佐证:同时代的中国文学往往象桥梁和触媒那样,起着沟通、化合中国作家与外国文学间关系的作用。
抒情,是巴金风格、艺术表现的又一重要特色。巴金是一个敏感、长于感受和体验、具有诗人气质的小说作家,这使他的绝大多数作品流贯有一种细腻哀婉的抒情调子。有些中短篇小说简直就是诗,整个故事被消融于诗的结构和氛围里,如《春天里的秋天》等。《激流》等长篇小说虽以叙事为主,但诗一般的人物情怀抒写和环境、氛围描写比比皆是。这种抒情风格,在《前夕》、《财主的儿女们》里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四世同堂》虽然与这种风格异趣,但巴金的这种抒情风格似乎在更大范围里激发、影响过老舍。我们知道,老舍创作中有两种几乎相反的风格:“或者极俗、白,不点染一点‘风月’,或者诗情浓郁,甚至采用‘诗’的形式,如《月牙儿》《微神》。”(17)短篇小说《微神》是这种风格的发端,它纤柔、精美、洋溢诗的色彩和调子,揭载于1933年10月的《文学》杂志。之后便是篇幅较大的散文诗式的中篇——《月牙儿》和《阳光》,分别载于1935年的《国闻周报》和《文学》。而巴金早期创作中堪称诗体小说的《春天里的秋天》在1932年即发表了,另一抒情气息甚浓的短篇——《月夜》载于1933年9月的《文学》。老舍何以会在三十年代用另一付笔墨写小说?除了有的研究者指出的“他的创作转为以悲剧为基调”的自身原因外(18),是否也与同时代创作、尤其巴金类似作品的激发有关呢?我们以为是那样。巴金和老舍都在《小说月报》同卷同号发表各自的处女作成名,三十年代前期又由文的认识进到人的认识,老舍还写过巴金作品的评论——这些都为这种激发、影响的可能存在提供了某种信息依据。
注释:
①《文艺研究》1992年第2期。
②《爱情三部曲》总序。
④⑥《灵魂的呼号》。
④《艺术论》。
⑤《谈我的短篇小说》。
⑦《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
⑧《他写,他也鼓励大家写》。
⑨《我忆巴金》,四川文艺出版社。
⑩《巴金书简》,四川文艺出版社。
(11)《写小说的辩证法》。
(12)《谈谈我自己》。
(13)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14)引自黄修己《赵树理评传》。
(15)《病中集·买卖婚姻》。
(16)引自陈望衡《以形写神》。
(17)赵园《谈老舍〈微神〉》。
(18)范亦毫《论〈月牙儿〉及其在老舍创作中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