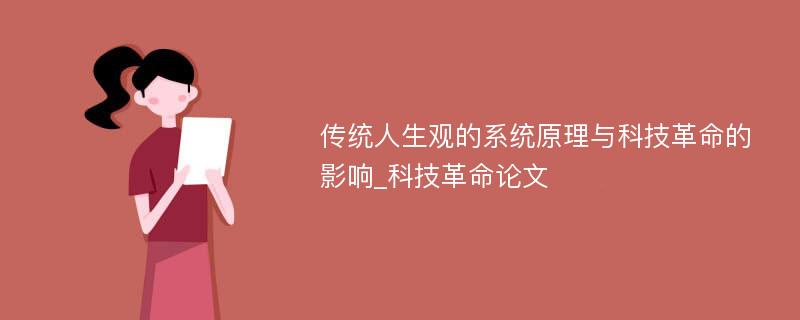
传统人生观的系统原理与科技革命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生观论文,原理论文,传统论文,科技革命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就近现代科技革命对传统人生观的作用和影响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在论证了中国传统人生观的系统原理及其主要特征之后,就近代科技革命与现代科技革命对传统人生观的作用作了客观的分析,其中也对西方与东方传统人生观念的表现进行了必要的比较。最后,从未来的高度对新的文化整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和影响是举世公认的。一般来说,这种作用和影响表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是精神层面,它通过建立和完善科技理论体系改造和指导了我们原有的思想模式和方法,即文化的认知系统。渐次这种认知系统也影响或决定了人类的价值观念,即文化的价值系统;其二是物质层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科学技术逐步转化为生产力,创造了各种生产工具及其产品,它改变了人们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的各种结构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即文化的物质系统。本文希望通过对传统人生观的系统特征及其变化的分析和讨论,以阐明科技革命的巨大作用和影响,以及建设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的思路。
1 传统人生观的系统原理
传统人生观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中国传统人生观,就是一种相比较其他民族的、由中华民族长期创造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相比较西方传统人生观,中国传统人生观在最初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较少受到宗教那种否定和超越现实的强制作用,而更多地肯定和接近现实生活,因此便构成了传统人生观的基本结构和主要特点,即在精神层面上,表现为人生的认知系统和价值系统两个部分。一般来说,这两个系统是紧密相关的,认知系统是对于世界和人类的总体的理解和把握,它解决的是人类在世界中的位置,人类和世界关系的事实问题;价值系统是对于人类应该如何生存以及存在的目的的理解和把握,它解决的是人生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的问题。而且,这个认知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价值系统。与此相对应,传统人生观的认知系统和价值系统又分别表现为两个最为主要的特征:一是系统的观念;二是人文主义。
在中国传统人生观的认知系统中,“系统的观念”的特征是与其认识事物的整体思维模式相关联的。所谓整体思维模式,即人们在考察事物时,往往着眼于事物的整体性,擅长于直觉、综合以及相互联系的思维方法。由这种思维模式去考察人生,其人生观就表现为两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其一:人生于自然,与其自然不可分割。这种思想无论是在老庄道家学说中,还是在孔孟儒家思想中,都不难看到。《庄子·知北游》中就有:“舜问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所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委顺也;子孙非汝有,是天地委蜕也。”儒家诸子虽然十分重视人的地位及其作用,但也没有否认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即便是宣扬天人二分的荀子,同时也强调了“顺天”的必要。到了董仲舒的汉代,儒学又走向了“天人合一”:“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春秋繁露·立元神》)。这种自然人生观同西方宗教人生观中那种上帝、人类、自然三分三立和互相竞争的观念是截然不同的(参见铃木《禅与生活》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88页)。其二:人活于类,与其群体不可分割。现代新儒家之先驱梁濑溟较早地提出:“中国人不当他是立身天地的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4页)。在这里,梁不是说中国人缺乏个性,而是强调中国人注重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中国人似乎清楚,无论从古至今,妇儒老幼,个人的生活总离不开他那个“群体”或“种类”,即一种较早的“社会”的概念。中国人不善于将“自我”看成是一个孤立的、抽象的和不同他人相联系的个体,而是一个生活在既定社会组织和家庭结构中的一分子。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每个人都生活在既定的君臣父子的关系之中,臣之谓臣,是相对于君而言;子之所谓子,是相对于父而言。个人的事一般都是大家的事,大家都必须按照一定的规矩办。这同西方传统中那种依赖上帝,“一旦离开了上帝,大家就变成了一个个手足无措的个人”的人生观念是截然不同的(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17页)。诚然,中国人的这种“系统的观念”在封建专制的背景下,容易衍生出盲目从众、泯灭个性、排斥异端等消极的后果,但这种观念从文化本质上来说,主要还是为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在中国传统人生观的价值系统中,“人文主义”的特征是极为明显的。虽然,我们已指出,中国人认识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个人是大家的一部分,并非说中国人忽视了以人为本的生活。恰恰相反,在中国人的传统人生观中,更为关注人类生活本身,我们称之为中国人的人文主义。中国人的人文主义同西方的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有所不同,后者是对宗教人生观的背叛和对古希腊传统文化的复归,前者则代表着一种具有中国传统色彩的人生处世哲学;后者往往讨论的是应该以人为本还是以神为本的本体论的问题,而前者则是执著于应该以什么态度和方法去领略人生及其价值。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当西方人因为一些形而上的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而中国人则更多地以其直觉去“享受淳朴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的快乐和社会关系的和睦”(林语堂《中国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2页)。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中国人善于追求一种具有宁静和谐调的人生价值。因为中国人知道,与大自然相比,人毕竟是非常渺小的一部分,所以中国人不象西方人那样狂妄,要与自然比美争辉,要征服自然,而是希望在大自然的统一运作下去体会人生。从这一角度去理解传统的中国人那种悠然而简朴的生活,就能使许多困惑的西方人茅塞顿开。例如,中国人烟酒茶三大文化的发达,更有助于中国人那种自由自在地去享受人生的快乐,充分体现传统人生的内涵。在处理人与大家的关系上,中国人追求一种长幼有序,君臣有分,夫妇有别具有稳定结构的人生价值。这种人生价值观念要求人们的行为方式按照既定的规范来进行,人们从中享受一种以家族为核心的亲疏、远近、轻重匀称的伦理生活。在中国人看来,那种离开群体靠个人去奋斗的生活方式是幼稚和危险的;改变目前的生活环境,不论这种改变能给人带来多么大的好处,也很难令人接受。所以,在中国春秋战国变革之际,孔子曾提出“克己复礼为仁”,关键在于对一种传统人生价值观的关怀(参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总括中国传统人生观中的人文主义特征,其要义就在于适当处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一体关系,这同西方逐步发展起来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是根本不同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里我们所揭示的中国传统人生观的认知系统和价值系统及其特征,是建立于人类文化的物质系统基础上的,即“系统的观念”和“人文主义”特征是同古代生产技术及其小农经济生活紧密相关的。人类文化的三大系统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以体现出文化系统的总体效应。同时,强调这两个主要的特征,并不等于说在任何时代和任何环境下中国人都会按照这种模式去生活,而是在于强调一种传统文化的潜在力量,以及人生价值取向和目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会造成新的矛盾和进行新的整合。
2 近代科技革命的影响
一千多年的中世纪历史,整个西方社会笼罩在上帝的观念之中。人们背负着与生俱来的“原罪”。通过忍受和忏悔,试图达到理想的彼岸。宗教告诉人们,上帝是原本的存在,是真善美的化身。为了强化这种宗教传统观念,经院哲学借助于托勒密的天文学和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对自然规律作了很多牵强附会的解释。例如,上帝缔造人和万物的学说,使人们相信人是万物的中心。然而,随着西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科学技术终于有了突破,即被称之为近代科技革命的理论发展。首先,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颠覆了长期以来的托勒密“地心说”的天文学体系;其次,由伽利略创造的物体动力学理论,也打破了亚里士多德的许多理论教条。第三,到19世纪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发表,彻底粉碎了上帝创造人和万物的神话。这种科学技术的变革终于向人类宣布:上帝是不存在的。因此,人们需要重新考虑人的尊严、人的利益、人的幸福和人的价值问题。因此,古希腊那种“人是万物的尺度”的理性主义的传统得到了复归。表现在人生观上,即每个人都是平行和独立的个体,从来就没有什么上帝,人类必须依靠自己而生活。
需要指出,这种对宗教传统人生观的颠覆,与其说是来自近代科学技术的具体内容和方法,倒不如说是西方人文主义者借助于科学技术的新观念,对宗教传统人生观的怀疑和否定,是一次具有启蒙意义的价值革命——上帝死了,人的地位自然也应该提高了。然而,如果真的要以近代科技革命的新观念来注释人的地位的话,那么人的地位并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哥白尼认为,人们居住的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环绕太阳旋转的一颗行星;达尔文认为人与生俱来并没有多么珍贵,而是其它动物不断演化的结果。所以,正如科学史家丹皮尔所指出的:“哥白尼的天文学不但把经院学派纳入自己体系的托勒密学说摧毁了,而且还在更重要的方面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和信仰”(《科学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74页)。
较为类似的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近代西方科学和民主的传播,基本上也是这种价值革命的全盘引进。对中国传统人生观发生作用的,并非是近代科学技术的具体内容和方法论本身,而是对传统人生观某种僵化价值系统的反动。因此,我们可以说,“五四”前期的中国人,与其是接受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倒不如说是接受了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念。不难看到,在“五四”期间,各种思潮云涌中国,尤其是青年学生表现了一种反抗封建传统和要求民主自由的解放精神。然而,我们同时也应该认识到,这些以强调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带有“全盘西化”倾向的各种思潮,虽然有助于推动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但还不能解决中国传统人生观中更深层次的认知系统的问题。事实上,对于近代科学技术本身来说,无论是牛顿力学还是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是对传统人生观中“系统的观念”的支持而不是否定。牛顿力学则把万事万物都归结为一个力的世界系统,在宇宙中,没有一个不受万有引力作用的单独的个体。这对传统中国人那种系统的观念则是一次物理学的论证;此外,达尔文那种生物渐变的进化论思想,同样可以视为是对传统观念中“人是自然一部分”以及“人文主义”的生物学的论证。卢梭说过:“人是生而平等的”,但达尔文指出:“人在他的身体的一切部门上面,和在他的心理能力上面,都不断呈现出个人的差别”(《人类的由来》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20页)。而这一点,与传统中国人所追求的那种体现差序结构的价值观念则是不谋而合。也许正是有了这样深层次的原因,传统人生观才有助于我们在“五四”后期逐渐摆脱了个人主义价值观,从而转向马克思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
诚然,近代科学技术革命不仅表现在它的启蒙运动的作用,而且由于它能够较快地转变为生产力,对传统人生观施加了强大的影响。应该看到,近代科技革命及其物质成果,对中国传统人生观的价值取向来说,起到了某种相反的作用。因为欧洲的工业革命,从蒸汽机到内燃机,从机械到电力时代,都大大改变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物质经济基础和传统的生活方式,因此也必然会对中国的传统观念发生重大的影响。首先,机械化的生产,创造了我们社会生活的统一模式:一样的作息时间,一样的行走穿戴,一样的房屋建筑…,因此会给我们传统中那种追求适度、谐调和悠然的生活带来枯躁和乏味的感觉。其次,商品经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从而改变了原先那种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商品经济的一个结果就是扩大了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使得一部分人变得富裕而贪婪;另一部分人贫穷而痛苦。这种在利益上的矛盾和变化,直接动摇了传统人生观中那种超越功利的价值取向。第三,机械电力以它不可阻挡的力量开进了我们传统的田园诗般的境界,打破了山乡原有的宁静。森林大量被砍伐,土地大量被侵占,人与自然的界限愈加分明了。这种由工业化直接带来的前所未有的世俗化给人们提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人生课题:怎样处理由科技革命引发并加剧的人与其物质利益的关系?近代科技革命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功利时代,追求物质的满足已成为人们最重要的事情,而正是这个特征,在传统人生观中却是得不到足够重视的地方。
由上可见,近代科技革命给中国传统人生观所造成的影响是极为复杂的。但有几点较为明确:一是近代科学技术伴随着西方价值观念对中国传统人生观中的封建主义成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否定;二是近代科学技术的具体内容和方法对中国传统人生观又提供了新的支持;三是科学技术的物质成果对中国传统人生观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动摇作用。
3 现代科技革命的新整合
正当近代科学技术的思想逐步深入人心之时,现代的科技革命及其成果也接踵而来,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更为突然。众所周知,20世纪科技革命是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发展为先导的。现代物理学终于动摇了近代物理学的完满大厦,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近代机械论的宇宙观和达尔文进化论的某些思想,也使能量守恒定律出现了悖论。因此,人们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并产生了新的价值观念。然而,在目前看来,对传统人生观发生影响的,主要还在于这种科技革命所表现出来的物质力量,即科技革命对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发生的实际影响。
现代科技革命的标志是微电子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它使得“信息”同“物质”与“能量”一样,构成人类世界不可缺少的元素,所以西方一些学者称之为“后工业社会”、“第三次浪潮”或“信息社会”。尽管目前人们对信息社会的实质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是关于信息社会的若干特征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同。这些基本特征是:(1)高度发展的信息技术;(2)全面高度的自动化;(3)建立了全社会的高度网络系统;(4)信息的重要性大于材料和能源;(5)在产业结构中,信息产业即第四产业占据主导地位;(6)在社会产品的总价值量中,信息价值越过了有形物价值;(7)社会的产业组织形式,主要已不是制造有形物的工厂,而是信息中心。在以上七个方面,前四个方面属于生产技术方面,后三个方面属于产业结构方面。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这种根本变化,必然会带来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及其它上层建筑的相应变化。那么,这种社会结构尤其是生产结构的重大改变对传统人生观将会发生怎样的影响呢?
第一,人们彼此联系的观念得到了加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人们的生产劳动的时间和地点虽然可以相对地分散和自由,但同时因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之间彼此的相互联系却更为紧密了。这种变化无论对于西方所强调的独立和平等的人生观念,还是对于中国传统人生观中那种“系统的观念”都发生了新的整合作用。一方面,西方那种主张人与人应该绝对独立自由的观念遭到了进一步的削弱,因为人们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依赖是信息社会的一大特征。当然,这种互相依赖只是削弱了人的个性而并不是取消了人的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人们这种彼此联系性质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会继续强化中国传统人生观中的“系统的观念”,从而强化了那种个体对整体的某种依赖性。当然,由于信息社会的特点,人们之间的彼此联系是通过一种信息网络系统而建立的,这使得建立一种在信息生产基础上新的公有制成为可能。这又与传统人生观中那种追求差序格局的理想模式有着很大的不同,具有显著的民主和平等的性质,因而使得传统人生观中那种不平等的以家庭为核心的伦理结构遭到进一步的削弱。在传统的差序结构中,人们彼此的互相联系是以血缘、亲朋、师徒关系为主的纵向联系,而“网络组织提供一种官僚制度永远无法提供的东西——横向联系”(奈斯比特《大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1页)。另外,信息社会增强了人们对社会的参与意识,这对于传统人生观中那种追求清淡寡欲和无知归隐的隐士式的人生价值观也是一次很大的冲击。
第二,人们的需求有了快速的增长。我们知道,人们的需求取决于人的欲望程度。人们的这种欲望并不是仅仅由主观所决定的,而且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在客观方面,有两个因素决定了人们的欲望水平:一是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二是信息交换水平。在信息社会里,这两个客观条件都有了高度的发展,因而必然地会促进人们新的欲望的产生,从而影响到人们的传统人生观念。就西方传统人生观来说,人们之所以要劳动和创造,通常有两个动力:一者是为了满足某种物质的欲望,或为了满足创造本身的欲望;二者是宗教改造信念的支持,比如马克斯·韦伯所坚持的那种“唯生产而生产”和“唯赚钱而赚钱”的宗教精神,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为了达到彼岸世界的一种特殊欲望。在这种情形下,劳动本身不是目的,通常是满足欲望的必不可少的手段。然而,就中国传统人生观来说,其情形与之西方有着很大的不同。由于中国人极为重视人生的存在方式及其终极性价值,对于为了满足物质欲望而劳动的那种功利的人生价值观较为轻视。所以,一般来说,如果不是生活基本需求所迫,中国人仍然乐于过着一种安于现状和自得其乐的伦理生活。但是,由于信息社会的发展,信息直接刺激了人们需求的快速增长,人们有可能改变传统的价值观念,对物质欲望以及满足这些欲望所必须进行的劳动创造相对地重视起来。因此,在信息社会里,中国人的传统人生观念和生活方式会得到新的改造,但同时传统人生观念也发生着顽强的作用,人们会在追求由新欲望所导致的物质利益与追求和谐和消闲悠然的人生观念之间徘徊动摇,举棋不定。当然,这种动摇不定是近代和现代科技革命影响的综合结果,近代科技革命及其商品经济造成周围的人们有了物质利益的差别,而现代科技革命则造成了跨地区和更大范围内人与人之间这种物质利益的差别,以及伴随着这种差别的欲望的增长。
第三,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虽然我们可以说,现代科技使人们更加认识到近代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造成的一定程度的生态危机,以及认识到生态和资源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但是事实上由于科技革命的能动作用,人口的逐渐膨胀,人们赖以存在的自然状态及其自然观念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首先,在一定程度上,新的科技革命更有助于增强西方那种“人是自然的主人”的传统信念,提高人类在世界上的地位。其次,新的科技革命也彻底改变了中国人那种认为“自然是人之本”的传统观念。以传统观念来看,人们原先生活的空间是无穷大的,人类生活在其中,宛如苍海之一粟,但随着新的科技革命的发展,这种空间不断在缩小,从地球的一边到另一边,只在弹指一挥之间;同时,社会由于高度的自动化,人们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但反而感到时间越来越少,时间的节奏在加快,似乎永远失去了传统人生观念中对时间和空间永恒和悠远的感觉。时间与空间,通常是人们理解自然生活的两个中介,但由于这样的变化,使得中国人那种追求传统人生审美情趣的人生价值观无可着落。这大概也是那些越少受到传统文化影响的人,越能适应高节奏的生活方式,越是长期受到传统文化影响的人,越不习惯高节奏生活方式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四,人类的生活方式日益趋同。信息社会的发展,使得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得到更广泛和更为迅速的交流。但是这种交流并不是平等和没有负面影响的。这种不平等性表现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沙文主义,它们借助于经济和技术的优势向经济和技术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扩张其文化形式和内容,促使各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也在相互学习和模仿中进行新的变革。由于这种文化沙文主义所具有的中心地位及不平等性,必然造成整个世界在文化上的趋向同一。此外,科学文化由于它的具大作用及其优越性,必然会与传统意义上的各种人文主义相抗衡,而最终可能导致人文主义文化走向衰亡。这也是造成人类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进一步同一化的客观原因。当然,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传统文化自身都有着一种抵制这种文化趋同的要求。但由于科技与经济等各种因素的制约,仍然不免于在文化及其人生观念方面走向西化。仅从传统文化这个角度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忧虑的倾向。这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民族人生观念和价值取向的问题。经济的发展不应该以环境的牺牲为代价,也不应该以文化价值的牺牲为代价,而只应该在经济和政治的改革中作最大的努力。未来社会学家奈斯比特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我们的生活方式越趋同,我们对更深层次的价值观即宗教、语言、艺术和文学的追求就越执着。在外部世界变得越来越相似的情况下,我们将越加重视从内部衍生出来的传统的东西”。(《2000年大趋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版第141页)。
4 简短的结论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科学技术革命对传统人生观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和作用方式是从三个层面展开的:一是从价值观念的表层开始。这种作用表现在政治信念上就是社会价值革命;二是由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物质层次开始。生产力的发展又促使经济、政治等社会结构的变革,从而产生新的生活方式及其人生观念;三是由科学技术本身所蕴含的方法和内容的认知层次开始。通过科学思维方式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人生观念。
此外,科技革命对传统人生观的影响仅仅是一种新的整合,即并不是为了完全适应科技革命的发展要求,传统人生观所作的单方面的调整。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传统人生观曾衍生了许多封建和保守的东西而加以全盘否定,其中确实存在有一定价值的成分,值得我们珍视和肯定。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正确处理科技革命和经济振兴同传统人生观继承和发展的辩证关系,尽可能防止一种片面的功利主义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