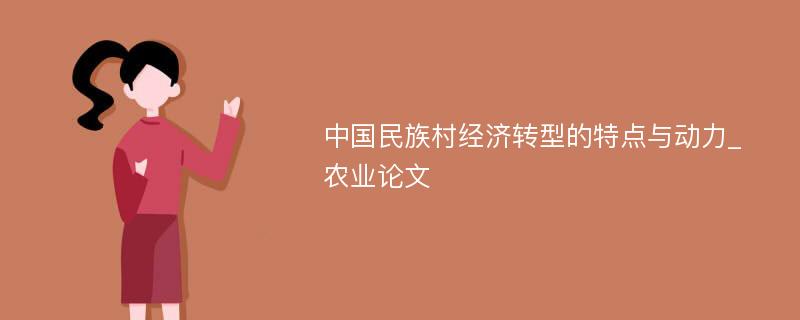
中国民族村寨经济转型的特征与动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村寨论文,中国论文,特征论文,民族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云南大学继对云南省25个少数民族村寨成功调查的基础上,于2003年组织了中国少数民族村寨调查,调查范围遍及全国14个省(区)的31个少数民族村寨。本文主要针对这两次少数民族村寨调查所展现的经济问题做一初步的探讨。(注:本文所用资料,除注明出处外,全部引自云南大学“中国民族村寨调查”有关资料。)
一、中国民族村寨经济转型的历史阶段性特征
中国民族村寨的经济转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前现代社会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国民族村寨的经济转型表现出以自然适应为基调的主流特征,从而呈现出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以渔猎经济、畜牧经济和农耕经济三大经济类型为主的基本结构状态。
自19世纪中叶开始,整个中国社会就被裹挟进世界经济体系的构筑过程中。从此,制度性要素在经济转型中的重要性日益显著,中国民族村寨经济的边缘化进入全面加速的过程,从而陷入贫困化陷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民族村寨的经济转型主要可划分为两个历史性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80年代。在这一阶段中,中国民族村寨的经济转型过程主要是在生产关系变革的引导下展开的。这一阶段的经济转型是以重构自由小生产的个体私有制为起点的。各少数民族村寨虽在此转型起点的构筑上呈现出一定的时间差异性,但都分别通过在内地普遍展开的土地改革和在云南、西藏、新疆、内蒙古等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以及甘肃、青海等少数民族牧区进行的、以和平协商为基调的不同形式的民主改革,相继完成了这一实质性的建构。在广大农区,通过没收地主土地重新分配的土地改革,以村寨为基点,为自耕农确立了大致平均的生产资料个体私有制框架。在牧区所展开的和平协商,则是以“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的主流方式来建立生产资料的个体私有制。如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黑孜苇乡库拉日克村吾依自然村的柯尔克孜族就是在1952年订立牧工分红合同,成活100只羊羔的分红比例一般是,代牧户分15%,最高是25%,最低是5%。与此相类似的还有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红石窝乡大草滩村的裕固族、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辉苏木乌兰宝力格嘎查的鄂温克族等,后者还确立了“牧场公有,放牧自由”的经营方式。
与此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相伴随,一些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先后发生了变化。如新疆伊犁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托斯特乡巴扎尔湖勒村,就是由哈萨克族在20世纪30年末从游牧转向定居开荒耕地而建立的,1951年该村已有40户哈萨克族居民农牧兼营;西藏米林县琼林村的珞巴族从1959年开始,由原来的游猎采集经济类型逐步转向农耕经济比重日趋增长的新的经济类型。又如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新生村的鄂伦春族,则是在1953年生产关系变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游猎经济向定居农业的转变:当年产粮收入占总收入的9.4%;1956年,猎业收入仍占总收入的62%;1980年,农业收入才在农副业收入中占47.3%;直到1982年,农业才成为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在全年总收入中占75.7%。于此,可提供的一个历史对照是,现居沈阳市新城子区兴隆台镇新民村的锡伯族,其先人长期以渔猎经济为主,在16世纪编入“蒙古八旗”并奉旨南迁盛京后,以“跑马圈地”的方式圈占了大量土地,逐渐转向农业生产。经历了3个世纪,完成了渔猎→以牧兼农→定居农耕的转变,直到清末,农业种植才成为该村锡伯族主要的谋生手段,而以牧兼农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这充分表明,经济转型是一个蕴涵多重内容的复合过程。在此过程中,经济关系的制度性建构可以凭借政治权力等多种手段来迅速完成,但当经济转型涉及生活方式转变等深层内容时,必然面临一个漫长的时期。
在确立起这一共同的转型起点后,中国民族村寨的经济转型日益显示出强烈的共时性特征。各民族村寨的生产资料个体私有制的重建,虽然在个体层面上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但这一框架规定了整个生产的现实前提是对某种资源和手艺的独占关系,从而使生产表现为局限性的片面生产,生产的扩展在根本上受到个体所拥有的资源数量和个体自身生产能力的极限约束,使整个经济活动只能以生计为重心而展开,并以主体性生产的短缺和小生产者的分化赋予整个经济体系脆弱性的基本特征。因此,互助的方式或关系的建构,历史地成为克服这种生产局限性的首选。更重要的是,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是剥削产生的根源的认识基点上,共和国选择了建立公有制来阻断剥削与贫困产生途径的方式,主导了这一阶段经济转型的全过程。生产资料个体私有制在不同的民族村寨仅短暂存活了1-3年,便迅速进入了以同一模式、共同步骤、统一号令实施公有制建构的过程。然而,要在平等的社会层面上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是一项必须以更具总体性的条件才能实现的社会改造工程。因此,这一公有制建构的过程并未全面实现该目标,社会层面上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仍需凭借某些中介才能得到局部性的建构。这样,中国民族村寨经历了合作社、人民公社和“一平二调”等组织形式和举措的强烈震荡,在1962年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原则后,这一阶段经济转型所奉献给历史的实质性结果是,重建起了为少数民族所熟悉和接受的村寨土地公有制。村寨组织成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最基本的中介,作为地方性和特殊性而存在的村寨组织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再次强化。这一阶段的经济转型表现为一个社会夷平化与地方特殊性交织一体的复合过程。
第二阶段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一阶段经济转型的实质性结果——村寨土地公有制——成为中国民族村寨第二阶段经济转型的共同起点。第二阶段经济转型的根本性变化,是从确保共同利益的基点转移到确认个体利益重要性的基点上;从生产关系变革主旋律转变到以利益诱导而牵引的经营方式和技术组合的变化以及市场参与的主流上;经济转型的主体行为,也从整体性的转型转变为个体行为的选择。
在此阶段中,经济转型的任何整体性成果,都是通过个体选择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来实现的。它所展现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表现为全部行为动因的共同利益,“只是在自身反映的特殊利益背后,在同另一个人的个别利益相对立的个别利益背后得到实现的。……同别人利益相对立的个别利益的满足,正好就是被扬弃的对立面即一般社会利益的实现”。(注: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6页。)它以对“有个性的个人与阶级的个人的差别,个人生活条件的偶然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6页。)的强调,超越了身份性共同体的社会限制,扩展了人们的选择范围和对随机因素的利用可能。个体的分化及其经济地位和现实状况的丰富的差异性,正是在这一开放性特征的基础上,在日益凸显为现阶段经济转型中的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在一个更大的普遍性层面上,为社会整合或一体化进程铺筑着更为广阔的道路。在此值得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当人们用“农村个体经济发展”的言说来描述时,这种“个体经济”并不具有产权制度层面上的存在意义,它主要是以“经营方式”而获得存在意义的。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当私有经济成分在中国整体经济中日渐增加的今天,村寨层面上的私有经济受到了村寨土地公有制的根本性制约。
中国民族村寨的经济转型在第二阶段所获得的最显著的成果是:在社会层面上,使经济转型获得了更大的稳定性;在经济层面上,实现了多元化和多样性的发展;在运行机制上,赋予整个经济体系更多的活性因素;在最直接的现实意义上,它有效地提升了中国农村、农民和农业的社会供给能力,使中国农产品的供求格局在20世纪的最后年代中历史性地结束了长期的短缺状态,这一契机终于为中国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乃至全面的社会改革提供了可能性,使中国农村、农民和农业成为中国在20多年改革开放进程中贡献最大的支撑点。
二、中国民族村寨经济转型的结构特征
在共和国半个世纪历程中所发生的经济转型,使中国民族村寨以渔猎采集经济、畜牧经济和农耕经济三大经济类型为主的基本结构状态得到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改变。进入这一历史阶段时,仍在一些民族共同体(如鄂伦春族、赫哲族、京族、珞巴族等)中有所保留的渔猎采集经济类型,如今已不复存在;畜牧经济和农耕经济成为当前主要的两大经济类型,并出现了村寨尚存而告别农业的个别现象。
促成渔猎采集经济类型消失的根本性原因,来自于资源约束的强制性转型。最典型的莫过于黑龙江省同江市街津口乡街津口渔业村的赫哲族。在20世纪50年代集体化转型过程中,他们被编入渔猎混合生产队,春、夏、秋捕鱼,冬季进行狩猎和冬网捕鱼,混合队有少量的农田,由汉族经营。就赫哲族人而言,渔猎经济类型仍得到总体性的保留。始于60年代的三江平原大开发,到80年代使野生动物资源彻底枯竭,猎业开始隐退而渔业仍占重要位置。虽然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后期,赫哲族渔业队一度弃渔务农,渔业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曾从1966年以前的80%,降至1977-1979年的29%,但借80年代的改革契机,赫哲族又开始专营渔业生产并使之成为其经济的惟一部门,继而全面进入商品经济网络。1990年在街津口村赫哲族的生产结构中,渔业占68.6%,种植业占3.6%,其他占27.8%。1994年以前渔业村的赫哲族村民主要以捕鱼为主,每年明水期渔业村至少有138人在不定期地从事渔业生产,渔业收入大幅度提高,到1993年达到了顶点。但由于整个松花江、黑龙江其他江段外来捕鱼人口急剧增加,致使两个江段整体出现超量捕捞的局面,资源消耗速度极快,过去每网可捕上百斤鱼,到1994年,仅能捕几斤鱼,而到了2003年,空手而归的渔船比比皆是。1994年,资源约束的强制性转型使街津口赫哲族渔业村被迫再次弃渔务农,上岸开垦土地。可喜的是,与此次经济转型相伴随的是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人均年收入从1994年的560元,猛增到1996年的2000元。渔业生产收入占经济收入的比重从1994年的44%下降到1996年的18%,而同期农业生产收入比重则从51%上升为78%。1998年全村转产率达95%,1999年达到100%。到2000年,渔业村共有土地1200多垧,其土地数量已超过街津口乡农业村的土地数。如今,在三江平原地区,由赫哲人耕种的土地已达到2万多亩。赫哲人从靠打鱼捕猎为生,到耕种土地,再到从2000年起的旅游开发,发展服务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街津口赫哲人如今已顺利完成经济转型,产业结构的调整已实现了多元化。2000年街津口赫哲族人总收入达3067万元,人均收入2491元。在整个收入结构中,种植业占27.8%,牧业占25.1%,副业占17.3%,渔业占6.5%,乡镇企业占22.1%,林业不及0.1%,其他仅占1.0%强。2002年,街津口村赫哲族人均年收入达到2807元。
中国民族村寨经济转型的结构状况所展现的一个重要事实是,尽管在村寨层面上,畜牧经济和农耕经济仍为主体类型,但人们再也不能简单地把它们相联于“传统”的概念。就其内部而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的生产组织形式的进入,已使这些村寨的经济类型呈现为一种复合型的结构。即便仍有个别村寨几乎完全从事畜牧或农业种植,但已经出现公司等企业组织的介入或农业种植中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的瓜果蔬菜和经济作物的种植多样化的现象。从外部来看,此次所调查的民族村寨都无一例外地相连于市场体系,村民的日常生活通过集市和村中的小商店来借助市场而运转,村民的生产无论是前期的投入,还是产品的流向,都更多地倚重于市场,现金支出和交易成为村民生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且重要性日渐增强。
据对广西环江县下南乡南昌屯毛南族的典型调查:谭会庆家1982年生产性货币支出127元,占商品性消费总支出的8.76%;2002年生产性货币支出达1940元,占商品性消费总支出的34.15%,现金收入在年总收入中占81.90%。谭承康家1982年生产性货币支出160元,占商品性消费总支出的7.89%;2002年生产性货币支出达1345元,占商品性消费总支出的22.17%,现金收入在年总收入中占75.90%。谭贵方家1982年生产性货币支出78元,占商品性消费总支出的11.30%;2002年生产性货币支出达533元,占商品性消费总支出的14.05%,现金收入在年总收入中占44.70%。
又如新疆木垒县大南沟乡阿克喀巴克乌孜别克族村,2002年的货币性收入已占总收入的56%,实物性收入占44%;出售产品收入在种植业收入中占63.6%,在牧业收入中占28.3%。据对50户家庭的典型调查,在年总支出中,生产性货币支出在20%-29.9%之间的有25户,占被调查户数的50%;10%-19.9%之间的有15户,占被调查户数的30%;30%以上和10%以下的各有5户,各占被调查户数的10%。
辽宁抚顺市新宾县上夹河镇腰站村满族的几乎所有家庭仍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收入也主要依靠农业,1996年农业收入所占比重为73.5%,但在农民人均收入达到历史新高的1997年和1998年,农业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分别降至39.1%和42.8%,建筑、运输、商业服务及其他行业的收入在总收入所占的比例则呈相对增长的趋势。在2001年的就业人口中,农林牧渔业占70.6%,其他非农产业占29.4%。2002年农业收入比重为45.6%,运输收入所占比重则从1997年的1%增长到8.1%,牧业、商业服务、外出劳务、建筑收入所占比重也分别达到13.1%、12.5%、5.9%和5.4%。
据2000年统计,广西东兴市江平镇京族聚居的山心村,从业结构是农业30%,边贸40%,渔业30%;收入结构是渔业60%,商贸30%,农业10%。边境贸易和渔业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农业的功能只是提供口粮。
在西藏错那县贡日门巴族乡所辖的贡日、色目两村2002年的收入结构中,农业占9.3%,牧业占33.0%,林业占15.2%,运输业占31.3%,商业占7.2%,采集业占3.7%,手工业占0.3%。提供的现金收入方面,运输业为260,000元,商业为60,000元,林业为126,105元,手工业为2084元,采集业及其他为37,811元;虽然农业产品主要用于自身消费和牲畜饲料,几乎没有销售,但作为主体生产的牧业所提供的现金收入为134,610元。牧产品商品率在色目村和贡日村分别为48.9%和49.5%,全乡为48.9%。排除4户人家从事的商业、运输业,全乡人均产值2963元中,现金收入占59.0%,为1747元。
在此次调查中,基本上告别农业而整体进入其他经济活动的村寨,以吉林省磐石市吉昌镇烧锅朝鲜族村最为典型。作为拥有150公顷肥沃土地、人均3亩地的村庄,自1982年以来,农业收入在人均收入中的比重就逐渐下降,而家庭副业、多种经营以及其他收入所占的比重逐步提高。在1990年1757元的人均纯收入中,农业收入仅为700元,所占份额不足40%,而卖咸菜和养鸡的收入占了40%强。1996年种地户数还有86户,1998年有60余户,2000年有40余户,2001年减少到18户,2002年全村只有6家种地,农业收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2003年全村仅有1户村民种植不到2公顷的水田,其他村民则不再从事农业生产。
附:
中国民族村寨经济类型简表
民族 村寨经济类型特征
鄂伦春族
黑龙江黑河市爱辉区新生村农业为主兼营养殖工商
赫哲族黑龙江同江市街津口乡街津农、牧、旅游服务三足鼎立
口渔业村
鄂温克族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辉苏木乌畜牧经济,外地企业介入
兰宝力格嘎查
蒙古族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贺日斯台畜牧经济,外地公司介入
苏木巴彦胡舒嘎查
达斡尔族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农业为主兼营牧业
旗哈力村
哈萨克族
新疆吉木乃县托斯特乡巴扎牧业为主兼营农业
尔湖勒村
柯尔克孜族
新疆乌恰县黑孜苇乡库拉日农牧兼营
克村吾依自然村
塔吉克族
新疆塔什库尔干县提孜那甫牧业为主兼营农业
乡提孜那甫村
塔塔尔族
新疆奇台县大泉塔塔尔族乡农牧结合,以农辅牧
黑沟村
乌孜别克族
新疆木垒县大南沟乡阿克喀农牧兼营
巴克村
维吾尔族
新疆疏附县吾库萨克乡木苏棉、粮、林果为主兼营工商
玛村
裕固族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红石畜牧经济,副业辅助
窝乡大草滩村
东乡族甘肃东乡族自治县坪庄乡韩农业为主兼营养殖、工商
则岭村委会老庄村
保安族甘肃积石山县大河家镇大墩农牧兼营,打工经商
村
撒拉族青海循化县积石镇石头坡村农、牧、工商兼营
土族 青海互助县东沟乡大庄村 以农为主,打工经商
珞巴族西藏米林县琼林村林、农、牧兼营采集、运输
门巴族西藏错那县贡日乡色目村 牧业、运输、林业兼营农业
仫佬族广西罗城县四把镇石门村田以农为主,打工经商
心屯
毛南族广西环江县下南乡南昌屯 以农为主,打工经商
京族 广西东兴市江平镇山心村 农、渔、边贸三业并举
仡佬族贵州大方县普底乡红丰村 以农为主,打工经商
侗族 贵州黎平县永从乡九龙村九林粮兼营,打工经商
龙寨
土家族湖南永顺县和平乡双凤村 以农为主,打工经商
羌族 四川汶川县龙溪乡阿尔村巴以菜为主的农业兼营工商
夺寨
畲族 福建罗源县八井村以农为主,打工经商
黎族 海南五指山市冲山镇福关村农胶兼营,打工经商
朝鲜族吉林磐石市吉昌镇烧锅村 第三产业,劳务输出
锡伯族辽宁沈阳市新城子区兴隆台以农为主,兼营工商
镇新民村
满族 辽宁抚顺市新宾县上夹河镇以农为主,兼营工商
腰站村
三、中国民族村寨经济转型动力
在一般层面上讲,经济转型的动力可大体分为外力介入和内生力量。而在具体层面上,这两种基本的动力类型又都可以表现为政治牵引、经济推动或资源约束的强制等不同的实现方式。
如果说,中国民族村寨经济转型的动力机制,曾以政治牵引和经济推动两个主要的实现方式,赋予其半个世纪的历程以阶段性的特征,那么,在当前正在发生的转型过程中,资源约束的强制性力量作为中国民族村寨经济转型动力的新的实现方式,其重要性和生成为主导性的趋势已初露端倪。
中国农业资源具有自然资源紧缺和劳动力资源丰裕的特征,其自然资源的人均拥有量是极其匮乏的。早在明清时期,有限土地上的人口激增,形成中国社会经济中持续加剧的口粮压力。从明至清中叶,人均粮食面积从3.23亩滑落到1.71亩,人均占有原粮数由1118斤下降到628斤。(注:参见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页。)这一基础性的事实,促成中国农业从以粗放农业为代表的资源密集型生产转向了以精耕农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帕金斯就中国单产提高和耕地面积扩大对粮食生产的贡献问题,以1400-1850年做了一个长时段的估算,认为在1400-1770年和1770-1850年的两个时段中,单产提高的贡献份额从42%上升为47%,而耕地面积扩大的贡献份额已由58%下降到53%。(注:参见[美]德·希·帕金斯著、宋海文译:《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页。)长期以来中国以不足世界7%的耕地养活20%以上的世界人口的事实,造成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粮食供应持续的极度紧张,最终沉淀为以粮为主的单一生产结构,使中国农民无法做出谋利型的结构调整,而以人畜同粮的单一生产格局,把整个社会经济推入低水平均衡的陷阱:口粮压力愈重,生产格局愈是以粮为重心;生产愈是以粮为重心,愈是失去了以多样化谋求发展的机会。直到20世纪的最后年代中,中国农产品的供求格局才历史性地结束了长期的短缺状态,这一契机终于为中国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提供了可能性。然而,这一由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带来的结果,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上述的资源约束的条件,资源约束的强制性在中国民族村寨的经济转型中日益突出。
资源约束的强制性在中国民族村寨的农耕圈内,集中体现为人多地少的矛盾;在畜牧圈内,也以草原退化和牧群过载的普泛化现象得到突出的表现。
如此次调查的蒙古族村寨巴彦胡舒嘎查,其所在的贺日斯台苏木从1986-2001年,乔木林面积减少了42%,灌木林面积减少了37%;可利用草场面积为90.55万亩,而退化面积达67.5%。草原退化和牧群过载的压力,使巴彦胡舒嘎查从2000年开始大批地售羊购牛,进行生产替代,牲畜数量较几年前有了很大减少。大牲畜从1997年的2205头降至2002年的1723头,小牲畜从6085只降至1212只,大、小牲畜总量下降幅度为64.6%。同时也限制了畜牧规模,目前该嘎查牧户拥有的牲畜数量大多集中在40-50只(头)之间。如此资源约束的强制性使相邻的图格日格嘎查10余户牧民围封草场,卖掉牲畜来到桑根达来镇开商店、开饭馆或开出租车,进入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和生活方式中。
在塔塔尔族聚居的新疆奇台县大泉塔塔尔族乡,草场的最佳承载量为1.7万只羊,而2003年黑沟村一村就达1.2万只,造成50%的草场退化,不得不从1984年开始实行“牧民定居”工程。全村151户843人中,有61户309人搬迁到大泉湖定居点从事农业生产,占全村总人口的37%,这部分人还兼营运输、商业服务等其他经济活动。2002年在全村经济总收入中,牧业占62.7%;农业占27.4%,其中出售种植农产品收入占种植业收入的40.0%;其他兼营占9.9%。资源约束的强制性从根本上限制了生产规模的扩大,不少村民尤其是村中的3家“首富”受哈萨克斯坦广阔草场的吸引,已意欲迁居国外发展生产。
在社会层面上,经济转型关联到生活方式的改变;在经济层面上,则直接意味着成本投入的增加。诱导转型的力量也关联于社会与自然两个层面:前者主要是以主导性经济类型利益的自明性确立起的“优势—劣势”的利益格局来推动的,后者则表现为现实生产的前提条件的制约。这两种力量来源在成本问题的基础上,利益推动以选择机会的增加显现出机遇与挑战的二重性存在;而现实生产前提条件的制约则直接宣告了特定共同体原有生活经验、经济知识和生存技能的失效,当社会条件的的合力作用使挑战的困难大于机遇的提供时,异地寻求自己久已熟悉的生活生产条件以谋发展,就成为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在当前农民进城打工成为社会聚焦的热点问题时,农民流向异地乡村的打工也从不同的角度证明了这一点。如在黑龙江同江市街津口乡的赫哲族村寨,外来打工者从1995年开始迅速增加,2000年以后,每年务工者达300人左右;在门巴族聚居的西藏错那县贡日乡色目村,2003年也有7名外来的经商打工者;乌孜别克族聚居的新疆木垒县大南沟乡阿克喀巴克村,2002年有29人从甘肃、江苏、新疆等地来此从事建筑、养殖和种植,有效暂住时间约为5个月;在福建罗源县的八井畲族村,外来打工者1995年有7人,1996年有44人,分别来自浙江、四川、江西和福建的泉州、福清、宁德、邵武、建阳、柘荣、沙县;在新疆疏附县吾库萨克乡的木苏玛维吾尔族村砖厂,有56名来自山东和四川的打工者;在四川汶川县龙溪乡阿尔村的羌族巴夺寨,2002年有来自本乡其他村寨的7人在5-10月种菜挣钱。近两年来,到春耕栽秧、秋收打谷时,贵州黎平县永从乡九龙村的侗族九龙寨,一些未外出打工的人从黎平转道湖南靖县,利用农时差异揽栽秧、打谷的农活,每天除去食宿后,有20-30元的收入,每年从事这种农活打工的有200人左右。
动力差异产生了经济转型的两种基本类型:整体性的突发转型和个体选择性的渐变转型。在社会层面上,前者表现为一个震荡性的过程和整个生活方式的突变,后者表现为一个稳定的过渡性过程和文化的浸润与渐变;在经济层面上,转型的成本增加在前者呈集中性与显性,在后者则为分散性和隐性所淡化。一般说来,外力介入性的经济转型多表现为整体性的突发转型,而内生力量性的经济转型多为个体选择性的渐变转型。但这种区别并非绝对,如在面对当前中国民族村寨中日益突出的资源约束矛盾时,虽有一些由政府组织的“整体搬迁”,但它并不排斥大多数在市场选择多样化的条件下而导向的个体差异性转型,甚至可以说,正是后者成为了当前中国民族村寨资源约束强制性转型的主体实现方式。
如甘肃积石山县大河家镇大墩村的保安族,在人均耕地面积从1952年的3.9亩下降到目前的0.94亩的制约条件下,其主要的经济来源,已不再是单一的农产品的交换,而是以差异性的个体选择,通过不同人的外出打工、经营畜牧业及其他副业,构成家庭收入的重要支柱并构筑起整个村寨的经济转型过程。
广西罗城县四把镇石门村田心屯的仫佬族,全屯人均水田约0.8亩、旱地0.1亩,而家庭承包的差异使人均耕地的上限可达1.3亩,下限只有0.3亩。养殖为家庭经济收入提供了30%-50%的份额。田地严重偏少使新增人口无地或田地极少,一年之中有一个多月需要买粮维持,导致全屯70%以上的家庭有人在外打工,全屯240个劳动力,外出打工的80多人,90%的外出务工的人员集中在省外,其余的少部分则分布在广西境内的玉林、柳州、南宁等地。1/3的劳动力已转入其他经济领域。此外,在农闲时候田心屯还有很多男性在县城里打短工。在田心屯2002年农户的年收入中,经商或务工的收入占了田心屯人的绝大部分,远远超过了来自农业与养殖的收入。在对全屯71户(占总户数80.7%)的典型调查中,种植、养殖占总收入份额在80%以上的有12户,占16.9%,其中有3户收入完全来自种植、养殖;种植、养殖占总收入份额在50%-80%之间的有42户,占59.2%;种植、养殖占总收入份额在50%以下的有17户,占23.9%,其中有5户低于30%。同时,经商、务工占总收入份额在30%-50%之间的家庭占了绝对的比重,共36户,占50.7%。
如果说,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建立,为中国民族村寨日益普遍的多样化经营确立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那么,资源约束的强制性虽不能说是中国民族村寨多样化经营的惟一的内在基础和动力,至少也是不能忽视的极其重要的内在基础和动力之一。正是这一内在基础和动力,早在明清时期,就以“耕织经济”的形象化特征彰显出中国小农的兼业化趋势。尽管多样化经营有可能提供较大的商品总量和较高的商品率,但这一内在基础和动力的制约,会使单个商品经济主体所能提供的商品量很少,它意味着这样一种可能性的存在:把多样化经营导向“商品经济低层次扩散”的道路,(注:参见陈庆德:《中国近代商品经济研究》,彭泽益主编:《中国社会经济变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以商品化和多样化的经营固化小农经济结构,而滑入经济学理论所描绘的“低水平均衡陷阱”。这是一个需要得到高度重视的问题。
综上所述,不管村民在经济转型中的这种市场参与或市场卷入是自愿还是强制,是主动还是被动,他们已存在于市场之中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中国民族村寨的诸多经济问题,如“落后”、“贫困”等等,其症结不在于“传统”与“现代”,而在于他们在市场参与中的地位和方式,在于他们对市场的边缘性参与的基本事实。中国民族村寨的经济转型以上述复合性的结构特征,充分展现出中国民族村寨经济类型的不完整性和过渡性的根本性质。它也明确地揭示了,必须以动态过程的角度而非静态的观点,才能充分了解和深刻把握中国民族村寨的现实经济状况,才能更妥帖、更切实地解决中国民族村寨的诸多经济问题。
在更具一般性的理论意义上,中国民族村寨调查资料揭示了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主题的视野扩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人的社会性存在意义出发,“在任何民族的框架内都不可能找到一个可理解的历史研究领域”。(注:[英]汤因比著、沈辉等译:《文明经受着考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这就意味着,任何一个民族共同体(更不用说村寨层面上的微观存在)都不是作为隔离的种群而存在的,都必须放置在一个更大的时空范围、甚至全球化背景中才能得到理解。也就是说,必须借助于宏观的视野,才能使其研究的微观对象得到总体性的说明。
而进一步的问题是,把微观对象放置于总体性联系中的预设基点的差异,会得到截然不同的理解结果。
在以往的研究中,经济转型问题最紧密地关联于“进步”、“发展”等概念并由此被赋予了定向性的特征。从而也就产生了“民族—传统”的关联,形成了“农民”概念的泛化使用,使“农业社会”、“农村”以至“农民”等概念都获得了巨大的伸延性。这些概念在蕴涵着趋向于揭示个体贫困极端的感情涵义的同时,也充溢着“不变性”、“无发展性”、“落后性”的暗示与判断。在少数民族与农民的双重交织中,如此的假定把他们视为一个空洞的、僵硬划一的类型。在把其作为经济类型比较的一般参照系的简单化中,产生了具有欧洲中心主义的、技术性导向的一个规范性发展模式,以及相关的少数民族是受到非理性的传统限定的分析视角。这种分析从一开始也就潜藏下了致命的缺陷,其整个研究的大前提是以对“非我”在时间上的排拒造成时间的空间化,以确立现代“我类”一端的文明优势。这一巨大的偏见把少数民族的村寨和农民的现实存在转译成“历史”的存在,从而消解了对他们存在的现实状况和意义的关注与理解。
如果把经济定义为人类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活动系统,那么,经济就不是一个自主的系统,而是一个受制于自然适应与社会文化选择的可变函数系统,并表现为在人与环境相互作用和过程的制度化两个层面上的构造。这一活动系统在与不同的特定自然适应与文化选择的情景结合中,产生了不同的经济存在形式,我们由此也就看到了诸多不同的经济类型。波拉尼曾以“经济嵌合于社会之中”的说法,指出“人的经济活动总是被淹没在他的社会关系中”,揭示了经济是靠非经济动机来运转的事实。(注:参见陈庆德:《经济人类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6-67页。)尽管在现代社会中,经济系统以社会分工和市场的专门化形式,实现了自身与社会的分离或相对的独立化,实现了经济对社会的支配,并以“市场规律”、“供求法则”等等概念,在直观表象上使经济呈现为一个自主系统。但是,只要稍具一点洞察力,即便是作为市场社会的忠诚支持者也能清晰地看到,“如果在一个非集体主义的秩序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它也只是在一个精心制定的法律和秩序框架下发生作用”。(注:[英]迈克尔·佩罗曼著、裴达鹰译:《资本主义的诞生——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诠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经济总是不可分割地与存在着的一个统治系统联系在一起。同时,作为一种可变函数系统,不同的经济类型既有空间上的共存,也有时间上的先后继起。然而,基于上述基础,经济类型本身并不具有真理自明性来构建“先进—落后”的等差结构。一旦扬弃经济类型的方向性进化排列,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某种已存的或新生的经济类型,在与特定自然适应和文化选择的情景结合中,从一种局部性的存在提升为一种支配性的主导范式,并在一定的时空中获得了总体性存在的意义时,它就会以利益的自明性确立起一套“优势—劣势”的实践评价体系,来完成对与之并存的、其他依然处于局部性存在状态的经济类型的边缘化,并以自身的利益自明性引导一个经济一体化的过程。所谓经济转型,就是在此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边缘化的经济类型为主导性经济类型所裹挟、吸纳和融合的现象。也可以说,所谓经济转型,是社会一体化在经济领域的具体展开和反映,它以过程中的力量冲突、利益交织与地位差异,实现了某一时点上的社会整合程度的加强。
这一新的理论基点,不仅明确地宣示迄今为止所有获得经验存在的人类经济类型都无一具有终极完美的存在性质,而且赋予经济转型问题丰富的历史动态感。在此新的理论基点上展开的中国民族村寨的经济转型研究,使我们更贴切地去感受和体验中国少数民族村寨实存状况,更准确地把握中国民族村寨在经济转型中的问题与难点。
标签:农业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 经济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新疆生活论文; 农民论文; 三农论文; 农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