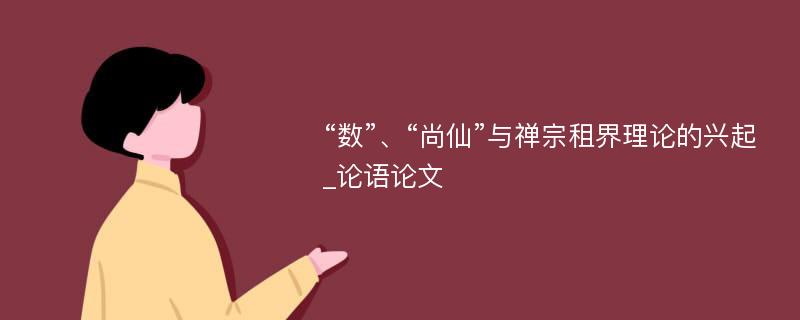
“歷数”和“尚贤”与禅让说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828(2006)03-0078-06
一、问题的提出
《论语·尧曰》有这样一段话:“尧曰:咨,尔舜,天之歷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1] (P411)对于尧舜禅让这类故事,古代学者一般相信儒家经典的记载,以为是理所当然,并不认为是某家的创造,也不会认为是一个需要怀疑的问题。
可是,进入20世纪,情况不同。20年代,顾颉刚先生提出了大胆的挑战。他运用当时理解的科学方法,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问题:尧舜禅让并非信史,而只是古史传说,既然是传说,就一定有发明者或创造者。那么,这发明者或创造者究竟是谁?他指出,《尧曰》章包含“歷数”的那段话是后代添加上去的;《墨子》有尧举舜为天子的说法,在时间上最早,墨家应是禅让说的发明者,他们的“尚贤”主张,应是禅让说的理论基础[2] (P102,102-103,50,31)。
本文首先讨论“歷数”和“尚贤”孰先孰后的问题,然后,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和比较,来确定“尚贤”和“歷数”表现了怎样的思想,这些思想在禅让说的理论基础中究竟占有何种地位,在禅让说的兴起中,墨家和儒家究竟起了何种作用,为解决禅让说之起源的问题,提出个人的意见,尚祈批评指正。
二、否认“歷数”出于《论语》证据不足
“歷数”和“尚贤”这两个词的发明在时间上孰先孰后?按照顾先生的理解,这是判定谁创造了禅让说的关键。他提出:“《论语》这章中最可疑的便是‘歷数’两字。”[2] (P59)为什么呢?他没有提供直接的证据,却从另一个方向给出了间接的说明:首先引纬书《论语比考谶》,说明“歷数便是帝王的历运”;接着引何晏“歷数,谓列次也”和朱熹“帝王相继之次第”,说明“歷数”来源于阴阳家邹衍;最后引《史记·封禅书》“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集解》引如淳:“今其书有《主运》,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断言“五行是永远转动的,转动的时候是永远依着它的生克的次序的,这便叫做‘歷数’”。以此为前提,他推论道:“所以我们敢说,从‘天之歷数在尔躬’一句看来,《论语》中这一章是阴阳家的说话。阴阳家是起于邹衍的,孟子还看不见,何况孔子!”[2] (P60)
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关于邹衍的记载,不见有“歷数”或“歷”和“数”的概念。据说《吕氏春秋·应同》篇保留了邹衍的五德终始说[3] (P8),其中也只提到“数”,而没有“歷”字。由此可知,说《论语》中的“歷数”与邹衍的“阴阳主运”说有关,查无实据。又按,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是以相胜说为原则的,它适应征伐式的王朝更替,先是为齐愍王实现“并周室为天子”的“大欲”设计,继而献给秦王政,为秦国以武力灭亡两周、统一天下作了合理的解释,更为秦朝制度和施政原则(如改正朔、易服色、尚法治、严苛少恩等)的确立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框架。而考之后世史籍,禅让式的王朝更替,绝无例外,都是以相生说为准则的。由此又可知,为禅让服务的“歷数”与邹衍的“阴阳主运”在道理上龃龉不合。因而,从这个角度,依据这些理由来否认《论语》有“歷数”观念,是没有足够说服力的。
另一方面,据我的初步了解,有许多材料倾向于说明与“歷数”观念相近的思想在儒家的思想渊源中有着丰富的资源。
按“歷”字已见于甲骨文,字形由两部分组成,上面象“双木林”或“双禾木”,下面象“止”(足形),大概与步行有关[4] (P336)。“歷”、“厤”、“曆”三字并见于金文。《禹鼎》:“至于歷内”;《毛公鼎》:“歷自今,出入敷命于外”;“曆”字见于铭文者甚多[5] (P0162,1259,0594)。三字古代通用。《论语正义》本的“歷数”,伪古文《虞书·大禹谟》同[6] (P136),而《论语注疏》本作“厤数”[7] (P2535);宋元人注《四书五经》和《四书章句集注》本均作“曆”[8] (P83)[9] (P193)。是“歷数”又可作“厤数”或“曆数”也。
《说文·止部》:“歷,过也,传也,从止厤声。”《步部》:“岁,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宣遍阴阳,十二月一次。”[10] (P68)。可见,“歷”的本义是“过”或“经过”的意思。与甲骨文和金文材料可以参证,在传统文献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伪古文《尚书·毕命》:“既歷三纪,世变风移。”传曰:“言殷民迁周已经三纪,世代民易顽者渐化。……十二年曰纪,父子曰世。”[11] (P245)这里的“歷”字即有“过”和“经过”的意义。“歷”往往又作“歷年”,今文《尚书》不止一见。《召诰》云:“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呜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连同以下,此章“歷年”凡五见。孔传曰:“以能敬德故多歷年数。”[11] (P213)宋儒蔡沈解“歷年”为“歷年长短”;所谓“歷年”,系就王朝统治的时间长短而言的。《君奭》:“多歷年所。”蔡沈:“享国长久。”[12] (P97,108)上天根据统治者是否敬“德”来决定王朝统治的长短,这个“歷年”里面,实在包含着统治之道。由此可见,“歷”就是一个以“民心”——“天命”为内容或原因,以统治时间长短为表现或结果的辩证概念。
按“数”字已见于《诗经》,《小雅·巧言》有“心焉数之”句[13] (P96);又多见于春秋战国文献中,《老子》五章有“多言数穷”①;《孙子·势篇》:“治乱,数也。”[14] (P76)《孟子·公孙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15] (P183)《商君书》有“凡知道者,势、数也。故先王不恃其强而恃其势,不恃其信而恃其数”[16] (P39)。《荀子·富国》:“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于)人,数也。”王念孙注云:“言万物于人虽无一定之宜而皆有用于人,数也。数也云者,犹言道固然也。《吕氏春秋·壅塞篇》:‘寡不胜众,数也。’高注:‘数,道数也。’”[17] (P113)《韩非子·孤愤》:“其数不胜”;《解老》:“寡之不胜众,数也”;《喻老》:“不随道理之数,而学一人之智”[18] (P56,100,122)等等。是“数”又有必然趋势的意义。
“歷”、“数”相通也有证据可寻。《尔雅·释诂下》:“厤,数也。”郭璞注:“厤数也。”邢昺疏:“推律所生之数。”[19] (P2576)《大诰》“大歷服”中的“歷”字,宋人蔡沈解释为“歷数也”。[12] (P82)
“歷”、“数”二字连用形成复合词“歷数”,还见于其他先秦古籍。今本《书·洪范》:“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数。”[6] (P189)刘宝楠云:“歷数,是岁日月星辰运行之法。”[1] (P411)此外,《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6] (P119)刘宝楠云:“歷象、歷数,词意并同。”[1] (P411)《庄子·寓言》:“天有歷数。”王先谦注云:“气数有定。”[20] (P183)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天有歷,一本作天有歷数。”[21] (P412)《洪范》、《尧典》、《寓言》诸篇的写定时间有争论,但最晚也不会是战国以后的作品,这是公认的,这说明它们与《论语》成书相去不远,或有一定渊源关系。刘宝楠引《曾子·天圆篇》:“圣人慎守日月之数,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时之顺逆,谓之歷。”[1] (P411)《史记·曆书》:“曆数失序。”[22] (P1257)可见从战国到西汉,“歷数”观念已经与阴阳四时相关,而且出现了历法化的趋势,与《大诰》、《召诰》和《尧曰》相比,发生很大变化,但可以看出其间发展的脉络。
以上的叙述表明,“歷”和“数”的观念早在西周初年就有了雏形,《论语》成书后不久,“歷数”便成为时代的通用语词。
说实话,我在阅读《论语》时,总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孔子的时代应该有尧舜禅让的传说了。比如:“子夏曰:‘……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1] (P278)这与尧舜禅让故事的讲述方式是很相似的。“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1] (P154)“让”是禅让观念的重要渊源和基础,“以天下让”就是禅让思想本身呀!“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朱熹注曰:“不与犹言不相关,言其不以位为乐也。”[9] (P107)我们知道,在法家的心目中,“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所以,“传天下而不足多也”![23] (P1041)因为在他们看来,尧舜禹之所以能够禅让天下,不就是“不以位为乐”么?为什么“不以位为乐”呢?实在是因为他们身在其位,得到的却是“监门之养”和“臣虏之劳”,太清苦了!对于尧舜禹的评价,儒法两家观点相反,但所谈的是同一件事,这应该不会有错。
以我愚见,否认“歷数”出于《论语》,证据尚嫌不足。
三、墨家“尚贤”意在选官治官而非禅让
除了说明“歷数”晚出之外,在顾先生的思想中还有这样一层意思,即禅让说的理论基础是尚贤论,而积极倡导尚贤的只有墨家,所以他们才是禅让的发明者。
我以为,即使承认尚贤论是禅让说的理论基础,也无须急着认定墨子是禅让说的发明者或首倡者,因为,在他之前,孔子也是主张任用贤能的。孔子说过:“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1] (P280)他还说过:“雍也可使南面。……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1] (P111,116)按仲弓出身贱人家庭[22] (P2190),在孔子眼里,居然可即诸侯天子之位,这说明,孔子有平民贱人担任君主的思想。前引子夏曰:“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这分明是选贤任能的思想,与后来墨子的尚贤已很相近了。众所周知,孔子主张“有教无类”;还通过弟子子夏之口喊出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响亮口号,这些都是打破旧的血缘藩篱,要求人人平等的思想。孔子弟子中出身平民者不在少数。在孔门之中,学与仕关系甚为密切,孔子主张做官凭学业,而非血统,这也是尽人皆知的。即使到了战国时代,这些思想和行为也可纳入尚贤的范畴。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墨家的尚贤主义是否为禅让而设?我们知道,在《墨子》书中,以《尚贤》为题的文章有上、中、下三篇,集中论述了尚贤主张,内容大同小异,学者认为是墨离为三以后,相里氏、相夫氏和邓陵氏三家的各自所传。最能表现尚贤思想,而且与禅让思想关系最为密切的,要数《尚贤下》。为了便于阅读,不作长篇引述,只把我的理解分为以下若干层次概述之。
其一,文章开篇,单刀直入,揭露问题:尚贤为治理国家、富国众民、端正法制的根本,是“政事之本也”,可是王公大人对此有茫然无知者。
其二,接着,提出问题:什么是尚贤呢?他举了一个例子,诸侯下令国内:善于骑射者赏,使他高贵;拙于骑射者罚,使他卑贱。忠信者赏,使他高贵;不忠信者罚,使他卑贱,这就是尚贤。
其三,接着,又指出尚贤的结果,为善者劝,为暴者止;用这个方法治理天下,就会使天下为善者劝,为暴者止。墨子之所以珍视“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就是因为它能使天下为善者劝,为暴者止。正如他说:“此尚贤者也,与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同矣。”可见,他的所谓“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就是“尚贤”,按传统文献,其中的汤、文、武是没有禅让的,因此,尚贤是否禅让即出现问题。
其四,接着,他对“天下士君子只知小利,不知大道”提出批评。举例道,如今的王公大人,宰杀牛羊,知道要请有水平的屠夫;缝制衣服,知道要请有经验的裁缝;马匹病了,知道要请良医来治;弓弩破了,知道要请良工来修;绝对不让自己的骨肉之亲、特权者和美貌幸爱者来做,其实既是知道他们没有这个本事,也是怕他们弄坏了东西,有损物件。这看起来似乎够得上“尚贤使能”的了。可是一到国家大事上,情况就不同了。这些骨肉之亲、特权者和美貌幸爱者们轻易就可任用为官。看起来,王公大人对国家的亲爱远不如对器物畜生的亲爱来得深厚。可是如果这样做,就仿佛让哑巴当“行人”(司仪官),让聋子当乐师一样,怎么能有好结果呢?
其五,很自然地,墨子又提起古代圣王的理想之治:“古之圣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贵,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尧之举舜也,汤之举伊尹也,武丁之举傅说也,岂以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哉,惟法其言,用其谋,行其道。”“是故昔者,尧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汤有小臣,武王有闳夭、泰颠、南宫括、散宜生,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远者归之,日月之所照,舟车之所及,雨露之所渐,粒食之所养,得此莫不劝誉。”“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选择贤者,以为其群属辅佐。”古代圣王是尚贤的典范,其中汤、武丁、武王没有禅让的记载。
其六,结论:“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实将欲为仁义,求为上士,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尚贤之为说,而不可不察此者也。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24] (P38—43)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到,墨子的尚贤是指有能者赏,无能者罚,赏要当贤,罚要当暴,如此才能忠劝邪止,天下大治。这与法家令行禁止、因能授官的法术说有相通之处,表现了变法图强、加强集权和平民政治的时代气象和风貌。
不错,该篇有“尧举舜”而“立为天子”的说法[24] (P40),可是,这与“禹举皋陶”、“汤举伊尹”、“武丁举傅说”和“武王有闳夭、泰颠、南宫括、散宜生”等一样,在墨子眼里,举人者仍然健在,被举者之所以被举,并非因为他们身为君主的“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而仅仅是因为统治者要“法其言,用其谋,行其道”,是因为“尚贤使能”。这种任人唯贤的做法,不同于世官制度,却与春秋战国时代新生的政治体制和社会风尚相吻合。该篇还有“选择贤者,立为天子”的话,但却和“选择其次”“立为三公”,“分国建诸侯”、“立为卿之宰”、“立为乡长家君”一样,目的是“使天下欲同一天下之义”,以免“一人一义”,即目的是尚同[24] (P56)。众所周知,《墨子》讲尚贤尚同,讲法治,倡导集权统治,他所孜孜以求的,是如何为王公大人提供为政之本,并不关心最高统治权的转移问题。《尚贤》三篇并无“禅让”意图,但却显示出,在墨子之前,尧舜禅让的故事已经流传,它的首倡者,当另有其人。
当然,从道理上说,如果天子也要选举贤人担任,那么“尚贤”与“禅让”就不能没有一致之处。墨家援引尧举舜为天子的故事来为“尚贤”说服务,虽非出于自觉,但客观上对尧舜禅让说的传播起到了促进的作用,这也是不可否认的。
总之,尚贤说为禅让提供了道理上的支持,但却无法说明墨家比儒家更有理由成为禅让说的发明者。
四、儒家“歷数”暨“天命有德”乃禅让说的基础与前提
墨子的“尚贤”说目的只为治官,它的某些原理客观上有利于禅让,这说明,墨子只能是禅让说的不经意的传播者,而非发明者和积极的首倡者。那么,“歷数”与“禅让”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如上所述,《说文》训“歷”为“过”、“传”、“越历”,得到了文献的证明。其实,“禅让”的“禅”字也可训解为“传”。“传”的本义指“传车”,类似后世的驿车,用为动词,可引申为辗转传承或传递[25]。在这个意义上,“歷”、“禅”二字可通用。“传”是个动词,是动词就一定有它的主体,这个主体是什么呢?或者说,究竟是什么东西在“传”呢?
按“歷”字在《周书》多作“歷年”,指王朝统治时间的长短;“数”既指年数,又指必然的趋势,后者与“道”、“理”相当。和起来,“歷数”应该既指统治时间的长短,又指决定统治时间长短的某种必然力量。因为经历若干年数的,一定是某种东西,这个东西(如“数”字所隐含的“力量”)是什么呢?《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曰:“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26] (P1868)这句话告诉我们,决定王朝统治历年的是“天命”。前面所引《召诰》之文,也表明王朝统治长短只是外在的表现或结果,决定它的内在的力量或原因是天命。所以说,天命是决定王朝统治长短的必然力量。
儒家天命思想认为,上天树立君主,是为了治民,而治民则是为了养民。天命论和民本思想是一体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②“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③ 天没有自己的利益,一切以“民”的要求为转移。由民本,必然发展到天命无常。由天命无常又必然导致革命——即天命的更改和转移。《尚书·多方》:“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有夏。”蔡沈曰:“言天惟是为民求主耳,桀既不能为民之主,天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使为民主。而伐夏殄灭之也。”这就叫做“殷革夏命”或“成汤革夏”[12] (P113,103,102)。由于宗法政治的特点,除了征伐,当时还看不到异姓嬗代的事情,不过,这个说法毫无疑问可为禅让提供理论上的前提。
天命论与禅让说的内在联系,在孟子那里得到了自觉的说明。《孟子·万章上》:“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15] (P385)朱熹解释道:“禅,音擅。禅,授也。或禅或继,皆天命也。”[9] (P309)禅和继都是天命使然。
按照孟子的想法,禅让和征伐,形式虽不同,但皆出于天命则是一样的。具体言之,“天命有德”是相同的。这个思想源于西周初年。《周书》有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④ 周公从殷革夏命和殷周递嬗的历史教训中认识到,天命是无常的,它不固定于某个人或政权,只以是否有德为转移。今文《尚书》中保留了许多这方面的资料。《召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6] (P213)
战国时期,燕国因子哙和子之的“禅让”而发生内乱,孟子认为“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15] (P168)他向齐宣王进言,请求出兵伐燕。孟子赞成禅让,可为什么公开反对这次的“禅让”行动呢?他的思想基础是什么呢?下面这段材料似可说明问题: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15] (P379-380)
万章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15] (P381-382)
在孟子看来,君主能荐人于天,而不能要求上天把权力转给他人,更不能擅自把天下转给他人。上天所爱的人,必是民所爱的。而民所爱的,必是有德的人。可见,孟子反对燕王哙和子之的“禅让”,是批评他们违背天命有德、擅自授受最高统治权。儒家尊贤思想其实就是天命有德的一部分。前面提到,孔子有举贤才的思想。孟子主张“尊贤使能,俊杰在位”[15] (P134)。尧舜之所以成为禅让故事的主人公,就因为舜的形象最符合天命有德的贤才标准。这在近年整理出版的楚简中得到很好的说明。如《郭店楚简》中的《唐虞之道》认为,禅让就是“尚德尊贤”,尧之所以把天子之位授给舜,是因为听说舜为人孝弟,能养天下之老,能嗣天下之长,可以为民之主[27] (P158)。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容成氏》历数上古帝王事迹,讲到尧舜禹的禅让,都是“不以其子为后”,而欲以贤者为后,选好贤者,才“以天下壤(让)于贤者”[28](第12简,13简,17简,34简,P258,259,263,275)。什么是“贤者”呢?“履地戴天,笃义与信,会在天地之间,而包在四海之内,毕能其事,而立为天子。”[28](第9简,P257)这样高的标准是特为选天子而定的,与墨家所谓先王“选择贤者以为其群属辅佐”的选官标准是大不相同的。可见,即使到了战国,讲禅让的仍然是儒家的天命有德的尊贤思想。
总之,在儒家,《尧曰》章中的“歷数”一词以及尧舜禅让故事有着丰厚的语言和思想背景,早期儒家传诵尧舜禅让故事,目前还不能证伪;作为表现最高统治权转移的重要概念,“禅”和“让”都为儒家所有;儒家天命有德思想可为禅让说提供直接的理论基础和前提。战国秦汉间,儒家天命论(含尊贤说)构成禅让说的理论基础(刘歆以后,五行相生的新五德终始说也纳入儒家天命思想,成为禅让说的又一个重要理论资源)。在墨家,并无禅让之说;其“尚贤”论以选官治官为目标,在趋向上与禅让说有着本质的不同,但它借用尧举舜为天子的故事,说明尚贤使能的必要性,在客观上,为禅让说起到推波助澜的呼应作用,虽为无意,影响却是不能否认的。在这样的背景上,禅让说的兴起庶可得到一定的历史的说明。
注释:
①马王堆帛书甲乙本均作“多闻数穷”,见高明《帛书老子校注》,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46页。
②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襄公三十一年,穆叔引《太誓》语,《十三经注疏》本,第2014页。
③焦循:《孟子正义·万章上》引《尚书·泰誓》,《诸子集成》本,第1册,第381页。
④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僖公五年虞大夫宫之奇引《周书》逸书语,《十三经注疏》本,第1795页。
标签:论语论文; 墨子论文; 儒家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尚贤论文; 孟子论文; 国学论文; 孔子论文; 周书论文; 墨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