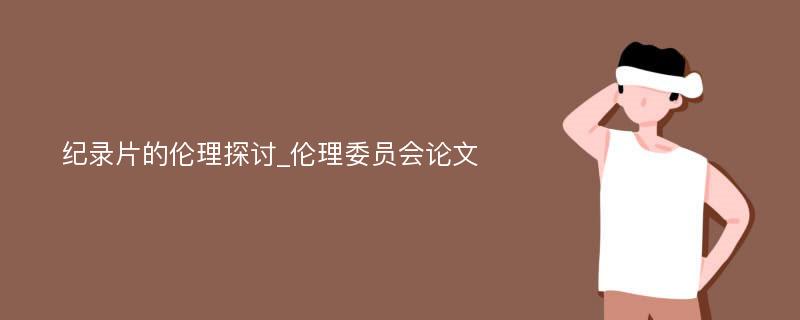
纪录片伦理问题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纪录片论文,伦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道德生活,它试图建构一种能够指导人类行为的法则体系来解决“我们应该怎样处理事件”以及“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处理事件”的现实问题。伴随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伦理学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从希腊罗马伦理学、中世纪基督教伦理学、文艺复兴时期理学到近现代伦理学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伦理学在各个时期出现了很多流派,划分这些伦理学流派的标准就是对“道德与经济利益的关系、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在纪录片制作中,对“道德与经济利益的关系、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的不同回答直接反映了制作者的价值观与审美观,如果处理失当,很可能导致纪录片艺术价值贬损。因此,纪录片伦理问题在纪录片价值判断中占有较重的分量,美国纪录片制作者Michael Rabiger甚至说:“唯有考虑到伦理问题,才能有真正纪录片的产生。”①纪录片伦理问题的核心就是分析制作者、被拍摄者以及观众围绕纪录片制播过程中的利益冲突而出现的道德困境。
纪录片伦理难以把握的主要原因在于伦理本身的复杂性。衡量标准因人因时代而异:不同民族有不同伦理标准,不同宗教有不同伦理标准,教育工作者有教育伦理,医疗工作者有医护伦理,既有社会普遍伦理,又有特定个体伦理。郝跃俊遵循让·鲁什开创的人类学纪录片工作模式,把《普吉和他的情人们》带回哈尼族村庄放映,因为该片呈现了哈尼族的真实生活,族人们看完后非常高兴。但是一些人类学家却对该片的拍摄手法提出了疑问,认为它侵犯了哈尼族的隐私权②。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对伦理的理解也有很大差别。在1998年上海国际电视节的评奖中,中国评委曾建议给《舟舟的世界》最佳人文类纪录片奖,但荷兰评委的意见与中国评委相反,他认为舟舟在这部片子中像一个玩偶,并说这样的片子在荷兰是不允许播放的,美国评委对此也有同感。③Michael Rabiger在BBC工作时制作的一部纪录片出现了这样的伦理困境:他在该片中加入了一个女工讲述同事性观念的镜头,结果播出第二天这名女工就遭到了同事的群殴。④纪录片影像公认的“真实性”产生的社会效应对被拍摄者未来影响的不确定性增加了纪录片实际操作中的难度和风险。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在播出《毛毛告状》时,曾制作了一分钟的预告片,宣传用语为“残疾人狠心弃女,外来妹千里寻夫”。这两句话使得当事人赵文龙非常害怕,他打电话给编导说:“昨天晚上看了你们的节目预告,今天一早我发现邻居们的眼神都变了,假如片子播出来我还能活吗?”⑤美国纪录片制作人芭芭拉·柯普尔(Barbara Kopple)的《美国哈兰郡》(Harlan Country,U.S.A,1984)一片记录了明尼苏达州奥斯汀肉类包装厂的劳资纠纷。因为摄影机的介入,整个事件最后朝向了有利于工人的方向发展。相反的例子则是东方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不了情》。由于摄像机的介入,一个远在云南的知青女儿回到了上海与从未谋面的父亲相会,但“也正是由于镜头的介入使得一个对女儿怀有爱心却极具自制力的父亲无法与女儿建立起一种正常的父女关系。因为镜头横亘在中间,破坏了那种带有私密性的极敏感而脆弱的情感交流。”⑥
斯洛夫斯基在拍摄纪录片《车站》的一个夜晚,刚好有一个女孩谋杀了自己的母亲,并把尸体分解后放进了车站的自动寄存柜,警察因此没收了基氏当晚拍摄的全部素材。虽然警察并没有在胶片上找到那个女孩,但是这件事对基氏产生了强烈的震撼:“没错!我们没有拍到那个女孩,可是万一我们拍到她了呢?只要当初我们把摄影机向左转,而不是向右转,就可能把她拍进去。然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就变成了与警方串通一气的告密者。就在那一刻,我明白自己再也不想拍纪录片了。”⑦制作者个人伦理与社会伦理的冲突也是纪录片的伦理困境之一。
纪录片伦理问题的主要指涉对象就是被拍摄者、制作者和观众,其相互关系构成了纪录片伦理研究的全部内容。在三方互动中,纪录片制作者应占据主体地位。因为观众是以未来时态不断形成的不确定集合体,所以对观众只能用社会普遍伦理来约束。而被拍摄者是纪录片制作者选定的,制作者是施动者,因此,纪录片伦理主要集中探讨以制作者为中心的三方关系。
一、制作者与被拍摄者的关系
王慰慈说:“纪录片常常吸引我注意的还不仅仅是纪录片的形式而已,主要的还是在于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⑧在制作者与被拍摄者的关系处理中,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制作者要尊重被拍摄者。《BBC制作人指导原则》要求纪录片制作人对被拍摄者以诚相待,不能欺骗他们。⑨在《电力与土地》的拍摄中伊文思也说:“不要不尊重别人的职业自尊心,不要叫一个农民去挤一个已经挤过奶的牛。”⑩纪录片制作的合作关系是建立在互信的心理基础上的,纪录片制作者要对被拍摄者的合理要求尽可能满足。段锦川《八廓南街十六号》的素材中有一个老头的生活片断,他不断向段锦川告状说女儿不养他,并为此要和女儿分家。段锦川认为这个部分很精彩,为此拍了很多素材,包括居委会到他家调解的过程都拍下来了,但后来那个老头认为他的形象在这部片子中不太好,表示不希望播出,于是段锦川就把这个部分拿掉了。(11)
纪录片制作者的艺术追求与被拍摄者的个人利益很容易产生冲突。《北方的纳努克》一片的拍摄实际上就形成了对纳努克私人生活的侵入,而弗拉哈迪制作该片的原意就是反对西方文明对原始部族的侵蚀与残害,这实在是一个悖论。无论弗拉哈迪在主观上怎样尊重纳努克,其拍摄行为在客观上都对纳努克一家产生了巨大影响。“最具讽刺意义的悲剧发生在《北方的纳努克》上映的第二年,由于纳努克一家过多地卷入了影片的拍摄,加速了自身生活形态的瓦解,生活在弗拉哈迪离开后变得更加困苦。就在纳努克的面孔和名字随着影片的轰动传遍全球之时,他却在饥寒交迫中死去。”(12)在纪录片《摩阿拿》中,弗拉哈迪为了重现一个消逝已久的习俗而让一个当地青年人进行刺青,这个过程对人的肉体来说是非常残酷的,而弗拉哈迪这样做的原因只是为了使他的纪录片获得视觉奇观。在《亚兰岛》一片中,弗拉哈迪为了拍摄渔民捕鲸的场面曾让被拍摄者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当时的拍摄地点邦格拉“濒临波涛汹涌的大西洋,海浪撞击崖壁,掀起三四百英尺高的巨浪。暴雨下的邦格拉,被掀上岸的渔船倒扣在岩石上任凭风雨蹂躏。鲍普(弗拉哈迪)说:‘为了拍我们的电影而让人丧命,光是这么一想就非常可怕。’”但最后弗拉哈迪为了展现这个壮观的场面还是选择了一个渔民来拍摄,拍摄时“天色阴霾,海浪像山脉一样汹涌而至,狂风嘶叫着穿过耳边。”幸运的是,最后没有出事,“这部影片在伦敦上映时获得了巨大成功。”(13)基耶斯洛夫斯基说:“并不是每件事情都是可以被描述的。这正是纪录片最大的问题。拍纪录片就好像掉进自己设下的陷阱一般,你愈想接近某个人,那个人就会躲得越远。那是非常自然的反应,谁也没有办法。如果我想拍一部有关爱的电影,我总不能在人家躲在房间里做爱时,跑进他们的房间里去拍吧!如果我想拍一部关于死亡的电影,我也不可能去拍某人真正死掉的过程。因为那是一个非常私密的体验,谁都不应该在那个时候受到打扰。我注意到当我在拍纪录片时,我愈想接近吸引我注意力的人物,他们就愈不愿意把自我表现出来。”(14)最终,基氏因为个人艺术追求与被拍摄者的利益冲突而放弃了纪录片制作。
纪录片制作者和被拍摄者在制作过程中对各自生活的相互进入(例如吴文光拍摄《江湖》时吃住在大棚里)很容易引发伦理问题。纪录片制作者似乎要为主动介入被拍摄者生活的行为承担相应的现实责任,即如果这种介入对被拍摄者的生活带来了损失和伤害的时候,纪录片制作者应该补偿。但是,现实往往比理论更复杂。“让·胡什(Jean Rouch)在制作《夏日纪事》(Chronicle of a Summer,1961)时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雷诺汽车厂的机械工安吉洛在上班时间接受了《夏日纪事》摄制组的采访,于是工头就到老板那里告他的状,同时故意给他压大量的活。这样安吉洛感到没法干下去就辞了职。因为安吉洛是参加纪录片拍摄而丢的饭碗,于是让·胡什就设法另外给他找了一个工作。但是这个工作安吉洛没干多久,因为他组织工会活动,并代表工会向资方交涉,不久他又被开除了。”林旭东于是在这里发问:“那么这个时候导演是不是还应该要继续对他负责任?”(15)有的制作者介入被拍摄者的生活为其带来了部分利益。基耶斯洛夫斯基在制作纪录片《初恋》时通过波兰电视台为这对新婚夫妇搞到了一套公寓房。在当时的波兰,按常理这对夫妇至少要等十多年才会有分配房子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拍摄的深入,新的问题出现了。基氏原打算每隔两年就去拍一段这对夫妇的生活,但是后来他发现这样做可能会拍出一些别人用来对付他们的不利证据,于是就停止了拍摄。基氏说:“我个人认为,我们不应该利用纪录片来影响片中人物的生活,无论是好,是坏,都是不对的。纪录片不应该造成任何影响,尤其是关于人物人生观的部分。这一点你必须分外小心,这是纪录片的陷阱之一。”(16)
制作者和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纪录片制作模式里有不同的界定,这种不同的界定使得一个统一的纪录片伦理观很难形成:它到底是一个商业工程?还是一个艺术项目?或者仅仅是一个等待进行大众传播的人际交往行为?纪录片制作者代表的是谁?他们是雇佣关系还是朋友关系?如是雇佣关系,付费后有可能使得被拍摄者迎合制作者而出现影像失真。如果是朋友关系,那么纪录片拍摄结束后这种关系该如何调整?
有很多纪录片工作者常常为了方便拍片而主动和被拍摄者交朋友。李红在谈及纪录片《回到凤凰桥》时说:“因为这种拍摄的行为而产生人和人之间密切的关系我觉得是具有太明确的目的性了。……好像我把这种亲密的关系变成了一个自己的东西。”彭辉说:“我觉得拍摄纪录片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跟拍摄的人物成为朋友,如此他才能把真实的生活情节表现在摄影机面前。”(17)这种带有功利色彩的朋友关系如果处理不当,事后会让被拍摄者产生被欺骗利用的感觉。怀斯曼在一次采访时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会尽量不那样去做,我会试着对他友好,我也希望自己是真诚而不是虚伪的,我会向他表明我们成为长久的朋友不太可能。我不会那样去做,因为它会形成误导。”(18)
法国纪录片《是和有》公映后出现的纠纷使得对纪录片伦理问题的追问指向了纪录片商业属性问题,对制作人进行伦理审判还是刑事审判似乎只在一线之间。“《是和有》的票房非常好,在当年的法国名列前茅。估算的影院票房收入约为1000万欧元(折合约1亿元人民币),再加上电视版权、碟版权、国外版权,总收入很容易被想象为天文数字。此时,被拍摄者不干了,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愚弄,因为他们配合拍摄时并没有收取酬劳。菲利贝尔以前的作品都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其他绝大多数纪录片制作者也很难碰到这个问题。菲利贝尔当时征求了所有被拍摄者的意见,并根据法律规定与孩子们的家长签订了书面许可。在长达数月的拍摄中,也没有想到要让长时间合作的成年人签订合约。《是与有》中的老师先把菲利贝尔告上了法庭,大意有侵犯肖像权和酬劳两个问题,两个问题还必须在两个不同的法庭审理,因为属于刑事和民事两个不同的部分。肖像权问题很模糊,因为作为一个成年人与一个纪录片摄制组合作了那么长时间,没有理由事后翻悔,而在当时不提出比如要化了妆再上镜等问题。肖像权问题的成立,在本案中只在与诽谤相关联的情况下才成立,而该片实在无法充当诽谤的证据,所以老师败诉了。少部分对老师有利的证据,就是菲利贝尔根据惯例曾经向他说明纪录片是一种基本不挣钱的买卖。这一点菲利贝尔并不否认。他拍了那么多年纪录片,这些影片一向是在影院放映的,影片《是和有》是第一回在全国大卖。家长们起诉的要求从2万元到20万元(人民币)不等,虽然他们胜诉的希望比老师更加渺茫,但非常让人揪心,尤其是个别家长甚至可能把孩子传唤到法庭上作证。现在,西欧的大部分制片公司都要求重要的被拍摄者签署文件表明自己同意被拍摄,酬劳问题在通用文件中并不涉及。在版权问题上的差别是,法国将道德权与经济权彻底分离。污蔑别人不是可以通过花钱来补偿的,而是要负刑事责任;剥削别人不是道德问题,只要把钱赔出来就完了。”(19)
二、制作者、观众和纪录片的关系
制作者因为纪录片拍摄而留下心理创伤的有这样一个案例。台湾纪录片工作者陈淑兰提到台湾阳光基金会曾去拍一个火灾事件的受害者。这个人在火灾中失去了婆婆、丈夫、小孩,目前只剩一个儿子,她本人在火灾中也有百分之八十的烧伤。当时距火灾事件已有四年,拍摄者以为她的心灵创伤已经愈合了。孰料一到她家,却看到房子里四处都还有火灾熏黑的烟渍。这个受害人说:“我要留住那些烟渍作为我最亲爱的人消失的纪念。”在拍摄过程中,拍摄者并没有做很多的引导,完全是她的自述。结果,她崩溃了。制作者事后说:“至今我回想起那段过程,仍会发抖。”(20)也有制作者把纪录片当成自我治疗的工具。《亲密的陌生人》的导演艾伦·贝利内(Alan Berliner)在叙述自己何以成为一名纪录片导演的时候,特别强调了自己内心的创伤和拍摄影片所带来的心理治疗的效果。他说:“事实上,我从来未曾下决心成为一个电影导演,也许应该说是内心的痛苦与彷徨,驱使我进入了这个领域。成年之后,我长时间地为家庭的冲突与矛盾所困扰。很多事情记住了,很多也已经忘却。当我偶然翻检过去的家庭录像的时候,那些早已经被我遗忘的画面竟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这些画面被用到影片中,就成为了一种影像的治疗,甚至成为治愈某些童年创伤的一剂良方。”纪录片《我的建筑师》结尾处导演自述:“通过这次旅行,父亲成为了一个实在的人,而不是一个谜。现在我对他了解更多了,这也让我对他更加地思念。我真的希望一切可以是另外的样子。但是他选择了他想要的生活。真的很难释然,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我想现在我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时间和地点说一声‘再见’。”在影片结束的时刻,导演纳萨尼尔终于化解了自己的痛苦,平复了长久以来的创伤。(21)
观众和制作者发生关系主要是通过纪录片这个载体来进行的,其中的伦理问题与纪录片本体论中的“真实性”问题密切相关。通常来说,不能欺骗观众是制作者所要恪守的伦理底线,即如果片中有搬演场景,应向观众说明。1993年2月2日,NHK制作于1992年的纪录片《禁区——喜马拉雅深处的王国:姆斯丹》有假一事被揭穿。该片中没有向观众说明的扮演、替代、臆造共有19处。最后,NHK节目制作局各负责人受到了降职或减薪的处分。(22)聂欣如在《纪录片研究》一书中(269-284页)对“搬演”这个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将搬演分为欺蒙和非欺蒙搬演两大类,非欺蒙搬演又分为告知搬演、自明搬演、无害搬演和非虚构搬演。聂欣如说:“‘无害’和‘非虚构’在美学上相对边缘,如不能很好把握分寸便会有堕入‘蒙蔽’和‘欺骗’的可能。”“无害”搬演的具体案例来自于陈晓卿就《森林之歌》一片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的采访,陈晓卿说:“我在日本培训的时候,学习他们那个《大白鲨》,一个小的大白鲨,从出生地跟着母亲顺着洋流漂流,从开始的懦弱、害怕、胆小、逃避、不愿意面对责任,到面对了海浪、潮汐、岛屿,躲过了人的捕杀,最后变得特别强大,变成了一条真正的鲨鱼。……但它是编的故事,不是这条鲨鱼它本身是这样的。它们拍了好几条鲨鱼,而且它大量的镜头是在鱼缸里拍的。比如鲨鱼加速、攻击,这些拍摄在海里面的的确确几乎是没有可能的,尤其是攻击的一刹那。这个片子得了艾美奖的一个技术奖。当时就知道外国人是这么做。2001年到英国BBC去看他们做《蓝色星球》的时候,就知道实际上大家都这么做。……一切为了观众,怎么能争取更多的观众就怎么来做。(23)这种没有说明的无害搬演是否对观众形成欺骗,聂欣如把它归结为制作者主体对“分寸”的把握。
换一个角度来看,陈晓卿提及的案例也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了高尚的制作目的,在制作手段上是否可以不顾伦理的底线?伊文思在拍摄《四万万人民》时曾遇到过这样的伦理困境。当时伊文思为了拍好台儿庄战役这一部分素材,让摄影师杰克告诉担架上的受伤士兵不要看镜头。但杰克并没有这样做,他说:“我不能对自己的人喊叫。他们打得这样苦,他们受了重伤。我非常尊敬他们,因此我不做声。指挥他们看这儿,别看那儿,是很残忍的,我希望能有什么办法来帮助他们。”伊文思说:“我们帮助他们的唯一办法是拍好一部影片,以电影的专门特点来感动人,使人们看到和了解到,为了抢救伤员需要一副好的担架。约翰、卡帕和我与杰克一样对中国伤员很尊敬,但是我们不能允许这在我们工作的时候影响我们的情绪。当然,从客观来说,这么触痛别人的忧伤、私生活和感情是考虑不周麻木不仁的。不过在西班牙,在博里纳奇和煤矿工人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们懂得了你非如此不可。”(24)与之相反的观点为台湾纪录片理论工作者王慰慈所述:“纪录片拍到后来就是一种态度和精神,重视的是过程的正当性而不是以不道德的手段去追求艺术性及价值性。”(25)基耶斯洛夫斯基说:“你永远都无法预知一部电影的结果。每部电影都会有一道窄阀,我们只能凭着自己的判断力决定自己是否应该跨进去。当我知道自己拍的电影《守夜者的观点》一旦在电视上播映之后将会对片中的主角马利安·奥索区造成伤害时,在那一刻,我撤退了。”(26)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再次说明了制作者在纪录片伦理中的主体地位。每个制作者的伦理底线都不一样。对于拍摄过程的具体操作,什么该拍,什么不该拍,该用什么样的角度和景别,这些技术细节都体现了制作者不同的伦理观点。安东尼奥尼在拍摄《中国》时“反常地一再坚持拍摄主人请求他不要拍摄的事情,比如停泊在上海港的军舰,乡村路边的集贸市场。他甚至用望远镜头拍摄了一个葬礼场面,尽管主人劝告他说拍摄葬礼场面是触犯中国人隐私的”(27),而伊文思制作《愚公移山》系列纪录片时只有一部运用了这种偷窥方法。台湾纪录片工作者彭世生说:“我比较关心所拍的片子会不会对不起主角。我认为只要对得起他,都可以拍。如果经过他同意,即使是法律不允许的打猎画面,我一样会剪辑进去。我一直以这样的心态拍他们,又一直得奖,可是对他们又似乎没有什么帮助,这才是我最在意之处。”(28)杨荔钠作完《老头》之后,每次骑车再路过那群老头时都没有勇气停下来和他们交谈。因为她觉得《老头》没有给这群可怜的老头带来任何实质性帮助,而自己却因为《老头》四处收获名利。(29)李红和王慰慈谈及《回到凤凰桥》时也表达了她面对类似困境的矛盾心情。
综上所述,纪录片伦理问题中常见的利益冲突主要有两类:1.制作者、被拍摄者和观众的利益冲突,包括经济利益的得失以及身体(生理和心理)的伤害或康复。2.制作者、被拍摄者和观众不同职业伦理的冲突以及职业伦理与社会普遍伦理之间的冲突。在这两类利益冲突中,起关键作用的都是纪录片制作者。因此,纪录片的伦理问题最后实际上是制作者的个人伦理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它只能通过制作者的个人良心来进行控制,并“必须依靠拍摄者的良知来建立良好的道德与权利关系。”(30)David M.Fetterman说:“制作者首先要认识纪录片本身,具有相当大的剥削力和侵犯力,以利益获得的角度来看,拍摄者是窃取被拍摄者的影像成就自身的声誉。制作者因此要永远面对内在自省的压力,建立自己与被拍摄者互利永续的关系。”当纪录片制作者把被拍摄者当成一种表现资源进行剥削而不自知时,有意利用各种伦理盲区为自己谋利益时,以制作者个人良心为对象进行的道德拷问与自我反思才成为了纪录片伦理研究的起点,正如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说:“有两种伟大的事物,我们越是经常、越是执著地思考它们,我们心中就越是充满永远新鲜、有增无减的赞叹和敬畏——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
注释:
①④Michael Rabiger:《制作纪录片》,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365页,第366页。
②(20)(25)(28)王慰慈主编:《第三届文化纪录片研讨汇集》,(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委托发行,第246页,第202页,第303页,第236页。
③刘敬东:《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关于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另一种感知》,《电影艺术》2000年第3期。
⑤王文黎:《我的朋友赵文龙》,出自《目击纪录片编辑室》,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版,第123-125页。
⑥吕新雨:《人类生存之镜——论纪录片的本体理论与美学风格》,姜依文主编《生存之境》,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⑦(27)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340页,第297页。
⑧王慰慈:《纪录与探索——与大陆纪录片工作者的世纪对话》,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96—195页。
⑨[英]劳伦斯·瑞兹:《如何制作纪录片》,陈刚译,《当代电影》,2002年第3期,第83页。
⑩(24)伊文思:《摄影机和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版,第175页,第154—155页。
(11)(17)(30)王慰慈:《记录与探索——1990-2000大陆纪录片的发展与口述记录》,国家电影资料馆(台湾),第135页,第422页,第625页。
(12)游飞、蔡卫:《世界电影理论思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页。
(13)本引文和前两处引文均引自(美)弗朗茜丝·H·弗拉哈迪《一个电影制作者的探索——罗伯特·弗拉哈迪的故事》,季丹、沙青译,《纪录电影文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239页。
(14)(16)(26)Danusia Stok:《奇士劳斯奇论奇士劳斯奇》,唐嘉慧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134页,第116页,第126页。
(15)林旭东:《影视纪录片创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页。
(18)2009年5月5日检索自http://www.geraldpeary.com/interviews/wxyz/wiseman.html。
(19)张献民:《成长的艰难——关于尼古拉·菲利贝尔的〈是和有〉》,《当代电影》2004年第5期,第154页。
(21)王迟、权英卓:《影像的救赎:论自我治疗纪录片》,《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第80页。
(22)钟以谦:《NHK:纪录片扮演风波》,姜依文主编《生存之镜》,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页。
(23)《陈晓卿:讲述〈森林之歌〉拍摄故事》,《北京青年报》2008年01月16日。
(29)《老头》系杨荔钠处女作,获1999年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亚洲新浪潮”优秀奖,2000年法国真实电影节评委会奖,2000年德国莱比锡电影节金奖、观众最喜爱影片奖,法国以12万法郎的价格购买其电视放映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