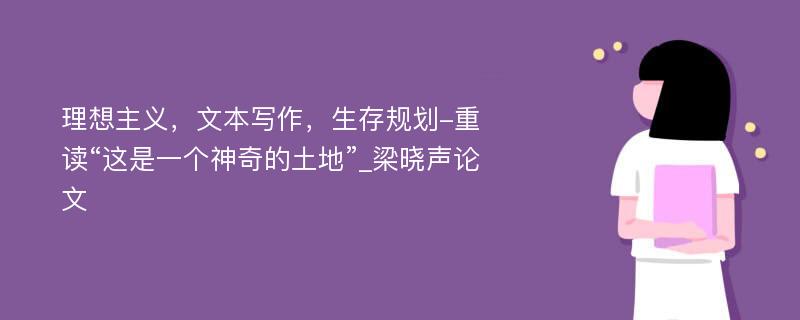
理想主义、文本写作、生存谋划——重读《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这是论文,理想主义论文,文本论文,神奇论文,土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文精神”大讨论自1993年开始以来到现在已经两年有余了,虽然景观不再那样轰轰烈烈了,但仍可说是不绝如缕。可是静下心来想一想,除了那近于漫画式的两幅脸谱外(带有红卫兵情结的、自我膨胀的、近乎偏执狂的理想主义,与清醒的、带有几分调侃的、操着后现代话语利器的解构者),究竟有多少切实、细致而真正富于建设性的成份?无怪乎有人提出这样的批评式的衷告:人文精神的讨论“一旦离开了真实的文化背景和作家必须直接面对的创作问题,讨论就难免不在抽象精神的迷宫中捉迷藏了。”〔1〕但是仅仅是批评与指责并无济于事, 重要的是去脚踏实地工作,以实际行动跳出“捉迷藏的话语游戏”。所以在此我们想仅分析一篇“理想主义者”的文本,具体看看作为一个切实的在世的存在的“理想主义者”的文本生产与其存在的谋化的同一性,进而试探“理想主义”之存在的复杂的意义侧度。至于为何选择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以下简称《土地》)作为样本,主要是考虑到梁晓声作为小说创作者,在作品题材、内在气质、叙述风格等方面的相对一贯性,以及《土地》对于他的整体创作的重要性与代表性。
一
我们都知道《土地》为梁晓声在当代文坛赢得了广泛的名誉,不过这更多的是关涉别人对他们社会性评价的问题,而不是我们所关心的重点,我要考虑的是这篇作品对他本身的生存谋划的意义。因为写作既不是人的主观思想情感的流溢,也不简单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而是具体的人的存在的行为、存在的谋化、存在方式的呈现。一个写作者以写作来谋划、呈现作为“这一个”的存在;反之我们通过阅读他的作品,在阐释和被阐释的对话性结构中,观照他的存在,并以此而反观我们自身。所以,人的在世的存在之谋划,就可以且应该是文本阐释的基点。
那么,《土地》对梁晓声作为一个小说写作者的存在性意义何在呢?我想重点围绕“象征”来讨论这个问题。
只要对梁晓声的作品有一定了解,就很容易发现他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其主要作品往往充沛着激情。而我们知道,浓烈的激情一般适应于以诗体来呈现,而相对于散文体的小说叙述来说,就有可能会是一种障碍。因为小说〔2〕相以来说是一种时间性的艺术门类, 一般是通过所叙述的事件的延展形成一种“线型”结构;而激情的燃烧则是一种空间化的“团状”结构。解决这种“文体矛盾”的方法之一是将象征“引入”叙述,将时间性的文本尽量空间化,借象征以激情之火熔化叙述之链。《土地》正是这种情况。实际上一个“象征化”的叙述文本的诞生,是以一个具体的写作者的存在性谋划为基础的复杂的文本生产。为说明此点我们需要先放下《土地》,引进梁晓声的其他几篇文本进行参照性分析。
梁晓声是以知青题材的写作称誉当代文坛的,但实际上他一开始的写作并非是知青题材,而且在《土地》同期及以后还写了一些并不很激烈的“市民”〔3〕小说。这里我仅举四篇分两组讨论。它们是, 《作品欣赏第一课》(以下简称《第一课》)、《在A城》、 《西郊一条街》、《八月十五月儿圆》。头两篇作品就内在的激情而言,显然是与《土地》一脉相承的,可看作是《土地》诞生的准备期作品。它们给人的直接阅读感受是“生硬”。《第一课》将叙述的场所安排在课堂上,他以教师、叙述者、事件的亲历者与见证者的四重身份,面对着讲台下的学生进行讲述,而且直接的讲述动机,就是想用有关美、正义的来感染、打动并教育听众(读者)。这种讲与听的模式显然是同文革中盛行的“英模报告会》、“忆苦思甜报告会”的模式一样。即讲述者——听者、教育者——被教育者、(话语权力)操纵者—被操纵者等多重二元对立结构的同构。而作品中讲述者与故事主人公阿衣拉达之间,又相当明显地含着“自我—镜像”的自恋性关系。主人公阿衣拉达是个少数民族姑娘,集真善美于一体。讲述者在新疆招生时发现了她,并许诺来年要将她招进艺术学院深造。可是命运多桀,他被“四人帮”的爪牙们贬落到新疆,与阿衣拉达在苦难中意外地相遇,最后阿衣拉达为了保护他《与恶势力相抗争的勇士)和爱他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由上述梗概很容易看出,与其说是讲述者在歌颂牺牲者,毋宁说是在钟情于自我完美形象的观照,观照之光的发源体之所以要照亮对象,是要这个对象来为自己献身。
《在A城》虽然表面上这种单一硬性的“讲—听”模式有所改变, 但实质上仍然没有变化。中心人物高远和老导演的关系,无论是细节性质还是结构关系仍然同上篇相同:老导演(讲述者、见证者、自我)—高远(被讲述者、英雄、镜像)。而且听众仍然是直接或半直接地作为纯粹被动的待感化者在场的。总体结构如此,而且具体叙述也非常密实。片断与片断之间、句与句之间、甚至词与词之间毫无间隙,直奔主题和中心人物及中心情感,好象连一个薄薄的刀片都插不进去,毫无语言的弹性。〔4〕作者写作显得吃力,很累,阅读后的感受也很累, (这倒不是文字有什么费解的累,而是某种被迫的正襟危坐听报告的累。)应该怎样理解这种“生硬”、“吃力”的叙述呢?当然可以推潮到文革话语的影响,或可说是因为作者没有学会怎样讲故事。但恐怕更本质的原因不在于技巧掌握的与否,似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历史影响的遗留,而在于作者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过于直接,直接受控于主流和传统意识形态的话语结构吧。这在第二组作品中表现得更为直接。
《西郊一条街》和《八月十五月儿圆》,都可算是写“城市平民”的〔5〕,写他们的生死聚散、悲难离合。 两部作品虽是短篇但时间跨度都相当大,起始于五十年代初工商业改造之前后,中间经过三年自然灾害、文革、一直到七八十年代之交个体工商业重新发达止。叙事的重点放在开始与结尾这两个时间段,涉及两个家庭“三代人”〔6〕, 三代人物的命运严格对应于历史时代的变迁。在第一阶段五十年代初,两家由于时代命运的支配,成为相互矛盾的双方,得势一方的家长坚决反对他们儿女双方的自由恋爱,造成年轻一代爱情、生活的悲剧。而转瞬间闪过六、七十年代,新的一辈人又上演了几乎同他们的父辈完全相同的生活与爱情戏剧。所不同的是由于粉碎了“四人帮”,纠正了极左路线,重新带来了集体或个体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并且原先代表善良、正义的弱者的一方,在政治经济上都翻了身,因此第三代人的爱情自然是“八月十五月儿圆”,有情人对饮把盏共赏嫜娟。真象是旧社会使人家破人亡,新社会使人重新幸福团聚。〔7 〕由此可以看出文本的时间框架完全符合于意识形态化了的历史时间逻辑,这个逻辑成为人物、故事、叙述延展性的绝对主宰。不仅如此,它还定死了文本的空间结构,人物基本活动在一种不变的位置场所中,并从事着相同的职业。在这种严格的时空限定下,人完全失去了任何偶然性,更不用提自主命运的真正自觉的谋划与选择,几乎就是意识形态化历史的傀儡。而作者正是又以这样一种存在方式的“记实性虚构”〔8〕之呈现, 展示他受控于抽象意识形态观念下的刻板的存在方式。
很显然听腻了文革“忆苦思甜”报告会的读者是不大会欣赏这种小说的, 甚至会反感或本能地抵触这种直接化的意识形态主体的招募〔9〕。他们需要的作品是所谓的生动、自然、形象的,是可赏、可喜、可悲的,要富于艺术感染力的。或换言之,他们的前反思的半透明意识〔11〕要抚摩的是,被经过软化、诗化、变形化了的意识形态的躯体——真而美的作品。而这样的要求不可能不反馈到小说创作者那里。因此,在此意义上《土地》可看作是对这种社会性阅读要求的反应,是这种要求间接促动下的产物。不过这涉及到读者反映的问题,姑且不论,还是将焦点聚在梁晓声这个个体存在者之上。
《土地》对他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营造一个象征化的叙事文本,他可以尽量回避前述的观念演绎的直白式的散文化叙述,而为自己的激情谋划一块诗意的象征空间,将自己的生存谋划与阅读的社会要求,更为有机地契合在一起。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块天地呢?
“那是一片死寂的无边的大泽,积年累月覆盖着枯枝、败叶、有毒的藻类。暗褐色凝滞的水面,呈现着虚伪的平静。水面下淤泥的深渊,沤烂了熊的骨骸、猎人的枪、垦荒队的拖拉机……它在百里之内散发着死亡的气息。人们叫它‘鬼沼’。”
“‘鬼沼’象希腊神话传说中令人恐怖的九头恶龙,霸占着它身后的万顷沃土上马平川,只要春天播下种子,秋天便能收回千万吨粮食。然而没有人敢涉过‘鬼沼’,去播下一粒种子。据说当年日本关东军的一个大佐,对那片沃土发生了兴趣,幻想在那里创建个农场,将来做个大农场主,曾亲自率领一个勘查小队在冬季越过了‘鬼沼’。他们如泥牛入海,一去未返……鄂伦春人把那万顷沃土叫做‘满盖荒原’。‘满盖’是鄂伦春语魔王的意思……”
“恐怖的‘鬼沼’!神秘的‘满盖荒原’!”。
仔细读上引《土地》一开始的描写会发现,经过作者的形象描述、传奇穿插和不同名称的交换(尤其是鄂伦春语和汉语称谓的变换),我们有些搞不清楚了那“神秘的满盖荒原”究竟指什么?是指那“恐怖的鬼沼”,还是指它身后的那片沃土,或是两者杂糅在一起都指?这是作者的笔误吗?或是与精神分析的“口误”相关的无意识呈现吗?都不是。这是一种叙述学意义上的语言修辞:指称的模糊性在此正是叙述者的一种语言策略,正与其要达到的叙述目的的含混性是一致的,或更确切地说是这种含混性的构成部分;否则就连小说的题目都站不住脚了。如果我们再进一步仔细分析这段文字还会发现“鬼沼”与其身后的“沃土”之间的方位上的“虚假性”。如果说“鬼沼”是有限域的,而且冬天因上冻是可穿越的,那么它并不能构成不可愈越的障碍,阻止人们去在沃土上开荒、种植、收获。因为按理来说人们完全可以在头年开化前穿过沼泽,到“沃土”上垦种、收获,等到第二年上冻后再返回原来的大本营,把丰收的粮食带回来;只要在进去时带够能维持到收获时的食物就行。而如果它是不可穿越的无限界域,那么它本身就不再是障碍,而是人物行动将要展开的场所。至于那片“沃土”不过是它上空的海市蜃楼而已,但却是使“鬼沼”神奇化、神圣化的不可或缺的幻影;如果没有这个幻影,作品主人公们的牺牲、叙述者对此牺牲的呕歌都失去了合法性。
也许会有人提出质疑:你这是在做考据,而非读小说:无论是“鬼沼”还是“沃土”并非是实指,而是艺术化的象征。不错正是因为如此,才需以批评的细读穿透“朦胧”、“暧昧”的象征表层,发现更核心的文本意韵。为此还需对文本进行结构化的辨析,发现文本的宏观结构与前引局部微观结构的一致性。
面对那块令人恐怖而神秘的土地,至少可以设想两种选择:掉头离开,把它从自己的视野中排除,或执拗地向它发起绝决的挑战,以牺牲来圣化它,使它成为“一片神奇的土地”。这两种选择就故事发生的起初来说,都是可能的,因为似乎并没有谁强迫那些兵团知青们去选择第二种行动,是他们自己拒绝被遣散;他们把这视为对自己青春生命的污辱,是对他们兵团战士名誉的贬损。文本这样的选择安排,就根本排除了第一种选择的可能性,而将荒原沼泽与知青们结构为不可分离的互证性存在关系:沼泽苦不可怕,不能吞噬年轻的生命,就无以证明知青们的英雄主义的存在;而知青若不是“自学自愿”地去牺牲,也无以圣化那可怕的沼泽。这样两者的互存关系,就脱离了具体实在的生活性意义,而上升为形而上的神化、圣化的象征性仪式表演。
然而正是这种象征性仪式化的转换,为激情的燃烧、情感的膨湃创造了最佳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情节延展的迟缓、叙述语言的密涩都可以被熔化。所以《土地》第一节的后一部分,和第二节关于“我”、李晓燕、妹妹等相关事情的叙述语言,虽然还是缺少弹性,比较直密,而且也较明显地裸露出作者的意图——证明他们是纯洁的,无愧于神圣的牺牲——但它们基本是做为叙述片断,被笼裹于激情化的象征天地里,而被忽略。或说,叙述的延展性被压缩了,历时性的链被相应地聚成了一个点;虽然这个点仍然在“横组合轴”上,但却以其浓聚性,隐蔽了线型叙述容易造成的苍白。因为激烈的情绪、硬直的观念、密实的语言,虽不适宜叙述,但却正好可以用来搅沸那潭死寂的沼泽。这样直接的意识形态的时空,就被幻觉似地超时空化了。再则,由于有了合适的象征化的言中介,讲述者与听者(读者)的关系也相应间接化了。讲述者不再是生硬地、直接地把读者拉进文本,对他们进行说教,而主要是以激情去“麻痹”他们的阅读的自主性抵抗,让他们“自觉”地从外部进入到这个象征性的空间中来。因为这个被诗意化了的空间,似乎更接近于独立,是与他们的感情相通的一个语言场,而不是令人生厌的作者的自恋冲动的外现;尽管从王志刚、李晓燕、“我”三人的关系上,也还可以看出“自我——镜像”的结构。
然而,如果我们的意识没有完全被诗意的语言所瘫痪,还能够抽身出来再向那归复了平静的沼泽投去一瞥,就会发现,除了泽边的三个木桩,并无其他生命的痕迹,更不用说什么神圣的生命的存在了。而那三根木桩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它们不会开口说话,不会讲述那逝去了的生命的故事。这样,整个故事发生的源头就发生了倒转,不是向前去追溯,而是要反回到讲述者那里去,反回到与作者同一化的“我”那里去。(梁晓声倒并不想隐瞒这种同一性)只是因为有了“我”,那本身是僵死的沼泽和木桩才有了生命,才被照亮,才被从时间的黑洞中释放出来,才能“还原”出那神圣而悲壮的一幕。于是,“我”就不单纯是一个过来人,也不仅是一个“圣迹”的讲述者与见证者,而且还是它的守护神,是它的光源体:“我”参预、“我”讲述、“我”见证了那圣化的故事,“我”也因此而得以圣化。所以“我”的意识之光,与其说是为他人照亮了曾有过的神圣的存在,毋宁说是照亮了“我”自己当下存在的神圣性。由此,讲述故事的行为与讲述者的存在谋划的同一性就昭然若揭了。
二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经大至可以看出,一个文学文本的诞生,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写作行为的结果,也非简单的生活反映,也不是作品间的艺术要素的自我生成,而是在意识形态话语网络中,与作者的生存谋化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复杂的文本生产。但是如果我们不把它纳入到更基本的人的存在的生存性选择上去分析它,它对写作者的个体存在性意义,还不能得到更透彻地揭示。而这正是此节所要探讨的。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反复地使用着“象征”这个概念,而并没有对它加以概念的解释或性质的描述。而且虽然我们将它同作者具体的存在性谋划、同意识形态召募主体相联系,但仍然还是隐隐约约地把它做为一种艺术手法看待的。那是为了行文安排方便的缘故,暂时性地暧昧地使用这个概念。现在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梁晓声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沼泽”作为其第一篇“成功”之作的象征物呢?我们能把它归结为艺术想象或形象思维的产物吗?恐怕不行。胡赛尔开启的现象学告诉我们,意识必须是对某物的意识,也即我们不可能凭空在脑中构造出一个形象性而非对象性的东西。我对一把椅子的想象,就是对某一椅子的对象性的意识,是一个对象性的存在物在我的意识中的表现方式,这种表现方式与我直接面对房间窗前的那把椅子的意识的表现方式,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异,只不过是意识把另一种对象在意识中的表现方式给予了对象。所以在任何情况下我们注意的不是形象而是对象。〔12〕
那么能把它归结为作者北大荒的生活经验吗?即作者过去的生活使他非常熟悉北大荒的“沼泽性”地质状况,所以当他进行写作时,就通过记忆与过去的经验发生了联系,进而把它表现在作品中。但这仍然是没有真正回答问题而是改变了问题的表述。尽管它承认了物本身的“客观性”,但却还是不能解释主观性的意识如何与客观性的物的存在联系在一起的;不管怎样理解记忆的性质,它仍然是属于意识,在这种观点下它仍然还是与那“自在之物”相分离的。物的象征意义,既不能归结为“自在之物”,也不能归结为主观意识。面对这种困境,萨特关于“物的精神分析”〔13〕的观点,给我们提示了从存在的基本谋划去解决问题的思路。就是说,我们这里要解决的问题“是事物的意义的真正起源和它们与人的实在的真正关系”。〔14〕而这就需要回到存在的“原始谋划上来”,即“回到划归已有的谋划”〔15〕上来。而化归已有的谋划意味着我作为一个人的存在在谋划做什么时,同时也就是在谋划要占有什么东西,并以此做、以此占有来呈现我的存在方式。这样我在把意识投向沼泽时,就是要迫使它揭示我作为意识的存在被感知的沼泽正是要被占有的沼泽,我和沼泽的原始联系,是我谋化成为它的存在的基础,因为它理想的是我本身。由此我们可以具体去看在化归已有的原始谋划下,梁晓声与沼泽的存在性关系及其意义。
当他的意识之光投向沼泽地时,就意味着他通过自己的涌现与沼泽形成卫个在世的存在性关系。正如前引《土地》的那段描写所表明的,沼泽在他的眼前呈现出一种黑糊糊密不透光的冷漠的存在,以其粘密、浊黑拒绝着他的目光的穿透。而他作为超越性的自为的存在,却要求他去穿透它的表面,穿透它的不透明性,看到它的内部、它底层的性质,或说通过认识它而占有它,超越它,从而超越他自己当下存在的意义的空无性,达到完满的理想的存在的彼岸;也即《土地》中所描述的沼泽那边的沃土。在那个境界中,所有的存在之烦都将消失,他将做为“神—人”而“自在—自为”地存在。可是这黑呼呼的散发着死亡气息的沼泽,将那理想之境封闭得密不透光,无人能真正窥见它。于是他就向那沼泽探进身去,用自己的身体去刺穿它,去探寻那沼泽的深处。然而当他插入之时,却立即感到一种粘糊糊的稠质围漫过来,反抗着他的探寻。这时他就陷入了一种“粘滞性”的存在中,陷于一种矛盾性的存在:一方面他将自己谋划为欲占有沼泽的存在,而另一方面又面临被其吞没的危险。为了超越这矛盾,他就把自己想象性地一分为二,分割成精神性的身体(以那些牺牲者为表征)和物质性的身体(沼泽旁的木桩):前者刺入到沼泽中去,想象性地占有它,后者则又钉在沼泽旁向他人证明前者的存在,两者互补构成一个不死的超越了超越性的存在。而正是在此想象性的存在的构想中,揭示了他的存在的自我物化性,即自我谋划成为欲占有之物的被占有之物。这颇类似于一个单相思者的存在方式。单相思者的存在是面对这样一个对象的存在:他(她)即想占有一个理想”的对象,却又无法占有,而且又不可能抛弃这个对象。因为他(她)把这个特定的对象设定为一种理想的对象,实际上就是为自己设定了一种“理想的自我”,对它的占有就是“完美”自我的实现,如果舍弃了这个对象,也就意味着舍弃理想的自我。这样单相思的存在者就陷入到了一种自设的关系中,苦苦挣扎,困兽犹斗而不能自拔。
既然那沼泽地,那片“神奇的土地”象征了他所寄托的理想,那么梁晓声与其所化归已有的理想之对象的关系,也就是上面所分析的那种面对“沼泽”的存在性关系,面对虚设的自我幻想的存在性关系;正是这种存在方式的谋划,呈现了他面对自我超越性的恐惧。而且在他这里,这种恐惧不仅是人的存在中常会感到的那种令人恶心的存在性恐惧,还是面对他人目光之下的恐惧。因为他(或他笔下的主人公们)之所以将自己的命运与理想相连,并不是一种纯自我的臆想,而是面对他人目光之捕捉而欲逃避这种捕捉的选择。而这种他人的注视又并非是直接在场的另一个实体的他人的注视,而是那些无形的、无所不在的、且也内化为他自我良心一部分的、抽象的社会观念价值。他将这些根本上来说是外在于他的普遍观念意识作为自己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同时,也就是将本来由他人所投射给他的外在的他者,设立为内在的自我的对象化他者,一个每时每刻都在凝视着自己存在的自我—他者。他之所以要设立这样一个自我—他者,并非象直接所表露的是一种心甘情愿地为理想的献身,而是想把自己谋化为这样一个理想的属于自己的他者的存在,把它化归已有。这样他者的目光就成了他自己的目光,他人之看就成了他自己的看,好象不再是被他人看,而是在看其他人,由此而摆脱被看的命运,而成了看的理想的本身。然而泛他设定了一种多么理想的自我——他者关系,这种关系仍然是外在于他的,时刻都在飞离他,于是为了维持他与它的存在性关系,保持自己理想的存在状态,他就要拼命地以不断的行为去维持它,持续地占有它。这样他就一方面在他人的目光下,胶固了自己的存在,同时又要以此去胶固其他人的存在。这也正是为什么理想主义者总是那样持恒,那样严肃,那样既爱他人又恨他人的原因。
至此我们的讨论就要结束了。一篇短文当然不可能对“人文精神”的讨论的深化与具体化产生立杆见影的效果,但就其为切实的尝试而言,似也不无意义。
注释:
〔1 〕雷达《人文精神质凝》转引自《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文艺理论卷》1995年第8期。
〔2〕这里指传统意义上的小说。
〔3〕这里仅就最宽泛的意义而言。
〔4〕因篇幅所限,无法展开具体分析。
〔5〕同〔3〕。
〔6〕就文本的人物实质性代系关系而论。
〔7〕由此可以看出意识形态传统的延续性。
〔8〕就小说而言是虚构,但作者的意向却是记实的。
〔9〕阿尔都赛语。
〔10〕萨特语。
〔11〕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转引自《小说月报》1982年第11期。
〔12〕参见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三联”出版社。
〔13〕、〔14〕、〔15〕萨特《存在与虚无》第四卷第二章。
标签:梁晓声论文;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论文; 艺术论文; 理想主义论文; 文化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