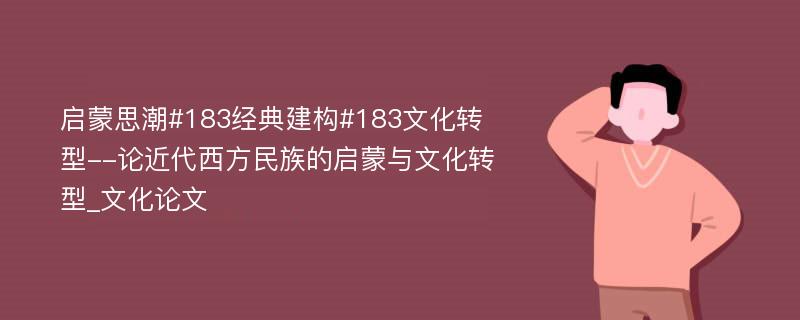
启蒙思潮#183;经典建构#183;文化转型——论启蒙运动与现代西方诸民族的文化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蒙运动论文,文化论文,思潮论文,民族论文,经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约翰·杰洛瑞在《文化资本》一书中提出,文艺复兴以后的近现代西方文学经历了三次重要的经典建构过程:第一次是17—18世纪西方各民族的俗语文学进入大学课堂,由此开始了诸民族文化经典化的过程;第二次是20世纪上半叶至中期,新批评派主张细读文学经典的文本,使之成为西方人文教育的核心课程;第三次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开放经典”运动,其主旨是挑战既有的西方文学经典,使边缘群体的文学作品经典化。①17世纪正是工业革命开始的时代,也是西方诸民族国家开始文化资本更新——形成民族语言体系和建构民族文学经典的时代,欧洲启蒙思潮就萌动于此时。这正如罗素所指出的:“就思想见解而言,近代从17世纪开始。”②由于启蒙运动推动西方各国摆脱了贵族和教会文化的思想控制,西方文学的经典谱系才最终完成了向诸国民族文学的裂变,即转变为以不同民族俗语为载体的“国别文学”。因此,17世纪确实是西方文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标志了西方各民族文化和文学的现代转型,而这也体现了西方文化“单源发育+主干+分枝”的“分体扩散型”(爱琴海文明+古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各民族文化扩散)的演变模式。
从发端于意大利城邦的文艺复兴运动到启蒙运动引发的法国大革命之间大约有四百年时间,现代西方诸国的民族主体认同也就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内逐渐形成。这段时期内的西方诸民族文化转型的催化剂就是中世纪以后逐渐成熟的各民族俗语,而这些民族语言经过俗语文学经典的优化和现代教育体制的规范,逐渐成为民族主体人群求知、思考和交流的工具。在启蒙思潮的影响下,各国的民族俗语书写经典化使得新的民族文化资本积累起来,并在现代民族国家的体制下消解了拉丁文化的霸权地位。如果没有西方的启蒙运动,王权政治体制仍将继续,贵族文化秩序不会瓦解,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和法治基础之上的现代社会难以形成,西方诸民族的现代文化转型也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说,17—18世纪的西方诸民族文学经典建构既是启蒙思想运动的一部分,也是各民族现代文化转型的一部分,而民族语言体制化和俗语文学经典化就是其中两个关键性的转变。
一、从“西方”到“诸民族”的文化裂变和转型
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主人公于连因为熟背拉丁文《圣经》而得到修道院长的青睐,并由此开始了他从平民向贵族身份的发迹之旅;但是,他最终没有能够立足于巴黎上流社会,却在贵族和教会的双重打击下失去了个人尊严和性命。于连的悲剧虽然只是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一桩“记事”,但却反映出从封建贵族体制到现代市民社会的转化过程之漫长、艰巨和曲折。实际上,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数百年间,西方社会和文化的转型从来就没有一帆风顺过,而是充满了矛盾、动荡、斗争以致革命。也就是在这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西方文化发生了从“西方”到“诸民族”的分体裂变,而启蒙思潮推动了这种裂变演化为现代各民族国家的文化转型。近来乔纳森·希尔认为,启蒙运动的起源应该上溯至中世纪晚期,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实际发端于1648年欧洲30年战争的结束,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为止;但是“许多事例说明了,理性时代至今仍没结束,我们现在仍然置身其中”。③从西方文学的演变进程来看,希尔的看法是有根据的。从1307年但丁发表《飨宴》介绍科学知识算起,到歌德1790年发表《浮士德片段》探寻“理性王国”,再到当代学者乔姆斯基等人对于启蒙理性的重申,这个长达七百年的西方思想文化史演变过程确实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④也正是在这风云激荡的漫长岁月里,西方各民族国家逐渐摆脱了拉丁文化霸权的控制,先后建立起完整的民族语言体系和各级教育体系,而各民族俗语文学的经典化建构则为各国积累新的民族文化资本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欧洲资本主义的海外扩张发现了“非西方”的伟大文明,促使人们不再从遥远的古代寻找乌托邦的理想社会,而是立足于现在和将来的发展变化。“地理的发现与征服也引起了一场欧洲人对语言观念的革命……从此刻开始,古老的神圣语言——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被迫要在平等的本体立足点上与一大群驳杂的庶民方言竞争对手混处一室”。⑤
中世纪以后的文艺复兴运动虽然标举人性论来挑战天主教会的思想禁锢,但是,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并没有一次性地完成建立现代社会必须的文化转型。在王权逐渐战胜神权之时,封建贵族专制却在古希腊罗马故土上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政治基础,即贵族+自由民+奴隶的“城邦民主制”社会理想。玛丽·比尔德等人指出:“古代世界中公民的特权生活依靠这些奴隶的劳力,他们没有公民权利,不过是劳力的来源:‘能说话的机器’……公元前5世纪奴隶约占雅典总人口中百分之四十(大约十万人),公元前1世纪意大利奴隶几达三百万。”⑥这表明,古希腊城邦民主制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社会体制,而16世纪以后的欧洲各君主国似乎在实践着柏拉图“理想国”的最高理想,即建立一个贵族统治的等级制社会。所以,文艺复兴运动一方面以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来挑战天主教会的势力,另一方面却也复兴了古代的贵族和君主专制理念,而这种政治理念正是通过拉丁文化传承下来的。不过,各民族国家的王权在对抗罗马教皇的神权时,打破教会文化霸权与建构民族文化主权的斗争是十分复杂和艰巨的。例如,亨利八世率先通过挑战罗马教皇的神权而巩固了自己的王权:他于1532年自主任命坎特伯雷大主教克朗默,1536年开始全面解散修道院,1538年拆毁托马斯·贝克特神殿。伊丽莎白女王1570年被教皇开除教籍更显示出王权与神权的对立。英国国教兴起之后,英文《圣经》又取代了拉丁文《圣经》,这显示了民族俗语对于拉丁文霸权的一个重大胜利。
在意大利,各城邦国从14世纪开始流行民族俗语,16—17世纪西欧各民族语言逐渐成熟,采用各民族语言的现代大学教育体系在西欧诸国开始逐步建立。在诸国君主与教皇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的背景下,这个漫长的民族语言体制化进程逐步削弱了拉丁文化对于各国语言文化的控制,并为建立新的民族身份和认同符号打下了基础。但丁早在1305年就发表《论俗语》一文,主张用佛罗伦萨的地方俗语来取代拉丁文。他的俗语创作《神曲》为意大利语言和文学奠定了民族文化的基础。哈罗德·布鲁姆认为,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等人都是近代西方的“民族诗人”。⑦这种界定其实指出了西方文化史的一个重大分期,即文艺复兴也是“西方”(罗马帝国和罗马教皇“治下”的西方)和“诸民族”(文艺复兴以后兴起的西方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分立和文化裂变的分野。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遵从《君主论》中‘君主’观念的民族君主们一定会与当时欧洲的两种力量发生冲突:教会和帝国。”⑧也正是由于这两种冲突的不断加剧,西方文化和文学的“分体扩散型”模式在这段时期内逐步形成,而民族语言经过体制化和规范化取代了拉丁文则是这个文化“裂变”的鲜明标志。格林菲尔德认为,民族主义在18世纪扩散开来以后,民族观念开始挑战帝国思想,并成了“现代性的构成要素”。⑨在启蒙思潮所传扬的现代社会理想的激励下,欧洲民族国家纷纷崛起,民族俗语文学的体制化推动了各自民族文化的独立和转型。这种文化民族化进程与启蒙运动相呼应,最终完成了西方诸民族文化从“分体裂变”到“民族建构”的曲折过程。
语言贮存着一个民族最基本的文化要素和基因密码,记载了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而民族俗语更是民族文化最真实的符号载体。正如海德格尔所比喻的,语言是人类心灵的家园。语言不仅被民族成员集体创造,而且也塑造了民族成员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特性,传承了民族的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性。当启蒙思想家要建立现代文化秩序时,他们首先需要清除古典文化中的贵族等级观念和君主专制思想。启蒙思想家们不是在古典文化基础之上做一些修正或改良,也不是简单地译介外来文化新作,而是注重从现实社会和民间文化中汲取思想的营养,并通过个人独立的理性思考,再利用民族俗语重新建构一套新的文化价值体系。这种文化创新活动就是狄德罗等人在编撰《百科全书》时所做的。启蒙思想家们希望通过民族文化的创新来塑造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批判封建贵族专制思想。狄德罗认为,撰写《百科全书》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人们普遍的思想方式”,爱尔维修则认为,“人的一切差别都是后天获得的”。⑩这些观点针对王朝专制的思想禁锢和等级观念,鼓吹思想自由和人权平等,主张以启蒙哲学话语和普及平民教育来改变传统的文化专制秩序。于是,从民间大众中汲取民族俗语并通过各级教育加以体制化则成了一个意义深远的文化传统再造运动。实际上,各民族国家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先后摆脱了“西方”拉丁文化霸权,逐步积累起本民族国家的文化资本,而民族俗语文学经典就是这种文化资本积累的体现。
在西欧诸国,拉丁文曾经是学校教育的唯一语言,受过良好教育的学者往往以书写拉丁文为荣,例如17世纪的霍布斯、笛卡尔和帕斯卡尔等人。在教育体制上,虽然自然科学课程已经进入大学校园,但是古典文化课程仍以希腊语和拉丁语文献为主。1642年,美国哈佛学院在课程表上列举的三个学年共40门课程中,希腊语言文化课占了6门,希伯来和西亚语言文化课占了3门,共计有近1/4的古典语言文化课。(11)当时的贵族和绅士为了维护古典文化的特权,或者说,为了维护自己占有的拉丁文化资本,对民族俗语相当排斥,甚至洛克也提出要让穷人的孩子保持其文盲状况。于是,古典文学教学成了维系贵族阶级文化特权的有效手段,拉丁文成了贵族和绅士后天习得的文化资本和展示阶级身份的符号。“由于绅士子弟继续接受传统古典文学的教育,他们的‘无用’知识到了18世纪晚期仍然是他们高贵地位的象征”。(12)然而从16世纪开始,作为唯一教学语言的拉丁文霸权遇到了廉价印刷品和市民流行俗语的挑战。例如,在1500年的西欧,有大约23%的出版物是用方言而不是用拉丁文来书写。(13)在法国,16世纪中叶出现了七星诗社,其成员杜·贝雷起草的“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言”成了该诗社号召统一民族语言的宣言书,为抵制拉丁文霸权做出了贡献。这表明,随着民族意识觉醒和工商经济发展,一些贵族阶级成员也附和市民阶层对于方言俗语的要求,而市民语言和市民趣味——方言俗语和通俗文学——也在这个过程中与新兴的民族国家同步进入了自主建构的时期。
正如中国文字统一的基础是书写文本而不是方言俗语那样,西方拉丁文统一的也只是书写文字,尤其是宗教经典书写文本,因此也形成了教会的宗教话语霸权。但是,罗马帝国和天主教会虽然推行拉丁文书写特权,却没有把各行省的方言统一起来,更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士”阶层。于是,拉丁文仅限于上层社会和教会使用,各地百姓多用本民族的俗语,甚至一些地方公国的君主也不识拉丁文。所以,一旦民族国家的君主决心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从地方首领转变为方国君主时,他们就要为树立自己的政治权威而提倡“专属于他的国家语言”。(14)此时,民间俗语就可能从地方性语言上升为国家语言,书写并传播民族主体意识,塑造并凝练民族身份。在这种形势下,民族俗语的优化和规范成了“诸民族”文化摆脱教会—拉丁文霸权的有力举措,而平民知识分子则成了俗语写作的主要群体。对于大多数出身微贱的平民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不能进入教会体系或受到贵族庇护,结果就只能走向民间,或投身商业,或安于小吏,或卖文为生,甚至被迫流落他乡。这些经历增加了他们的本民族文化认同意识,而他们使用民间俗语写作更能为平民读者所接受,也更易于在文化市场上流通。可以说,许多近现代西方文学大家都成名于这段漫长的西方文化裂变时期,例如塞万提斯、莫里哀和笛福等人。平民作家使用民族俗语写作推动了民族语言的规范化,也促进了民族语言文字教学的通俗化,即从古典的拉丁文教育转向通俗民族俗语教育。这种新的教育体系采用民族俗语文学经典作为学习范本,从而为各民族国家积累新的文化资本提供了便利。
二、启蒙思潮与民族俗语文学的经典建构
在启蒙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民族俗语被规范化和体制化——进入教育体系并成为官方语言——使得作为民族主体的广大市民获得了读写能力,为他们积累个人文化资本、参与文化和经济活动提供了条件。到了18世纪前期,这种发展趋势逐渐把民族俗语提升到国家语言和教育体制的层面,甚至引起了大学教育的改革。就在这一时期里,德国出现了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大学改革运动。德国的哥廷根大学在1737年颁布章程,主张教授享有教学和思想的自由,反对神学院从中世纪以来对于其他学院的监护权。(15)哈勒大学聘用的著名教授如沃尔弗和托马西务斯等人使用德语而不是拉丁文进行教学。哥廷根大学还建立了“欧洲第一个现代意义的科学图书馆”,并在现代世俗课程改革中使“神学第一次丧失了它在大学迄今为止一直享有的凌驾于其他学科之上的特殊地位”。(16)如果联系歌德、莱辛和赫尔德等人都到过哥廷根大学图书馆借阅图书这个事实,那我们就不难理解,德国狂飙突进运动与新的教育体制之间存在着相当深的文化关联。那些引领德国启蒙运动的先驱们首先要在新的教育体制中接受民族语言文化的训练,吸收新的文化知识,积累新的文化资本。实际上,启蒙思想家对于现代文化教育极为重视。例如,狄德罗认为教育是人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经之路,而每一个人无论出身如何都应有受教育、学知识的权利,教会权力应该从教育体制中退出。在英国,1828年成立的“伦敦大学学院”掀起了“新大学运动”,主张多建私立大学,以民族语言取代拉丁文,以世俗学问取代经院典籍,以自然科学取代宗教神学,以平等招生取代门第、信仰和性别歧视等等。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西方现代读写教育也从拉丁文转向民族俗语,从而在书写和交流工具上实现了从“西方”文化向“诸民族”文化的转型。这次转型为各民族国家更新集体记忆,培育新的文化资源,巩固以俗语为载体的民族符号共同体打下了广泛的语言文化基础,而俗语文学的经典建构就是这种文化转型的重要组成之一。
由于中世纪以来欧洲各国的文化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教会神职人员,而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各民族国家的第一代双语知识分子,既熟悉拉丁文又精通本民族俗语,特别是俗语书写中的雅言。这些人也起到了从拉丁文到民族俗语转换的桥梁作用,如马丁·路德用德语方言翻译《圣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马丁·路德在16世纪采用德国中部的图林根俗语和萨克森官方语言翻译了《圣经》。这部《圣经》译本从1522年到1546年就出版了430种版本,从而造就了“一个真正的大众读者群和一本人人随手可得的通俗文学”。(17)但是,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世俗精神虽然冲击了教会文化的神圣地位,却并非足以颠覆教会神权和封建王权的思想武器。在王权与神权的冲突中,以及尔后在民权与王权的斗争中,拉丁文化不断地成为各民族国家实现文化现代化的思想障碍。拉丁文由于承载了厚实的古典文化资本,因此也在工具理性的层面上阻碍了工商经济和现代社会的发展。为了适应工业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大扩张,各民族国家在部分君主和贵族的默许下,出现了一批依靠市民社会和文化市场而不是宫廷恩准生存的平民知识分子阶层。他们积极开展了民族俗语的书写和创作活动,出版了许多民族俗语写就的文学作品。法国、德国和英国的一些启蒙文学作家就是这样一批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人物,他们在古典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担任了起承转合的作用。例如,法国的伏尔泰一方面受过贵族学校教育,写过古典主义的戏剧,却受到过贵族的侮辱和迫害;另一方面,他依靠经商积累起大笔钱财,既创作哲理小说讽刺神权和王权,却又赞同开明君主统治。这种人生和思想的双重性正是启蒙时期文化转型所造成的,而当时的教育体制也出现了贵族和平民的两种教学模式,推动了民族俗语的规范和俗语文学的经典形成。
在最先发生工业革命的英国,17世纪以后出现了日益壮大的市民阶层。市民子弟进入各级学校接受教育的同时也急需学习与他们有关的文化课程,而不是中世纪经院典籍或古希腊罗马经典。在社会人口结构迅速转变的背景下,英语俗语经典作品于18世纪进入了英国的学校课程体制,而莎士比亚、斯威夫特、艾迪生和约翰逊等人的俗语雅言(vernacular "polite" language)成了这类俗语文学的代表。英语俗语经典进入学校教学体制是对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古典文学经典的挑战,因为这些作品不仅取代了拉丁文古典作品如维吉尔的《爱涅阿斯记》,也取代了蒲伯等古典主义作家模仿罗马诗风的英雄双韵体诗歌。例如,来自苏格兰乡野的诗人彭斯用方言写的诗歌充满了世俗情感和爱国精神,他的诗作“红红的玫瑰”和“苏格兰人”等成为英语诗歌的经典之作,他的名字和塑像也被镌刻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诗人角,获得了国家祭祀的崇高待遇。包括莎士比亚和彭斯等本民族俗语作家进入国家祭祀的庙堂,这既标志了英语文学传统的更新,也是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举措。正如桑德斯所指出的:“拉丁文似乎从来没有阻碍过任何一种充满活力的英语文学传统的生存与发展。”(18)在德国,启蒙思潮影响下的狂飙突进运动带来了德意志民族意识的高涨。莱辛主张创作“市民悲剧”,提出戏剧要模仿自然而不要移植法国古典主义悲剧,而赫尔德与歌德共同编写的《德国的风格和艺术》进一步表现了建构独立民族文化的意志。歌德的长篇诗剧《浮士德》最深刻地表现了德意志民族的进取精神,为摆脱民族落后和分裂状态、建立现代国家意识打下了思想基础。在启蒙运动的发祥地法国,人们把法语文化经典视为抗衡古典文化的典律,并且积极地向欧洲其他地区扩散法语文化的影响。(19)1721年,孟德斯鸠的书信体小说《波斯人信札》发表;1734年,伏尔泰的《哲学通讯》出版;1750年,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发表;1772年,狄德罗主持的《百科全书》出版。这些启蒙思想家在上述经典作品中提出了理性、自由、平等和科学等观念,并对文学艺术赋予了“道德学校”的功能。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启蒙思想家首先做到了自我“启蒙”,即通过对自我的理性批判来认识人类自身。例如,卢梭的《忏悔录》和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就体现了这种自我反思意识,正如马克思引用黑格尔对《拉摩的侄儿》的评价所指出的,这本书是“意识到自己的支离破碎状态并把这种支离破碎状态表露出来的意识,是对于现有的存在以及对于整体的错综杂乱状况和对于自己本身的一种刻薄的嘲笑”。(20)
正如古罗马文学为拉丁文积累了贵族文化资本那样,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期间日益繁荣的各民族俗语文学也为诸民族国家的语言——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俄语等等——积累了各自的民族文化资本。但是,一个新兴民族的文学经典建构也是其文化资本和民族身份的重新建构,这种建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和曲折的新旧文化交锋过程。例如,英国俗语文学经典建构历程如果从1623年莎士比亚戏剧“第一对开本”出版为起点,那么经过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1719)和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1726),再到1765年塞缪尔·约翰逊出版《莎士比亚集》并为之写序和大量注释,这一段历史进程大约有140多年。但是,这一段时期内也出现了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和古典主义风行的复旧势力,例如德莱顿的戏剧和蒲伯的诗歌等对于俗语经典建构产生过消极的影响。这些贵族趣味文学的复苏,表明了文艺复兴运动虽然倡导以人性反对神性,但是并没有确立现代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更不能真正解决社会公正和个人自由等现实问题。人文主义所憧憬的古典理想如古希腊城邦民主制实际上也是一种等级制度——雅典的俘虏和奴隶就没有公民权利,而古罗马更是实行元老院贵族专制。所以,复兴古典社会理想在相当程度上意味着延续贵族文化秩序,例如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延续了沙龙文学的品味,排斥彰显市民趣味的写实文学。这种历史和思想的局限只有在启蒙运动的冲击下才逐渐被突破。
恩格斯指出:“法国启蒙思想家不承认任何种类的外界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等一切都受到最无情的批判。”(21)在启蒙思潮的影响下,广大的市民阶级要求在法理上废除贵族享有的各种特权,取得平等的社会权利,包括获得俗语教育和身份平等的权力。于是,西方诸国为了在现代化过程中建立新的文化秩序和社会机制,各民族俗语文学也在国家体制力量的支持下兴盛起来。也就是在这一复杂的文化转型过程中,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从哲学中分离了出来,并在大学教育课程中自立起学科门户;而启蒙思想运动则推动了俗语文学的经典化和“文学”学科的体制化。这个体制化过程对于西方文化转型是意义重大的,因为它意味着“西方”文化主体在经历了爱琴海文明、古希腊罗马文化到基督教文化等三个发展阶段后,逐渐出现了由主干裂变而来的多元分体文化。这种多元分体文化虽然有着共同的“西方”渊源,但是西方“诸民族”却在中世纪后期用本地俗语把各自民族的文化传统书写和固定下来,为新建民族文化身份开辟了道路。随着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学校教育在平民大众中普及俗语读写知识和科学知识。来自民间的鲜活语言,即文雅俗语所书写的文学经典取代了拉丁文经典成为文科教育的主导教材,于是形成了从教会到民问、从宫廷到城市的民族语言规范化转变。
现代西方诸民族的俗语文学保存了鲜活的言语和修辞,传诵着本土的故事和情感,其独特的“文学性”赋予其语言形式和风格以特有的民族文化印记。在俗语文学繁荣的基础上形成的俗语文学经典也成了传播新思想和新知识的重要来源,成了民族俗语规范化和审美化的重要范本。德国的赫尔德和英国的华兹华斯等人都曾把流传于民间的歌谣加以收集、整理并出版,以此丰富了本民族的文化资本构成,为民族文学繁荣提供了动力。正如哈罗德·布鲁姆对英国谣曲所评论的:“我们有许多[短篇叙事]通俗歌谣作于12世纪到17世纪……被布莱克、彭斯、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和济慈等诗人所模仿。”(22)以西方诗歌转型为例,它的三个来源最终延续到启蒙时代而转化成新的俗语文学经典。它的第一个来源是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诗歌传统,例如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史诗。第二个来源是罗曼语系的各民族诗歌传统,包括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和不列颠等民族俗语文学。例如普罗旺斯抒情诗在12世纪就已经流传开来,被恩格斯认为“在新时代的一切民族中第一个创造了标准语言”。(23)英国12世纪出现的《不列颠列王记》据称就是从一本不列颠语古籍转译而来,其中包含了记载亚瑟王和圆桌骑士传说的最早素材。(24)第三个来源是古代日耳曼诗歌传统,即日耳曼氏族文化中的歌谣和传说,例如中古高地史诗《尼伯龙根之歌》。这三个来源在西方诗歌的传承中逐渐融入各民族的俗语文学创作,并在民族俗语体制化和俗语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中产生影响,形成了各自民族国家文学传统的本土文学源头,即不同“国别文学”的民族文化源头。
三、两种文化生产与现代市场机制的形成
启蒙运动的进步意义在于它的批判性、现代性和平民性。当启蒙思潮冲击着贵族政治文化和宗教思想桎梏之际,西方大学教育也在努力摆脱罗马天主教会的体制性影响。18世纪以后,欧洲许多大学除了神学院以外,还设立了文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等教学机构以培养现代社会急需的世俗人才。此时,印刷机械的发明使得廉价出版物大量进入市场,学校教育的成本也在降低,教学语言的俗语化更符合平民学生的文化水准和现实需要。在这种形势下,更多受过现代教育的作家从模仿古代文学经典转向创作通俗文学作品,特别是各类小说的创作。许多人创作了可以拿到市场上出售的文学作品,例如狄更斯所写的报刊连载小说和大仲马所写的通俗小说等等。于是,文学创作成了文化生产的重要部门,文学作品也成了可以进行市场交换的某种文化商品。换句话说,这种“商品化”趋势一方面使文学摆脱了皇室或贵族的控制,增强了文学的自主地位;另一方面,写作亦成为“稻粱谋”的手段,市场使高雅和通俗的审美品味也更难区分。于是,文学作品流通的文化市场竞争更为激烈,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也更加充满了挑战,而创造性天才和平庸的写手之间差距也更大。正如桑德斯对18世纪英国小说的分析:
小说艺术在1720年至1780年间获得巨大发展,其教化娱乐作用很快被以中产阶级为主的读者所接受……随着工商阶级的发展,教育水平会提高,闲暇时间会增加多……那些由于清教诚实传统影响和社会地位及教育所限而对宫廷风格敬而远之的读者,尤其易于接受简明易读、又有严肃教育意义的“写实”文学。如果说深受商业职业和伦理价值观影响的都市观众逐渐摒弃了戏剧表现的英雄主义偏见,英国小说的发展则迎合了读者对强调个人经历重要性的新型文学的要求。(25)
这段话明确而具体地解说了18世纪小说兴起与工商社会之间的关系,即在市民文化形成中逐渐繁荣的文学新形式。更有意义的是,文学从宫廷走向市场的转型不仅巩固了“文学”的学科自主地位,而且提升了文学作为创建民族文化资本的巨大潜力。
文学生产市场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市场秩序取代了权力秩序,权力无法强制塑造经典,而读者作为消费群体则参与了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不过,消费大众的参与也造成了作品瞬时效应和持久效应之间的矛盾,速成名作和天才独创之间的冲突也不断加剧。司汤达和大仲马两人生前遇到的文名反差——即前者的被冷落和后者的受欢迎——典型地反映了这种矛盾现象。这种矛盾是市场机制的一种表现,因为一定时代和社会的读者只能依据个人的文化素养和审美品味去选择文学作品,而文化消费群体的选择往往反过来决定了一部作品的现实“命运”。由于文学创作是具有公共性的文化生产,其产品的市场价值不在稀缺性而在流通性,读者的作用因而举足轻重。广大读者不会遵照什么权威的指令来读书,而是依照自己的品味、喜好和需要来阅读。姚斯认为,读者是“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没有接受者能动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26)这也意味着,文学经典的形成必然地需要读者群体的参与,而不能仅仅期望学院体制的分封。但是,启蒙文学的公共性不仅在于其具有市场消费的公共商品性质,更在于具有社会批判的思想观念性质,具有启迪第三等级思想解放的教育性质。因而启蒙文学也可以通过市场来塑造自己价值观念的消费者。当时许多俗语文学生动地体现了启蒙思想的精髓,引领了现代新文化秩序的形成和扩散。例如,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表现了资本主义的开拓精神和科学理性,即主人公在荒岛上凭借大胆进攻和商业道德收服了“星期五”为自己劳动,并依靠精准计算和辛勤劳动制造了脱离险境的独木舟;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礼》则揭露了封建贵族专制的虚伪和罪恶,歌颂了平民大众的勇敢和智慧。这些作品代表了时代的呼声和大众的愿望,人物刻画和剧情描写生动感人,因而顺理成章地成为西方启蒙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
18世纪以后,文化市场和报纸传媒成了抗衡宫廷和教会专制势力的重要的公共空间,也成为民族文学经典的锻造场所。当时不少启蒙文学作家直接介入了社会政治活动,用他们的艺术才情和社会良心共同打造了自己经典作家的地位。例如,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席勒和英国的斯威夫特等人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呼应了时代的要求,宣扬了启蒙的理想,引领了社会的思潮。恩格斯曾经评价席勒的《阴谋与爱情》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27)卡尔维诺在论及伏尔泰《老实人》中的人物形象时也指出:“邦葛罗斯和马丁虽然以无望、荒谬的态度来对待一切,但骨子里他们会挺身反抗生活中的各种艰难险阻。”(28)孟德斯鸠的启蒙文学代表作《波斯人信札》1721年在荷兰匿名出版后,很快被走私运入法国,并发行了八个版本。这表明,启蒙时期文化市场的力量超过了封建权贵的封杀,宫廷“对于书商和作者的禁令与恐吓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有时对作者却反而有利”。1748年,官方下令公开焚毁伏尔泰的《哲学通信》,这个举动却“帮助该书即刻成名,并极大地提高了作者的威望”。(29)在英国,斯威夫特曾匿名发表了《关于雅典、罗马时期的分歧与斗争论述》一文,1704年又发表了《一只澡盆的故事》、《书的战争》和《圣灵的机械作用》等三篇政治讽刺文章。他的小说《格列佛游记》当时获得了200英镑的稿费,而书中的思想锋芒直到今日仍然闪亮不已。在俄国,公共剧场在1756年建立起来以后,其上演的剧目既有宗教剧也有骑士传奇剧和日常生活喜剧。虽然宫廷贵族赞助了圣彼得堡的剧场演出,但莫斯科的剧场也依靠市场的票房收入运行,而受到启蒙思想影响的剧作家在一定程度上把剧场变成了“挑战权势”的公共空间。(30)启蒙时期的文学创作通过市场机制在市民大众中流行,表现出文学和市场这两者之间在现代社会中某种“文化共生”的状态,预示了今日大众文化艺术的生存状况。
布迪厄提出,存在着两种文化生产场域,即高雅艺术和文化商品两个生产场域,以及三项合法性原则:自主(纯艺术)的艺术家认可原则、主导阶级和机构的道德和品味原则、普通消费者或大众读者的选择原则。布迪厄相信,文化资本形成和感受与阶级构成和市场体系有关,因为不存在纯粹的审美感受领域,也不存在这样的客体。(31)杰洛瑞进一步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文化产品作为消费客体,它体现的审美倾向表明了文化资本的存在,而文化资本的衡量标准有赖于其交换价值的变动。(32)换句话说,文学创作的艺术价值可以在市场上转化为经济价值,如功成名就的作家本身就成了某种价值“符号”,即享有市场品牌声誉和经典作家身份的双重价值符号。实际上,英语俗语经典作家并不回避文化市场的价值规律,例如莎士比亚就是依靠写作和经营戏剧而获得了财富,他的文化产品——37部戏剧、2部叙事诗和154首十四行诗在他生前就实现了符号资本向货币资本的转化。哈罗德·布鲁姆指出,“莎士比亚是在经济上获得了巨大成功的剧作家,他去世时是一位富人,他对社会地位的雄心(就像当时那样)也获得了满足。而塞万提斯虽然因《堂吉诃德》而名满天下,却拿不到分文版税,也没有获得什么赞助。”(33)这种差别也许是两者所处的国家分别支持新教和天主教的缘故,但是,英国社会市场机制的最早形成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说,启蒙运动把文学从宫廷和教会的思想束缚下解放了出来的话,那么,它又使文学不得不面对市场的势利和无情。在市场秩序中,每一部作品也是一种文化商品,是一个具有符号—交换双重价值的客体。这个客体一旦进入市场流通领域——被人购买、传阅、评论或收藏——就具有了独立的商品特性和公共的审美特性。非物质形态的资本会转化为物质形态的资本,文化产品会转化为市场商品。布迪厄在有关文化生产场域的论述中把这种状况视为“反经济”的状况,因为文学还具有自主的、非功利化的特性。由于文学作品可以作为一种以满足消费需求而生产的商品出现,文学创作的个人独创性还会导致“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化生产,即一些才华独具的作家进行不以市场为目的的纯艺术生产。正是这种双重特征使得现代文学经典建构难免在两种生产(高雅艺术和文化商品两种生产)之间游移波动、此消彼长。
从启蒙运动促进民族文学经典形成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启蒙作家创造了新的俗语文学经典,还在于他们为现代民族文化建构积累了新的资本——这种文化资本不单单是作家个人劳动所创造的,而且是全体消费者(读者)所创造的。这些作品具有较大的文化再生产能力,能够激励历代读者和作者去阅读、思考、传扬、评价、模仿和增补这些经典之作。显然,这些作品中所积累的文化资本是在长期的流传和阅读中不断增值的,因而这些作品的符号价值将更为贵重和持久。由于启蒙时代的俗语文学经典形成正好处于西方文化史的重要转折时期,即从“西方”一统文化转化到“诸民族”的多元文化,从拉丁文化霸权转化到民族主体文化。从文化资本形成的角度看,这种转型既是文学创作的市场化所致,也是现代文化秩序形成的必然结果,因为西方诸民族国家必须积累新的民族文化资本以应付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无情竞争和他者的挑战。
四、“文学性”与民族文化资本的积累
西方启蒙思想家创作了不少哲理小说来传播启蒙思想观念,例如狄德罗和伏尔泰的小说。这种叙事体裁的出现也是当时市民社会读者消费的需要,因为一般的消费者乐意通过自己熟悉的大众语言来欣赏戏剧和小说,以此来怡情悦性、接受教诲。可以说,启蒙时代俗语文学在娱乐消费者的同时也向他们传递新的思想观念和审美情趣,因而也提高了自身的艺术品位和符号价值。卢梭的《新爱洛依斯》就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小说在叙述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之时还表达了对于宗教、家庭和艺术等诸多社会人生问题的看法。《新爱洛依斯》受到市场热烈的欢迎,说明了启蒙思想在广大市民阶层中的传播也要依赖小说和戏剧等通俗文学形式在市场中的广泛流通。其实,这也是现代工商社会新的文化生产力的具体表现,通俗文化创作载体——戏剧和小说——取代了长篇史诗和颂诗的地位,成为积累现代民族文化资本的有效生产方式。启蒙运动开始的欧洲文学发展适应了新的市场秩序,作家和文学也正是在市场秩序中找到了自身的自主地位,小说和戏剧形式的“文学性”也从民间俗语中获得丰富的营养。雅可布森认为,文学性就是“在语言运用上,突出修辞功能并使其超过语法和逻辑的功能”。(34)德曼所谓的“修辞性阅读”进一步点出了文学作品的独有特性,即文学性的问题。在探讨文学性的问题上,这个定义的可取之处在于它有助于解说文学经典对于民族语言的优化作用。一个民族的语言如果仅有语法功能和逻辑关系,那它与语言机器并无二致。民族语言的成熟需要修辞性语言或文学性语言不断对之进行丰富和优化,拉丁文在西方能够维持一千多年霸权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经过了古罗马文学经典的长期优化,特别是维吉尔的史诗、普劳图斯的喜剧、西塞罗的散文和塔西陀的历史叙事等等都运用了丰富多彩的文学性语言,从而大大提升了拉丁文的修辞水平。富于修辞色彩的拉丁文所书写的文学经典甚至被当作罗马帝国的文化武器来维系它的统治。博尔格在论述罗马帝国的文化统治时指出:
随着罗马军团保护力量的衰弱,帝国的统治开始依赖对其无形资产的前所未有的扩张;卓越的希腊—罗马文化被当作适用的诱饵来维系不可靠行省的忠诚。由于钢铁短缺,因此需要一种不同的镣铐把各行省捆绑在罗马的灵魂上。文学作为对罗马生活方式的介绍而被充满热情地传授着。(35)
上述这段话提示人们,拉丁文化曾被罗马人用来粉饰帝国统治,而拉丁文学则以无形资产的形式帮助过罗马帝国扩张和维护其文化—政治霸权。尽管对于18—19世纪的西方诸民族国家来说,拉丁文霸权已经好景不再,但是,罗马帝国借助文学经典的力量来维系和巩固其文化统治的历史却值得人们反思。启蒙文学兴起以后,大量生动活泼的民间俗语进入文学书写,极大地丰富了民族语言的修辞色彩。莱辛、卢梭、华兹华斯以及普希金等人就十分重视借鉴民间文学的语言词汇,他们的文学作品对各自民族语言的优化和民族形象的美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出自经典作家的作品对于提升民族语言和民族形象具有很大的优势,因为文学文本塑造的艺术形象可以被人们一读再读,感同身受;而经典化的文学性文本更能丰富民族语言的表现力,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对于英法等国来说,17世纪以后的英语和法语文学经典对其殖民主义扩张也起到过重要的作用,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对此有过细致的分析。
随着启蒙运动的深入,现代市场秩序取代了封建专制秩序,俗语文学的审美趣味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市民大众的消费需求而不是专制权力的政治意志决定了文化产品的生产。布迪厄认为,文化产品可以摆脱市场规律而完全自治,形成某种“审美专擅性”。(36)但这不等于文化资本会从市场中消失,因为文化产品所体现的文化资本在消费过程中会产生增值或贬值。杰洛瑞认为,“文化生产者还会通过相互竞争来吸引人们阅读、学习、观看、倾听、使用、吟唱、穿戴他们的产品,并以‘声誉’的形式积累文化资本”;(37)于是,“经典建构就会成为更大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它不会被限于具有物质优势的机构之中。”(38)文学创作和接受在市场机制下运行时,会与其他形式的文化产品如音乐和绘画等形成竞争。在这类竞争中,“文学性”代表了文学这门语言艺术的独特性,而“文学性”的强弱往往对文学作品经典化产生很大的影响。毕竟,大学人文教育中对语言修辞的关注是文学经典得以遴选的重要指标。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经典必然也是文学性的语言经典,而一部文学作品只有在文学史、文学选集、文学课程这三个方面同时赢得较高的声誉才会实现经典化建构,完成其文化资本的增值过程。
18世纪以后,西方印刷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文化市场的繁荣,作家也常常通过出版商在市场中寻找生存之道。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系列中就有一些是为了市场效益而写的“文化商品”。但是,现代市场的繁荣也刺激了文学生产的竞争,作家必须以创新而不是模仿来增强其竞争实力,必须以大众而不是以权力为其主要消费对象。这种变化在启蒙运动之后更为明显,市场竞争而不是王室垂青往往涉及一位作家能否生存的问题。英国著名诗人济慈生前依靠卖文度日,26岁就因为贫病交加而去世,身后留下了《夜莺颂》和《希腊古瓮颂》等经典诗篇。罗伯特·达恩顿在文化史专著《启蒙运动的生意》中指出,图书消费大致可以指示读书公众的趣味和价值观,“《百科全书》变成畅销书的故事说明了启蒙运动在法国社会的上层和中层——如果不是在制造了1789年大革命的‘大众’中的话——具有巨大的吸引力”。(39)达恩顿的研究集于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的出版史,他的研究深入探讨了这部启蒙主义经典之作的市场成功之路,即“18世纪最大生意之一”的完成经过。达恩顿从文化出版商策划和推销《百科全书》的成功经验中发现了启蒙思想运动与现代市场机制的密切联系,这对我们认识启蒙运动与诸国民族俗语的文学经典建构有着相当大的借鉴意义。从文化生产的角度看,作为法国现代文化典籍的《百科全书》不仅具有传播启蒙思想观念的社会进步价值,而且具有赢得众多消费者的文化市场价值。《百科全书》是法兰西民族文化资本积累的巨大成就,它的影响早已越过法国边疆而波及世界。虽然文化和资本之间的关联所引起的批评论述和经济话语间的纠葛会导致“双重话语”的矛盾,即人文学科话语与经济学科话语之间的难以兼容。但是,启蒙文学经典传承至今的事实提示我们,文化资本不仅具有文化特性,而且具有商品特性。或者说,文学经典不仅具有艺术作品的审美和认识价值,而且具有文化资本的交换和积累价值。在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或社会资本的过程中,文学经典的符号价值和经典作品的市场价值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从西方文学史的角度看,那些创造性地体现了“文学性”的作品——语言优化和美化的作品,或者按照哈罗德布鲁姆的说法是体现了“陌生性”的作品,常常就是具有符号和市场双重价值的经典之作。
启蒙运动以来西方诸民族文化转型的历程还表明,随着物质商品竞争而来文化资本竞争也是西方诸国国家间文化软实力竞争的重要场所。例如,国际交往中使用法语和英语孰优孰劣的长期竞争至今未息,这也体现了某种文化资本的竞争。哈罗德·布鲁姆曾明确指出了西方经典作家与前辈大师之间的传承和竞争关系,却没有指出作家与同时代人,同他国作家之间的影响和竞争关系。在文化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这种“同类相争”更是经典作品脱颖而出的必经之路。在数代时间和读者大众的检验下,一部文学作品是否成为经典还要在时代横向和历史纵向的两个维度上与其他文学创作进行竞争。只有那些在语言艺术上不断创新、思想内容上启迪心智的作品才会得到人们的嘉许和传阅,才能成为文学经典之作。可以说,文学经典的形成也是“文竞天择”的结果,是经典作品与其他作品之间长期的影响、借鉴和比较的结果。其“天择”的真正决定者则是读者、批评家、时代精神、民族特性、体制力量和文化市场共同作用的“合力”结果。于是,文学经典建构也是对作品所处的文化传统进行的资本更新,即淘汰旧的文化资本,注入新的文化资本,也就是文化传统本身在吐故纳新过程中经历的自我更新。西方文学经典的建构正是给特定文化传统输入新鲜活力的文化输血活动,也是增强民族认同感召力的文化资本积累过程。杰洛瑞把这种变化称之为文化领域的“资本飞跃”(capital flight),(40)而我认为这里使用“资本更新”似乎更为贴切。无论如何,对于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多民族共同体来说,以民族主体语言创作的文学文本所积累的文化资本——丰富的语言、审美的品味、民族的习性、人群的形象、历史的记忆、价值的体系以及作家的声誉等等——都会通过经典化过程而以符号资本的方式积累起来,并再次进入市场被持续消费,从而实现其资本价值的增值。罗钢认为,市场消费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消费文化“直接参与了近三百年来西方现代性的历史建构……它与支持西方现代性的许多核心的价值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41)从文化的精神生产过程来说,文学经典被历代读者消费就意味着它作为“民族教化之书”得到了传承,意味着它成了民族认同的精神产品标志物,即作为民族的文化符号而延续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文学作品的文学性越强,其作为民族文化标志物的经典性也越彰显和持久。
五、结语
我们今日阅读和研究的“西方文学史”实际上包含了不同的西方文化发展阶段,例如爱琴海文明的西方文学(荷马史诗)、古希腊城邦社会的西方文学(希腊悲剧)、罗马帝国的西方文学(史诗和散文)、蛮族南下入侵的西方文学(氏族英雄史诗)、天主教会控制下的西方文学(宗教文学)以及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出现的西方“诸民族”文学(从但丁、莎士比亚到卢梭和歌德等人的文学经典作品)。实际上,现在的“国别文学”分类就来源于西方文学主干裂变之后民族俗语文学的“分体扩散”的结果。在这一文化转型过程中,启蒙主义运动和工商社会发展大大地推动了文学自主和市场竞争这两种机制的完善。朗松指出:“我们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父辈身上有着诚挚的智力和活跃的理性,引导他们对别人意欲限制他们自由的一切戒律加以批判,也不附和别人强制他们尊而敬之的一切典章制度。”(42)正如狄德罗拒绝《百科全书》出版商译介英国《百科全书》的要求,而力图通过自己的理性反思和探索来铸造新的百科观念词语那样,启蒙思想运动不仅颠覆了贵族文化的思想专制,而且在各民族国家中培育了一批思想观点敏锐、艺术素养深厚、语言表达鲜活的文学大师。他们的文学成就不仅开启了“西方”现代文学的新纪元,而且体现了民族文化生产力的活力与创意,而启蒙文学经典所形成的西方诸民族文化资本积累至今仍在对这些国家的民族文化认同产生着巨大的作用。
注释:
①参见约翰·杰洛瑞:《文化资本》,江宁康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②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3页。
③Jonathan Hill,Faith in the Age of Reason:The Enlightenment from Galileo to Kant,Illinois:Inter Varsity Press,2004,p.7.
④乔姆斯基1992年指出:“一般来说,讨论人文关怀是有广泛基础的,而这类关怀一直就是‘启蒙事业’的一部分。”Norm Chomsky,Rationality/Science,in Daphne Patai,et al.ed,Theory's Empire,New York:Colunbia University Press,2005,p.536.
⑤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3—84页。
⑥玛丽·比尔德等:《古典学》,董乐山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4—45页。
⑦Harold Bloom,Genius,New York:Warner Books,2002,p.91.
⑧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董书慧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24页。
⑨Liah Greenfeld,Nationalism:Five Roads to Modernit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18.
⑩柳鸣九等:《法国文学史》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362—363页。
(11)参见郭德红:《美国大学课程思想的历史演进》,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28页。
(12)John Guillory,Cultural Capital,The Problem of Literary Canon Forma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p.97.
(13)(14)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第19—20、49—50页。
(15)参见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页。
(16)贺国庆:《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4页。
(17)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第48页。
(18)安德鲁·桑德斯:《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上,谷启楠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26页。
(19)Erich Auerbach,Mimesi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343.
(20)柳鸣九等:《法国文学史》上册,第378页。
(21)恩格斯:《反杜林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页。
(22)Harold Bloom,How to Read and Why,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0,p.99.
(23)柳鸣九等:《法国文学史》上册,第36页。
(24)参见安德鲁·桑德斯:《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上,第50页。
(25)安德鲁·桑德斯:《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上,第444页。
(26)参见姚斯:《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见《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页。
(27)恩格斯:《致敏·考茨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3页。
(28)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黄灿然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121、117页。
(29)Gertrude Himmelfarb,The Roads to Modernity,US:Alfred A.Knopf,2004,p.160.
(30)Elise Kimerling Wirtschafter,Russian Enlightenment Theater,Dekalb: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2003,pp.12-13,and 29.
(31)Pierre Bourdieu,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Poetics 12,1983,p.331.
(32)John Guillory,Cultural Capital,The Problem of Literary Canon Forma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p.339.
(33)参见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95页。
(34)(35)John Guillory,Cultural Capital,The Problem of Literary Canon Formation,p.213,60.
(36)Michael Grenfell ed.Pierre Bourdieu,Durham:Acumen,2008,p.107.
(37)约翰·杰洛瑞:《文化资本》,第318页。
(38)John Guillory,Cultural Capital,The Problem of Literary Caron Formation,p.339.
(39)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叶桐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516页。
(40)John Guillory,Cultural Capital,The Problem of Literary Canon Formation,p.45.
(41)罗钢等主编:《消费文化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1页。
(42)朗松:《朗松文论选》,徐继曾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409页。
标签:文化论文; 法国启蒙运动论文; 贵族等级论文; 贵族精神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古典语言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百科全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