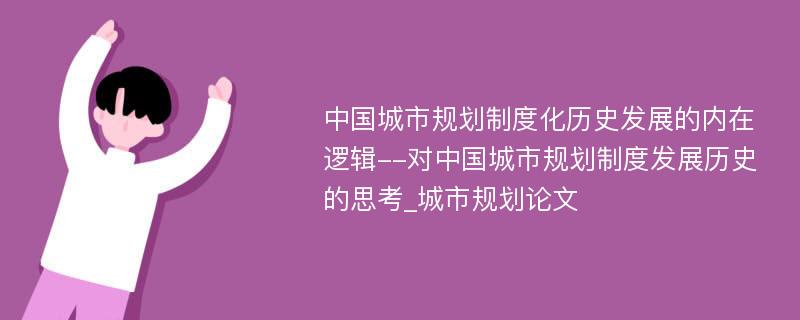
中国城市规划制度化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关于中国城市规划制度发展史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市规划论文,中国论文,发展史论文,逻辑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制度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进入西方经济学视野的历史并不很长,但其在20世纪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目前对制度的生发、型构、扩展及变迁的理论研究方面,尽管同样以欧美市场经济作为理论建构的现实阐述范型,西方经济学界却出现了两种泾渭分明、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理论体系的分野,并分别以两位大师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代表人物,即以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为代表的演进理性主义思径取向和以诺斯(Douglas North)为代表的工具理性主义分析理路(注:参见《社会秩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一书,著者:韦森,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简而言之,哈耶克认为一系列具有明确目的制度的生成,既不是什么设计的结果,也不是发明的结果,而是产生于诸多未明确意识到其所作所为会有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是自生自发地生发与型构出来的。而诺斯则认为,制度的发明与创新,并不像哈耶克所理解的那样来自市场过程中的自发制序的生成,而是来自统治者、经济或政治的企业家们的理性计算和心智建构。
虽然城市规划制度(体系)的发展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性,并不完全一致,但其作为城市发展的社会建制之一,是直接在社会、经济、政治体制运作所许可的范围内生存、发展和发挥作用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因素对城市规划来说具有先决定性(孙施文,1999)。因此,要考察城市规划制度化的行程,必须将其制度功能的发挥及作用方式的演变还原到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结合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加以考察,以大历史的眼光,从长时空探求城市制度演变的历史发展脉络和深层内在逻辑。
唯有依托这种对长时空下制度变迁脉络及特点的分析,才有可能对我国城市规划制度化当前所处的历史阶段,所面临的特殊困境及可能的对策出路做出一个更为清晰和准确的判断。
1 三个历史阶段的划分
作为一个部门及学科发展的缩影,中国城市规划制度化的发展折射出中国现代化进程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所饱含的种种艰辛曲折与彷徨困惑。在多重制度惯性及数度外界强制因素的持续交织作用下,其发展迥异于西方内涵式的发展道路,表现为一条亘古未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变迁道路。以各个历史时期我国城市规划制度型构、运演的主要影响因素和主导运行机制为依据,笔者运用诺斯及哈耶克的相关理论将其划分为3个历史阶段:
1.1 内卷中的复制(1840年之前)(注:有学者认为,在人类社会制序的变迁中,有三种“路径力量”在起作用:即革命(revolution)、演进(evolution)和内卷(involution)。简单说来,“革命”是一种间断性的、突发式或者说是剧烈的社会制度的改变与更替;“演进”是指一种连续性的(往往是缓慢地)、增进性的(incremental)、发散性的或沿革式的社会变迁;“内卷”则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社会体系或制度在一定历史时期中在同一个层面上的内耗、内缠、自我维系和自我复制。)
由于弥漫于整个传统中国社会和传统华夏文化中强烈的泛道德化倾向,法律制度并没有像从古罗马时期以来的西方社会那样,成为传统中国社会基本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反,在超稳定、泛伦理化的礼治社会中,传统中国社会在制度化的进程中经历了一种与欧美社会所不同的“反向制度化”过程。具体而言,即西方制度演进过程是一种内在于社会交往、尤其是经济运行和市场发育过程中的自发社会秩序的扩展,是一种趋向法治的制度化进程;而我国则正相反,是把文化观念、道德伦理、意识形态向法律体系的浸透、注入和改造(注: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道德因素在中国的泛滥,有源自地理、技术及组织等方面的原因。)。
从法源上讲,由于无论是在传统中国社会上层的主流意识,还是在民众的一般认识中,都没有一个超验的至高无上者作为一切法律和公义的最终渊源,因而浓重的现世情结很自然地使法律被理解为人的意志建构的结果。这就必然为以“礼治”为表层形式的“人治”留下了充分的空间。
在以刑法为主体的伦理型中华法系中,缺失成型的民法体系,正式的法律总是以垂直方式发生作用(由国家指向个人),而不是以水平方式在个体之间发生作用,它主要作为维护道德秩序和自然礼仪秩序的一种补救手段而存在。这显然就与以民法为主体的罗马法系、欧洲大陆法系、以及以调整市场交换关系为主的英美普通法系有着根本性的差别,即中华法系不是像罗马法和普通法那样主要在水平层面上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经济学上制度效率的角度来分析,由于整个社会的交往活动主要靠伦理规范或者说礼俗来调节,即注重个人修身和道德自律,那么这种制度安排自然会从社会整体上节省一定的交易费用,不像欧美现代制度那样需要高昂的交易成本来维护和支撑。但它同时却是以巨大的、不可估量的经济激励和制度效率损失为代价的,在总体上是一种内向而非竞争性的制度,因而是一种无效率的制度(注:参见韦森.社会秩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01.第275~283页。)。
泛伦理化社会中的中国古代营造制度,独树一帜地成为礼治的一个分支或曰工具,在严格意义上并不具备正式制度的含义。在理论及操作上,一切依礼而行,中规中矩而又等级森严,从而把臣民及各种功能纳入既定的礼制规则框架中。从周至清,《周礼·考工记》历来被奉为城市建设的圭皋,影响绵长悠远,其统一的型制在笼盖四野的过程中因时、因势而加以变通,遂与庞大的帝国体系相吻合一致。
帝制的庇荫使得古代营造制度绵延数千年而静滞于礼俗的层面上,在无休止的内卷中重复着简单的复制,它虽然天然具有礼制的权威优势地位,但其致命缺陷也正在于由于缺乏真正的合法性根基,因而具有较大的脆弱性和依附性,一旦其权威地位受到质疑或外界条件发生变化,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体系崩溃的危险。
依据制度的经济分析方法,传统城市规划制度强大的内卷张力根源于已陷入所谓“锁入效应”的中国传统礼俗社会的自我维系机制,而这种机制尚无从由社会内部破解,遑论中国传统城市规划制度区区一个局部的社会礼制建构。
对于传统城市制度来说,“锁入效应”的打破只能来自外部(中国传统社会)的外部(西方近现代社会),历史业已证明,正是在外来强制力量的强大作用下,旧制度随着其所赖以维系的社会基础——礼制的崩溃而崩溃,这一方面造成了空前的制度断层与制度空白(在严格意义上讲,制度空白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城市规划制度范式的根本转换带来了契机。
不容忽视的是,巨大的制度惯性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根除,法制传统的缺位,以及根植或曰内嵌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传统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将是长期而又深远的,并历史地成为中国城市规划制度化演进的逻辑起点和基本问题语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1.2 冲击下的嫁接(1840~1949年)
18世纪日益走向没落的中华帝国体系,与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后的西方近现代社会已形成巨大的文明落差,在一个日益走向开放的世界体系中,“文明的冲突”已然势所难免。中国近代史不仅是一部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抗争史,同时也是在世界范围内的制度竞争中,中国传统社会在强大外部因素作用下被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
鸦片战争以降,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紧闭千年的“天朝上国”之门,传统礼制社会的锁入效应由此被彻底打破(注:诚如诺斯所言:“战争、革命、入侵和自然灾害,均是这种间断性的制度变迁的原因”。但接踵而至的天灾人祸使得近代中国社会少有喘息的机会,其制度化进程一直未能在战争的间隙中进展多少。),其所赖以维系的封建伦理道德被五四启蒙宣判了死刑。无疑,由此形成的巨大的制度真空必然引发全方位的拿来主义,中国城市规划制度变革的闸门也随之洞开,在制度竞争的舞台上,各种新旧制度因素开始比权量力。
在当时内外交困的特殊社会条件下,一方面是传统城市规划格局与体系面临全面崩溃,日趋瓦解和消亡,仅仅依靠文化、心理层面的制度惯性得到延续;另一方面,各种新的、外来的城市制度源在经济政治力量的角逐中得以崭露头角,并在中国孕育和催生出了畸形的果实,即一种相对生硬的嫁接式规划。
这种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范畴内的嫁接式城市规划,虽或多或少地显现出殖民地、半殖民地色彩,并给以后的城市建设埋下了巨大的隐患。但同传统城市规划相比,其改革与发展也是极为显著的,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城市经济的组织和发展,促进了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的近代化,并引发了中国人自己的城市规划。
从制度发展的脉络及内在逻辑看,西方近代城市规划,是西方社会、经济、特别是工业革命发展的直接后果,是西方城市规划从古典到现代的连续发展谱系中的一个环节,是承前启后的,内因是主要因素(李百浩,2000)。
而我国的近代城市规划的发展则主要是一种被动的“冲击——反应”模式,是各种外部制度因素对传统制度锁入效应被打破后,所形成制度真空的强势输入与填充过程。这种粗糙、生硬、仓促的嫁接式跳跃发展不可避免缺少合理的内在演化逻辑,其近代性具有较大的不完善性。
1.3 建构后的渐变(1949年至今)
近代以来,国家和民族危机的持续刺激使饱受苦难的国人更倾向于接受一种乌托邦救世主义神话,终于在1949年,国人重又主宰了自己的命运,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激进主义思想也因之在制度层面上得到了较为直接、集中的表达与体现,具体表现在我国从前苏联移植进来一整套发端于法国建构理性主义的行政控制经济体制。在这种社会体制之中,传统中国社会中礼治、德治和人治的精神又以现代意识形态承传下来,并与从前苏联引进并植入的行政控制经济体制一起进行整合,从而产生了一种两者互相联系、互补共生的社会经济制序。
1950年代导入的前苏联规划模式作为计划经济的延伸,基本上是随着一整套行政控制经济的模式,在现实中成套地照搬过来的。在当时大规模物质建设及特定国际战略格局下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对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功不可没,也为我国的城市规划事业奠定了开创性的基础。但由于激进主义往往缺少有建设性的科学文化底蕴的支持而极易滑入异化的深渊,所以强烈依附于国家计划体制的城市规划不可避免地由于种种外部原因而几度沉浮,几遭封杀。最终中国城市规划不仅没有取得新的转折,反而几乎落到了一种历史“完成”感的地步(徐巨洲,1999)。
随着神话的破灭,改革大幕徐徐拉开,自由主义思想势力开始在中国复苏并有所抬头,中国的发展从此开始步入渐进改革的正途,并在实践中不断趋于完善与成熟。到了1990年代,改革之初那种过于模糊,也过于天真的改革热情已被更为现实,往往也更为保守的社会态度所取代,改革的日趋理性也使人们对依法而治以臻于法治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认识。因借国家法治化建设的东风,20年的改革发展使我国城市规划事业得到了全方位的巩固与提高,规划的管理、技术、科研、职业教育都基本实现了一定的制度化,并有了一定的本土特点(张兵,2000)。
此一时期的制度化建设步入了一个相对开放的全面发展期,正是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性带来了制度间的学习与交流,从而推动了我国的城市规划制度化建设(注:大而言之,一个社会或一种文明能不断向前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是外部世界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也正是各种主动或被动的封闭状态才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如此艰难。)。
强劲的内、外部需求拉力与压力使我国的城市规划制度化建设表现出较强的制度移植特征,只不过与过去单一、被动的前苏联指向不同,此时的制度源在开放性与本土化的基调下表现出了一定的多样性与目的选择性。尽管有一定程度的,不可避免的盲目性和急躁情绪,但人们毕竟高兴地看到,我国在城市规划制度的引进和消化吸收方面已日趋理性和成熟。
有目共睹的是,20年来沿着试错路径的改革已使我国城市规划制度化取得了可喜的长足进步,并显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被认为是我国规划事业发展的“第二个春天”。这一时期在立法方面,有作为核心法、宣言法的《城市规划法》的颁布与修订,以及适应各地特殊情况和要求的地方、部门法规和条例的纷纷出台和对法系的充实完善;在编制体系方面,则有在1990年代大开发热潮中大显身手的详规、深圳法定图则法制化的有力探索,以及新近浮出水面的战略规划、都市区规划、近期建设规划等,不一而足。
应当指出,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社会整体的渐进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这一特定历史背景密不可分的。在强势政府主导的社会博弈格局中,从属于政府体制安排的城市规划部门不得不在现实的政府目标函数及权力范围内,以“均衡”和“边际变动”为哲学理念,尽可能通过各种过渡性安排来延迟和减缓各种利益摩擦,并力图通过对外部增量的倚借来实现整体上的帕累托改进和熨平不均衡的分配效应。即在对外部体制主动或被动的调适中不断试错(trail and error),从而实现规划制度的“有限合理”。
另一方面,对外部世界的开放也使现行体制中的许多软肋暴露出来,市场化、工业化及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使得城市规划制度因其“技术一行政”的内部化操作而更显僵化与滞后,来自各方的压力使得的合法性权威地位屡遭践踏。高唱理想口号却缺少制度武器的城市规划,在短期物质利益至上的社会博弈中显得苍白无力,手足无措。对一些新问题,特别是各种分利集团利用新旧体制转轨的缝隙漏洞,大肆瓜分超额土地利润的时候,要么反应不够敏感,要么就是心余力绌,无能为力。
身处夹在国家与社会的缝制之中,备受指摘的城市规划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在崇尚经济增长数字的国家看来,所谓的整体长远利益使城市规划成为“发展的绊脚石”,有碍于政府特定目标函数的实现;在民主意识不断增强的社会看来,规划是与开发商沆瀣一气的帮凶,不仅对强势集团大肆攫取国有土地资产的不法行为不闻不问,而且其封闭的政治黑箱操作反倒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
发展中的问题加重了危机感与使命感,但人们更应看到事物发展的主流。总体看来,在全面理性建构解体之后,渐进的制度化适应了形势发展的需要,在不断荡涤旧制度的同时生发出日益壮大的新制度安排,从而不断改变着新旧制度的力量对比,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完善着我国的城市规划制度体系。
这一切诚如哈耶克所言:“在我们力图改善文明这个整体的种种努力中,我们还必须始终在这个给定的整体中进行工作,旨在点滴建设,而不是全盘的建构,并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中都运用既有的历史材料,一步一步地改进细节,而不是力图重新建设这个整体。”
2 整体回顾后的反思
2.1 历史的总结
我国城市规划制度的演进历程根植并同步于中国100年来曲折的现代化进程,已被打上深深的历史烙印。自近代以来,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基本路径力量作用下,各种内外、新旧制度因素不断改变着实力对比和相互作用方式,使得我国城市规划制度化表现出独特的发展历程,在这一特定发展理路的背后隐藏着深层的历史发展逻辑。
我国近代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规划制度化与西方内涵式的发展有着根本的不同,是以传统城市规划体系的锁入效应被外部强制力摧毁为历史基础和逻辑发展起点的,是在这一特定初始条件下,多种外生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力量与既存制度体系中各种内生力量,尤其是各种非正式制度的冲突与协调过程,即是制度变迁外生力量的内生化过程。此一过程中,外生力量的作用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首先,在力量对比上,外生力量绝对占优,具有压倒性的强势话语地位。在新旧力量强烈的对抗与冲突中,任何制度效率的获得都伴随着巨大的制度变迁成本。其次,在作用频度上,外生力量反复冲击,使得本可连续的制度化进程在若干不同性质的外力作用下被数度割裂或中断。
正是强势的外生力量与中国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内生力量之间的反复激荡与磨合,使我国城市规划制度在保有巨大的多重制度惯性的同时,兼具明显的复合制度移植痕迹。这可以作为笔者对100年以来我国城市规划发展基本特点的一个判断。
2.2 两条理路在中国的问题语境中的“反思平衡”(注:笔者在此借用罗尔斯(John Rawls)在《正义论》中提出的“反思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的原则:无论是普遍的规范论证,还是经验性的道德知觉,都不是终极的判断标准,需要通过相互的反思,取得某种平衡,以求得深入的讨论。)
转型期中国的问题语境具有特殊的复杂性,即各种自发因素在全面建构松动瓦解而产生的缝隙中潜滋暗长,自发与建构两种路径力量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联机制和机理,在实践中更是盘根错节,难以区分。因此,不应偏执地固守一端,而应在中国问题语境下对哈耶克演进理性和诺斯的构造理性进行一种审慎的“反思平衡”,从而使之在经验和规范两个层面上皆能与中国国情相妥贴匹配。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制度的进化既是自发的,又是可控的,中国城市规划制度化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诺斯与哈耶克思想彼此对峙,相互理解并逐渐包容的历史,也正是借助这两种,制度分析理路传统之间的紧张,人们才有了自我反思和完善的内在资源。
2.2.1 演进主义的解释力与局限性
综观20余年来中国改革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这一跨度颇长的改革时段本身,似可归纳为中国社会自发型构的社会经济秩序的出现、型构、成长和扩展,而在过去的行政控制经济时期为人们所刻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经济秩序的衰微、缩小和弥散这样一种历史过程。改革的巨大成功,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哈耶克所揭示的自发社会经济秩序的型构机制及其背后的逻辑力量的一个印证和展开。
可以认为,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经济秩序”理论与分析理路,并不仅仅是对欧美近现代市场经济型构、演进、扩展和变迁历史进程的学理归纳与理论抽象,而且也是中国从这样一种从僵化的行政控制经济模式,向一种充满生机活力的市场经济秩序过渡的历史行程的理论再现(注:参见韦森.社会秩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01.第64页。)。渐进改革路径的选择可以说是在痛定之后,不期而然的对人类自发秩序的理性回归,具有某种内在必然性。
同时,必须看到这种演进主义路径自身的局限性,即其在价值上的优势并不能弥补其在落实到制度实施层面时可操作性差的劣势,而这一局限性恰恰在中国当前的问题语境中得到了放大和强化,从而使改革有滑入新的泥潭的可能。这种可能性表现在,我国渐进改革的历史及逻辑起点是旧有计划体制,尽管起因于自下而上的努力,但主要还是经由自上而下的督导推动起来的,在总体上是国家主动或者被动的向社会放权的过程。此种初始条件下,对旧体制的依赖使得在原有体制下的形成的社会准则、规范以及行为方式等均未有根本改变,而由其所产生的思维定势和行为习惯以及在原有体制下形成的社会结构、政治体系和权力网络尚未及全面改造(孙施文,1999)。
于是在中国现实的政治力量对比和实力较量过程中,在新、旧分利集团分化组合后崛起的新“权力——资本”联盟将主导制度改革的实际进程,他们有可能出于自己最大化利益的考虑而构造出在整体上对社会来说是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的制度来,演进主义这种潜在的危险性可能在中国形成新一轮从内部难以突破的“锁入效应”。
2.2.2 有限理性下的建构作用
人们必须把我国城市规划制度化这一历史进程看成是演进性与构造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辩证统一,并在有限理性思想的指导下充分发挥人类理性的制度建构作用。
笔者认为,在总体认识上应当秉承哈耶克演进主义的基本哲学理念,承认人之理性不可能完全把握和控制制度变迁这一自发的历史过程,承认制度的演进具有不能被人们完全认识和控制的内在逻辑,承认传统和经验的重要意义。而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只要运用人的抽象的推理能力,便能够建构出普遍有效的和完善的制度及其所有细节”。相反,全面的规划,精确的计算远不如自发的、从局部到整体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方法有实用价值。
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制度设计实践中,则应更多地借鉴诺斯制度变迁理论中的实证内容,力求理性地从中国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中寻求切实可行的操作基点。因为人的理性的有限性并不排除人之理性的有限(理性)运用。而在人的信息和知识的可及范围内,人之理性的理性运用恰恰构成了社会制序制度化过程的主要使命亦即先决条件。
制度化是社会的一种自觉活动,任何一项(正式)制度安排自始至终都离不开人类理性的推理与建构作用的支撑。必须指出的一点是,人们重视理性不是因为其建立体系的能力,而是为了理性在具体实践中的遇到的问题——道德的、心理的、社会的、政治的、科学的问题——上的机制性和实用性的应用。
标签:城市规划论文; 哈耶克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制度化管理论文; 自发反应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