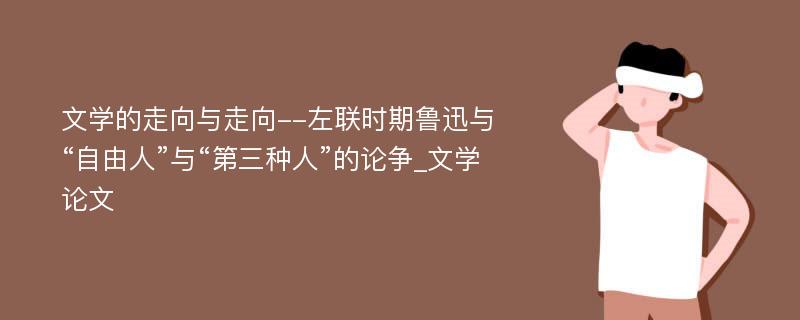
文学的方向与倾向——左联时期鲁迅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自由人论文,种人论文,倾向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关于“第三种人”、“第三种文学”
对“第三种人”的定义以及所包含的范围目前学术界还没有清晰的界定。笔者认为“第三种人”定义的范围应是:(1)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2)在“知识阶级”的“自由人”和政党的领导之间。值得注意的是,苏汶和后来也自称“第三种人”的胡秋原都怕把资产阶级的恶名加到自己头上去。苏汶在《“第三种人”的出路》中说,因为无产阶级的文学被几位指导理论家几次三番的限制,其内容已经缩到不能再缩的地步。因此许多作家都不敢赞称无产阶级作家,只以“同路人”自期。“然而这些‘不敢冒充’为无产阶级的作品,却未必一定是拥护资产阶级的作品。反之,它们纵然在意识上还有许多旧时代的特征,但多少总是向于无产阶级的;即使这一点倾向都看不出,那么至少可说是中立的。然而在左翼文坛看来,中立却并不存在,他们差不多是把所有非无产阶级文学都认为是拥护资产阶级文学了。”①苏汶在这里是想为中立者的文学辩护,不认同不是无产阶级文学便是资产阶级文学的左翼文学理论,最担心的是怕被左翼理论家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致使很多“作者之群”不得不搁笔,怕被指摘为“恶意”②,“资产阶级的走狗”③,“艺术至上主义”④等。鲁迅在对“第三种人”的答复中也是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立场来论左翼文坛和“第三种人”的关系的。“因为不问那一阶级的作家,都有一个‘自己’,这‘自己’,就都是他本阶级的一分子,忠实于他自己的艺术的人,也就是忠实于他本阶级的作者,在资产阶级如此,在无产阶级也如此。”⑤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第三种人’的‘搁笔’,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评的严酷。真实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这样的‘第三种人’,做不成这样的人,也就没有了第三种笔。”⑥并举出纪德的例子,认为他在关键的时刻“就显出左向来了”⑦,还是做不成不偏不倚的“第三种人”。
另外,一些左翼的文艺评论家冯雪峰、瞿秋白、周扬等都是持非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论“第三种人”的。像瞿秋白就说:“每一个文学家,不论他们有意的,无意的,不论他是在动笔,或者是沉默着,他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⑧1932年11月共产党人张闻天以哥特之名在《斗争》报上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指出这种关门主义,“第一,表现在对‘第三种人’与‘第三种文学’的否认。我们的几个领导同志,认为文学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或是无产阶级的,一切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一定是资产阶级的文学,其中不能有中间,即所谓第三种文学”⑨。张闻天认为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文学“是中国目前革命文学中最占优势的一种”⑩,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在无产阶级文学与资产阶级文学之间有第三种文学的存在,批评了左翼文坛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其实鲁迅早在1931年发表的《上海文艺之一瞥》中就指出:“在现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最容易希望出现的,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11),“因为他生长在这正在灭亡着的阶级中,所以他有甚深的了解,甚大的憎恶,而向这刺下去的刀也最为致命与有力”(12)。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还没出现的时代,鲁迅肯定了小资产阶级文学存在的合理性和革命性。
第二,“第三种人”应被理解为处于“知识阶级的自由人和政党的领导之间”。“在‘智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的阶级争着文坛的霸权的时候,最吃苦的,却是这两种人之外的第三种人。这第三种人便是所谓作者之群。”(13)挑起关于“第三种人”论战的是苏汶发表于《现代》杂志一卷三期上的《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在这篇文章里,苏汶是把“智识阶级的自由人”胡秋原等放在“第三种人”的对立位置的。胡秋原在《是谁为虎作伥》中对自由的智识阶级的定义是:“我们所谓自由的智识阶级,不过表明我们:1.只是一个智识分子;2.是站在自由人的立场。事实是如此,因为我们:不愿自称革命先锋,3.我们无党无派,我们的方法是唯物史观,我们的态度是自由人立场。”(14)苏汶把胡秋原的知识阶级的自由人立场看作是“书呆子马克思主义”(15),他认为“第三种人”既在左翼文学、民族主义文学之外,也不包括“争着文坛的霸权”的“智识阶级的自由人”,“第三种人”即是简单的作者,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没有任何主义和理论作为写作背景。虽然胡秋原后来也认同自己是“第三种人”:“不要勉强他一定要写什么,怎样写。所以,我之所谓自由主义态度与唯物史观方法的意见,实际上只是一种第三种人的意见而已。”(16)胡秋原认为自己的“自由主义态度与唯物史观方法的意见”是一种“第三种人”的态度。他后来把“作者之群”界定为“既非南京的‘民族文学家’又非普罗作家的“中间群”,这和苏汶的作者之群的界定是有区别的(17)。苏汶的“作者之群”是把智识阶级的自由人胡秋原排除在外的,这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按照施蛰存的说法,“是指无产阶级及其文艺理论”(18),胡秋原却把自己界定为“第三种人”,并且把“第三种人”界定为“既非南京的‘民族文学家’又非普罗作家的‘中间群’”,这样,“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就不仅仅指“无产阶级及其文艺理论”,还包括南京的“民族文学家”,“第三种人”就有了在知识阶级的自由人和政党的领导之间的意义了。无疑,苏汶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作者的眼光更犀利,他批评胡秋原站在自由人立场高擎马克思主义,看到了胡秋原的文艺自由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内的,在阶级斗争白热化的年代最终将导向不自由,而他的“作者之群”的文艺自由理论,因关注现实、关注真实的要求,又没有特定的文艺理论支撑,最终又不可避免地倒向文艺还是可以暂时为政治服务的圈套。苏汶作为“作者之群”的文艺自由要求在当时的历史现实条件下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最终倒向承认“第三种人”只是对左翼文艺政策的一种反弹,实际上在现实中是没有“第三种人”的说法(19)。
苏汶曾在《文艺自由论辩集》的《编者序》中明确地说过:“一九三二年中国文坛上的论争,是以文艺创作的自由为问题中心的,虽然牵涉到旁的方面去是很多。”(20)可见文艺创作的是否自由在当时已成为一些知识分子对于文学创作现状的忧虑。苏汶从自己创作时不自由的切身经验感到了文学创作的诸多禁锢,是一个有良知的文学创作者发出的对于文学创作自由要求的内在呼声。所以苏汶提出了一个名词:作者之群,可看出这个名词不带任何政治等利害色彩的中立意义。“我所发表的意见,大部分可说是根据于从事于创作时或不敢创作时的一点小小的感想。”(21)左翼却不承认有第三种立场,认为在“在一九三一年底,中国阶级斗争紧张到了争取政权的阶段”,“‘逍遥自在的书生们,打起好好的反民族主义文学,反法西斯文化的旗帜,都因他们的‘自由智识’,想在严阵激战之中,找第三个‘安身地’,结果是‘为虎作伥’!”(22)
刘微尘在《“第三种人”与“武器文学”》中指出中国的“第三种人”即苏联的“同路人”,这个比方是恰当的。指出了“第三种人”的特殊身份,是摇摆于左翼文学和民族主义文学之间的,与当时的自由主义作家又有区别。这种区别即在“第三种人”与左翼的亲近关系,不像自由主义的作家,本身就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他们或者是从左联分离出去,如苏汶、杨邨人等,或者本身即标榜是马克思主义者,如胡秋原等。
张闻天第一次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中创造性地提出“第三种文学”这一名称,经冯雪峰在《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一文中系统阐述。无疑,关于“第三种人”、“第三种文学”的知识和论争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化史、文学史上关于文艺自由论的认识。
二、政治立场与文学立场的内在冲突
一般被认为是中间刊物的《现代》的主编施蛰存先生晚年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是左派,但是左翼作家不承认我们。我们几个人,是把政治和文学分开的。文学上我们是自由主义。所以杜衡后来和左翼作家吵架,就是自由主义文学论。我们标举的是,政治上左翼,文艺上自由主义。”(23)“《现代》杂志的立场,就是文艺上自由主义,但并不拒绝左翼作家和作品。当然,我们不接受国民党作家。”(24)朱光潜也曾说,“我在文艺的领域维护自由主义”(25)。“政治上左翼,文艺上自由主义”,也即中国文化自由主义的特色。自由倾向的作家在救亡图存的时代,既选择了政治上的左翼倾向,也不想放弃文艺上的那一点自由,这也是自由主义在中国本土化,形成以文化自由主义的传播为主的特点。
1930年10月10日《前锋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发表国民党御用文人“六一”社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我们认为现在中国文艺的危机是由于多型的对于文艺底见解,而在整个新文艺发展底进程中缺乏中心意识。因此突破这个当前的危机的惟一方法,是在努力于新文艺演进进程中底中心意识的形成。”胡秋原于1931年底发表了一篇《阿狗文艺论》的文章,他站在艺术立场而不是政治立场上来批驳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所以也招来左翼文坛的围攻。胡秋原说:“文化与艺术的发展,全靠各种意识互相竞争,才有万华缭乱之趣,中国与欧洲文化,发达于自由表现的先秦与希腊时代,而僵化于中心意识形成之时。同一种中心意识,独裁文坛,结果,只有奴才奉命执笔而已。”(26)“艺术虽然不是‘至上’,然而决不是‘至下’的东西。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艺术家虽然不是神圣,然而也决不是叭儿狗,以不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学,是对于艺术尊严不可恕的冒渎。”“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27)谭四海最先写文章批判胡秋原,认为胡秋原的“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的主张是否认文学受阶级、社会的限制,把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论提高到政治立场的高度来批判。周扬认为资产阶级主张“艺术至上主义”,高谈“艺术的价值”,是要“在意识形态上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胡秋原在《是谁为虎作伥?——答谭四海君》中说:“我敢大胆告诉四海君,我是从朴列汗诺夫、佛理采、马查出发,研究文艺的人,我在一切讲文艺的文字中否认过阶级性没有?我在分析民族文艺的时候是否指出它的阶级性?四海君必须明白:对于文学持比较自由的态度,是与否认‘阶级性’毫不相干的。”(28)虽然胡秋原承认自己受过普列汉诺夫等的影响,也不否认文艺的阶级性,但他明确说过他不想站在政治立场上评论文艺:“我并不想站在政治立场赞否民族文艺与普罗文艺,因为我是一个于政治外行的人。……对于文艺的态度,也有根据艺术理论的分析与根据艺术之政策的排斥扶植的不同。但是我并不能主张只准某种艺术存在而排斥其他艺术,因为我是一个自由人。”(29)胡秋原的矛盾即在承认文学有“根据艺术理论的分析与根据艺术之政策的排斥扶植的不同”,却又申明自己是个自由人。既承认文学艺术政策的排斥扶植功能,又主张各种艺术的同时存在。而不管是无产阶级的文学政策还是民族主义的文学政策都是不允许其他文艺的存在的。“我是反对一切凯撒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后裔侵略文艺,这就是说,并不反对耶稣的门徒利用文艺。”(29)“即我决不是‘立定主意反对一切’利用艺术的政治手段,而对于利用艺术为革命的政治手段,并不反对,为什么呢?因为革命是最高利益。不能为艺术障碍革命。为革命牺牲一切,谁也无反对之自由。”(30)胡秋原认为革命是最高利益,为了革命可以利用艺术。这和左翼的革命文学理论最终又走到一条道上。不过胡秋原又清醒地说:“那补助革命的艺术,不限定是真正值得称为艺术的东西而已。”(31)苏汶的言论和胡秋原如出一辙:“干涉在某一个时候也是必要的,这就是在前进的政治势力或阶级的敌人也利用了文学来做留声机的时候。”(32)苏认为做前进的政治势力的留声机的文学,多少还有它存在的必要。至于那种做反动的政治势力的留声机的文学,应该在可能的范围内消灭它的存在,“这方面的干涉主义是正当的,它有利于政治,同时也有利文学的永久的任务。”(34)而对于革命与文学的关系,苏汶这样说:“并不是怪左翼文坛不该这样霸占文学。他们这样办是对的,为革命,为阶级。不过他们有一点不爽快,不肯干脆说一声文学现在是不需要,至少暂时不需要。”(35)可见胡秋原和苏汶的文艺自由论的妥协和不彻底性,在另一方面来说,也可以说是一种对于左翼文学理论改造过的折中的文艺自由论。
当时左翼理论家也正是看到了胡秋原、苏汶文艺观点的内在冲突,他们就用一种非常干脆的被苏联篡改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胡秋原、苏汶等的文艺自由论一棍子打死。洛扬(冯雪峰)在《致文艺新闻的一封信》中说:“胡秋原的主义,是文学的自由,是反对文学的阶级性的强调,是文学的阶级的任务之取消。”(36)冯雪峰认为提倡文学的自由就是取消文学的阶级性。文学包含阶级意识是正常的,但如果认为文学要自由就与文学中的阶级性势不两立,这是文艺阶级性理论。还是瞿秋白说得比较直接:“在阶级的社会里,没有真正的实在的自由。当无产阶级公开的要求文艺的斗争工具的时候,谁要出来大叫‘勿侵略文艺’,谁就无意之中做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派的留声机。”(37)余虹认为:“苏汶与胡秋原一样从文艺阶级性的复杂性到文艺工具性的多样性出发反对文艺上的政治干涉主义,为文艺的自由争得了一点缝隙。但是,他也与胡秋原一样,出于阶级道义的选择,他又最终取消了这一自由的缝隙。”(38)按照余虹的说法就是因为胡秋原与苏汶都是在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范畴内从道义化的阶级论出发,没有真正的自由主义理论为其立论辩护,所以,他们必然地为文艺争取不到一条真正通向自由的路,最终落入到以谈文艺之名而谈政治的左翼思路。“死抱住文学不放”偷偷变成了文学为政治服务。
胡秋原和苏汶对文艺自由的主张是中国特殊的历史现实条件下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文学本身功能的一种维护,所以他们对于文艺自由的要求又是不彻底的。鲁迅不承认“第三种人”存在更多只是左翼的一种应战策略,他又说过“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39)的话,说明他是承认有同路人存在的,同路人按照一般的解释应就是“第三种人”。冯雪峰也曾在《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中说过:“同时我们对于苏汶先生等的理解,固然需要全面的注意,但我们首先注意那对于革命有利的一面,即苏汶先生等现在显然至少在消极地反对着反动统治阶级及其文学了。因此,我们不把苏汶先生等认为我们的敌人,而是看作应当与之同盟战斗的帮手。”(40)就在左翼检讨自己的关门主义,希望招“第三种人”一路走时,最终促使这场论争发生质的变化的,是“第三种人”的“转向”。1933年以后,先是发生了杨邨人的脱党并宣称“愿意作个“第三种人”,“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41),要求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小市民和农民的作家有自己的文学,能发表自己的心声。接着又发生了1933年底的“献策”事件。加之韩侍桁、苏汶等人连续不断地发表与左翼阵营相对抗的文章,“第三种人”发展至此,引发了左翼文学阵营对其重新进行政治定性。鲁迅后来又写了《又论“第三种人”》、《脸谱臆测》、《中国文坛上的鬼魅》等文章。在《脸谱臆测》中,鲁迅认为“第三种人”“终于显出白鼻子来了”(41)。“反对文学和政治相关的‘第三种人’们,也都坐上了检察官的椅子。”(42)“第三种人”的转向,可以看出“第三种人”的做不成,“第三种文学”的失败。到底是否有“第三种人”和第三种立场?也就是胡秋原所说的“自由人立场”,鲁迅虽不承认有“第三种人”存在,但其有关文学创作的言论表明了鲁迅的文学观与“第三种人”的一致的地方。不承认“第三种人”,是鲁迅的政治立场,但对文学的看法却又表明了鲁迅对于文学创作的自由主义立场。施蛰存和他主编的《现代》也面临着这种选择和分裂。“政治上左翼,文艺上的自由主义。”这也许就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特殊的历史现实环境下的特殊表现吧。左翼表示,在一个大众失去自由的时代,追求自由是奢侈的,他们宁可让文艺失去自由,也要让文艺挑起无产阶级解放的使命。而鲁迅并没有这方面的直接言论,他只是提到在有阶级的社会让文学不关涉阶级是不可能的。可以看出鲁迅对左翼文学抱着充分的同情心的同时,对左翼文学与阶级、政治的关系及其创作手法等是抱着谨慎和审视的态度的。苏汶的文学立场相对于胡秋原来说更具有不带任何理论色彩的纯粹的作者之群的立场的意味。在左翼、鲁迅、自由人、第三种人之间,他们的文学立场和观点都有一些细微的不同。仔细辨析开来,可看到鲁迅与冯雪峰、瞿秋白等左翼人士论述时的决断语气有所不同,鲁迅在论述文学的阶级性和文学的关系时只是说的部分,而不是全部,这和胡秋原、苏汶的承认文学有阶级性却不是全部是阶级性是一致的。关于文学写什么的问题,鲁迅说过:“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44),“以为一个艺术家,只要表现他所经验的就好了”(45),“倘不在什么旋涡中,那么,只表现些所见的平常的社会状态也好”(46)。鲁迅对世间往往误以两种文学为革命文学的观念给予了讽刺:“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对手的;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47)鲁迅更注重于革命文学的先锋性和反抗性。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鲁迅认为文艺与政治始终是冲突和矛盾的,文艺家常常要得罪政治家。不能忽略鲁迅这个复杂的思想体的特点,在任何时候,鲁迅都会用多疑的眼光不随意附和于任何一种观点。他的存在就是中国文化文学转型时期的所有复杂思想集于一身的表现。
三、方向和倾向的困惑
与左翼坚定地立足于文学的政治、阶级立场不同,鲁迅和自由人、第三种人更倾向于认同政治、阶级是文学的一部分,而不是文学必与政治、阶级相关联,都比较关注于文学的真实和对虚伪文学的排斥。
鲁迅在左联时期为了斗争的需要虽较注重于文学的方向,但并不表示鲁迅对文学的审美的忽视。沈从文曾说过:“当朝野都有人只想利用作家来争夺政权巩固政权的情势中,作家却欲免去帮忙帮闲之讥,想选一条路,必选条限制最少自由最多的路。”(48)而鲁迅就是在必得选择文学的倾向和方向的年代,把文学中的阶级等因素看作是一种带倾向性的因素,而不是政治、阶级立场问题。
从“五四”前期到“五四”后期,因国际国内的左倾形势,历史要求从批判封建礼教到提出如何建设一个新国家的问题。“于是1925-1927年前后,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坛上,出现了一种不约而同、不谋而合、自觉自愿的方向转换的现象。”(49)在国民党推出“民族主义文艺”,希图把文艺统一于国民党的“中心意识”之中时,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左联的上级领导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蒋光慈就曾说:“为着要执行文学对时代的任务,为着要转变文学的方向,所以也就不得不提出革命文学的要求。”(50)文学的社会功能被过度地扩大,超过了文学本身所能负载的意义,文学此时也就会如胡秋原所说不是“真正值得称为艺术的东西”了。
左翼更坚定文学的方向和立场是斗争的需要,而“自由人”、“第三种人”在感到创作不自由的同时,希望从长久的眼光来挽救文学免于堕落。知识分子的困惑,“第三种人”的不许存在,也表现了中国现代迫切的救亡图存的现实不允许关注时代现实、有着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立场的稍许动摇和模棱两可。左联时期,冯雪峰,瞿秋白都曾著文反对“自由人”、“第三种人”。“自由人”、“第三种人”当时是作为中立者的姿态出现,虽然鲁迅是作为左翼文学的代表出现,但是鲁迅与“第三种人”关于文学自由和阶级性的争论只是一个着重点的不同,没有根本性的不同。而在政治立场上,鲁迅曾否定“第三种人”的存在,是要做具体分析的。鲁迅承认文学上阶级立场的存在,并不是“只有”。他曾说过:“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85)
鲁迅部分认同“第三种人”的文学自由观,只是声明“第三种人”不存在,做不到。那么,胡、苏是否做到?后来,“第三种人”的投向国民党当局是“第三种人”立场破产的一个证明。中国的现实使知识分子不可能有一个自由的空间谁也不依附,最终必倒向一方。这也是鲁迅的远见。一个战争的年代,在一个千年古国负载着沉重使命的文学未取得独立的时代,文学扮演的政治角色因时制宜地产生了。
“第三种人”的转向,表明了“第三种人”的做不成。“第三种人”确实存在,但在中国当时的特殊现实背景下,“第三种人”最终只能像鲁迅所说在青白之间“露出白鼻子来了”。政治立场上的“第三种人”虽做不成,但文学并不是与政治一一对应的。施蛰存所说的“政治上左翼,文学上自由主义”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第三种人”处境和信仰的真实写照。“第三种人”又不同于当时的自由主义作家,自由主义作家像徐志摩、沈从文、梁实秋等,并没有左翼的经历。他们是有分别的,也可见“第三种人”的夹缝处境,比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处境更其尴尬,身份更其复杂。他们对左翼的文学理论有同情和吸收的地方,又无法信奉左翼的文学政策,更不认同民族主义文艺政策,对自由主义作家的用西方自由主义人道主义作为支柱的自由主义文学观又是不全部认同的。如果说,当时中国文学分成四派,左翼文学、民族主义文学、自由主义文学、第三种人文学,应该说,“第三种人”文学是最没有文学理论立足点的文学,一些人在政治上最终倒向国民党也是势在必然。在当时的社会现实条件下,第三种人是做不长久的。
第三种政治立场存在不长久,第三种文学“作者之群”的写作也将成果寥寥。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苏汶否定胡秋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下的自由文艺主张,也否定不自由的政党文学,但苏汶的自由文艺观仍然赞成文艺的表达先进阶级的思想,赞成文艺的一定的政治功能。纵观胡秋原和苏汶的文艺观,我们可看到中国的特殊历史现实在“第三种人”的文学观中的反映。他们是希图保持文学自由又对中国的历史现实不能不关注的一群。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使即使是自由知识分子也不能漠视现实,他们对于文学的自由的论争只能是一种学理上的,或者是一种力求保证文学自由的努力,但对现实的关注都是一致的。
“自由人”、“第三种人”的存在表示着他们主要是对个体文学创作自山的维护,而不重视文艺本身的独立和本体审美性。他们呼吁创作者创作的内心自由,至于他们创作的是无产阶级的作品还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作品,只要他们是真实地反映着社会和人生的,都应该允许它们的存在,有它们发言的自由。胡秋原、苏汶赞成文学在某一时刻为先进的政治服务。不赞成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纯粹的文艺批评家在1930年代几乎很少,例如自由主义者梁实秋就提倡文学为道德服务,道德一般也可以理解为某一种政治下的道德。
胡秋原的“自由人”强调的是“一种态度”,而且是指在“文艺或哲学的领域”,而苏汶认为胡秋原的学院式马克思主义是不了解左翼文坛的,他认为与其把左翼理论家的主张当作学者式的理论,却还不如把它当做政治家式的策略。苏汶的文学创作观用“作者之群”的文学创作观最为恰当,也即是“创作者”。这个创作者是一个中立者,不依附于任何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不执任何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所领导的文学观。胡秋原的文学观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马克斯主义的自由主义”(52)。一方面,胡秋原、苏汶可以说陷入一个怪圈,既想争文艺的自由,又要承认文学的阶级性的正当,特别是先进阶级的表现的正当,而且都承认革命的优先性,这不得不造成他们的自由理论与其先进阶级理论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胡秋原、苏汶的文艺自由沦都主张写作者的自由写作状态,不受任何主义的约束。这无疑是文艺自由的一大前提。“我所谓‘自由人’者,是指一种态度而言,即是在文艺或哲学的领域,根据马克斯主义的理论来研究,但不一定在政党的领导之下,根据党的当前实际政纲和迫切的需要来判断一切。”(53)而苏汶更是真诚地提出自己的真实困惑:“问题并不在无利又无害的中立文学是否存在,能否存在,或应否存在,而是在:一,文学作品纵然在客观上脱离不了利害关系,但在主观上,即作者在写作的时候,是否应当时常有个利益的观念?二,主观上有利害观念是否会损坏对现实的把握?三,主观上的超利害观念是否会有使作品流于有害的危险?”(54)从这里,可看出胡、苏重视的是主观的自由写作状态,至于写的是什么,只要是真实的,都有写作的价值。鲁迅也赞成苏汶的“与其欺骗,与其做冒牌货,倒还不如努力去创作”(55)的观点,而不是如周扬那些绝对论者所说的:“因为无产阶级是站在历史的发展的最前线,它的主观的利益和历史的发展的客观的行程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对于现实愈取无产阶级的,党派的态度,则我们愈近于客观的真理。”(56)
“自由人”、“第三种人”文艺观点的内在矛盾即在其政治观和文学观的不一致产生的矛盾,鲁迅同样也面临着此种矛盾。他们都是在认同先进阶级(无产阶级)存在的合理性的前提下,追求文学的最大限度的自由。所以,他们的文艺观的理论窘境不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自由主义文艺观的区别,而是革命的优先性和文学本身的独立性之间的矛盾。如果以倾向于中立者施蛰存先生上述的话来理解左翼和“第三种人”的文学观,我们就更能理解,关于“第三种人”、“第三种文学”的论争,我们更可把它当作是一种对于文学与政治、文学与革命、文学本身的一次有益的探讨。政治与文学分开的历史现实使中国现代很多知识分子不得不面临着思想的分裂,在这种分裂中,更加深了我们对于中国现代历史、文学自由的理解。
注释:
①②苏汶:《“第三种人”的出路》,《现代》第1卷第6期(1932年10月)。
③苏汶:《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现代》第1卷第3期(1932年7月)。
④“但因为艺术至上主义已经成为一个很好的骂人的名称,因此他们便津津乐道了。”见苏汶:《“第三种人”的出路》,《现代》第卷第6期(1932年10月)。
⑤鲁迅:《又论“第三种人”》,《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7页。
⑥鲁迅:《论“第三种人”》,《鲁迅全集》第4卷,第452页。
⑦鲁迅:《又论“第三种人”》,《鲁迅全集》第4卷,第539页。
⑧易嘉(瞿秋白):《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现代》第1卷第6期(1932年10月)。
⑨⑩张闻天:《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张闻天文集》第1卷,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308页。
(11)(12)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第307页。
(13)苏汶:《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现代》第1卷第3期(1932年7月)。
(14)胡秋原:《是谁为虎作伥》,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第17页。
(15)苏汶:《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现代》第1卷第3期(1932年7月)。
(16)胡秋原:《浪费的论争》,《现代》第2卷第2期(1932年12月)。
(17)“所谓‘第三种人’,原指所谓‘作家之群’,然而这名称马上变为用以指那既非南京的‘民族文学家’又非普罗作家的‘中间群’之称了。……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种‘第三种人’是存在的。”时夫(胡秋原):《论“第三种人”》,巴黎《救国时报》1936年3月20日“救国谈”栏。
(18)施蛰存:《现代杂忆》,《北山散文集》(第2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50页。
(19)见苏汶:《一九三二年的文艺论辩之清算》,《现代》第2卷第3期(1933年新年号)。
(20)苏汶:《编者序》,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第1页。
(21)苏汶:《编者序》,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第3页。
(22)谭四海:《“自由智识阶级”的“文化”理论》,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第16页。
(23)施蛰存:《为中国文坛擦亮“现代”的火花——答新加坡作家刘慧娟问》,《沙上的脚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81页。
(24)施蛰存:《为中国文坛擦亮“现代”的火花——答新加坡作家刘慧娟问》,《沙上的脚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1日1页。
(25)朱光潜:《自由主义与文艺》,《朱光潜全集》第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80页。
(26)(27)胡秋原:《阿狗文艺论》,《文化评论》创刊号(1931年12月)。
(28)胡秋原:《是谁为虎作伥》,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第19页。
(29)胡秋原:《勿侵略文艺》,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第10页。
(30)(31)(32)胡秋原:《浪费的论争》,《现代》第2卷第2期(1932年12月)。
(33)(34)苏汶:《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第192页。
(35)苏汶:《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现代》第1卷第3期(1932年7月)。
(36)洛扬(冯雪峰):《致文艺新闻的一封信》,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第58页。
(37)易嘉(瞿秋白):《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现代》第1卷第6期(1932年10月)。
(38)余虹:《革命·审美·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9页。
(39)鲁迅:《论“第三种人”》,《鲁迅全集》第4卷,第451页。
(40)冯雪峰:《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雪峰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97页。原载《现代》第2卷第3期(1933年1月)。
(41)杨邨人:《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现代》第2卷第4期(1933年2月)。
(42)鲁迅:《脸谱臆测》,《鲁迅全集》第6卷,第138页。
(43)鲁迅:《中国文坛上的鬼魅》,《鲁迅全集》第6卷,第161页。
(44)鲁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378页。
(45)(46)鲁迅:《致李桦》(1935年2月4日),《鲁迅全集》第13卷,第372页。
(47)鲁迅:《革命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第567页。
(48)炯之(沈从文):《再谈差不多》,《沈从文全集》第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50页。
(49)陈伯海主编:《近400年中国文学思潮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507页。
(50)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太阳月刊》第2期(1928年2月)。
(51)鲁迅:《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第128页。
(52)胡秋原:《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台北:学术出版社,1980年,第6页。
(53)胡秋原:《浪费的论争》,《现代》第2卷第2期(1932年12月)。
(54)苏汶:《一九三二年的文艺论辩之清算》,《现代》第2卷第3期(1933年新年号)。
(55)鲁迅:《论“第三种人”》,《鲁迅全集》第4卷,第453页。
(56)周起应:《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现代》第1卷第6期(1932年10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