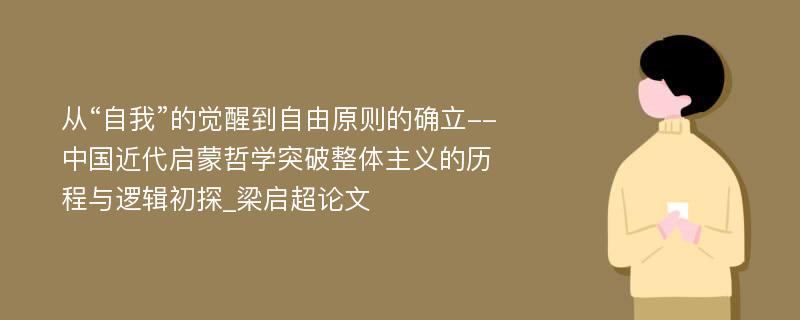
从“自我”的觉醒到自由原则的确立——中国近代启蒙哲学冲破整体主义的历程与逻辑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近代论文,逻辑论文,历程论文,哲学论文,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说,从自然中发现人,是人类认识史和智慧史的第一次突破,那末,从人类的群体生 活中发现个体的价值并承认个体的独立与自由,是人类自我认识的又一次飞跃。就社会史而 言 ,后者构成了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换的必要条件——思想启蒙的主要内容。在中国,伴 随资本主义萌芽在明代中后期的发生,产生了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在对黑暗社会现实和宋 明理学的批判中,早期启蒙思想阐发了个性解放的要求,凸现了对人的个体存在的重视。中 国 近代进步思想家上承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以对人的存在之个体性的重新发现为突破口, 对理学为代表的本质主义及其相关联的权威主义、专制主义展开了冲击。与明清时代的启蒙 思想不同,近代思想家的批判意识中既包含了从现实中汲取的时代内容,也广泛援入了西学 作为思想武器。在他们的理论视野中,与群体秩序相联系的“天理”被转换为以民主、自由 、平等、博爱等为内容的“公理”。环绕着个体的存在和本质两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近代 进步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提出和论述了功利原则和自由原则,对理性专制主义及其禁欲主义 倾向展开了批判。对“自我”、“心力”等的高扬,对“独”、“群”及其关系的理论思辨 ,对非理性主义的同情和首肯,是近代哲学家在形上学层面关注和思考群己关系,并试图走 出传统的整体主义价值体系的具体体现。
一、“自我”的觉醒与天命的没落
十九世纪初,随着清王朝的鼎盛期——“康乾盛世”的结束,中国封建社会也进入了总崩 溃的前夕。在近代的入口处,龚自珍以诗人的敏感,意识到一个不同于“衰世”的新的时代 即将到来,这个新的时代的特征就是“自我”的觉醒。
事实上,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特别是在儒家哲学中,并不乏肯定乃至高扬“自我”的理论 资源。然而,作为独立个体意义上的、特别是作为权利主体的“自我”概念,却迟迟未能“ 发育成长”起来。儒家对“自我”的重视,更多的只是强调道德自我的挺立,其目标在群体 道 德的维护而不是个体权利的确认。从孔子的“无我”、“毋我”到宋儒的“存天理,灭人欲 ”,所追求的目标实际上都是以泯灭个体来维护社会的整体秩序。在传统价值体系中,由于 纲常伦纪的绝对化,个体不可能有独立之价值,而只有在“事父事君”、“尽伦尽职”中才 能获得生存的意义,对群体的义务压倒了一切自我意识,“无我”成为理想的道德境界。龚 自珍继承了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和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及其道德的腐 朽性,认为其最大的罪恶就在于扼杀了“自我”。他从哲学的高度推崇和论证了“自我” 。他说:“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圣人也者,与众人对立,与众人为无尽 。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变造毛羽肖翘,我理造文 字语言,我气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别造伦纪。”(注:《壬癸之际胎观第一》,《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第12-13页。)在这里,龚自珍不仅提出了“自 我”的概念,而且把“我”作为世界第一原理提了出来,这虽然有强烈的唯意志主义色彩, 但它所表达的思想信息无疑是近代意义的。
在龚自珍看来,“我”既创造世界,同时也为世界立法。他说:“既有世己,于是乎有世 法。民我性不齐,是智愚、强弱、美丑之始。民我性能记,立强记之书,是书之始。……” (注:《壬癸之际胎观第二》,《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第14页。)总之,一切法则皆出于“民我性”,从文字、数字、天文历法、几何学、医药学到宗法、 礼教和政治制度,都是由“我”的本性创造出来的。“我”的这种创造力,实际上也就是“ 心力”,“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注:《壬癸之际胎观第二》,《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第14页。)人们只要“自尊 其心”,发挥主观意志的创造力,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
对“自我”和“心力”的推崇,极大地冲击了尊奉“天理”、“天命”的正统儒学思想, 吹响了个性解放的时代强音。在《病梅馆记》中,龚自珍以隐喻的手法,生动地描述了封建 专制制度对人的种种“约束”、“羁縻”的不合理,表达了人们要求在自由的天地里发展个 性的愿望。这种重心力、尚才性、尊情感的个性解放思想,对社会思想和文学艺术产生了重 要的影响。
就中国启蒙思想的历程来看,从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要求个性解放的主张到龚自珍的张扬 “自我”,其间经过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并且有着历史性的差异,但其共同之处是对人的 个体性的发现和重视。龚自珍对“自我”的推崇和“心力”的赞美,不仅在鸦片战争前后对 中国哲学思想的转型起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可以说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梁启超在《清代学 术概论》中写道:“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 ”。 (注:《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二》,《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第5 4页。)这实际上代表了这一时期追求进步的思想者的共同感受。从“自我”到“新民”再到 五四时期对独立人格的呼唤,其间贯穿着一条使个人得到解放、使人的主体性得到伸张的思 想主张。中国近代思想家们对“自我”、“自性”、“心力”、“独”等的推崇,在世界观 特 别是形上学意义上说,正是人的存在的个体性的发现和理论表露。
近代以降,社会思想的主要特征是天理世界观的崩溃和整个传统价值体系的危机。从一定 意义上说,各种思想派别和社会思潮及其冲突,皆环绕此而产生和展开。如果说洋务派思想 家的“中体西用”思路表明他们尚致力于维护和挽救传统儒学为代表的价值体系的话,代表 资产阶级的维新派和革命派思想家则力图冲破这种价值体系,主张对其进行变革和改造。新 文化运动时期的进步思想家们则进而认为,传统儒家为代表的价值体系不仅是早该退出历史 舞台而未退出的东西,而且它本身在理论上也是漏洞百出的。在他们那里,“激进反传统” 的形成,不仅仅是出于道德的义愤和救亡图存的急迫心情,同时也有学理上的依据,他们从 西方进步思想学术中获得了理论的支持。
近代进步思想对“天理”、“天命”世界观的冲击和批判,不仅在传统价值体系上打开了 缺口,而且也为其整体坍塌造就了条件。传统价值体系的核心是一种消解个体价值、把个人 定义为一种工具性存在的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它是以天理天命世界观为支持的,是包裹在天 理天命世界观的理论体系之中的。随着天理和天命的没落,整体主义也无可奈何地走向了衰 落。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传统的价值结构是‘权威’与‘权力’合一,以皇帝为首的行 政权力系统以及士绅代表着价值原则”,构成了传统价值体系的物质承当(注:高瑞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导论》,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第3-4页。)。而随着辛亥革 命对帝制的推翻,传统价值体系失去了其物质承当而不得不走向瓦解。近代历史的这一巨大 变迁,是整体主义价值体系走向衰亡的根本性原因。与整体主义的衰落相伴随的是个体自由 和个性解放思潮的兴起,它不仅逐渐成为中国现代精神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一定历 史时期成为了思想界的主旋律。
二、“独”与“群”:秩序重建及其矛盾
伴随天命世界观的衰落,传统文化所构筑的意义世界也开始塌落,群体秩序出现了严重的 危机。晚清以来,各种新思潮的出现,都表现了重建秩序的努力。接触西学较早的康有为、 梁启超、严复等人,对中西政治文化的优劣分别进行了比较。受进化论思潮的影响,在他们 的思想深处,包含着这样一种共识:原有的制度已不能有效地将民众组织起来以适应近代以 民族国家为单位进行的生存竞争,必须对原有的群体秩序及群己关系重新进行思考。因此, 在甲午战争后,随着启蒙与救亡矛盾的展开,随着西方思潮特别是进化论的传播,“独”与 “群”的矛盾关系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问题。以至有的研究者认为:“清末民初西化运动的 思想精髓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便是进化论;两个基本点便是围绕严 复《群己权界论》书名中点明的‘群’与‘己’所展开的理论探讨。”(注:王思睿:《人权与国权的觉悟》,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无论人们是否同意 这 种说法,但有一点应该承认:“群”概念的提出以及围绕“群”与“己”或“群”与“独” 展开的理论思辨,是对传统思想的突破,包括了重建秩序的新的思考路向。对此问题有较深 入研究的张灏指出:“群”是一个主要受相反社团组织和政治结合能力的事例所激发的新的 概念;(注: [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8页注二。)“群”作为改良派学者讨论的一个焦点,“反映了很多人对中国社会与政治组织进 行的反思”,“对‘群’的讨论是社会政治秩序出现危机的一个明显标志”。 (注: [美]张灏:《危机中的知识分子》,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51页。)张灏还认为 :“在19世纪90年代,‘群’的概念变成中国知识分子争论的焦点。这种关于‘群’的概念 争论证明,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正在滋长做某些自晚周轴心时代以来从未做过的事的 要求。即:重新考察中国社会政治秩序的制度基础。”(注: [美]张灏:《危机中的知识分子》,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页。)应当说,这种分析很有见地。
如果说,古代思想中的整体主义倾向是因为有一个“天下”意识和视华夏为中央之国的观 念背景的话,那么近代思想家们则再也无法固守“夷夏之辨”中的中国文化优越论立场。相 反,在许多人思想的深处,都有着一个中国文化边缘化的危机意识或者说“情结”。正是出 于这样一种情结,他们重视思考中国社会的结构,试图通过对社会群体的肯定和辩护,来实 现对作为“独夫”的君主的制约。康有为明言“群则强”(注:《上海强学会后序》,《康有为全集》(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95页。);梁启超认为“群故通,通故智 ,智故强”;(注:《变法通议·论学会》,《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31页。)谭嗣同则把学会这种群体的存在,放到“无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注:《群学》,《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444页。) 的高度加以肯定。在他们对群体及其意义的认识中,已吸收了西方的民主思想和观念。正如 有的研究者指出的:“在晚清时代,‘群’、‘社会’和‘国家’范畴的引入导致了对人的 重新界定,即人是‘国民’”;(注:汪晖:《公理世界观及其自我瓦解》,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2期。)“晚清思想中的“‘公’、‘群’和‘公理’概念的确 为论证国家的必要性提供了某种证明,但这些概念并不必是国家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注:汪晖:《公理世界观及其自我瓦解》,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2期。)“梁启超的‘社会’、‘国家’都是与今天的社会、国家概念相区别的,它们根植于他关 于‘群’的道德理想之中,或者说,它们被理解为一种具有道德一致性的共同体。”(注:汪晖:《公理世界观及其自我瓦解》,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2期。)然 而,即使这种带有传统色彩的概念,也为保守思想所不容。保守派学者王先谦对“群”概念 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认为,“天下之大患曰群”,“群者学之蠹也”。(注:王先谦:《群论》,《虚受堂文集》卷一。)在他看来,“ 群”的提倡,必然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民权,从而导致对王权的威胁。从这里可以看出,无 论是维新派思想家还是保守派学者,都意识到了这一概念及其所包含的论题的重要性——它 的提出意味着对个体、社会、国家、王权等复杂关系的新思考。
中国近代的时代主题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围绕这一时代主题,进步思想家在文化 上展开了启蒙,在政治上则致力于挽救民族的危亡。启蒙和救亡作为解决中国近代社会问题 的两条途径或手段,都具有工具的意义,虽然其方向一致,且相互促进,但又有相冲突和矛 盾的方面。就群己关系来看,两者的着眼点是略有不同的:前者主要着眼于个体,后者则主 要着眼于群体。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矛盾的特殊性,救亡压倒启蒙,群体解放优先于个体自由 ,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不应忽视的是:启蒙之目标——人的解放与发展不仅有工具的 意义,而且它本身就有终极的价值。近代进步思想家的失足,往往在此。即仅仅从工具意义 上去理解个体之地位与个体之发展,将其视为群体解放与发展的条件和手段。事实上,无论 是个体或是群体,都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或者说,二者互为目的与手段。割裂二者的这种关 系,不仅会导致片面的认识,而且极易导向对传统的整个主义的回归。
近代社会启蒙与救亡、群体独立与个体解放的矛盾,反映在哲学思想上,就是思想家们在 “独”与“群”两种致思倾向上的徘徊与挣扎。
中国近代哲学一方面借鉴或者附会西方自然科学,以力、电、以太、元素、原子、细胞等 作为世界的本原;另一方面也汲取传统思想包括佛学等的内容,以“心”、“心力”、“自 我”作为世界之最高原理和动力;也有的哲学家还试图把这两者杂揉在一起来建立哲学体系 。然而无论采取何种立场,近代哲学都表现出与传统的以“理”、“气”为世界本原的不同 致思路向,折射出对“独”、“自力”、“自性”等的推崇。康有为以“元”作为世界之本 原,而又把“元”解释为“仁”,也就是“不忍人之心”。在他看来,正是这种主观的精神 力量,才是万物的主宰和改造世界的动力。(注:参见《孟子微》,中华书局,1987年,第9页。)谭嗣同认为,国家的落后,人民的贫弱,皆 由于“心源不洁”,“劫”由“心”成,须以“心”解之:“虽天地之大,可由心成之、毁 之、改造之,无不如意。”即变革社会现实,必须借助于“心力”;凭借“心力”,一切目 标 皆可达到。从中国近代哲学总体来看,在思想资源方面,无疑有本土和外来两个方面。就 本土资源的吸取而言,陆王心学起了显著的影响。宋明时期的陆王心学,凸现了“自我”或 人的主观精神的作用,将“心”提到了宇宙本体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突出了人的主 体性,恢复了人的自身价值和尊严,从而从内部对理学的天命论体系构成了否定,包含着产 生新思想的契机和萌芽。就外来文化的影响而言,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和哲学中的 浪漫主义(非理性主义)也对近代以来的思想家产生了深刻影响。可以说,对“独”及“心力 ”的推崇,一方面是社会变革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撷取本土及外来精神资源而产生的新的 思想观念。
在重视“独”的同时,近代哲学家又普遍重视和强调“群”的意义。从康、梁、严到孙中 山以至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此都有相当多的论述。严复指出:“夫既以群为安利,则天演 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能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注:《天演论》导言十三按语,《严复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347页。)要“保种”“保国”, 必须要“能群”“善群”。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之所以不振,乃在公德之欠缺,故必须收集 中西之道德,改造吾“喜独”之国民性,树立“合群”“乐群”之新民德。他探讨了西方社 会“群”的几种主要形式——“国群”(议院)、“商群”(公司)、“士群”(学会)各自的特 点和作用,并特别强调学会的意义。在他看来,无论是政治群体,或是经济群体,皆以学会 为基础,因为心智之开,能力之培养,皆从学而来,“故学会者,又二者之母也。”(注:
《变法通议·论学会》,《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33 页。)“ 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注:《变法通议·论学会》,《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31页。)梁启超还从“群”与“群”竞争的角 度,论证了中国当时弃“独术”奉“群术”的重要。他说:“天下之有列国也,己群与他君 所由分也。据乱世之治群多以独,太平世之治群必以群。以独术与独术相遇,犹可以自存; 以独术与群术相遇,其亡可翘足而待也。”(注:《说群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109、4页。)
梁启超还把“群”提到世界观的高度加以论证。他认为,“群者,天下之公理也”、“万 物之公性也”(注:《说群一 群理一》,《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第4-5页。)。在他看来,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从宇宙天体到地球上的万物,从低 等生物到高级生物,以至人类社会的个人、民族和国家,都是以“群”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群”是一种合力,是事物的普遍联系,是各种关系的总和;是若干因素联合(结合)而成 的单位;宇宙是一个最大的“群”、“变”世界,万事万物都是处在大大小小的“群”、“ 变”系列之中,“群”“变”的根本原因和动力在自身的内部。注重“人道”同“天道”的 一致,是梁启超的“群”、“变”说思想的重要内容。他说:“故欲灭人之家,灭其群可也 。……欲灭人之国者,灭其国之群可也。使之上下不相通,彼此不相恤,虽天府之壤,可立 亡也。”(注:《说群一 群理一》,《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第 6页。)梁启超依据“群”、“变”的一般发展规律,结合中国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 特别强调了“以群术治群,群乃成;以独术治群,群乃败”(注:《说群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4页。)的思想,以打破君、民之间 的不平等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不团结和不合作倾向。
与梁启超对“群”的理论思辨不同,章太炎试图从本体论上论证个人的独立与自由。章氏 在甲午年写的《明独》一文,是中国近代最早对个性自由进行哲学论证的重要著作之一。在 这篇文章中,他对独和群的权界关系所给的解释是颇为独特的。他借用佛家的“自性”(约 略相当于本质和特性)来说明二者的关系:群体为个体所积,故无自性。这实际上是西方自 由主义理论关于国家是实现个体权利之手段的思想的一种思辨表达。章太炎的个体概念与晚 清以降中国思想的主流看法是颇为不同的:他揭露“社会”和“国家”的虚幻性,认为个体 对于政府、国家、社会、家族等等具有优先性,个体不是群体进化的工具。从无政府主义的 个人主义出发,他强调只能把人类个体看作是真实的,反对把集团或组织看得比个人更具有 真实性。在他看来,个人除了自己以外,不对任何人负有义务,“故人之对于世界、社会、 国家,与其对于他人,本无责任。责任者,后起之事。”(注:《四惑论》,《章太炎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300页。)可以看出,在个人的独立与自 由问题上,章太炎比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孙中山等人走得更远,也更为彻底。
梁启超和章太炎对“群”与“独”及其关系的不同看法和理论论证方式,在近代思想史上 有相当的代表性。它体现了中国近代的思想世界在启蒙与救亡、群体与个体关系问题上的矛 盾和冲突。然而,无论是“独”的推崇,或是对“群”的重视和论证,都表明近代哲学围绕 着时代的中心问题赋予了它们新的理论内涵,已与传统的整体主义价值体系对个体与群体、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解有了根本性的不同。
三、人的存在个体性的发现与对本质主义的批判
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其存在是二重化的:既是个体,又是群体和类(最大的群体即整个 人类)的成员。前者意味着每个人生命存在的独特性,后者则意味着每个个体共有着群体或 类的特性。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人是普遍本质与个体存在的统一。元典时代的中国哲学, 对此问题已有相当的理论自觉,儒道两家分别代表了对以上两个方面的关注。在孔子为代表 的原始儒家那里,对道德作为人的本性的过分强调,使得人的存在方面难免有所遮蔽,但一 般说来并未使存在与本质尖锐对立起来。随着儒学的经学化和被体制化,特别是发展到宋明 新儒学,对普遍天理作为人的本质的强调,进一步虚化和消解了人的存在方面,使人的个体 存在淹没于普遍本质之中。近代启蒙思想通过颂扬“自我”和批判“天命”,以及围绕“独 ”与“群”展开的理论思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继先秦发现和重视人的群体性、明清之 际突出人的个性以来,对人的认识的又一个新的进展——即人的存在的个体性的重新发现。 这一发现是伴随着对以理学为代表的本质主义的批判而实现的。
分析地看,儒家的仁义礼智忠信等条目,作为理性的产物,都是从共同人性出发所确立的 人人应当遵守的道德规范。这种从理性主义出发对于共性的强调,具有重要的和合理的意义 ,对于保证传统社会中的秩序特别是维系中华民族的统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其负面作 用,也是极其明显的。从孔、孟到后来的儒家思想,都包含有以牺牲个性或个体的差异性来 维护共性和普遍性的主张。由于儒家长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主流地位,其所提倡的作为 普遍共性的道德规范,逐渐内化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使得中国人缺乏独立的个体性和主体 意识。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被拉长,近代资本主义难以孕育及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历 史表明,正统儒家一方面高扬道德理性主义,另一方面却导致了理性的异化,走上了理性专 制主义的道路,使道德理性超出了合理地节制和调节非理性从而提升人的尊严和生命存在意 义的合理界限,转而成了扼杀个体和个性的工具。
从理论上说,理性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本质特征之一,也是人的主体性的一个核心内容。 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与人的理性的成长分不开的,理性原则是指导人们走出蒙昧和野蛮的一面 旗帜。然而,理性原则的过度膨胀,就会导致理性专制主义。中国传统哲学中道德理性的极 度膨胀,甚至被“天理”化,就是理性专制主义的突出表现。在“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中 ,无疑包含着强调人的理性,认为人应当是理性的特别是具有道德自觉性的这样一些因素, 但总体说来这种主张违背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人类个体的生命存在必然是有血有肉的,有情 感和欲求的。否定和排除人的感性方面,而要人成为纯理性的人,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强求如此,只能造成畸形的或异化的人,并且导致自我人格的丧失与普遍的道德虚伪。中国 封建社会的“高调”道德和黑暗腐败并存的历史实际,对此是最好的注脚。从人本身的全面 发展看,理性专制主义是片面而有害的,它必然要导向禁欲主义,而这种禁欲的结果,反过 来又使理性的发展失去动力。从共同体或群体与其中的个体的关系来看,理性专制主义由于 消极地抑制个体和扼杀个性,其结果必然导致共同体内部仅仅靠强制的“同质性”来维系其 团结,使共同体失去丰富的内涵和革新发展的活力,从而无法在多样性中得到发展。在中国 传统思想中,先秦儒家虽不是禁欲主义者,但是,他们思想中的理性主义的片面性已十分明 显。事实上,这种理性主义的片面性已经是跨向禁欲的理性专制主义的桥梁。宋明理学的禁 欲主义倾向,正是儒家理性主义片面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
就西方哲学史来看,近代可以称之为理性主义凯歌行进的时代。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到黑格尔描述的运动着的“绝对精 神”,都是理性主义的典型体现。理性主义推崇理性和科学、重视逻辑思维,把人看作是具 有理性本质的人,把世界看作是合乎理性的和谐的世界。这一切无疑是合理的和积极的。但 是,理性主义由于对理性的过分推崇而使人的理性能力和理性本身的功能被过分膨胀,一方 面使得理性被形而上学化:理性不仅是人把握事物本质的手段,而且它也就是事物的本质 自身,甚至是绝对的精神本体;另一方面,作为理性的主体的人则仅仅成了理性所观照的一 种对象性的存在,人变成了一种与自然对象没有差异的“物”。同时,这种理性主义包含着 某种本质主义的倾向:它不仅把存在于事物背后的某种永恒不变的东西作为解释事物存在的 根据, 而且把这种形而上学化了的“理性”视为人的“一般”或本质,这不仅导致对人的存在和人 的个性的忽视,而且极易导向权威主义和独断论——因为按照本质主义的逻辑,只有某种把 握了所谓“本质”的理论或权威人物才是唯一正确的。
因之,中西方哲学史都表明:理性主义事实上是一把双刃的剑:一方面,它具有伟大的意 义,它借助于理性确立起人的主体地位并使人获得解放;另一方面,它由于对理性的片面推 崇而忽略了人的感性存在方面,对共性的渴望和追求而漠视甚至抹煞了个性。理性主义发展 到后来,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它不仅使理性被异化了,而且成了人的发展的新的桎梏。非理 性 主义思潮的兴起,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理性主义的异化方面的抗议和纠偏,它以个体与个 性解放为目标和旗帜,与理性主义对共性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普遍秩序的追求是颇为不同的。 而从追求人的个性自由和解放这一点来看,它与近代理性主义刚刚兴起时的启蒙作用又是颇 为相似的。正如许多研究者早已指出的,非理性主义对人的个体存在的关注和个体自由的追 求,正是回到了近代理性主义最初的出发点。
中国近代哲学和社会思潮中非理性主义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一方面是对儒学理性专制主义 的反叛,另一方面也是由中国近代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对于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来说, 他们处在黑暗而又急剧变革的时代,肩负着沉重的历史责任:对内要冲破封建主义的牢笼, 谋求社会的民主和个体的自由;对外要抵抗帝国主义的压迫,谋求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 。完成这样的历史重任,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毅力。前者需要弘扬人的个性和主体精神; 后者需要激起国人的自尊、自信和自强精神。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对个体意志及主观精神力 量的重视,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所贯穿着的个性自由原则和反抗精神,既为中国近代思想家 提供了自我激励和唤醒民众的精神动力,也为他们提供了建构理论体系可以利用的思想资源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近代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因素的突出就毫不奇怪了。
近代中国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虽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但在如下方面是共同的:它们都反 对把理性作为绝对的权威,都对个体及个性必须绝对服从整体和普遍性这样的原则加以怀疑 和批判。换言之,都反对理性的异化,反对理性压抑和扼杀个体及个性。在中国近代启蒙过 程中,出于对个体存在的关怀,进步思想家们从不同角度对理性专制主义展开了冲击。陈独 秀甚至公开推崇“兽性”——他将其解释为“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 然”、“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注:《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0页。),以改造缺乏对黑暗势 力抗争的国民性格。在中国近代非理性主义思潮中,唯意志主义是影响最大的一族。正象冯 契先生指出的,中国近代确实形成了唯意志论的传统,唯意志主义“以其特殊的形式包含着 相当激进的革命内容:反对以天命论为中心的旧价值观,提倡斗争和创造原则;反对正统儒 学的理性专制主义和禁欲主义,提倡意志自由、自然情感,要求个性解放、独立人格”。(注:《冯契文集》第八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第484页。)
中国近代非理性主义不仅对冲破把道德理性绝对化的理性专制主义起了积极的作用,而且 它也是对传统整体思维方式的突破。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具有明显的整体思维的特点,它强 调从整体观照局部,以局部显现整体。其着眼点和落脚点都是整体,其认识的目的主要是为 了打通整体内部的关系。这种整体思维不仅限制了科学的理性思维,而且也影响到对群体和 个体关系的认识,导致群体与个体之界限和关系不明,个体之自由及个体之权利得不到彰显 ,使中国传统社会长久处于礼俗社会,无法孕育和转向近代的法理型社会。与此相反,近代 非理性主义所引导的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新的思维方式,其思考的着眼点不在整体或和谐, 而在个体和自性。这无疑是与社会趋向现代化的过程相一致的,是一种“现代性”的思维方 式。
中国近代非理性主义的兴起不仅仅是受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使然,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 景 和人道主义内涵。它体现了近代思想在走出中世纪的历程中对人的个体生命的重视和关怀。 从合理的人本主义的哲学立场来看,人不仅有物质的生命,而且也有着精神的生命(精神生 命的本质很大程度上就是自由及生存意义的实现)。与前者关联着的是人的利益,与后者关 联着的则是人的自由。因此,功利原则和自由原则是确立人的生命存在及其地位不可或缺的 两个方面。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不仅贬斥功利原则,而且就其极为重视的对精神生命的关怀来 看,也更多的只是与道德认同相联系的。与西方文化将人的生命意义归之于“与上帝同在” 相异,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推崇的“三不朽”说,充满了现实的并且在一定意义也 是人文的精神,其实质是主张将个人有限的生命融入无尽的历史长河,其途径即为“立德、 立功、立言”——其核心则为个体对群体的归属和关怀。这种中国式的“终极关怀”不仅造 就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而且对培育历史上以民族大义为重、以百姓安危为己任的无数豪 杰之士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之德行名垂青史,一方面是自我生存意义的实现,另一方面也 是对群体关怀的实现。但是,正如前文已分析指出的,儒家的这种人生理想及其所引导的精 神生命意义的方向,却又有着负的一面。对精神生命意义的高扬是以对人的感性存在方面的 贬抑为前提的,对道德义务的看重使得个体人格的独立和精神自由的权利被轻视和贬低, 从而把个体的精神生命限制在仅仅是道德认同这样一个狭窄的领域。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在批 判 传统思想贬斥人的感性存在的同时,对传统思想重视人的精神生命这一点也进行了批判性的 改造,以具有丰富内涵的自由原则取代了以道德认同为核心的意义原则。
需要指出的是,自由原则在中国近代思想界的确立,不仅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 而且是与进化论的传播分不开的。正像有的研究者指出的:“毫无传统思想资源可作依托的 自由主义,是在进化论的召唤下,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注:陈卫平:《世纪末的新世界观》,见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 大出版社,1996年,第79页。)如首先向国人介绍自由主义 的严复,对自由主义的看重就是以进化论为中介的。他所介绍的自由主义思想,多半出自具 有进化论思想的斯宾塞、赫胥黎、密尔等人。因之,在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的萌生和演变 中,“进化论始终是其理论基石”。(注:陈卫平:《世纪末的新世界观》,见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 大出版社,1996年,第80页。)这主要表现在:进化论为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确立了 关于个体自由的价值观。无论是西方或是中国,自由主义区别于其他学说的根本标志,在于 重视个体自由的价值。但是,中西方自由主义构筑个体自由价值的理论支点却是不同的。西 方自由主义从洛克到卢梭都通过“天赋人权”即每个人生而自由的预设为前提,肯定了个体 自由的价值。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则主要借助于进化论来论证个体自由的价值。例如严复不仅 不认同西方视自由为自然权利的观念,而且对以卢梭为代表的“天赋人权”说提出了批评。 他把个体自由的价值与社会的进化联系起来。在他看来,自由是通过社会的进化来实现的, 人类进化的目标就是趋向自由,进化的程度越高,自由就越多。这种观点无疑包含着合理的 因素——依照这种观点,自由不是天赋的,而是获得的;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变 化发展的;人不仅是自由的享有者,而且是创造自由的主体。同时,严复还认为,只有让个 体在自由竞争中优胜劣汰,才能演进到理想的社会,因此自由也是人类进化的动力。由此, 严复 在肯定个体自由的价值的同时,更以进化论为基础来说明了个体自由与国家富强之间的 关系。在他看来,人类进化是以群体的形式实现的,所以,作为人类进化产物的个体自由应 从属于国家(群体)的富强。严复思想中的这种倾向和观点,在中国近代从戊戌到辛亥时期的 启蒙思想家中有相当的代表性。当新文化运动兴起特别是五四前后,自由原则才更多地与个 体自由和个性解放联系起来。
总之,从“自我”的觉醒,到“独”与“群”的思辨讨论,再到自由原则的确立,标志着 中国近代启蒙哲学在群己关系上试图走出整体主义的大致历程。这一历程从形上层面说,是 个体主体性和个体自由的逐步凸现;从具体方面来看,则主要展开于对制约群己关系的外在 秩序、制度和内在价值观念的变革两个维度。换言之,自由既包括社会权利方面的政治自由 ,也包括道德人格方面的意志自由,在群己关系中以自由原则取代整体主义,既要去除内在 的奴性人格,又要突破外在的制度性压制。前者主要表现为对个体人格的独立和个性自由的 追求 ;后者则主要表现为对政治自由与民主权利的追求。正是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中国近代启蒙 思想的核心内容。
标签:梁启超论文; 理性主义论文; 龚自珍全集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战略与管理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群体心理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