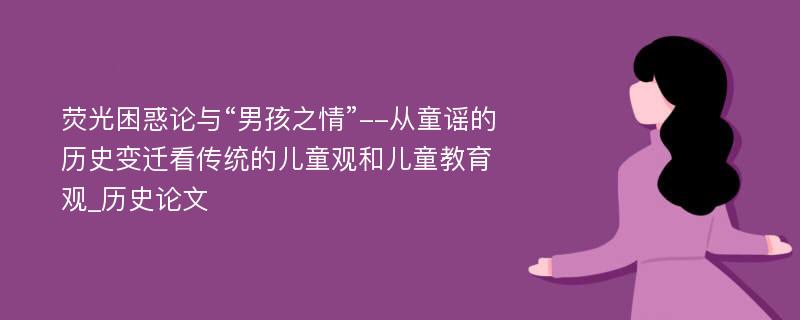
“荧惑说”与“童子之情”——从童谣的历史变迁透析传统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荧惑论文,童谣论文,儿童教育论文,童子论文,之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09)06-0107-07
童谣者,“儿童歌讴之词”,[1]亦即传唱于儿童之口、无乐谱的歌谣。果戈理曾说:“歌谣不是手里握笔,根据严格的计算写在纸上的,而是在旋风中,在忘情的境界中创作出来的。”[2]作为歌谣的一部分,童谣尽管未必产自“旋风”抑或“忘情的境界”,似乎也应该是由生活中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但回顾中国传统童谣的历史,却有一个颇为刁诡的现象,那就是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童谣不仅经由“严格的计算”创作而成,甚至是经过苦心的策划而传唱于儿童口中的。在明代以前,这种现象尤为突出。
一、溯源:从“檿弧箕服,实亡周国”说起
中国传统童谣之源当追溯于西周末年。《国语·郑语》云:“宣王之时有童谣曰:‘檿弧箕服,实亡周国。’”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周宣王于公元前828年即位,“共和”罢,次年称元年,崩于公元前782年,在位凡四十六年。征诸典籍,宣王时童谣应是现存最早的童谣。既然这是传统童谣的源头,我们势必须要多费些笔墨来对其作一番分析。事实上这种分析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首童谣几乎奠定了传统童谣两千年的基调,影响不可谓不远矣。
“檿弧箕服”,指山桑木做的弓和箕草做的箭袋。这短短的两句话是说:那卖桑木弓和箕草箭袋的,就是使周灭亡的人。作为中国传统童谣的“始祖”,这首宣王时童谣竟毫无儿童的影子,而是将关怀赫然放在了王朝的兴衰更替上,且充满了神秘气息,有一种原始的恐怖。关于这首童谣的前后始末,《国语·郑语》及《史记·周本纪》都叙述甚详,可谓说来话长,此处仅撮其要言之。据说当周宣王听到这首童谣时,即下令捕杀售卖弓箭的一对夫妇。这对夫妇在逃亡途中适逢宫中小妾所遗之女婴,哀而收之,奔于褒。幽王时,褒人得罪于周,献此女示好,是为褒姒。幽王十分宠爱褒姒,为博红颜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致使诸侯日渐远之。当外敌真正入侵时,烽火却再也招不来救兵,幽王遂被杀于骊山脚下,西周亡。童谣就这样离奇地应验了。《国语·郑语》说:“天之命之久矣,其又何可为乎?”更将童谣与天命捆绑在了一起,使得传统童谣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一种异样的面貌,彻底背离了儿童自身的生活,并赋予其传唱主体一种莫测的力量,致使本来与兴亡大事毫不相干的黄口小儿却成了诡谲动荡的政局的预言家。
再看《左传》。《左传·僖公五年》:
八月甲午,晋侯围上阳。问于卜偃曰:“吾其济乎?”对曰:“克之。”公曰:“何时?”对曰:“童谣云:‘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鹑之贲贲,天策焞焞,火中成军,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醜奔京师。
僖公五年为公元前655年。以传唱年代言,这首童谣晚于宣王时童谣约一百多年;以见于记载时间言,则这首童谣更早,且应该是最早的。①它袭用《诗经》体例,基本为四言句式,句句押韵,从形式上看还是比较适于当时儿童吟唱的。但是观其内容,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童谣预言了一场侵略战争的胜利。更神奇的是,连胜于何时都言之凿凿,毫厘不爽。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当然不相信童谣有如此玄而又玄的力量,其或为晋献公故弄玄虚玩的一套把戏,借童谣为本是侵略性质的战争披上了天意的外衣,或为《左传》作者以后见之明将之安放在了前面。不管哪种假设有成立的可能,我们需要思索的是:为何童谣在政治生活中有如此举足轻重的地位?反过来说,为何童谣会成为被利用的对象?童谣若为晋献公或其臣僚所造,那说明当时已很流行视童谣为天意之体现的观念。童谣若后起于晋之灭虢,则创作者虽然不详,但将一场战争编予儿童吟唱本身就很引人深思。若是《左传》作者有意将“后事”作“前事”,那只能再次证实童谣与天意紧密相连的观念在当时是如此深入人心。
回看周宣王时童谣,情形大概也不外如此。这两首童谣开中国传统童谣之先河,但却与儿童及儿童生活毫不相干,这就成了问题。更成问题的是它们并驾齐驱,共同为传统童谣打上了一抹挥之不去的底色,使得传统童谣始终笼罩在一种奇特的氛围中,而且越到后来越将这种色彩和氛围点染描画得具体生动,并进而理论化了,以至于到魏晋时终形成了完备的“荧惑”之说。从此影响更是绵邈深远,历千载而不绝。
二、“荧惑说”盛行之下童谣的异化
《左传》和《国语》虽录有童谣,并将其与天命联系起来,但数量有限,也未作过多阐释。到班固(32-92)作《汉书》时,在“五行志”中集中收录了五首童谣,其中有两首为《左传》所载,一首为《史记》所收,另外两首则是《汉书》独有的。将童谣收入“五行志”无非是承继了《左传》、《国语》的观点,认为童谣与天命气运相关,可以预示吉凶。班固的做法影响了后世修史的人,自《汉书》开始,相当数量的童谣均被收入历代官修史书之“五行志”,以至于周作人直接称之为对待童谣的“五行志派”。[3]这也可说是“荧惑说”的滥觞。
荧惑是古人对火星的称呼。因其色呈金红,荧荧如火,亮度常有变化,而且运行轨迹无定,令人迷惑,故曰荧惑。至于将童谣与荧惑联系起来的说法起于何时,现在已经比较难以考定,不过王充(27-约100)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论衡·订鬼》说:
天地之气为妖者,太阳之气也。妖与毒同,气中伤人者谓之毒,气变化者谓之妖。世谓童谣,荧惑使之,彼言有所见也。荧惑火星,火有毒荧,故当荧惑守宿,国有祸败。火气恍惚,故妖象存亡。……《洪范》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火同气,故童谣、诗歌为妖言。言出文成,故世有文书之怪。世谓童子为阳,故妖言出于小童。
从上面这段话可以知道,至少在王充生活的时代已经有了童谣是荧惑使之的说法,而且他认为这种流行的说法也还颇有见地。
《通志》和《文献通考》均载有这样一条材料:
张衡云:荧惑为执法之星,其精为风伯之师,或童儿歌谣嬉戏。
王充曾拜班彪为师,与班固是同时代人。张衡(78-139)则稍后于他们。与王充力求用“气”来解释童谣为荧惑使之的说法相较,张衡所言要简单通俗得多,因此也较容易理解。
由班固到王充再到张衡,关于童谣的“荧惑说”逐步成型了。到魏晋时,则进一步发展完善了这种观点,且更具象化了。《晋书·五行志中》云:
孙休永安三年,将守质子群聚嬉戏,有异小儿忽来言曰:“三公锄,司马如。”又曰:“我非人,荧惑星也。”言毕上升,仰视若曳一匹练,有顷没。干宝曰:“后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废,二十一年而吴平。”于是九服归晋。魏与吴、蜀并战国,“三公锄,司马如”之谓也。
由此条记载我们可以获知,到三国或至迟至晋时,关于童谣为荧惑使之的说法不止甚为流行,且描述得活灵活现,宛然如在目前。
《晋书·天文志中》又言:“凡五星盈缩失位,其精降于地为人……荧惑降为童儿,歌谣嬉戏……吉凶之应,随其象告。”这是将“荧惑说”最终理论化了。此后书史中关于“荧惑”之说引述不绝,唐人潘炎甚至作《童谣赋》云:“荧惑之星兮列天文,降为童谣兮告圣君。”(《文苑英华》卷八十五)
童谣由作成到与天命气运等变得相关大致不外乎通过如下两条途径:
其一,如杜预所说,“童龀之子未有念虑之感,而会成嬉戏之言,似若有凭者,其言或中或否。博览之士,能惧思之人,兼而志之,以为鉴戒,以为将来之验,有益于世教”。(《左传·僖公五年注》)剥掉“似若有凭”这层意思,这段话其实还是比较平实的。儿童自己创作童谣,原本只为自娱娱人,拥有充沛联想力的人却将此与一些历史上比较重大的事件联系起来,录而存之,并附加“鉴戒”之类意见,童谣就这样莫名其妙和天命气运云云发生了关系。还有另一种情况,也或者童谣为成人所作,本意原只在教导或愉悦儿童,传唱之后却“一不小心”就变成了占验的童谣或曰谶谣。
其二,童谣为时人有意之作,“流行于世,驯至为童子所歌者耳”。[4]这是一条相反的途径。与无意于“其言或中或否”的童谣创作情况不同,这是有心为之,但却未必局限于“将来之验”,可能多的倒是过往之鉴和现实的投射,所以其言常中,或“虽不中亦不远矣”。如果为了造成“似若有凭”的效果,在时间上聪明地做一些手脚,将前事做后事,后谣作前谣,童谣就真成了天意所授一般。
不论起始点有何差异,传统童谣有很大一部分最后是殊途同归的,即变得与时政有关。既与时政相关,或为避祸,或为图谋,在创作和传播方式的选择上都不得不隐晦迂回一些,童谣和儿童就成了最佳利用对象。“荧惑说”就这样出世了。
自汉而下,从大传统即精英文化层面来说,“荧惑说”在童谣领域近乎一统天下,这深刻影响了童谣的整体生存状况。
首先是占验类童谣的大量涌现。《后汉书·五行志》载十二首童谣,全部为政治预言类童谣,大大超过了《汉书》所录。晋时占验类童谣更是层出不穷,与成型的“荧惑说”互为唱和。《晋书·五行志》收二十六首童谣,于二十四史中为最,并赫然冠以“诗妖”之名。
综观历代书史中录占验类童谣,其样貌均不脱周宣王时童谣窠臼,所述之事与儿童生活悬隔万里,晦涩难解,加之又要故作神秘,常常不知所云。但一般而言,这类童谣也会在形式方面稍稍顾及传唱主体的需要,比较注重音韵节奏,尽量做到朗朗上口,以使儿童乐于诵唱。当然,这一切最终还是为了达到童谣创作者特定的目的。可以想象,逢大事变时,群儿齐唱,众口一词,再假预言之形式,披“荧惑”之外衣,对于欲诉复杂心曲的成人来说,真是再好不过的保护伞。而传唱童谣的儿童们,唯闻其声,不见其人,集体性隐没在那些诡谲莫测的谣词中,彻底沦为了成人的工具。
其次,在“荧惑说”笼盖四野之下,普通童谣亦被曲解为占验类童谣,从而使其真实面目反而变得模糊了。
《旧唐书·五行志》云:
元和小儿谣云:“打麦打麦,三三三。”乃转身曰:“舞了也。”及武元衡为盗所害,是元和十年六月三日。
武元衡是唐宪宗时宰相。元和十年(815)六月三日,在上朝途中遭暗中突击,丧命。对于上述童谣如何与此事相关,《旧唐书·五行志》未作解释,只言其为“诗妖”。《旧唐书·武元衡列传》说得就比较详细了:
先是长安谣曰:“打麦麦打,三三三。”既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解者谓:“打麦者,打麦时也;麦打者,盖谓暗中突击也;三三三,谓六月三日也;舞了也,谓元衡之卒也。”自是京师大恐。
生于千载之下的我们不需多么费力就可看出,这首“元和小儿谣”是儿童游戏时念唱的歌谣,极富动感,词句也很简单,是真正意义上的“童”谣。但经其时“解者”一番曲说,竟变得如此复杂。由此足可见出“荧惑说”强悍而无所不至的影响力,它不止滋生预设的占验类童谣,而且横扫那些本来全无心机的童谣,生拉硬扯亦要为之覆盖一层神秘的面纱,将其与某些特定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对应起来,并尽量显出若合符节的效果。经如此一番曲折,历来书史中录童谣竟变得千人一面了,似乎全部和“荧惑”之说脱不了干系。童谣就这样被异化了。因于此,它也不幸而致成为传统儿童教育弃置不用的废料,长期以来静静地躺在“历史的垃圾箱”中,备受冷落。
三、童谣回转与王阳明的“童子之情”
童谣发展到宋代时,情况略略发生了些变化。郭茂倩辑《乐府诗集》收“杂歌谣辞”七卷,内有二卷基本全为童谣。这是历史上首次跨越朝代对童谣所作的大规模整理,也是童谣第一次脱掉“五行志”的帽子集中出现在人们面前。另外,《宋史》卷数虽为二十四史之冠,却仅载两首童谣,远远少于前后《汉书》、新旧《唐书》甚至《隋书》。郭茂倩辑《乐府诗集》则不涉当代。故两宋三百多年,流传下来的童谣并不太多。这恐怕与理学思潮不无关系。不过宋时童谣虽不再局限于“荧惑说”狭窄的天地当中,但大多仍与朝政有关,是民意的一种表达,与儿童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童谣并不多见,整体来说童谣面貌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特别到元代时,再经反复,童谣重新入驻“五行志”,在打了个转之后似乎一切又回到了原点。童谣真正的转变是在明清时完成的。
先说《明史》。在二十四史中,《明史》卷数仅次于《宋史》,童谣却只一首可见,而且该首童谣虽如前例录入“五行志”,却薄占验色彩。《明史·五行志三》云:
正统二年,京师旱,街巷小儿为土龙祷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来,还我土地。”
是为祈雨歌。
明地方志《帝京景物略》又云:
凡岁时不雨,家贴龙王神马于门,磁瓶插柳枝,挂门之旁。小儿塑泥龙,张纸旗,击鼓金,焚香各龙王庙,群歌曰:“青龙头,白龙尾,小儿求雨天欢喜。麦子麦子焦黄,起动起动龙王。大下小下,初一下到十八。摩诃萨。”
细述了祈雨仪式,且尚有续文:
初雨,小儿群喜而歌曰:“风来了,雨来了,禾场背了谷来了。”雨久,以白纸作妇人首,剪红绿纸衣之,以笤帚苗缚小帚,令携之,竿悬檐际,曰扫晴娘。
如果说上述几首童谣已然洋溢着童趣,但与儿童生活还不是那么近的话,下面这首童谣说的则全然是儿童自己的事:
杨柳儿活,抽陀螺。
杨柳儿青,放空钟。
杨柳儿死,踢毽子。
杨柳发芽儿,打拔儿。
童谣一口气列举了四种游戏,且都以“杨柳儿”开头,回环复沓,极易引起儿童吟唱的兴致。每个句子的两个分句又基本押韵,使得儿童念唱时更加顺口。可见不论是内容还是形式,这首童谣都是考虑到了儿童的特点,满足了儿童的需要的。
明人朱国祯撰笔记《涌幢小品》又有:
塘下戴,好种菜。
菜开花,好种茶。
茶结子,好种柿。
柿蒂乌,摘个大姑,摘个小姑。
是一首纯粹的文字游戏童谣,用的是“顶针续麻”辞格,目的在于训练儿童的语言和思维能力,而这种不求意思贯通的表现形式也很适合儿童跳脱的思维方式。
前此引用的几首童谣分别采自正史、方志及笔记,其共同趋向就是贴近儿童,走进儿童生活。这些童谣犹如一缕清新的风,吹入微微有些沉闷的传统童谣这“一面湖水”,激起点点微澜,然后渐渐扩散,直至波及到其整体生存方式。
此外,明人杨慎辑《古今风谣》二卷,并特为童谣辟出一块空间;吕坤则改编民间童谣而成《演小儿语》一卷。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
明时童谣展现出的新气象应该不是偶然为之,而是有其背后深刻的原因,尤与王阳明的“童子之情”一说密不可分。
正德十六年(1521),王阳明于江西南昌揭“致良知”之教(《王文成全书》卷三十三,《年谱二》),认为“良知”就是天理,而且“这良知人人皆有”,“众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完具此知”。(《全书》卷三,《传习录下》)既然相信人性自足,人人都有“良知”这“天植灵根”,那不止士农工商一律平等,孩童和成人亦当平起平坐。自王阳明始,传统儿童教育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王阳明认为儿童教育须顺应“童子之情”: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全书》卷二,《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这让我们想到朱熹。
在中国教育史上,朱熹可说是对儿童教育强调得多、研究得多、贡献也较大的一位教育家。他一生有大量关于儿童教育的言论,也编定撰写了不少童蒙读本,其中以《小学》和《童蒙须知》影响最大。分析朱熹的儿童教育思想,“拘检”恐怕正是极为突出的一个特色。虽然朱熹认识到,“天命非所以教小儿,教小儿只说个义理大概,只眼前事或以洒扫应对之类作段子亦可”(《朱子语类》卷七),《童蒙须知》也确是从“眼前事”入手,对儿童日常生活言行作出规定,但其要求的细琐刻板在一定程度上却与儿童的天性相背,基本是做不到“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的。而《小学》所收格言、故事虽然也尽量做到了通俗易懂,但通观其内容,说教色彩依然甚浓,对幼儿来说是比较沉重的。
王阳明则不同,他反对把孩子当小大人,指出儿童教育应依循儿童性情,顺应其年龄和身心特点。由此出发,他提出栽培涵养儿童当“诱之歌诗”,“导之习礼”,“讽之读书”。如果说朱熹提倡通过格言、故事向儿童灌输道德观念,通过须知、学则训练儿童的行为规范是板起脸来说话的,王阳明则要随和得多。从亲缘关系论,“歌诗”与童谣可说相当的近。这种儿童教育观念深刻影响了与他同时代及之后的人。
这里重点说说吕坤。嘉靖三十七年(1558)秋,吕坤之父吕得胜撰成《小儿语》上下二卷,以为训蒙之用。是书为自作格言,旨在使童子于“欢呼戏笑之间”,体认“义理身心之学”。后又以该书为未备,命吕坤续作之。吕坤承袭《小儿语》一书体例,作《续小儿语》三卷。难得的是他又别出心裁,借小儿原语演成一卷书,名曰《演小儿语》。所谓“小儿原语”,即童谣也。吕得胜在《小儿语》书前写道:
儿之有知能言也,皆有歌谣以遂其乐,群相习,代相传,不知作者所自。如梁宋间“盘脚盘”、“东屋点灯西屋明”之类,学焉而与童子无补。
万历二十一年(1593),吕坤写了篇“书后”,道其父子编书始末:
小儿皆有语,语皆成章,然无谓。先君谓无谓也,更之;又谓所更之未备也,命余续之,既成刻矣;余又借小儿原语而演之。
由此可知,《演小儿语》是由童谣改编而成。
吕得胜虽然认为“群相习,代相传”的童谣鄙俚可笑,“学焉而与童子无补”,但已经认识到要让儿童在“欢呼戏笑之间”,体认所谓的“义理身心之学”,还是很有见地的。吕坤则更进了一步,看到了童谣的价值所在,从而略略加以改造,就成了现成的训蒙用书。在《社学要略》中他又提出:
每日遇童子倦怠懒散之时,歌诗一章。择古今极浅,极切,极痛快,极感发,极关系者,集为一书,令之歌咏,与之讲说,责之体认。……至于汉魏以来乐府古诗,近世教民俗语,凡切于纲常伦理道义身心者,日讲一章。
可以极清晰看出受王阳明影响的痕迹。而“近世教民俗语”,则大致不出童谣、谚语之属。
也是在万历年间,在吕坤写成《演小儿语·书后》之前的1590年,李贽的《焚书》刻成。他对“童心”倍加推崇:“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李贽指出,读书固然可以多识义理,开阔闻见,但教育更重要的目的是“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焚书·童心说》)这比王阳明的正视“童子之情”又进了一步。
与李贽私交甚笃的袁宏道曾说:
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劈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袁中郎全集·叙小修诗》)
可以看出,王阳明之后,儿童和儿童歌谣在文人眼里的地位在逐渐走高,而且和“荧惑说”绝无干系。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切入点。
中国传统儿童观由奇异的两面组成:一面是把儿童当作小大人;另一面则视其为不完整的存在,是成人的附庸。这种儿童观直接影响到儿童教育观。周作人就曾指出:
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5]
这种观念也生动映照在童谣与“荧惑说”两千年来纠缠不休的历史中。因为将儿童当作小大人对待,故在儿童教育中也倾向于采用成人的话语方式,天真稚气的童谣成了弃而不用之物。另一方面,在儿童教育世界中无立足之地的童谣并未就此枯萎,在政治生活中,它反而得到了分外蓬勃的生长。而“荧惑说”钻的,正是传统儿童观的另一个空子。幼童的无知无虑,成为心有城府的成人最方便利用的一点。
儿童教育发展到宋明时,经朱熹的大力提倡,到王阳明的“拨乱反正”,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开始逐步走出那奇异的双面组合,向“童子之情”靠近。与此同时,童谣也挣脱了“荧惑说”这层枷锁,展露出它原本的清新面孔。故此,传统童谣由被困于“荧惑说”到向“童子之情”的回归,恰好清晰地反映了传统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变化的历史。
四、余论
童谣在明代虽踏上了回归之旅,但其发展却并非就此顺风顺水。清中前期,童谣一度又变得比较沉寂,这恐怕与清廷的高压政策不无关系。《大清律例》规定:
凡有狂妄之徒因事造言,捏成歌曲,沿街唱和,及以鄙俚亵嫚之词刊刻传播者,内外各地方官即时察拿,坐以不应重罪。若系妖言惑众,仍照律科断。
童谣俨然在被禁之列。且清代自顺治、康熙始,即再次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康熙赞朱熹为“继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皇朝文献通考》卷二百二十五)从另一层面来说,似有冲决网罗之势的“王学”必然会受到抑制。牵连而及,童谣也再次被冷落了。
不过历史毕竟在滚滚而前,沉寂并不代表消亡,到清代后期,真正意义上的童谣集骤然间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积淀了两百多年,这一次童谣真的“回家”了。
同治八年(1869),浙江书局印钱塘郑旭旦辑《天籁集》及山阴悟痴生辑《广天籁集》。两书所辑,多是江浙一带童谣,基本不离儿童日常生活所见所闻,也有不少仅仅是随韵粘合,还有一些则取滑稽戏谑之意。光绪四年(1878),范寅著成《越谚》,主要记录当时越地方言,兼及民歌童谣。范寅与周作人舅父有旧,周作人幼时常听到有关他的逸事。据说范寅编《越谚》时,常常召集近地的小孩唱歌给他听,以糖果为酬[6],可见该书所收童谣是完全依照口头传唱写下来的。1896年,意大利人韦大利(B.G.Vitale)编《北京儿歌》出版,内有中英文对照的童谣一百七十首。此外,清代后期还曾出现无名氏编《北京儿歌》,收录乾隆至光绪年间流传的儿歌。1900年,美国传教士何德兰(T.Headland)编《孺子歌图》在纽约出版,收录了北京地区儿歌一百三十八首,并配有大量与儿歌内容相近的图片,非常难得。
清代后期童谣回归首先是明代传统的延续。宋明时,“荧惑说”在童谣领域渐行消退,王阳明的儿童教育观更为传统童谣开了一扇转向“童子之情”的窗口。这为清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次,在“西学东渐”浪潮的影响下,清后期儿童教育踏入了近代的门槛,这对童谣的回归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1904年颁布的《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要求,在幼儿五六岁“渐有心喜歌唱之际,可使歌平和浅易之小诗,如古人短歌谣及古人五言绝句皆可,并可使幼儿之耳目喉舌运用舒畅,以助其发育,且使心情和悦为德性涵养之质”。并提出在幼儿集体游戏中,可“使合唱歌谣,以节其进退”,“要在使其心情愉快活泼,身体健适安全,且养成儿童爱众乐群之气习”。《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又将古诗歌列入功课,规定“须择古歌谣及古人五言绝句之理正词婉,能感发人者……遇闲暇放学时即令其吟诵,以养其性情,且舒其肺气”。
在西方教育观念的冲击下,“癸卯学制”的拟订者在竭力从传统教育资源中找寻可以与之相契合的部分。王阳明和吕坤均提倡儿童“歌诗”教育,与西方的“唱歌音乐”若相符合,故可师其意而将“古诗歌”列入功课。在“童子之情”说问世三百多年后,“歌诗”正式写入了中国近代第一个颁布并获实施的学制系统。颇为难得的是,《章程》在明确“古诗歌”功课的学习内容和要求时,不曾忘记歌谣,童谣也终于堂而皇之成为了中小学堂功课的一部分。
自“檿弧箕服,实亡周国”诞生起,伴随着传统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的沧桑变迁,童谣在跋涉了近三千年之后,至此似是走出了严格计算苦心经营的怪圈,恢复了它原本应有的模样。不过颇耐人寻味的是,童谣在艰难走出与儿童离异的悖论后,发挥的教育影响却依旧十分有限。
1919年,中原书局重印《天籁集》和《广天籁集》,并附“序”曰:
《天籁集》一卷,钱塘郑旭旦辑;《广天籁集》一卷,山阴悟痴生辑。这两部书,都是豆腐干式的小册子,清同治八年浙江书局初印本,竹纸铅字,字迹都很清楚,但这书在十年以来,是早已绝迹于坊间的了。有没有再版,也不得而知。
《重印〈天籁集〉序》作者又回忆说:
记得二十年前,那时我至多不过八九岁罢,正在家塾里念《孝经》。晚上散了学,坐在天井里乘凉的时候,有一大丫鬟名巧儿的常常教我唱什么“萤火虫,夜夜红”之类的小歌,我也自然很高兴。巧儿会唱的歌很多,不止十几只,因此我常想世界上学问最深的人,除掉教我《孝经》的老师以外,大约就要算巧儿了罢。
作者未留姓名,以时间推论,当是19世纪90年代生人。这段材料从一个侧面说明,即令时光已届清末,童谣往往还是只能活在不起眼的小人物的记忆里,经由她们不经意的传唱,或能为儿童乏味的教育生活零敲碎打增添一点兴味。可见即便是在“童子之情”进入人们的考量范围之后,传统儿童教育依然不曾真正走出“重教轻养”的藩篱。自此看来,传统儿童观的“深入人心”致使传统儿童教育具有一种别样的执拗性,要彻底扳转非朝夕之功可蹴。这也正是历史留给新文化运动时期关注儿童教育的学人们的课题。
注释:
①据杨伯峻考证,《左传》成书在公元前403年之后,公元前389年以前。而王树民、沈长云则通过分析《国语》所叙事件推断其当作于晋亡之后,亦即公元前376年后。《国语》成书在《左传》之后。检先秦典籍,《尚书》《诗经》《周易》甚至《论语》都未见童谣,则以《左传》载童谣为最早见于文字者。
